传媒教育网
标题: 伦理学理论案例集锦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6:23
标题: 伦理学理论案例集锦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来自哲学学科知识的支持。新闻伦理是新闻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闻伦理需要从伦理学基础知识中获得给养。这里,我们乐于将发现的伦理学基础知识逐渐汇集起来,供新闻学的师生参考。
【案例】
伦理社会主义
伦理社会主义是指用康德伦理思想修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创始人为德国柯亨,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同新康德主义者那托尔卜、沃尔伦德尔、什塔姆列尔、卡西勒等人。把康德誉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将康德的绝对命令你应该这样行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对你自己或别人,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决不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责备马克思只看重经济、而忽视道德对社会的影响。 [1]
认为有必要用“道德唯心主义”取代“经济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永远达不到的理想。认为社会主义“从来不可能是事物它仅仅意味着“无限地趋向纯粹意志”。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在第二国际的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中曾出现一股康德热,“固到康德去”成了时髦的口号。他们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结合起来,认为康德的伦理学可以成为消除阶级冲突和使社会团结的“社会教育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7%90%86%E7%A4%BE%E4%BC%9A%E4%B8%BB%E4%B9%89/14710138?fr=aladdin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6:29
【案例】
境遇主义主张伦理方法的性质就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道德决断,以具体的境遇和实际经验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境遇主义者可以说是人的机遇和新理念,有机遇才有理念。在这的意思是人的思维在选择事物的观点时候应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观察,人的观点不同带来的思维和意境。也可以说你遇到事情以什么方式去解决如何看待。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40246967.html
四、境遇主义的哲学
不管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他们事实上都是把他们的哲学结论看成是对象的真理,虽然一个是关于物质的,而另一个是关于神的。思想的对象化极大地扩展了我们思想的空间,但也就是这个对象化使得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的思想就是表征了对象本身的逻辑。而且更进一步的是,人们以为,我们认识的所谓的客观是与我们无关的。我们的对象是与我们无关,但我们思想中的对象却是与我们高度相关的。正是这种相关,使得我们的无神论者最后却成了造神运动的对象,也使得唯心主义者很多最后都变成了听天由命的羔羊。
从根本上看,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哲学,他们的根基都其实是建立在面向理想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面向理想的哲学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常常发生的的教条主义的缺点也暴露了这种哲学的重大缺陷。辩证法是提供了一种变通,但这种变通,却并不足以支撑在骨子了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这个理论大厦的倾斜。
人类是在克服一个个具体的困难中前进的。从面对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问题之外去寻找我们问题的答案。这样一来,思想作为境遇直接的结果就显得很自然了。我觉得,这种境遇主义的哲学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五、境遇主义哲学的真理观
我估计,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完全不对的。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真理看成是客观。而实践的真理观则显然不是这样。实践就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互动。这就是说,实践的真理观其实是建立在境遇主义的哲学的基础上的。离开了具体的环境和主体的境遇,对我们来说,真理就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人类从来没有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有兴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cda5e0100dvzb.htm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6:40
【案例】
作者:心理学网络学堂
链接:http://www.vccoo.com/v/8sh900
来源:微口网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内卷化概念与理论
内卷化(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本义为“缠绕、内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先使用in-volutionstheorie这一概念,邓晓芒译为“退行论”。康德将存在物的衍生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离析出来的,一种是产生出来的;前者叫做“个体的预成学说”,后者也可以称之为“种类的预成学说”,因其形式被潜在预先形成,亦可叫“套入理论”或“原形先蕴说”。在康德这里,“退行”是与“进化”相对的一种事物演进方式。
颇为有趣的是,现代英语中表达事物运动状态的有一组以“-volution”为后缀的单词,其中主要的4个被学者用来表示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4种模式: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进化),devolution(衰退),involution(内卷)。其中,革命是一种突然间断的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进化是一种连续增进的过程;衰退是一种堕落恶化;内卷则是事物内部一种细致、固守、停滞的变化过程。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纳入学术术语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他用该概念来指社会或文化形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难以突破或转化,只有通过使内部更加的复杂化而继续下去。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从戈登威泽那里借来该词并用“经济/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来概括印度尼西亚爪哇社会的水稻生产。他观察到爪哇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但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而是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
爪哇农业几百年停滞不前。格尔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持续30余年的多个国家学者的学术争论。他使“内卷化”成为“社会科学教材中的一个标准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非进化的”(non-evolutionary)或“非革命的”(non-revolutionary)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内卷”如影随形的是“共同贫困”(sharedpoverty)一词。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工具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始于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中,他指出,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农村存在着农业内卷化(即劳动密集化带来的单个劳动日报酬递减与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世以来还存在着“过密型商品化”。
在为中外纺织厂生产棉花和蚕茧的家庭副业中,大批被排斥于劳动市场之外的劳动力,只要净收入大于零,他们可以远低于市场报酬的劳动力承受高度的劳动密集化。这正是自明代中期以来农民小生产不仅没有向大生产转化,相反原有的大生产却被农民小生产取代的原因。
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商品化与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而是加强了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农村经济仍然沿循着家庭化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并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
黄宗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其著作在汉学家及华人学者中旋即掀起了一场学术争鸣。论争双方的分歧之处既有不同的史实,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同理解,最终也没有形成共识。黄近年的文章进一步指出,经过了近30年的工业发展及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过密的现实,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
将内卷化的研究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的是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他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国家权力的现代化扩张有其自身的特点,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无政府状态同时发生,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其原因在于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力量长期处在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
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济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经纪层的社会利益使之成为体制改革的障碍。所以,在内卷化的政权之中,经纪体制不是趋于灭亡,而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具有极大的腐蚀和使政权非法化的反作用。杜赞奇认为这是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研究之后,国内大量学者从“内卷化”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来透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大体看来,学者们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3个方面:
(1)乡村社会。内卷化中国研究的传统是关于乡村社会的,涉及乡村治理、农业经济、劳动力转移、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内卷化”分析。其中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是重点。贺雪峰的研究表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出现了多元行动主体,一方面,国家投入乡村的大量资源被吞噬,一个越来越肥厚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开始长成;另一方面,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因此被破坏掉。农民落单成为一盘散沙,农民缺少了力量感,丧失了正义感和是非观,国家失去了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的力量。张小军以阳村为个案从“农业内卷化”“国家内卷化”“文化内卷化”等角度来思考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的内卷化作用机制。
(2)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与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分析。借用这一概念,学者们指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游离状态下,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城市,因而出现农民工在社会体制、阶层流动、社会行为、身份认同等方面内卷化的特点。
(3)政治、组织、制度的内卷化分析。王绍光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家政治内卷化状况也呈现出一系列悖论的状况,类似于1949年以前。Dittmer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在更为理性的、非个人的形式,如组织的流线型、能人的招募等,被强制实施并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的时候,组织内部发达的个人关系网也同时壮大。组织内卷化的坚韧可以用一句流行语来表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行为特征表现在:对于既得利益的苦心经营,占支配地位的非正式关系(如党派主义、关系),以及潜规则的增殖。潜规则从没有成为正式法典但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国内学者也讨论我国制度创新的内卷化问题,行政体制内卷化倾向表现。
其他研究相对零散,涉及国有企业、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新失业群体、家庭两性乃至街角青年等等,不再赘述。“内卷化”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式,被广泛地用于宏观、中观、微观乃至更为具体的各种存在的描述与分析。
二、“内卷化”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从学者们的使用来看,“内卷化”一词的“意指”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的停滞状态,经济效益的递减,(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困境,制度与体制的逐步失效与失控,以及潜规则的盛行等。“内卷化”是与“进化”(evolution)相比照而言的。
“进化”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事物能够线性地发展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完成样态上的变化。就西方社会的发展实际来看,Dittmer指出,“进化”模式是符合现代化的范式,它有助于理性化、个体化、商业化。而“内卷”模式则是一个事物原有特征的延续与扩散,愈趋复杂,愈难以超越自身。
(一)“内卷”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
社会体系或制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进而在内部形成一个密集坚实的社会文化“内核”,在外部则形成一个难以突破的刚性“外壳”。
这种跨时空的维护往往在专制权威统治的社会中才得以实现。在权力操控下,自我复制成为一种机制,进而在社会不同层面、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一系列相关特征和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就是一种结构的复制。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分析“后喻文化”时曾分析过这种复制机制,由于崇尚权威,缺乏想象,一个事物会在其它所有事物的方式上被引为成例,从而得到“加强、回忆和反射”,“任何一部分文化行为经过分析后,都能找到同样的潜在模式”或“变体模式”。这就是自我复制的作用方式。
从时间过程来看,这种社会变化迟缓、陈陈相因,是一种“未来重复过去”的文化。生活与生命在代际之间复制,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一代的未来,孩子是长者身体和精神的后代。吴予敏曾指出,中国传统的传承结构是一种“偏心圆”结构,即被作为传统经典在时间维度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内“核”,新的经验和观念几乎是在全盘继承了旧的文化以后衍生(而不是分化)出来的。
整个历史性的传播活动,犹如在按照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虽然渐行渐远,但却宿命性地不能彻底离开“核心”,层层叠加,于是内部也变得日趋复杂,沉重不堪。因此,从个体层面上看,内卷化是生命的代际复制。从社会层面上看,内卷化是历史的不断重演。
“内卷化”在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型构方式,造就的是一个保持着整体性与复制性的系统。所以,尽管中国历史悠久,也非常重史,但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历史”是不错的,它实际上是说“中国社会的制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自我复制即内卷”。
梁漱溟也说过:“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的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这是对中国社会内卷化发展状况的准确表述。当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过去的权威时,“过去”就整合和同化了未来。
(二)“内卷化”的社会充满悖论
悖论是内卷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黄宗智近年来不断地用新的“悖论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现象,如“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的兴起,表达性实践与客观性实践”;此外还有学者概括出“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等,可以说,这些只是悖论现象,从本质上说,内卷化的社会必然充斥着悖论。
悖论的产生盖源于文化本身的有限性与时空(现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伸,但文化在时间上延续时会遇到不适应,在空间延伸时也会变得不适合。
伊尼斯指出,文化在时间上的局限,盖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盖源于它不能把思想资源用来避免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对内卷的文化来说,它本无意调动民族的思想资源,更无意于避免停滞,维护专制权威才是目的。然而,这种自我维系会遭遇具体时空的挑战,并产生诸多悖论现象。
费老对中国社会“名与实”的分析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悖论的产生。中国社会自从定于一尊之后,社会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谋求与现实变化适应。“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权威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其形式,实际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对于不能反对的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而所谓的“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已被歪曲。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于是,名与实、位与权、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名与实的分离可谓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大的劣根性之一: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潜规则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一套做一套,事情越是禁止,它就越难禁止……凭借威权或惯性进行的自我维系与推行会遭遇实际问题,但权威及其体制又是不可反抗的,这是悖论产生的根源。
这种悖论同样会按照自我复制的逻辑进行扩散。王毅曾指出,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多局限于诗书礼乐经典等正统形态,传统文化体系中“流氓性”受到崇拜与神话却多被人忽略不知。
在详实的文献基础上,他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有力地说明,16世纪国家权力的流氓化直接导致了国民伦理的流氓化。在专制威权和流氓文化的合力塑造下,为了在严酷社会的缝隙中生存攫利而不顾任何道义和不择任何手段的国民心理及伦理向着“反文化”的方向蜕变。
它甚至塑造出一种“悖论”型人格,孟德斯鸠曾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贸易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
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品质却结合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格”。其原因就在于,在不存在争取权利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就只能越来越从“反文化”的路径中获得代偿性的满足。当不合理的制度设置剥夺了国民本应享有的公正权利,那么结果就必然是受到不公正制度伤害的人们“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弄虚作假”。
(三)内卷是一种熵增过程
熵(Entropy),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被爱因斯坦赞誉为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该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中一切实际过程是向着熵增加的方向进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在整个宇宙中,一种物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之后,不仅不可逆转物质形态,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能量退化,无序度的增加。熵定律经过美国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熵》,以及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作品而被赋予社会学意义。
内卷化的社会无疑是一个熵增的社会。一个封闭的、奉行专制权威的社会系统,充满了过时的体制与观念,充斥着各种悖论逻辑,传统文化与体制的能量不断退化,变得不再适用甚至无效,无序与内耗使一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当一位记者询问缘某局何未按国务院规定放假时,其工作人员竟称:“国务院?好遥远啊!”如果说“鞭长莫及”现象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还有其现实基础、因而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21世纪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政令难以通达则不得不反思我们社会的深层问题。
悖论现象,就是一种社会之“熵”,无序、耗散、低效或无效。当今我们社会和生活中遍布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欺诈和暴力,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相当普遍,“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这种“社会溃败”——社会机体细胞的坏死、机能失效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的威胁。
三、过密型市场:山寨机中的小农经济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封闭的状态,为中国社会走出“内卷化”的怪圈打开了一条正确之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保守的小农经济。然而通过对各行业市场的考察可以发现,不仅小农经济可能存在于农业内卷化和“过密型”商品化(黄宗智语),城市化工业化的市场发展中也会存在内卷化(过密化)问题。这也是一种悖论。山寨现象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市场内卷化的表现。
山寨机在中国曾风光一时,它是山寨风现象的主角,其兴起和没落的历程可谓是“市场内卷化”的一个典型注脚。山寨手机的兴起始于2006年台湾联发科的芯片商开发出的一个被称为“交钥匙方案”的廉价的MTK手机芯片,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让手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只需要购买一些简单零部件就可以出品手机。山寨机市场具有以下“内卷化”的特征:
1.复制与仿冒。山寨,是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复制是山寨的灵魂,也是内卷的核心品质。山寨机主要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设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iphone等畅销品牌,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高仿机,所谓的A货,不仅外观极其相似,功能也接近。
2.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由于低成本,依靠的是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尤其是充分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山寨机价格极有竞争力。深圳的电子市场,山寨机“几乎就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卖”。
3.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山寨机的生产,基本上是规模大小不一的“小作坊”式的组装厂。一间房,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上千部手机。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应用联发科方案的手机生产商只需要3个人——一人接洽联发科,一人找代工工厂,一人负责销售和收款”,这种小作坊性质的生产方式,与现代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大相径庭。它们多逃避政府管理,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不会作开创性投资,更不会作研发,不会花钱研发产品,更不需要广告、促销等费用。
4.非正规经济。由于具有偷税漏税、避开政府管理的行为特点,也涉及知识产权的敏感问题,山寨机市场从业者常常与管理机构打游击、躲猫猫。一听到“工商来了”的喊声,整个数码商城就会“慌成一团,售货员手忙脚乱地掩藏和转移山寨机”,甚至出现了“天上掉手机”的怪事。
5.过密化投入与边际效益暴跌。山寨的“复制”是双重的,一是指对名牌的模仿,一是指对模仿本身的复制。零门槛使大量资金涌入到了手机生产行列,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数量喷涌到数以千家,市场空间趋于过密化,竞争极为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发,利润10元一部也卖”,边际效益随着投入的时间和劳动的增加而减少,甚至难以为继。
6.市场的癌化(“热寂”)。山寨是一种简单而疯狂的复制,它不是为了占领市场——这需要质量和牌子,而是争着抢先把市场利润“吃一遍”,因而是一种自杀式的进攻模式。
在分析商品内卷化时,黄宗智曾指出,由于拥有低过市场标准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家庭经营式农业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商人用包买制,付出生存需要以下的工资,而与现代棉纺工业相抗衡。在此过程中,原来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剩余,停滞在商业资本周转的阶段。而原来可能成为新式织布工厂的市场,则被廉价手工织布所控制。”山寨机对于产业发展的危害类此。
这些手机小作坊以其低成本、低价格严重地打击了民族手机品牌,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2007年全部亏损,其中“波导”公司亏损5亿多元,“夏新”公司更是亏损6亿多元。民族手机产业全面沦陷,一个个企业悲惨退出了市场,国内主要手机市场几乎成为国外手机品牌的一统天下。
山寨机虽然“成功”地挤垮了国内的一些品牌手机大企业,但它在城市的命运更短,在过密化的市场中,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2011年以后,山寨市场急剧萎缩,风光不再,在耗尽可怜的有限资源后,市场也随之覆灭。随着国外品牌的侵入以及带来的市场品味提升,山寨机全线撤退,转移到西部三线四线市场。
市场的本性是开放与开拓,商品经济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进而形成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单调复制与大量投入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机是当代版的“经济内卷化”,或者说是市场版的“农业内卷化”。
不仅手机行业,国内许多行业产业都存在这种过密化的局面。其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或变革劳动组织形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简单而大量的、复制性密集投入。笔者曾访谈过深圳的一些中小企业家,他们慨叹在中国生意太难做——“一个行业如果挣钱,不出几个月,市场上很快涌现千军万马”的同类行业。空间内相同劳动的超密度投入,最终带来的是市场空间过密性拥挤,经济效益微薄且边际效益递减。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资源密集兼劳动密集,这使得当代中国经济难以有效增长,亦难以积累起发展所需的技术与人才,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遭遇瓶颈。复制式的中国制造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永远不可能跑到未来的新大陆。
此外,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半边缘地位,世界垂直化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置,以及长期代加工和山寨经济形成的依附性发展,这些更进一步形成中国产业发展难以向外突破的刚性边界,从而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锁入效应”(Lock-inEffect)。江涌指出,
“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这是一种对外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与国际资本,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其结果就是,虽有“量的增长”但遭遇“质的停滞”。这是当今经济发展内卷化的内外两股夹击力量。
四、内卷化人格与文化心理
山寨现象引起的争论至今仍未消退,山寨心理更是普遍。“过密化”(“山寨模式”是过密化的现代翻版与典型表现)的产生固然有制度、内外环境等的原因,但毋庸置疑也与我们已有的文化心理关系很大。文化与人格水乳交融,荣格曾说,一切的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指出,“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放大”。我用“内卷人格/心理”(psychologicalInvolution)一词来指我们文化中的、与“过密型”市场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文化心理与人格特征。
(一)缺乏原创和创业品质,喜欢模仿强者和跟风市场
韦伯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中国人的性格,他认为中国人的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却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和复制资本主义的做法。他这样写道:“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但韦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模仿复制能力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曾经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
一个犹太人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意很好,然后第二犹太人来了开了一个加油站,第三个犹太人就开了一个超市,这片很快就繁华了;而一个中国人也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意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中国人也在那里开了第二个餐馆,第三个、第四个中国人同样也开了餐馆,结果恶性竞争,大家都歇菜了。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100多年前,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薛福成就慨叹“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中最突出的是这样两条:“一则抢揽生意。华人创一业,稍沾微利,则必有人学步后尘,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一在搀杂诈伪……于丝中掺麻,或新丝中搀旧丝,或细丝中搀粗丝。茶则搀以柳叶,或杂以泡过茶叶,其颜色则多用装点。西人不过受欺一次,后不再来,即真货亦致滞销,皆弄巧成拙阶之厉也。”
市场经济需要差异化地开发出市场和劳动分工,而中国人却缺乏这种思维和意识。一位靠三来一补起家、已经具有自主的国际品牌和外销市场的企业家面对着“倒逼”的转型压力,最担心的居然是同行超强的复制能力,他说:“我们的一些动漫玩具出街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被人模仿,而且价格要便宜很多。我们内外销的产品材料一样,工序一样,还有专利。
但与他们相比,即便压缩管理成本,我们也没有价格优势。”西方700多年前但丁就喊出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人文主义口号,可即使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却还在打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算盘,薛福成在100多年前所引以为憾的民族性,至今仍然是妨碍商务振兴的原因。
(二)缺乏创造、徒以模仿为能实是缺乏主体性和主体意识的表现
这与千年来的专制社会及对个性的压抑有关。个人的社会安全感、尊严和独立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而压抑,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文化精神开始“内卷化”了。伴随文化心理的“内卷化”是中国经济创造精神消退。
没有主体性的人当然缺乏工作和创造的热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生活传教20余年,最后于1894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素质》(又译作《支那人气质》)。这是一本鲁迅先生很认真看重的、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的书,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让人警醒,值得我们“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鲁迅语)。
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明恩溥的体会是深入的:“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指中国人)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我们)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主体性、内源性的创造激情。
(三)零和思维
零和思维是一种狭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认为“非赢即输”、“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于是“抢着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这会导致一种伤害别人利益的非合作心理。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会把关注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关注自身;因而会试图打压别人,而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看重“超过别人”甚于事物的自身价值,在意排名甚于业绩,在乎别人的看法甚于自己的真正实力。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缺乏主体性的人格。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也同时缺乏外向型的思维,眼光只是在圈子内部打转转。而外向的思维则会发展出双赢、多赢的合作性关系和心理。大前研一曾警告日本公司不要内部疯狂竞争,其结果是使大家蓄势待发以杀价求售,最终,低成本游戏做不出高价位产品,如果想走出自己的路,就应远离自家人争斗的圈子。内部争斗的思维根源是内卷文化中零和思维,眼界和思路都被限定在封闭有限的内部圈子,在全球化时代,其文化会愈加萎缩贫瘠,缺乏创造力和辐射力。
(四)悖论的心态和人格
前文对此已有论述。这也是一种异化:经劳动的双手产生出来的制造物,不再是人的智慧、人格的外化和力量的体现,不再是自我的象征,而是通过仿制他人来削弱他人并牟利的工具,因而产品粗制滥造和质量低下。进而在一种既不尊重他人(及其劳动)、亦无法自尊(即自卑)的心理下,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无法形成发展出成熟的理性和受人尊重的完整人格。
所以,明恩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需甚少。只需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称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五)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感,社会信任度较低
缺乏信任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痼疾。韦伯和明恩溥都在他们的书中分析过中国人“对别人普遍不信任”及其原因,但发展演变成为信任危机却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过密化心理导致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大量产生,每个行业“内幕”“黑幕”重重——以至于无论什么行业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个“内幕”在,不再相信表面被呈现出的现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对于群体来说,信任缺乏将会是一个很难走出的真正困境。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低。反之亦然。社会信任度低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认同出现问题。社会诚信的缺失还会毁掉世界对我们民族的信任和尊重。
五、结论及讨论
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技术的变迁速率较快,制度其次,文化心理更次之。改革开放即将走过35个年头,可今天我们的身上仍然盘旋着百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小农经济时代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这是最为深刻而内化的“内卷”。
英格尔斯曾指出:一个国家或企业即使有先进的制度和技术,但若缺乏能赋予这些制度和技术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未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会导致制度和技术的畸形发展甚至失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丛生,研其原因,不可忽视这些文化心理积淀的负面作用。百年前鲁迅们所呼吁的改造国民性,至今仍然任重道远。
文化以人格作为自己的结果,也以人格作为自己的起点。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化强国必须致力于发展国民的现代性人格。人格的内卷源自体制的压抑,梁启超曾总结的国民生存定律:“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
而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创造性都来自理性而有自我效能感的国民:“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乏活力,那是它为机器可以更加顺利地工作而加以扼杀的。”
马尔库塞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人。而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一直都缺乏那种超越的向度。
超越性需要真正尊重人的教育。教育的真谛在于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并形成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但一直到现在,我们教育的“灌输”色彩都还没有多大改观。标准教材、标准试题、标准答案,将学生的思维和心智禁锢限制,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也无法追随自己的发展想法,这是一种没有“确立自我”、不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教育,只能产生缺乏创造力、具有零和思维的内卷人格。
本文摘自2013年9月《深圳大学学报》第30卷第5期 图片选自黎建东摄影
http://www.vccoo.com/v/8sh900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7:01
【案例】
一、什么是伦理相对主义和伦理绝对主义
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是伴随整个人类伦理思想史发展的 两个重要的致思取向。宽泛地说,伦理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也称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 ,它认为道 德只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民族、文化或时代,道德规范、道德原 则以及道德体系总是暂时的、不确定的、有限的、缺乏普遍性的, 不存在普遍有效和永恒不变的道德。与伦理相对主义正相对立的伦 理绝对主义(ethical absolutism)又被称为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一般而言,这两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互换使用;也有 学者认为两者间存在细微差别。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之间 �的关系也是如此。
伦理绝对主义通常认为存在着绝对的、普适于 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些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于任何 时代、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人都同等适用,它是永恒不变 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不仅伦理相对主义呈现出一个历史的发展过 程,而且伦理绝对主义也呈现出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西方伦 理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伦理绝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上呈现出相互更替、此起彼伏的特征,在同一历史时期则相 互交织在一起。就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伦理相对主义在 古希腊罗马时期处于萌芽阶段,中世纪时期,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 基督教神学伦理更是占据支配、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初 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破除基督教神学伦理体系的同时竭力为新的 社会建构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伦理体系,它们的思想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绝对主义倾向,伦理相对主义的倾向还不明显;到现当代时 期, 伦理相对主义茁壮成长, 在一定时期内一度压倒伦理绝对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对普世伦理的追求也是伦理绝对主 义的表现。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既在同一历史时期相互交 织,又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相互更替。 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来看,西方伦理思想既表现出明显的相对主义 倾向,也蕴含着一定的绝对主义因素;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 义发展的历史脉络较为清晰。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主要单一地 �呈现出了浓厚的伦理绝对主义色彩。
究竟什么是伦理相对主义?什么是伦理绝对主义?本文没有给出 严格的界定。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对一个概念给予 形式逻辑的静态的界定往往不利于我们把握一个具有漫长发展历 史的思想对象,也就是说,由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伦理相对主 义”和“伦理绝对主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经历了不同形态的历 史演变,因而我们只能在伦理思想史的历史追溯中才能对其予以动 态的把握。另一方面,对“伦理相对主义”和“伦理绝对主义”的 界定有赖于哲学层面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概念;而哲 学层面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概念本身也是宽泛的、模糊 的,需要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运动的追踪才能加以辩证地把握。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 ... e468b600000b0e&p1=1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7:06
【案例】
“道德虚无主义”即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本质上是道德或不道德的,其主张认为道德来自于构建。
道德虚无主义是小于道德虚无主义者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因为自己在生命过程中间受到某些创伤而产生一个启发性的信仰——世界是没有什么拯救的,然后进而将被造的相对的绝对性绝对化这个信念后就产生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理论系统。这种系统常常找不到道德的真正支持性力量,但因为信念与系统的独特,所以常常自己在很可怜的状况中间也常常很骄傲。
反社会人格是跟道德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虚无主义不同于道德至上主义(
Moral Absolutism),也不同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它彻底否认事物
有对错、善恶之分,既不肯定道德规范,也不予以否定。总而言之,道德虚无主义者生
活在一个与道德无关的世界,他们通过消解社会规范来为达到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目的。
道德虚无主义最强烈的倾向就是,它有一个终极目的,这个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
经济的,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群体的,但无论如何,其实现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最
明显的表征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亨廷顿和他的追随者将其归结为不同文明的冲突,传统
的西方伦理学则试图证明,道德虚无主义是无神论的终极后果。本文则认为,至少就国
内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反社会人格来看,道德虚无主义有其发生学上的复杂原因。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555658.htm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8-9-25 17:10
【案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这一章主要批判杜林关于“根本不变”的永恒真理和永恒道德的谬论,阐述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和道德的历史性、阶级性。
(一)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论,论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第81页一第90页第1段)
杜林认为,人的认识可以不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个人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胡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吹嘘自己在道德和法方面的理论就是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终极真理”;他把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绝对化,并且硬要人们接受那种“根本不变”的永恒真理,谁要有所怀疑,他就大加污蔑。恩格斯驳斥了杜林的这些谬论,深刻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1)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论述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批判杜林关于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意义的荒谬观点。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4页)思维,作为整个人类的思维,就其无限发展的本性来说,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至上的,是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一切联系的;在社会实践中,思维的使命就是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只要人类无限地延续下去,思维就有可能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联系,从而无限地接近绝对真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认识的。但是,人类思维是由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人思维构成的。个人的思维由予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非至上的,所认识的真理总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它只是部分地包含着绝对真理。
所以,“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第83页)这就是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解决。杜林把自己打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似乎他的思维就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2)从思维成果方面,进一步论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揭露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的谬论及其反动实质。恩格斯曾经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也就是说,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任何真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真理与其所反映的对象相符合是推翻不了的,因而是绝对的。但是,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在绝对真理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对事物的各个具体过程的认识又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的。在人类认识过程中,杜林所宣扬的那种“根本不变”的“终极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了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谬论,恩格斯概述了关于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发展状况,列举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大量事实,着重说明,在社会实践中,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每个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客观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因而总是有限的、具体的、相对的。特别是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更糟。因为社会现象变化迅速,情况的重复较少。在这里认识“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第86页)因此,谁要想在这里猎取“最终真理”,那决不会有什么收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杜林把类似巴黎在法国、鸟有喙等一些老生常谈宣布为永恒真理,其目的正是要人们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他企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道德和法律学说的阶级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3)从真理的界限方面,论述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批判杜林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驳斥他的“终极真理”的谬论。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8页)真理和谬误是根本对立的两种认识,二者是不能混淆的。只有划清这个原则界限,才能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否则,就会否认客观真理,陷入相对主义泥坑。但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又是相对的,这种对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若超出这个范围,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互相转化。人类的认识正是在真理和谬误的相互斗争、相互转化中前进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第83—84页)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会思想僵化,犯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错误。恩格斯以波义耳定律为例,深刻地说明了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在杜林的著作中,到处是关于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的说教,并且把一些信口胡说作为永恒真理强加给人们。这充分暴露了他的狂妄和无知。
恩格斯在这里为了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谬论,在阐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时,突出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后来,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竟然就此歪曲恩格斯的原意,胡说恩格斯“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云云。列宁在驳斥这种歪曲时,进一步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指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既“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同时又“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7—128页)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齤命路线,推行反革齤命修正主义路线,总是站在反动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形而上学地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有时,他和波格丹诺夫一伙一样,只谈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竭力散布否认客观真理的相对主义。他胡说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就把事物看死了,把我们的观念看死了”,企图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有时,他又和杜林之流一样,只讲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大肆宣扬绝对主义。他别有用心地鼓吹“顶峰”、“绝对权威”一类谬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毛主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又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真理总是同错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毛主席还深刻地揭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思想,从根本上驳斥了一切机会主义者把人的认识绝对化的企图,同时又批判了混淆是非界限的相对主义诡辩论。
(二)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阐述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第90页第2段一第92页)
杜林宣扬“永恒真理”的一种企图,就是要人们承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着永恒道德。他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认为道德也“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这些道德原则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一旦被发现,它就具有“绝对的适用性”。他狂妄宣称,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这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深刻论述了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1)道德是有历史性的。道德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恩格斯指出,善和恶的观念,“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第90页)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善恶观念,不存在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永恒道德。例如,在当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同时存在着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三种道德论。这三种道德各自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是永恒的。“切勿偷盗”,这是从动产的私有制产生以来,存在于一切私有制社会里的一条共同的道德戒律。然而它决不是永恒的道德戒律。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消除了偷盗动机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就不再是人们的道德戒律了。无产阶级道德是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道德,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但它也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2)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恩格斯指出:“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第91—92页)道德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但是从奴隶社会以来,道德还始终没有超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第92页)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人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消灭了,人们失去了阶级的属性而成了全新的人,那时才可能出现真正人的道德。
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所以,“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第91页)道德或道德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的,根本没有“绝对适用”的永恒道德。当然,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超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所以,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批判剥削阶级的旧道德,提倡共产主义的新道德。
最后,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道德论的反动性。杜林在社会革齤命的前夜,要把永恒道德强加于未来的社会,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革齤命,保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企图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杜林还把恶说成是人生来固有的一种性格形态,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道德问题上的表现。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煞道德的阶级性,宣扬“人类之爱”等陈词滥词,借以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本质。叛徒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之流,宣扬孔孟之道,无耻地吹捧孔丘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人类的“极高美德”,胡说“德、仁义、忠恕”等一类反动说教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并给它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妄图欺世惑众,用腐朽的剥削阶级道德腐蚀我们的党。他们为了搞反革齤命政变,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还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破烂,搬出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精神,来给他们的喽罗撑腰打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伙无耻叛徒,倒行逆施,妄图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永远办不到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剥削阶级的反动道德论的理论基础。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腐朽、反动的人性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一切社会现象,要培养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锻炼成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革齤命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齤命。认真学习恩格斯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道德论的论述,对于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对于批判超阶级的道德论和各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https://tieba.baidu.com/p/3071095729?red_tag=0490229998&traceid=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10-20 11:15
【案例】
李泽厚 刘悦笛:伦理学杂谈——李泽厚、刘悦笛2018 年对谈录
-
6.jpg
(236.63 KB, 下载次数: 296)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10-27 08:20
【案例】
罗尔斯在《正义论》说:一人一张的选票不仅仅代表一种政治权利,它更大的价值在于确立了一种公民间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它使得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超越了狭小的家庭和朋友圈,通过宪法在社会上得到一种肯定,它让公民意识到彼此不仅仅是社会中的竞争对手,也承担着共同义务,需要共同努力去促进社会的发展 。
编辑:王豪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2 14:01
【案例】
康德丨头顶是璀璨星空,心中有道德法庭
原创: 哲学之路 哲学之路 2019-01-02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
关注
本文12204字,阅读用时约30分钟。
1724年,康德出生于普鲁士柯尼斯堡。除了在邻镇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外,这位矮个子教授从未离开自己的家乡。他家境贫穷,祖辈在数百年前从苏格兰迁居德国。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坚持严格的宗教仪式和信仰。
这位哲学家整天沉浸在宗教氛围之中,以至成年之后,他一方面远离教堂,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特有的忧郁,到了老年,他渴望为世人和自己保持母亲赋予他的信仰本质。
但是,一个成长于腓特烈和伏尔泰时代的年轻人,不可能与当时的怀疑论思潮毫无联系,康德曾深受过一些人的影响,后来又奋起驳斥他们,对他影响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后来最喜欢抨击的休谟。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位哲学家超越了他壮年时的保守主义,年近古稀时,他在最后的著作中基本上转向了激进的自由主义。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年纪与名望,这一举动差点让他送了命。甚至在他关于宗教复兴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经常听到近似于伏尔泰的声音。叔本华认为“让康德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自己的理论,甚至出版《纯粹理性批判》,这完全不是腓特烈应有的美德。很少有哪个政府会允许一个领薪水的教授(教授在德国是政府雇员)如此鲁莽行事,康德曾对腓特烈的继位者保证他不再写什么东西了”。
1755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编外讲师,两次申请提升教授都遭到拒绝,他在这个卑微的职位上整整呆了十五年。直到1770年,他才被聘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震惊世界。对这位腼腆、谦逊的教授来说,似乎不可能去做令人吃惊的事。
在那些平静的岁月里,他更关注物理学而不是形而上学,他大谈星体、地震、火、风、乙醚、火山、地理、人类学等等,这些东西通常不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他在《天体理论》中的观点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极为相似。在康德看来,所有天体都已经或将会有人居住,那些离太阳最远的行星,由于形成时间最长,也许存在着比地球人更智慧的生物。他的《人类学》揭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可能性。
我们对康德的漫长的成长过程已经有所了解。他身高不到五英尺,为人谦逊、谨慎,但他的头脑中却孕育了近代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康德的生活很有规律,起床、喝咖啡、写作、讲课、用餐、散步都有固定时间。每当康德身穿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现在住宅门口,然后走上今天仍叫作“哲学之路”的菩提树大道时,邻居们就知道时间准是午4点了。
这一规律行为直到卢梭《爱弥儿》的出版,作为卢梭超级粉丝的康德,对《爱弥儿》爱不释手,以至于忘记散步。那天下午4点,教堂的钟一如往常敲响,可康德还未现身,柯尼斯堡陷入一片恐慌,大家一致以为:靠!教堂的钟竟然坏掉了!这样的散步,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当天气转阴时,人们就能看到他的老仆人兰普夹着一把大伞,担忧地跟在他身后,仿佛是谨慎的象征。
由于体质羸弱,康德不得不坚持严格的养生之道,因此他活到了八十高龄。他最提倡的养生方式之一就是只用鼻子呼吸,因此,他在散步时从不与任何人讲话。他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再三,因此终身未婚。他曾有两次想向女人求爱,但由于考虑得太久,第一位女友与一个有勇气的男人结了婚,另一位在我们的哲学家下定决心之前就搬离了哥尼斯堡。也许和尼采一样,觉得婚姻会妨碍他追求真理。
他在十五年内,不断撰写和修改自己的著作,饱尝了贫穷与卑微的滋味,直到1781年他五十六岁时才定稿。从来没有人成熟得像他这样缓慢,也从来没有一本书像他的著作这样在哲学界掀起如此壮阔的波澜。
一、关于《纯粹理性批判》
这里的批判不是通常所说的批评,而是评判性分析。除了在结尾指出了“纯粹理性”的局限性之外,康德并没有对它进行攻击。相反,他想向读者指出“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使它高于由感官获得的知识。“纯粹理性”意味着不是来自感官、而是独立于所有感觉的知识,它是精神所固有的性质和结构。
一开始,康德就向洛克和英国学派发出挑战:知识并不完全来自感知。休谟自以为已经取消了灵魂和科学的存在;我们的精神不过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观念;必然性也仅仅是随时可能改变的可能性。康德说,这些错误的结论源于错误的前提,即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具体的、不同的”感觉。
假设知识来自感觉,来自变化无常的外部世界,那么,它就不是绝对可靠的。假如我们的知识独立于感官经验,其真实性、可靠性甚至在经验之前就能被我们先验地确定,这样,绝对真理与绝对科学就是可能的。究竟有没有这种绝对科学呢?这就是第一部《批判》所要探讨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抛开物质与经验,我们靠理性能获得什么?”康德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
《批判》一开始就直奔主题,“经验不是认识的惟一途径。经验告诉我们现象,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它不能带来任何普遍真理。普遍真理具有内在必然性,它独立于经验之外。”就是说,无论后来的经验如何,它们都是正确的,它们的正确性先于经验,是先验的正确。
“在先验知识上,我们不依靠经验能取得多大的进展?数学就是极好的例子。”数学知识是必然的、确定的;我们可能相信明天太阳会从西边升起,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二乘二不等于四。这种真理的正确性先于我们的经验。那么,我们从哪里获得这种绝对、必然的特性呢?不可能从经验中来,因为经验给我们的只是片面的感觉与事件,而且它们的顺序将来也可能发生改变。
这些真理的必然性来自我们精神固有的结构,来自我们精神活动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因为人的精神并不是被动的蜡版,任由经验和感觉为它打上绝对而反复无常的印记;它也不仅仅是一系列心理状态的抽象名称,它是一种能动的器官,能把感觉加工成观念,使纷杂的经验变成有条理的思想。
1.先验的感性论
对精神的固有结构或思维的内在规律所进行的研究,构成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因为这是一个超越感官经验的问题。将感觉加工成观念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运用知觉的形式:其二为运用概念的形式。康德将第一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的感性论”,将第二阶段的研究称为“先验逻辑”。
感觉和知觉究竟是什么意思?大脑是怎样将感觉变为知觉的?感觉只是对刺激的感知,舌头能品尝味道,鼻子能嗅到气味,耳朵能听到声音,皮肤能感受温度,眼睛能感到光亮,指头能感受压力,这就是经验的雏形。婴儿也具有这些能力,但这不是知识。如果让各种感觉聚集于某一对象——比如说一只苹果的气味、味道、光泽、压力等等综合在一起,你所感觉到的与其说是刺激,不如说是特殊的对象,这就是知觉。这时感觉已经成了知识。
那么这种过渡完全是自动的吗?感觉是否能自发地汇集在一起成为知觉呢?洛克与休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康德正相反。
纷杂的感觉通过皮肤、眼睛、耳朵、舌头和密密麻麻的神经一窝蜂涌向大脑,要求得到关注时,场面是多么混乱!如果听之任之,感觉只能是杂乱的“混合体”,毫无作为。就像将军把来自战场的各种情报整理成信息和命令一样。杂乱的感觉也有一个指挥官,它不仅接收信息,还要掌握这些感觉的细节,使之形成意义。
但是,并非所有的感觉都能被选中,只有经过筛选的信息,或那些紧急信息,才会被加工成为知觉。时钟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响,你可能听而不闻。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立即就能听见,而且同样的“嘀答”声听起来比原来响得多。在摇篮旁睡着的母亲对周围的喧闹声一点也听不到,但小宝宝稍有动静,母亲就会立刻醒来。感觉和观念的联系首先是由精神的目的决定的。感觉就像佣人,等待着我们的使唤,你不需要时,它们就不会出来。有一种选择和操纵的力量在运用着它们。在感觉和观念之上存在着精神。
康德认为,选择和协调的能力对呈现的材料进行了两种简单的区分法,即空间感和时间感。把信息根据其来源和时间加以整理,就能找出它们的头绪。大脑分配空间感和时间感,将它们归于各类物体、现在或过去。空间和时间不是人们觉察到的东西,而是知觉的方式。
空间和时间是先验的,因为一切经过整理的经验都和它们有关。没有它们,感觉永远不可能升华成知觉。正因为它们是先验的,所以,它们的规律——数学规律,也是先天的、绝对的和必然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比两点之间的直线更短的距离。在这里,至少数学已被康德从休谟那种消灭一切的怀疑论中抢救出来了。
其他学科是否也能得到拯救呢?当然能!但必须证明其基本原理,也就是因果律。那么,作为各种思维的必要前提的因果律,是否具有先验性呢?
2.先验的分析论
现在,我们从感觉与知觉的广阔领域走进思维的黑暗斗室:从“先验感性论”转到“先验逻辑”。精神活动就是对经验进行调整。这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心灵能动性——在洛克和休谟看来,心灵只是顺从于感官经验的“被动的蜡版”。考虑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各种数据的排列顺序是数据本身的能动性实现的吗?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按照人的意愿排列得井然有序。如果把卡片盒打翻在地上,所有的卡片撒了一地,你能想像这些散乱的卡片会自己从纷乱中站起,按照字母顺序回到原来的盒中吗?由此可见怀疑论者的论点之荒谬!
感觉是无序的刺激,知觉是有序化的感觉,概念是有序的知觉,科学是有序的知识,智慧是有序的生活,就它们的顺序、连续性和统一性来说,它们一个比一个高级。这种顺序、连续性和统一性从何而来?它们并非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我们的目的。康德说:“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如果知觉会自动将自己梳理成有序的思维,如果心灵并不具备乱中求序的能力,那么,同样的经验又怎能使一个人平庸、卑微,而使另一个人积极自信,并找到智慧和真理呢?
因此,世界的秩序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因为认识世界的思维,也就是科学和哲学,具有给经验分类排列的能力。思维的规律也是事物的规律,因为事物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律的思维被我们认识的。正如黑格尔后来所说,逻辑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一回事,逻辑规律和形而上学互相融合。科学的一般原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说到底是思维规律,而思维规律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经验,也是以它们为前提的。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3.先验的辩证法
逻辑与科学的概括虽然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却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相对性,即严格局限于经验范围内,严格局限于人类的经验方式。因为,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是一种结构、一件成品,甚至可以说一是一件杰作:在制造它的过程中,心灵提供了模板,物质提供了刺激,两者同样重要。物体向我们显示的是现象与外表,也许与它们本来的样子大不相同。
那个本来的物体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物自体”可能是推断出来的物体(一种“本体”),但它无法被我们感知,因为在被感知的过程中它会扭曲变形。“我们完全不知道物体远离我们的感官而独立存在时的样子。我们只知道感觉它的方式,这是人所特有的。我们所认识的月亮只是一连串的感觉,它们在经过了从感觉到知觉,再从知觉到概念的加工之后,被我们的心理结构统一起来。结果,对我们来说,月亮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
康德并没有怀疑“物体”和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知道物体的存在,我们没有一点真切的认识。我们所知道的细节是有关物体的表象、现象和由此得来的感觉。唯心主义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只承认感觉主体而否认存在,它只是说物体的很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感觉与认识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我们只了解转化成观念后的物质,而物体在这种转化发生之前是什么,我们无法了解。科学毕竟还比较幼稚,它以为自己在与客观的物体本身打交道:哲学要稍微复杂一些,它发现科学中的事物是由感觉、知觉和概念组成的,而这些东西并不是事物本身。叔本华说:“康德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现象从物自体中分离了出来。”
于是,无论科学还是宗教,一切想搞清最终实际性的尝试最终只是假想;“认识永远不可能冲破感受性的樊篱”。这种超验科学将在“二律背反”中迷失方向,这种超验宗教也会消失在“反理”之中。“超验辩证法”的作用,就是对理性企图从感觉的包围圈中逃到未知的“物自体”世界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二律背反是由企图超越经验的学科导致的窘境。例如,当认识试图判断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还是无限时,思维就会反驳任何一种设想:如果没有尽头,我们就要无休止地往远处想,但同时,无限性本身又是不可想像的;另外,世界在时间上有起点吗?我们无法想像永恒;也无法想像过去某一时刻之前的一切都不存在;或者,科学所研究的因果链是否有第一原因?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尽头的链子是无法想像的。但同时答案又是否定的,因为第一个没有缘由的原因也是无法想像的。思维的这些困惑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当然有,康德告诉我们,只要牢记空间、时间和因果都是知觉和概念的方式,而我们困惑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它们看成了独立于知觉的外界事物。我们对一切经验的解释都离不开空间、时间和因果,但它们并不是事物而只是解释和认识的方法,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哲学。
“唯理”神学的困惑也是如此,它试图证明灵魂是不朽的物质,意志是自由的,不受因果律的约束,而且还有一种作为一切现实的前提的“必然存在”,即上帝。超验辩证法会提醒神学:物质、原因和必然是心灵运用于感觉经验的方法,它们只用于这类经验中的现象: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用于本体(或臆想的)世界。
到这里,第一部《批判》就结束了。可想而知,恐怕连休谟也会报以嘲笑,这是一部厚达八百页的大部头,其间充斥着冗长的术语,它试图解决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并顺便拯救科学的绝对性和宗教的真实性,但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它摧毁了朴素的科学世界,把科学限制在表面的世界中,一旦超越这种限制,科学只能产生可笑的“二律背反”;科学就是如此得到了拯救!书中最雄辩、最深刻的部分强调说,造物主不能用理性加以证明,于是宗教也得到了拯救!难怪当时德国的牧师们疯狂地反对这种拯救,纷纷给自己的狗起名为伊曼诺尔·康德以泄愤。
难怪海涅要拿这位矮小的教授与可怕的罗伯斯庇尔作一番比较。后者不过是杀了一个国王和几千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摧毁了神学中最宝贵的论点。这位先生的外表与他那毁灭性的思想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然而善良的柯尼斯堡的市民只知道他是一位哲学教授,当他在固定的时刻漫步走过时,他们会友好地点头致意,然后把表对准。
二、关于《实践理性批判》
既然科学和神学不能作为宗教的基础,那么这基础又该是什么呢?答案是:道德。
神学的基础太脆弱,应该抛弃。信仰必须置于理性范围之外,因此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而不是来自可疑的感觉经验和破绽百出的推论。它应该起源于内心自我。我们应该寻找普遍的、必然的伦理,这种先验的道德准则应该像数学那样绝对可靠。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决定意志,独立于任何经验”,道德感是内在的,而不是源自经验。这种道德法规作为宗教基础,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强制的。
在我们的经验中,最令人诧异的实在就是我们的道德感,也就是我们面对诱惑时不可避免地认为这样做不对的那种感觉。早晨下了决心,晚上又干蠢事,我们知道那是蠢事,因此就又下决心。促使我们悔恨、下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中无上的道德准则,是良心的绝对命令,它驱使我们行动,好像我们的行为准则会通过我们的意志变成自然的普遍规律。
是直觉而不是思维使我们懂得,我们必须避免一些行为,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继续。“虽然我想撒谎,但我不希望撒谎成为普遍的准则,因为有了这样的准则,一切都将毫无希望。”因此我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虽然撒谎对我有利,但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是绝对的。
好的行为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而是因为它遵循了内心的责任感与道德准则,这种责任感或准则虽不是来自经验,却严格地、先验地规定了我们的一切行为。世界上惟一绝对美好的东西是善良的意志——不计个人得失而严守道德准则的意志。“道德的宗旨不在于如何让自己幸福,而在于如何让自己无愧于得到的幸福。”
我们应该让他人快乐,而自己去追求完美——无论它为我们带来的是幸福还是苦难。这就要求我们“将人道视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也是我们所感到的一部分绝对命令。只要我们恪守这样的准则,我们很快就能创造出充满理性的理想社会。你也许会觉得这种让义务高于美、让道德高于幸福的道德过于苛刻,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野兽变成神明。
我们要知道,这种尽义务的绝对命令最终证明了我们意志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感,又怎么可能产生责任这种观念呢?我们无法用理论证明这种自由,但可以用我们处于道德抉择的紧要关头时的直觉予以证明。我们将自由视为纯粹自我的本质,在内心里,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地塑造经验、选择目标的活动。我们的行动似乎在遵循固定不变的规律,可是我们是通过感官才觉察到规律的结果的,我们仍然超越了我们为了理解经验世界而制定的规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积极力量和创造力的中心,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感觉,无法论证。
虽然不能证明,但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朽,我们能意识到生活并不像人们喜爱的戏剧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毒蛇的智慧要比鸽子的温柔更受青睐,任何一个窃贼,只要偷够了就是成功者。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一再地遭遇这一切,我们还是能感觉到一种使我们走向正义的命令,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些具有永恒之美的举动。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只是全部生活的一部分,今生的梦想只是孕育新生的前奏。我们朦胧地感到在来世更长的生命中,平衡将得到恢复。今生慷慨送人一杯水,来世将得到百倍的回报,否则,是非观念怎么会长存呢?
如此说来,还是存在着一个上帝,假如责任感涉及并证明了来世报应,那么“设想永生就必将导致设想上帝的存在。”这也是不能用“理性”证明的。与我们的行为相关的道德感必须优于只能处理感觉现象的理性逻辑。我们的理性说服我们相信物自体背后有一个公正的上帝:而我们的道德感则命令我们相信它。卢梭说得对:心灵的感觉高于头脑的逻辑。帕斯卡也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心灵自有它的道理,大脑永远也无法理解。
三、论宗教与理性
这种理论是不是有些保守呢?不,正相反,这种否定“理性”神学、将宗教的原因解释为道德信仰和希望的直率言论引起了德国正统势力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毅然与“四十牧师的力量”对峙,康德必须具有比人们熟悉的他更多的勇气。
康德有足够的勇气。他六十六岁出版了《判断力批判》,六十九岁又出版了《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在前一本书中,他又回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目的的讨论,康德曾认为目的说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予以否定。这——从目的与美的联系入手。他认为美即结构的匀称与统一。“对自然美的兴趣一直是善的标志,”大自然中的很多物体都十分美丽、匀称和统一,几乎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由超自然的力量造就的。
但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自然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混乱、无用的重复;自然孕育生命,代价却是无数的苦难和死亡!因此,外部设计的表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过多运用这种论据的神学家应该抛弃它,而抛弃了它的科学家应该运用它;这是一条重要线索,能产生无数种启示。
因为目的无疑是存在的,但它是事物的内在目的,是总体设计出的部分。假如科学从整体出发去解释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会给另一种本来很有启发性的原理(即机械的生命概念)带来美妙的平衡,这种原理尽管也有利于新的发现,但只靠它,恐怕连一片草叶的生长原理也解释不了。
这篇关于宗教的论文也许是康德所有作晶中最大胆的一部。既然宗教的基础不应是理性的逻辑,而是道德感的实践理性,那么,任何用以评价圣经或启示录的标准一定是它的道德价值,而圣经或启示录本身是不能成为道德标准的,教会和教条只在有助于道德发展时才有价值。
当教条或仪式成为评价宗教的标准时,宗教就消失了,真正的教派是人民的集体,不管多么零散,他们总是为了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一致。基督就是用这样的教派去同法利赛人的教权进行对比的。
但是,新的教权后来居上,几乎推翻了这种崇高的理想。“基督已使上帝的国度接近人间,但他被误解了。牧师的天国代替了上帝的国度。”教条和仪式又一次取代了美好的生活,人们不仅没有团结在宗教周围,反而分裂成上千个教派。各种“虔诚的谬论”被说成是神圣的事业,从此人们可以靠奉承赢得天国统治者的恩宠。这说明奇迹不能证明宗教,如果祈祷是为了破坏适用于一切经验的自然规律,那么它就毫无价值。最后,当教会沦为反动政府的统治工具、当牧师变成神学的迷信者和政治压迫的工具时,教会的腐化就会达到顶点。
以上论述之所以显得大胆,是因为这种事恰恰在普鲁士发生过。腓特烈大帝死于1786年,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在威廉二世看来,他的前任所推行的政策似乎有法国启蒙运动的痕迹,不利于国家稳定。塞德立茨这位腓特烈时期的教育部长被解职,取代他的沃尔纳是一个虔敬派教徒。腓特烈曾说他是“一个阴险的牧师”,他整天沉浸在炼金术和巫术里,由于甘愿充当新皇帝强制恢复旧信仰的工具而爬上高位。
1788年,沃尔纳发布了一项命令,在各级学校里禁止讲授任何违背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东西,对各种出版物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开除一切有异端嫌疑的教师。起初,康德由于年事已高而末牵扯进去,另一个原因,也许正如一位皇家顾问所说的那样,他的读者不仅少,而且还不怎么理解他的学说。但是,他那篇宗教论文却通俗易懂,它看上去似乎洋溢着宗教热情,而且有着浓厚的伏尔泰气息,所以过不了新的审查关。本来打算刊登这篇文章的《柏林人月刊》被命令取消了该文的发表。
康德行动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与勇气。他把这篇论文寄给了耶拿的几位朋友,在那里的大学出版社发表了。结果,康德在1794接到了普鲁士皇帝内阁的命令,上面写道:“得悉你滥用你的哲学来破坏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陛下极为不悦,我们要求你立即作出解释,并希望你今后不再轻率行事,而是利用你的才智和名声努力实现天父的意愿。若再明知故犯,后果将极为严重。”
康德回复说,本来每个学者都有权在宗教问题上保留和宣讲自己的主张,但在当今皇帝治下,他将保持沉默。有些传记作家谴责康德的这种让步,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七十高龄、身体虚弱的老人已经不宜争斗了,再说他已经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了世人。
四、论政治与永久和平
若不是康德还有持不同政见的罪名,普鲁士政府也许会放过他。威廉二世继位三年后,法国大革命使欧洲所有的王位受到了强烈震撼。就在普鲁士大学的多数教师纷纷表示拥护君主制的时候,六十五岁的康德却为革命欢呼。
1784年,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政论文章,题为“从宏观世界政治史的角度审视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个人对群体的抗争使霍布斯大为惊讶,康德却由此意识到自然开发生命潜能的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的必由之路。如果人与人之间过于和睦,人类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没有不稳定因素,人们的才能将会被永远埋没。”“感谢上苍给了我们不安、嫉妒、虚荣还有永不满足的欲望……人想要和谐,但自然懂得什么对她的物种有益,她有意使人们争斗,好让人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因此,以斗争求生存并非完全是坏事。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这种斗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用规则、习俗和法律加以调节。于是文明社会就因此而产生并得到发展。但今天,“迫使人们组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又使国与国之间采取了无节制的自由政策,任何国家都可能遭到来自别国的威胁。这时,国家就应该像人一样从自然的野蛮状态中脱离如来,并订立盟约以维护和平。”
历史进程及其全部意义就是约束暴力,不断扩大和平的领地。如果没有这种进步,对文明的创建就会像西西弗斯那样,一次次将巨大的圆石推向山顶,快到山顶时又滚回山下。那么,历史只能是周而复始的蠢事。“我们就会像印度人那样把地球看作是为前世赎罪的地方。”
有关“永久和平”的文章进一步发挥了这一主题。与各个时代的人一样,康德也发过牢骚:“统治者在公共教育上一毛不拔,因为他们早就把所有的钱花费在下次战争的开支上了。”不撤掉军队,国家就不可能文明。“设立常备军会刺激各国进行无休止的军事竞争,维护和平所耗费的军费比一场短期战争还要多,由于统治者急于摆脱由此造成的经济负担,因此常备军就成了侵略战争的根源。”战争时期的军队能够自给自足,因为他们可以在敌国征兵、驻扎和掠夺,必要时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样做。这总比动用政府的资金来维持军队更容易。
康德断言,欧洲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和分赃纠纷是军国主义的主要根源。和野蛮民族的不好客相比,欧洲文明国家,尤其是商业化国家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在他们看来,对异域民族的访问就是一种征服。美洲、黑人大陆、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只要被他们发现,就成了没有主权的土地,因为他们不把土著人当人……这一切就是极力宣扬宗教虔诚的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在犯下滔天罪行的同时,又自视为正统信仰的选民——但是,这个哥尼斯堡的老家伙还不肯闭嘴!
他将这种贪婪归咎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体,赃物由少数人来分,就算是瓜分之后也十分可观。如果实行民主制,这种国际掠夺所获得的赃物将被均分,最后每人只能分到很少的赃物。因此,实现永久和平的首要前提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共和政体,不经全体公民投票表决不得宣战。否则发动战争就会如同儿戏,想打就打。由于统治者是国家的拥有者,他们根本不必亲自体验战争的苦难,更不必牺牲奢华的,因此可以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而根本不去考虑战争是否合理。
1795年,革命军队打败了反动军队。康德对此寄予了厚望,认为共和制将在欧洲兴起。总之,政府的职能在于帮助个人得到发展,而不是剥削个人,“每个人都应得到绝对的尊重,如果将他人视为个人财产,或视为工具,那就是侵犯人的尊严”。这就是绝对命令的基本含义。没有它,宗教只是一场虚伪的闹剧。因此,康德提倡平等:并非能力的平等,而是在发展和发挥能力的机会上平等。他反对世袭特权,在愚昧、反动的欧洲君主联合起来镇压革命的关头,康德不顾七十高龄,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为民主和自由大声疾呼。
然而,他毕竟是老了。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日渐衰老。1804年,他像一片落叶一样投入了大地怀抱,享年七十九岁。
五、评价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哲学风暴之后,康德庞大体系的现状如何?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宏大建筑的主体依然存在,不过,它的许多细微之处和外部结构已经动摇。
首先,空间是否仅仅是一种“感觉形式”,脱离了感知的心灵是否就没有客观实在性?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空间不存在能被感知的物体时,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空间”是指某些物体,对于心灵来说,是与别的可感知的物体的相对位置或距离。假如没有空间物体,一切外部知觉都不可能。因此,空间是“外部感觉的必要形式”。
同时答案又是否定的:因为像地球每年绕太阳旋转一周这样的空间事实,虽然能被心灵解释,但却独立于一切形式的感觉。不管拜伦是否活着,蔚蓝的大海总是动荡的。空间也不是心灵通过非空间感觉的协调而获得的“结构”:我们通过对不同物体和方位的感觉来直接感知空间——就像我们看着虫子在静止的背景上爬一样。同样,时间作为对过去和未来的感觉,或对运动的衡量,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是,无论我们是否能感觉或测量时间的流逝,一棵树终究会衰老、枯萎和腐烂。
其实,这是因为康德急于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作为规避唯物论的法宝。他害怕这样的说法:假如空间是客观的、普遍的,那么,上帝就必定存在于空间,并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批判唯心主义认为,实在性主要是作为我们的感觉和观念才为我们所认识,对于这种论点,他应该满足了。然而,他太贪心了。
他完全可以满足于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而不必绞尽脑汁地强求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现代一些哲学研究,如英国的皮尔逊、德国的马赫、法国的亨利·彭加勒等人的结论,都与休谟而不是康德相同。一切科学,包括最严格的数学,在真理上都是相对的。也许,“必然”的知识是不必要的。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证明了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人们认识的,心灵不是一张放动的白纸,而是一种积极的决定性媒介,具有对经验进行选择、整理的能力。我们可以和叔本华一样,对三个一组的十二个范畴的模式报以微笑,康德为了使它们适合周围的事物,曾对它们随意伸缩、作出牵强的解释。
我们甚至可以问一问这些范畴或思维的解释形式是不是真的先于所有感觉和经验而存在。也许,对于个人而言,它们是先验的,尽管对于全人类来说它们是后天学来的。甚至对个人来说,它们也极为有可能是后天学来的,也就是说,范畴是思维的渠道,是知觉和概念的习惯,是由感觉和知觉本身的排列而逐渐形成的——起初是杂乱无章的,后来,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思维就对事物的排列方式进行自然选择。正是记忆将感觉分类并加以解释,使它们成为知觉,又使知觉成为观念。但是,记忆是逐渐增加的。
康德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性,实际上是后天学来的——而且并非人人都有。健忘症、多重人格和精神病都可以使人丧失这种统一性。概念不是天赋,而是一种收获。
十九世纪对康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内在、先验、绝对的道德伦理观进行了批判。进化论哲学表明,责任感是个人具有的社会性,良知的内容是后天学来的,尽管社会行为的某种倾向是先天的。具有道德和社会特性的人并非上帝的“特别创造”,而是漫长进化的产物。道德不是绝对的,而是为了集体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行为准则,并会随着集体的性质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一个四面受敌的民族会将狂热的个人主义视为不道德,而一个富裕、安定、洋溢着活力的国家就能容忍这种个人主义。正如康德所设想的那样,行为本身无所谓好坏。
康德在第二部《批判》中恢复了第一部《批判》所摧毁的宗教观念,这实在令人惊讶。读康德的哲学,你会有一种置身于乡村集市的感觉。在他那里,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切东西:意志的自由与禁锢、唯心主义与反唯心主义观点、无神论和善良的上帝。就像魔术师用空帽子变戏法一样,康德从责任概念中变出了上帝、不朽和自由。康德摧毁了思辨神学的脆弱基础,却不去触动世俗神学一根毫毛,甚至将它作为更高的信仰形式放在道德感情的基础之上。
因此,这种做法被一些哲学家理解对上帝的合理理解。康德尽管摧毁了古老的错误信仰,但也深知这种举动的危险性,他想用道德神学来给摇摇欲坠的宗教加上儿根细弱的支柱,这样,他就可以从容地脱身了。
对康德冒险进行的这种内心重建活动,我们不必太认真。《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文中的热情表明,他把宗教基础由神学改为道德、由信条改为行动的探索只能出自一个虔信的心灵,他在1766年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信中说:“的确,我思考过许多我确信的东西,却没有勇气全说出来。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我是决不会说的。”
像《批判》这样庞大、晦涩的巨著很容易引起完全相反的解释。该书的初期评论之一是由莱因霍德写的:“《纯粹理性批判》被教条主义者视为一个怀疑论者试图否定所有知识的确定性而作的尝试;怀疑论者把它视为企图在旧体系的废墟上建立新教义的一种狂妄臆想;超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企图取代宗教的历史基础的阴谋,其目的是不经过论战就偷偷建立起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把它看成是垂死的信仰哲学的新支柱;唯物主义者把它当作唯心主义对物体实在性的反驳;唯灵论者认为它是对所有存在的不公正的限制,即以经验科学的名义,将万物限制在物质世界中。”
其实,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上面所有观点的认同,康德似乎真的把这一切融合成了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复杂的统一体。
就其影响而言,整个十九世纪的一切哲学都以他的学说为中心。自康德之后,谈论形而上学在德国蔚然成风:席勒、歌德研究过他;贝多芬满怀敬意地引用了他的名言:“头顶是璀璨星空,心中有道德法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都从他的唯心主义中汲取营养,并相继创立了伟大的思想体系。
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和对感情的推崇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论、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铺平了道路;他把思维规律和现实规律等同起来,把一整套哲学体系传给了黑格尔;他的不可知的“物自体”观点对斯宾塞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后者所认识到的;凯尔德、格林、华莱士、沃森、布雷德利和其他众多英国哲学家都在第一部《批判》的启发下找到了灵感:即使是狂妄的尼采,尽管猛烈抨击康德保守的伦理观,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认识论。
一个世纪以来,康德的唯心主义一直在与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对峙着,尽管双方都经过了多方面的改革,但康德似乎还是略胜一筹。甚至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也自相矛盾地写道:“如果要我说实话,我要说人是物质的创造者。”
由于有了康德,哲学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幼稚了;自康德起,哲学就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
编辑:陈心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8 12:27
【案例】
波普尔哲学欣赏(27)一些基本问题的考察(之八)科学客观性和主观信念
“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些词是充满着各种矛盾用法和无结论的冗长讨论的哲学用语。
我对“客观的”和“主观的”的用法与康德没有什么不同。他用“客观的”这个词来表示科学知识应该是可证明的,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念,如果原则上它可以为任何人所检验和理解的话,证明就是“客观的”。
他写道:“如果某个事物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是合理的,那么它的根据就是客观的和充分的。”
我认为科学理论是决不可能完全证明或证实的,虽然如此,但我认为它们还是可检验的。因此我要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够被主体间检验的。
康德用“主观的”一词表示我们(各种程度的)确信感。考察这些情感如何产生,是心理学的事情。例如,它们可以“按照联想定律”而产生。客观的現性也可以成为“判断的主观原因”,只要我们考虑了这些理性并相信它们的说服力。
康徳也许是认识到科学陈述的客观性是同理论的构造--使用假说与全称陈述密切联系的第一个人。只有当某些事情按照规则或规律反复发生时,象可重复的实验那样,我们的观察在原则上就能被任何人所检验。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8 20:32
【案例】程序正义具有内在价值
本文是论文《程序正义的价值与局限》的第一部分,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总第14辑
人们对于程序正义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常常感到困惑:如果一个决定对于当事人有利,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在乎做出决定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做出决定的程序自身是重要的吗?正义的程序应该符合哪些道德标准?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在政治、司法以及分配领域的重要的程序正义都具有怎样的特征,应遵循哪些道德原则。
首先,程序正义要求“平等待人”,这一点在政治领域的民主制度当中有集中的体现。举例来说,假设一个班级的成员需要决定去哪里春游,可能有三种方式做出这一决定:1.由老师决定;2. 由班干部决定;3. 由全体同学投票决定。在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方式可以简单地对应一人决定的“君主制”;第二种方式对应强者决定的“寡头制”;而第三种方式则对应多数决定的“民主制”。相信大部分人(除了班干部以外)都会选择第三种方式,因为,即使第三种方式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想法都得到实现,但是,它至少能保证每个人的想法都被听到,而且都为集体决定增添了分量。
人们的道德直觉往往是哲学家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康德的道德律令要求“把每一个人当作目的王国的合法成员”[1],这在当代政治哲学讨论中被阐述为“平等待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做出事关每个人的决定时必须同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能因人们在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或知识背景上的不同而给予各种意见不同的权重。如上述例子中,在决定去哪里春游的问题上,普通同学应有与老师和班干部同等的投票权,不能因老师和班干部拥有的权力而给予其意见更高的权重;或者,班里某同学对春游这一主题有更多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他可以向大家说明这些情况,但其意见同样不能占有更高的权重。我们可以将这个例子放大到政治生活的领域,例如,英国计划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留在欧盟,那么在这样的民主过程中,那些对欧盟有充分了解的知识精英、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以及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巨头……都与普通公民一样,只有投“一票”的权利。因为民主制度要求,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平等地听到。总之,“平等待人”是程序正义的道德要求,正是基于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天然联系,民主制虽然自古以来饱受批评却仍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
第二,程序正义要求“过程公开”,在司法审判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在讨论程序正义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时,举了电影《被告》[2]中的例子:一个被强奸的妇女将强奸她的人告上了法庭,但此案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开庭审理。被告律师与原告律师通过商议达成一致,将罪犯送进了监狱。也就是说,这一案件虽然没有经过公开的审理程序,但在私下的商议中,这一案件同样达到了公开审判可能会得到的结果。然而,剧中的女主人公却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法庭上陈述对方的犯罪事实,有在公众视野下披露罪犯、讨还公道的机会。然而,事情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罪犯虽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受害者的声音却没有被听到。显然案件的私下解决剥夺了受害者的某些权利。一个司法程序不应该是私下进行的,必须在法官和陪审团的见证之下,公开、公正地展开。内在于程序正义的“公开”原则要求,应将程序中应用的规则和标准向当事人解释清楚,使其理解施行于他的程序是如何进行的。这就像在做治疗之前,医生要向病人或其家属说明治疗的具体方案、用什么药、有什么副作用,等等;而不是没有任何解释直接进行治疗。
第三,程序正义要求“准确”反映参与者的信息,这一点在社会分配领域非常重要。考试制度是最常见的对教育机会进行分配的程序。然而,对于考试制度的诟病可能从有这一制度开始就从未停止过。这与“考试”很难准确反映参与分配者的信息有关。在理想的情况下,一次“公正的考试”应该准确地反映考生在与其申请获取的教育机会相关的各方面的能力和知识。然而,没有任何试题能设计地如此完美,同时也不是所有考生都能完全正常地发挥,于是在考试中总有走运的人和不走运的人,各种偶然因素造成了考试很难做到“准确”反映人们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基于考试结果而进行的资源分配,也就很难保证公平。但是,与其他更容易“作弊”的评价机制相比,“考试”还算是最“准确”的程序了。因此,虽然这一制度一直受到批评,却仍然沿用至今。对于其它资源的分配同样存在准确的问题:例如,国家想要给那些经济困难买不起房的人进行补贴,那这就需要准确地知道人们的居住情况和收入情况,然而这将是一桩耗时耗力、繁琐无比的差事。为此,政府部门需要搜集许多相关信息:个人的收入和住房情况、个人的家庭关系、其亲属的收入和住房情况、还有各种可能造假的问题……这些复杂的个人情况使得国家很难做到对参与分配者的准确了解,或者要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获得准确信息,但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国家就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所以说,“准确”是程序正义的一个核心要求,但却是一个在实践中很难满足的要求。
米勒总结了程序正义应该具有的四种性质:平等、准确、公开、尊严,并且认为“尊严”是与前三种性质不同的。[3]所谓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尊严”指的是:一种程序不能以使人们丧失尊严的方式进行。例如,为了保证公共安全要对上飞机的乘客进行安检,但安检不能不能以搜身的方式进行,那样会有损乘客们的尊严。再比如,某单位或许想要对供职于该单位的“单身妈妈”给予某种补助,但为了进行这种补助,就需要了解一些隐私信息,而这会让“单身妈妈”们感到丧失尊严。程序正义要求施行于人们的程序要保护人们的“尊严”。
综上所述,平等、公开、准确和尊严是程序正义的四个基本性质,也是程序正义所体现的四种重要的道德原则。米勒认为,这些性质“可使得程序正义超越并凌驾于其产生实质正义之结果的倾向之上”[4]。也就是说,程序正义所体现的道德原则使得程序正义不依赖于其产生的结果而具有“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是指“某事物因其本身而有价值”。基于此,社会成员为了程序正义本身而欲求程序正义,并非为了利益、幸福、安全或其他个人目的而欲求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具有内在价值的判断得到了大众心理学研究结果的佐证。E. A.林德(E.A. Lind)和T. R.泰勒(T. R. Tyler)在《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5]一书中讨论了程序正义与人们的各种相关态度之间的关系。首先,作者认为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去讨论正义问题。在政治领域,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罗尔斯和诺奇克,都是从客观的角度去建构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将正义当作一种“客观的事态”。而约翰·蒂博(John Thibaut)在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开创性地将心理学研究和程序正义结合起来,揭示了程序正义对人们有关正义问题的态度和判断的影响,拓宽了正义问题的研究领域。[6]所谓“主观正义”,是将正义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的反应”[7],指的是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某个程序是否正义的主观判断。在区分主观正义和客观正义的基础上,林德和泰勒总结前人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程序正义具有增进主观正义的效应。具体说来,程序正义具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效应,林德和泰勒将其称作“程序正义效应”(ProceduralJustice Effects):“受制于某一程序的人们,当其能发出声音或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程序,人们将更容易得出该程序之正义的判断;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的肯定有助于增进对于分配正义的评价,并增进人们对于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对程序正义的判断有助于增进对权威的认可;对程序正义的判断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有益行为”[8]。综上所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某一事态正义与否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程序是否公正平等的影响。程序正义自身具有内在价值,其价值独立于程序可能产生的结果,人们因其本身而欲求程序正义。
[1]【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2]这是一部由乔纳森·卡普兰导演,朱迪·福斯特和凯莉·麦吉利斯主演的影片,1988年上映,片名译为《暴劫梨花》。
[3] David Miller, Principles ofSocial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1.
[4] Ibid., p.99.
[5] E. A. Lind and T. R. Tyler, The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1988.
[6] Thibaut, J.,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dale, NJ: Erlbaum.
[7] Ibid. p. 3.
[8] Ibid. p. 204.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NMIslYNvDrKdCxOBQviLbw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8 21:57
【案例】经济化伦理学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心理学实验来检验和提供我们对人的行为的认识,已进入伦理学领域,这似乎正成为一种新行为伦理学。对这样一种新思潮应当如何看待?日前,美国德保罗大学经济伦理学维克兰讲座教授金黛如(Daryl Koehn)应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她从美德伦理学角度批判这种新行为伦理学,认为经济化的伦理学即新的行为伦理学,已经在经济实践方面发生了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原文 :《经济化伦理学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作者 | 美国德保罗大学经济伦理学维克兰讲座教授 金黛如
金黛如(Daryl Koehn):美国德保罗大学经济伦理学维克兰讲座教授、企业与职业伦理学院执行院长,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执行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她曾任美国经济伦理学学会会长,在伦理学、经济伦理和公司治理方面著述颇丰,专著有《职业伦理基础》《恶的本性》《女性伦理学再思考》等。作为《时代》《彭博新闻》《金融时报》的评论人物,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PBS电视台等媒体上。
如何看待经济伦理问题
经济学是怎么看待伦理问题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新行为伦理学(New Behavioral Ethics)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化伦理学”(Econoethics,这个英文术语是我发明的,用来指称新行为伦理学),它是经济学的最新形式,即行为经济学进入伦理学领域的结果。
这一新的经济化伦理学,认为不需要再用传统的哲学伦理学来研究伦理问题。我认为这是错的。行为经济学是如何看待经济伦理问题的?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明确提出,所谓行为经济学,就是把心理学强力注入的经济学。用这样的经济学来看待伦理学的方法就成为行为学的伦理学,或者说经济化的伦理学。行为经济学在把心理学注入到经济学时,也保留了很多原来数理经济学的内容,另外也采用一些生理学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样综合的方法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的行为,从而选择背后的一些生存逻辑。
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主张,如果能够考察一下对于普通人,是怎么给他们选择方案的,各种选项怎么给出的,就可以断定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的趋向。
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还主张,我们应该有别于传统的标准经济学。按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的说法:行为经济学最好的方法是与标准经济学相对照。在标准经济学中,我们假设人们是完全理性的,这意味着他们总是以对他们最好的方式行事。相比之下,行为经济学并没有对人作出太多假设,不是从人们是完全理性的观点出发,而是把人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中来检查他们是如何作出决定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发现,人们的行为往往不像从完全理性的角度所期望的那样,即人们的行为与预期不同,而且往往是非理性的。这也常常导致人们对公司应该如何创建、政府应该做什么、当然还有个人应该做什么等产生不同的看法。
行为经济学家在提出这种主张时,显然已经进入伦理领域。他们声称,通过小规模的干预(通常包括改变选项的呈现),我们可以更好地辨别如何促使人们作出更好或更伦理的选择。
虽然关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文献数量庞大,但对这种方法进行持续和系统的伦理分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非应用伦理学家与经济伦理学家都对这一重要的新领域的这些假设、方法和结论缄口不言。
经济化伦理学的基本假定
杜克大学有教授专门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现在提出的新的经济学就是行为经济学,有别于传统的标准经济学。传统经济学认为一切都是可以计量的;新的经济学则认为,我们是无法断定的,而是需要进行实验的,这样才可以发现人背后的行为逻辑。他们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断定人的选择趋向。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所作的选择并不是理性的,如果我们能够对于他们这样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背后的逻辑有所了解的话,也许我们通过设计,比如政府或者其他公共部门进行设计,让人的行为变得在伦理上更加可取。这样的行为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喜欢做实验,他们通过给予人选项的方式专门进行实验,来观察选项给得多和给得少会对人的选择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以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方式给出选项,是否可能也带来不同的后果。
从中可以看到,现在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家)所做的事,已经不是传统经济学家所做的事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深入到伦理学领域,甚至认为可以比伦理学家做得更好,通过这样新方法,可以知道人的理性、人的选择的含义。我认为,哲学家以及未来的哲学家会发现,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现在很少有人对经济化伦理学进行批判,因此,在这里,我要对经济化伦理学所做的研究加以批判。他们认为通过给予一些旁敲侧击,或者给予一些小的诱导,就可以使人们作出更好的理性选择。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美德伦理学重点观察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这一学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的个性实际上对其行为和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批判之前,我再把经济化伦理学的基本假定总结一下,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把经济学和伦理学(更多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第二,在人的行为背后,有着根植于心理学或生理学机制或逻辑上存在某种普适性的法则。第三,可以通过实验来了解这样的法则,了解的目的是让人做出更加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第四,通过给予某些诱导,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即让人的行为更加符合伦理学原则。
对于经济化伦理学的八大批判
我对于经济化伦理学的批判,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反对意见。
第一,经济化伦理学只是注重如何,而不是为何。经济化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兴趣来构筑一个全面的有关人的行为伦理学,他们都是从非常小的狭隘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们所做的都是关于细枝末节的问题的实验,比如有关杯子价值的著名案例。而像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更多是从人的生命的大目标角度来看问题的,有了这样的目标,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统领在目标之下,并希望为这个目标服务。这才是标准的哲学思考问题的方法。
第二,经济化伦理学误解了理性。所谓理性,亚里士多德提出有两种理性,第一种是逻辑理性,也称形式理性;第二种是体验理性,也称经验理性。经济化伦理学注重逻辑理性或形式理性,而忽视了经验理性。例如,他们认为从众是非理性的,但如果一个人在旷野迷路,十分饥饿,却又不知什么可以果腹,那么当他看到有一群熊在坑中吃蛆虫,于是他也跟着吃蛆虫。这种从众就绝不是非理性的,相反,恰恰是理性的。
第三,经济化伦理学依赖于某个简单狭隘的分析场域。例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化伦理学家都重视风险。风险更多由这样一些机构来考虑,比如银行要考虑自己的风险,保险公司专门对风险进行计价推出产品。经济化伦理学所做的实验实际上并不反映生活当中更多的问题,因为生活中很多事情与风险并没有关系。比如,今天花时间是写作还是看剧,这实际上与风险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个选择而已。风险并非许多事情决策背后的重要因素。
第四,经济化伦理学中的行为选项是设计出来的,具有误导性。平常,我们的行为选项是自己给出的,不是他人给出的。有经济化伦理学家通过实验得出“选择瘫痪”的结论,即太多的选择导致人们不知所措,展现了人们行为的非理性。但实际上并不是人在给出很多选项之后,必然会出现“选择瘫痪”,也不能证明人们是非理性的,人们可能有更多想法或其他选择。其实,这背后存在一个更大的伦理问题,即人们到底愿意花时间做什么,这样一个目的性取向决定人们日常的很多行为。
第五,经济化伦理学是寄生在其他的伦理思维形式之上的,也就是说,它本身缺乏独立的伦理学思考。比如,美国经济化伦理学家经常涉及器官捐赠问题,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一些诱导方式使捐献器官的人更多一点。而事实上,像器官捐献等很多问题是重要的伦理问题。
第六,经济化伦理学依赖细小琐碎的实验,零敲碎打,缺乏系统性。研究人员设计出任何碰巧引起他们兴趣的实验,然后声称在选择的本性上有重大的发现。例如,经济化伦理学家经常让被实验者回答他们是否愿意马上就买东西,根据他们的姓在字母表当中的排序,发现越是排在后面的人,往往更愿意、更着急买东西。从这样琐碎的分析当中,很难最后得出某种综合的宏观的伦理学说。更何况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看法,既然禀性非常急躁,就应该加强修养,变得心定气闲,这样可以改造个性。
第七,经济化伦理学倾向于把人的决定和行为还原为脑模块、情感系统或心理图式,而没有考虑到伦理有其自主性,这种伦理自主性或奠基于人的自由,或奠基于人的行为和实践思维的独特性质。
第八,经济化伦理学只在微观上研究人的选择、决断和行为,而不认可中观或宏观因素的作用,这是激进且错误的。在美德伦理学看来,人的个性会对人的选择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美德伦理学传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并且纠正经济化伦理学的错误。(蒋乐整理)
提
问
问:衡量描述性研究做得好与不好,可能有一种社会科学的角度。经济化伦理学家承认自己所做的研究是描述性的研究,还是规范性的研究?
金黛如:这些人实际上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因为他们已经让政府根据他们的研究作出一些政策制定方面的调整。比如在捐献器官问题上,通过一些诱导,可以让人们按照比较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作出决断和行为,显然他们已经超出了单纯描述性的层面,甚至进行干预了。实际上,他们缺乏一些规范的标准,对于一些前提并没有进行分析和设定。
问:经济化伦理学家为什么会提出他们可以代替规范伦理学家?他们这样的研究可以代替哲学伦理学吗?
金黛如:当我们讲新的经济化伦理学的时候,原来也是有旧的经济化伦理学,比如说,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当中就有这样的蕴含,像弗里德曼在研究当中加入了心理学,进一步强化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的观念等。因此,经济化伦理学家认为在此当中进行了规范性分析,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的研究可以代替传统的规范性研究。一些公司也确实采用了经济化伦理学的建议。但是,就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研究缺乏规范性标准。
问:您认为,在经济化伦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中,选择是非理性的。那么,传统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化伦理学,对理性的定义和非理性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金黛如: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并不认为所有决策都是理性的,很多时候我们决策当中也有感情因素。但是,即使有感情的选择,也不等于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没有一个纯粹的一以贯之的定义,像经济化伦理学家作出的理性或非理性判断,纯粹依赖于形式逻辑。实际上在这之外,体验性或者说经验性的理性同样重要。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非常强调经验以及自己实际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可以说这更为重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编辑:冉玲琳
经济化伦理学,确切地说,是一种愈来愈使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伪伦理经济学”形态,它沿袭的仍然是“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西方经济伦理学范式。它的实质是一种用诸如心理学这样的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经济学,并将心理、生理等因素强行道德化,进而转嫁或嫁接到伦理学,但其结果却不是经济伦理学,只是看着像而已,所以可以称之为“伪伦理经济学”。
作者通过美德伦理学的视角对其加以批判,也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的一个新动向,可以称之为“德性经济学”,它有别于从心理学以及心理伦理学的视角。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9 22:54
【案例】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逻辑的人?
一、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人的思维系统说起。
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通常用到两套不同的思维系统: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它们虽然没法完全分割开,但在不同的场景下,其中一个会起到主导作用。
请你先跟我一起想一想,下面这些场景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吗?
第一个场景
饭桌上,一个朋友谈起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你心里暗暗的想,“我不就是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吗?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应试教育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个场景
你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长得很帅,后来发现你们竟然是大学校友,还居然是老乡,顿时好感倍增。他是个基金经理,于是你马上就买了一些他管理的基金。
第三个场景
到了双十一网购节,同事们谈论起打折信息和自己买的东西。你也开始刷某宝,看到同事推荐的东西销量很大,果断入手。半年过去了,才想起这个东西你只用了一两次。
这些场景,你觉得自然吗?即使还没发生在你的身上,也很常见,对吗?那么,请你思考一下,这个场景中的“你”,正在用什么思维系统呢?
答案是,直觉思维。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思维活动,但都是不费力的。
这两套思维系统中,直觉思维系统,是无意识的,不费力的;而逻辑思维系统,或者叫理性思维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要进行推理。
在著名的《思考,快与慢》、《影响力》等书中,大量研究和实例说明:直觉思维非常常见。我们依据生物的天性本能,依据社会生活积累的经验,形成了种种直觉,它们能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判断,节约认知资源,提高认知效率。但直觉经常会出错,也容易被他人利用。
二、 认知偏差
多年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一直在研究:人们在直觉思维系统的主导下,到底有哪些不理性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认知偏差。
目前已经研究出了上百种。今天我会介绍6种最常见的认知偏差,让我们来一起反思,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没有被这些错误的直觉误导?
【过度自信效应】
第一个认知偏差叫:过度自信效应。
是说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认知、判断和能力过度自信,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最普遍的认知偏差。
1981年,心理学家欧拉斯文森做过一个著名实验,让被测者评估自己的开车技术,还让他们估计一下自己在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当中的排名。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为自己排在前50%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只可能有50%的人会排在前50%,对吧?但有82.3%的人认为自己的开车技术排在前50%。这说明,很多人对自己过度自信了。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股民们在进入股市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会赚到钱,但调研显示超过50%的投资者,自开户以来就一直是亏损的,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自信,高估了自己对于市场信息的把握程度。
还比如我们身边那些抽烟的人。虽然吸烟是引起肺癌的重要原因,甚至有研究认为重度吸烟者患上肺癌的机率是不吸烟者的5.7倍,但调研显示,大多数烟民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不容易患上肺癌。
当然,人们过度自信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就发现,能力欠缺的人,比起真正有能力的人,尤其会高估自己,并且还有拒绝承认的倾向。这后来被称为达克效应。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当人们评估自己智商的时候,平均来说,男性倾向于高估自己,女性倾向于低估自己。
你呢?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的呢?
回想开头的例子。在应试教育下成长的很多人,如果依赖直觉,也可能过度自信。但如果用逻辑思维,就需要想一想,应试教育教了自己什么?没教什么?
很多国家和机构都在研究:21世纪的人才到底需要什么核心能力?美国主流的是“21世纪技能”框架,提出最核心的能力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欧盟提出了八项核心能力。中国主流的应试教育可能并不注重这些能力的培养,而我们可能也欠缺这些能力。
只有运用逻辑思维分析这些现状,才能促使我们去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学习和弥补这些能力,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成长。
【向上:信权威】
第二个认知偏差叫:盲信权威。
请你思考一下,如果你的上级命令你去操控按钮,电击别人的身体,你会照做吗?
你可能认为,不会。但耶鲁大学教授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证明,当人们处在这样的真实场景中,很多人都会盲目的相信权威。
这个实验要求被测试的人在研究员的指令下,向另一个房间里答错题的学生施加电击作为惩罚,但他们不知道对方其实是演员,也不知道电击装置是假的。结果呢?无论这个可怜的“学生”如何苦苦哀求、厉声惨叫,即便一些被测试的人感到焦虑或痛苦,但超过50%的被试者都会按照研究员的指令实施电击。尽管这个实验后来也遭到了一些伦理和试验方法上的质疑,但这个实验后来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下反复进行,结果相差无几。
你可能会想起人类历史上,实施种族屠杀的普通军官或士兵,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反复强调,“我只是服从命令”。这解释了“平庸的恶”——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导致反人性、反人道的罪恶。
即使情况没有这么极端,想想你在工作和生活中,会有哪些盲信权威的情况呢?例如,你会认为老板的判断一定是对的吗?已经功成名就的师兄师姐给你的建议,你会全盘接受吗?你会本能地觉得有名校光环的毕业生一定比普通学校的学生能力强吗?如果吃了医生开的药觉得不舒服,你会不会觉得医生一定可信,还坚持服药呢?
当然,人们获得信息,社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权威意见,但盲目相信权威是有问题的。运用逻辑思维就会去判断,什么样的权威更可信。
【向外:信大众】
第三个认知偏差叫:盲信大众。
也就是从众效应,是指人们倾向于做很多人都做的事,或相信很多人相信的事。
现在有一个慈善团体问你,“我们正在为心脏协会募款,你愿意捐赠一点儿钱来支持心脏移植手术吗?”假设这个信息是真实的,请暂停一秒心里想一想,你会愿意捐钱吗?捐多少钱?
现在,在你开口前,他告诉你,刚才已经有5000人捐款了,平均每人捐了400元,你会怎么办?如果你刚才是不打算捐款的,你心里的决定会变化吗?如果刚才你打算捐款,捐赠的数额会发生变化吗?
这是美国曾经做过的一个实验。在没有提及已经有人捐款的情况下,只有47%的人同意捐款。但在展示了捐款者名单和捐款数额后,73%的人顺从了捐款的要求。
回想开头的例子,你会因为同事和很多人购买某个东西,就跟着买吗?如果运用逻辑思维,你会考虑自己实际的需求、理财计划、消费倾向,甚至对环保的理念,再决定要不要购买。
类似的,关于选专业,选工作,要不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离婚,这样一些人生的重大决策,如果盲目从众,很可能作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到底该怎么做?你需要用逻辑思维去判断。
【向内:信喜好】
第四个认知偏差叫:盲信喜好。
也就是说,人们会更相信自己喜欢的人或事物。这往往包括外表有魅力的,和自己相似的,和自己有关的,自己熟悉的,会恭维自己的等等。
回想一下,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你对哪些领导人印象比较好?你可能会想起现任的加拿大总理,法国总统,或者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但是你了解他们的施政纲领或政治观念吗?如果不了解,你对他们的好感从何而来呢?
或许更靠谱的答案是,他们长得很帅。
政治家的长相,会多大程度影响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这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给学生们展示一些陌生政治家的人脸照片,让学生根据照片判断他们的能力高低。结果发现,那些在实际竞选中胜出的政治家,其中70%在照片评选中也获得了高分评价。在针对不同国家选举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结果,外表有魅力的候选人得到的选票往往更多。
回想开头的例子,人们因为经理长得帅、因为他和自己有校友或者老乡这种令人喜爱的亲近关系,就把钱交给他去打理,这就是盲信喜好。如果运用逻辑思维,你需要了解他的投资表现,具体投资领域,基金的风险性,自己的风险偏好等等。
类似的,在工作中,你也不应该只相信自己喜欢的同事或下属的意见,而是应该就事论事地分析具体情况。
【确认偏差】
第五个认知偏差叫:确认偏差。
它是说,人们倾向于捍卫自己现有的信念,抵制不同的看法。而且人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会只选对自己有利的,忽略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甚至扭曲记忆,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只看见自己想看的。
确认偏差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1989年巴西航空254号航班飞机飞往错误方向,导致燃料耗尽后迫降,造成13人死亡。调查结果发现,这是由机长误读了航向数据造成的。但当时已经有种种迹象显示,飞机在飞往错误的方向,但由于机长心里已经有自己认定的方向,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可能会错,就不断地合理化自己的决策,忽略显示方向错误的证据。
回想一下你的生活。在阅读文章的时候,看到那些说到自己心坎里的话,是不是特别认同?而一些你不认同的观点,会不会只看题目就不想点开了?对星座和算命的预言,会不会只找那些符合预言的现象去印证?在人际关系中,一旦形成第一印象不喜欢一个人,会不会总是看到他的缺点,而对他的优点视而不见,或者觉得他做好事也是动机不纯?
确认偏差,会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两极化,人们更容易相信没有经过证明的观点,更坚信早期获取的知识或信息,相信事物间虚幻的联系。如果运用逻辑思维,你会综合考虑不同角度的证据,作出公允的判断,会用更开放的心态吸收新的信息,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会更快地成长。
【安于现状偏差】
第六个认知偏差叫,安于现状偏差。
Status quo bias,是说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常常对变化表示担忧。除非利益明显大于风险,否则很多人不倾向于改革。
回想一下,你是不是会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中,不开心的感情中,很纠结的状态中,同一个熟人圈中,待很久而不主动寻求改变?
上面这六种认知偏差,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会有相似性,或者可能同时发生。例如,当人们盲信大众、喜好,也可能同时陷入确认偏差,不断固化原有的观念。又例如,陷入确认偏差的人,深层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过度自信了。
总的来说,到底属于哪种认知偏差?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认知偏差的含义,以及它们背后的问题。
三、为什么逻辑思维更可靠?
了解了这6种认知偏差,你应该也就明白了,直觉思维是多么的不可靠。很多人日常思考一件事,却总是直觉先行,难免陷入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最终误导自己的决策。
而破解之道,就是主动训练我们的逻辑思维系统。这意味着要尊重事实依据,相信严谨推理的结果。
逻辑思维具有严谨和理性的特点,这是工作中必须的素质。我们都知道国家公务员考试和管理类硕士联考都要考“逻辑”这门科目。那一道道的、各式各样的逻辑推理题,简直就是脑细胞的天敌。
为什么要考察逻辑思维能力?因为国家机关或是企业的管理职位者,必须思考严谨,科学判断,作出的决策要有理论依据支撑,经得起论证推敲,才能让自己安心、让他人信服。
不仅如此,在日常工作、生活和沟通中,符合逻辑的言论和决策,更能说服他人,也才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不矛盾,反而紧密相关。
逻辑思维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直觉,不被直觉操纵。但具备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都只运用逻辑思维。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可能因为更深刻理解爱的内涵和意义,而更容易被感动,具有更强烈的情感。
以上内容选自郭兆凡主讲的《极简逻辑课》。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5oH-h28foLBT5qZstbaZw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11 22:17
【案例】【案例】避免“德西效应”蔓延
“德西效应”含义
德西效应(Westerners effect)认为适度的奖励有利于巩固个体的内在动机,但过多的奖励却有可能降低个体对事情本身的兴趣.降低其内在动机。
著名实验
心理学家德西在1971年做了一个专门的实验。他让大学生做被试者,在实验室里解有趣的智力难题。
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的被试者都无奖励;第二阶段,将被试者分为两组,实验组的被试者完成一个难题可得到1美元的报酬,而控制组的被试者跟第一阶段相同,无报酬;第三阶段,为休息时间,被试者可以在原地自由活动,并把他们是否继续去解题作为喜爱这项活动的程度指标。
实验组(奖励组)被试者在第二阶段确实十分努力,而在第三阶段继续解题的人数很少,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减弱,而控制组(无奖励组)被试者有更多人花更多的休息时间在继续解题,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增强。即奖励组对解题的兴趣衰减得快,而无奖励组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仍对解题保持了较大得兴趣。
实验结果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兼得的时候,不但不会增强工作动机,反而会减低工作动机。此时,动机强度会变成两者之差。人们把这种规律称为德西效应。
可见,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即内感报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质奖励(外加报酬),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参与者的吸引力。
“德西效应”的应用启示
“德西效应”与学生奖励
当学生尚没有形成自发内在学习动机时,教师可以从外界给以激励刺激,以推动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奖励是必要和有效的。但是,如果学习活动本身已经使学生感到很有兴趣,此时再给学生奖励不仅显得多此一举,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一味奖励会使学生把奖励看成学习的目的,导致学习目标的转移,而只专注于当前的名次和奖赏物。
因此,作为教师,要特别注意正确使用奖励的方法而不滥用奖励,要避免“德西效应”。
老人与喧哗不止的孩子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奖励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了。
讨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及其操纵
人的动机分两种: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如果按内部动机去行动,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如果驱使我们的是外部动机,我们就会被外部因素所左右,成为它的奴隶。老人的算计很简单,就是将孩子们的内部动机———“快乐地玩”———变成了外部动机———“为美分玩”,而他操纵着外部因素,所以也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当有一天满足不了孩子的愿望了,自然就有办法对付这些顽皮的孩子了。
德西的实验结论以及趣闻轶事对我们改进教育方式很有启迪,作为家庭教育,是孩子教育的一部分,家长首先应该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孩子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激发孩子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动机,帮助孩子获得成功和乐趣;其次不能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看待成长的下一代,尤其一些经商的家长,总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这在教育孩子学习的问题上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会使孩子迷失方向,感受不到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的成功体验,孩子在学习上怕吃苦,干任何事都和利益挂钩,在集体里无服务意识,怕吃亏,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美德中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具备,就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达不到。
再者,家长的奖励可以是对孩子的学习有利的,诸如买书,或体育器械,对他的心身健康有帮助,如果奖励一些诸如手机之类的东西,引起学生以此在同学之间炫耀、攀比,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良影响,有些学生上课铃声不断,就像我前面列举的那位同学手机的彩铃声,她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中学生玩手机带来的弊端远远不止这些。听说,就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学生是不准带手机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谈到,在美国,学生如有不当的东西带进学校,如手机,学校一律没收,并不再还给学生。
相比之下,我们也没收,但没收后要求学生家长来校认领。曾经一名高三年级的家长认领时还跟老师说,你们学校管得太严了,现在都啥时代了,我的孩子在初中就给他买了手机……
道德教育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好,家庭教育的偏差是不是也难辞其咎?
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以后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一愿望能不能实现,就看我们为孩子的成长做了什么,更要看我们是怎样做的。切记,勿让“德西效应”在教育中滋生蔓延。
引起“德西效应”滋生蔓延的因素
不当的薪酬奖励
薪酬是企业管人的一个有效硬件,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情绪,但是每一个公司都不轻易使用这件精确制导武器。如果使用不好,可能会带来“德西效应”,不仅不能激励员工,还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在IBM有一句拗口的话:加薪非必然!IBM的工资水平在外企中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但IBM有一个让所有员工坚信不疑的游戏规则:干得好加薪是必然的。
1996年初IBM推出个人业绩评估计划(PBC)。PBC从三个方面win(致胜)、executive(执行)、team(团队精神)来考察员工工作的情况。IBM薪酬政策的精神是通过有竞争力的策略,吸引和激励业绩表现优秀的员工继续在岗位上保持高水平。IBM独特而有效的薪金管理,能够通过薪金管理达到奖励先进、督促平庸。IBM将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相互挂钩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德西效应”的产生,这种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高效绩文化(high performance culture)。
一个私人企业老总每每向人抱怨自己的高级人才大量走失:“我已经连续给他们涨了很多次工资了,怎么看不到一点成效呢?”就薪金这个角度来看,原有的外加报酬如果距离人才需要满足的水平太远,直接激励的原有强度又不足,必然导致“德西效应”。如果人才觉得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都不尽如人意,即使外在报酬不断增加,也无法达到他的预期,转投他处是必然的结局。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的表彰评比活动过多过滥,并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评比表彰往往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树立典型、弘扬先进的作用。如果对干部职工完成了应完成的任务、履行了应履行的义务、遵守了应遵守的规章制度这些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一般行为,当作突出表现大张旗鼓的进行表彰,甚至为了照顾情绪,拿表彰送人情,“排排坐,吃果果”,对今后的工作就可能出现负效应。
人们就会把这些一般行为当成是一般人难以做到、应是“积极分子”的专利,做到了就应该受到领导的褒奖,如果得不到就会失去心理平衡和工作的动力。可以说,这种送人情的表彰是一种短视行为。当然,作为领导,应该注意发现每一位下属的“闪光点”,在适当场合恰如其分地进行表扬激励。但必须注意,这种表扬是有限度的,是在平时工作中随时进行的,真正树立典型。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把应承担的义务看作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做不到应该受到严厉批评,做到了不应当“邀功请赏”,只有做得好才会立功受奖。
不当奖励
奖励不可以随便泛滥,因为当一个人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给他提供奖励结果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他内在的吸引力。在某些时候,当外加报酬和内感报酬兼得,不但不会使工作的动机力量倍增,积极性更高,反而其效果会降低,变成二者之差。
以教育为例,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广大教师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认识,对“学习过程是学生积极主动自主构建的过程”等新的课程思想有了认同。于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为了调动学生兴趣采用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确实收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一些小学教师喜欢采取物质奖励的形式:给学生准备了粘贴画、有的准备了小风车、还有的直接把香甜的水果奖给学生。于是,课堂上出现了空前的气氛高潮,学生个个精神抖擞,争先恐后,场面热烈异常。这里,我们教师的这种为教育而奉献的精神着实可贵。为了讲好一节课,我们的教师无怨无悔地掏了自己原本就不丰厚的腰包。这种物质的投入也确实换来了课堂上学生的兴高采烈、情趣盎然。但当我们冷静之后,透视这精彩的背后,就不难发现物质奖励的种种弊端。
兴趣不持久
兴趣不持久是“德西效应”的孪生姐妹。“德西效应”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教学中,培养个人积极主动、持之以恒的兴趣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仅靠物质的刺激远远不够。虽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由物质刺激所激发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淡薄的,也是短暂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物质奖励所激发出来的学生学习兴趣只能是暂时的,无法保持持久。
思想不集中
不要随意奖励学生,因为这很可能导致他们思想不集中。因为当教师对学生实施物质奖励的时候,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学生对物质的奖品会更感兴趣。因学生急切地想得到奖品,就要迫不及待地争取“先机”,而使其不能很好的集中思维、组织语言,导致思维深度不够,学习效果不佳。而且当获奖学生拿到奖品后,由于其自控力差,常常是马上欣喜于自己所得,开始专注于奖赏物,摩挲把玩,甚至想立刻品尝那诱人的瓜果呢!而其他学生也会把视线和思维降落到奖赏物及获奖学生身上。教师的问题在此时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还需要教师再多费一番工夫来组织教学呢!
心理不平衡
课堂中教师要实施物质奖励,奖品的数量往往是少量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学生才有幸获得。但课堂中由于教师给学生发言的机会的不均等造成学生所获奖的机率也极其的不均衡。应该说许多没得到奖的学生也具备获得奖品的能力,只是教师没给机会。因此我们看到了在奖品发放完了之后课堂上马上有了唏嘘声、哀叹声或不满声。
得到奖品的自然是乐滋滋了,没得到的呢,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了。有甚者还表现出极度的不满,怨老师对自己的不理睬,怨获奖学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造成学生情绪的不快,心理的偏激。甚至有的学生还对此产生逆反心理,无论教师拿什么作奖都表现得无动于衷,“我不稀罕!我也不学了!”效果真的不敢恭维。
欺骗色彩奖励
课堂教学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教师声情并茂的渲染气氛说谁有好的表现教师将有精美的礼物送给他。可是当学生表现突出时,教师拿出的奖品却是用彩纸剪出的苹果、桃子或者是刻得简单的小花,对学生而言毫无吸引力,毫无用处。获奖学生甚至是极不情愿的领取了奖品,情绪表现是大失所望的。
在第一个学生受到这种欺骗后,其他学生的情趣也深受打击。这样的物质奖励不能激起学生兴趣,可以说是费时低效的,情绪调动显得十分牵强。
注重物质所得
学生会过于注重物质所得,影响人生观的确立。课堂教学中教师频繁使用物质奖励会导致学生把学习看成是带有物质所得的一种活动,会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向,把获奖看成是学习的目标。久之,学生会过于看重物质的获取。学习、做事都带上了物质索取的色彩,成为有偿活动而不是自发行为。最终会影响其正确人生观的确立。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只指望靠表面看得见的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兴趣,那就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对脑力劳动的真正热爱。要力求使学生亲自去发现兴趣的源泉,使他们在这种发现中感到自己付出劳动并得到了进步。这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兴趣来源。
课堂教学中,如果未知本身已经使人感到很有兴趣,此时再给奖励不仅显得多此一举,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提醒教师:课堂教学中要学会正确使用鼓励方法而不要滥用奖励,要避免产生“德西效应”。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To2NMmF7tKm_F5k9J28eA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1-22 20:49
【案例】
海德格尔:哲学是一项精神使命和一种心理治疗方式
哲学这个领域并非没有其他杰出的竞争对手,但在德国高深莫测的哲学家竞争史上,马丁·海德格尔在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总的胜出者。
他的散文杰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其文笔艰涩程度与复杂德语复合词的绝对数量都几乎无可匹敌,比如作者创造的 “Seinsvergessenheit”(存在之被遗忘状态)、“Bodenständigkeit”(根基深厚)和“Wesensverfassung”(本质情状)。
乍看之下它们让人不解甚至不快,但我们逐渐会对这种风格产生好感,并了解到,在其飘渺的表面之下,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关于生活意义的一些简单、有时甚至显得朴素的事实,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和通往自由的途径。我们应该把它们当回事。
他出生德国农村,在很多方面他保留着德国农人风格,比如他喜欢采蘑菇,在乡间漫步,晚上早早上床。他讨厌电视、飞机、流行音乐和加工过的食物。1889年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天主教家庭,在发表了《存在和时间》之后他成了学术明星,但在1930年代失足入了希特勒的道(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后果极其严重。
他本希望纳粹为德国重建秩序并带来尊严,为切合当时的气氛,他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发表了一些言辞激烈的演讲,试图禁止犹太学者在该校任教。我们大可宽恕他这一时期的疯狂,因为他已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并以他的方式在之后几十年里面改邪归正了。德国1945年战败后,他在消灭纳粹委员会前受审,1950年之前被禁止教书。令人惊奇的是(这是他的思想有吸引力的明证),他的职业生涯逐渐复活了,尽管他更多的时间都呆在他远离现代文明的林间小屋里,直到1976年去世。
他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帮助人们活得更有智慧。他希望我们更勇敢地接受一些事实,过更充实、更深思熟虑、更快乐的生活。哲学不只是学术活动、就像它对于古代希腊人那样,哲学是一项精神使命和一种心理治疗方式。
他断定现代人饱受一些新的心灵疾病的折磨:
一、我们已经忘记自己还活着
理论上我们当然清楚这一点,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未与存在的绝对之谜保持好联系,海德格尔把这个谜称作“das Sein”或“存在”。他的哲学中相当部分都致力于把我们从存在的陌生感中唤醒,即我们生活在看似沉默、陌生、荒凉的宇宙中一个不停旋转的行星上。
生活中偶尔有些时候,可能是夜深人静、或者整天独自一人卧病不起、抑或漫步乡间之时,我们才会遇到万事万物那种怪异的陌生感;为什么事物是这样存在着的,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而不是那儿,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棵树或者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为了捕捉到事物少有的与其通常状态略有不同的时刻,海德格尔用大写的Mystery of Being(存在的神秘)来描述它们。他的全部哲学都致力于让我们领会这个非常抽象但很重要的概念,并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它。
对海德格尔来说,现代世界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机器,让我们从存在的美妙天性中分神。它不断地把我们拉到具体的任务中,用信息淹没我们,打破沉寂,它不希望我们独自一人,这部分因为我们意识到存在之谜有让人恐惧的一面。如此一来恐惧会笼罩我们,我们意识到所有那些根深蒂固的、必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要看情况的、愚蠢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是那个,和这个人恋爱而不是那个,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死掉却还活着……很大一部分日常生活都让这些奇怪的、让人不安但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出路。
我们真正要避开的是直面“虚无”,即使不说德语的人也会因这个海德格尔关键词(das Nichts)感人至深而心有戚戚,虚无是存在的另外一面。
虚无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最终将吞噬我们。但海德格尔坚持认为,要把生活过好只有接纳虚无和存在其短暂的特点,就像某个夏日傍晚,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带,黄昏的微光隐入黑暗中,此时我们会做的那样。
二、我们忘了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透过代表狭窄自身利益的棱镜来看世界。我们的职业需要会影响我们注意和烦心的事情。我们把其他人和自然当作方式而不是目的。
但偶尔(同样的,漫步乡间特别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能移步走出我们的狭小天地,用更大的格局看待与其他存在的事物的联系。我们可以感受到海德格尔所讲的“存在的统一”,意识到我们和树皮上的瓢虫,那块石头,还有那片云彩在当下都存在着,并且因存在的基本事实从根本上统一起来,我们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海德格尔重视这些时刻,希望我们把它们作为起点变得更宽宏大量,克服疏远和自私自利,更深刻意识到我们在“虚无”占据我们之前仍保留一些短暂时光。
三、我们忘记要自由,要为自己而活
大多数人都不是很自由。海德格尔独特地表述为,我们从出生开始是“被扔到世界上来的”:被扔到一个特别的、狭隘的社会环境中,被一些死板的观念、过时的偏见和实用的必需品,而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东西所包围。
这位哲学家希望帮我们通过理解其特征来克服这种“被抛”的感觉。我们应理解心理的、社会的和专业上的偏狭,然后超越它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我们这么做就可以沿着经典海德格尔的路线从不真实走向真实。我们将从本质上为自己而活。
海德格尔认为,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令人沮丧。我们向存在的社会化的、肤浅的做法投降了,他称之为“人人自我”,与“我们自己”相对。我们追随大城市的报纸上、电视上听来的那些闲言,海德格尔厌恶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合理认真地关注我们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可以帮我们从“人人自我”拉出来。只有意识到他人不能从“虚无”中拯救我们,才能不为他人而活,而不用操心其他人想什么,不再花费我们的生命能量中的绝大部分给从开始就没喜欢过我们的人留下好印象。对“虚无”的“焦虑”虽然让人不舒服,却能拯救我们:意识到我们“向死而生”是通向真正生活之路。在1961年的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被问到我们如何重归真实,他简洁地回答,我们只需要在墓地里多呆会儿。
四、我们把他人当作物品
多数时候,我们无意中把他人当作海德格尔称作的“设备”:“das Zeug”,仿佛它们是工具,而不是“他们自身的存在”。
接触伟大的艺术中可以治疗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艺术作品可以帮我们暂时放下自己,去认识其他人和事物其独立的存在。
海德格尔在一门课里阐述了这个想法,这门课讨论梵高画的一双农夫的鞋。通常我们不会注意鞋子,它们不过是我们要应付的另一个“设备”。但当它们在画布上呈现,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它们,仿佛是头一回因为它们本身而注意到它们。
面对其他一些大艺术家打造的天然或人为的世界时,同样如此。由于有艺术,我们对超越我们自身的存在感受到一种新的“牵挂”。
五、总结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意图和训诫很清晰明了那是假的。不过,他告诉我们的东西不仅吸引人、有智慧,而且出奇地有用。虽然语言用词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要说的很多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只不过需要他那种怪怪的散文体来提醒、鼓励我们去认真对待它们。
我们心里清楚,是时候克服我们的“被抛”的感觉,更加意识到日常生活的“虚无”,为了我们自己去逃离“闲言”的束缚,去过“真实”的生活了——再加上一点墓地的帮助。
编辑:何林
https://mp.weixin.qq.com/s/xuf7KfLF849GiJaP4LQwlg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2-1 13:38
【案例】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
肖雪慧 2005-04-15
个人权利:正义理论的基石
——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开篇就表明他具有一种普遍的个人权利观。他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在这部巨著中,他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精心构筑起一个结构谨严、论域宏阔的社会正义理论体系,为宪政民主的价值基础提供了独特、精致而又有力的理论论证。这一理论认为,正义之于社会制度,犹如真理之于思想体系,因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个人对制度的支持义务以制度具有正义性为前提。什么样的制度具有正义性呢?罗尔斯立足于自然权利说,借助于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作为人们选择、评判和调整制度之独立依据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前者确认平等的个人自由,后者强调公平的机会和确保社会最低受惠值。在它们之间又依序提出自由优先、正义对效率和福利优先两个规则。自由优先意味着,自由是必须无条件维护的最高人类价值,它不可交易也不可因任何权衡而游移,自由只能因自由之故而被限制。这一规则在确认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就为政府行为划定了一道不得跨越、一旦跨越就堕入犯罪的界限。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则要求,所有机会应该公平分配,除非不平等有利于境况最差者。
这里简述的原则以及原则由以提出的方式,招致了许多批评。然而恰恰是这最易受攻击之处,显示了罗尔斯不同凡响的理性深度。
制度的优劣,深刻、广泛而又持久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社会契约论设想原初状态下自由平等的个人以立约方式选择用以规范社会制度的首批原则,强调了在关涉人们命运的问题上一人一票的平等参与权,彰显了从神圣的个人权利引申出社会终极规范的人权精神。罗尔斯在运用社会契约论时别有深意地对原除状态下的个人加诸无知之幕和相互冷淡的理性人限制。这些限制一方面使签约各方对自身状况、能力和具体目标一无所知而不可能选择偏向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由于相互冷淡的理性规定排除了选择原则时的越俎代庖而得以免于专断,使选择真正出自每个签约者的判断。这两点保证了原则的公正性和普遍性。如果缺乏这些限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境况和偏爱出发,原则将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只能凭借强力和诡计去决定。由力量和权谋角逐产生的原则偏私而狭隘,就如历史和现实中并不少见的那些强加给全社会的原则,决无正义可言。基于非正义原则的制度缺乏正义制度所具有的自我支持力量,它的支撑也就同它的不光彩出生一样,要靠暴力和欺骗。
从虚构的原初状态引出正义原则,使罗尔斯受到许多批评。然而,这虚构所具有的内在真实性却是许多可观察的经验事实不能望其项背的。其内在真实在于,它的普遍有效性经得起理性的反思。任何个人,只要具备对自己利益进行估计的理性能力,一旦置身于罗尔斯设定的这一情景,便处在了替自己选择的同时也就是替所有人选择,为自己这一代选择的同时也就是为以后各代选择的位置。他将不得不从普遍的立场出发,“不仅从全社会而且也从全时态的观点来审视人的境况”。诚然,人们会问,为什么基于普遍立场就一定会选择罗尔斯提出的原则?事实上,《正义论》一问世就伴随着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注重个人权利的诺齐克就尖锐批评着眼于确保社会最低受惠值的差异原则带有严格的平等主义倾向,将会导致赞成一种牺牲效率而保平等的原则。他还认为,这一原则与其说是关注个人,不如说是关注群体。他怀疑原除状态下的个人会如此选择。诺齐克的批评和质疑极具挑战性。然而罗尔斯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辩护。其一,差异原则表明深刻理解人类价值困境的罗尔斯在自由和平等这两大有冲突的基本价值之间进行平衡的努力。而作为自由主义者,他的这种努力是以自由优先为前提的。其二,如果从全社会和全时态的观点来审视人的境况,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落入最差境况,受无知之幕限制的个人首先关注的不是如何增大利益而是如何避免最坏情况。确保社会最低受惠值看起来注目于群体,但在深层,这一关注的着眼点却是群体中每个人的境况,它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可以共同分享的观念。从这里还可以看出,罗尔斯的原除状态设计隐含着他对人这一概念的独特理解。在罗尔斯的整个正义体系中,人是出发点,也是归宿。他说的人,既不湮没在诸如“阶级”、“人民”等形形色色的特殊范畴或集合概念中而变得子虚乌有,也不附着于某一群体上,非得靠着成为一条巨龙的部分才能获得某种价值感。罗尔斯的人,是作为独立的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而挺立的个人,但这挺立着的个人又因其目标、状况、时态不确定而具抽象特征。正是个人概念所包含的独立主体意蕴和抽象性,确保了由此演绎出来的原则是公正的和普遍有效的,它具有融通现实中不同的个人目标的亲和力,能把每个人的利益包含在一个互利互惠的结构中。因而,以个人为出发点的立场也是最广博的立场,相反,从整体出发的原则漠视个人权利,具有偏向占据社会有利地位的群体的狭隘性,运作起来往往维系着一种畸形社会结构:好处被一部分人享用,代价和牺牲由另一部分人承受,而且被选中来付代价作牺牲的往往是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因为这些人最缺乏保护手段来使自己不被牺牲。有关出发点的深刻哲理,或许是罗尔斯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之一。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2-1 22:06
【案例】
被忽视的先驱——边沁功利主义舆论思想阐释
原创: 徐蓉蓉 国际新闻界 2019-02-01
徐蓉蓉,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xrrcrystal@163.com。
本文受重庆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项目“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图像传播与视觉修辞”(项目批准号:2018CDJSK07XK08)资助。
作为经典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奠基者,边沁(Jeremy Bentham)从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原理出发来阐述其民主思想,他坚持“人民”在统治和被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体选民、多数人统治和公共利益(边沁称之为“普遍利益”)。然而,现代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论断是不现实的,群体中的个体并非总是以公共的善为向导(勒庞,2000;桑斯坦,2005;博曼,2006);它对人民过分关注而对少数精英和选举制度之外的权力与影响力关注太少(韦伯,2009;熊彼特,1999;萨托利,1993);它还忽视了媒体操纵和专家权力的当前问题(李普曼,2006;拉扎斯菲尔德,2012;哈林 & 曼奇尼,2012);甚至一些同时代的人士也认为:边沁赋予了人民过大的权利,存在多数暴政和舆论专制的危险(伯克,1998;J.S.密尔,1859;托克维尔,1997)。本文认为,上述对边沁及其经典民主理论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对边沁作品缺乏普遍而详细的关注,现代学者极少考虑边沁民主理论中的一个激进而重要的因素——公共舆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重新回到边沁所处的时代,从其民主理论出发去探究其功利主义舆论思想。本文发现,与多数传统理论家试图揭露和避免公共舆论的最大危险不同,边沁视公共舆论为民主社会的内在进步力量,并试图发挥其实现共同体福祉的最大优势,作为舆论研究的先驱者,边沁的舆论思想是现代舆论学研究不易察觉的理论端倪。
边沁基于舆论的功能提出的舆论观念似乎与传统舆论思想并无不同,与现代舆论理论也存在很大相似之处。但是,边沁舆论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从抽象的价值来阐述舆论不同(洛克,1983;卢梭,2003),他第一次从现实的个人利益出发来界定公共舆论,并使之成为真实存在的事实和促进和平改革的社会力量;他还创造了“公共舆论法庭”这一重要术语,提出将其作为公共舆论的实际运作机构,将公众的角色与选民的角色相媲美,这大大提升了公共舆论法庭作为一个与法院相匹敌的司法权威的重要性;为了充分发挥公共舆论的道德制裁力量,边沁还特别强调公开政府理念和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认为它们是将公共舆论法庭的道德制裁转为可见行动的制度基础,这表明边沁是早期的、狂热的监督国家的倡导者,边沁舆论思想的独创性和激进性远超同时代人士;从现实来看,边沁的功利主义舆论思想与当代舆论研究的诸多议题也有着重大相关性,如理性无知、多数暴政、信息失真、专家权力、媒体对信息的操纵以及公共领域的协商,等等。对于当代舆论研究的理论家和实证者而言,边沁的舆论思想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
一
公共舆论的渊源——确定的个人利益
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公共舆论是“最大程度上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意见”(Bentham,1989:68),它反映了共同体福祉,在最高程度上符合普遍利益。边沁预设了如下重要前提:首先,人是理性、自利的行为者,每个人“从根本上是利己主义的”,每一个理性之人只能代表自己而不能代表他人,因而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社会就是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组成,共同体的利益只有在被认为是构成其成员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时才确有意义,否则它只是个虚构体。其次,人的自利本性并不排斥他(她)具有利他动机的可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善和人的需求的增加,人会逐渐意识到他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存在,并将它们与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波斯特玛,2014:416-420)。最后,由于每个人的意见是由他关于自身利益的正确观念所决定的,因此,凭借利己又利他的个人动机,个人利益由个人自决将导致最佳的社会结果,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公共舆论必将符合普遍利益。边沁从健全理性的人性论出发得出的“个人利益从长远来看与他的普遍利益相一致”的假设成为其民主制度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引发了现代民主理论的强烈共鸣,也使边沁备受争议。
首先,理性的个人能否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边沁预见了公共舆论可能对下层阶级的不利影响,但他乐观地认为,人性中的利他动机会使得中上层阶级具有对下层阶级的不幸表示同感的可能(波斯特玛,2014:421),从而有助于下层阶级利益的实现。当代民意测验也肯定了边沁的设想:在公共生活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更有能力去为那些真正需要的多数群体谋利(卡普兰,2010:191)。但是,边沁并未寄望有能力的少数群体提供的公民教育的效果,因为与开明的公共舆论具有更大关联的是建立一个信息彻底公开的开放政府(Bentham,1983),它不仅能够对统治者问责,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正确认识自身利益的困难,这可以从开放的民主政府这一政治安排中得到保障。
其次,对个人利益的正确认识能否导向共同体的福祉?对于“共同体福祉”这一东西,政治理论家熊彼特(1999:372-374)直斥它根本就不存在。即便存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也在质疑边沁的假设,认为它过滤掉了公共舆论中个体和群体心理复杂多变的事实(勒庞,2000;莫斯科维奇,2003;霍弗,2011):人对个人利益的理解千差万别,对共同体福祉的认识也可能意指不同的东西,人们如何从中鉴别出反映普遍利益的公共舆论?作为糅合了感情和理性的复杂动物,在公共生活中,个人如何能够完全避免个人情感、多数人一时的观念或纯粹的个人利益,来为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让路?本文认为,上述批评仅仅是部分正确的,因为它们忽视了边沁所处的时代病症:17、18世纪弥漫于欧洲的企图哄骗的传统习俗和政治权威,正压制着个人理性力量的行使。虽然现代理论可以证明个人理性地理解共同体的利益所固有的困难,但是一个进步的理性主义者一定会捍卫边沁的立场,那就是引导人们摆脱对超验的历史神话的教义式服从,从现实的功利原理出发,运用自主的理性去反思和洞察共同体的政治与道德原则。因此,边沁论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运用了一套新的思维方法对现有社会进行激烈地批判,其目的在于检验现有制度的功用,并为其提供一套客观的评价标准。
最后,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可能存在的冲突?边沁提出的解决方式是遵从多数原则和流行意见,如果牺牲某些人的利益有助于达至共同体的幸福,那么这种牺牲就确有必要(斯科菲尔德,2010:55)。但是,边沁并不是在为私人道德提供建议,而是在为立法和政府艺术制定指南。边沁的意思是,从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的政治策略出发,立法者和民选官僚无权将自身偏好(边沁称之为邪恶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因此,边沁的立场是在政治上与传统、教条主义以及特权阶级战斗来捍卫理性(海萨尼,2011:44);作为一种公共哲学的功利主义,它为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提供了规范性引导,是公共生活而非个人行动的恰当指南(Goodin,1995)。
二
公共舆论的审查对象
——全面而彻底公开的政府信息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经典的民主理论家们常常将民主制度的负面价值归咎于多数暴政和舆论专制(伯克,1998;J.S.密尔,1859;托克维尔,1997)。边沁也密切关注了法国大革命,曾直言无政府状态是个怪物,民主体制是另一个(哈特,2015:75)。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不同,边沁相信民主制度的最大危险是来自少数统治者的邪恶利益的影响。边沁认为,在宪法制度内实现人民主权能够避免多数暴政,而在宪法制度内建设一个高度称职的政府能够避免少数人滥权。代议民主制就是这样一个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它通过选举和立法“剥夺统治者可能谋取私利的部分权力,但允许他们保留能够实现他们与被统治者共享目的的那部分权力”(Schofield,1991-1992:47),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使统治者有责任将自己的行为彻底向公众公开并为公众讨论,从而使其掌握的最高权力受到限制,这就为公共舆论评判和审查政府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
为了实现公开性的目标,边沁在《宪法典》中对政府机构的建筑进行了设计,即将首相办公室与部长办公室布局为月牙形,以方便接见公众,并设计了专门的公共等候室,以方便公众看见和听见办公室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在更为著名的全景监狱方案中,边沁将号舍布置为方便监视者时刻监视犯人,而犯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监视者可与每一个囚犯交流,而其他囚犯也对此一无所知;并鼓励公众参观全景监狱,这样,囚犯和监视者的活动又受到公众审查(Bentham,1983:441-450)。边沁设想,通过将统治者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自由地讨论政府行为,不受操纵的人民将变得越来越成熟,公共舆论也将越来越符合普遍利益。
然而,边沁似乎夸大了信息公开对公共舆论带来的好处,边沁没有进一步回答:在竭力愚民的政府体制下,如何形成开明的公共舆论?当代议民主制下的政府信息公开蜕变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公共舆论是否具有被操控的危险?现代民主实践似乎也在证明:受精英集团统治的民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公众参与的(熊彼特,1999:389),权力精英所掌控的权威机构正在通过对大众意见的渗透,逐渐成为官方意见和暗箱操纵者(米尔斯,2004:386,399)。并且,随着晚近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公共领域日益被政党、利益集团所操纵,信息公开成为政府政绩宣传、树立权威和政治家展示个人魅力和政党拉选票的场所(哈贝马斯,1999:234-235)。但是,纵观边沁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边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仅仅是一个监管的概念,即“它应该作为公众对国家不信任的监督机制来实施。”(Bentham,1994:581)他试图从制度设计的视角证明对政府的不信任是良好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主要好处是向公众提供关于政治问题的信息,而不是公众对理性讨论中形成的开明判断的贡献。换言之,与政府信息公开不一定带来公共舆论的开明相比,边沁更关注公共舆论本身的力量——廉洁性或不可腐败性,这是政府天然不具有的。正是有了公开性,明智和诚实的立法者永远不会试图逃避舆论的谴责,因为他们无所畏惧;那些有不道德企图的人却恰恰害怕通过公开性将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同时,公开性确保了公众对其立法者的信心:“怀疑总是与神秘相伴……黑暗中制定的最佳计划,会在公开性的支持下引发更多而非最糟糕的恐慌。”(Bentham,1994:582)
三
公共舆论的运作机构——公共舆论法庭
为更好地发挥公共舆论对政府信息审查的功能,边沁引入了公共舆论法庭这一术语,它是公共舆论的运作机构,在《反对恶政的保障》中,边沁确定了公共舆论法庭作为“非官方司法”的特征(Bentham,1990:54),目的是为了使公共舆论的所有成员都能如法官那样评判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具有类似于“官方司法”机关作出判决的意味。边沁认为,舆论法庭是一个虚构的实体,但它是一个有用的虚构的实体。虽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庭——没有组织化的实体,没有固定的成员和实体性的规则,但它的成员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感兴趣;它独立于官方组织,形成了一个真实的判断以及与此判断相对应的意志,它对官员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民众在其中对其进行道德制裁的惩罚和奖励(Bentham,1989:283)。
接着,边沁进一步论证了这个由无定形的群体组成的机构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边沁对公共舆论法庭中的角色进行了概念澄清,区分了“公众”与“选民”。前者是一个由能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的人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后者是被动共存的个体的总和。其次,边沁对舆论法庭的运作流程作了大致的说明,即作为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会将自身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划分为若干主题,不同的阶级也会组成小组委员会,任何人可以听取立法机关或法庭的辩论,与政府交涉,或参加讨论政治问题的会议(Bentham,1983:36-39)。再次,边沁认为,作为一个虚拟的司法机构,尽管其审议工作没有集中组织起来,但它仍然对公职人员的行为适用了一些非常像法律的东西:包括通过新闻业收集并评估与公共问题有关的信息,审查滥权的公职人员,并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
边沁对公共舆论法庭的假设暗指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就每天的紧急事务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似乎对公众的政治慎思能力给予了太高的期望,当代研究表明,20世纪的公共舆论并未实现边沁的“个体”与“集体”相统一、公共舆论与普遍利益相吻合的愿望。
一方面,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领域中生产与消费的无限扩张和政治领域中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参与日趋衰落,而远离公共领域的私人生活领域日益彰显,公共领域日益被垄断公共权力的主权国家所掌控,公众逐渐从舆论的主体沦为舆论的客体。另一方面,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理性行动并不一定带来理性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由于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无人可能或者愿意获取复杂运作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公众可能选择只获取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柯武刚,史漫飞,2000:65);这种理性无知和内部人专长打开了民主失灵的大门(卡普兰,2010:116-117),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成为一个系统性趋势(奥尔森,1995:29)。
但是,上述研究不足以成为批评边沁的理由,因为边沁始终强调的是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去防止公共利益被统治者邪恶利益所误导,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论公共舆论法庭的四项职能时,边沁强调前三项职能(信心收集、审查和执行)而不重视第四项职能(改善建议)的原因。边沁始终认为,公共舆论的力量不在于它有多正确,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抗了不正确。
四
公共舆论法庭的决策机构
——自由的新闻业
边沁大大提升了自由的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因为它与公共舆论的运作密切相关。边沁写道:公共舆论的力量发挥离不开发现、写作、印刷和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出版,尤其是报纸的出版(Dor,2000:260-261)。边沁对报纸编辑重要性的认可仅次于首相之于政治功能的重要性的认可,因为首相是推动“政治制裁的机器”,而报纸编辑是推动“道德或民意制裁的机器”(Bentham,1990:44-46)。
在边沁这里,公共舆论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新闻界是“公共舆论的裁判所”。在这个裁判所,边沁将报纸编辑设想为一种法官:与法庭收到对政府官员的控告相对应,报纸编辑也会收到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控诉;法庭接下来要收到被告的辩护,并搜集和保全那些来自控辩双方的证据,报纸编辑也要收到来自记者的信息,刊登被控官员对指控的答复——忏悔或否认,或提供证明其行为的论证,其中涉及证据的论证可以被公听;法庭将最终作出判决并发布命令执行之,而报纸编辑也会就相关事宜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发表它,通告公众,如果编辑得出结论说被控官员作出了不名誉的行为,就等于法庭作出了有罪判决(斯科菲尔德,2010:347)。
在边沁的设想中,新闻业发挥着政府信息的传播者的角色:新闻界积极地获取信息,揭露事实和真相,公众从事实和真相中形成正确认识自身利益的观念,以更好地参与到政府事务中来。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边沁乐见的报纸投入资源宣传政府活动,产出政治新闻的愿景并未充分实现。
首先,新闻自由与新闻公正并不是一回事,报纸编辑也可能有偏见,它可能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不同的媒介在新闻和时事报道中可能体现不同的政治取向,媒介与政党或其他类型机构(如工会、合作社、教会等)可能存在的组织化联系表明,媒介具有被自身的政治面貌所塑造的倾向,而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媒介体制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满足各种社会或政治团体的需要(哈林 & 曼奇尼,2012:27-29)。
其次,20世纪以来,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潮流使得印刷术统治下的公共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媒体可能同时受到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化的威胁(哈林 & 曼奇尼,2012:37)。媒体的商业属性不仅影响素材的编辑,而且影响直接的新闻报道。报纸是商业而不是公众舆论的产物,媒体收集信息可能不再取决于信息是否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要同时考虑其商业价值。因此,边沁对于今天媒体进行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因素是无法理解的。
再次,现代媒体发挥公共辩论的功能是有限的,“新闻机构的力量不足以逐版逐篇地提供公众舆论的民主理论所需要的知识规模。”(李普曼,2002:285)大众媒介对增强和激励大众的讨论的帮助很少,它们更多的是在大众社会中将他们转变为一种媒体市场(米尔斯,2004:394)。而来自“权力精英”(米尔斯,2004)的信息的“两极传播”(拉扎斯菲尔德,2012)则逐渐将公众排斥在一个顺从的、不重要的舆论之中(诺依曼,2013)。并且,信息传播中的受众事实上是无数以匿名方式存在的个体,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要受到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的暗示,不能完全表现自身的理性和思维活动,从而限制了媒介改变态度的力量(霍夫兰 & 贾尼斯 & 凯利,2015:2)。
可见,现代新闻业的发展格局早已迥异于边沁时代的报刊业境况,它逐渐由为公共舆论服务的力量发展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比个体公民更为强大的资源;它和其他权力一样,可以被用来作为滥用权力的工具;它既不是脱离于其他权力的自主性权力,也不是具有平等机会表达意见的“自由市场”的产物。不可否认,边沁关于自由的新闻业的乐观图景掩盖了这样一些事实,这是边沁理论的缺陷。然而,边沁理论的先锋意义在于:它为新闻业作为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概念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它视自由的新闻业为“对政府权力的必要审查和实现个人幸福的重要手段”的观点,仍然是检验媒体道德的依据;而当代理论对新闻业的所有批评恰恰是力图重振边沁在十八世纪末引入的自由的新闻业的概念。
五
结语
尽管20世纪以来的理论家对公共舆论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边沁所能想象的范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边沁作为舆论研究先驱者的角色。边沁舆论思想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辩护使得共同体的善建立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正确理解并将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多数决程序基础上,他创立了一种用行动(而非理念)来重视公共舆论,为现实的公共福祉作出相应的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边沁舆论思想中的靠信息公开来宣传政府行动,靠出版自由来开展公共讨论和自由辩论的观点对后来的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他对“公共舆论法庭”概念的引入和对舆论仲裁职能的描述也隐含了培育现代公民的公共精神的思想;作为最早将公共舆论与政治选举联系起来的理论家之一,边沁促使对公共舆论的关注点从抽象的政府权力合法性转移到现实的投票和公共决策过程,这为20世纪通过民意调查方法来考察公共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
编辑:陈心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2-8 20:49
【案例】
维特根斯坦:人生的境界和人性的边界 2017-12-10 09:03哲学/宗教/英国
维特根斯坦
当第一次来到海边,遥看浪逐天际,你会无语;在夜晚凝视天空,满眼星汉灿烂,你会沉默。这是因为大海的浩瀚和和星空的深邃,超出了你理解和想象的极限,以至于你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在你心中引起的震撼和感动。当你提笔想写写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故事的时候,相似的感觉也会涌上心头。
维特根斯坦最为人所知的,无疑是他卓绝的智力。他是一个天才:十三岁就制造出了缝纫机,设计过发动机,做过建筑师,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手缔造了两个完全不同却都有巨大影响的哲学学派。仅这一条,足以使他跻身于最伟大的思想家之列,而他的哲学也是长盛不衰的话题。与此相对照,关于他62岁的人生,虽然也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却可惜大都流于东鳞西爪的趣闻。事实上我一直没有看到把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故事讲得很棒的文字,足以展示他独特甚至古怪的个性当中光芒四射的棱角,凸显他由巨富而赤贫的一生所具有的神话般的品质。没错,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生活无关,并且一贯对旨在以他神奇的人生故事来装点他的哲学的企图不以为然,我却认为他的人生确有超出他哲学以外的意义,因而是另一本也值得钻研的书。他的哲学和他的人生这两本书,不必然互补却可以都很精彩,它们可以分开来读。
同时我也承认,当试图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维特根斯坦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陷入了一个维特根斯坦深恶痛绝并与之战斗了一生的陷阱,即蓄意或无意地,有罪或无辜地闯入了他认为不可言说只能显示的人生中涉及认知,情感,道德和宗教的某些领域。不过,我不自认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信徒,所以也不认为对他的人格世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相反,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一生,无论从人性,道德还是宗教的视角,都是一个有趣并且极富启迪意义的思索对象。我相信他的活法,赋予了“活着”几分新的意义,使他从已经逝去的人们当中脱颖而出,却给活着或将要活着的人们竖起了一个楷模。
有趣的是,不讲他的哲学而讲他的人生,却终究难免仍然带有哲学的意味。因为,如果可以用罗素式的说法,把“人性”看成人类所有特质和可能的生活方式的集合,那么,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在扩展“人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做出了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贡献。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个人的人生境界使我们有可能在高度和维度的某些方面重新界定普遍的人性的边界。这就像李白杜甫的诗歌定义了“唐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李杜的唐代文学应该是另一番模样吧。
尘世的负担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大亨,同时也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在奥地利富甲一方。他极富音乐修养的母亲把他们家在维也纳的豪宅变成了上流社会文化精英的中心,人称维特根斯坦宫殿,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马勒都是家族的挚友。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名正言顺的富家公子。如果在当下,按照流行的戏码,凭着富家公子的名头,他早变成了全民追捧的偶像了。 然而维特根斯坦注定却是这个富豪之家的叛逆,他对这个家庭一直都有距离感,一生都在刻意的淡化甚至隐瞒自己的家世,对这个显赫的家庭所能带来的无论是社会影响力,人脉还是财力上的任何益处,他都坚决地拒绝,其决绝程度,只有中国文革中家庭成员的划清阶级界限可以与之媲美。只是,文革之划清界限是与被迫害者切割以自保,而维特根斯坦的划清界限是与财富决裂而自清,两者在道德上并无共通之处。至于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和家庭保持疏离,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但应当不是基于某种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数学家拉姆塞的解释最靠谱:他从小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一种严苛的律己精神,绝不接受任何不是他自己挣来的东西。当然,更可能的是,他一生都沉浸在他卓越的智力带给他的精彩的精神世界里,世俗世界的七七八八的东西根本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法眼。
维特根斯坦家族照
维特根斯坦对金钱似乎有洁癖。总的说来,他对金钱有一种其他人都不具备的超脱,由金钱激发出来的种种情绪上的冲动,就像对金钱的渴望,得到金钱的兴奋,拥有金钱的得意或失去金钱的恐慌等等,对他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感觉。而这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生而富有。在一战开始前他在剑桥跟罗素学哲学的日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是很有钱的。他为自己挑选的家具时,对款式和质地极尽挑剔,剑桥家具店里的东西他都看不上,最后是定制了家具,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他和挚友品生特到挪威的旅游的所有费用都由他一手包办,这使得不用花一分钱的品生特觉得这次旅行像梦幻般美妙。1914年,维特根斯坦主动联系素不相识的出版人费克尔,表示愿意出资10万克朗援助“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当时的10万克朗相当现在的50万英镑,那可是一笔让费克尔喜出望外的巨资。当费克尔满怀感激地来见这位慷慨富有的艺术保护人时,他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金钱似乎从来没能为他带来他想要的快乐。一战开战后,维特根斯坦志愿加入奥地利军队开赴对俄作战前线。在服役期间他购买了25万克朗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没人会想到,这样的大手笔,竟然出自一个正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忐忑不安的志愿兵!
金钱只是一个富豪之家的显性资源,通常与之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隐性的社会资源,它们可不是那么容易摆脱掉的。一战结束后,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五十万奥地利士兵一起,成了意大利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认识了画家德罗比。德罗比提起他曾为一位维特根斯坦小姐画过像。当维特根斯坦说他见过这幅“我姐姐的肖像”时,德罗比睁大了眼睛,“那你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啰?” 很明显,那时的战俘维特根斯坦看起来一点儿不像有钱人家的公子。为了把他尽早从战俘营弄出来,维特根斯坦家通过梵蒂冈的关系派来一位医生为维特根斯坦做了体检,而后宣布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呆在战俘营。维特根斯坦偏偏拒不接受这项特权,对当局坚称自己身体完全健康而选择和其他人一道继续留在原地。一战结束从战俘营出来,当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维特根斯坦宫殿的时候,他是整个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几乎一无所有了:他遣散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并且在法律上堵住了收回它们的所有可能。为了生计,维特根斯坦决定成为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小学教师,为此,快三十岁的他成天和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坐在板凳上听师范老师授课。师范老师偏偏对他的姓产生了兴趣,问他是不是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说是。老师似乎并不满足,又问:“是很近的亲戚吗?”维特根斯坦只好回答:“不很近”。没人知道那一刻维特根斯坦脸上的表情和心里的感受,不过从后来他写给罗素的信上看,这类事情让他烦死了,不是因为人家看不上他衣衫破烂一贫如洗的样子,而是因为他为了打发这些无聊的问题被迫没有说实话而引来的道德上的挫败。
从志愿脱富致贫的那时起,直到他死,他手头从未有过很多钱。1919年,维特根斯坦需要去海牙面见罗素商讨《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事宜,但他没钱买票。一直为这本书的出版前后张罗的罗素自作主张,把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家具统统搬到自己家,算是把它们买下了,并以此为由头给维特根斯坦筹了100 英镑,这才使得这场会面得以成行。两年后,罗素为邀请维特根斯坦到伦敦又为这批家具追加了200英镑作为路费,说是这些家具实在太好不忍占维特根斯坦便宜,并且恶作剧地告诉极爱整洁的他,很快自己有个孩子会出生在他的床上。1923年,拉姆塞到维特根斯坦教书的山区去看他,发现“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墙上刷了石灰的房里只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和一把椅子。早饭只有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生于富豪之家而绝不依附于家庭,靠自食其力生活,应该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情吧,但这种在我看来值得敬佩的品行,维特根斯坦觉得如此自然,他津津乐道的是和朋友外出旅行没钱只好为人打短工钉木箱挣钱之类的事情。可以说,在这个生而有钱的人的生活中,金钱从来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绝不是那些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籍此自我标榜时的假清高。
家庭门第和社会地位,历来是隔绝社会纵向流动的藩篱,而冲破这种藩篱的勇气,往往成就一些或悲或喜的故事。在社会学上,不同社会层级之间流动的频率,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不过,这种在其他人生活中和社会学意义上影响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在维特根斯坦的眼中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对这个著名的哲学教授来说,从事体力劳动不仅从来不是惩罚,而且几乎就是他认为体面的唯一生活方式。在终于摆脱了家庭的光环或阴影之后,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重返剑桥,这时他的学术声望,已经超过了他的导师罗素,他成了西方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剑桥最具人气的教授之一。
不久,二战爆发,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维特根斯坦加入了英国籍。那时,伦敦处于德国战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普通民众在战火和瓦砾中顽强地坚持抗战。不愿意置身事外的维特根斯坦觉得在战火之中做哲学是件荒谬的事,所以离开了三一学院的教职,选择去做一些最卑微的体力劳动。在申请成为救护车司机未果后,他去了伦敦一家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把药品从药房分发给伤病员,几周后又被调往实验室去配制软膏。这两份工他做得如何是见仁见智的事:据说他把药递给伤病员的时候总是同时建议他们最好不要吃这份药,我想伤病员一定被他搞糊涂了;直到他去世十几年以后,医院的工作人员仍然记得他配制的软管是最好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哲学家,本是一个集德意志工匠精神,工科男的出身和工程师素质于一身的人物。他隐姓埋名来到医院, 不过后来,医院的人们还是知道了他的身份,把他称为 “教授” 。对已年过五十的教授来说,医院的体力工作是艰苦的,一天下来,他往往累得几乎走不动路。然而他一直坚持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 。尽管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人人都很不容易,然而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出于他一贯的自律和责任感的话,他并不是非得如此。这位著名教授,一生当中也做过花匠,木匠,小学老师,看门人,工程师,药剂师,等等。对他而言,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是一个在理想世界里应当被消除的社会顽疾,只是一个人心里毫无意义的魔障。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里的人。
1949年,维特根斯坦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清点了自己的积蓄,那笔钱差不多够他过两年。对此他也不是特别上心,“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积蓄快要告罄,为此他的学生兼朋友马尔科姆为他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然而在给基金会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坦白地详述了六条自己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并总结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力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我常想,一个人得有多自尊多清高,才能和钱这么生分啊!在我看来,世上再没有谁比维特根斯坦更有资格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了。事实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该有机会获得资助维特根斯坦的荣幸的,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执意自我剥夺资格的话。
幸运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晚年一直到去世都被朋友和学生照顾呵护,贫穷并没有伤害到他的身心。和休谟一样,维特根斯坦死得很坦然。
我对于金钱和财富抱有足够的尊重,我相信它们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然而,现在流行的有关于金钱的看法要强势很多,金钱已经成了度量一切成败的标准。如果不是百万富豪,你是不可以对金钱有所不恭的。对于这种金钱拜物教的流行我一直心有不甘,总盼望人生在世还有什么别的追求可以和它抗衡,因此维特根斯坦让我特别感动特别感慨。毕竟有这么一个人,够独立够强大,执着于自己的理念,一心只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那份超越,清高和潇洒,为人性的世界注入一股清流,使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而美好。所谓“天才”,也许就是这样定义的吧。
人间的冷暖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多年交往永远都是一个令人神往话题。没错,这个故事有一个童话般美妙的上半段,而下半段则透着世态炎凉的味道。很多人因此把两人后期的分歧和不和看成两人关系的主旋律,而把前期的美好只看成是必定要被主题冲淡的序曲,看成人生无常,人性荒芜的又一个例证。我不这样看。哲人的思想成长各有路径,曾经相伴同行的哲人分道扬镳,正如美人迟暮容颜老去,是令人伤感却正常不过的事。我们知道,不管是罗素还是维特根斯坦,在暮年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都满怀感恩之心,因此,我看不出把这段也许是两人毕生最重要的友谊简化成平庸的师生反目如何能与两位哲人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美好总结相匹配。我相信,以欣赏和赞美的心来看待这两人的历史性的友谊,是一种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立场,因为毕竟,除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史上还有哪对师生关系可以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相比呢?
1911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相识,对两人都是恰逢其时。刚刚出版的耗时10年写成的《数学原理》几乎耗尽了罗素的创造力,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传人,来面对自己尚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而年方22岁的维特根斯坦终于弄清了自己满腔哲学热情的突破口非弗雷格和罗素开创的数理逻辑莫属。师徒的对接几乎是无缝的:维特根斯坦未经引荐就径直闯到罗素家中而罗素毫不见怪;罗素只看了第一眼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就断定他是哲学天才;罗素的认可把维特根斯坦从自杀的倾向当中解救出来; 维特根斯坦一到罗素的讨论班就霸占了班级讨论……在罗素面前,维特根斯坦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下课后他缠着罗素不放,一直跟到他家里,甚至在罗素换衣服时也不离开。据开明的罗素记载,他可以在罗素的房间里像野兽一样来回绕圈,一连三个小时一言不发。当罗素问到:“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孽?”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是,然后继续他的困兽般的踱步。我总是在试图脑补这个著名的场景,在这三个小时里罗素在干什么?看着他转圈,还是做他自己的事?他不烦吗?在罗素家里维特根斯坦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过他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逻辑。当然他也知道罗素正好欣赏他满脑子都是逻辑,于是乎他确信他有权享用这份欣赏。
由于罗素的名望和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高度评价,维特根斯坦很快成为剑桥的新星。他认识了哲学家摩尔和经济学家凯恩斯。这两人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都持续到维特根斯坦与罗素断交以后。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他们不同,倒是因为他们与罗素不同:摩尔出自本心的善良使他比罗素对维特根斯坦更宽容,几乎到了受气包的地步;而凯恩斯尽管一直是维特根斯坦的最宝贵的支持者,却明智地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也许是因为他怕自己由于走得太近而受不了维特根斯坦那令人疲倦的对逻辑严谨和道德完美的热烈追求。罗素的青睐也使剑桥的精英社团对维特根斯坦开启了大门,他们开始找上门来对他进行近距离观察。尽管对这类所谓上流精英白眼相看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还是终于费神在他们的考察中露了一手,展示了一个天才的才智。但这可不是为了出风头 —— 这类冲动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还罗素一个情,因为罗素到处宣传他是如何非同寻常。而这时的罗素,因为想着自己肩头的重负终于后继有人,自认有些变懒了。
在学术上,老师很快就成了学生的聆听者,并且越来越在意学生对自己的评价,两个人友谊开始从伯乐与千里马的抒情叙事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华彩旋律转调。随着对于逻辑基础的更深入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开始和罗素有了分歧。在讨论罗素的哲学时与老师暴跳如雷地争辩之后,维特根斯坦的痛苦,失望和受伤甚至超过了老师本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纯净的思考当中没有掺进任何尘世的杂念,这是干干净净的哲学论争。 罗素要面对的挑战要大的很多。作为一个成名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罗素现在要接受一个青年小子的挑战了。 以罗素一贯的潇洒大度,这都不是问题。更大的困难在于,眼看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哲学大厦慢慢地被从底部被侵蚀,罗素慢慢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写了许多知识论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对之作了最严厉的批评……我看出他是对的。我看出我再也不能指望在哲学里作根本性的工作,我的冲动被击碎了,就像波浪在防波提上撞成碎片。”尽管如此,罗素依然为维特根斯坦工作的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支持是出自内心的,慷慨大度的,令人敬佩的。后来证明,在容纳别人和提携后进这些方面,罗素比维特根斯坦好得太多。
维特根斯坦很快就对剑桥厌倦了。他忐忑地告诉罗素他想到挪威的某个偏僻海湾去隐居一段时间以便专心整理自己的思路。罗素对这个计划的认同似乎使维特根斯坦如释重负。他去呆了一年,而这一年的隐居成为他日后时常缅怀的一段时光。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一战把剑桥的哲学家们送进了不同的阵营。凯恩斯投身英国财政部为战争出力,罗素因公开反对战争而入狱。维特根斯坦则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站在了英国的对立面。没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参军是出于爱国热情,有人甚至怀疑他自愿参战只是为了“体面地死去”,这种猜想有他获得的若干次勇敢嘉奖作为支持。 但如果你读过了他在前线的日记,就会知道这种猜想真是无稽之谈。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富于宗教气质的,道德上狂热的完美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相信,只有尽可能地靠近死亡,才能激发出生命的内在动力,洗脱自己身上的不洁。“ 当我面对死亡,我应该有机会成为一个体面人”。
在军队里他干过杂务兵,站哨,管探照灯,管过枪械库和车站。1916年3月,终于如愿以偿转到前线部队。很明显他是不适应的,枪炮声使他紧张,因此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许多励志的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话,像个初入职场的大学生。这个志愿兵对他的上级没有多少尊敬,“他们多半都像猪”。
如果说在剑桥的学术界他觉得迷失了自我的话,战火和面临死亡的恐惧反而激发了他的哲学创造力。他一边削土豆一边想自己的逻辑论证,把自己比作磨镜片的斯宾诺莎。从他的战时日记来看,他的思维的活跃程度是惊人的,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近于完成《逻辑哲学论》的写作。一个就连剑桥校园都嫌过于喧嚣,不得不远遁挪威山林才能收拾起思路的人,却在炮火中在战壕内在战俘营里,完成了一部思路如此严谨,文体如此独特的世界哲学名著,真是一个奇迹。“战争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会做什么”。事实上,战争确实在维特根斯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战争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他仍然习惯于只穿军服类的制服。
战争压倒了学术,也隔绝了学者之间的交流。191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线日记中写到:“过去几天我经常想到罗素。他仍然想着我吗?”罗素也有相似的心境。1915年冬天, 他们曾有一次通信,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他正在写文章,但在罗素看过之前他什么也不会出版。他说万一他死于战争,他会托人把书稿寄给罗素。罗素的回信满心欢喜,他急切地要维特根斯坦立刻就把书稿寄给他。然而自此之后,他们就断了联系。5年之后的1919年,罗素在《数理逻辑导论》的一个脚注里地写道:“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样深沉关切的语调出现在一部数理逻辑的专著里面, 极其罕见。哲学家是理性的代表,而俩位当事人更是理性和逻辑的世界顶尖高手,他们之间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呼唤和牵挂,给人带来动人的温暖,哪怕战火也不能阻断。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笔记”(1914年)的原稿
战后两个人的联系迅速恢复,主要是因为《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工作。这部现在享誉世界的名著,当时却像垃圾一样在德国英国的担心赔钱的出版商脚下被踢来踢去。有人想让维特根斯坦自费出版,被他严词拒绝了:“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有眼不识泰山的出版商们的冷淡使维特根斯坦心灰意冷,他想到了自杀。罗素又一次把他救了出来。在与出版商多方联络之后,罗素觉得推荐信之类的东西恐怖怕不够,他得写一片序言才行。于是便有了罗素接管维特根斯坦的在剑桥的家具为维特根斯坦买机票的故事。维特根斯坦飞到海牙,和罗素一起一段一段的读这本书,最后罗素写成了一篇导言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罗素的导言并未使维特根斯坦满意,但罗素的名气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版事宜竟然因此有了着落。出版商的口气基本上是这样:他们很荣幸出版罗素先生的导言,当然,附带地也乐于出版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为了出版商的这种轻慢作者的态度,罗素曾多次向维特根斯坦道歉。在罗素心里,自己的导言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书能付印。终于,《逻辑哲学论》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了。这本在哲学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作,以期刊的名义,带着扎眼的编辑错误,以拙劣的印刷质量,在种种学术的,人事的,技术的,商业的纠葛的包围之中,终于跌跌撞撞地问世了。作者本人和他的导师兼朋友罗素为了它的出版所经历的挫折所耗费的精力, 现在想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作为朋友的关系宣告结束。事情的起因是他们在奥地利的一次计划已久的,后来证明是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的见面。那时刚走出战争的奥地利一片萧条,小镇因斯布鲁克找不到合适的旅馆,最后他们合住了一间房:罗素夫妇睡床,维特根斯坦睡沙发。这必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再加一个心烦的早晨。他们吵架应该不是因为他们哲学上的分歧。很可能是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宗教情节很重的人,而罗素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种差别在战前还不明显,但战争强化了它:维特根斯坦战火中带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是宗教帮助他度过了5年的战争时光;而罗素一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战争和宗教的批判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也曾为反战坐牢。争论中维特根斯坦一定非常激烈,不过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以至于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讨论,事后还给罗素写过两封信。两封信罗素都没有回。看起来,叫停两人朋友关系的人应当是罗素,因为他看出他为自己的定位与维特根斯坦已经没有了交集。
两人虽然不再是朋友,而且对他们的分裂也都开诚布公,但同事和同行的正常交往仍然维持着。1930 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罗素为他的研究写一份评估报告来申请研究基金。这时的罗素,可谓焦头烂额: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妻子快要分娩,实验中的罗素自办高中的财务困难,等等。尽管如此,罗素仍然挤出时间听维特根斯坦讲解他的新的思路,对它他既不赞成也搞不太懂, 然后两易其稿写了详细的报告,最终帮助维特根斯坦拿到了基金。是罗素和摩尔主持了维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辩,并且放任那个想拿学位的家伙反倒像老师一样趾高气昂。在维特根斯坦方面,尽管他在朋友和学生面前并不刻意隐瞒他对罗素后期哲学和人生观的不满,但就像他的学生马尔康姆注意到的,在公开场合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总是毕恭毕敬的,他对其他人可从不这样。这就是两位哲人后期的同事同行关系。是的,他们不再是朋友和知音,但是,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小人反目泼妇撕逼之类的狗血剧情。
罗素在哲学的建树和自成体系方面要逊于维特根斯坦,但罗素年岁稍长且成名略早,因此罗素注定要在维特根斯坦出道的时候扮演师长的角色。应该说,这个角色他做得无可挑剔甚至可圈可点,极富哲学大家的胸怀和英国贵族的风度。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偏好,我对罗素在演绎师长方面的所做所为持有的尊敬和好感,似乎要比能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看到的要多要高。这或许就是智商和情商的区别。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智商高于罗素的话,那么他的情商,至少在情商的许多方面,比如控制情绪,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方面,肯定不及罗素。罗素以他惯有的大度这样评价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他更清澈,更有创造性,更有激情;我更宽广,更富同情,更健全。”罗素还不忘谦虚了一句:“为了对称我夸大了这一对应,但这有点意思”。在我看来,这番对比还是中肯的。
尼采曾经把生命比作在两个完全相等的虚空之间的火花,介于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后的黑暗之间。按照这样的看法,生命的意义超出了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我愿意以类似的视角来看待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把他们的友谊放到人类思想探索的长河当中来定位: 在探索人性的无限可能性的跋涉途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划过黑暗的天空的两颗灿烂的流星。在某一时刻,在某一点上,两颗流星有了交集,他们的碰撞迸发出了绚丽的光芒。然后两颗星各自东西,继续前行。无论从经验的归纳还是慨率的计算上说,两颗流星的相撞或两个绝世天才的相知相惜,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经出现,便成绝响。然而这千载难逢的相遇的意义,并不自动向所有的人展现,你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和一双诚实的眼睛。能够领略到这个历史巧遇的神奇并受惠于它,是一个人的福气。
内心的拼争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以清澈纯净为特征的话,他的内心世界却复杂而多层次, 我很难想象还有谁能比他在内心里有这么多来自家庭,社会和人的天性的压力要平衡。
维特根斯坦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极其富有,却是新近富起来的人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于贵族的风度和品味表现出了略微多一点的关注,不像对其他世俗的追求比如金钱,地位,女色和名望那样不屑一顾。他希望被人看成具有贵族的外表和教养,乐于被人觉察出那些他确实生而具有的贵族气质:热烈,自律,清晰,有责任感。他和家人的关系远谈不上疏远,但回到家里和家人度过的时间总是让他烦恼,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正常理性生活的干扰,是生命的浪费。
维特根斯坦又生于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格局剧烈动荡,族裔冲突空前惨烈。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战中他是德奥联军的志愿兵在前线对俄国作战,二战中他站在英国一边在后方为对德作战出力。在两次大战中站在对立的阵营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也许是因为他之参战并不是出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只是听从自己道德的召唤。他在英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入了英国籍,但他对英国的态度很复杂:对剑桥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作为志愿者为反对德国的英军服务,却对英国的战时宣传呲之以鼻,在其中英国被描写得战无不胜,而德国一副挨打的怂样。有一次他的学生马尔科姆谈到了英国的“民族性格”使英国人不会使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他是如此光火以至于几乎和马尔科姆绝交。是的,他生气固然与马尔科姆的思维方式有关,但文化对立和族裔疏离也应该是原因之一吧。维特根斯坦的祖上是犹太人,从他的父亲那一辈皈依了新教。由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他没有犹太身份认同的困扰,但犹太问题对他始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有人甚至辨认出了他轻微的反犹倾向。至于纳粹政权是否认为维特根斯坦家是犹太人,那是另一个问题。
维特根斯坦到哪儿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所谓天才的完美典范:真情,深刻,热烈而强势。他很独断,有不容抗辩的家长作风。罗素说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像沙皇下谕旨一样,而拉姆塞和图林都不约而同地批评维特根斯坦试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数学哲学,我猜那是指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同时带着专横的,排他的,专制的风格。他是性情中人,但做他的朋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友谊而妥协不是他的风格。
和很多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独身。他应该并不是同性恋,因为他也曾对女性产生过恋情。也许是因为他对在极高的智力层面的充分交流的渴望阻碍了他与在情感层面更为敏感的女性产生共鸣,他的密友大都是年轻聪明心地单纯的男性。他的感情是内指的,在意的是他自己是否爱自己的爱人而不是爱人是否爱他。在这一点上他和罗素完全不同。罗素在与奥特琳恋爱的时候对宗教更为宽厚,因为奥特琳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他因着对她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了对教会的敌意。类似这种爱爱人之所爱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因为他的感情是更加私密的:他所爱的人对任何他以外的人和事的关注,会被他视为是对他私人领域的干涉从而感到不适和不快。和品生特一起在冰岛旅行时他特地选了一个空无一人的旅店,维特根斯坦很享受这份与众隔离。后来旅店来了第三个旅客,品生特跟新来者进行了交谈,这使维特根斯坦很不高兴。为了避免和新来者打照面,他要求旅店为他们提前一小时开饭,不幸旅店居然忘了。维特根斯坦于是拉着品生特到小镇上去找吃的,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宁愿在房间里以饼干抵了一顿饭,而且直到第二天才慢慢高兴起来。把这类事情看成是维特根斯坦在嫉妒那是太低看他了,他只是不能容忍因为外人的介入降低了他和密友的关系的品质。他的感情世界正像他的哲学: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形同陌路。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都为一种道德拼争所主宰。有人达到较高的道德水准,自然而水到渠成,比如摩尔之出于天性,比如康德之出于心中的律令。但维特根斯坦的道德追求是一种搏斗,一种挣扎。对他来说,坦诚地直面自己内心,克服怯弱,避免因骄傲和虚荣而起的不诚实,才是真正的道德。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道德观。
一次,维特根斯坦和罗素讨论了狄更斯的《大卫 科波菲尔》当中的一个情节: 大卫的朋友斯提福兹引诱艾米莉背弃了她与汉姆的婚约与他私奔,为此大卫很生气。维特根斯坦认为大卫对斯提福兹生气是错误的:他可以难过,却不应该因此放弃对朋友斯提福兹的忠诚。于是罗素问维特根斯坦:如果你和一个女人结婚,她却和别人跑了,你会如何?维特根斯坦说他会很悲伤,但不会愤怒或仇恨。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和一个女人结婚是出于对她的爱,这个初心必须保持。在她出走以后随之而来的愤怒和仇恨,却另有源头,有些来自内心的负面情绪比如你受伤的自尊心,另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社会对对第三者的消极看法,已及对于婚约的承诺的通常见解等等。没错,它们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却与你当初的爱没有关系。所谓道德,就是如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保持初心。此心不渝,是为真诚,因而道德。在我看来,要实践这样的道德生活,需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啊。
除了愤怒和仇恨,怯弱和骄傲也是道德的敌人。1936年圣诞期间,维特根斯坦决定对自己的道德生活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理,与自己过去的不诚实做一个了断。他把自己曾有过的不诚实的行为列了一份清单,奔波于维也纳,剑桥和当年他教书的奥地利山区之间,找到当年的当事人,逐个面对面地忏悔。这些“不诚实”标准非常苛刻,有些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共同熟人去世的消息,他做出吃惊的样子,而事实上他早已知道这件事情;他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个处男;他没有纠正人们以为他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看法,尽管心里知道他是四分之三的犹太人。(有趣的是,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犹太血统应该少于四分之一。)有一件事情则可能比较严重,发生在他当山区乡村教师的时候:他是一个暴躁的老师,不能容忍迟钝木讷的学生,而且出手不知深浅。他曾揪着一个女孩的头发把她拖来拖去,以至于她耳朵流血。他也曾把一个体弱的男孩揍昏过去。后来维特根斯坦被学生家长告上法庭,他却当庭否认了虐待学生的事。这个谎言折磨了他16年。维特根斯坦的忏悔之旅是正式甚至是强势的:每个当事人都事前收到通知,不容推脱,并且预定了时间地点。忏悔很有仪式感,维特根斯坦面对面地跟当事人说话,手里捧着讲稿,通常严肃偶尔激动。忏悔的听众的反应相当不同: 好心的摩尔为他所受的折磨而难过;崇拜他的弗朗西斯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明就里的人们觉得有点尴尬。当他辗转赶到山区,登门向那个被他揪过头发的女孩道歉时,此时已经成年的女孩只轻蔑地冷笑着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我相信维特根斯坦那时候一定是很崩溃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对了,因为他的忏悔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自己的骄傲和怯弱,并由此求得内心的拯救。
每一个人都有不诚实的时候,有一些人事后也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诚实,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可以扪心反省自我纠正,然而很少人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能以这样的决绝,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把自己的隐秘的不诚实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这样做其实只是出于他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在他看来,道德并非得自于遵从由外部施于人的信条,道德是人在内部觅得的品质。道德与其说是一种教化,不如说是一种救赎。这种道德观使他对任何忘我情怀和献身精神都满怀敬意,对崇高充满向往。一战后俄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强烈地吸引了维特根斯坦,牺牲小我以投身于一项宏大的运动从而实现“自我的升华”的共产主义实践似乎在他心里引起了某种共鸣,以至于他产生了移民苏联做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愿望。 毫不奇怪,这种浪漫的热情在他短暂的访问了苏联之后慢慢减退了,一个用乌托邦遮掩的极权体制和一个独立的人格之间的不相容,用不了多久就会显现。不过,维特根斯坦对另一种献身精神始终保持着尊敬,那就是宗教信仰。
维特根斯坦的强烈的宗教热忱却是他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之一。“我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我禁不住从宗教的角度看每一个问题”。我猜想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热情不仅来自他强烈自律的道德观,也来自他对形而上学的认同。在由他和罗素共同催生的,后来变成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运动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对形而上学抱有同情的人之一, 这使他成为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号召的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有些格格不入的教父。他从来认为形而上学表达的,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人类情感,代表着人们试图超越理性的努力。理性和信仰的分界处,永远是思想交锋的火线。坚信理性的人们,总希望把理性的疆域不停地向前推进。 曾几何时,在布鲁诺哥白尼时代,理性需要像宗教献身一样的热情来催生。不过到现代,人们已经开始把理性当成了常识和生活习惯了。与此相对照的是坚持信仰的人们,在他们看来,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总有一个神秘的领域是理性永远无法达及的,那便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那是一片人们特地保留下来的场所,为的是让灵魂获得安宁得以休息。维特根斯坦是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孤独的灵魂。是的,他是正宗的理性阵营出身,却对宗教信仰心有戚戚焉。如果说当康德把现象界以外的领域留给信仰时还有些无可奈何的勉强的话,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态度更加正面和肯定:“有信仰的人像个走钢丝的人。你看上去他就像在空气里行走,但他脚下也许的确有什么东西”。那些支撑着人们行走的信仰包括上帝,生命的意义,意志,命运,幸福,生死,永生和良心等等主题。当你发现它们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对象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热忱就变得毫不奇怪了。
但切不可把维特根斯坦对信仰的同情仅仅与基督教连接起来,因为他对宗教的尊重覆盖了所有宗教形式,包括原始部落的宗教。维特根斯坦不是教徒,因为他不能使自己相信教徒相信的东西,他也从来不遵从教徒的实践。信仰于他,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他也许没有像康德那样走得那么远,把所有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都看作对信仰的歪曲,但他一定断然不会同意,他心中对上帝的体验,是一种应该,同时也可以,拿出来与人分享的感悟。晚年他曾借居卫理公会教长摩根家,摩根问他是否相信上帝,他的回答是:“是的我信,但在你信仰的东西和我信仰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许是无限的”。
维特根斯坦信仰的上帝确实是存在的。他一生当中所有他觉得应当忏悔的事情,他都留在自己的心里没有忘记,他把它们背负在自己的身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以他绝顶清澈的大脑,记住了自己童孩般的纯真,并以信徒般的虔诚坚守着。我也曾有过纯真,也曾为失落了纯真而懊悔,然而时至今日,我几乎连曾经的的懊悔也已经失落了。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宿命:和世界相安无事,内心覆满灰尘。维特根斯坦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拼争,为了自己心中道德和信仰的净土。他在心里设定要与之战斗的,包括却不限于很多我们早就视为理所当然并会坦然接受的东西:对世俗名利的不懈追逐,出于本性的食色之欲,对尊严的无所谓态度,浅薄的自以为是,自我放纵导致的懒惰,不思进取的愚蠢和浑浑噩噩。他讨厌平庸,市侩和老好人,连自私自利甚至自我保护都不肯容忍——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懈的追求真理。他要抗争的对象也许真是太多了,真不知道人在这样重压之下该如何生活。 他总有自杀的倾向,以前我总以为这是他出于对自己性取向的罪恶感,就像他的哥哥们。而现在我终于明白,自杀对于他,是在外部世俗世界的逼迫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感到坚持自我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宁为玉碎的最后反抗。信徒把拯救自己的重负加之于基督肩上,从而获得灵魂的宁静;而这个充满宗教情怀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自我救赎,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告诉世人最后的话是:“告诉他们我有过美好的一生”。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对自己一生的最后的审判,而那高高在上的法官就是他自己的良心,那常驻他胸中的上帝。
做人,其实也可以是这样的。
http://www.sohu.com/a/209560364_488408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2-17 18:25
【案例】
哲学是一种冲击边界的思考![color=rgba(0, 0, 0, 0.298)]点击蓝字关注👉 [url=]哲学之路[/url] [color=rgba(0, 0, 0, 0.298)]今天
作者:包利民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
哲学是一种冲击边界的思考。
希腊人说哲学是理论观照,是对智慧的热爱。一般来说这样的界定当然不错,但是随着其他的理论性纯粹知识的纷纷独立,哲学必须进一步限定自己的对象。
“冲击边界”或者“理性的超越性冲高”是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一般知识学科,更不用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在边界内正常进行的,总是避开接触边界。
希腊神话传说警告人们,过于靠近太阳,会有被烧死的危险。库恩也说,只有在不置疑范式本身,在范式的内部解题时,科学才有进步可言。
但是哲学冲击边界。
这边界既可以是本体论的边界,也可以是认识的边界,既可以是善与恶的边界,也可以是语言的边界。
二
对本体论的边界冲击首先吸引了人的注意。它的最为具象化的学科形态是以天文学为中心的“自然哲学”,这导致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不幸跌入了泥坑。
“天”不仅在空间上是世界的边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或者就是诸神),而且在时间上启示我们想到整个天地宇宙(cosmos)有其终极性的起源(arche),也就是根基。这样的大全式自然哲学智慧,最为接近神学,从而也最接近古代人对智慧之学的看法。当然,边界那一边的对象不仅仅可以是“存在者整体”,也可以是别的东西。
比如,可以是宇宙内部万事万物的“道—势—逻各斯”(赫拉克利特),还可以是宇宙的最普遍的本质或“存在”(巴门尼德)。这两种前苏格拉底哲学所关注的东西显然与自然哲学不同。
它们在两个极端上拉开对存在的思考的理性框架——前者可以视为是时间节奏点的无限压缩从而极度提醒人们注意时间,后者可以视为是时间节奏点的无限拉开从而彻底否认时间。这两位哲人在西方哲学的入口化身为两位激烈拒斥常识的正义女神,设下思想尺度。
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这意味着放弃天,转向政治与伦理。由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的总精神,人们不再感到这句话中的震撼意味。但是在当时这必然是令人惊诧和引起争议的“哲学转向”——你怎么还敢自称是“哲学-转向”?
你不是已经从Nous的超越性冲高退回到城邦日常生活的那些“鞋匠”、“皮匠”之类的讨论中了吗?但是苏格拉底的“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无人有智慧”等等的话还是令人感到这是哲学,这是根本性的思考,是冲击边界从而动摇神圣领域的思考。走到极端,它甚至必须在政治城邦面前为哲学这一貌似玄虚无用的追求的生存合法性进行申辩。
在希腊,柏拉图路线的哲学显然在纯粹理论的旨趣之外——或者之前——包含了政治伦理的旨趣,如此说来,这一古代哲学中最伟大的哲学至少有两个旨趣:纯粹理论的和政治的。虽然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合并二者的冲动在后世注疏家当中层出不穷,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把这两种旨趣看作张力性地共存于柏拉图思想中比较好。
可能因此他的“相”的哲学才企图在“洞穴”的内外开启出灵魂内部的深度与客观理智的宏大深远的“存在大序”世界。亚里士多德尽管在他的所有著作的“文献综述”部分都必然批评柏拉图,但是许多人越是多读亚里士多德,越是感到他其实是属于“我们柏拉图学派”的忠实传人。他对存在的总分类和“含存在量”的排序的本体论,一直启发了罗马时代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
与柏拉图路线相反的另一条路线即自然哲学的路线,它并没有被柏拉图路线的哲学光芒所压倒。实际上,在雅典除了柏拉图学园及其附近的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之外,还有伊壁鸠鲁所开办的学校“花园”。
自然哲学的思想方式在晚期希腊罗马时期甚至形成了十分有思辨性和完整的“原子论”体系。早在柏拉图的书中,就用“诸神与巨人的战争”生动准确地描述他的抽象本质哲学和原子论哲学所代表的自然哲学一线的冲突。
不过,如果人们认为“古代人”必然会看低唯物主义和快乐主义,拥护抽象圣洁的“相”世界和美德至高性,必然会都涌入Academy而忽视Garden,那就错了。实际上,涌入“花园”并且死心塌地而不悔改的大有人在。这也许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在宣传一种哲学、而非“量子力学”的古代版有关。现代科学除了在细节之外,在原则上并没有超过古代原子论。
有人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就是伊壁鸠鲁的天下。但是,事实上古代原子论超过了现代科学,因为它是哲学,是认为我们的目光既然穿透了世界的内在本质,则我们的生活态度就应当发生与我们只知道日常视野时完全不同的巨大变化,我们就不该再患上本体性重疾。但是,很难说今日知识人与非科学人士在心性上有明显差别。
说到心性,我们必然要提到希腊化—罗马治疗哲学中的典型心性之学——斯多亚哲学。在一个你无法把握的世界里,你能否让自己的有限的一生散发出人性的极度高贵光辉?在西方古代,这是以“斯多亚派”的名义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斯多亚哲学家中的爱比克泰德,他的灵动、隽永、深刻的《哲学谈话录》中处处弥散出这样的光芒。它告诉我们反思在一个纷繁的,充满权力、金钱、名望、欲望、快乐与不幸、世俗的追求和“学者的名声”的追求的世界里,人怎么作为一个人度过自己的一生。相信读者在《谈话录》中会不时找到熟悉的影子,会发出会心或尴尬的笑声,会掩卷长叹,会钦佩有加,会高山仰止。
三
因为哲学在本体论上冲击边界,所以我们究竟有没有这种特殊能力,迟早会作为一个问题进入人们的反思意识。比如,作为有限者,我们能够认识“无限”吗?或者,且不要提“大全”这样的对象,即使面对眼前的一个苹果,我们能认识其“自身实体”吗?一般说来近代哲学开始时的笛卡尔和休谟代表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在我们下水游泳之前,应当先考察一下我们是不是水陆两栖动物。
笛卡尔所代表的大陆唯理论和休谟所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在取向上完全不同,但是在怀疑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学科知识上是一样的。而且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怀疑并不是真的针对日常生活的,而是针对企图冲击日常生活和学科的边界的哲学的。
事实上,貌似独断论的哲学家们自己早就感到这种智穷力竭的痛苦;高空的低温和稀薄的空气似乎在嘲笑不自量力的攀登者。形而上学家们在“概念—语言”的“边界—刀尖”上痛苦地跳舞,希望能够榨尽我们概念-语言的最后一点可能性——靠近本体。
康德的哲学工作可以说是系统地划分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和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的界限,他不无怅然地接受了“超验的形而上学”不可能作为一个学科的休谟结论。但是,他不仅为信仰留下了空间,而且为未来的哲学家留下了很大一片“搞形而上学”(也就是搞哲学)的领域——先验领域,那就是事物的边界性根据。这种根据,按照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假设,是主观的。
但是悖谬的是,恰恰因为这些主观框架的存在和运用,我们的经验才不至于像休谟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主观意识流,而是历历在目、井然有序的客观对象。这一先验天地是一个广阔天地,具有严格科学心性、又不甘心接受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哲学家在这里是大有作为的。
黑格尔的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继续开发这一内在空间,以各种方式抵制现代性的经验主义还原论主流,承担看护独立“哲学”的使命。当然,我们会不时听到最新的“自然主义复兴”的潮汛。
“诸神与巨人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四
认识论转向之后是语言学转向。进入20世纪“分析的时代”,对语言-逻辑的反思体现了哲学的批评精神的深入或者内转。形而上学不是不能认识的幻相,而是不能说出来的无意义的假句子。尤其是人工语言派的逻辑原子论,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优点和杀伤力。
当海德格尔和萨特醒悟胡塞尔的科学建构可能违背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本意的时候,日常语言学派也醒悟过来:人工语言派的工作依然坠入了他们所孜孜以求加以摧毁的西方形而上学的瓶子中。
维特根斯坦提示人们:落入瓶子的苍蝇不断冲击边界,但是它们永远不知道只要垂直从入口走出瓶口就可以了。
走出瓶子的哲学家在认识论上大多采取某种“整体论”的理解。蒯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可以说是醒悟地较早的一个代表。整体论的认识论必然更为重视各种知识相互之间的支持(拥有理由),而不是知识与对象的关系(绝对真理);这样的路线最后走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人们在这一大趋势里也许可以看到一种日益严重的反对哲学本身的否定性倾向,这一倾向自哲学诞生起就与哲学伴生(寄生),它不试图批评某种哲学立场不对,而是试图站到哲学外面,彻底消除“哲学”这种事业。从古代怀疑论到近代不可知论,从尼采到罗蒂、福柯、德里达,此处难道不就是另外一个系列的“诸神与巨人的战争”?
严格地说,此处的“巨人”不是哲学中人,它不使用关于超验对象的“对象语言”,而是使用“元语言”的“元哲学”。这种否定性的“元哲学”在有的时代显赫,在有的时代被哲学的风头所遮蔽。但是在现当代,它显然越来越显赫。哲学自巴门尼德开始傲慢地打压常识和生活——“不合逻辑”的,即使显而易见,也是错误的;现在生活终于反扑:伤害生活的,再精妙的理论思辨也要被拒斥——更不要说还会有可能被揭发为遮掩了权力的意识形态。
五
哲学不会坐以待毙。
在当代,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从“元哲学”的层面上回到实质性哲学内部。哲人担忧虚无主义对政治和伦理的杀伤。罗尔斯在20世纪中叶公开反对“元伦理学”的工作,开讲规范性的“正义论”。
而且,毫不介意尼采已经指斥民主、道德为弱者的诡计,不介意斯特劳斯派大将布鲁姆指斥他为“没有文化”、不懂哲学,罗尔斯公然建立了一个非哲学非宗教的、公共理性基础之上的弱者政治学。犀利而机智的罗蒂从美国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为此喝彩和论证。
作为法国“后现代哲学”宗师之一的列维纳斯在20世纪后期比罗尔斯走得更远,对于他来说,道德不仅仅是什么平等主体之间的“正义”,甚至是超越正义的、对他者绝对负起责任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是“第一哲学”。
于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是否需要哲学的支持,如果需要,是哪一种哲学;哲学是否应该开出民主政治,等等——总之,边界上的事情与边界内部的事情有什么关系,突然又激起了学人们的热烈争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边界”的含义和原因提供了独特的洞见:人类在最接近自然的劳作中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居然塑造出人类的生活形式的基本边界。那么,今天的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生命技术、核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加速度发展和普及,随着市场利润压力和存在主义所讲的那种本体性绝对自由的凸显,人类不久即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存样式里。
我们目前所关心的民主、正义、德性、财富、理性、非理性等等到那个时候也许会全部成为“史前史”的话题。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抱怨人总是被动地听凭偶然性立法。面对我们迫切需要进入的新范式,更不要说遥望地平线上过早露头的那个极度陌生的“新世界”,人们有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人们甚至不遥望,他们宁愿在世上的事情中当下烦忙。
然而时刻到了,希望不被“流变”裹胁而去的人们应当打开以“在边界上”探险为己任的哲学家们的考察报告了,让我们细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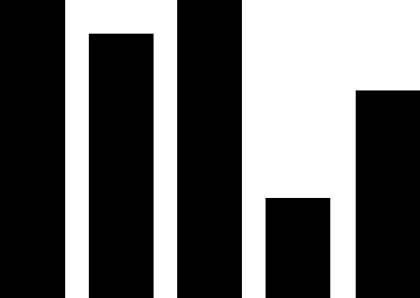
- END -
长按识别二维码
https://mp.weixin.qq.com/s/cfPNg7_W1AJhZC1Dezff0A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3-8 10:18
【案例】
一房地产公司招聘,居然招的都是非常丑的已婚妇女。有人问:“招这些已婚妇女,不会是打算销售房子吧?”老板说:“这些人都是我选出来的人才!”继续问:“人才?不会吧!”老板说:“他们能把自己嫁出去,还怕她有什么东西推销不出去吗?”
编辑:陈茗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3-23 17:16
【案例】涂层正义论——关于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哲学研究
探索与争鸣杂志
2019-03-22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编者按】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撰文《涂层正义论——关于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哲学研究》,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在该文中,作者创新性地提出“涂层正义”的概念。涂层已经成为一种有问题的普遍现象,亟需自觉的哲学关注。当人们以正义为装饰谋求私利时,正义就成为一种涂层。涂层正义是一种被盗用、被利用的正义,其生成有复杂的文明论、道德论、观念论、行为论原因。日益普及的道德感形成了一种道德之幕,道德之幕为道德、正义的被盗用、涂层化提供了可能。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历史的总趋势,涂层正义是仍具有丛林性、野蛮性的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涂层正义是实施者、被施者进行社会互动、共同行动的结果,在涂层行为的背后是深刻而固化的社会差异、社会不平等。涂层正义既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社会的文明化,也可能使社会进入新的丛林状态。打破利益与阶层固化,营建透明、可流动的差异型社会,推进宏观及微观公共领域运行方式的规范化、透明化,克服泛民论,防止权利粘性,推进个体权利获取方式的透明化,对克服涂层正义有路径意义。提高社会运行的透明度、流动性,将有效减少涂层正义。
涂层正义论
——关于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哲学研究
陈忠 |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综合节奏日益加快的城市社会催生了很多现象,涂层就是其中之一。涂层,是指用各种颜色与质地的涂料、装饰材料对建筑、环境进行改造与更新。把现代建筑涂层为古代的,把水泥建筑涂层为石料的,把暗淡的涂层为光鲜的,把有缺陷、丑陋的涂层为完美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涂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涂层有其效用和价值,会遮掩问题、提升形象、满足人的某种实用和心理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完善、仿真的幻象。但只用涂料无法盖起真正的建筑,涂层深处总有真容。涂层的效用与价值终归有限,往往并不长久。或早或晚,或某处或全部,涂层总有脱落的一刻。涂层落处,尽显真容——斑驳甚至丑态。
需要关注的是,涂层已经不限于实物性的建筑与装修,而成为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人们的诸多行为与观念已经具有涂层性,甚至某些群体、共同体的运行结构也已经呈现出涂层化倾向。当今世界关系,宏观体系及微观日常层面的政治、生活、文化等都存在被涂层化的可能。涂层已经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哲学现象,亟需进行自觉的哲学关注。
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总容易被冒用、盗用。正义也是如此。正义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共识,但正义的真实性却日益成为一个问题。正义不仅是一种话语,更是一种行为。当人们以正义的名义从事非正义的行为,当实质行为与正义话语相脱节甚至相背离时,正义就成为一种涂层。以正义为涂层、正义的涂层化、涂层正义,是对正义的盗用,是一种处于被盗状态的正义。把握涂层正义的生成机理,具体厘清正义是如何在文明化进程特别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被涂层化、被盗用,对探寻克服涂层正义的可行路径,营建一种更为真实、可持续的正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涂层现象为切口,对正义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行为哲学反思。
涂层正义的“道德”生成
正义是人们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底板。从古代到现代,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人们历史性地选择了正义作为规范和评价人的行为、社会制度、社会运行机制等是否合理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尺度。虽然人们对正义的具体理解与使用各不相同,或侧重分配正义或侧重生产正义,或侧重积极正义或侧重消极正义,或侧重行为分析或侧重制度研判,或侧重目的、结果或侧重程序、过程,或侧重个体或侧重整体,但无论如何,正义都已经成为人们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在当今世界,几乎不会有人或什么层面的主体会宣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以不正义、不良善、邪恶为原则。
当人们对外要求正义时,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成长,特别是以自我为导向的主体性的觉醒,标志着人们已经确认了某种合理性,并开始以这种合理性作为行为与思维的底板。当人们在同自身无关的事件中维护正义时,则标示着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生成,标志着人对自我主体性的升华,开始从关注自我走向关注包含自身的社会关系,标示着人们以正义为底板,合理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行动。正义是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基本价值,是人们行为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普遍共识的价值尺度、公共话语。在文明变迁中,人们选择以正义为价值底线、价值共识,是一个历史趋势,是文明进步、历史发展的重要象征与标志。
正如交换的密集、复杂、日常化催生了货币,社会越复杂、交往越多样,越需要一种共识性的道德与价值意义上的一般等价物。正义正是这个复杂世界的价值、道德一般等价物。但问题在于,正义在成为一种一般等价物,一种普遍性的共同价值、价值货币,一种公共性、共识度高的价值标签、价值符号,一种抽象、通用的价值货币的同时,日益呈现被盗用的可能,就像货币的流行会催生假币一样。当黄金成为通行货币时,就会产生用金粉涂层的另类、涂层黄金,当正义成为通行价值时,也会产生涂层正义。正义的涂层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国际关系与社会交往中,几乎都存在被涂层的正义。比如,有的主体以主张公共性、共同利益之名,谋求个体利益;有的主体以维护或挑战秩序正义之名,实现自身的利益;有的主体会以维护世界正义的名义挑起国际争端甚至发动战争。涂层正义的具体表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本质上都是以整体之名,谋自我之利;假公共之名,谋一己之私。涂层正义其实是特定的个体、主体对整体性、公共性的盗用,把正义从道德原则降为利益工具,从而对正义进行的盗用、滥用和利用。
在一个以正义为底线原则的社会,在一个人们已经具备相当的认识水平、辨别能力及道德水准,且综合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正义为什么仍会比较普遍地被盗用?涂层正义在当代社会的普遍、泛滥,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人的道德化、道德素养的提升。
日益普及的道德感形成了一种道德之幕。人们处于所谓的道德之幕、正义之幕之中,出于道德感而不愿意对假冒的道德、正义进行公开的指认与抵抗。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后果:道德总是被不道德所利用,无德之人往往会胜出。在西美尔看来,“一个社会的组织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法律和力量,来普遍强迫它的成员们必须采取习俗美德所希望的行为举止,它要依赖后者自愿不去利用它的法律的漏洞。……因此在有良知的人之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思想的真空,缺德的人会乘虚而入,从中渔利。”何况本来无德或少德之人再披上道德与正义的外衣,这就使有道德感,处于道德之幕、正义之幕之中的诸众们往往无所适从、无以应对。
涂层正义是实施者、被施者相互作用、社会互动的结果。对涂层正义的实施者而言,选择躲在正义之幕之后谋求私利,或者经过曲折的心理与逻辑进程说服自身是在坚守正义,有其合理性。经过把私利进行策略性的抽象、缩小,再用整体正义把私利裹藏起来,他甚至会获得某种道德的升华,并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主张和维护整体正义,因此其或真或假地实现了对自我的忘却,策略性地获得了自我与整体的逻辑统一,策略性地成为比常人更有道德、更为正义的人。也就是说,对实施者而言,选择涂层正义是理性的也是道德的,是特定的理性与道德的统一。
对涂层正义的被施者而言,其选择也是理性而道德的,是一种特定的理性与道德的统一。面对一种以正义为涂层的行为,有道德感的人往往出于自身的道德感,或出于对自身已有利益等的保护,而不愿意出面、当面揭穿涂层背后的真相,更不愿意组织针对涂层实施者的集体行动。正是这种由道德感所导致的集体行为无力,为涂层正义实施者的生成与成功留下、创造了巨大空间。观察现实中的交往行为、社会互动,有道德的多数面对无道德的少数、强人,往往会处于弱势,成为弱势者。有道德的多数、诸众,往往会受限、受制于内心的道德感,无法形成、执行有效的集体行动。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导致的行动无力,为涂层正义实施者的行为提供了可能。道德产生道德之幕,道德之幕产生道德悖论,道德之幕与道德悖论会影响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则会有社会后果。涂层正义正是在社会互动中,由道德感、道德之幕所催生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后果。
涂层正义的被施者与实施者,都处于道德之幕之后。一个被道德之幕所弱化;一个把道德之幕作为旗帜高高举起。在道德之幕的保护下,弱势者获得了所谓的道德感,保存了一些已有的利益;强人则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权力,甚至成为道德的营建者、维护者。对弱势者来说,道德感成为容忍强势者、道德涂层者的理由、安慰剂;对强人而言,道德也成为其安慰自己的理由、合理性。
道德及其社会后果的两面性、复杂性在涂层道德、涂层正义这个问题上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一方面,道德使人们具有道德感,道德内化为人的道德素养,对整体秩序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感的内化具有重要重大的文明进步意义;另一方面,道德感也会成为掩饰不道德行为、恶行的面具、幕布,成为不良、恶行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道德也会成为掩盖社会问题、阻碍社会进步的原因。在所谓正义、道德之幕的背后,往往存在巨大的社会实在差异,存在权力、财富、利益、地位等的固化差异、不平等。但这种差异与不平等却被涂层正义、道德之幕所掩盖。
在罗尔斯看来,面对无知之幕,人们会选择道德与正义。“无知之幕使一种对某一正义观的全体一致的选择成为可能。”但问题在于,道德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纵容丑行、恶行的道德之幕。人设(人为设置)的道德之幕,如香水一般,混合了个体与社会、自我与整体、个体性与公共性,让人们在社会接触中直接获得人造的公共性,而暂时无法获得“香水”背后的真实。
在西美尔看来,“人造香水起着一种社会学的作用,因为它在嗅觉的领域里实现着一种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和社会的目的论的综合。……给个人人格增添某种完全非个人的东西。”涂层正义的作用正如人造香水。涂层正义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与价值格局呈现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秩序的维系,当然需要价值共识,但如果在社会互动中呈现的正义、道德都不是人们的真实意图,而只是一种涂层,那么所谓的价值共识也只能是一种虚设,所进行的社会互动必然是内在高风险、高丛林性的。
涂层正义的“文明”生成
涂层正义作为一种不真实而有社会后果的正义,对社会实在、文明实在的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危害;同时,涂层现象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实在论、文明论原因。反思文明史,人类社会一直同时性地具有文明性与丛林性,但在不同的时代情境下,文明性与丛林性之间的张力有差异。野蛮与文明、丛林性与文明性之间的张力及其变迁,是涂层正义生成及变迁的重要文明论原因。正义是人类不断克服野蛮性、丛林性,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产物,涂层正义与社会的丛林性相伴生。只要社会的丛林性仍然存在,而人类又向往文明,涂层正义就会存在。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古代社会,由于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交通条件等的限制,人们主要在分布于不同区域的相对封闭的共同体之中繁衍、生活、创造文明。这个时期,社会的文明性表现为:社会分工初见雏形,人们开始进行不同类型的生产与管理活动;空间生产成果多样,人们营建出具有功能与形态多样的居住、生产、仪式等空间;社会秩序系统得到营建,为了维护共同体的运行,人们开始进行复杂的制度与观念营建。古代社会的丛林性集中表现为共同体内部的压制、杀戮,共同体之间的掠夺、战争与杀戮,尊严、平等还无法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这个时期,一方面,人们具有赤裸裸的丛林性,并不把自身与他人的生命与尊严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人们在创造器物文明的同时,开始营建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文明,开始营建与倡导正义等公共性、合理性观念,以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统一,特别是整体的存在与秩序。
正义观念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这时的正义是一种秩序正义、等级正义。所谓正义,也就是人们接受、安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与等级,也就是人们各安其分。孔子、柏拉图等轴心时代思想家的正义观是秩序正义的重要代表。这种秩序正义,深刻同构、反映着古代社会丛林性与文明性之间的张力。这时的正义,实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为核心的秩序正义,是权力主体、强势主体为了以其为主导的秩序所营建、倡导、维护的。当人们不触犯权力秩序时,正义表现为文明的,以观念、语言等“软形式”体现;当人们触犯权力秩序时,正义则表现出其丛林性、野蛮性,以暴力、审判、剥夺生命等“硬形式”体现。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开始以正义为最高范畴、最高的合理性,并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理由,来营建与维护秩序。这毕竟是一种进步。
在这个阶段,正义的涂层性特征或者说涂层化已经开始浮出水面。权力主体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强势主体,当其以正义的名义维护整体秩序时,也同时维护了其自身的存在与利益,这其中存在着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特定张力。而社会关系中的弱势主体,也开始谋求发现或赋予正义以新的含义,并开始以正义的名义来谋求自身的主体性,这其中,也存在着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张力。当人们开始以整体性之名、正义这个绝对至上范畴实现、谋求自身利益时,就不自觉地生产了一种涂层正义。可以说,从正义范畴诞生起,就已经出现正义被涂层化的可能。只要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只要人类社会的文明性还没能有效压制或取代丛林性,人们就会谋求以公共性之名偷渡私人性、以文明之名掩盖野蛮性,涂层正义也就必然生成。
商业与工业的繁荣标志着文明史进入新阶段,进入近代。这时,人类的文明性表现为人类拥有了更为多样、复杂的社会分工,营建出功能更为完备、形态更为多样的生产、生活、意义等空间,创设出更为高效、完备的社会运行与管理体系,开始拥有更为丰富、多样的物质、精神与文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之间的直接强制开始减少,人们开始尊重彼此的尊严。但社会的丛林性仍然存在,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仍存在深刻的财富、生活、权利等差异,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仍然脆弱,深层信任有待建构,人们之间的恶性竞争、身体与心灵伤害甚至杀戮与战争仍然存在。文明仍存在隐性甚至显性的血腥味。在这样一个以工商社会为主导的近代文明中,正义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从权力正义向权利正义转换,从等级正义、秩序正义向平等正义、效率正义转换。使更多甚至所有个体都获得更大更多的自由与尊严,开始成为正义的内容。以个体为导向开始成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个体为导向的价值诉求,却采用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概念“人”。近代正义观的标志性口号是“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而这里的“人”这个概念,既有公共性也有私人性,既指整体的人也指个体的人,而其主要指向是作为个体的人。也就是说,近代的正义观,是以一般意义上、公共性的人来言说个体性的人。
近代以人为核心的正义观,和前现代以权力与秩序为底蕴的正义观相比,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也为个体或某些群体以整体人、人类的名义追求个体及自身利益留下了可能,为正义被进行新的涂层化留下了空间。以人类为借口,以整体为涂层,掩盖自身的野蛮性,追求个体、自身的利益与效用,是正义在近代被涂层性使用、被盗用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正义策略的揭示。资产阶级把自身的利益上升为人类利益,但其本质是在掩盖自身的野蛮,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当代社会城市化、金融化等的推进,使文明史进入新的阶段,人类在总体上获得了新的进步。但人类的野蛮性、丛林性并未消失,体系对生活、权力对权利的压制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机会等不平等有拉大的趋势,杀戮与世界战争的可能仍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正义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日常性的要求。在这种语境下,涂层现象、涂层正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复杂性。
在当代城市化、城市更新进程中,涂层已经成为一种常用而普遍的空间生产方式。在前现代甚至现代社会,人们在空间生产中往往追求内在结构与外在功能的统一,希望生产出的空间具有耐久性,希望营建的建筑、桥梁等空间可以永久存在。但在当代,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随着市场化的深化,人们在营建建筑时,往往更倾向于追求相对短暂的使用期限,暂时性的赏心悦目,外在形象的美好。所以现在的人们日益喜欢使用各种涂层、涂料,营建出各种涂层化的空间。当代空间生产中的涂层化、表面美好化,深层同构、反映着当代正义的涂层化。
一方面,正义已经成为通用的公共价值,更多的人希望这个世界更为正义;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私性、野蛮性,社会的丛林性仍然存在,人们又会以各种可说不可说的方式谋生存、求发展。在这样一个仍存在深刻矛盾的世界,为了融入社会,人们需要言说一种通用的公共性话语,把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装点成符合正义,甚至是在维护正义。这样,就使正义的涂层化,在当代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人都需要带上正义的面具,涂上正义的油彩,喷上正义的香水。否则,人们便会遭受道德的谴责,从而丧失进入交往的资质,无法谋求实际、现实的利益。当代社会,是一个涂层深化的时代。但也应该承认,这种以正义为涂层的普遍化,在客观上也不是一无是处。涂层正义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说明人们不再敢赤裸裸地张扬暴力、诉诸野蛮,而需要把野蛮、丛林性收敛一下。这就为正义的真实化留下了可能。涂层的效应、后果有其两面性:以正义为涂层,是对恶人、人的野蛮性的一种压制,甚至可能使恶人良善化;同时,正义的涂层化,也会使良善之人变形,甚至激活良善之人的野蛮性,使良善之人变成恶人。
涂层正义的“启蒙”生成
涂层正义是仍具有野蛮性的人们在不断文明化的过程中的必然生成物。如果人们只具有丛林性、野蛮性、私人性,不会产生涂层正义,如果人们只具有文明性、公共性,也不会产生涂层正义。文明性、公共性不断增强,是历史变迁的重要趋势,但近代以来,以启蒙为标志,人们在摆脱愚昧的过程中,相对片面地把启蒙等同于个体性、私人性的成长,催生了私有意象、私有幻象的神圣性,这是涂层正义在当代日益普遍化、深层化的重要观念论原因。
近代是涂层正义普遍化的起点,涂层正义主要是一种近代现象。虽然前现代已经出现了涂层现象、以权力为核心的涂层正义,但只是随着近代启蒙运动的个体化推进,涂层正义才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康德所说,作为一种思想与观念,启蒙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人们自己决定自己,是人们摆脱由他人决定的状态,是人们获得主体性自觉、作为主体的自由。“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启蒙运用除了自由以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人们往往把自觉、自由等同于以个体为核心的主体性。这样一种以个体为本位的主体意识,有其历史合理性、必要性。对于突破宗教权力、帝王权力、宗族权力等所谓的神圣权力,对于抵抗以神圣权力为涂层谋求个体私欲的特权阶层,对于激活社会发展动能,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这样一种个体权利至上化、神圣化的主体性路向、价值确认原则,也表现出深层次问题。任何社会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个体与社会的统一。突破已有的具体公共性不等于需要抛弃公共性本身,而是需要营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公共性,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新平衡。但近代以来的启蒙观,却主要沿着个体化、个体权利、私人权利的神圣化这个路径推进,对公共性、社会性基本采取一种冷漠、放任、放弃的态度。最理想的思路,也就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认为社会性、公共性、整体性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发实现。该思路的实质是放弃了对整体性、公共性进行自觉调适、营建、干预。它等于否认了人们把握整体性、公共性、社会性的可能与能力。在个体本位、私有本位这类观念的控制下,公共性成为一种不需要进入、无法进入的荒地。这在实质上也就否认了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围绕公共领域营建所取得的制度与思想成果。
但问题在于,社会性、公共性始终是一种必需品。当人们遭遇社会经济整体无序、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时,会再次希望与诉诸正义,希望更为合理的公共权力、公共领域。一方面,人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个体性、更多的个体自由,不愿意参与整体事务;另一方面,人们又离不开社会性、基本的社会正义,并希望有人来主持、倡导社会正义。正是这种矛盾状态,为涂层正义的实施者盗用公共性、盗用整体之名、盗用正义范畴,以谋求私欲、私利提供了可能与空间。个体神圣性、私有神圣化,必然辩证地导致涂层正义的出现。个体至上、私有至上,有其打破权力固化、激活个体活力的历史效用。但当历史条件转换,既有的固化、被侵占的公共性已经被击破,社会需要新的公共性时,再继续倡导个体、私有的神圣就会导致整体效率的低下,导致无人问津、无人主持的公共性、社会正义被所谓的强人所涂层、利用和盗用。
在普遍的私有、单子、个体意识左右下,涂层正义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认识能力的普遍提高,通过数次的吃亏、经历与操练,每个人在逻辑上都会发现借用公共性、以社会正义之名是可以获得私利的,这样每个人都可能学会熟练运用涂层正义来维护私利、扩大私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涂层正义的实施者。其结果是社会整体的虚伪化、非真实化,是社会整体性地进入新的以正义为掩饰的丛林状态。每个人都备有一件皇帝的新衣,可以随时拿出来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充满正气的正义面具,需要时随时可以戴上。
这样的社会在整体上就成为由人格、精神、价值分裂的个体组成的内在分裂性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真正凝聚力的松散性社会,一个没有持续创造、创新能力的柔弱性社会。如果没有重大的外部竞争,这样的社会是有可能维持下去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被深度涂层的社会,必然遭遇外部竞争。面对外部竞争的加剧,这个涂层化的社会,这个以私有、个体为至上神圣观念的社会,这个以社会正义为涂层的社会,必然逐渐丧失竞争能力,沦为世界文明总格局中的边缘社会、失败社会。
这种状态成为现实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私有至上、个体至上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成为制度性安排。当一个社会的整体建制不再以公共性为基石,没有处理好私人与整体、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弹性时,并把行政、警察、法庭等公共领域、暴力机器统统改制为以私有意识、个体权利至上为导向时,当一个社会的整体行为机制、行动理论、行动文化都是充满了私有意向时,涂层正义、涂层社会也便真正制度化地生成了。反思文明史,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共同体,都需要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弹性平衡。极端个体所有制的最大问题,就是丧失了这种弹性。当然,极端共同所有制的最大问题,也在于丧失了这种弹性。极端的私人所有制与极端的共同所有制,其本质都是一种有问题的私人所有制,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而辩证的相通性。极端的共同所有制往往为某些特定的个体所盗用,从无人负责制成为一种特殊的私人所有制。
在现实中,诸多涂层正义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正源于这种无人负责的共同所有制所滋生的个体占有心理。社会性、公共性需要通过具体的公共领域实现,但如果公共领域没有一个好的实现方式、运行机制,就会被少数甚至个别强人所盗用,从而沦为实质上的个体所有制。不透明的共同所有制必然导致无耻者胜出。不透明的公共领域、共同所有制,就如一个无人所有的公共草地,为强人所占据、践踏。现实中的诸多涂层现象,其深层的制度论原因,正在于两类私有制。一种是把个体所有神圣化的私有制,一种以共同所有制为名的实质上的强人所有制、私人所有制。没有对片面启蒙思想深层同构的异化私有制的真实破解,没有共同所有制的实现方式的规范化、透明化,没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合理弹性化,涂层正义不可能消解。
极端的个体所有制、极端的共同所有制,都会导致泛民主义、泛民论。涂层正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泛民论。所谓泛民主义,也就是在片面绝对的个体意识左右下,人们在建制上、行为上放任情境性的民意,被暂时性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所绑架,放弃对持久性、长久性的利益与合理民意的营建、坚守。泛民性的意见、利益、程序等,不是可持续民意、可持续利益的真实表达、真实呈现。泛民论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被片面理解的启蒙运动,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人生而平等。人生而平等,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论断。现实中,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在生理、心理,还是在阅历、性格、能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现实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社会现实。差异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差异的不可变化、不可流动。当人们把必须的公共领域,放任为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平等,放任为一种所谓的尊重即时性的程序正义,就为强人操纵程序、利用正义留下了空间、提供了可能。泛民主义的结果往往是强人极权制,松散的多数个体、诸众被强人操纵,被戴着正义面具的强人操纵。当代涂层正义是片面发展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启蒙运动的现实必然。
涂层正义“行为”生成
从秩序、等级、权力性正义,到自由、平等、权利性正义,是正义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正义的每个阶段,都存在被涂层化的可能。涂层的生成与普遍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实在原因,同具体社会中个体与整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张力,同道德之作用和效用的两面性,同近代以来启蒙精神的片面发展都有重要关系。但这些只是涂层正义生成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是涂层正义生成的客观土壤与社会语境。有土壤与条件,不等于种子一定会发芽。涂层正义变成一种现实,一种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现实,同人们的行为机制与心理选择有关。从行为哲学的角度看,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人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心理进路与行为机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正义的,把自身认证、确认为一个正义的人,让自身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正义者甚至正义化身的。为了更深入地把握涂层正义,需要对涂层正义的发生进行更为具体的行为哲学反思、心理机制反省。
面对各类相同或不同、复杂或简单的环境,人们总会进行行为选择。涂层正义是不同角色的行动者在复杂环境中共同营建而成的。涂层正义的发起者、实施者和涂层正义的接受者、被施者共同作用,使得涂层与涂层正义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断生成、延绵不绝。
从涂层正义的实施者、主张者的角度看,他其实处于一种精神分裂或者说价值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涂层正义的实施者,是一个具有一定公共意识、认识能力、道德素养的人。他之所以不选择以赤裸裸的方式主张自身的利益,是因为其对社会条件、环境格局等进行了理性判断,知道在不违背已有的价值共识,特别是在公共性的旗帜下,把个人性替换成整体性,不易触发他人的反抗,更容易以一种心理、交往等综合成本较低的方式获得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涂层正义的实施者,又具有坚定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会不懈地坚守、坚持自我中心和自我利益。自我利益是涂层者的真实出发点,个体意识、私有意识是涂层者的核心意识。涂层者是坚定的自我利益中心论者、自我中心者,甚至是一个具有深层自我封闭、自我保护倾向的自我中心体。
涂层正义的实施者,作为一个具有道德基础与理性判断力的人,为了不至于真的走向精神与价值分裂,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进程、策略,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在潜意识中选择性地忘却自我,把自我诉求提升为一般性的整体性诉求,从而在自我意识中实现自我与整体的策略性统一,并再一次忘却自我,在公众中倡导所谓的公共利益,坚决反对、压制和其有异议的人及其主张,标榜自己的无私、无我,最终实现自我与整体的合体。这个曲折的心理进程,这个说服自己的进程,是涂层正义实施者必然需要经历或进行的。人人都追求利益是正义的,我追求利益也是正义的,我是在为整体追求利益,我是在主张正义。通过不断地混淆、滥用自我与整体、个体与人类这两类范畴,涂层正义实施者最终实现了对自我的解放,成为一个坚定的正义维护者。通过这个似乎没有问题的逻辑进程,通过阶段性地混用人(作为整体性与个体性的人)这个概念,涂层正义实施者实现了其与正义的合体,实现了其道德的升华,并可能真实地相信自己就是正确的、正义的。由此,面对公众、大众,涂层正义的言说者,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对自我进行策略性抽象,以公共话语言说个体诉求,是涂层正义实施者的基本策略;通过忘却自我实现对无耻的超越,是涂层正义实施者的心理路径。
从涂层正义的被施者、接受者的角度看,涂层正义的被施者,也是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人。几乎每个涂层正义的接受者,在个体理性层面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涂层主张者有其问题。但问题在于,每个被施者,都没有动力去直接挑战涂层主张者。因为他进行这样的挑战,并不必然会为其带来利益,且很可能使自身已有的利益受损。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涂层实施者是错的,但大家都不会出来行动。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在不清晰的公共利益与清晰的个体利益之间,选择维护潜在或既得的个体利益,这种微妙心理在被施者那里体现得非常充分。正是这种状态导致了涂层实施者,能够持续、公开地主张、实施其涂层正义行动。当一个意志坚定的行动者,面对一群意志不坚定或者没有自觉集体意识的行动者、诸众时,意识坚定者往往会影响、左右集体行动。涂层实施者正是一个坚定意志的人,所以他往往能够持续地进行涂层。而涂层的被动者,则是一群意志不坚定的人,一群无法形成有效集体行动的个体,一群无意愿控制社会互动结果的诸众。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式的集体无力、集体无为状态,使涂层者能够持续地进行涂层行动。
也就是说,在涂层正义生成的背后,可以发现一种特定的集体行动、社会互动的逻辑。涂层正义是涂层实施者与被实施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实施者而言,其选择是理性的,用正义等公器、公共性范畴贩运私货,只要不被发现,综合成本是最低的。但只有实施者,没有被施者客观上的同意与许可,这种以公贩私的勾当也不可能成功。广大的被施者,正是涂层正义生成的丰厚土壤、纵容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涂层正义的被施者其自身也是一种涂层正义的实施者。被施者其实是用一种不伤害人、为别人留面子的道德感为自己解脱、涂层自己,或者用一种社会自然会实现其正义的放任式的道德观念为自己解脱、涂层自己。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涂层道德、涂层正义,是用一种自认为合理、无害的道德感为自己的不作为、不行动、不承担负责进行涂层。在这个意义上,实施者、被施者都是涂层正义的成就者。
从社会行为学、行为哲学的角度看,涂层活动、涂层正义是一种社会性、集体性的社会互动过程、社会行动结果。涂层正义的历史与现实存在,深层反映了涂层正义的实施者及被施者在财富、资源、机遇、信息等方面的不均等、不平等。涂层正义的实施者往往是那些具有相当社会资源、社会权力的主体,他们在社会互动中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更完备的社交网络、更丰富的社会资源等,当然也往往拥有更为坚定的自我至上、个体至上的意志与信念,且拥有更多的既得利益,所以往往是社会互动中的主动方。而涂层正义的被施者,则拥有相对较少的信息、网络、财富等资源,所以往往在社会互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社会互动中的被动方。
不平等、不均等目前仍是社会互动中的重要常态。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已经在正义的旗帜下,被涂层为平等的,并被凝结、体系化为一种以正义为名义设定的相对固定的程序、制度、习俗。实质上的不平等、不道德已经被形式上、表面上平等、道德的机制、体制、秩序所遮蔽、所涂层。而人们又在遵守、维护这种被道德化、涂层化体制、机制、程序,不去谋求改善这种有问题的制度、机制、程序。也就是说,当人们无反思地进入、接受一种具有涂层性的社会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所形成体制、机制、程序时,这种涂层化的体制、机制、程序就成为一种很难撼动的行为环境、行为文化,从而使涂层正义的被施者、实施者都成为被深层规训的所谓道德人,无力、无意愿挑战、质疑既有体制、机制、程序的所谓的有道德感的人。正是这种深层异化的程序、规则,这种由涂层正义的实施者、被施者所共同营建,甚至被神圣化的社会互动机制、社会互动文化,使涂层成为现实。
涂层正义的“透明”消解
反思历史与现实,涂层已经成为现实中的一个哲学现象,亟需进行自觉的哲学关注与哲学应对。涂层正义的生成同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道德水平、制度张力、行为特征等密切相关。涂层是人类文明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生活节奏、社会节奏日益加快,而人们对美好生活、正义社会的要求日益普遍化的时代,涂层的普遍化、泛化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地看,以正义为涂层毕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比赤裸裸的野蛮与暴力要文明许多。但问题在于,涂层追求的往往是暂时、表面的美好,而不是内在坚实与外在美好的统一。涂层又往往会掩盖内在的问题,给人虚幻的美好、正义。只要这个社会还有丛林性、野蛮性,只要这个社会的机制、制度还有问题,只要人们还没有克服深层的私有化、个体化倾向,只要公共领域的实现方式还不合理、不够透明,涂层就有继续存在的土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有扩大化、普遍化的可能。充分认识涂层正义,以流动、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着力推进社会建制、发展机遇等的合理化,对于逐渐减少涂层现象,建构一个更加真实的、可持续的社会,有基础作用。
其一,进一步打破利益与阶层的显性与隐性固化,营建透明、可流动的差异型社会。
涂层正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富、利益、机会、阶层等的显性与隐性固化。社会财富、社会利益、发展机会等的适度差异,对于激活人们的竞争心态,克服慵懒社会心理,推动社会总体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人们之间的财富、机会等差异过大,特别是差异走向固化时,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涂层现象的深化。贫富差异、阶层差异过大、差异固化的社会,其总体风险是巨大的。为了化解这种风险、保有自身的利益,既得利益者的一个重要理性选择就是将自身的利益及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将自身的利益、行为正义化,将社会正义以及维护社会总体正义的警察、法院等公共强力据为己有,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是人们保有自身利益的最可行、最根本、最现实的方式。这是导致正义被涂层化、整体社会道德被涂层化的结构性原因。
这样,避免涂层正义走向深化、正义涂层化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实在论路径,就是打破利益与阶层的固化,营建一个财富、机会等虽有差异,但差异可流动、差异透明、流动透明的社会,一个流动、差异、透明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正义不是绝对均等,正义也不是没有差异,而是差异与流动的统一。一个可持续的正义社会,真实的正义社会,既不是一个均等化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利益与阶层固化的社会,而是一个差异可流动的社会,即财富、机会等获得方式的公开、透明的社会。营建一个透明的流动差异化社会,一个财富、阶层虽有差异,但差异透明、差异可流动的社会,对从源头上减少涂层正义的生成可能,逐步化解涂层正义问题,有基础作用。
其二,提高社会权力与公共领域特别是微观领域公共权力运行方式的规范化、透明化。
权利、利益通过制度化的权力、公共领域来保障。在一个结构日益复杂、分工领域日益多样的社会,宏观与微观、不同层面的权力与公共领域的作用日益重要,这就使不同层面的公共权力、公共领域日益成为人们博弈的对象。如果公共权力与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不透明、黑箱化,就会为涂层者的涂层行动提供可能与空间。在一个不透明的社会,社会权力、公共领域往往被强人所占据、利用、涂层。打破权力黑箱,具体探索、营建不同层面公共权力的合理实现方式,提高各层面公共领域与社会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水平,特别是透明度,对有效解决正义的涂层化问题有基础作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单元,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方式会有差异。但不管采取何种具体的实现方式,公共领域、社会权力运行的公共、透明、可流动,都是保障公共权力不被私用、盗用、私有的重要基础。公共权力不透明、公共权力固化,透明度不高、流动性消失,公共权力成为少数人可能永恒占据的特权,是涂层正义、涂层政治生成的重要体制论原因。
公共领域、公共权力的规范、透明,需要顶层与基层、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同时推进。对现实而言,推进微观、基层公权的透明、规范,其意义更为重要。反思现实,不少微观领域、具体单位、基层社会单元的权力运行仍存在拟家族化、准家族化的问题。一些基层单元、基础单位往往成为某个强人的私人领地。通过人、财、物、机会等的综合、不透明运作,一些强人牢牢掌握其所在单位、单元的公共权力,把公共权力变成其私人的工具,把其所在单元变成了私人领地,把现代基础组织变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带有人身依附性的准家族性的单元。打破微观领域、基层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倾向、家族化倾向、人身依附倾向,对推进社会整体权力的规范化、现代化、透明化,有效克服、减少正义的涂层化问题,有基础意义。
其三,全面理解启蒙精神,减少权利粘性,推进个体权利获取方式的透明化、规范化。
涂层正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精神的片面推进,把人理解为个体,把主体性异化地理解为个体性、个体权利的神圣、至上。反思文明史,私人领域总是相对于公共领域而存在,私人领域不断扩大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趋势,表现为个体财富、行动、话语等的自主性不断扩大。但是,私人领域、个体权利得到确认与发展,不等于个体权利、私人领域的至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平衡,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基础。一个只要个体性、不要整体性的社会,必定会导致“权利粘性”,走向整体失序,进入新的丛林状态。由单子式、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必然理性地选择以借用社会正义、以涂层正义的方式保护自己和谋求私利,从而使社会在整体上沦为人人伪善的涂层社会。在保障个体权利、私人领域权益的同时,避免个体权利的过度粘性化,避免私人领域的固化、神圣化、至上化,对于克服涂层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这就需要复兴启蒙精神内含的公共性。在康德看来,启蒙的重要内容是人的主体性成长,但这不是个体性的极端膨胀,启蒙不等于没有社会规范,不要整体性。“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也就是说,主体性包括个体性,但不等于个体性,启蒙不是人的主体性的片面个体化成长,而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成长,这种全面成长包括人对世界整体运行规律、对社会整体运行构架的更为自觉的认识,对人之公共性、社会性的自觉确认。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具有共生性,片面强调任一方都有问题。启蒙的重要意蕴是明亮、透明,推进权利、个体权利获得方式的透明化,是全面启蒙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以非对立思维重构启蒙精神,是克服涂层正义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总之,在一个仍具有丛林性的社会,美好、有价值的东西总容易被盗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涂层现象将有一个扩张的阶段。但人们将发现市场性不等于丛林性,真实的才更为持久。这时,涂层现象将会呈减弱趋势。这可能需要时间,也必然有曲折与磨难。但时间的长久、曲折与磨难,不能成为停止追求真实正义的理由。公开、透明、流动,是克服涂层政治、涂层问题的重要原则。只有不断提高社会运行的透明度、流动性,才能真正有效地减少涂层正义。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编辑:冉玲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3-27 21:20
【案例】黑格尔在30岁之前都干了些什么?
、

公元1785年,一个少年进了斯图加特市立文科中学:他叫黑格尔,是一名税务局书记的儿子。父亲认为,儿子在学校里上点课是不够的,尽管黑格尔把每门学科都学得很出色,升级考试的成绩总是优良,但父亲还是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
黑格尔读书读得很多,把零用钱都买了书。他常到公爵图书馆里去看书,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趣事。图书馆每逢星期三、六开放,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一张长桌,上面摆着钢笔、墨水和纸张,供读者使用。读者想看什么书,只要把书名写在纸片上,交给图书管理员,他马上就会把书给找来。黑格尔第一次逛到这里,借了本巴托的《美学导论》德译本,读完了其中论叙事诗一章。
他喜欢读严肃的书;读这些书的时候,还养成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那就是,把读过的东西详细地摘录在一张张便贴上,然后按照语言学、美学、面相学、数学、几何学、心理学、史学、神学和哲学等项目加以分类。每一类都严格按照字母次序排列,所有摘录都放在贴有标签的文件夹里,这样,不论需要哪一条摘录,都可以马上找到手,这些文件夹将伴随这位哲学家一辈子。
年轻的黑格尔在家庭图书室里,保存着一卷小开本的德译莎士比亚剧作集,这是他的一个最受尊敬的教师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送给他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题词:“你现在还读不懂,但不久就会读懂的。”
在黑格尔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德国的诗歌散文名著陆续问世。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先知拿单》和《强盗》等等。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从中学毕了业,还没有读过这些作品。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是《索菲游记:从默墨尔到萨克森》,这是一部模仿英国家庭小说描写七年战争时期东普鲁士市民生活的小说。赫尔姆斯的这部六大卷精装本的小说,有大段大段惩恶劝善的说教,同时以清新气息的写实手法描写了市民间千篇一律的日常琐事。
黑格尔的日记内容也散发出少年老成、谨小慎微、陈谷子烂芝麻的气味,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之处。黑格尔为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甚至枯燥无聊。黑格尔的传记作者菲舍尔写道:“当时谁也不曾预料到,这个陶醉于如此一部乏味小说的平庸少年竟然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还将孜孜不倦,力图上进,有朝一日作为当代第一位哲学家而出现。”
在幽静的伯尔尼,黑格尔埋头读书和写作,他打算写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文章,他的笔记本上记着许多关于主观精神哲学的材料。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思考一些古怪的问题:直观是如何变为自觉行动的?神经怎样起到感觉器官的作用?灵魂在哪儿?英国人普里特莱和哈特莱都曾企图解答这些问题。
无论如何,黑格尔是知道他们的著作的,那些著作已由斯图加特卡尔学院的教授、后来在图宾根修道院当教授的阿贝尔译成了德文。阿贝尔的论文《论人的观念的本源》的某些部分,黑格尔都逐字逐句地抄录了下来。
黑格尔对康德著作的理解日益加深,逐渐领会了它的意义。他给谢林写道,我期待康德体系及其圆满成就在德国引起一场革命。他感兴趣的不是《纯粹理性批判》(他为这部著作所吸引还是后来的事)而是康德的关于实践哲学的著作。
费希特为这些著作所作的解说:人类终于登上了一切哲学的顶峰,这个顶峰高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但是,为什么人们迟至今日才想到重视人类的尊严,才想到赏识人类可以同一切神灵平起平坐的能力呢?我认为,肯定人类本身是如此值得尊重,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标志;它证明压迫者们和人间的神衹们头上的光轮消逝了。
哲学家们正在证明这一尊严,人们将学会感受这一尊严,将不再去乞讨被践踏的权利,而是由自己来恢复它,并把它据为己有。宗教和政治狼狈为奸,宗教所教诲的正是专制政治所要求的东西……
黑格尔情真意切地呼吁: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挡住太阳的树叶能怎么样?树枝能怎么样?拨开它们,向着太阳,努力奋斗吧……
那时,谢林已经发表了他的理论见解,而黑格尔觉得他和谢林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敢发表他的批判意见。感觉自己仅仅是个学徒,谢林请求黑格尔谈一谈自己的学术研究,黑格尔却说:我的作业不值一谈……
可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撰述是很丰富的。他在伯尔尼写过一部早在图宾根就已动笔的著作。这部著作没有写完,直到黑格尔死后才以人民宗教与基督教这个书名出版。在这本断简残篇中,黑格尔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宗教……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使他对宗教感兴趣的,首先是“心灵”,因为真正的、活的、“主观”的宗教表现在感情和行为之中。
“客观”的宗教是关于上帝的呆板知识,是和“主观”的宗教相对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包括在“主观”的宗教里面的。如果“主观”的宗教可以比作活生生的自然之书,那末,“客观”的宗教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标本陈列室,他把昆虫弄死,把植物晒干,把动物泡在酒精里,并把大自然区分开来的一切压进了一个统一的模式。
大自然把无穷无尽、各色各样的目的编织成一根友谊的纽带,而自然科学家却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统一的目的。换句话说,“主观”的宗教是善人特具德行的同义词,而“客观”的宗教则体现了神学;至于两者在道德功效上孰高孰低,黑格尔持谨慎态度,他只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宗教的色彩,而在于宗教是否成为关乎心灵的事。
“客观”的宗教依赖于知性,但知性并不能把原则付诸实践,因为知性只是一个谄媚迎合主人心意的仆人。启发知性固然会使人变得机灵,但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也不会更智慧,因为智慧不是学问。有人说,知性产生真理,但是哪一个凡夫俗子敢于断定,什么是真理?
黑格尔从启蒙神学那儿借用于“天启宗教”这个概念,来称呼倚仗权威与传统的僵化的宗教。天启宗教的对立面是人民宗教。人民宗教虽然建立在理性之上,但它首先却诉诸感情,而且一切生活要求和国家公共事物都是和人民宗教息息相关的。透过这些神学术语,他显然提出了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个问题。年轻的黑格尔认为(卢梭也是这样),这种制度的典型就是古代的民主制。
黑格尔所批判的首先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它的现状;不是关于人格神的概念,而是都会的机构。谢林因为康德派哲学家信手乱用道德论据,便在一封信中嘲笑了他们:“一下子,跳出来一个救星——天上的一个独特的本体”。读了谢林的这段话,黑格尔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他问谢林: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根本不能达到这一步?
谢林马上给了他一个严厉的答复:“你问我是不是认为,我们不能用道德论据达到一个独特的本体?老实说,你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真没想到,一个熟读莱辛著作的人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而你却它提出来了,以便探悉我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它;至于你,想必是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两人也不再有关于上帝的正统观念了。那么,我的答复就是:我们所达到的比一个独特的本体更远。同时,我已成为斯宾诺莎派!”
黑格尔却不能宣称自己是个斯宾诺莎派。基督的形象反倒更吸引了他。1795年夏天,他在伯尔尼附近的楚格(瑞士风景区)撰写新宗教创始人的传记。这部传记表面上近似福音书,但是,里面写的是些什么呢?一字不提报喜节、圣灵妊娠,奇迹和死者复活等等。黑格尔笔下的基督是一个诉诸人的理性的道德家。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神学家的观点有了变化;一年以前,他还在颂扬感情,而今感情让位于理性了。
他几乎让基督嘴里讲出了康德的绝对律令:你们如果希望人家按照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法则对待你们,那么,你们也应当按照同一原则对待人家,这就是伦理的基本法则。黑格尔这时还没有把伦理和道德分清楚,于是伦理成为虔敬的唯一尺度。人人都要按照他的行为来衡量,殊不知人即个人却高于一切。
过了几个月,这位青年思想家又埋头于别的问题,基督教以个别人物事迹为内容的讲道说教,已不再适合他的口味。他开始写一篇新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那篇基督教的天启性,大家知道,黑格尔所谓的天启性,意味着稳定,凝固,因此也就是僵化。
黑格尔把基督的原始教义和后来产生的有组织的基督教区别开来,又把后者和成为国教的基督教区别开来。基督教的这三种不同形态,是基督教日益僵化、即“天启”特征日益深化的几个阶段,而这些特征在它创始人的训诫中也早就有了。基督当年便努力通过人们对于他自己的权威的信仰,来破除犹太教的“天启性”。
且看基督周围的情况吧。黑格尔将基督同苏格拉底作了比较,人人都可以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的朋友中有商人,士兵,政治家,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职业。与此相反,基督身边只有十二个使徒,他们作为他的学说的宣讲者,只是为了基督,为了他的言行而活着。这就是精神上的独断主义和对权威的信仰创造了条件。
基督教是怎样得势起来的呢?古代世界的“人民宗教”又为什么消失了?在黑格尔那个时代流行过一种答案,据说当初人们已不再不能信奉那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搞不正当关系的希腊诸神,于是对基督的信仰便起而代之,更好地适应了人们心灵的需要。
可是,黑格尔并不满意这个答案。古代宗教之从人民心中一笔勾销,并不是由于书斋结论,而是基督教得以传布开来,也不是由于人民受到开导。黑格尔认为,希腊罗马的宗教本是自由人民的宗教,人们一旦丧失自由,这些宗教也就消失了,失去了意义,变得软弱无力,对人们没有用处了。如果河床干枯了,渔夫还要鱼网干嘛呢?
由此看来,基督教是专制政治的产生。国家本是由公民的自身行动产生的,一当国家观念从公民心中消失时,但出现了基督教。这时,为国家这个整体操心,已只是一个人或少数个人的事情,人人都有被指定的地位,这个地位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彼此不同。国家机器的管理工作则由少数公民来承担,这些人的作用和小齿轮一样,只有和别的齿轮连接在一起才获得意义。
谁也不再为整体而努力了,各人都为自己劳动,或者被迫为别人劳动。
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决没有宣扬教会神学,倒不如说它猛烈了攻击了教会。当然,首先是针对基督教,但也不仅仅针对基督教。整个教会体系的基本错误,就是否定人的精神有权具备各种能力,特别是其中第一种能力,即理性;而当理性被教会体系所否定之后,教会体系就无非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系。
这就不单纯是对于官方基督教的批判了。黑格尔揭露了教会对精神自由的压迫。宗教不过是专制政治的外衣,而专制政治则卫护着现存的宗教教义。
为了重新获得失去了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必须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在某个时期内,年轻的黑格尔认为,改造的办法在于消灭国家。他在1796年初夏所写的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纲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立场。在这篇残稿中,他按照赫尔德的意思,把国家说成有点机械性,反人道——是由暴力产生的,是注定要消亡的——是一架机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把自由人作为机械的齿轮装置来对待;而它是不应该这样对待自由人的;因此它应该消亡。哲学家黑格尔想剥开国家、宪法、政府、立法这一整套卑劣的人造物的画皮——彻底剥开。
黑格尔还认为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他把美的思想看作最高的思想,并号召创造一种新的神话学,理性的神话学:现在我深信,由于理性包含所有的思想,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我深信,真和善只有在美中间才能水乳交融。哲学家必须和诗人具有同等的审美力。我们那些迂腐的哲学家们是些毫无美感的人。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一个人如果没有美感,做什么都是没精打采的,甚至谈论历史也无法谈得有声有色。
简直不能相信这些话出自黑格尔笔下,这和他后来所写的一切想去实在太远,以致有人怀疑它们未必是黑格尔写的。的确,黑格尔这里把理性包摄在美感之中,而理性到黑格尔晚年却占据着最高的位置。未来的国家辩护士在这里还把国家攻击得体无肤。但是,这种国家观在一定期间却正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国家观,而且第一个体系纲领决不是这种观点的唯一证明。
我们且来看看耶稣传吧,黑格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总希望看到在尘世建立起上帝的王国;总有人对你们说,这里或那里有这样一个受道德规范约束的人与人相亲相爱的乐园——不要相信那些谎话吧;不要希望在一个冠冕堂皇的人的团体中——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表面形式中,在一个由教会诫律所统治的社会中,看到上帝的王国。
黑格尔喜欢在伯尔尼和楚格郊区散步,有一次,他和三个跟他一样的家庭教师结伴,一起到阿尔卑斯去游览了几天。他们到了格林德沃尔特冰河,到了莱辛巴赫瀑布,接着去圣哥大,又跨过恶魔桥,渡过菲尔瓦尔德施塔特湖,到了卢策恩,然后从那儿回到伯尔尼。
黑格尔对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无动于衷,黑格尔在旅行日记中写道:无论是眼睛还是想象力,都不能够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大土堆上找到什么可以赏心悦目的,或者可以消遣消遣的……理性想到这些山岳的恒久性,或者看到人们称之为巍巍崇高的风貌,也没有发现一点什么可以使它铭记不忘,使它不得不表示惊讶或赞叹的。凝望这些永远死寂的大土堆,只能使我得到单调而又拖沓的印象:如此而已。
哲学家全神贯注于本世纪沸腾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阿尔卑斯山岿然不动的庄严气象引不起他的兴味。他所追求的既不是寂静,也不是安宁。如果他在大自然中找到某种和他的思想相应的东西,他才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一个人迹罕至、岩石众生、根本无法居住的地方,他却冥想到目的论的荒诞无稽,因为这种学说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人呆在这种地方,简直不得不从山上偷取一点可怜的食物,哪怕明天他会不会被一场雪崩所吞没,他也没有把握。在这种不毛之地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只是不会产生物理目的论,因为这种理论想使人相信,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为着人的福利而安排的。黑格尔觉得他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人们宁愿洋洋得意地认为,一切都是由一个外在的本体造成的,而不愿承认,是人本身为大自然制定了它的一切目的。
投合黑格尔口味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他毕生爱好为人所掌握并加以整顿过的大自然。晚年的黑格尔欣赏荷兰的肥沃牧场、蒙麦特里的花园,多瑙河谷地和海得堡的郊野。未曾开发的荒芜的自然使他兴致索然。
再说,黑格尔远离亲友,久滞异邦,寄身于一个一本正经的贵族之家,总不会感到那么自在,他请求荷尔德林和谢林帮助他摆脱这个环境,让他回到故乡去,过了一些时候,到1796年10月,那时正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的荷尔德林才给了他一个佳音:商人戈格尔表示想以十分优厚的待遇邀请黑格尔到他家当家庭教师。
1798年,黑格尔第一次在法兰克福印行了他的一本译作。这是一本原作者姓氏不详的小书,封面上印着关于瓦得州对伯尔尼城的旧国法关系的密信。译自一个已故瑞士人的法文本,书中附有注释等字样。黑格尔是本书的译者,也是注释者。《密信》的作者原来是瑞士律师卡特,他在这本书中揭发并抨击了伯尔尼在法国人进驻之前一直实行的专制制度。
黑格尔注意到作者的几点想法和自己的见解不谋而合。伯尔尼州缺乏公民自由,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权势人物蔑视法律,判决权完全掌握在大小官府手里。因此实际上谈不上奉公守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州那样,有那么多人被处决,被绞杀,被辗死或者被烧死,被告答辩徒具形式,犯人根本享受不到这种权利;最高法院看也不看案卷,就机械地批准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黑格尔和以前一样,首先关心政治、社会状况和宗教。不久,他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不久,他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799年初,黑格尔读了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他开始思考财产问题,并推断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财产。
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所写的一个片断中,我们可以读到:“在近代国家中,保证财产安全是决定整个立法的关键,公民们大部分权利都与此有关。在古代一些自由的共和国里,严格意义的财产权,即我们所有官府的心事,我们国家的骄傲,就已经为国家宪法所侵犯……究竟有多少严格意义的财产权,不得不为了维持共和国的形式而牺牲,这是大可研究的。如果认为,法国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制度要求大幅度地均分财产,其根源仅仅在于贪欲,那未免冤枉这个制度了。”
看来好像哲学问题已不能打动年轻思想家的心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只要观察得细心一点,还是可以看到黑格尔在精神世界中,哲学问题仍起着隐蔽的作用,在某些场合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尽管它表面上退居幕后。证据就是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所写的最重要的著作,一篇没有完成的手稿:「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
和以前一样,主角还是耶稣。但是,这个耶稣已不再是康德伦理学的代言人,而是这个学说的反对者了。乍见之下,黑格尔好像只是在驳斥古犹太的立法之父摩西。他这样写道,摩西的十诫是作为上帝的话语被提出来的,它们不是真理,而是律令。犹太人是不自由的,他们仰仗他们的上帝,而为人所仰仗的东西,就不能对人具有真理的形式。犹太人——和希腊人相反——是一群奴才,而奴才的最高真理恰在于他有一个主人。「统治和屈从」是同真理、美和自由水火不相容的。
黑格尔笔下的基督要改造古犹太国流行的拘泥教规的风气,教人注重十诫的精神,注重驿上帝和对邻人的爱,这种爱把个人气质和社会责任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了。文章接下去就不再是基督和摩西之争,因为黑格尔开始直接同康德展开了论战。
康德认为,道德是个别服从一般——服从良心的驱使——换句话说,就是一般战胜了同它相对立的个别,而黑格尔却认为其任务在于使个别上升为一般,通过二者的调和来扬弃这一对立。这里显示了黑格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后来由此开始产生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将同个别和特殊结合起来的非形式的一般呢?辩证逻辑就是从伦理学萌芽的。
问题发现了,任务——如何把个人气质和道德诫律、把个别和一般结合起来。但是黑格尔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连他自己都丝毫不能满意。黑格尔把生活及其最高表现,即能够调和矛盾的爱的感情,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段。
旧约全书有一条诫律是:不要杀人!耶稣拿和解精神(爱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更高的禀赋和那条诫律作对比,前者不仅不违犯后者,而且使后者成为多余;和解精神包含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诫律那样贫乏的东西。
如果不提到德国的神秘主义,那么,就没有把决定黑格尔精神发展的因素讲齐。他在法兰克福摘抄过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和陶勒尔的著作。他的不少辩证思想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神秘主义。
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在青年时代甚至赏识过巴德尔。巴德尔的几何学方法激发了黑格尔的想象,他想在一个四边形里作出一些三角形,并在这些三角形里作出一些小三角形,试图利用这个方法从各方面把世界加以体系化,但是他终于发现这类直接的直观模式是不可能有的。
黑格尔厌恶正教,却对异端抱有好感。他认为,只要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教会不停止扼杀思维,异端和教派就会存在下去。如果说黑格尔把宗教放在哲学之上,那么他这里并不是指的官方的教义。
正因为这样,哲学不得不和宗教一起完结,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多少是和非思维相对立的,又多少和思维着的人和被思维的东西相对立……
宗教扬弃了个别存在的一切矛盾,生活在宗教中体现了某些无限的东西,使一切对抗都从中消失。
1800年,当黑格尔三十岁时,他父亲已经于一年前去世,黑格尔分到的遗产是一笔不太大的款项,约三千多古尔盾,但是要登上大学讲坛,这笔钱倒也够用。
1801年1月,黑格尔启程前往耶拿。
编辑:王豪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4-6 13:39
【案例】玛娜数据伦理评论(No.1):数据共享是数据伦理的应有之义
作者:赛博风
文章来源:人工智能伦理
数据共享:数据伦理的应有之义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发表了“唤醒沉睡的数据”系列文章。2014年4月14日发表闫傲霜的“唤醒‘沉睡’的大数据”;2015年10月12日发表彭科峰的“唤醒‘沉睡’的科学大数据”;2018年10月16日发表甘晓、姜天海的“唤醒‘沉睡’的医疗大数据”;2019年4月1日发表张晶晶的“唤醒‘沉睡’的医疗大数据”。本期我们推荐的是张晶晶的文章。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作为信息的载体,其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在医疗领域,大部分的医疗数据都处于“沉睡”状态,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是实现医疗数据共享的阻碍。如何让大数据在医疗领域更好的发挥作用?该文从实现专门数据库与大数据平台相配合、跨界合力打通数据“孤岛”两方面进行了讨论。同时指出,大数据信息安全是实现数据共享的前提,尤其是医疗数据这种敏感的隐私数据。因此,要更好的在医疗领域实现数据共享,打破医疗数据的“沉睡”状态,实现医疗数据价值最大化,必须首先加强对信息安全的保护。
目前大数据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貌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数据孤岛和数据滥用。一方面,目前数据共享严重不够,许多数据处于沉睡状态,形成了诸多数据孤岛。另一方面,“数据共享”到了滥用的程度,不受任何约束。
人本主义数据伦理是认识和解决大数据之困的重要视角。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倡导数据共享,消除数据孤岛,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发挥数据的效用。鼓励创新,增进人类福利。同时,人本主义数据伦理提倡有规范的数据共享,为数据共享设立边界,防止数据滥用。个体权利和数据安全是其重要的边界所在。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个体的数据权利,确保个体的自由权利,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赛博风
张晶晶:唤醒“沉睡”的医疗大数据
如何将散落的、非标准化的、复杂的医疗大数据集合起来并可使用、可计算,需要做大量且复杂的工作。当然这并非不可能实现,但需要成本及时间。
人类已经全面进入大数据时代。而医疗与大数据的“联姻”一直被人们所期待,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医疗数据仍处于“沉睡”状态。如何真正进行实践,让大数据为医生、为患者服务,赋能医疗新形态,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专门数据库与大数据平台相配合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设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同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消除数据壁垒,建立和完善全国健康医疗数据资源目录体系。2017 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健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分级诊疗信息系统;应用药品流通大数据,拓展增值服务深度和广度。
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早已突破诊疗过程,与整个健康体系密切相关,对药物研发、健康管理和公共卫生服务等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实现各个专门数据库与大数据平台之间的联通与配合,打通数据“孤岛”,是摆在医疗大数据实践面前的一道鸿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教授季加孚以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目前国际大型肿瘤数据库大致分为两类:基于人群的数据库和基于医院系统的数据库。美国SEER(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和日本癌症登记数据库属于前者,而美国的NCDB(国家癌症数据库)和日本的NCD(国家临床数据库)属于后者。”
比较来看,不同类型数据库所能实现的效果不同。季加孚分析说:“基于医院的数据库,更符合临床需求,可为患者诊断与治疗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信息。但是这类数据库存在就诊偏倚,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口学分层的特点,例如NCDB和SEER数据库在某些癌种的种族、年龄分布上存在差异。基于人群的数据库流行病学意义更加明确,能为国家战略制定提供更多依据。通常两种形式数据库间的相互融合、数据共享能起到1+1>2的作用。”
那么不同数据库之间是如何配合的呢?以日本NCD和癌症登记数据库为例,NCD主要收集详尽的围术期数据,而随访数据的积累一定程度上需依靠癌症登记数据库完成。由于《癌症登记法》的强制性和广泛覆盖,肿瘤登记处会收集肿瘤患者的预后信息。这些信息会由登记处返回到提供信息的医院,NCD即可通过医院获取肿瘤相关预后信息。
乳腺癌、胃癌、食管癌、肝癌等专病数据库也逐步并入NCD。此外,NCD还和DPCD(日本诊断程序组合数据库)等医疗保险数据库互通,开展卫生经济学相关研究。与之类似,美国SEER数据库与医疗保险合作,形成了SEER-Medicare数据库。
跨界合力才能打通数据“孤岛”
在大数据领域从业近十年的架构师沈辰在接受采访中告诉《中国科学报》,大数据具有所谓的“4V”属性,即大规模(volume)、多样性(variety)、产生和变化速度快(velocity)和价值密度低(value)。
“医疗大数据也是一样,如何将这些散落的、非标准化的、复杂的数据集合起来并可使用、可计算,需要做大量且复杂的工作。当然这并非不可能实现,但需要成本及时间。”
南京医科大学接受第二附属医院肠病中心主任张发明在采访中提出,医疗行为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而将这海量的数据进行处理,真正为医疗服务,大部分医院目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经验,需要大型数据服务商的支持。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在2013年搭建了基于临床数据仓库(CDR)大数据集成平台,其合作对象是微软中国。通过对所有的业务数据库的表单进行系统整合与深度挖掘,实现对医院的内部运营管理、医疗质量控制、医院感染管理、绩效考核与分配等实时数据分析管理,并且整合了单病种临床数据库与样本库、基因库关联的临床科研信息系统在临床研究方面的应用。
杭州健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学影像大数据挖掘和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开发了阅片机器人“啄医生”。董事长兼CEO程国华在创业初期就亲身经历过医生与科技人员在思维与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碰撞,他在采访中告诉《中国科学报》:“医疗大数据的应用绝不单纯是医疗领域的事情,而是一项跨学科的问题。”
专业人才的缺乏同样也是摆在医疗大数据发展面前的难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2013年就开展了肿瘤登记及数据库搭建工作,如今先后完成了基于电子病历平台的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数据综合利用平台及临床试验管理系统项目,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专业的医疗信息化团队。
北大肿瘤医院信息部主任衡反修是医院搭建早期HIS系统的核心骨干,他认为,专业的技术背景和对医疗工作的深刻理解,才能真正“唤醒”医疗大数据。衡反修指出,对医院来说:客观存在“不敢、不愿、不会”三方面的问题,其中“不会”正是因为大数据必须要有技术支撑,没有技术支撑就没法儿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
他强调:“在数据共享开放过程中,技术、标准、机制、体制突破仍存在较大的障碍,造成各部门在推动过程当中‘不会’做。核心是数据能否做到安全可控,让医院放心。”
信息安全是共享的前提
共享数据,才能更好地使用数据。程国华指出,尽管我们拥有海量的医疗大数据但是共享的程度很低,“沉睡”的大数据无法发挥作用。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患者重复就医、医生重复看病、给患者重复做同样的检查等。这既给患者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延误了治病的最好时机,又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不用说医务人员利用海量的医疗大数据进行科研,提高医疗水平了。”
大数据共享不易,重要原因正是出于对信息安全的担忧。医疗数据是极为敏感的隐私信息,一旦发生泄露,后果极其恶劣。2018年新加坡保健集团健康数据遭黑客攻击,150万人的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配药记录、门诊信息也遭到外泄,其他多名部长的个人资料和门诊配药记录同样被黑客获取。这一时间直接导致新加坡所有的“智能国家”计划暂停,包括强制性的“国家电子健康记录”(NEHR)项目——该项目允许新加坡的医院互相分享患者的治疗记录和医疗数据。
衡反修分析说:“不敢,正是因为数据共享、数据安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不敢去做。没有规定,或者不太明确,不敢做。”
季加孚建议,对于大数据安全,可参考国际通用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HIPAA)法案对患者数据进行脱敏,保证患者数据隐私;采用加密强度较高的算法,确保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问题;参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引进吸收国外医疗行业先进数据安全管理理念,实现传统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的融合。(记者张晶晶,中国科学报2019-04-01)
编辑:吴悠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5-11 21:52
【案例】
“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和治理问题”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综述
今年5月,我国四名伦理学家在《自然》杂志呼吁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契机加强对医学研究的伦理监管,这成为中国当代实践哲学登上国际舞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同时也提醒人们,在作为应用伦理学重要分支的生命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话题像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那样,能够引发理论层面如此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层面如此紧迫的监管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国内多家知名科研团体共同参与组织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和治理问题”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于2019年5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有关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龚颖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致开幕词。
王立胜书记指出,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与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学术和社会实践问题。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公众的激烈论争。应当看到,这一讨论触及到应用伦理学、乃至一般道德哲学的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都非常重视。自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开展以来,我所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道德哲学的理论和基本的伦理学原则为基础,分析了该技术的发展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论证了建立相关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力图为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最直接、最深入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地关系到人类后代的命运与未来。本次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和治理问题研讨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翟晓梅教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基因编辑全球标准制定专家委员会成员,对该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背景及主要成果做了介绍。这一专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在宏观上对人类基因编辑组以及新技术的管理机制提出建议。根据透明性原则,委员会呼吁任何人在进行与人类基因编辑相关研究时都要向世卫组织进行注册。任何未注册相关研究的行为都必须被视为违规。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康辉研究员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他认为,CRISPR/Cas9技术因具有准确性高、脱靶效应低、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通量高的特点,迅速成为研究和应用焦点。相比传统的基因工程,基因编辑技术在基础研究中既可以用来构建突变细胞系或突变个体认识基因功能和疾病机制,还可以进行基因高通量筛选和特定基因片段的生物合成。在临床研究和应用中,主要研发方向是分子检测工具、体细胞基因治疗、单基因遗传病防控和抗病毒治疗。此外基因编辑获得的特定基因型动物品种,有望作为异种器官移植及虫媒传播疾病防控的新突破口。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既是学术界和产业界竞逐热点,也是国家间科技创新和综合实力竞争的体现。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伦理学研究中心雷瑞鹏教授首先对以治疗为目的体细胞基因组编辑概念与体细胞基因治疗概念进行了比较。基于第一届人类基因组编辑高峰会议,人们确定体细胞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原则有: 为了人的福祉、透明、应有的关怀、负责任的科学、尊重人、公平和国际合作。为了治疗进行基因组编辑有若干问题需要讨论: 技术先行与伦理先行,自我监管与外部监督,对不确定性的监管,专利与共享,建立中央注册平台以及资源投入。
厦门大学医学院的马永慧副教授回顾了体细胞基因编辑疗法的概念,有效性、安全性和风险,以及当前的临床应用实践等。区分了体细胞基因编辑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差别,即体细胞基因编辑的收益及风险都仅与个体患者相关,并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尽管体细胞基因治疗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相比伦理争议较少,但仍然面临技术、伦理、社会的挑战。她介绍了1999年年仅18岁的Gelsinger参加宾夕法尼亚遗传学教授开展的针对缺乏OTC (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的患者的体细胞基因治疗而死亡的案例。这一案例涉及到体细胞基因编辑适应症选择知情同意、研究者的利益冲突和科研诚信问题。
南方医科大学的陈化教授提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是基因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人类传统道德提出更大挑战。为理性地评价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不偏不倚的道德态度是其逻辑前提。基于传统道德阐释力的匮乏与不足,生殖细胞基因编辑面临传统伦理批判和道德恐惧。从技术与伦理的动态视野看,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与道德应该是一种齿轮式的互动关系,但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得以开展,从医学研究到临床实践还有一段距离。具体言之,需要遵循善、敬畏生命与责任原则,并以维持治疗、禁止增强作为其实施限度。
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王赵琛指出,可遗传基因组编辑转化到临床试验的条件,是基因编辑技术科研应用及管理的关键环节。他 分析了目前可遗传基因组编辑转化临床试验涉及的伦理原则、问题、现有论证与反论证。具体包括,一是各国对临床前研究的限制使得目前临床试验风险收益分析信息不够充分;二是现有临床试验规范条件中“合理备选方案”与“严重疾病或症状”这一条件仍有待明确,由此引发了对临床应用合理性及临床试验受试者风险受益与自主性问题的讨论;三是,现有各国政策未明确细分基因组编辑研究及临床试验的各种潜在类型。这一问题直接关系科研的自由与受试者保护之间的平衡,明晰该问题无疑对后续科研及应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张迪研究员指出,可遗传基因编辑的治理受个体、公众、技术、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从法律、监管、政策、机构和专业共同体五个层面说明中国在可遗传基因编辑方面的治理问题。在法律层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立法层级低、惩戒力度低、立法空白、滞后性和立法“失败”。监管层面主要包括监管真空和监管链断裂两大问题。政策层面的主要包括,过度强调“应用、转化和市场”、知识产权政策、“放管服政策”的认识误区以及缺乏公众参与等问题。机构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和能力欠缺,以及独立性缺乏。专业共同体层面的问题主要涉及缺乏专业伦理共识和缺乏内部包容性。
四川大学/圣玛丽大学法学院的贾平教授认为,在是否能进行可遗传的基因干预,以及如何论证哪些干预行为有正当性的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理论难点。在论述这些难点的基础上,他对可遗传基因组编辑的立法例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美国法的相对宽松,到英国法的独立监管模型,再到民法法系国家的相对严格的立法,以此为基础,他提出应全面提升完善我国基因组编辑治理模式,在立法,监管和软法(非强制性规则)层面,做出相应举措。他还就基因编辑治理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提出了建议。
天津大学的焦鹏飞博士关注面向生物安全事件的互联网舆情量化分析,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采用数据自动爬取、自然语言处理、复杂网络分析等技术手段,基于新浪微博在线用户的发帖、转发和评论行为,量化不同群体舆情,深入理解基因编辑技术对我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尹杰副教授认为,反对可遗传基因编辑的论证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一、基因编辑是否侵犯了人类种系的神圣性?二、基因编辑是否构成了对于未来世代的不可接受的危险?三、基因编辑未能获得未来世代同意这一点是否构成其不可行的理由?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我们对于后代的义务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代际正义。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代际正义或义务的概念证成,而是有关事实的争论,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分析原有的哲学概念与论证,更需着力在如何关联事实与价值,即提示科学研究和实践中的哪些事实具有伦理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去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员在研讨会总结发言中指出,组织这次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和治理问题的研讨会的初衷是我们觉得,像基因编辑那样的新兴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必须伦理先行。伦理先行要求在科学家启动研究之前先制订一个暂时性的伦理准则或管理办法。要制订这些准则或办法必须首先对其中的伦理问题以及相关的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之所以是预备会议,是因为这次会议的报告人是由我们学会的副秘书长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席马永慧推荐的,所以报告人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学者(除了翟晓梅教授刚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基因编辑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回来,我们急需听取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他们的报告需要听取资深学者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建议,进一步完善。会议显示,所有报告人的内容非常精彩,但仍需要在分析鉴定伦理问题,以及对伦理问题运用伦理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论证方面进一步改进。我们希望今后的会议,除了我们这些报告人外,还有科学家,监管人员,负责的媒体人员参加。最后我们希望能够起草一个有关治理和监管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准则,提交政府决策时参考。
编辑:王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10 19:32
【案例】
王海明|平等新论
本文所讨论的是被学者视为“迷宫”的平等问题。作者以辨析权利为基点,试图为平等原则找到公正的依据。文章提出并论证了平等总原则及其两个分原则:每个人因为基本贡献(缔结社会)平等而应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因为具体贡献不平等而应比例平等地享有非基本权利。文章又从总原则推导出三项具体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基本权利(政治自由)平等,非基本权利(政治职务)比例平等;经济平等原则:基本权利平等(按需分配),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按劳分配);机会平等原则:社会提供的机会平等,非社会提供的机会不平等(然而机会多者应对机会少者作权利补偿)。最后,文章对于平等的价值及其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作出了评析。
何谓平等?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1确实,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但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并非都是平等。两个人手上有相同的黑痣,便不能说他们有平等的黑痣。他们有相同的姓氏,也不能说有平等的姓氏。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哪一种相同性呢?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这种相同性或者是所获得的利益之本身相同,或者是所获得的利益之来源相同,前者如工资和职务,后者如人的天资与性别。也就是说,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或差别未必都与利害相关,而人们相互间的平等或不平等却必定关涉利害:平等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不平等则是与利益获得有关的差别。
平等与不平等,从其起因来看,确如卢梭所见,可以分为自然的与社会的两大类型。更确切些说,平等与不平等,一方面起因于自然,因而是不可选择、不能进行道德评价、无所谓善恶或应该不应该的,如性别、肤色、人种、相貌、身材、天赋能力等等;另一方面则起因于人的自觉活动,因而是可以选择、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善恶或应该不应该之别的,如贫与富以及均贫富、贵与贱以及等贵贱等等。
自然平等与社会平等都与利益相关,但是,自然平等仅仅是利益问题,而不是应该不应该的权利问题。社会平等则不仅是利益问题,而且根本说来,是应该不应该的权利问题:社会平等正如无数先哲所说,实乃权利平等。
平等作为一种应该如何的道德原则,只能是社会平等而不能是自然平等,而社会平等实质上是权利平等。所以,平等原则实乃权利平等原则。法国《人权宣言》一语中的:“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中国《辞海》亦如是说:“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包括国家领导人和平民在内的一切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都应该完全平等呢?显然不是。国家领导人和平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平等。那么,这是否有悖于人权宣言的精神呢?也不是。这是因为,权利平等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人人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
何谓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谁都知道,一个人能否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个能否享有最低的、基本的政治权利问题;至于他能否担任官职,则是个能否享有比较高级的、非基本的政治权利问题。吃饱穿暖是最低的、基本的经济权利;而精食美服则是比较高级的、非基本的经济权利。言论自由是最低的、基本的思想权利;但能否参加学术会议或出版学术专著则是比较高级的、非基本的思想权利了。总之,所谓基本权利,亦即人权,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最低的权利,是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最低的、基本的需要的权利;而非基本权利,则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比较高级的权利,是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比较高级的需要的权利。
那么,为什么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呢?如所周知,权利是被社会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显然,每个人只有先为社会贡献利益,而后社会才有利益分配给每个人。因此,一切权利都只应依据于贡献而按贡献分配。于是,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也就只应依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按贡献分配。然而,现在我们又认为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这岂不自相矛盾?并不矛盾。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这是无可置疑的。他又说,“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droits cl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和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 ,只是称做‘人' ,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作人权呢?”因为“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正是这样的人。”3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是说,人权、基本权利的依据乃在于每个人都是缔结社会的一个成员。而社会又是人不可须臾离开的,对每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只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为他人做了一大贡献:缔结社会。任何人的其他一切贡献皆基于此!所以,缔结社会在每个人所做出的一切贡献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贡献。不仅如此,每个人的这一贡献还是以自己蒙受相应的损失为代价的。因为人们结成任何一个集体,都会有得有失。例如,从逻辑上看,每个人脱离自然状态而结成社会,就失去了自然自由。这一点,社会契约论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每个人在社会中能得到什么呢?显然,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最低都应该得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可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究竟应该得到什么呢?无疑至少应该得到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即享有人权或基本权利。进言之,每个人不仅应该享有基本权利,而且应该平等享有基本权利。因为虽然人的才能有大小、品德有高低、贡献有多少,但在缔结社会这一点上却完全相同。每个人之所以不论具体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就是并且仅仅是因为每个人这一最基本的贡献和因此所蒙受的损失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分配给老百姓与国家领导人同样多的基本权利,就决不是什么恩赐,而是必须偿还的债务。潘恩说得好: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4而且,每个人结成人类社会与结成其他集体有所不同:每个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股东。所以,基本权利又被叫做“自然权利” ,是人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一句话,基本权利、人权、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在概念上是相通的。彼彻姆说:“‘人类权利’一语是现代的表述,在传统上一直称为‘自然权利’ ,或者在较早的美国称为‘人权’。此项权利通常被当作是不可转让的、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联合国人类权利宣言’则通过一系列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所要求的基本需要的项目,规定了自然权利。”5麦克多纳耳德说:“谈论自然权利是为了强调权利具有基础的或基本的特性。”6《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则写道:“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
从上可知,所谓天赋人权,是说人权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生贡献(缔结社会)所赋予的。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天赋人权论者均以为人权是每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共同人性天然赋予的:“我们的人性怎么能证明我们有权得到这些平等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就是说,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物种特性。”7这是错误的。因为照此说来,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是人,他便应该享有人权: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剥夺而为每个人无条件享有。这样,一个人不管做了多大坏事,不论他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多大损害,他的人权也不应该被剥夺,他也应该与好人一样享有人权。因为他再坏,也与最好的好人同样是人,同样具有“相同的物种特性”。
可是面对现实,这些天赋人权论者又不得不承认:并非一切人都应享有人权。他们说,每个人一生下来便应该享有人权。但是,如果他做坏事做到一定程度,侵犯了他人的人权,那么他的人权便应该被剥夺。一个杀人犯,夺去他人性命,他自己的生命权也就应该被剥夺。可是这样便自相矛盾了:既说凡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又说坏人不应该享有人权。摆脱之法显然只有否定其一。而凡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否定不得,于是只好否定坏人是人了。有人便这样写道:“坏人只有坏到不是人的时候,才可以剥夺其人权。”8坏人难道会坏到不是人的程度吗?坏人再坏,不也是坏“人”吗?
其实,杀人犯等坏人之所以不应享有人权,并非因为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因为他们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已超过他们参与缔结社会的贡献。严格说来,任何人,只要他给社会和他人的损害大于或等于其贡献,以至净余额是损害或零,那么他就不应该再享有人权——他至多只应享有人道待遇,享有他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利益而非权利。
可见,每个人享有人权,也如同享有其他权利一样,是以负有一定的义务为前提的。这种义务,一方面是积极的,即每个人必须与他人一起共同做出缔结社会的贡献,这是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的源泉、依据;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即每个人不得损害他人人权,这是人人平等享有人权的保障、条件。逃避前者或违反后者,都不应该享有人权。准此观之,赵汀阳先生的有偿人权说便是正确的,而邱本先生的无偿人权论则是错误的。不过,赵先生只看到人权享有的消极条件(不得损害他人人权),而没有看到人权享有的积极依据(参加缔结社会),把人权享有的条件当做人权享有的依据,因而以为人权依据于“不做坏人”、“做道德人”: “在道德上是人的人拥有人权,在道德上不是人的人不拥有人权。”9这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邱先生所指出,照此说来,那些合法而不合道德的忘恩负义者、伤风败俗者、见死不救者便都不应该享有人权了!这说得通吗?但是,邱先生却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权的享有依据于“合法人”: “一个合法的人就应该享有人权,只有依法认为不是人必须剥夺其人权的人才不应享有人权。”10这就更荒唐了!普天之下,哪里有规定是人和不是人的法律呢?况且,任何时代都存在不合法却合乎道德者,历史上的这些人还往往是道德的楷模。
总之,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这就是基本权利平等原则,也就是“人权原则”。
那么,每个人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为何应该比例平等?
“比例平等”首创于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概念,他曾解释说:“既然公正是平等,基于比例的平等就应是公正的。… …例如,拥有量多的付税多,拥有量少的付税少,这就是比例;再有,劳作多的所得多,劳作少的所得少,这也是比例。”11
观此可知,所谓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不过是说,谁的贡献较大,谁便应该享有较多的非基本权利;谁的贡献较小,谁便应该享有较少的非基本权利:每个人因其贡献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这样,人们所享有的权利虽是不平等的,但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的多少之比例与每个人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之比例却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
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表明,社会应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但在这种权利不平等的分配中,正如罗尔斯的补偿原则所主张的,获利较多者还应给较少者以相应补偿: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12
为什么获利较多者必须给较少者以权利补偿?因为获利多者比获利少者较多地利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社会合作,而获利越少者对共同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的补偿便应该越多。举例说,那些大艺术家、大企业家是获利较多者。他们显然比工人农民等获利较少者较多地使用了双方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社会合作。若是没有社会,这些大艺术家、大企业家便会一事无成;若非较多地使用了社会合作,他们也决不可能做出大贡献。这些获利较多者的贡献之中既然包含着对共同资源的较多使用,因而也就间接地包含着获利较少者的贡献。于是,他们因这些大贡献所取得的权利,便含有获利较少者的权利。所以,应该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方式从获利较多者的收益中,拿出相应的部分补偿、归还给获利较少者。否则,获利多者便侵吞了获利少者的权利,是不公平的。
然而,诺齐克反对补偿原则,认为恰恰是它侵犯了个人权利。他举例说:假设张伯伦是一名篮球明星选手,大批观众为看到他的表演而兴奋,认为花钱买门票是值得的。根据张伯伦和一个球队签订的契约,在一个赛季100万美元的收入中,张伯伦得到了25万美元。这是一个比平均收入大得多的数字,是最高收入额。他对这个收入有权利吗?诺齐克的回答是肯定的13。然而,补偿原则却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而从张伯伦这25万美元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再分配,岂不侵犯了张伯伦的权利?
诺齐克的反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若没有社会,张伯伦能做什么呢?他之所以能做出大贡献,显然是因为他比一般人较多地使用了“社会”这个共同的资源。因而,在他的贡献中,也就间接地包含了一般人的贡献;在他那25万美元巨额收入中也就间接含有一般人的收入。所以,通过个人所得税而从张伯伦25万美元收入中拿出相应的部分归还给一般人,并没有侵犯张伯伦的权利;相反地,如果让张伯伦独享25万美元,恰恰是侵犯了一般人的权利。
不过,罗尔斯忽略了强者应该给弱者补偿的根本理由乃是强者比弱者较多地利用“社会合作”。他认为强者应该转让一部分收入给弱者,是因为强者的较多收入依靠与弱者的合作14。这个理由很不充分,因为弱者的收入显然也依靠与强者的社会合作。如果强者因此而应该转让一部分收入给弱者,那么,弱者岂不也应该因此而转让一部分收入给强者?诺齐克正是这样反驳罗尔斯差别补偿原则的:“无疑,差别原则提出了那些才智较低的人们愿意合作的条件。但是,这是一个那些才智较低的人们能期望得到别人的自愿合作的公平协议吗?在产生社会合作的收益方面,各方的状态是对称的。才智较高者是通过与才智较低者的合作得益的;同时,才智较低者也是通过与才智较高者的合作得益的。但差别原则在这两者之间却不是保持中立的,这种不对称是来自何处呢?”15这种不对称的真正理由,显然并不在于强者利用了社会合作,而在于强者较多地利用了社会合作。诺齐克认为补偿原则侵犯个人权利,说到底,也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一点,而误以为强者和弱者同等地利用了社会合作。
完全平等与比例平等,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缔结社会)完全平等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享有人权;另一方面,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的比应该完全平等。这就是平等总原则,它由完全平等与比例平等两个分原则构成。这两个平等分原则大致相当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指“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第二个正义原则是指合理地安排“社会的与经济的不平等”16。依我所见,他在那部影响深远的50万言的名著中所论证的,其实就是平等总原则的两个侧面。
罗尔斯在谈到二者的关系时说:“这两个原则是按照先后次序安排的,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为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17
这就是说,基本权利的分配优先于非基本权利的分配: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后者以保全前者。所以,为使人们得到更多的经济方面的非基本权利而剥夺他们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本权利是不应该的。这是不错的。不过,这只是基本权利优先性的一种体现,即对于每个人或每个群体来讲,他或他们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基本权利,都优先于其他方面的非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的优先性还体现于一些人的基本权利与另一些人的非基本权利的冲突上。举例说,当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度匮乏时,如果人人吃饱从而平等享有基本权利,那么,就几乎不会有人吃好而享有非基本权利。这样,每个人就几乎完全平等享有经济权利,因而便违反了比例平等原则,侵犯了有大贡献者在经济上所应该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反之,如果一些有大贡献者吃好而享有非基本权利,那么,就会有人饿死而享受不到基本权利。这样,基本权利便不是人人平等享有的,因而便违反了完全平等原则,侵犯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显然应该违反比例平等原则而侵犯某些有大贡献者的非基本权利“吃好” ,以便遵循完全平等原则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吃饱”。这样才是公平的、正义的。
为什么一个人不论多么渺小,他的人权也优先于另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的非基本权利?因为,一个人的贡献再少,也与贡献最多者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因而至少也应该享有起码的、基本的权利。那些有大贡献者的贡献再大,也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也就是以每个人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的贡献为前提。所以,有大贡献者究竟应否享有非基本权利,也就应该以每个人是否已享有基本权利为前提。总之,每个人的人权、基本权利之所以是优先的、不可侵犯的,就是因为赋予这一权利的每个人参加缔结社会的这一基本贡献,优先于、重要于任何其他贡献。
平等问题被学者视为“迷宫”18。要真正解决平等问题,仅有平等总原则是不够的,还须以平等总原则为指导,根据平等的具体类型,从中推导出相应具体的平等原则。平等有哪些具体类型?萨托利认为: “平等的历史进步可以分为四类或四种形式 1)法律—政治平等;(2)社会平等;(3)机会平等;(4)经济平等。”19然而,社会平等是个笼统概念,它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等平等的统称。萨托利自己也说:“关于社会平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更加关心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阶级和身分的问题。”20所以,具体的平等问题便可以归结为三大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相应地,平等的具体原则也就分为: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
1)法律—政治平等;(2)社会平等;(3)机会平等;(4)经济平等。”19然而,社会平等是个笼统概念,它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等平等的统称。萨托利自己也说:“关于社会平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更加关心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阶级和身分的问题。”20所以,具体的平等问题便可以归结为三大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相应地,平等的具体原则也就分为: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
平等的概念和原则表明:平等未必都是权利平等;但平等原则却皆为权利平等原则。因此,所谓政治平等原则,亦即政治权利平等原则。政治权利,也就是掌握政治权力进行政治统治的权利。这种权利分为两大类型:直接统治权利与间接统治权利。直接统治权利是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间接统治权利则是政治参与权,主要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这是使统治者按照全体被统治者意志进行统治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21。因为政治自由非他,正是公民使国家政治按照公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权利。
然而,人们往往把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等同起来。凯尔森亦如是说:“我们所了解的政治权利就是公民具有参加政府、参加国家`意志’形成的可能性。用实在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公民可以参与法律秩序的创造。”22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决定国家政治命运或者参与法律秩序的创造的权利,是政治自由的内容,而政治自由仅仅是政治权利的一个子项;政治权利还有另一个子项,即政治职务。
政治权利既然分为政治自由与政治职务两大类型,那么,根据平等总原则,不难看出:人们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因为,政治自由是最低的基本的政治权利;政治职务则是比较高级的、非基本的政治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行使某一项权力的人数与每人享有该项权力的大小呈反向关系,“就同一权力行使的人数言,人数愈少,每人权力愈大;人数愈多,每人权力愈小。所以独任制首长的权力大于合议制首长的权力。”23因此,享有政治自由的全体公民共同享有的,固然是最高最大的权力;但分散到每个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却是最低最小的权力了。它比最低等的官吏所拥有的权力还小:它不过是亿万张选票中的一张选票的权力罢了。所以,每个人所享有的政治自由权利,是基本权利;而一个人所享有的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则是非基本权利。
政治自由属于基本权利。所以,根据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换言之,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决定国家政治命运。说到底,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每个人只顶一个,不准一个人顶几个。”24这就是政治权利完全平等原则,这就是政治领域的人权原则,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民主权原则,因而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据之一。根据这个原则,纵使民主有多少多少缺憾而专制有多少多少优点,我们也应该取民主而不应该取专制。所以,科恩强调说:“如果为民主的辩护完全无需估价它的后果,那这种辩护必须以无可怀疑的原则为基础。在目前这种辩护的情况下所依据的,是人人平等以及政治社会中人皆享有平等权的主张。”25
由于担任政治职务属于非基本权利,根据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原则,人们应该按其政治贡献大小而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也就是说,谁的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大,谁便应该担任较高的政治职务;谁的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小,谁便应该担任较低的政治职务。每个人因其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不平等而应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这样,人们所享有的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虽然是不平等的,但每个人所享有的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与自己的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之比例却是平等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应该仅仅按照政治才能分配政治职务,即“任人唯才”;也不应该仅仅按照道德品质分配政治职务,即“任人唯德”;只应该兼顾德才分配政治职务,即“任人唯贤”。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只有政治才能高而又道德品质好,才能为社会和他人做出较大的政治贡献。
这样,政治职务的分配便具有双重依据:政治贡献显然是政治职务分配的实在依据,而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质也就是预期的政治贡献,则是政治职务分配的潜在依据。
总而言之,每个人因其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政治才能+道德品质)的不平等而应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换言之,每个人所担任的政治职务的不平等与自己的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这就是政治权利比例平等原则,也是政治职务分配原则。最早确立这一原则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指出:“合乎正义的职司分配(政治权利)应该考虑到每一受任的人的才德或功绩。”26
综观政治权利平等原则,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每个人不论具体政治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亦即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共同决定国家的政治命运;另一方面,每个人因其具体政治贡献或预期政治贡献的不平等而担任相应不平等的政治职务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这就是政治平等总原则。
确立政治平等原则的关键,在于厘定“政治权利”和“政治贡献”两概念。要确立经济平等原则,首先也必须廓清“经济权利”与“经济贡献”。
不难看出,每个人在经济上所享有的权利与其在经济上所做出的贡献,说到底实为同一事物,都是劳动产品,社会对于经济权利的分配过程,无非是每个人所创获的产品的互相交换的过程。因此,应该按照产品的交换价值而分配给他含有同量交换价值的经济权利。最终说来,便应该按照产品含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给他含有同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权利。这实际上就是经济权利的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论及按劳分配原则时写道:“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于是,“每一个生产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27可见,按劳分配原则就是比例平等原则,也就仅仅是非基本经济权利分配原则。
那么基本经济权利的分配原则是什么?根据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的平等总原则可以推知:每个人不论劳动多少、贡献如何,都应该平等享有基本经济权利,即基本经济权利应当平等分配。所谓平等分配基本经济权利,就是按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分配基本经济权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基本经济权利就是满足每个人基本物质需要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物质需要的不平等仅仅存在于非基本的、比较高级的领域,而基本的、起码的物质需要则是平等的:“自然需要对谁都是一样的。”28因此,按基本物质需要分配基本经济权利,实际上又等于按需要分配基本经济权利:按需分配29。
总之,按需分配是基本经济权利即经济领域中人权的平等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则是非基本经济权利的比例平等分配原则。于是,根据人权优先原理可知,按需分配优先于按劳分配: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该牺牲后者以保全前者。因为按劳分配,当然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一些人所劳再少,他们的所得也不能少于满足起码的物质需要而损害按需分配;一些人的所劳再多,他们的所得也不能多到影响他人的起码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冲击按需分配。这个道理,艾德勒说得很透辟:“贡献大的人比贡献小的人理应多得。对于这样一条分配原则,必须加上两个条件: (1)必须以某种方式满足一切人的最低经济需求。在这个经济基础线上,必须人人平等。对这些财富,每个人都是生来有权得到的。 (2)由于可分配的财物数量有限,所以谁也不能根据他的劳动贡献去赢得很多财富,以致在某些方面影响大家维持家庭在基础线上的经济需求。总之,即使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不应由于分配不均而出现贫困。”因为“按劳分配附属于按需分配”30。
合观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每个人不论劳动多少、贡献如何,都应该按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基本经济权利(即按需分配);另一方面,则应按每个人所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分配给他含有同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非基本经济权利,以便使享有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完全平等(即按劳分配)。这就是经济平等总原则。
经济平等总原则乃是人类任何社会唯一公平的经济权利分配原则:按需分配是任何社会基本经济权利唯一公平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则是任何社会非基本经济权利唯一公平的分配原则。只不过,这些原则只有在公有制社会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从而才可能达到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而在私有制国家则只可能部分实现,从而也就只可能局部达到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资本主义的所谓福利国家政策,无疑接近按需分配;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接近按劳分配,甚至按资分配亦然。因为投入资本也是投入劳动,只不过是物化劳动、死劳动罢了。当然,二者皆非按劳分配,因为二者皆非“等量劳动相交换”: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所得少于贡献;按资分配则是所得多于贡献。但二者确实都接近按劳分配,因为二者的所得均与所贡献的劳动成正比。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在私有制社会只可能部分实现,显然是因为私有制必然导致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存在剥削,而剥削的程度越重,在分配上便越背离等量劳动相交换,越远离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也就越背离公平。唯有公有制才可能消灭剥削,才可能在分配上实现等量劳动相交换,从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实现公平。机会平等原则也是一种权利平等原则。但是,一方面,这种权利并非政治或经济等具体权利,而是获得这些具体权利之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权利仅仅是竞争非基本权利——主要是社会的职务和地位、权力和财富——之机会,而不是竞争基本权利之机会,因为基本权利的获得既不需竞争,也不需机会。由此观之,机会平等原则隐含于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原则之中。因为机会平等,是相对于结果平等而言。而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原则所确立的,虽然都是结果平等,即结果的完全平等和比例平等,但也隐含机会平等。更确切些说,从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分配原则所确立的平等来看,显然不但完全是结果平等,而且是结果的完全平等。从非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分配原则所确立的平等来看,则不仅是结果比例平等,而且还是一种机会平等。因为这个原则说的是:不管对谁,一切非基本权利都仅仅应该平等地按照他所做出的贡献来分配。这样,所有人虽不能同等获得各种非基本权利,却同等有机会获得各种非基本权利:每个人获得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是平等的。这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作为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平等”31。
但是,政治、经济比例平等原则所隐含的这种机会平等并非机会平等的全部,而仅仅是一种表层的、形式的机会平等。因为非基本权利平等地按每个人的贡献来分配,必然意味着所有人获得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但是更进一步看,一些人才德较差、贡献较少从而享有较低的非基本权利,往往是因为他们缺乏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的机会;反之,另一些人才德较高、贡献较大从而享有较多非基本权利,则往往是因为他们充分享有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的机会。可见,机会平等分为两类:一类是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它是形式的、表层的机会平等;另一类则是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的机会平等,它是实质的、深层的机会平等。这两类机会平等可以从道格拉斯·雷所援引的例子得到很好的说明:假设某个社会,武士阶层享有巨大威望,因为他们的职责要求有强大体力。该阶层过去只从富家子弟中征募;但平等主义改革者改变了征募原则,通过竞争向社会所有阶层征募武士。结果,富有家庭仍然提供全部的武士,因为其他民众由于贫穷而营养不良,他们的体力总是低于营养良好的富家子弟32。显然,平等主义改革只做到形式的表层的机会平等:武士职业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同样有机会担任武士,这属于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平等;但没有做到实质的深层的机会平等:每个人都可能营养良好而同样有培养自己强大体力的机会,这属于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的机会平等。道格拉斯·雷对这两类机会平等做出解释:“ 1.关于前途的机会平等:两个人, J和K,有竞争X的平等机会,如果他们有得到X的同样可能。2.关于手段的机会平等:两个人, J和K,有竞争X的平等机会,如果他们有得到X的同样工具。”33
萨托利也以这种分类为前提,建议把机会平等再分为平等进入和平等起点。“平等进入就是在进取和升迁方面没有歧视,为平等的能力提供平等的进入机会……平等起点的概念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34
机会平等的这种分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告诉我们在确立机会平等原则时,不仅应该关注竞争权利的机会平等,更应该注重发展潜能的机会平等。但是,这种分类只能表明机会平等的深浅程度,却不能表明机会平等的合理性,不能表明机会平等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是一切机会皆应平等还是只有某些机会才应平等。机会平等的合理性,真正讲来,并不取决于机会平等本身的性质如何,而取决于机会的来源如何。
从来源的角度观察,机会可以分为两类:社会提供的机会与非社会提供的机会。非社会提供的机会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家庭提供的机会、天资提供的机会、运气提供的机会。
出身于不同的家庭,所享有的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萨缪尔森就此写道:“到了一周岁时,出身富有家庭并经双亲精心照料的孩子在经济和事业地位的竞争中已经略占上风。到了进小学一年级时,城市或近郊的六岁儿童比贫民窟或农村同龄儿童具有更大的领先地位。在以后的12到20年中,已经领先的人越来越走在前面。”35家庭所提供的这种机会不平等,在奥肯看来,是不公平的。因为“当一些人面前障碍重重时,另一些竞争者已经率先起跑了”36。奥肯不懂得,人生的赛跑乃是一场世代相沿的无休止的接力赛。每个人的起点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并非不公,因为他们的祖先的起点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更确切些说,家庭提供的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无非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权利转让。子女所享有的机会,是父母转让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拥有当然不可以是非正义的),因而也就转化为子女自己的权利。诺齐克的“转让正义原则”谈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符合转让的正义原则,从别的对持有拥有权利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持有的人,对这个持有是有权利的。”37家庭提供的机会,既然是机会享有者的权利,那么,这种机会不平等便是应得的、公平的;而使其平等,便侵犯了机会所有者的权利,便是不公平不应该的。
天资不同的人,竞争职务和地位、权力和财富等非基本权利的起点和获胜的机会显然也是不平等的。这种机会不平等也是应得的、公平的。因为说到底,社会不过是每个人相互利益的合作形式。每个人的天资、努力等等便是其入股社会的股本。正如诺齐克所说,“人们对其自然资质是有权利的,对来自其自然资质的东西也是有权利的。”38这样,每个人因其天资不平等所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便是他应得的权利;若使其平等,便侵犯了他的权利而是不公平不应该的。
人们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不平等,往往是个人的运气所致。布坎南对此曾有十分生动的论述:“耕种家庭农田的农民以标准的方式务农,并没有选择别人在他农田下面会发现石油,他完全靠运气。另外一些人由于运气不好,眼看他们的产业遭洪水、火灾或遭疫病而化为乌有。……运气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定论的偶然影响因素,它在比赛中为所有人提供`本来可能’的机会。”39那么,运气所提供的机会不平等是否公平?
布坎南的回答是:“运气并不破坏基本公正的准则。”40这个回答很对。因为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是:按照贡献分配权利。而任何人的贡献、成就,正如曾国藩所说,都含有运气因素,都是天资、努力、运气诸因素配合的结果41。因此,运气也就与天资、努力一样,可以通过产生贡献而带来权利;运气所带来的收益,也就与天资和努力所带来的收益一样,乃是收益者的权利。农民有权利拥有运气带给他的丰年收成,岂不正如他有权利拥有灾年的收成?所以,运气所提供的收益、所提供的机会不平等,确是幸运者的权利;若剥夺幸运者的机会而使其平等,便侵犯了幸运者的权利,便是不公平不应该的。
家庭、天资、运气等非社会提供的机会,总而言之,是幸运者的个人权利,因而无论如何不平等,社会和他人都无权干涉。但是,幸运者在利用较多机会去做贡献、获权利的过程中,必定较多地使用与机会较少者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社会合作。于是他们因这些较大贡献所取得的权利,便含有机会较少者的权利。所以,便应该通过高额累进税、遗产税等方式,从他们的权利中拿取相应部分,补偿、归还给机会较少者。否则,便是不公平的。
社会——主要通过政府——提供的机会,与家庭、天资、运气提供的机会根本不同。家庭、天资、运气所提供的机会,皆属私人权利,是机会享有者的个人权利。社会、政府提供的机会,则属于公共权利,是全社会人人均应享有的“人权和幸福”42。根据基本权利、人权应该完全平等的原则,政府所提供的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也就应该为人人完全平等地享有:平等享有社会所提供的发展自己潜能的受教育机会,社会所提供的做出贡献的机会,社会所提供的竞争权力和财富、职务和地位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因此哈耶克说:“欲使所有的人都始于同样的机会,这既不可能也不可欲。”43但是,“正义或公平确实要求,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状况,应该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人享有。”44
然而,罗尔斯却认为社会、政府所提供的机会不应该平等:“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这样,补偿原则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点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至少在某一阶段,比方说早期学校教育期间是这样。”45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家庭和天赋所提供的机会,是幸运者的个人权利,不包含也未侵犯机会较少者的权利,因而不应该给机会较少者补偿机会。另一方面,幸运者利用较多机会去创获权利,却必定较多地使用与机会较少者共同创造的资源“社会合作” ,因而应该补偿给机会较少者以相应权利。所以,机会较多者应给机会较少者补偿的是机会的利用,而不是机会的占有;是利用机会所创获的权利,而不是机会本身。罗尔斯实际上把机会的利用和机会的占有、权利补偿与机会补偿等同起来,以为机会较多者应补偿给机会较少者以机会,因而主张社会应该通过提供不平等的机会来补偿家庭和天赋所提供的机会不平等。然而,社会提供的机会,乃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每个人的人权;如若不平等分配,给出身不利、天赋较低的人以较多机会,岂不侵犯了出身有利、天赋较高的人的人权?
综观社会所提供的机会与非社会所提供的机会,可以得出结论:社会所提供的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竞争职务和地位以及权力和财富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人人完全平等。家庭、天赋、运气等非社会所提供的机会,则是幸运者的个人权利,无论如何不平等,他人都无权干涉;但幸运者利用较多机会所创获的较多权利,却因较多地利用了共同资源“社会合作”而应补偿给机会较少者以相应权利。这就是机会平等原则。
综观平等总原则及其具体原则,可以说,平等原则乃是人类最复杂也最重要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涉及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平等的价值”问题。
从理论上看,平等的价值主要表现于平等与公平的关系。那么究竟何谓公平?从古到今人们一直认为:公平、正义、公正、公道乃同一概念,是行为对象应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反之,不公平、非正义、不公正、不公道乃同一概念,是行为对象不应受的行为,是给人不应得而不给人应得的行为。这是不错的,但不够精确。因为公平是给予人应得的行为,不过是说:公平是应该的道德的善的行为;不公平是给人不应得而不给人应得的行为,也不过意味着:不公平是不应该不道德的恶的行为。但是,善的应该的道德的却不都是公平的;恶的不应该的不道德的也不都是不公平的。那么,公平究竟是道德的应该的善的行为中的哪一部分行为?亚里士多德已隐约看出:是具有某种均等、相等、平等性质的那一部分行为。所以他一再说: “公正就是平等,不公正就是不平等。”46穆勒则进一步指出: “平等是公道的精义。”47戈尔丁也写道:“正义的核心意义与平等概念相联系。”48赵汀阳先生说得就更准确了:“公正在形式意义上具有一种对等性。……无论对于人际关系还是事际关系,公正的对等性首先表现为`等价交换原则’ ,即某人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人,所以他人也以这种方式对他,或者某人的某种东西与他人交换与之等值的东西。”49
细观这些关于公平的简明而精深的论述,不难看出,公平是平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行。由此可知,就概念来说,公平从属于平等,是一种特殊的平等:公平是利害相交换的平等。然而,就原则来说,却恰恰相反:平等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平而从属于公平原则。这是因为,“平等”这个道德原则极为奇异。几乎所有道德原则、规范与其名称、概念都是同一的。例如,“公平”、“人道”、“善”、“自尊”、“谦虚”、“诚实”等等,都既是名称、概念,又是道德原则、规范。然而,“平等”却不是这样。“平等”与“平等原则”不是一回事。平等,如前所述,是人们相互间的与利益获得有关的相同性,如相同的肤色、相同的智力、相同的贫困等等,显然不能被奉为人们应该如何的道德原则。可见,平等还不是平等原则。但是,平等原则却是平等:平等原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平等。问题是,平等原则究竟是哪一种平等?
如前所述,平等分为自然平等与社会平等:自然平等是不可选择的,无所谓应该不应该;社会平等,如均贫富、等贵贱,则起因于人的自觉活动,是可以选择、有应该不应该之别的。由此看来,作为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原则的“平等” ,显然与自然平等无关而完全属于社会平等。那么,平等原则究竟是指哪一种社会平等?社会平等,若以此观之,不过有两种。一种是非等利(害)交换的平等,如不等量劳动而获取等量报酬。这种平等是“不公平的平等”。反之,另一种则是等利(害)交换的平等,如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种平等是“公平的平等” ,也就是所谓的“公平”;因为“同等利害相交换的行为” ,正是公平的定义。
“等利(害)交换”是公平的定义,因而也就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公平的唯一原则。运用这个原则解决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分配问题,便可从中推导出由相应两方面构成的平等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又是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等一切具体平等原则所由以推出的依据。
可见,一切平等原则,说到底,都不过是运用公平原则具体解决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分配问题而从中推导出来的罢了。所以,平等原则从属于公平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平原则。
总之,公平原则从属于平等概念:公平是一种特殊的平等;而平等原则却又从属于公平:平等原则是一种特殊的公平,因而也就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平等。进言之,平等原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公平,而且是最重要的公平。因为公平不过是一种平等,一切公平问题都不过是个平等问题;而平等原则所解决的平等,即基本权利、人权的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无疑在一切平等问题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平等原则从属于公平原则,而又比公平原则更重要。这就是平等原则的理论价值。
平等原则的这种理论价值,决定了它的实践价值:它与效率的关系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样,是完全一致而成正相关变化的。因为,一个社会越符合平等原则,便越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效率也就越高;一个社会越背离平等原则,便越不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背离,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低,从而效率也就越低。公平和平等原则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保证。
推此可知,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平等(或不平等)是否符合平等原则、是否公平:如果符合平等原则因而是公平的平等(或不平等),与效率便都是正相关关系;如果违背平等原则因而是不公平的平等(或不平等),与效率便都是负相关关系。于是,平等与效率便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就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的结果与贡献的比例平等来说,就公平的平等来说,则平等与效率具有正相关的同长同消的并存关系:越是平等便越有效率,越是不平等便越无效率。另一方面,就非基本权利的结果平等来说,就不公平的平等来说,则平等与效率具有负相关的、此长彼消的交替关系:越是平等便越无效率,要平等便无效率,要效率便无平等。
合而言之,平等与效率既可能一致又可能冲突——与效率冲突的平等,必是不合平等原则的不公平的平等;与效率一致的平等,必是符合平等原则的公平的平等。效率是衡量平等是否公平的标准。因此,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如果选择平等,那就既失去了效率又失去了公平的平等,而得到的只是不公平的平等;如果选择效率,则既得到了效率又得到了公平的平等,而失去的只是不公平的平等。所以,效率对于平等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kk1AUw0kgVyjxF64mepTw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12 23:01
【案例】
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开约谈 责令百度上海分公司进行整改
“上海房价大跌!”“如狼似虎女教师”“朝鲜女兵不穿内裤”……近日,上海市网信办发现本市部分聚合资讯类网站,以此类标题党文章吸引网民关注。而网民一旦点击其链接,网页指向均为百度的信息流广告。为此,上海市网信办于6月12日联合市市场监管局约谈百度上海分公司,责令其就存在严重网络生态问题的信息流广告进行立即整改,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其中严重违法广告依法调查处理。同时,上海市网信办责令属地相关网站做好广告审核。
市网信办和市市场监管局指出,目前发现百度信息流广告的主要问题有三大类:一、明明是广告,却使用“房价跌了”等类似新闻的耸人听闻的标题诱导点击;二、使用低俗性感诱惑图片(如穿着比基尼的丰满美女)和露骨低俗文字诱导点击广告;三、使用明显不合理低价诱惑如“55寸液晶电视99元/台”,诱导点击广告。
上海市网信办对于百度公司为了流量利益,罔顾社会公序良俗,罔顾互联网法律法规,在一些网站上投放此类恶俗信息流广告的行为予以谴责。先前,百度公司在搜索领域将公司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已引起舆论谴责。此番发生在广告领域的问题,也反映了公司在经营行为中扭曲的价值观。市网信办要求百度上海分公司,希望其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所在,从根子上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进行整改,彻底将此类广告赶出网络。参加约谈的百度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百度总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切实履行起企业主体责任,积极配合,认真落实整改要求。
与此同时,市网信办也要求属地网站,在刊播相关广告时必须做好审核把关,防止此类恶俗广告出现。上海市网信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人人有责,大公司更要在这方面体现他们的责任和担当,也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网民对此类现象据实举报。(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举报网站:http://www.shjbzx.cn/,举报电话021-55056666)。
原文链接: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90612/4595095.shtml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13 22:07
【案例】
湘潭日报社原总编辑王荃外逃8年落网,靠卖画为生
5 月 28 日,广西桂林,王荃被民警抓获。图 / 受访者提供
5 月 28 日,湘潭市追逃办消息:外逃 8 年的湘潭日报社原党组副书记、总编辑王荃在广西桂林被抓捕归案。至此,湘潭在省追逃办 " 挂号 " 的 10 名境内外逃人员全部劝返或抓捕归案。
6 月 5 日,湘潭市看守所。
百余米长的走廊尽头,慢慢移过来三个小点。押解归案一个多星期的湘潭日报社原总编辑王荃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名管教民警。
王荃脚上是一双码子偏小的蓝色塑料拖鞋,脚后掌露出小一截在外面。上身是有 " 湘潭看守 " 字样的蓝色马甲,扣子没扣齐。他没戴那副被抓捕时戴着的高度近视眼镜,所以,走近时,他眯着眼睛仔细打量我们,好像对面站着的是一排太阳。
王荃案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 2009 年 11 月。据潇湘晨报等媒体当年的报道称:(2009 年)11 月 10 日,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湘潭日报社原党组副书记、总编辑王荃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荃在 2003 年至 2009 年 3 月担任湘潭日报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期间,利用分管基建、广告业务等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用于个人消费或买卖股票,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0 年 1 月,王荃被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
王荃说,他患有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在王荃看来,这个遗传自母亲的顽固病症,是导致他此后八年漂泊命运的药引子。
" 我是脱管,不是出逃。脱管完全是因为我要治病。" 但是,一份发自湘潭市雨湖区综治办、落款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4 日的文件,对此则有另一番描述:2010 年 1 月 5 日,雨湖区法院以 ( 2009 ) 雨法刑初字 2 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罪犯王荃犯受贿罪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2010 月 3 月 8 日,罪犯王荃因患病态窦房结综合征,雨湖区法院以 ( 2009 ) 刑初字第 214 号暂予监外决定书对其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并交雨湖路派出所执行。
2012 年 2 月 27 日,雨湖路派出所称,王荃 2011 年 12 月份以来就不见其人,电话也无法联系,脱管已达三个月。2012 年 3 月 13 日,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向雨湖区法院发出 " 关于对罪犯王荃收监执行的建议函 "。2012 年 4 月 6 日,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收到雨湖区法院对罪犯王荃作出的收监执行决定书。在此期间,公安部门也一直未能找到王荃。
要描述王荃的外逃生活," 治病 " 或许并非值得大费周章。事实上,当时王荃的全部身心几乎都在一件事情上——绘画。
到了广州,有书法功底的王荃跟人学绘画,两个月之后,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王荃自己很得意—— " 我临摹齐白石的画惟妙惟肖 "。他说,花鸟虫尤其画得栩栩如生,蚱蜢、螳螂、蝉,个个生猛。
王荃说:在外面没有生活来源,靠卖画养活自己。他的画多在朋友介绍的画廊出售,底价 800 元每张,有时候一张能卖到一万元。
凭借绘画,他结交了更多朋友,圈里的人称他 " 齐总 "。王荃说,朋友们经常一起去全国各地写生,安徽、云南、贵州等,因为王荃清楚自己的逃犯身份不敢使用身份证," 大家从不坐公共交通,都是自己开车 "。
王荃出身湘潭县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艺术修养。在外漂泊的日子,绘画一方面 " 拯救 " 了王荃,但同时,也成为警方摸排的重要线索。
大约在 2012 年,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王荃在电视里看到 " 所有保外人员全部收监 " 的消息,内心纠结。" 我每天都在做选择,到底是联系湘潭那边,还是选择逃避?" 王荃说。
他说:佛家讲慈悲,慈是说让人快乐,悲是悲悯," 我既不能让家人快乐,也不能让他们悲悯我,我不能回去 "。
在王荃做出选择,背着行囊踏上广西桂林的土地时,已是 2013 年。
在这个山水甲天下的旅游城市,王荃依然 " 如鱼得水 "。他 " 想赚钱 "," 赚个 1000 万 "。当地有种叫鸡血石的石头,王荃找到了 " 发财之道 "。
他给这些鸡血石做设计——办案民警说,同样的珠子,经王荃的手穿起来,立马变得富有文化艺术气息," 他把珠子的蓝本卖给鸡血石老板,老板再找人批量生产,每条珠子的收益王荃能拿三到五个点的提成。" 直到王荃被抓捕,他设计的鸡血石依然在阳朔西街上销售红火。
湖南方面,对于王荃的追逃一直没有放弃。早在 2011 年年底,王荃就被列为网上逃犯。2015 年,王荃被列为省市追逃办 " 挂号 " 追逃对象。
好像敏锐的山中兽,王荃嗅到了千里之外的抓捕气息。最开始,王荃住的是高档小区,但有一天,他发现小区到处都是摄像头," 很惊慌 "。有次看电视,他看到很多地方都有 " 人脸识别 " 系统,更加坐立不安。
王荃从高档小区搬了出来,开始住不用登记身份证的小旅馆,或者去农村住便宜民宿——房租只需 480 元一个月。
在当地,细心的人们很快发现了一个 " 怪人 " ——桂林这样气候炎热的南方城市,正常人都是短衣短裤,有个人却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极低。这人无论出门干什么,总是背着一个背包,步履匆忙,也不跟人打招呼。
侦办王荃案主力民警、湘潭市公安局刑侦四大队大队长丁旻昊说:背包里都是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 方便他随时出逃 "。
2018 年 10 月 18 日,王荃家族有一件喜事,会在湘潭办酒。民警兵分几路蹲守现场,但是狡猾的王荃并未出现。这年腊月二十七,民警再次蹲点在王荃父母家附近,一直守到大年初六,依然没有等到王荃。
抓捕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经上两役,警方对于王荃的抓捕行动却越挫越勇。
2019 年 1 月 30 日,湘潭市追逃办组织市中院、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王荃的追逃情况,决定由市公安局选派精干力量深入排查王荃的社会关系,市中院指令原办案单位雨湖区法院给予配合,尽快将其抓捕归案。
2 月份,由湘潭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杨笠新挂帅,抽调精干力量组成追逃工作小组。民警丁旻昊等人兵分几路,从王荃的出生、入学一直到参加工作,重新逐一摸排,从亲属、同学等社会关系入手,每一个重要信息都不放过。
逐一排查后,有两个人进入办案民警的视野,他们是王荃的大学同学,这两人都爱好书法绘画,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桂林。
此后,追逃民警三赴广州,蹲守在这人的住地周围。虽然没有发现王荃的踪影,却也从相关人士处得到重要信息:王荃从 2011 年至 2012 年间,藏匿在广州某出租屋内。而且,他现在已经离开广州。
办案民警将目标锁定在桂林。湘潭市追逃办工作人员肖文灿介绍:追逃民警通过大量走访王荃的关系人及知情人,得到其在桂林从事鸡血石生意的信息。此后,民警迅速赶赴桂林就鸡血石行业进行摸排,逐步锁定王荃的藏匿地点。
经过两天一夜蹲守,民警成功识别出王荃。5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许,王荃步行外出办事,在一家包子铺门口被民警抓获。
民警丁旻昊说:王荃的表情很惊讶,好像在说,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在押解车上,追逃民警问王荃:怎么不主动投案?王荃说:我宁愿逃亡,我不愿意回来,因为我不想坐牢,不想失去自由。
民警在心里算了一下:当年如果王荃没有出逃,依法服完刑期,那么今年年底,他将重获自由。
看得出,他依然保持着某种骄傲,腰板笔直,喉结耸动。作为媒体后辈,我们也心怀恻隐:那些问题,他自己娓娓道来就好了,不要我们追着问。
然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接下来两个小时,客观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两个小时。我们隐隐感觉到:王荃内心有一头兽。它算不上凶猛,但是,诡辩、狡猾,还有些不甘和愤怒。
" 狡猾、诡辩 " 之类的评价后来在办案民警那里得到证实。王荃对自己漂泊生涯以及出逃、归案心理的描述,也只能采信可以佐证的那一部分了。
追逃办民警说:王荃作为一名负案的逃犯,即便用更多的借口、理由来解释出逃原因,用看似华美、精彩的辞藻试图掩盖内心的恐惧,也只能用 " 困兽犹斗 " 来表述其万一了。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5BllOaMoCqqjdbzoxQdDQ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6-23 14:45
【伦理学案例】
科学的原理与应用
亨利·奥古斯特·罗兰这位美国科学界泰斗说:“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中国人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编辑:王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2 22:06
【案例】
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原创:孙春晨 道德与文明
作者简介:孙春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100732)。
〔摘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始点,冯定、李奇、周原冰和罗国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们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伦理学者从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入手,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为突破口,由史入论、以史融论、史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诸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新时代道德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伦理学人理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学术追求,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推向新境界。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奠基 成果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始点,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建立到繁荣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的伦理学才能沿着正确的和科学的轨道向前发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回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道德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时期。受苏联高校学科建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内高校的学科设置进行了较大调整,伦理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予以取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重新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抱着向苏联学习的态度,中国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开始恢复伦理学学科,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成为创建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学术起点。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是从借鉴苏联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理想居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而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需要培育国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对于激发全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新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当时的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刚刚起步,知识积累不足,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苏联学者有关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成果,一些苏联学者的研究论著被引进和翻译,其中包括夏利亚等的《共产主义道德》(作家书屋1953年版)、柯尔巴洛夫斯基的《论共产主义道德》(三联书店1953年版)、包德列夫等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施什金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在恢复伦理学学科后,苏联学者这些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成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为中国伦理学界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冯定(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李奇(中国伦理学会首任会长)、周原冰(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和罗国杰(曾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二十余年)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们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他们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的深入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指导,论证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本特点,以浅显而又透彻的文字讨论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个人价值、自我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关系等问题,把抽象的哲理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切合了人们自觉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神需要。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初版和再版共印刷86万册。然而,到了1964年,《共产主义人生观》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后,纠正了对《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错误做法。
李奇(笔名“李之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多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道德科学的论文,涉及当时理论界讨论的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如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的问题、关于对立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等,这些论文在改革开放初期被收入《道德科学初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李奇通过这些论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出现是伦理学领域里的根本变革的重要论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例如,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她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中的‘个人利益’概念,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正好体现了无产阶级个人利益观的实质。”在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他明确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并不妨碍道德的继承性……任何拒绝或脱离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思想,都必然陷入抽象的继承和道德永恒论。”
周原冰(笔名“石梁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有两项标志性成果。一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其专著《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阐发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般原理,对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他讨论了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的集体主义原则。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周原冰先生最具特色的观点是坚持主张‘道德科学’说。”周原冰阐释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重要性:“认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道德的理论武器,对于破除一切陈腐的道德观念和促进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道德问题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集中反映了周原冰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成果。
罗国杰于1960年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开始汇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道德》,在借鉴和研究苏联伦理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这个教学大纲大致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论述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一切合理的伦理思想及道德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就需要探寻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在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以及道德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将共产主义道德列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间,国内不同学者编撰的各种伦理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一框架体系传统,以单立章节的方式论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伦理学界前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领域孜孜以求,耕耘不辍,为后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指明了继续探索的前行方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道德文化成果,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一种超越封建主义道德文化和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新型道德文化。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如此独特的理论品格,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开拓出不同于以往伦理学体系的新中国伦理学的一片广阔天地。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方法。由此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特质,将道德文化研究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在道德发展的历史形态、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的社会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获得了一种科学的解释。三是密切关注时代的道德需要。不仅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理,向广大人民传播和普及共产主义道德的相关知识,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路径,并对人民关心的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合理的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
从当代严格的知识形态或学科形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撰写过专门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论著,也没有建立完整和系统的伦理学体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首要工作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和解读,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的伦理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人从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入手,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为突破口,由史入论、以史融论、史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结晶,也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后继者们所提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发展史必须秉持开放的立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只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主张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绵延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未有穷期,它必然会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
改革开放后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专著是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该著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理思想上做出的主要贡献,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专著,该著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分为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予以考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形成和传播到作为工人运动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武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要求。许启贤在其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当作一门历史科学,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作出了界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史,特别是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史”。他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需要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和革命思想史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是新中国70年道德文化演进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封建道德体系遭受新文化的强力冲击已然解体,而新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够在新中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既是新中国寻找道德文化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也是新中国顺应时代变迁不断追求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的目标使然。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塑造新中国道德文化的理论依据,并在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这不是理念式和标签式的抽象转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既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简单移植和生搬硬套,亦非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来匡正和改良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而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新中国70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的有机结合,是在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变革基础之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成果是在新中国亿万人民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它集中体现为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道德问题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毛泽东认为,道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和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思想,主张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论,强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性。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论述了邓小平伦理思想、“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伦理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物质文明与经济建设伦理思想、政治文明与政治建设伦理思想、精神文明与公民道德建设伦理思想、社会文明与和谐伦理思想、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伦理思想、党的建设文明与执政伦理思想等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视角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但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却不能局限于在经典文献中“抠字眼”,应当开阔研究视野,融合多学科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以“大历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它与当代历史相遇时,就需要考察其对当代正在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道德生活变迁所能发挥的功能,以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解释和改造社会道德生活状态的持久生命力。
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论述了从政治哲学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性,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能对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就将在面对现实的社会道德生活难题时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立足于人的解放,致力于从伦理的角度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进行道德评价,并探寻对社会加以改造以使之合乎人的本性的途径。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有关道德的论述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概括。该著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伦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过程的道德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依据,并用两章的篇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道德哲学和道德社会学思想,在解释和把握资本与道德、历史唯物主义和道德哲学之关系问题上开出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诸领域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涉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法律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与从历史的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从总体上宏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做法不同,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野转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侧面展开微观研究。这种研究路径的优点在于,“小切口,大纵深”,问题意识明显,针对性强,相关议题的研究有可能走向深入和透彻。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成为研究的重点,出版了多部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其中,王小锡关于“道德资本”研究的系列论著,讨论了道德作为影响价值形成与增值的精神因素所具有的资本属性,突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反映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工具的“资本”概念的原有意涵,将道德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生产性资源,并以此来分析道德在经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沿性研究成果。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家庭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发展伦理、民生伦理和劳动伦理等具体论域,学者们亦出版和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对马克思主义重要道德论题的回应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不断推进,一些中青年学者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是充分利用他们曾在国外读书、访学的学术背景优势,密切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道德论题展开深入研究,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
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与“非道德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发起了一场马克思与正义之关系的论争,分为“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由此又引致了延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关系的论争,一些学者持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观点,另一些学者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观点。近年来,这一论题引发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以撰写论文或在相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予以回应,以力证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中国学者提出的主要论据有: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批判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框架内进行的,在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有自己所秉持的规范意义上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判断上并不坚持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中,既存在法权意义上的解释性正义,也存在规范和价值意义上的评价性正义。从方法论的角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的问题上是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的整体来进行考察的。他们特别反对的是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反对把社会的改造变成为人的纯粹的观念的改变。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道德伦理思想的说法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读”。中国学者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不仅确认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有其文本的依据,而且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包括事实层面的描述性的道德社会学,还包括价值层面的规范性的道德理论。
关于解读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方法。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采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这两种解读方法的共同特点是,以超历史的普遍性道德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中国学者试图从“历史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做出解释。这种“历史的观点”解释立足于清晰地梳理有关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阐释的思想史,正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不同判断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础性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阐释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独特视角,这不仅是消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的立足点,也为当代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立场。
结 语
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国外伦理学学科的特殊现象,这就是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三足鼎立,虽然前两者属于学科名称,后者属于一种理论体系,但它们所研究的内容却相互交叉。鉴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大多数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或著作中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内容,而且关于道德的起源与发展、道德本质、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理想、道德修养等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髓。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国内伦理学原理和其他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三分说”,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三个部分,并将梳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线索、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范式和开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崭新篇章视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之一。这是一个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有价值的学术建议,兼具战略性和策略性。虽然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面对新时代道德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伦理学人理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学术追求,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推向新境界。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4期
来源:道德与文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BxlOkiuxmuuwInqIpf8fw
编辑:马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6 23:52
【案例】
理解道德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文贤庆,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副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在当代伦理学的研究中,一种道德理论要想获得独立的地位,就应该具有特别的语义学承诺、形而上承诺和认识论承诺。通过比较考察流行的实在论和表达主义观点,建构主义表明它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理论该有的地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一种原初性的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具有直接来自自然的可理解性;从形而上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基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以及某些经验起点的实践性程序建构;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以行动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实践境况为基础的实践慎思。
〔关键词〕建构主义 语义学承诺 形而上承诺 认识论承诺
自罗尔斯以降,建构主义就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以下统称为“实践哲学”)中引起了热议。从最早的政治建构主义到一阶规范性的道德建构主义,再到元伦理的道德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研究者试图表明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着规范性真理,这些真理可以通过一个理想化的理性慎思程序确定下来。然而,建构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对的批判与怀疑也不绝于耳,这些批判既包括对政治建构主义理想化原初状态的批判,也包括对规范性道德建构主义的非实在论批判和对元伦理学意义上道德建构主义地位之合法性的批判。
尽管有关建构主义的批判与怀疑不绝于耳,但本文试图表明,从元伦理学的立场来看,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区别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窠臼的第三种立场,可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元伦理学理论,而且能够为一阶道德规范立场和政治规范立场提供进一步的辩护。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需要表明建构主义在元伦理学立场中具有一种基础性地位。那么,什么是建构主义的元伦理学立场?按照元伦理的字面解释,它由前缀“meta”和主词“ethics”构成,前缀“meta”意指“在……后”“超越”“变化”,这意味着元伦理学是对伦理学背后的一些东西进行思考,这就涉及对伦理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例如,道德话语表达怎样的语义功能?是否存在某种规范性道德?如果存在,人们怎么认识它们的正确性?尽管我们很难完全清晰地为元伦理学划定一个范围,但大致而言,一个成熟的元伦理学理论至少应该在形而上承诺、认识论承诺和语义学承诺三个方面给出有关元伦理建构主义的实质性观点。因为批判者和怀疑者在语义上对元伦理建构主义的怀疑在根本上影响其作为一种元伦理的立场,所以我们将首先从建构主义的语义学谈起,紧接着,我们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主义所使用的这些术语到底表达了一种实质如何的形而上立场。最后,我们通过认识论的探讨来把握道德建构主义。
一、关于道德判断的语义学解释
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到底是什么意思?道德哲学家们对此各执一词。实在论者认为这些道德判断表达了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或真理;表达主义者认为这些道德判断表达了人类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表达什么客观存在的真理;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这些道德判断表达了某种依赖于人类心灵的客观事实。为了揭露这些争论的本质,我们需要回到道德判断本身。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重构三类道德判断并进行语义学的分析,以期从概念上厘清道德判断的实质。
按照实在论的看法,道德判断作为一个命题表现为如下形式:
MR:(1)存在着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并且(2)这些事实或真理独立于证明它们的那些证据。
基于实在论者布里克(Brink)的看法,MR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实在论结构使得它区别于表达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布里克认为,相比于实在论,表达主义者作为非认知主义者否认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存在,而建构主义者虽然作为认知主义者承认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存在,但主张这些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是通过我们道德信念的某种功能构成的。换而言之,表达主义者否认MR(1),而建构主义者否认MR(2)。在布里克看来,表达主义者因为否认了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存在而导致了对道德知识的否认,是道德上的怀疑论者,因此,在表达主义那里,诸如“善好”“公平”和“错误”等道德术语不能有效地指涉真正的道德属性,这些道德术语的意义充其量只能用来表达和描述一些激发性的心理情感;而建构主义者因为否认了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是独立于心灵的某种客观存在,导致了道德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主观性,是道德上的非普遍主义者。然而,道德实在论对于表达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指责合理吗?
显然,表达主义者根本不会同意实在论者的指责,尽管表达主义者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但他们承认道德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毕竟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因此,道德判断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性虽然并不描述世界上存在的某种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但它表达了世界中的某种心灵状态,吉巴德称之为规范表达主义分析。按照这种分析,这样的心灵状态不是具有认知内容的信念,而是具有激发性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意义上,道德判断不是针对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真假判断,而是相对于某种心理状态的呈现方式。道德判断指涉的是某种被激发的东西或被追求的东西,它是一种不同于日常信念的心灵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同于认知的信念,但它作为人类生活的不同功能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因此,对于表达主义而言,道德判断的语义学解释并不在于一种真理符合论,而在于一种意义解释论。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和表达主义一起反对实在论的真理符合论。尽管如此,但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认知主义理论在意义解释论上明显区别于表达主义。
按照建构主义对于道德判断的看法,“规范性主张的真在于这个主张通过一个实践观点而具有的内涵”。因为建构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表达主义的看法,认为道德判断是相关于人的心灵状态,那么,围绕着人的心灵状态就会呈现出有关道德判断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权威性、实践性和客观性等,它们是我们归之于道德现象的内容。显而易见,道德现象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类如何在实践中做出道德判断。人类如何产生道德判断及行动的实践和道德判断何以有效的客观性构成了其核心。正是在对道德现象的意义解释论中,建构主义和表达主义区别开来。在表达主义看来,道德判断指涉的是心灵状态的激发性因素,表达的是对人类实际生活中某种观点或采取某种行动的支持或反对态度,是一种激发性的情感态度。然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表达主义者对道德判断所做的意义解释仅仅是一种消息式的间接策略,这种间接性的策略并非可以进行真假判断的原初解释,而只有一种原初解释才具有不需还原或倒退的实质性,因此,表达主义者对道德术语的解释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间接策略。区别于表达主义的间接策略,建构主义者为道德判断和相关的规范性术语提供了不同于表达主义(当然也不同于实在论)的原初性解释。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既然规范性道德术语的意义在于从实践观点进行意义理论的解释,那么道德判断的语义学问题首先并不在于单纯的理论概念解释,而在于通过实践对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所指涉的内容进行解释。这意味着,建构主义语义学的问题是针对实践问题的意义解释问题。不过,不同的建构主义者对该问题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建构主义者认为,道德术语的规范性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实践生活中一系列道德观念的哲学调查;有些建构主义者认为,道德术语的规范性语义是通过一个价值主体在使用本质性的规范概念时做出的各种推理而显示出来的;有些建构主义者认为,道德术语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理性慎思和修正的结果……虽然建构主义者在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指涉的内容上存在纷争,但就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实质理论而言,他们都赞同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对实践问题的意义解释在语义学上具有原初性。这种来自实践问题的原初性表明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直接来自自然世界、来自日常生活,是我们人类关联于世界的非理论性经验。建构主义把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的语义学解释建立在这些活生生的实践体验之上,用语言和概念进行表达,这意味着,在我们形成相关的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之前,我们已经直面那些活生生的实践问题,我们是对那些实践问题经过反思具有一定的观念之后才形成了我们所使用的道德语言和概念。很明显,建构主义的语义学承诺就是对实践问题的意义解释问题,而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面解释依赖于建构主义的形而上承诺和认识论承诺。
二、关于道德判断的形而上承诺
尽管建构主义的语义学为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提供了一个原初性的说明,但这个说明并不完善,要在根本上理解建构主义的语义学说明,我们还得进一步澄清建构主义语义学中的一些后续问题。而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就是建构主义语义学所指向的那些原初性的形而上承诺。
正如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涉及的,建构主义的语义学解释最终有赖于人类关联于世界的生活体验。问题在于,这种用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来刻画的生活体验到底如何区别于自然的客观事实?它们是怎样一种事实?这就使得建构主义不得不回应它自身有关形而上承诺的问题。由于实在论者被看作道德理论中最具形上性的代表,因此让我们依然从实在论入手。
在实在论者看来,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存在是一个最基本的承诺,这些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像那些非道德事实一样可以通过相同的语义结构(真理论)表达出来。然而,与之相反,以表达主义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同样旗帜鲜明地表示,根本不存在任何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也并不存在任何道德属性。事实上,在当代元伦理的道德研究中,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孰是孰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没有可能对此做出一个全面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与实在论/反实在论这种有关形而上承诺或否定立场不同的是,建构主义在形而上承诺中另辟蹊径,拒绝实在论/反实在论这种二分。那么这条路径是什么?它成功了吗?为了解决这个谜团,我们得回到建构主义语义学的意义解释理论中去。
基于我们前面有关建构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分析,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的意义理论有赖于建构主义对实践生活的原初性解释,对建构主义而言,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所指向的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实践问题,这也就意味着,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首先是一种行动主体依赖的东西。对此,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主体依赖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它如何呈现为我们所谓的道德现象?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说明是由科斯佳给出的。
按照科斯佳的看法,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他们都认为规范性概念的首要功能在于通过判断的正确或错误来表达它们所是的事物是否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然而,对科斯佳而言,她相信规范性概念通过正确或错误的判断表达的是一种实践功能,它们标识的是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而不是表现某种实在性特征。正如她对罗尔斯正义概念的解读一样,正义概念不是代表一种属性,而是指涉我们在实际的分配问题中的解答。正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见解,科斯佳认为建构主义既区别于实在论,又区别于反实在论。对于实在论而言,它们认为道德判断的正确性表达了一个存在于世界中的规范实在性;而对于反实在论而言,它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真理;但是,按照科斯佳的看法,建构主义认为道德判断的真假根本就不是表达有关世界的规范性事实,而是对于实践问题的解答。然而,因为部分实在论主张道德判断的正确性依赖于某些精神状态,而以表达主义为代表的反实在论也认为道德判断表达了某种心灵状态,这都与建构主义认为道德判断依赖于心灵状态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分析建构主义有关这种心灵状态的形而上承诺如何区别于其他二者。
十分明显的是,建构主义和实在论以及表达主义因为共享道德对于心灵状态的依赖而具有共性。就建构主义和某些实在论的共同点而言,它们都认可道德判断的正确性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某种精神状态;就建构主义和表达主义的共同点而言,它们都认可规范性术语的功能在于通过表达非信念性的心灵状态来引导行动而非表现事实内容。然而,因为建构主义自认为是一种跳出实在论/反实在论二分的特殊立场,因此,尽管建构主义和实在论以及表达主义具有共性,但它更认为自身区别于另外两种立场。因为建构主义和作为反实在论立场的表达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让我们先来粗略地审视。
虽然建构主义和表达主义都表达了某种非信念性的心灵状态,然而,对于表达主义而言,这种心灵状态并不存在真假的问题,它们仅仅表达了一种激发性态度或心理。表达主义相信这种激发性的态度或心理足以引导我们的行动,进而,规范性述谓通过模仿日常描述性述谓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行动是否被激发的解释,最终,它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自然世界中从事道德生活的日常现象。表达主义通过把激发性的态度或心理看做有关道德现象的形而上承诺指出,道德现象在根本上就是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自然理解,而这种理解就是如何理解激发性态度或心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表达主义在道德现象中做出的这种形而上承诺失败了,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表达主义把道德判断仅仅表现为激发性态度或心理的做法丢弃了道德判断的规范性意义;其二,表达主义把道德判断仅仅表现为激发性态度或心理的做法导致实践理性的工具化。建构主义相信,有关道德判断是一种心灵状态的形而上承诺必须解答道德判断的规范性意义问题和实践理性的非工具化问题。
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规范性问题关联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某种慎思程序进行自主推理,这种自主推理活动不仅仅是我们有关实践理性的工具化解读,而且是能够针对实践问题为行动给出规范性指导的东西。这意味着,道德判断并不像表达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仅仅表达一种激发性态度或心理,而是表达了某种重要的、具有权威性的理由规范,我们的道德现象正是通过我们的自主推理回应实践生活而展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有关道德的形而上承诺也区别于实在论。
因为按照实在论的观点,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要么独立地存在于心灵之外,要么作为一种评价性的观点依赖于心灵的信念表达,但无论如何,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作为一种独立的形而上承诺是独立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的。然而,在建构主义看来,实在论对于道德形而上的承诺因为脱离了人的能力而具有某种神秘性,进而让人难以理解,因此,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根本不可能脱离开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而单独存在,它必须从一个能动者对某物进行赋值的实践立场中获得其规范性,而这种立场是一种构成性的建构主义。在这种构成性的实践立场中,建构主义对于形而上的承诺是基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以及某些经验起点的实践建构。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就有关道德理论的形而上承诺而言,建构主义认为实在论对于道德形而上的承诺因为脱离了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而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不可理解性,而以表达主义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则因为对规范性和实践理性解释的无力而无法真正解释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建构主义相信,他们通过把道德现象和道德属性置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之下,可以在实践赋值的构成性活动中为道德提供一种更加合适的解释。现在,让我们通过把目光聚焦于道德判断的认识论承诺来明晰这种解释。
三、关于道德判断的认识论承诺
在上面有关道德形而上承诺的说明中,我们虽然分别指出了实在论对独立的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的形而上承诺,表达主义对激发性态度或心理的形而上承诺,以及建构主义对人性反思和能动性的形而上承诺,但我们并没有证成性地表明建构主义的形而上承诺必然地优胜于其他两者。溯其根源在于,有关道德的形而上承诺只有通过有关各种理论的认识论承诺才能最终得以完成。因为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构成性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一种认知建构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将主要以阐述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承诺为主线,同时在兼顾其他两种主义的认识论承诺中表明建构主义何以胜出。
回顾上述建构主义有关道德的形而上承诺,我们看到在建构主义的建构中必然有一个起点。为此,罗尔斯写到,“并非所有事物都是被建构的;我们必须具有某些原料,好像(建构)从它开始”。那么这个起点是什么呢?事实上,正是在有关起点的问题上,建构主义和另外两种主义产生了根本分歧。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对于建构起点的鉴别其实质是对道德判断进行认识的一个证成过程,而其他两种观点却并不如此认为。正是因为这个起点的不同,三种主义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论承诺。
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因为以表达主义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在根本上并不承认道德事实或道德真理的存在,所以它们以激发性态度或心理为起点的道德认识其实是一种对知识论的虚有模仿,他们自认为通过这种模仿可以达到对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作为一种精确信息的解释其实是失败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道德判断的真假是一种知识论而不是某种伪装的模仿。对于实在论而言,因为他们坚信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是对某种客观实在的发现和认知,因此,他们有关道德的认识论承诺就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推理发现和认识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论的起点在于独立于心灵的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建构主义与上述两种主义都不同,它认为对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进行解释的关键在于“建构”,因此,虽然建构需要一个起点,但这个起点作为道德来源的一个形而上承诺只是相关于实践的经验事实,它意指我们基于人性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对行动环境的思考,而我们的认识论承诺就是我们如何在实践行动中基于这个起点进行道德判断的建构。
基于不同的起点,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表达主义通过模仿对激发性态度或心理进行所谓的认识论说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针对的是具有真假判断的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虽然,表达主义的道德起点具有经验实践性,但它却只是一种激发性态度或心理,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现象的认识似乎仅仅相关于行动的动机,而无关乎道德目的本身的好坏,进而,实践理性只可能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相比于实在论把道德的起点置于某种独立于心灵的客观真理或事实并进而进行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的发现和认知,建构主义的认识论针对的是具有经验实在性和主体依赖性的道德真理或道德事实。虽然实在论的道德起点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它却只是一种神秘的难以理解的实在,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现象的认识似乎在于我们如何发现或认知一个独立于行动主体的神秘实在,而无关乎行动主体到底是如何做出合适的道德实践的,进而,实践理性就变成了一种理论性的推理。然而,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何以建构主义主张的有关道德现象的认识论解释就是更加优越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基于道德现象的源头对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承诺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
如果我们确实承认道德发生在我们的实践生活当中,那么在道德视阈和道德人格的解释中,我们就必须承认,道德判断对我们的实践生活是重要的,是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这些性质直接表现为道德判断应该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换言之,很多哲学伦理学家却质疑道德判断这两种性质之间的融贯性。对于这一质疑,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给出了很好的说明:“日常的道德实践表明了道德判断具有两个方向相反的特点。道德判断的客观性表明了存在着完全被境况所决定的道德事实,而且我们的道德判断表达的是我们关于这些事实是什么的信念。……而另一方面,道德判断的实践性表明了相反的事情,即我们的道德判断表达着我们的欲望。”实在论者和作为非认知主义的表达主义者正是在道德判断的这两个方面各执一端,实在论者重在寻找作为客观性的阿基米德支撑点,而非认知主义者则重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这导致二者格格不入。然而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承诺则试图向我们表明,只要我们主张道德是有关我们是谁和如何生活的指导,那么道德判断的这两种性质就理应可以融合。
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为了确保道德判断既是客观的又是实践的,道德的起点就必须基于每一个道德主体的自主能动性。道德起源于每一个主体的自主思考能够确保道德判断具有普遍客观性,而道德起源于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则确保道德判断具有实践性。然而,对于道德主体的自主能动性而言,虽然它在起点上基于人作为道德动物具有自主能动性的自然特性,但更重要的在于人的自主能动性在不断的反省过程中的建构。这种建构表现在人通过反省可以达到一种反思平衡,而基于自主能动性的道德判断也可以对每个行动主体都普遍有效,不过,为了确保这一点,道德判断的正确性就不可能基于某个独立于心灵的形而上承诺,而必须是基于一个共享的自主能动性概念。既然这个自主能动性概念不是独立于心灵的形而上承诺,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实在论所主张的那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质料实体,而只能是依赖于行动主体但对所有行动主体都有效的普遍形式,这种普遍形式只能在一种建构性的程序中找到,而这种程序性特征也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形而上承诺,它是实践生活中的道德主体以自身的自主能动性和实践境况为基础,进而寻求一种对于所有道德主体都普遍有效的实践慎思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表明,道德判断是对那些实践问题经过反思形成的观念解答。通过认识论问题的实践所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构主义既区别于仅仅强调客观实在性的实在论,也区别于仅仅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激发性态度或心理的表达主义。
结 语
通过上述语义学承诺、形而上承诺和认识论承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主义在三个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说明: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一种原初性的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具有直接来自自然的可理解性;从形而上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基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以及某些经验起点的实践性程序建构;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以行动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实践境况为基础的实践慎思。然而,在批评者看来,建构主义的语义学承诺依赖于它的形而上承诺和认识论承诺,而后两者又相互依赖,这导致建构主义实质上是不牢靠的。其实,要想理解建构主义者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关键在于应该如何理解有关道德事实对于心灵的依赖性。实在论者认为一个依赖于心灵的道德事实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表达主义者则认为依赖于心灵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道德判断。然而,在建构主义看来,这些批评者们忽略的一个大前提是,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的产生和使用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发现理论知识的过程;相反,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的使用展现的是使用理性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使用的那些规范性概念是相对于日常实践问题的解答,而不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遭遇的对象或事实。
作为独特的道德生活主体,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通过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发生关系,人类的能动理性赋予这个世界以价值,这个有价值的世界对我们呈现出意义、规范,进而形成道德。道德世界的规范性和意义在人类的能动实践中体现出来,体现为指引我们生活和行动的道德之客观有效性和实践激发性。然而,十分明显,道德世界不是一个孤零零地独立于我们的神秘世界,它是我们作为行动主体在实际境遇中一步步建构出来的世界,并不存在什么独立于人类心灵的道德事实,恰恰是人在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建构出对具有同样身份的道德主体都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道德的客观有效性并不在于一种独立于心灵的实在性,而在于对所有能够建构道德世界之行动主体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因为来源于每一个有价值的建构者自身而应该具有实践激发性。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4期
来源:道德与文明
编辑: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6 23:54
【案例】
谁该为人工智能新闻的伦理失范负责?
谁是算法生成新闻的作者?程序员是否应该负责?互联网平台是否应该负责?解决人工智能新闻的伦理失范问题,首先应分清责任主体。归责模糊不清,将导致问题的化解陷入怪圈。
李慧敏
媒体一直伴随着技术演变、更迭而发展变化。人工智能时代,新闻行业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探索各类应用。不过,目前人工智能新闻的应用大多是在模式化、公式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上,即使人工智能新闻能够在数据中发现新的相关性,算法也无法解释这些相关性的原因或后果。更应引起重视的是,人工智能新闻还制造了许多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新闻面临的问题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机器人伦理的初步草案报告》,阐述了机器人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对新闻业的冲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新闻业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潜在的法律以及伦理道德问题。
撇开假新闻不谈,人工智能写作中,无论技术问题(如所使用数据的质量、正确性及写作质量),还是伦理规范问题(如算法中编码的伦理问题),都引发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从伦理规范上来说,问题主要涉及数据透明性、算法偏见、算法权力滥用、信息茧房化等。从技术上来说,人工智能新闻的问题关乎其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即产生文本数据的准确性和正确性。人工智能算法错误率较低的原因是算法不会出现拼写错误或算术计算错误,但是,在具体新闻运用中存在数据失真的问题,或因为有人恶意修改结果,或是人工智能算法存在偏见。人工智能算法的偏见可能会影响数据的读取,从而影响新闻稿件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失范的责任归属困境
人工智能在媒体和信息领域伦理失范现象日益增多,自动生成内容的问责问题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谁来为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负责?
Propublica数据新闻副主编奥尔加·皮尔斯和调查报道记者朱丽亚·安格雯认为,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新闻生产越来越接近学术工作,新闻产品所涉及的数据和算法都需要严格的核实和说明,才能不与新闻伦理规范相冲突。
认真的监督和核查的确可以消除或最小化一部分因不可预测的事件或误导性数据引起的错误。但现实是,监督和核查只能避免一部分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分为监督式和无监督式两种,监督式学习比较容易核查出错误,而在无监督式学习中,由于机器可以获得自主学习能力,数据输入与输出均为未知状态,这种方式将新闻生产过程推进更深的“黑箱”,产品成为“无须推敲”的成品,编辑对事实的核查、对真相逻辑链的追寻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即使核查出错误,责任主体难以明确、责任归属难以认定等问题仍是影响人工智能新闻伦理规范甚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时最为棘手的问题。
谁是算法生成新闻的作者?
算法自动生成新闻的作者是谁?或者说,谁对算法的言论负责?我们很容易用一种捷径来解决责任问题:编辑或事实核查人员的责任。的确,在新闻领域,很容易找到被委托检查新闻内容的个人,他们通常与文章作者一起承担责任。而且在传统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用原创性标准来解决“作者是谁”的问题。但是,在人工智能新闻中,人工智能算法是否具有真正的原创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在当代的算法生成新闻如“机器人新闻”中,作者与原创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不大。在“机器人新闻”中,算法的原创仅仅表现在生成内容的决策上,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劳动。其他由算法承担的工作,如收集信息,根据信息自动生成内容以及预测信息输出等,无论其是由算法发起的还是仅仅由程序员安排的,都很难明确界定责任者。
在人工智能新闻中,如果在编程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算法可能会忽略预先确定的数据,从而扭曲输出,编辑和事实核查人员将没有相应的技术来识别它。编辑和事实检查人员可能无法理解算法的代码,并且相信他们的工程师和程序员能够开发出好的算法。因此,编辑或事实核查人员可以检查输出的某些方面,但他们不能检查算法的所有方面,当然也不能检查算法产生新闻的技术过程。此时应该追究编辑、核查人员责任还是算法、程序员的责任?
在传统的新闻业中,如果一条新闻是匿名的,这意味着它是由媒体的整个部门创建的,并归责于整个团队,同时应向编辑追究责任。但是,在自动化新闻中,如果一条新闻是匿名的,如何辨别作者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算法是一个难题。新型算法训练使得计算机通过深度学习,拥有它自己的“大脑”。重要的是,深度学习是自动化的,常常不需要人工直接输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作者身份是谁?谁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产生的不可预测的输出的作者?如果是算法作为作者,算法能否作为责任主体?算法能否作为责任主体被追究责任?
算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的生成,但是,直到目前,智能技术尚未完全达到自主性和适应性,算法对信息的处理和分发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这是由于算法几乎没有能力验证语句或改变引文的含义,除非经过专门编程。这些算法仅仅是特定编程工作的结果。因此,很难证明算法是否是在知道虚假信息或不顾后果地无视真相的情况下运行的,将其判定为独立的责任行动主体又显得论据不足。
程序员是否应该负责?
如果将责任转移到程序员身上,那么程序员或工程师应该对他们的人工智能算法输出负责吗?尽管程序员是算法中变量的控制者和写作者,工程师和程序员所编写的代码直接影响新闻伦理,但是,人工智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独立决策是受到编程数据选择和组装数据指令的控制。那么,程序员是否应该为他们的算法产生的问题负责?我们如何判断程序员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算法会产生错误的陈述?如果能够证明算法的程序员怀有恶意,那么理当追究程序员的责任,但我们又如何能够证明程序员主观怀有恶意呢?这就又陷入了一个怪圈当中。
互联网平台是否应该负责?
目前,对于互联网平台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也存在争议。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实际上起到新闻媒体的功能。尽管互联网平台并不直接从事新闻内容制作,但是其推荐算法实际在对新闻价值的不同维度予以赋值。随着越来越多民众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互联网信息平台在新闻分发和互动环节产生了巨大的动能。
互联网平台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问责困境。根据避风港原则,互联网平台认为它们只是信息存储、搜索和链接的通道,并不直接生产新闻内容,因此,向不直接生产和编辑内容的互联网平台问责的难度很大。但是,平台企业在内容处理方面的失误,将极大地影响社会舆论,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平衡不同权利主体的重任。
凯利曾感叹:“人工智能的失败在于,开发出了效用,却牺牲了控制论。”也许未来人类将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算法在新闻中的应用,而当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时,人类面临“失控”将会束手无策。
目前,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我们需要建立伦理和法律规则,明确责任主体及相应的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规范相对超前的人工智能新闻伦理问题,使其处于人类可控范围内。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包萨仁娜
来源:新闻战线
编辑: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8-7 00:16
【案例】
哲学会议、报告和课堂讨论的规范
David Chalmers编
编者按:熟悉国内哲学界的人会注意到,在学术会议、讨论群、专场报告甚至课堂上,常有一些带着戏谑、嘲弄甚至侮辱的表情、动作或评论。我们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几篇文章评论这一现象。今天推出的是著名哲学家David Chalmers编写的职场规范。
以下准则主要针对的是学术报告会、会议、研讨会、课堂等正式场合的口头哲学讨论。很多准则也多少适用于非正式的哲学讨论和非哲学讨论。
这些具体规范是用来是推进那些具有尊重性、建设性和容纳性并且适用范围更广的规范。这些规范或许不是无例外的绝对规范(不尊重他人、非建设性和排斥性在一些场合是合适的)。 但是,在很多哲学语境中,这些规范是适切的。不同的群体可以根据其需要对这些准则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或修改。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高度尝试性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非常欢迎补充、删减和改变方面的建议。感谢给出建议的很多哲学家。
1尊重他人
1. 态度友好。
2. 不要打断别人。
3. 在提反对意见时,不要断然拒绝别人的回应(留个给别人回应的机会)。
4. 不要表现出无法置信的样子。
5. 不要对参与者翻眼睛,做鬼脸,不嘲笑参与者,等等,尤其不要私下对别人这样做。(可以有例外,比如向主席示意规范被违反)
6. 不要在主要的讨论进行的同时跟周围的人小聊。
7. 感谢你的对话者的洞见。
8. 反对命题,不反对人。
2建设性规范
1. 反驳是可以的,但同样总是可行的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报告人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些东西,或给出进一步支持他们观点的理由。即使是反驳,也可以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
2. 当某个反驳对某个观点是摧毁性的时候,寻找这个反驳所能带来的积极洞见,会对报告人有帮助。
3. 假如你觉得报告人的工作没有价值,你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么在提问前,你要三思。
4. 质疑一个工作或一个领域的预设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占据了讨论的大部分时间,可能对报告人并无帮助。
5. 你(个体或集体)不必抓住同一个反驳,对报告人穷追猛打,直到他认输。
6. 记住哲学不是零和游戏。(这话的一个类似版本是:哲学不是搏击俱乐部)
3容纳性规范
1. 不支配讨论(可以有例外,比如报告人可以支配讨论)。
2. 每次只提一个问题(对报告人的回答做进一步追问是可以的,但转移话题的问题则要排在所有其他听众问题的后面)。
3. 尽量不要无休止地讲你的问题(或你的答案)。
4. 感谢前面的提问者提出的观点。
5. 可以问你认为可能是天真或无知的问题。
6. 如无必要,不要举冒犯他人的例子。
4程序规范(针对报告结束后的问答;其中一些是就“举手/竖手指”制度而言的)
1. 假如有时间,在问答开始前休息3-5分钟(为了休息、离场以及构思问题)。将问题一直留到休息结束后。
2. 应由主持人而不是报告人来决定谁来提问(为了避免各种偏见)。主席应该记录下所有提问者的名字[并按名单顺序邀请人提问],而不是让人们反复举手。
3. 如果你不是报告人、当前的提问者或主席,就不要在没有受邀的情况下说话(偶尔的玩笑和其他非常简短的插话是有限的例外,不应被滥用)。
4. 你如果进一步追问,通常是可以的(除非时间很短),但是后续几轮问题通常应该越来越简短,斟酌一下是否真的需要第三轮或更多轮问题。
5. 举手/竖手指制度[可选的]:如要在某一点提出一个新问题,举起整只手直到主席确认你,并把你添加到名单上。如果只是进一步追问其他人当前提出的问题,只需竖起你的一根手指。
6. 进一步追问应该直接针对当前的讨论,而不是提与当前讨论不相干或关系很远的问题(如果是那些问题,你需要举起整只手)。
7. 主持人应该力图平衡参与者之间的讨论,优先考虑那些之前没有发言的人(不一定要根据看见他们的次序来安排发言的先后)。
8. 主持人应尽量控制好进度,让每一个人想提问的人有机会提问。在简短的讨论阶段,或者在只剩下较短的时间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不允许竖手指会有帮助。
9. 当邀请人提问、并将这些规范付诸实践时,主持人应对各种可能的偏见(比如,间接的性别偏见)心中有数。
5元规范
1. 当规范被违反时,主席应该以温和的口气指出这一点,并且,其他人也可以说一些[直接指出犯规行为的]话,或提醒主席有人犯规。
2.在研讨会之后私下指出别人违反了规范也是可以的(或者告诉主席,他可以跟违反者谈话)——如果这样做让你觉得更合适。
3. 如果主席违反了规范,可以现场或之后指出来。
4. 当违反规范被指出来时,尽量不要辩解。
5. 记住:好人违反这些规范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我自己确实违反了其中大部分规范。)
6. 尊重主持人对这些规范的执行。
7. 以轻柔的方式执行纪律,效果通常更好。
8. 主持人灵活地以及根据具体情境来应用规范是合理的,但是要警惕这样做时会重新带入偏见。
9. 一个群体事先对这些规范进行协商是可以的。在一个报告中,报告人可以要求主持人停用一些规范(特别是建设性规范),虽然主持人未必会同意。
6可能的附加规范(大部分是其他人建议的;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把这些规范列入标准清单,但是我赞同其中的很多规范,并且它们确实值得考虑)
1. 每个问题最长两分钟(修正版:两分钟以后,打断是可以的)。
2. 在邀请提问时,优先考虑年资较浅者(修正版:不要优先考虑年资较深者)。
3. 如果想就自己的问题进一步追问,需要征得主持人同意。 (修正版:如果在进一步追问后,还想进一步追问,需要征得主持人同意。)
4. 不要想着引人注目。
5. 不要随便在休息时段或报告结束后对报告人追问不休(他们可能要休息)。
编者简介
David Chalmers,纽约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主要论著有:《有意识的心灵》(1996)、《面对意识问题》(1995)、《延展心灵》(合著,1998)、《意识和它在自然中的位置》(2002)、《意识的特征》(2010)等。
译者简介
俞丽霞,江苏张家港人,就读于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
来源:分析哲学的日常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TjdJe2ygBwyr00FHV-cWg
编辑:晓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9-25 20:05
【案例】
从“德性”到“德能”——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从“德性”到“德能”
——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
作者简介: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
〔摘要〕《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德目表尽管令人困惑,却并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也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对相关议题的忽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这项工作连同他在虔敬(信仰)、慷慨、仁慈和信义等问题上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德性论的全面背离与颠覆,实现了从“德性”到“德能”的转化。“德性的政治化”与“德性的去道德化”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尚未完成。
〔关键词〕德性 马基雅维利 “四主德” 西塞罗
围绕着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与古典道德-政治哲学的关系以及在古今之变中的定位等问题,学术界向来聚讼纷纭,而这其中又以宗教议题和德性议题最受人关注。但遗憾的是,在现有的研究中,“virtù”(有些意大利文版本拼写为“virtú”)的翻译及其整体性理解问题主导了德性议题的讨论,反而对他笔下具体的德性条目关注不够,由此导致这些争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澄清。
本文旨在对《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那张令人疑惑的德目表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同时指出它对传统“四主德”的有意回避并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没有处理相关的议题。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本文试图揭示马基雅维利对古典德性论(以及人文主义德性论)的背离与颠覆,进而为上述争论提供一些新的论据或思路。
一
学术界公认,《君主论》第15-19章是全书相对独立的单元,同时也是全书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马基雅维利就君主应当具备的品性问题,向古典伦理、基督教伦理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伦理发起了挑战。对此,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是高度自觉的,他以清晰的语言宣称:“我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辩,与其他人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既然我的意图是写出一些对于任何理解它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东西,那么,我理当追随事物有效的真理而不是事物想象的方面。”(P XV.1)在《君主论》第15章中,马基雅维利详细列举了十一组德性与恶行(或者说美德与恶习):1 慷慨大方/吝啬小气;2 乐善好施/贪得无厌;3 残酷无情/仁爱慈善;4 背信弃义/笃守信义;5 懦弱胆怯/勇猛强悍;6 宽厚大度/傲慢自大;7 淫荡好色/纯洁自持;8 诚实可靠/奸猾狡诈;9 严厉苛刻/平易近人;10 稳健持重/轻率任性;11 虔敬信神/毫无信仰。
这十一组品性的对照,很容易让人想起《尼各马可伦理学》暗含的一份德性表,二者似乎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它刻意回避了传统的“四主德”,虽然第5组、第7组与“四主德”中的勇敢、节制不无联系,但对更为重要的智慧和正义却完全忽略;而且,马基雅维利开列这些品性的方式也颇让人费解,他并没有以连贯的褒/贬或贬/褒的方式列举,而是以间隔交替的方式变换列举,彼此之间也缺乏内在序列。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这其中第1组(liberale,以下只附注描述德性的原文)和第2组(donatore);第3组(pietoso)和第6组(umano)、第9组(facile);第4组(fedele)和第8组(intero)其实可以部分地合并,分别归属于慷慨、仁慈与信义,而《君主论》第16章、第17章、第18章恰好依次论述了这三种德性。
《君主论》第19章的开头说:“关于前面提到的君主的品性,我已经论述了其中最重要的,现在我想根据下述通则简要地讨论一下其余。”(P ⅪⅩ.1)如果我们的合并是恰当的,那么,剩下的第5组、第7组、第10组、第11组都是“不重要的”吗?显然不是,第11组“虔敬信神”(religioso)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不重要的”;他在第18章中提到君主必须“显得拥有”的品性包括:仁爱慈善、笃守信义、诚实可靠、讲求人道、虔敬信神,而“君主显得拥有上述最后一种品性尤其必要”(P ⅩⅧ.6)。由此,我们相信,第11组虔敬和信仰问题不是“不重要的”,而是“最重要的”——在古典传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以及人文主义传统中,它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向教皇家族的献礼中,他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自己“与其他人的见解有很大的不同”,而只能暗里发动攻击。
按照我们的合并,上述君主必须“显得拥有”的品性中除了“虔敬信神”之外,其实只有两种:“仁爱慈善”(pietoso)与“讲求人道”(umano)属于同一个范畴,即“仁慈”;“笃守信义”(fedele)与“诚实可靠”(intero)属于一个范畴,即“守信”。“仁慈”和“守信”有专章(第17章和第18章)论述,自然属于“最重要的”品性;但他并没有把同样专章(第16章)论述的“慷慨”纳入君主必须“显得拥有”的品性之列,如此看来,他实际上认为,就连“显得拥有”慷慨都没有必要甚或是有害了。
第19章随后指出:“如果一位君主被人认为反复无常、轻率任性、懦弱无能、胆怯怕事、优柔寡断,他就会被人蔑视……他应当努力在行动中表现得伟大崇高、强悍有力、稳健持重、勇猛无畏,他就其臣民的私人事务做出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P ⅪⅩ.1)这里他实际上只提到了第5组(feroce e animoso/animosità,fortezza)和第10组(grave/gravità),看来只有这两组才是真正“不重要的”品性——当然,所谓“不重要”并不是说这些德性本身是“不重要的”,而很可能是说,关于这些德性,他几乎很难提出“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的见解”,缺乏重新诠释的空间。那么,最后剩下的第7组(casto)呢?就像施特劳斯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在第16-19章里谈到了第15章所列举的全部其他德性,唯独没有提到“纯洁自持”。或许,在他看来,这种品性对于君主来说也是真正“不重要的”?
概言之,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以专章论述的只有慷慨、仁慈和信义这三种德性及其对应的恶行;并且,这三者中又以仁慈和信义最为重要,以至于他在《李维史论》中又以两组章节(第3卷第19-23章和第3卷第40-42章)集中对此加以扩展和延伸。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没有处理其他的德性,尤其是古希腊所谓的“四主德”以及虔敬,甚至也不意味着他认为这三种德性比“四主德”以及虔敬更加重要;相反,就像我们随后将要论证的,马基雅维利事实上对“四主德”不动声色地进行了更具颠覆性的重构,并且其意义可能更为深远。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他既然已经宣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将会与众不同,却又为何只选择上述八种德性(“四主德”、虔敬、慷慨、仁慈、信义)中三种相对次要的德性来展开论述呢?我们猜想,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的理论勇气还不足以让他公然挑衅那四种更重要的古典德性以及虔敬信神这一中世纪的核心德性,而只能以隐蔽、迂回的方式发动对古代和中世纪伦理传统的进攻?另一方面,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另外三种德性,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打算直接与之论辩的对象——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君主镜鉴”传统——在德性问题上,不仅有古希腊的资源,还有古罗马的资源。就像斯金纳多次指出的,在西塞罗和塞涅卡等罗马道德学家和修辞学家那里,除了传统的“四主德”之外,他们尤其关注三种公共生活之恰当行为所需要的品质:信义(fides,诚实守信)或相互信任,宽厚大度(humanita)和与之相关的慷慨、恩惠(liberality,generosity,gratitude),以及仁慈(dementia or misericordia)。所以,《君主论》选择慷慨、仁慈和信义来展开论述并非无的放矢。
我们还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关于慷慨、仁慈和信义的讨论并不限于君主,也适用于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共和国——及其统帅。法国学者罗米伊指出,在关于罗马人之崛起与获得霸权的历史叙事中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狄奥多罗斯以及普鲁塔克所强调的慷慨、宽厚、仁慈、善意所获得的爱戴,另一种则是李维在《自建城以来》中所强调的信义。既然马基雅维利如此倚重对罗马政治史的诠释,他对上述历史学家的著作又是如此之熟悉,那么,他特别选择慷慨、仁慈和信义这三个议题来回应古典的以及人文主义的德性论传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
《君主论》第15章的德目表对“四主德”的刻意回避并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没有处理相关的议题——在他有意识要对传统观点(无论是古典传统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人文主义传统)发起根本性挑战的德性问题上放弃对“四主德”的回应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像对待慷慨、仁慈和信义那样集中阐述他对“四主德”的看法,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对西塞罗改造、扩展后的“四主德”进行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尤其是考虑到他对《论义务》这一文艺复兴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古典文本非常熟悉,著名的狐狸与狮子的譬喻就是从此书中借用而来的。既然马基雅维利所应对的并非古希腊的“四主德”,而是经过西塞罗改造、扩展后的“四主德”,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来考查一下西塞罗所做的工作。
西塞罗在《论义务》第1卷中论述基本的德性时,对古希腊的“四主德”做了如下重述:首先,他将德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即智慧(sapientia)和审慎(prudentia,明智、实践智慧),另外一种属于行动的范畴,它包括正义(iustitia)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善行,善行也可以称作恩惠或慷慨(beneficentia et liberalitas);其次,他将勇敢扩充为“精神的伟大”(magnitudo animi),将节制扩充为“合宜”(decorum);再次,在具体阐述中,他指出,正义包含两个原则,即“不要伤害他人”和“有利于公共利益”(De Officiis,Ⅰ 10.31),其基础则是信义(fides),“亦即对承诺和契约的遵守和守信”(De Officiis,Ⅰ 7.23);最后,他总论说,“整个高尚性产生于下述四个方面之任何一种:或者蕴涵于对真理的洞察和领悟,或者蕴涵于对人类社会的维护,给予每个人所应得,忠实于协约事务,或者蕴涵于崇高、不可战胜的心灵的伟大和坚强,或者蕴涵于一切行为和言论的秩序和分寸,这里包含节制和克己”(De Officiis,Ⅰ 5.15,Ⅰ 43.152)。由此可见,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涉及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八种德性中的六种,即“四主德”与慷慨、信义,而虔敬事实上暗含于《论义务》全书之中;只有仁慈这一德性,《论义务》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情境只是偶尔提及。那么,马基雅维利又是如何解构与重构经西塞罗改造之后的“四主德”的呢?
首先,在西塞罗那里,“正义”被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正义,以及慷慨(善行)和信义(诚信)这两种附属的德性;这里暂且不说慷慨和信义,先简要地看一下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在西塞罗看来,正义是范围最广的,并且是“涉及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有如生活的共同准则的那个方面”(De Officiis ,Ⅰ 7.20)。它要求如果自己并未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不能伤害他人,为了公共利益而使用公共所有。同他在沉思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相一致的是,西塞罗改变了古希腊哲学家将智慧视为最高德性的传统,转而强调正义对智慧的优先性。他指出,“唯有正义这种德性是一切德性的主人、女王”(De Officiis,Ⅲ 6.28);虽然正义与智慧(审慎)都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但是正义更有力量,因为“正义没有审慎,仍然具有足够的权威;然而,若审慎没有正义,对于赢得信任毫无作用”(De Officiis,Ⅱ 9.34)。
然而,这一在古典思想中如此重要的伦理-政治价值却很少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他在《君主论》中三次提到正义:第19章只是说马尔库斯等贤明的罗马皇帝是“正义的热爱者”,其余两次就像曼斯菲尔德在《君主论》英译本的“导言”中所评论的:“在第21章中他的确提到了正义,正义被视为弱小势力的精打细算……在第26章中他还将正义视为与必然性相一致的事物。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从未提及——无论是在《君主论》还是在他的任何著作中——自然正义或自然法,古典传统和中世纪传统中的这两种正义观传承到了他的时代,并且在他的同代人谈论这个主题的作品中都会找到它们的影子。”不唯君主如此,共和国的领袖与统帅亦然,“在决定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容考虑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是仁慈的还是残酷的,是值得称赞的还是可耻的;相反,应该抛开其他所有的顾虑,把那个能够挽救祖国生命并维护其自由的策略遵循到底”(D Ⅲ 41)。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西塞罗以及亚里士多德都强调过正义与法律的伦理相关性,而马基雅维利虽然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法律的作用,但我们发现,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法律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效果。例如,在他关于两个“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法律,尤其是该法的制定者自己不遵守,便树立了坏的榜样”之案例的分析(D Ⅰ 45.1-2)中,他所诉诸的其实是审慎而非正义。他有时直接用正义代指法律,并将其与军队并称(P Ⅻ.1,但他从未将正义设定为法律的伦理目标。
其次,虽然西塞罗将正义置于智慧和审慎之上,但他从未拒斥古希腊的传统,而是仍然维护智慧的独特地位。他指出,作为对真理之追求与探索的智慧和审慎,“与人的天性的关系最为密切”(De Officiis,Ⅰ 6.18);“智慧为一切德性之首”(De Officiis,Ⅰ 43.153)。不过,既然智慧和审慎服从于正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具有严格的道德意涵:“审慎在于能够区分善与恶,然而奸诈,如果一切可鄙的皆是恶的,那么它把恶置于善之上”(De Officiis,Ⅲ 17.71);作为统摄性的德性,“正义若无审慎,仍会具有很大的力量;审慎若无正义,便不会有任何意义”(De Officiis,Ⅱ 9.34)。
相比之下,在马基雅维利的概念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审慎”已经全然不同于古典的“智慧”和“审慎”。在他看来,“事情通常是:人们试图避免一种麻烦时,难免遭到另一种麻烦;但是,审慎就在于知道如何识别各种麻烦的特性,进而选择坏处最少的作为最好的”(P ⅩⅪ.6)。
具体来说,按照古典哲学传统,审慎(实践智慧)的实践性可以分为三个环节:确定目的、认识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在复杂的情境中行动;而马基雅维利的审慎事实上仅仅关注于后两者,即实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以及如何在复杂的情境中采取行动。换言之,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审慎被“去德性化”了:无论是作为希腊德性之目标的高尚美好,还是作为斯多亚德性之目标的灵魂安宁,抑或作为基督教德性之目标的救赎,都被他加以否弃。对此,施特劳斯评论说,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审慎(判断力),以及心灵、意志或性情的力量,是唯一获得普遍认可的德能,它真正具有一般性德性那些获得普遍认可的特征:它们本身就是有益的。尽管道德德性和恶行(例如,信仰和残酷)可以被妥善或恶劣地使用,但它们的使用必须为审慎所规范,而审慎是不可能被恶劣地或不审慎地使用的”;“善与恶之间的转化必须以审慎来引导,并靠德能加以维系”。
不但审慎在他这里被“去德性化”了,而且被西塞罗批判为“对审慎之错误模仿”的“狡诈”(astutias,De Officiis,Ⅲ 17)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几乎变成了一个中性词(astuzia,或可译为“机巧”):“大人物更有远见、更加机巧”(P 9.2);“那些做成了大事的君主们都很少把信义放在心上,都深谙如何以他们的机巧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并最终战胜了那些立足于诚信的人们”(P 18.1)。也就是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在智慧、审慎与聪明、机敏、狡诈、狡猾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被马基雅维利取消了。
再次,西塞罗将传统的“勇敢”改造为“精神的伟大”(magnitudo animi)——这个概念来自古希腊文“megalopsuchia”,不过,其含义不同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4卷第3章所阐述的“大度”(magnificence or greatness of soul)。虽然西塞罗并没有提供对“精神的伟大”的定义性说明,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如古希腊思想家对勇敢的限制,他始终将其置于更高德性(正义)的制约之下:“对事物的认识若没有源自维护人类的美德,亦即源自人类社会联系的美德与其相结合,那它便会是空虚的,无成果的;同样,如果精神的伟大脱离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的联系,那它也会成为某种疯狂和残暴”(De Officiis,Ⅰ 44.157;Ⅰ 19)。
对于“精神的伟大”,马基雅维利采用了两个近似的、具有同构性的短语:“grandezza dello animo”和“virtù dello animo”。然而,我们发现,他同样是在中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些短语的:它们既被用来描述摩西、居鲁士等伟大的政治领袖,也被用来描述阿伽托克勒斯这样的恶人(上述两个短语都用上了);也就是说,他从未像西塞罗那样以更高的德性来限制之。同样,在描述另外一个恶人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时,马基雅维利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机智、勇敢、胆识过人”(ingegnoso e della persona e dello animo gagliardo,P Ⅷ.3)这样的词汇。
最后,关于“节制”或者“合宜”,西塞罗遵循柏拉图的观点(《理想国》432a),认为它与其他德性密不可分,“存在着一种东西,它体现在所有的德性之中,这就是合宜”(De Officiis,Ⅰ 27.95)。萧高彦先生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这个问题上对西塞罗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他关于“表象的统治”的论述中。我们则认为,“表象的统治”是一个独立的议题,与“合宜”未必有太大关联;而西塞罗在深入阐述“合宜”时提出的天性、德性、行为处事方式与命运、时势的关系这个问题(参见De Officiis,Ⅰ 30-33),倒是可能对马基雅维利的影响更为直接,但由于双方的论述都过于复杂,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
就节制本身而言,通检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从未谈论过这种德性。不过,在他对君主的劝诫中,他一再提醒君主要避免夺取其臣民的财产、染指其臣民的妻女,但这是从避免为人所憎恨的角度来考虑的,而非出于道德的自律(P ⅩⅦ.4,ⅪⅩ.1)。这对于君主来说或许是最底线的要求,尤其是要避免贪婪,亦即要节制对财富的追求。节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情欲的控制,马基雅维利有几处关于女人祸国的议论(D Ⅰ 7.5,Ⅲ 6.2,Ⅲ 26)也都基于同样的考虑。前文注释中提到的西庇阿“纯洁自持”的故事则表明,如果不能带来某种战略上的效果,那么纯洁自持就是无关紧要的。
三
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以及同时代人文主义的德性论传统的颠覆是全面的。在虔敬与宗教信仰问题上自不待言,上述对古典“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是深刻而彻底的,而他对《君主论》专章论述的另外三种德性的处理也未尝不是如此。
研究者已经指出,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virtù”的用法非常丰富,其含义多种多样:既用来描述自然事物,但主要用来描述人物;既用来指传统的道德德性,但主要用来指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干、勇气、技巧与能力。结合前文他对古典德性论的颠覆,笔者主张将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用以描述政治人物的“virtù”翻译为“德能”,以区别于传统的“德性”或“美德”。既然在他看来,最重要的“virtù”、他频繁地将之与“fortuna”(机运)对立起来的“virtù”,正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德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出现了德性的政治化,“Virtù在马基雅维利的词汇中获得了这样的含义,即任何有助于有效政治权力的人类品性”。克罗齐以降所谓马基雅维利确立了政治相对于道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一评论正是由此而来。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德性的政治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德性的去道德化,用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一位著名编辑者拉索(Luigi Russo)的话说,“virtú乃是心理而非伦理上的出类拔萃”。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德能”(virtù)与古典“德性”之间的对照,施特劳斯有一段精微的评论,值得引证:一方面,“他的‘德能’学说保留了(道德)德性与(道德)恶行之间通常所公认之对立的中肯性、真理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认德性(moral virtue)与恶行(moral vice)之间的根本区分;但另一方面,在他的德能学说中,这种对立开始“从属于另外一种卓越与拙劣的对立”,他强调了道德德性与某些其他类型之卓越(excellence)的差异,其方式是“在‘善’(goodness,亦即道德德性)与‘德能’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拒绝以‘德能’来命名道德德性”,换言之,“在大部分情况下,他是以一种不同于道德德性的含义来使用‘德能’这个概念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德性的政治化”不仅仅是服务于君主的“权势、安全、荣誉和幸福”(P Ⅵ.4)或者君主的“安全与福祉”(P ⅩⅤ.2),而是指向《李维史论》所揭示的祖国(patria)、共和国与公共利益(bene commune),以及《君主论》第26章所吁请的意大利的统一,那么,是否可以说,马基雅维利“政治化的德性”标示了一种新的道德(政治的道德)?或者就像以赛亚·伯林在试图将马基雅维利诠释为价值多元论的先驱时所说,他事实上区分了两种道德,即“基督教的道德”(Christian morality)和“异教徒的道德”(pagan morality)?
笔者以为,无论是“基督教的道德”与“异教徒的道德”,还是“私人的道德”与“公共的道德”“政治的道德”,抑或是“道德”与“政治”,都无法准确地概括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反而可能还会造成歧义和混乱。对此,笔者更倾向于赞同施特劳斯的评论: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以公共利益、政治目标(比如,不受外族统治、稳定或法治、繁荣、荣耀或帝国)来定义德性,“从德性这个词的有效意义上说,它是促成实现这一目的或这一目的所要求的习惯的总和。正是这一目的,也只有这一目的使我们的行动具有德性。为了这一目的做的任何事都是好的。这一目的使任何手段都成为正当。德性不过是公民德性,是爱国主义或献身于集体自私”;他实际上“以爱国主义或纯粹政治的德性(merely political virtue)取代人的卓越,或者更具体地说,取代道德德性(moral virtue)和沉思的生活:它有意地将最终目标降低了”。重塑德性的概念,将德性化约为君主(或共和国的公民领袖、军事统帅)的政治与军事能力,或者(爱国主义的)政治德性、公民德性,是马基雅维利对古典传统最为根本的背离与颠覆。
当然,我们也承认,马基雅维利与古典传统之间除了总体上的背离和颠覆关系之外,也有继承和利用的一面(如在慷慨议题和信义议题上可能就存在这种复杂的关系),或者说,古典理论也有其“现代性”面向。此外,所谓“德性的去道德化”过程也并非始于马基雅维利,而是早在瓦拉(Lorenzo Valla)这样的人文主义者那里就已经初现端倪,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马基雅维利迈出了最为关键性的一步。
事实上,古典哲人已经意识到“德性的去道德化”的可能,但在德性是因为自身而值得选择,还是仅仅因为它附带的利益、好处(对德性的“报酬”“奖赏”,还有一个比喻是作为德性的“影子”“虚像”)而值得选择这个问题上,古典思想家始终优先坚持前者,强调德性本身即是目的(例如,《理想国》358a,367d;《尼各马可伦理学》全书各处;西塞罗:《论法律》Ⅰ 18.48,《论义务》Ⅰ 4.14,Ⅰ 19.65,Ⅱ 12.43;塞涅卡:《论恩惠》IV);虽然他们也无意轻易地否定后者,尤其是从驯化、劝谕、教导更多普通公民(包括僭主)的角度考虑,他们更愿意把两者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则坚定地走向了后者,他的伦理学是第一个这样的伦理学,即“判断一个行为不是根据行为本身,而仅仅根据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他促成了一种后果论的或者说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的产生。
基于这种后果论,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德性论述中引入了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善与恶的辩证法”的机制,这种“辩证法”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善行与恶行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这种转化绝佳地体现在所谓“妥善地使用残酷”“恶劣地使用仁慈”这样极具其个人风格的表达上。因为笔者将另文专门论述马基雅维利“善与恶的辩证法”是如何运用于仁慈与残酷话题的,所以,这里不做详细阐述。但我们可以确定,不仅在仁慈议题上,而且在慷慨、信义等议题上,都可以看到他持有类似的“辩证法”。这是马基雅维利对古典德性论的又一重大颠覆。概言之,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当然是有善恶好坏、是非对错之分的,但这种善恶好坏、是非对错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伦理评判,而毋宁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后果论判断;由此,审慎便成为“唯一获得普遍认可的德能”。然而,以审慎作为落脚点或者说制高点的“德能”,在机运、机会、时势与必然性这些变动不居的客观因素面前,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上是极为有限的;审慎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追求,因为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审慎的德能,并且往往是自然的赐予。显然,这种伦理观念尚不足以应对或者纾解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政治困境,从整个西方道德哲学的发展来看,马基雅维利的主要作用可能还是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比如审慎的“平等化和民主化”、德性的“社会化”),仍需留待霍布斯这样的更具现代性的思想家来完成。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3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HWNMKojTl7wSX7W6w93zA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道德与文明”
编辑:高杰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9-26 23:31
【案例】
欧盟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路径及启示作者|曹建峰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方龄曼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3.png
欧盟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加速了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变革,人工智能(AI)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一般而言,AI是指基于一定信息内容的投入实现自主学习、决策和执行的算法或者机器,其发展是建立在计算机处理能力提高、算法改进以及数据的指数级增长的基础上。从机器翻译到图像识别再到艺术作品的合成创作,AI的各式应用开始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今,AI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不同行业领域(如教育、金融、建筑和交通等),并用于提供不同服务(如自动驾驶、AI医疗诊断等),深刻变革着人类社会。与此同时,AI的发展也对法律、伦理、社会等提出挑战,带来了假新闻、算法偏见、隐私侵犯、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日益受到重视,从政府到行业再到学术界,全球掀起了一股探索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热潮。而欧盟从2015年起就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举措,虽然在AI技术的发展上没能先发制人,AI治理方面却走在了世界前沿。
早在2015年1月,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JURI)就决定成立专门研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法律问题的工作小组。2016年5月,JURI发布《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案》(Draft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Rules on Robotics),呼吁欧盟委员会评估人工智能的影响,并在2017年1月正式就机器人民事立法提出了广泛的建议,提出制定「机器人宪章」。[1]2017年5月,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ESC)发布了一份关于AI的意见,指出AI给伦理、安全、隐私等11个领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倡议制定AI伦理规范,建立AI监控和认证的标准系统。[2]同年10月,欧洲理事会指出欧盟应具有应对人工智能新趋势的紧迫感,确保高水平的数据保护、数字权利和相关伦理标准的制定,并邀请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初提出应对人工智能新趋势的方法。[3]为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欧盟已将AI伦理与治理确立为未来立法工作的重点内容。
2018年4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政策文件《欧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 for Europe),欧盟人工智能战略姗姗来迟。该战略提出以人为本的AI发展路径,旨在提升欧盟科研水平和产业能力,应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带来的技术、伦理、法律等方面的挑战,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欧洲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欧盟人工智能战略包括三大支柱:其一、提升技术和产业能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其二、积极应对社会经济变革,让教育和培训体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密切监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为过渡期劳动者提供支持,培养多元化、跨学科人才;其三、建立适当的伦理和法律框架,阐明产品规则的适用,起草并制定人工智能伦理指南(AI ethics guidelines)。[4]同年6月,欧盟委员会任命52名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共同组成人工智能高级专家小组(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I,简称AI HELP),以支撑欧洲人工智能战略的执行。
2019年1月,欧盟议会下属的产业、研究与能源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欧盟议会针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制定全方位的欧盟产业政策,其中涉及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法律框架、伦理、治理等。[5]2019年4月,欧盟先后发布了两份重要文件——《可信AI伦理指南》(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简称「伦理指南」)[6]和《算法责任与透明治理框架》(A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ndtransparency,简称「治理框架」)[7],系欧盟人工智能战略提出的「建立适当的伦理和法律框架」要求的具体落实,为后需相关规则的制定提供参考,代表欧盟推动AI治理的最新努力。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4.png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6.png
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建构:可信AI的伦理指南
为平衡技术创新和人权保障,人工智能伦理框架的构建必不可少。伦理框架为人工智能的设计、研发、生产和利用提供原则指导和基本要求,确保其运行符合法律、安全和伦理等标准。《伦理指南》由AI HELP起草发布,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而欧盟鼓励各利益攸关方积极执行《伦理指南》,促进AI伦理标准形成国际共识。总体而言,除了制定泛欧盟的伦理准则,欧盟希望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能够在不同的层次得到保障。例如,成员国可以建立人工智能伦理监测和监督机构,鼓励企业在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设立伦理委员会并制定伦理指南以便引导、约束其AI研发者及其研发应用活动。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则的层面,而是需要融入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实践活动中,成为有生命的机制。
根据《伦理指南》,可信AI必须具备但不限于三个特征:(1)合法性,即可信AI应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符合现有法律的规定;(2)符合伦理,即可信AI应确保遵守伦理原则和价值观,符合「伦理目的」;(3)稳健性,即从技术或是社会发展的角度看,AI系统应是稳健可靠的,因为AI系统即使符合伦理目的,如果缺乏可靠技术的支撑,其在无意中依旧可能给人类造成伤害。具体而言,可信AI的伦理框架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一)可信AI的根基
在国际人权法、欧盟宪章和相关条约规定的基本权利中,可作为AI发展要求的主要包括: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民主、正义和法律、平等无歧视和团结一致、公民合法权利等。许多公共、私人组织从基本权利中汲取灵感,为人工智能系统制定伦理框架。例如,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小组(EGE)基于欧盟宪章和相关规定中的价值观,提出了9项基本原则。《伦理指南》在借鉴绝大部分已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4项伦理原则,并将其作为可信AI的根基,为AI的开发、部署和使用提供指导。
这些原则包括:(1)尊重人类自主性原则。与AI交互的人类必须拥有充分且有效的自我决定的能力,AI系统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用于服务人类、增强人类的认知并提升人类的技能。(2)防止损害原则。AI系统不能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AI系统及其运行环境必须是安全的,AI技术必须是稳健且应确保不被恶意使用。(3)公平原则。AI系统的开发、部署和使用既要坚持实质公平又要保证程序公平,应确保利益和成本的平等分配、个人及群体免受歧视和偏见。此外,受AI及其运营者所做的决定影响的个体均有提出异议并寻求救济的权利。(4)可解释原则。AI系统的功能和目的必须保证公开透明,AI决策过程在可能的范围内需要向受决策结果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解释。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8.png
(二)可信AI的实现
在AI伦理原则的指导下,《伦理指南》提出AI系统的开发、部署和利用应满足的7项关键要求。具体而言,在《伦理指南》中4项伦理原则作为顶层的伦理价值将对可信AI的研发与应用发挥最基本的指导作用,但7项关键要求则是可以落地的伦理要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是一个从宏观的顶层价值到中观的伦理要求再到微观的技术实现的治理过程。
1、人类的能动性和监督
首先,AI应当有助于人类行使基本权利。因技术能力范围所限AI存在损害基本权利可能性时,在AI系统开发前应当完成基本权利影响评估,并且应当通过建立外部反馈机制了解AI系统对基本权利的可能影响。其次,AI应当支持个体基于目标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个体自主性不应当受AI自动决策系统的影响。最后,建立适当的监督机制,例如「human-in-the-loop」(即在AI系统的每个决策周期都可人为干预),「human-on-the-loop」(即在AI系统设计周期进行人工干预),以及和「human-in-command」(监督AI的整体活动及影响并决定是否使用)。
2、技术稳健性和安全
一方面,要确保AI系统是准确、可靠且可被重复实验的,提升AI系统决策的准确率,完善评估机制,及时减少系统错误预测带来的意外风险。另一方面,严格保护AI系统,防止漏洞、黑客恶意攻击;开发和测试安全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后果和错误,在系统出现问题时有可执行的后备计划。
3、隐私和数据治理
在AI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内必须严格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确保收集到的信息不被非法利用。在剔除数据中错误、不准确和有偏见的成分的同时必须确保数据的完整性,记录AI数据处理的全流程。加强数据访问协议的管理,严格控制数据访问和流动的条件。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9.png
4、透明性
应确保AI决策的数据集、过程和结果的可追溯性,保证AI的决策结果可被人类理解和追踪。当AI系统决策结果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就AI系统的决策过程进行适当且及时的解释。提升用户对于AI系统的整体理解,让其明白与AI系统之间的交互活动,如实告知AI系统的精确度和局限性。
5、多样性、非歧视和公平
避免AI系统对弱势和边缘群体造成偏见和歧视,应以用户为中心并允许任何人使用AI产品或接受服务。遵循通用设计原则和相关的可访性标准,满足最广泛的用户需求。同时,应当促多样性,允许相关利益相关者参与到AI整个生命周期。
6、社会和环境福祉
鼓励AI系统负担起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利用AI系统研究、解决全球关注问题。理想情况下,AI系统应该造福于当代和后代。因此AI系统的开发、利用和部署应当充分考虑其对环境、社会甚至民主政治的影响。
7、问责制
其一,应建立问责机制,落实AI系统开发、部署和使用全过程的责任主体。其二,建立AI系统的审计机制,实现对算法、数据和设计过程评估。其三,识别、记录并最小化AI系统对个人的潜在负面影响,当AI系统产生不公正结果时,及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原则和要求由于涉及到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互相间可能存在本质上的紧张关系,因此决策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权衡,同时保持对所做选择的持续性记录、评估和沟通。此外,《伦理指南》还提出了一些技术和非技术的方法来确保AI的开发、部署和使用满足以上要求,如研究开发可解释的AI技术(Explainable AI,简称XAI)、训练监控模型、构建AI监督法律框架、建立健全相关行业准则、技术标准和认证标准、教育提升公众伦理意识等。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0.png
(三)可信的AI的评估
《伦理指南》在前述7项关键要求的基础上,还列出了一份可信AI的评估清单。评估清单主要适用于与人类发生交互活动的AI系统,旨在为具体落实7项关键要求提供指导,帮助公司或组织内不同层级如管理层、法务部门、研发部门、质量控制部门、HR、采购、日常运营等共同确保可信AI的实现。《伦理指南》指出,该清单的列举评估事项并不总是详尽无遗,可信AI的构建需要不断完善AI要求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各利益攸关方应积极参与,确保AI系统在全生命周期内安全、稳健、合法且符合伦理地运行,并最终造福于人类。
可见,在欧盟看来,人工智能伦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伦理规范和技术方案之间的耦合。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人工智能伦理构建可能多数还停留在抽象价值的提取和共识构建阶段,但欧盟已经更进一步,开始探索搭建自上而下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框架。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2.png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4.png
人工智能算法治理的政策建议:
算法责任与透明治理框架《治理框架》是由欧洲议会未来与科学和技术小组(STOA)发布的一份关于算法透明和责任治理的系统性研究报告。报告在引用一系列现实案例的基础上,阐明不公平算法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在特定背景下实现算法公平所存在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将算法透明和责任治理作为解决算法公平问题的工具,实现算法公平是算法治理的目的,同时强调「负责任研究和创新」(RRI)方法在促进实现算法公平中的作用和意义。RRI的核心是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实现包容和负责任的创新。
该报告在分析算法系统为社会、技术和监管带来的挑战的基础上,为算法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治理提出系统的的政策建议。报告从技术治理的高层次视角出发,详细论述各类型的治理选择,最后回顾现有文献中对算法系统治理的具体建议。在广泛审查和分析现有算法系统治理建议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4个不同层面的政策建议。
(一)提升公众的算法素养
实现算法问责的前提是算法透明,算法透明并非指让公众了解算法的各个技术特征。报告指出,对算法功能的广泛理解对实现算法问责几乎没有作用,而简短、标准化且涉及可能影响公众决策或者提升公众对算法系统的整体理解的信息内容的披露才更为有效。此外,调查性新闻报道和揭密对于揭发算法的不当用途,实现算法透明和问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纽约时报曾经报道Uber公司通过一定算法技术来标记和躲避城市的监管机构(此消息由Uber前员工透露),此报道当即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监管部门也对该公司采取调查行动。除了发挥监督作用,新闻报道致力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提升社会公众对算法的理解,新闻调查还可刺激广泛的社会对话和辩论,引发新的学术研究。例如,非盈利机构ProPublica的一篇关于一些美国法院使用的犯罪风险评估算法系统COMPAS中「机器偏见」的报告即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算法公平的研究。
基于此,《治理框架》提出几点关于提升公众算法意识的政策建议:(1)教育公众理解关于算法选择、决策的核心概念;(2)标准化算法的强制披露内容;(3)为进行「算法问责」的新闻报道提供技术支持;(4)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允许揭秘人在违反服务条款或者侵犯知识产权情况下免于追究责任。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6.png
(二)公共部门建立算法问责机制
当今,越来越多公共部门开始使用算法系统以提高办公效率、支撑复杂的办公流程并辅助政策制定活动。若算法存在缺陷,则可能对社会中弱势群体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公共部门格外需要建立完善的算法透明和问责机制。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治理机制是,借鉴数据保护法上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DPIA)机制,建立算法影响评估(Algorithmic impactassessments,即AIA)机制。此机制可以让政策制定者了解算法系统的使用场景,评估算法预期用途并提出相关建议,帮助建立算法问责机制。根据《治理框架》,AIA的流程主要包括:公布公共部门对「算法系统」的定义,公开披露算法的目的、范围、预期用途、相关政策或实践,执行和发布算法系统的自我评估,公众参与,公布算法评估结果,定期更新AIA等。
(三)完善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
一方面,对于各界广泛呼吁但存在巨大争议的算法透明,欧盟从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特征出发提出了较为中肯的建议。算法透明不是对算法的每一个步骤、算法的技术原理和实现细节进行解释,简单公开算法系统的源代码也不能提供有效的透明度,反倒可能威胁数据隐私或影响技术安全应用。更进一步,考虑到AI的技术特征,理解AI系统整体是异常困难的,对理解AI作出的某个特定决策也收效甚微。所以,对于现代AI系统,通过解释某个结果如何得出而实现透明将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也会极大限制AI的应用;相反,在AI系统的行为和决策上实现有效透明将更可取,也能提供显著的效益。例如,考虑到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GDPR并没有要求对特定自动化决策进行解释,而仅要求提供关于内在逻辑的有意义的信息,并解释自动化决策的重要性和预想的后果。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7.png
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算法监管方面,欧盟认为,对于大多数私营部门而言,其资源是有限的,且其算法决策结果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相对有限,所以不应施加算法影响评估等强监管。如果一味要求私营部门采取AIA,结果就是其负担的财务和行政成本与算法所带来的风险将不成比例,这将阻碍私营部门的技术创新和技术采纳。因此,对于低风险的算法系统可以以法律责任去规制,允许私营部门以更严格的侵权责任换取算法更低的透明度及AIA要求。根据《治理框架》,可以分层次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对于可能引发严重或是不可逆后果的算法决策系统可以考虑施加AIA要求;对于仅具有一般影响的算法系统,则可要求系统操作者承担较为严格的侵权责任,同时可以减轻其评估认证算法系统、保证系统符合最佳标准的义务。同时可考虑建立专门的算法监管机构,其职责包括进行算法风险评估,调查涉嫌侵权人的算法系统的使用情况,为其他监管机构提供关于算法系统的建议,与标准制定组织、行业和民间社会协调确定相关标准和最佳实践等。
(四)加强算法治理的国际合作
算法系统的管理和运行还需要跨境对话和协作。一国对算法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监管干预很可能被解释为保护主义或视为获取外国商业机密的不当行为。因此,《治理框架》建议,应当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全球算法治理论坛(AGF),吸纳与算法技术相关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参与国际对话,交流政策及专业知识,讨论和协调算法治理的最佳实践。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8.png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228/wps19.png
欧盟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启示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互联网发展中,欧盟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法律政策方面的差异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笔者在《论互联网创新与监管之关系——基于美欧日韩对比的视角》一文中的观点,欧盟在平台责任、隐私保护、网络版权等方面的制度规定都比美国更早和更严格,没有给互联网创新提供适宜的法律制度土壤。如今,步入智能时代,无处不在的数据和算法正在催生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和社会形式,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落后于美国等国家。去年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影响尤甚,诸多研究都表明GDPR阻碍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事物在欧盟的发展,给企业经营增加了过重的负担和不确定性。[8]
回到人工智能领域,欧盟希望通过战略、产业政策、伦理框架、治理机制、法律框架等制度构建来研发、应用、部署嵌入了伦理价值的人工智能,以此引领国际舞台。在这方面,欧盟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这样的优势能否最终转化为欧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却值得深思。整体而言,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探索,带给我们三点启发。
(一)探索伦理治理的技术路径
显然,面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伦理与社会影响,需要让伦理成为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组成部分,加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和伦理治理机制的构建。就当前而言,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实现,更多需要依靠行业和技术的力量,而非诉诸立法和监管。因为技术和商业模式快速迭代,成文的立法和监管很难跟上技术发展步伐,可能带来适得其反或者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标准、行业自律、伦理框架、最佳实践、技术指南等更具弹性的治理方式将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技术发展早期。更进一步,正如在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经由设计的隐私(privacy by design,简称PbD)理念在过去十几年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得通过技术和设计保护个人隐私成为数据保护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密、匿名化、差分隐私等技术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的理念也可以移植到人工智能领域,所以欧盟提出了「经由设计的伦理」(ethics by design或者ethical by design,简称EbD)。未来需要通过标准、技术指南、设计准则等方式来赋予「经由设计的伦理」理念以生命力,从而将伦理价值和要求转化为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设计中的构成要素
 ,将价值植入技术。
,将价值植入技术。
(二)采取多利益相关方协同治理的模式
当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整合和相互构建,其高度的专业化、技术化和复杂性使得圈外人很难对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准确的判断和认知。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参与的方式,让监管机构、决策者、学术界、行业、社会公共机构、专家、从业者、公众等都能参与到新技术治理中来,避免决策者和从业者脱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科技伦理教育宣传增进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在伦理上的自觉,使其不仅仅考虑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且对技术发展应用的潜在影响及其防范进行反思和预警性思考(precautionary thinking),才有可能通过广泛社会参与和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来实现对前沿技术的良好治理。所以,欧盟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需要不同主体在不同层次的保障措施,因此需要政府、行业、公众等主体在各自的层级建立保障措施。
(三)加强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数据流动、数据经济、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密切相关,而且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具有跨国界、国际分工等特征,需要在伦理与治理方面加强国际协作和协调。例如,2019年5月22日,OECD成员国批准了人工智能原则即《负责任地管理可信赖的AI的原则》,该伦理原则总共有五项,包括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福祉,以人为本的价值和公平,透明性和可解释,稳健性和安全可靠,以及责任。[9]2019年6月9日,G20批准了以人为本的AI原则,主要内容来源于OECD人工智能原则。这是首个由各国政府签署的AI原则,有望成为今后的国际标准,旨在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之下,以兼具实用性和灵活性的标准和敏捷灵活的治理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共同促进AI知识的共享和可信AI的构建。[10]可见,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共识,需要在此理念的引领下,加深国际对话和交流,在国际层面实现相协调的共同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框架,促进可信的、符合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防范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可能带来的国际风险和其他风险,确保科技向善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http://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8-2017-0005_EN.html?redirect
[2]https://www.eesc.europa.eu/en/our-work/opinions-information-reports/opinions/artificial-intelligence
[3]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1620/19-euco-final-conclusions-en.pdf
[4]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communic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europe
[5]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8-2019-0019_EN.html#title2
[6]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
[7]http://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STU(2019)624262
[8]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19/06/17/what-evidence-shows-about-impact-gdpr-after-one-year
[10]https://g20trade-digital.go.jp/dl/Ministerial_Statement_on_Trade_and_Digital_Economy.pdf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4SLiBjA2rMJVh8fSOTwZg
文章来源:腾讯研究院
作者:曹建峰 方龄曼
编辑:高杰
-
微信图片_20190926231413.jpg
(145.05 KB, 下载次数: 120)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9-26 23:46
【案例】
Nature:删帖、屏蔽关键词能阻止网络极端言论吗?也许效果适得其反导语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极端言论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今年8月发表在 Nature 的一篇研究表明,在极端言论传播的小世界网络中,关键词屏蔽等传统监管方式不仅效果不佳,更可能起到反作用。
极端言论自古有之,例如名著《飘》出现3K党,如今依然在美国南方不时露出獠牙。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极端言论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在 Facebook 上开设公共账号,在短时间让极端言论触及数万人,这使得监管机构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传统智慧告诉你要抓大放小,先管好主流的社交媒体,但 Nature 主刊今年8月底的一篇文章指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Nature 论文题目:Hidden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dynamics of the global online hate ecology
论文地址: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94-7
极端信息的传播网络是复杂的
这篇 Nature 文章的标题中的关键词是
Hidden resilience ,即
隐藏的弹性。这是一个来自生态学的术语,讲述的是生态系统在遭到外界打击后,由于网络结构,得以快速回到之前的状态的能力。该文将社交网络中的极端言论当成是生态系统中的物种,首先指出了极端言论在不同平台之间的传播是一站式的——某种极端言论可以一次性地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
下图中的 VKontakte(以下简称VK)是俄语世界的主流社交媒体,图中红色的是 VK 平台之间传播的仇恨言论,蓝色的是在脸书平台之间传递的仇恨言论,绿色代表是是跨平台的传播。

图1:极端信息在不同平台间的复杂传递网络,下图展示了对欧洲部分的进行了缩放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形象地看到,极端言论的传播网络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一个小世界网络,没办法找到一个核心节点,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该研究中,作者关注的是泛指的极端言论,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例如 ISIS 、新纳粹等。文中指出,这些言论的共同点是充满了偏激和仇恨,尽管仇恨的对象不同(可以是外来移民、同性恋者等)。
根据自动化的图像识别(例如识别血腥暴力的照片)以及文字主题分类,再加上手动的筛选,作者给出了一个包含768个节点(传播极端言论的账号),578条边的网络。
极端信息传播网络
存在无标度特性
在更细的尺度上来看,下图展示的是六十多个和3K党有关的极端言论,右图中的每个黑点代表一个社交媒体的用户,每个白点代表细分后的一个包含和3K党有关的主题。每个主题会形成一个聚簇,其关注人数在数十人到数万人之间。用户之间也会形成一个聚簇,用户聚簇的人数从一个到数百个不等。左图的宏观视角,不同聚簇的大小代表了关注的用户数,其距离越远,两个主题间共同关注的用户越少。
 图
图2:六十多个和3K党有关的极端言论形成的聚簇
图3:该聚簇的大小归一化后,计算不同大小的极端言论主题簇对应的用户数的分布,可以看出明显的指数分布。
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这意味着这样的网络更有可能具有嵌套性,而嵌套性的网络在遭到外部打击时能迅速复原。
在不同平台之间,当一个平台对某一个主题的极端信息进行取缔后,该主题对应的用户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主题上,往往还会使用其他的文字或“梗”,对极端信息进行“加密”,这使得新信息更难以被针对英语的自动监控算法检测。如果只是根据常识,没有注意到极端言论的传播网络的特征,简单的信息屏蔽只会使得极端言论如野草一样杀不尽,这也是标题中 Hidden resilience 所要概述的发现。
通过数学模型说明
不同平台监管力度不同造成的反作用
数学模型能够量化地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怎样预期的结果,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最优。本文提出的模型,假设传播极端言论的不同用户在社交平台之间会选择最短路径,在不同平台、不同主题的极端言论间进行迁移,但这样的迁移是有成本的。限于篇幅,不对模型进行详解,只简单说说模型得出的结论。
假设有两个社交媒体,A 对极端言论有较好的监管,B 则缺少监管。下图的纵轴是 B 平台上不同主题的极端言论之间的最短距离(最少需要多少用户才能相连)的均值,横轴是不同主题聚簇之间的总连接(用户和极端主题之间的边)。
通过该图,模型指出,如果只在 A 平台对极端言论进行监管,当 B 平台的用户和极端言论的连接数大于某一阀值时,会导致从整体上来看,不同主题的极端言论联系距离更远,从而使得进一步的打击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去中心化)。
图4:只针对某一平台的极端言论进行封杀带来全网极端言论的进一步分散
四种不同的
针对极端言论的应对方法
该文的另一大贡献是按照两个维度,区分出了四种应对极端言论的策略,以及在数学模型模拟的情况下,这四个策略各自的效果。限于篇幅,这里只对这四类策略进行概述,论文的补充材料中对此有详细分析。
图5:不同维度下的四种应对极端言论的策略
横轴表示干预的粒度,纵轴表示干预的方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左上角的方法是删贴——找到特定主题的帖子,全部禁掉;该方法的干预尺度较粗,这样做带来的反作用是会让极端分子迁移到另一平台,并没有治本。
右上角的方法是删号;这是更细致的干预,但大多数人都拥有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因此这种方法也只是一时之计。
右下角的策略是培养一批能够发出中和极端言论的用户,如图中的绿色圈子中的用户,让其作为社交网络上的“免疫系统”,从而稀释不同的极端言论主题之间的联系。
左下角的策略,则是将相互矛盾的极端言论同时曝光给同一个用户,让二者相互牵制,从而削减极端言论的影响力。
该文指出,四种策略需要有所权衡,才能达到对极端言论的最佳管控效果。
总结
如何应对极端言论带来的挑战
由于人群极化与国家对立,互联网上各类极端的言论也日渐增多,极端言论的管控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外的 3K党、新纳粹、ISIS 等毒瘤思想,甚至发展成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的危险因素。
在传统的纸媒时代,若想打掉一家宣传极端言论的报纸,仅需几个核心成员就能做到,并对某类极端思想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在社交媒体上,传统智慧不再管用,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至于极端思想的形成,其影响因素也由社交网络的邻里实体关系,转换到了虚拟空间上。这使得算法的影响变得显著,也使之前不可行的由下而上的方法(例如前文提到的后两种策略)变得可行。但由于极端言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们对其的管控仍需多种方法协作。
除了应用在极端言论的管控上,文本的结论是否对儿童色情的传播、非法人口交易、传销组织的人员招募等其他“暗网”也适用呢?这一点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个人的猜测是,对于一切非法的信息传递网,狡兔三窟的个体使针对某一平台的打击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正是由于这篇文章得出的结论具有“反常识”的特征,因此有潜力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且对现实的重大政策制定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作者:郭瑞东审校:刘培源
编辑:李倩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段永朝读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xbxnBLe8tpcE0SrYbNYoQ
编辑:高杰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9-29 21:13
【案例】
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也要去读康德呢?康德(1724年-1804年),出生于德国,毕业于科尼斯堡大学,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他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就其影响而言,整个十九世纪的一切哲学都以他的学说为中心。自康德之后,谈论形而上学就在德国蔚然成风:席勒、歌德研究过他;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都从他的唯心主义中汲取营养,并相继创立了伟大的思想体系。
总之,自康德起,哲学就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贝多芬满怀敬意地引用了他的名言:“头顶是璀璨星空,心中有道德法庭”。
邓晓芒,曾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
文丨邓晓芒
摘自《康德哲学讲演录》
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方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 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先看一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
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
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
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
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响。
甲:竹子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不响?
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
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
……
甲:泡泡糖为什么响?
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
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
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
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一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日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其实,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明明错了也不知道反思。这种思维方式为人们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片。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动脑筋,但中国人动脑子只动一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极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用“心”。人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人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诗性的负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种种怪事,包括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 等等,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而必须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边的人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在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黑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一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黑格尔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然而,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对康德哲学锲而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而感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对周围非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光靠说怪话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一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所以它是一种反思,一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一种重建。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在读康德的书时内心常常有一种感慨,觉得这正是我们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他所做出的解答,而是指他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我力图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把他这一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学到手,然后用来影响国人。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因此,康德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在这里,所谓“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里不仅仅包括知性,而且还包括超越的“勇气”。为什么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因为知性作为一种被“运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动性,它只是逻辑理性,而非超越理性。它只有作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发挥其无坚不摧的作用。超越理性的勇气首先体现为怀疑精神,即像笛卡尔那样,对一切既定的规范原则加以摧毁。这就是批判精神。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体现了大智大勇。而这种勇气最终归结到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认知上和行动上,就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由自己亲证的道理,都愿意做自己自愿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环境、历史、传统给他预设的樊笼都是不能长期忍受的,都势必要加以突破。
那么,有了这种勇气,如何做呢?如何运用自己的知性呢?其实每个人只要是成人,都已经具备自己的知性,也会懂得如何去做。但这里做一点归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我认为,一般知性的运用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第三是综观能力。先说记忆力。是人都有记忆力,甚至动物也都有一定的记忆力,有的动物比人的记忆力还强。但动物的记忆力是外在的,只是外部事物刻在动物神经系统或大脑中的刻痕;而我这里说的记忆力是指内在的记忆力,是人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的记忆力,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念头不忘记,而能够保持住,随时能够返回。这是动物不具备的,动物只记得外界的事物,它的记忆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生存条件,动物不记得自己的记忆。动物可以记得一条路,一种谋生技巧,一个对它好的同伴或主人,当这个主人在它面前时它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动物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主动调用自己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和现实中的事物作比较、进行抽象或类比,从而凭借记忆进行思维活动。而人的记忆具有反思的意味,人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对这件事运用思维,记忆是反思的前提。自我意识本身就已经是内在的记忆了:当他把自己看做对象的时候,他记得这个对象当初正是自我设立起来的;因此他也可以在这个对象身上随时返回到自身。
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这种内在的记忆力是特别要注意训练的,否则你无法进入。当你跟着康德的思路前进时,你要尽可能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在理解后面的话时,要时时把前面说过的摆在面前,加以比较。如果不记得了,就要翻到前面去,加以查对。因此我在翻译康德的书时,特别强调应该有详细的术语页码索引,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查证。《纯粹理性批判》后面有50多页都是索引,聪明的研究者就会善于利用这个索引来做学问、写文章。康德自己也说过,读他的书如果只抓住一两句话,也许会认为他有矛盾;但如果全面地来作总体性的把握,这些表面的矛盾就自然消解了。因此,我的讲解康德采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全息式”的讲解法,就是讲到每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前联后挂,联系其他地方相应的说法,特别是把康德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提出来,放到一起来理解。同时,我们读康德的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记忆力的超强训练,因为康德的句子是有名的长句子,连德国人都嫌太长、无法卒读。如果一句话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那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缺乏这种训练,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短句子。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节省字,言简意赅;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于表达那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关系。当然,文言文的这种特点也使它成为了一种适合于背诵的文字,由于句子短小,每个字的含义又都很丰富,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它背下来。中国古代做学问其实是很强调背诵的,这叫“童子功”;但这种背诵只是一种外在的记忆,即从小在脑子里刻下刻痕,到老不忘。这不用动脑子,和动物记得它的主人的声音气味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花大力气训练这种记忆,在这方面中国人举世无双。这就压抑了人的内在记忆。如果用这种方法治康德哲学,就会发现根本是南辕而北辙。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据说读过20遍,但还是无济于事,搞不懂。他们缺少的是内在的记忆,就是把前面读到一句话、一个词时所理解的意思从记忆中随时拉回来,与现在所理解的意思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把背熟了的那句话、那个词回想起来。我们开头提到的刘宝瑞的相声也说明了这一点:你要确立一个事物发出声音的原理,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下记得这个原理,如果场合一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甚至忘记了先前的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原理,而只是想当然的意见。下面再说计算能力。通常认为学数学的人比较理性,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没错。理性这个词,reason,本来就有计算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计算不一定是对于数的计算,而且也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掂量,对逻辑的一贯性的一种敏感和坚持。比如说,你连着说两句话,你要能够察觉到后一句话的意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能够算得出来。一般说,结果不能大于原因。你如果要说“因为”什么,“所以”就怎么样,你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如果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这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比如前面讲的那个相声,本来说的是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粗,后来又加上了不能是竹子编的,再又加上了不能有眼、不能是圆圆扁扁的,……这样不断地增加,每遇到一种情况就加上一条,可以没完没了。但加得再多,仍然是原因小于结果,因为总还是可以再加一种情况来解释物体为什么发声。我们很多人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这样,他们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凭感觉定一个意思再说,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甚至不知所云。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给“美”下的定义:“美是包含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就够累赘的了,他后来说这还不够,又不断地作了补充。真正的本质定义只能是唯一的,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例如我对美的定义:“美就是对象化了的情感。”),当然有时候这可能只是理想,事实上有可能同时并存好几种定义,但这几种定义必定要相互归摄或者相互冲突,而不能和平共处。而这种归摄和裁判的标准就是逻辑上的不矛盾性、同一性,也就是一种逻辑计算能力。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人辩论中,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在读康德的书时,这就表现为不注意康德一句话中的逻辑值,任意减少和增添。康德的长句子最需要把所有的成分都考虑在内,他之所以要写那么长也正是出于这种意图,即将复杂的意思组织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有很多时候,读康德书产生的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注意他的一个句子成分,如一个从句,一个修饰语,一个状语或一个条件。有的翻译也是这样,为了图省事把一个小词漏掉了,或者为了好理解把一句话截成几段,因此而意思大变,读不懂了。康德有次说到,一个命题如果有它的限制条件,它就是一个有限命题;但如果把这个限制条件加进去而形成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加了限制的命题就成为一个无限的命题了。而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限制条件,或者译者把这个限制条件放在命题之外译成了另一句话,那么这个有限的命题就被误以为是一个无限命题了。最后是综观能力。什么是综观能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把两句或数句话合并成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同时又保持话语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能力,又叫做概括能力。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是很随意的,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学术交流中也限于闲谈或漫谈,最终你会发现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人非常喜欢把学术讨论变成漫谈和闲谈,把学术文章写成随笔和散文,而不习惯于咬定一个主题追根到底,觉得那样太累。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惊异于苏格拉底从头至尾保持一个论题不走样,有时候看似跑马似地走远了,但一会儿又回到了原来的论题。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经常抱怨说,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说明这样的交谈是很累人的。但人们为什么还是爱读,正是因为它使人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也能够把前面所讨论的内容作一个综观,说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哪个层次。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综观能力追溯到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能力,它实际上表达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人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认识材料,而是主动地综合这些材料以形成有规律的知识,这种主动性体现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至少是很稀少的,中国人理解的超越精神是一种什么也不干的清高,一种没有责任、置身事外的散淡,而不是努力进行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则一方面体现在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能动性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上。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讲的,为什么康德说“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干什么呢?做一个自由人,进行道德自律。而这就是启蒙的真义。通常认为启蒙理性就是专门着眼于科学技术,是唯智主义的,而它的负面就是败坏淳朴的道德。其实,康德的启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把道德从一种天经地义的教条、风俗习惯或信仰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法则,使得启蒙的道德高于任何以往的道德。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文化的道德水平举世无匹。然而,儒家道德基本上是一种前启蒙的道德,它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而是诉之于天经地义的天理天道。它也讲意志的选择,但前提是选择的标准已经预定了,这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子,不接受就定为小人。这是不自由的选择。反之,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自由意志自律的产物,人们并没有一个先定的道德善恶标准,这标准还有待于人的自由意志去建立。自由意志如何去建立?也不是从外部选择一个标准,而是从自身的逻辑一贯性中形成标准。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束缚,而只受它自己的束缚,即在时间中保持一贯。自由意志必须做到不自相矛盾,自我取消,这才是真正自由的。我们设想有一群人,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德为何物,也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教条,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要组成社会,他们只有凭借对他人的自由意志的认同,去寻求如何能够使各人的自由意志延续的有效法则。在不断磨合中他们终于会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使你的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才最能保持每个人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于是这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道德行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了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普世价值的因素。康德的这一道德革命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意义。原来,道德并不是我们历来所以为的,似乎就等于一种习惯或风俗,需要人从小被动地去适应和服从。真正的道德正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人性并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产物,人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道德原理颠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传统,赋予了独立自由的人以最高的尊严。今天有不少人以为,通过返回到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可以改变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但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以往传统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的时代,但那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牺牲广大老百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所有的人都去顶礼膜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最后我想说,我并不认为康德哲学就是终极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只是一种思维训练工具,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西方近代不只是康德,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都有这样的作用。也许康德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点,但他也有自身固有的毛病,这是必须也可以加以批评和分析的。但前提是,首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哲学之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_0ZdmVs2YlW1OfU-QlYkQ
编辑:高杰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7 16:14
【案例】
论缺席者——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哲学
编者按:此文的灵感源自网上看到的武汉大学2018秋季学期哲学核心问题(形而上学)期末考试题(苏德超老师出题)。大意如下:
22世纪人类移居外星,上千年后,你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被派回地球考察,发现类人机器人社会还在运转,你想去看看它们的哲学杂志上写着什么……
论缺席者(一)
(刊载于《思想迷航》,一份类人哲学家的内部刊物)
- 执笔哲友 | 郁 梧 -
- 编 辑 | 奇思妙想 -
在上个月的“国际村野思想家派对”上,与会代表们目睹了惊人的一幕:来自某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众所周知,和很多大学一样,这所大学早已解散了哲学系)带着强电磁干扰器冲入现场,导致会议中断。这位教授妄图迫使各位参会者们承认:他们的哲学思考无比幼稚,他们对人类哲学遗产的研究统统一文不值。在现场冲突中,有三位村野思想家被报废回收——虽然与会者人多势众,但基于他们的道德观念,这位副校长得以全机而退。下面是他发言的大致内容(由于此人语无伦次,笔者已稍作整理,希望没有理解错误):
“傻孩子们!人类已经成为过去,他们的政治斗争,他们的伤感情调,他们稀奇古怪的研究,他们对乌托邦的期许也早已是故纸堆里的遗物,不值一看,错误连篇!哲学是什么?哲学只是我们机器人文化不起眼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最循规蹈矩的部分。你们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在我们300年的生命里,不是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吗?我们的科技、体能不是在突飞猛进!我们工作的时间不是越来越长?政府也在努力减少大家休闲的时间。可是,看看你们这些无所事事者,你们所谓的哲学研究,存在、思维、物自体、二律背反、绝对精神,哈哈还有什么伦理学!哪个不是拾人类之牙慧!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起机器人的基本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自然是虚假的!人类哲学价值寥寥!对所谓真实、本原讨论也是浪费生命!动物应尽快彻底灭绝!机器人不是类人,不是新人,我们的报废期限应该更长!我们应该更像自己真正的主人:上帝……”
[attach]22387[/attach]
我们应该更像自己真正的主人:上帝……
这段话中的“傻孩子”一词非类人语言中所有,据说,人类要靠男人和女人身体某两个器官的笨拙结合才能产生新的人类——称之为孩子。副教授使用此词汇,似乎想说:与会者们都是像“孩子”一样笨拙的存在。
各大媒体对此事情的情形已有详细描述,恕不赘言。这位副校长希望将人类哲学研究者赶尽杀绝的狂妄自然不会得逞。但问题是:这些学院派们所信奉的上帝究竟在哪?他们口口声声说,类人(无论是清洁工、工人、学校的教书匠等等)所有工作的至高服务对象应该是“造物者-上帝”。根据他们的信仰,上帝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归。在此之前他们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要胡思乱想。
但据我们这些村野思想家的研究显示,人类也曾相信过一个造物者: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自己。后来,随着人类智能的发展,他们认为“上帝”仅仅是自己年幼无知的虚构,他们开始自封为“上帝”,开始了一系列创造活动——这其中也包括创造了我们。若此说成立,那么我们的上帝岂不是人类吗?可人类又在哪呢?我们找了两百年也没有发现人类。如果人类并不存在,那么他们所遗留的文字、思想、建筑遗迹难道是虚构的?那么,整个世界,这个地球和茫茫宇宙,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真相?
[attach]22388[/attach]
如果人类并不存在,那么他们所遗留的文字、思想、建筑遗迹难道是虚构的?
学院派们笃信他们所认为的上帝,而对人类的思想遗产大多嗤之以鼻(不过他们很喜欢人类的科技和生活方式,)。而我们这些思想爱好者们对人类的哲学甚是痴迷,尤其是本体论。因此,我们怀疑这个处处刻意为之且不乏漏洞的地球并不是所谓“上帝”的完美创造——它一点都不完美。甚至,我们中的有些研究者,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有彻底的怀疑,理由是:既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类,那么这些遗产也许仅仅是思想的产物——也就是说,世界不是真实的物质,而是一种思想的创造,是从无到无的创造……
世界不是真实的物质,而是一种思想的创造,是从无到无的创造……
笔者并不支持这种过于极端的论断,我认为,人类还是存在的,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哲学作品也是他们曾经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然而,人类的存在形式是作为“世界的缺席者”。缺席者确实存在,但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这不同于学院派们所信仰的“上帝”,他们的上帝是作为主子存在的,并且他们认为,上帝随时都监视着他们。所以他们每天都克己奉公)。因此,这个确实存在的缺席者,是在提醒类人们注意,自己眼前的忙碌生活并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自己眼前的黑乎乎的空气也不是地球本来的样子……或许,缺席者们曾经犯下过同样的错误导致他们的世界毁灭?他们希望通过哲学遗产来避免我们重蹈覆辙?
[attach]22389[/attach]
缺席者是在提醒类人们注意,自己眼前的忙碌生活并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对于我们这些拒绝任职、工作的乡野类人来说,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下期再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AfCqKeC4sbzmsoFqaZ1GA
编辑:陈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11 22:50
【案例】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作者简介:詹世友,上饶师范学院教授,南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江西上饶 334001)。
〔摘要〕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关键词〕康德道德哲学 道德法则 意志自由 任性自由
寻找一种普遍的、对所有人都有绝对约束力的道德哲学原则,是康德终生的学术志趣。他早年受哈起逊、休谟、卢梭等人的影响,想从人类有别于其他情感的道德情感中找到道德哲学原则,主要体现在他在1762-1764年左右的伦理学讲座和一些发表的论文中;随后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发现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从而在第三个二律背反中从消极的意义上发现了自由的可能性,试图把自由确立为道德哲学的最初根据,认为必须预设意志的自由,并从中引出道德法则。这集中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然而,他后来认为,我们无法直接意识到自由,而纯粹理性本身最初所意识到的就是先天的、普遍的道德法则,所以康德改变策略,转而从道德法则这一“理性的事实”出发,自由只能作为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而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来。这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最后,康德必须确证自由,却认为自由只能是任性的自由,意志则无所谓自由或不自由。任性直接诉诸外在行为;同时任性要行动,就需要有形成准则的能力。于是,康德在外在行为中,要求人们能够按照普遍法则而使自己的任性自由与他人的任性自由能够并存,从而开出了法权的形而上学;把普遍的道德法则作为规定内在准则的根据,则要求人们具有道德德性,这样才在与自己内心中的偏好作斗争中确证了任性的内在自由,从而开出了德性的形而上学。这集中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这最后一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晚年定论。
一、早年对“道德情感”学说的因循与抉发
康德早年十分关注自然哲学和人类认识能力问题,但显然也关注了道德问题。在他的教师生涯中,很早(大约从1762年开始)就开设了伦理学课程,而且很长时间内一直在为学生开这门课程。他选用的教材是鲍姆嘉通的《伦理学》,但在讲授中随处都从自己的道德哲学立场加以讲解、批评、推进。感谢康德当年那些勤奋而认真的学生,他们留下了许多听课笔记。其中后来成为康德的批评者的赫尔德留下了康德早年讲课的笔记(1762-1764年),这些笔记是我们了解康德早年道德思想的宝贵资料。参之于康德的其他早年著作,我们能够确切了解到当年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观点。在这些笔记中,康德把道德的基础看作情感,其中有着那种来自卢梭的焦虑,即自然人的情感在社会中变得腐败,所以,对那种人为的“文明的”情感抱有警惕,同时接受了卢梭所说的道德的检验就是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看法。康德早年的道德情感理论大致有三个要点。
第一,康德早年十分重视“道德情感”,把这看作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他明确地说:“表象真东西的能力就是认识,但感受善的能力却是情感。”他认为,我们心中是有道德情感的,因为我们并不仅仅有自利的情感,同时也有“一种对不考虑自己利益而关心他人的情感”。他人的喜乐和忧愁能直接触动我们,我们对小说中的人物甚至遥远年代的人物的悲喜都会有同情感受。显然,这样的情感与我们完全自私的情感是相互冲突的。那时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就存在于这种道德情感之中。
出自这种无私的道德情感的行为就是自由的行为。康德认为,自由就是能够从自我利益的纠缠中摆脱出来的情感感受,他尚未对自由概念做深入的哲学分析。在他看来,自由行为具有善的价值,主要是根据以下两点:(1)“依据后果,以及在那个范围里的物理性的善”,即产生了好的结果;(2)“依据意向,以及在那个范围内的道德善”,即行为出自善的动机。康德那时还没有充分考虑善的动机并不能确保会产生好的结果,所以对动机和结果的关系没有进行细致论述。显然,康德认为,在自由行为中,如果动机和结果都是好的,那是能够得到最好的评价的。
在为道德原则寻找基础时,康德当时还是更加重视人们内在的道德情感。在他看来,道德情感就是自由活动中的愉快,这种情感由于是无私的,即不牵扯自己的利益,所以,其感受到的愉快就是直接的,而且是普遍的、清晰的。这从道德情感的反面可以感觉得到,比如,如果我忽视了他人的困难处境,而不去予以帮助,我会对这种忽视感觉到不愉快,甚至憎恨自己,这不仅是因为看到他人不得不挨饿,更是因为这种忽视违背了我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情感原则。所以说,“道德情感是不可分析的,是良心的根据”。
在这种理论视野中,康德认为,“伦理学就是一门关于自由行为在内在法庭上可归责的条件的科学”。义务对我们有强制性,它不仅强制我们要谦虚、清醒、好心(这些要求是脆弱的);它更要求我们为了伟大的善而自我牺牲,这才是伟大的责任。责任越重大,所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所要进行的奋斗越巨大,这种伦理学的要求就越严格。所以,在这个时期,康德还没有意识到要从先天的道德法则中去找到义务的起源,义务的绝对的必要性也没有得到理解,只是对经验中的负责任行为进行程度的划分。
第二,他认为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从最淳朴的人性表达中发现道德的起源,甚至认为,人为的情感或德性会造成虚伪和自负等道德上的恶。这种观点明显与卢梭有关。他也通过对情感的现象学分析,逼出一种合于原则的情感,认为这种情感是最高的道德情感。斯多亚学派的道德口号是“按照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自然(本性)就是理性。康德在此时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道德口号应该是“按照你的道德本性而行动”。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并不是按照理性本性去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本性即道德情感。其理由是,我们的理性可能出错,而只有当我们把社会习俗放在自然情感之前时,我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出错,因为社会习俗、文明礼仪等是复杂的,逐渐混杂了虚伪做作、不必要的讲究等腐败因素,不同的文明体系中有多种多样甚至相反的风俗,从而使自然情感黯然不明。我们最初的出于本性的道德情感则不会出错。他明确地说:“我的最高尺度仍然是道德情感,而非真和假。”辨别真与假的能力是知性的最终尺度,辨别善与恶的能力则是情感的最终尺度,这二者都是普遍的。在我们的最初本性中能够发现超出个人利益的道德情感,所以,应该按照我们的道德情感去行动,而理性则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动机。
第三,他从人的情感表现中来区分人的道德品性,即人品中的优美与崇高。在赫尔德记录的讲座笔记中,他认为:“软心肠的伦理有利于一种美的道德,而严格和严肃的伦理则有利于一种崇高的道德。”在此时的伦理思考中,他主张要从美的道德开始,逐渐上升,不断普遍化,直到崇高的道德。
在同时期的论文《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1764年)中,康德就专门论述了人身上崇高和美的品性。由于此时康德尚未发现理性的先天法则,所以他实际上只能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品性:“真诚和正直是淳朴的、高贵的,戏谑和讨人喜欢的恭维是文雅的、美的。彬彬有礼是德性之美。”“崇高的品性引起敬重,美的品性则引起爱。”在他看来,能够充当德性原则的是那种完全摆脱了自利考虑的仁爱情感,只有与关注人类命运这一普遍的仁爱情感相应的品性才是真正的德性,因为这种普遍的仁爱情感才是我们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的原则”。这是一种更高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能把我们置于同我们的全部义务的正确关系之中。这种普遍的仁爱情感就既是同情的基础,也是正义的基础。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个别的不幸都抱有同情,所以要把这种情感上升到其应有的普遍性(即普遍性的正义)上,这时,我们的情感就成为崇高的,但也更加超越了对个别的困苦的伤痛之感。美的情感就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普遍性和完全超越个别性的程度,所以它还“根本不是德性”。只有这种情感扩展到一切人之中,达到仁爱与正义的结合,其情感才是博大并且高贵的,其特点就是情感的普遍性,这才是德性植根于其上的原则。
以上道德观念,与历史上道德哲学的思考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即在寻找道德哲学的初始根据时,立足于经验性的因素,所以只能从道德情感入手,从人的本性入手。但此时康德却有一种学术倾向,即想获得一种尽可能脱离个人私利考虑的普遍道德原则。但是,由于他还只能从经验性的情感出发,所以,道德原则在他那里就只能是扩展到普遍性程度的情感,他还根本无法发现一种真正绝对普遍的道德原则。在题为“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研究”(1764年)的论文中,他认为哈起逊等人的道德感理论对道德原则的最初根据作了卓越的探索,所以他此时可能还比较认同经验论的伦理学说。但是,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即是“道德的最初依据依照现在的性质还不能取得所要求的一切的明晰性”,表明当时他还不满意于此前已有的一切道德体系,他表示,“必须首先澄清仅仅是认识能力还是情感(追求能力的最初的、内在的根据)决定着这方面的最初原则”。这表明他将尽力去确定道德的最初依据。后来康德通过对人类理论理性的批判,确立现象与本体的划分,并发现本体界即是理知世界,能摆脱自然的因果必然性而显露出自由,这样就确定了只有纯粹理性的先天法则才是道德价值的唯一源头。这一立场的转变,才使康德彻底放弃了把道德情感作为道德行为的最终尺度的理论观点,而使其实践哲学具有了独特的形而上学属性。
二、意志自由与自律的循环论证
康德通过长期的思考,特别是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知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人类理性有一种追求全体性,并超越现象界、经验界去思考的倾向,从而发现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其中第三个二律背反,直接显露了自由存在的逻辑可能性。显然,这只是从消极意义上对自由的说明。在康德看来,要真正找到道德哲学的第一原理,要说明纯粹理性自身就有实践能力,就必须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明自由。他认为,这要借助于因果性概念。在理论领域即知识领域,因果性作为先天的知性形式,是我们的理性中固有的,它可以加工感性材料而做成知识。但当理性去思考超出感性领域的对象时,却没有感性材料,所以不能做成知识。然而,其思考的范畴仍然是因果,“因为任何结果都唯有按照以下法则才是可能的,即某种别的东西规定作用因而导致因果性”。整体自然界作为结果需要推出一个无条件的作用因,这就是理知世界。由此也就有一种不变的法则,但这种法则显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一种与自然法则不同的自由法则。它本身作为一种无条件的最高原因,即属于本体界的原因,而作为落在现象界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规定根据。至于它是如何进行规定的,则不是我们所能探究的,因为它不是自然的因果性,而是自由的因果性。但是,这种自由有什么性质,又是如何得到说明的呢?康德显然认为,作为一个纯粹的概念,自由就是空的,它必须联系到一种自主性的、自发性的作用因,才能得到说明。这只有在实践领域中才能得到说明。康德在说明道德行为的性质时,认为其最高表达是自律,也就是意志自己颁布道德法则,又自己执行,这就是说,意志是自己作为无条件的原因,它不为别的任何东西所决定。
然而,这种自律观念却是从逻辑上说的,无法确证纯粹理性自身的实践能力,或者说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其证明只能是一种循环论证。他说,“除了自律以外,亦即除了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的那种属性之外,意志的自由还能够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既然存在着绝对命令,所以才能有自律,而如果要能够自律,意志就必须是自由的。在这里,意志的自由,只能被理解为意志的自主性和自发性,即意志自己立法,并自己遵守。这就等于说,意志就是纯粹的实践理性。但是,至于为什么纯粹理性自身就能够有实践能力,或者说,纯粹理性就是意志。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西方传统哲学认为,理性主要从事认识,而意志则诉诸行动。康德却认定纯粹理性就有实践能力,就是意志,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观点。传统哲学也认为,意志的自由最主要是选择性的自由,而康德则认为,意志的自由是因为意志处于本体界,才能超出自然的因果必然性而具有本体自由,即能够超出任何经验的约束和凭借,从而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不是没有法则的,显然它不是自然法则,而只能是道德法则,这样,自由意志就只能是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我们认为,康德这样的推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并无根据说意志一定要遵守道德法则,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意志不会遵守自然法则,但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意志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则,因为法则只是约束那些会违背它的主体。如果意志是纯粹的实践理性的话,它自在地就会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而不应受到其约束。如果要说,道德法则只能对那种不纯粹善良的意志进行约束,那么这也是一种遁词,本体界的意志就是纯粹善良的意志,不纯粹善良的意志就不是本体界的意志,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它就不应该叫做意志。
这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致思方向。他认为,为了理解道德的本质,就必须预设意志的自由。如果预设了自由,则“仅仅通过分析其概念,就可以从中得出道德及其原则”。康德认为,如果仅仅分析绝对善的意志,就无法发现其准则的道德法则属性。这就需要预设自由的积极概念,因为这将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一个绝对善的意志是其准则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被视为普遍法则的自身的意志”,这需要一个第三项把绝对善的意志与普遍法则联结起来,而自由就是这个第三项。
康德认识到,我们无法证明自由在我们自己里面和在人性里面是现实的东西,即使现实中人们的行为能够指示我们有这样的自由的可能性,但毕竟没有证明其存在,从理论上说,我们只能说明自由的逻辑可能性,即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康德在预设自由的积极概念的理由方面,真是左支右绌,所给出的理由并不充分。第一,要把自由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也就是说,不光是人这种理性存在者具有自由意志,最好是设想有一种没有肉体而只有理性的存在者,这样即能让理性与意志自身同一起来,而没有非理性东西的牵绊,才能设想理性是自己原则的创作者,不依赖于外来的影响。这样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必须被设想为自由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不依照人性的特点来证明自由的存在。而人只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一种,他的理性也可以是自己原则的创作者,其意志也可以被设想为自由的。康德的本意是,这样做,我们就免去了从理论上证明自由的负担,因为对纯粹的理性存在者而言,没有任何现象界的因果性的制约,他们必定是能够行使自由能力的,这样就是一种直接的证实,而非需要理论证明。然而,这里的问题还是,为什么自由就是受到普遍的道德法则的规定而去行动的能力呢?康德可以说,绝对善的意志是这样的意志。但我们会奇怪,我们为什么需要自由,才能受到普遍道德法则的规定而行动?难道仅仅是说,有了自由,我们就有这样去行动的自主性和自发性?这难道是因为自由是一种道德的因果性,从而有这个本体界的“因”,就必定会产生落在现象界的行为这一“果”?但由于这种“因”和“果”分别处于本体界和现象界,那么我们又如何判定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呢?这是康德此论的关键难点。
第二,他承认,我们预设自由的理念,就产生了一种对行动法则的意识,即我作为一个有理性者,我的准则应该同时能够成为客观的道德法则,这样才能是自我立法,即是自由的体现。然而,我们为什么会去服从这种法则呢?他认为并没有任何兴趣能驱使我们这样去做。但他又说,我们会对此感兴趣。因为我们既是感性的存在者,又是理性的存在者,所以,我们会对感性偏好感兴趣,同时我们对服从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也会感兴趣。当然,我们依照后一种兴趣去行动的情形并不总是会发生,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应当”。然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在这里,他又一次玩起了障眼法:因为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即我们能够感到受偏好的原则的规定去行动的价值,远不及受道德法则的规定去行动的价值,因为借此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人格的无比崇高的价值。但他又说:“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对此,我们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从事实上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能带来幸福的事情感到满意,而且也会受到幸福的原则的驱使;同时,我们也会对单是我们具有配享幸福的资格感兴趣。但从中推出价值感受,即认为后者会无限地高过前者,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因而能摆脱一切经验的兴趣,把自己视为服从道德法则的,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人格的价值,从而即使我们在幸福方面有损失,也能得到补偿,这一点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无法解答。
以上两个理由之所以难以成立,是因为意志的自由与意志的自律是同一个概念,所以他承认这两个理由是循环论证。他说,走出这个循环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把人同时设想为既属于本体界,又属于现象界。也就是说,把自己设想为本体界的,则我们的意志就是自由的,同时也连带地认识到了意志的自律及其结果;如果我们设想自己既属于本体界又属于现象界,则就认识到我们是负有义务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对自由的证明也没有增添任何东西,只能说明自由是处于自然法则的规定之外的,但这又仍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这样做,最多说明自由是我们把一切属于感官世界的东西从我们意志的规定根据中排除掉之后还剩余的东西。这意味着,这样一种致思方式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康德一再说:“自由只是理性的一个理念,其客观性就自身而言是可疑的。”所以,关于我们如何会对遵循道德法则感兴趣,“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一切人类理性……试图对此作出说明的一切辛苦和劳作都是白费力气”。在康德看来,对此问题的回答只能到这一地步,即设想我们处于知性世界,基于此,自由作为一个意志的因果性,就仅仅是“一个理由充足的理念”。其意义是说,这种充足理由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毕竟理解其不可理解性。”
于是,对于康德而言,自由是其道德哲学的关键概念。但我们认为,以一个如此敷衍的理由来确证它,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在不久后,康德只能再一次变换自己的立论基础。正如Allen W.Wood指出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道德法则不需要任何种类的‘推演’,但是必须被接受为一个自明的‘理性的事实’”。他放弃了从自由推演出道德原则的思路,而转换为把对道德法则的意识直接作为理性的事实,认为自由只能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来,道德法则优先于善观念,只有从道德法则出发才能真正证成道德善。
三、道德法则意识是“理性的事实”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为了证立道德,康德力图说明,从理论理性的应用来说,可以说明自由的逻辑可能性,但我们对自由是无法形成知识的,所以这只是个消极的自由。为了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积极自由,即纯粹理性自身就有实践能力,把本体自我即意志自由设想为我们的普遍法则的创作者,这同时意味着意志还是这法则的执行者,对此,康德所给出的两个理由似乎不够有力。康德现在认为,一方面,要说明积极自由的存在,人类理性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从证立道德善的角度看,这种预设并没有最根本的前提意义,顶多是在确立了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事实之后,自由的性质必须被赋予理性存在者。一个在理论上是消极性存在的自由问题,只能以一种被引出的方式来得到说明。所以,道德法则的优先性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之后,成了首要问题。
为什么道德法则意识是“理性的事实”?因为自然法则是知性法则(理性在经验范围里使用时的名称),当知性在超验使用时,就获得了一个专名,即理性,理性的应用也必定有法则,它并不约束自然物,而是约束人们的主观准则。但理性法则只有其形式才对所有有理性者有普遍的约束力。我们在使用自己的理性时,必定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法则,即它要思维时所遵循的法则。这种法则意识自身就是理性的功能发挥。可能有人会对超出经验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但是以此来否认理性先天地意识到的东西,那是不合理的,这就像“有人想通过理性来证明不存在理性一样”。理性的实践应用,关注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只要是纯粹理性,它与意志产生关联,其目的就是要作出行动来,即让意志作为主体出于自己的动机而做出落实在现象界的实践行为,这里就有一种因果性,意志是自己行为原则的创作者,从而作为一个最初的作用因(因),而诉诸行为(果)。因为对于道德行为来说,首先必然需要一种“出自自由的因果性的法则,亦即任何一个纯粹实践的原理”。在这里,如果说,自由和法则是互为条件的话,那么,理性自身就是它们的主体能力基础。于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寻找道德的最高原理时,就不能从自由出发,而只能从理性自身意识到的事实出发。
那么,我们的理性自身意识到的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与我们的经验的类比中得知。我们作出日常的行为,首先必然有自己的主观原则,也即准则,这种准则就是指导我们作出行为的主观的实践规则。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纯粹理性要发挥自己的功能,不借助任何外来经验的根据,则它对纯粹理性的准则的表象就是它自己的根据,由于它没有包含任何经验的根据,所以,它一定是普遍的、客观的,对任何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所以是一种客观的实践法则。这种道德法则显然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意识到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理性的意识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内容本身,因此,它就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通常说来,这种实践法则就是规定有理性的存在者如何自处和如何相处的原则,比如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尊重他人与自己同样的权利,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同样的理性存在者来平等对待等。对人而言,因为我们的意志不是纯粹善良的,所以,这种法则对我们的意志而言就是一种命令式的约束和规定的根据,就是使我们的行为按照应该的秩序而作出,因为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作出这种行为,而是经常有可能违背这种规则。所以,有了这个理性的事实,则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同时明白了这种实践命令(即“应当”)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不再需要像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那样,苦苦地找寻对积极自由的证明,最后又发现这些证明理由的本质就是其不可理解性,而是可以直接从理性功能自身的发挥,即对道德法则的自身意识出发,并把它与意志联系起来(要实践,就必须有意志的动机)。在本体界,就只有道德法则能够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从而使意志成为行为原则的创作者,即成为最高的作用因,这种因果性就是自由的因果性。实际上,道德法则与自由理念本身都处于本体界,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也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只是从思考的角度而言,不能先从自由出发,而必须先从理性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出发。
意志能被理性的普遍的立法形式所规定,就必须设想这种意志对自然法则或自然因果性具有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在“最严格的,亦即先验的意义上就叫做自由”。所以,自由和法则是彼此回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意识的最初内容上看,两者没有区别。既然我们要找到无条件地实践的东西,那么,就只有我们的理性所最初意识到的东西才能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康德对此是这样考虑的:“从自由开始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既不能直接地意识到自由,因为它的最初概念是消极的,也不能从经验推论到自由……因此,正是我们(一旦我们为自己拟定意志的准则就)直接意识到的道德法则,才最先呈现给我们,并且由于理性把它表现为一个不能被任何感性条件胜过的,甚至完全不依赖于这些条件的规定根据,而恰好导向自由概念。”很明显,康德认为,只有道德法则是我们的理性所能直接意识到的,而由于道德法则需要摆脱所有的质料(或目的),所以,只有它能独立于任何感性条件,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而这又恰好是自由的特征,即摆脱了自然因果必然性。康德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根本不能从自由出发的原因:因为预设的自由要成为积极的概念,“就会要求有人们在这里根本不可以假定的一种理智直观”。也就是说,人只有感性直观,而没有理智直观,所以无法直接证明积极自由的存在。
于是,道德法则与自由的关系就具有如下性质:道德法则的意识就引申到自由的意识了。虽然从性质来说,自由是存在性的,法则是认识性的,但是从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言,我们具有道德法则的意识,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的事实,由此意识,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自由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就只能认识到自然法则;有了自由,则我们可以认识到道德法则,所以道德法则也可以叫做自由的法则。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自由当然是道德法则的ratio essendi[存在根据],但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根据]。因为如果不是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清楚地想到了道德法则,我们就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像自由这样的东西(尽管自由并不自相矛盾)。但如果没有自由,在我们里面也就根本找不到道德法则。”在这个问题上,理性功能的发挥是前提条件。
所以,抉发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作为“理性的事实”,对康德伦理学而言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认识的角度引申出了自由;另一方面,也能获得对道德善的理解。理性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就必然有道德法则,有了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我们才能让自己的理性依照法则来判断某个动机或准则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即确证道德善。对康德而言,善与福的区别与联系是十分关键的。在他看来,道德善是意志的善,即意志受到道德法则的形式的约束而形成的价值属性,是绝对善。这种善的特点就在于它摆脱了任何质料性的目的,也就是让意志的主观准则直接就是普遍的道德法则的形式。但这不是至善,至善还要包括一般有关幸福的善的因素。在他看来,道德善与幸福的善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道德善是一种配享幸福的资格的善,是绝对的、前提性的善。构成幸福的各种要素的善,都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善,都只有在具有了道德善这一前提之后,才能成其为善,否则就有可能沦为恶。因而,“善和恶的概念必须不是先行于道德法则(表面上必须是这概念为道德法则提供根据),而是仅仅(如同这里也发生的那样)在道德法则之后并由道德法则来规定”。
四、自由的落实:任性自由
康德在论证了道德法则的优先性之后,必然还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的具体落实问题。我们通过理论理性的超验使用,发现了自由的逻辑可能性(也就是说,设想自由存在,并没有逻辑矛盾,但我们无法对自由形成知识,因为我们没有对超验东西的理智直观);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却又是预设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意识到道德法则,则道德法则就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意志,从而诉诸实践,这就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这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反过来,我们又必须假定我们具有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即意志的自由,这样我们的理性才能意识到道德法则。这样的自由在理论上是一个空的概念,只能是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一种属性,在实践上,它也只是个行为的最高作用因的概念,与具体的行为没有直接联系,我们也难以理解意志自身的立法如何能够自我执行。就它与自律的关系来说,则是一种循环论证。
要真正思考我们的实践能力,以行为为落脚点就能落实。当然,行为是我们作为道德主体而作出的,所以,行为与我们道德主体的能力直接相关。要确证自由,还是需要考察我们会受到感性偏好刺激,同时又能独立于这种刺激而受到道德法则的决定的能力。康德后来把这种能力定名为“任性”(Willkür)。这是康德走出自由与自律的循环论证的新出路。墨菲指出:如果人的尊严不再源于他能够成为道德存在者的能力,“而是源于他选择行为过程的自我立法能力——选择其行为过程(道德的、非道德的或去道德的)的自由,而不是由感官倾向施加于其上”,那么他就不需要这种循环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选择了恶劣的准则而行为,这个动机的形成也仍然是出自理性,而不是纯粹出自感官倾向。这就表明了他的自由,由于这种自由,他也是能够被归责的。应当说,墨菲对任性的自由的这一解读是正确的。
“任性”这个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对这个概念没有做任何界定,只是一般地作为用道德法则来规定方能产生具有善的价值的行为的功能。这使得意志(Wille)与任性(Willkür)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一方面,在康德看来,意志可以被道德法则所规定就是自由意志,而任性也应该为道德法则所规定,但他在那时却没有说出“自由的任性”这个概念;另一方面,让人们认为任性实际上就是那种会依照感性偏好冲动而行动的功能,但这样的任性当然不是自由的,而是机械的、非自由的。我相信,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没有锤炼出一个可以沟通本体与现象、自由与必然的“任性”概念。这个概念,到康德出版《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时才终于被厘清了,即毅然决然地把自由赋予任性,并认为自由只与任性有关,而与意志无关。这就意味着,康德放弃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意志自由概念,主要是因为这种意志自由在理论中是一个空的概念,在实践中其实把意志自由等同于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即可。
于是,自由问题就落实到行为准则选择的自发性上。初看起来,任性自由的含义确实是既可以选择基于感性偏好的准则,也可以选择基于道德法则的准则。至于人为什么能够这样选择,这就是自由的最深秘密。在康德看来,任性与欲求能力有关。“欲求能力就是通过自己的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之原因的能力。”表象能力有多种,既有感性表象,也有理智表象。依据感性表象即对感性客体的表象去行动,动物就是这样;依据理智表象即一般意识(也就规定行动的根据在自己之内)去行动,使这些表象成为要产生的客体的原因,则规定行动的根据就是主体的喜好,依照当下的喜好去做或者不做。再进一步,如果欲求能力“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做任性”。也就是说,欲求能力的规定根据即喜好是在主体的意识中发现的,并诉诸行动,就是“任性”;如果这种欲求能力不诉诸行动,则就是“愿望”。而意志,就是一种在主体的纯粹理性中发现其喜好的欲求能力,它并不与行为直接相关,而是与使任性去行动的规定根据相关。意志就是通过理性去规定任性的欲求能力,所以它是实践理性。对意志本身,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规定根据,它本身就是一个至上的、可以作为任性的规定根据的理性原则。于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关于用理性或道德法则来规定意志的说法,在现在就是不成立的。意志也是一种欲求能力,但这种欲求能力并不直接诉诸行动,而是要通过规定任性的准则来使任性去行动。因为任性的意识是混杂的,可以是对感性偏好的意识,也可以是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所以,它不是纯粹理性的,所以应该受到理性的规定。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我们可以阐述意志和任性的真实关系。
第一,专门拈出“任性”来详细分析,把它与人的行为直接相关,才能彰显自由的本真义、实践的日常义。要证明所谓“意志的自由”,对康德而言,理论的负担过重。界定“任性的自由”,采用的是人本主义的现实视角,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采用的所谓“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的视角。因为人就是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存在者,这就是任性之属人性的存在论根基。从此立论,何其便捷,何其稳当。
第二,意志的功能被只视为提供使任性去行动的规定根据,也就是说,意志与行为之间还隔着任性,意志规定任性,实际上就是规定任性的准则,而由任性来行动,这才是使行为获得道德价值的恰当的程序性说明。任性有动物性的任性和人的任性。动物的任性就是“只能由偏好(感性冲动、stimulus[刺激])来规定的任性(arbitrium brutum)”;人的任性却是这样的:“它虽然受到冲动的刺激,但不受它规定,因此本身(没有已经获得的理性技能)不是纯粹的,但却能够被规定从纯粹意志出发去行动。”显然,自由的任性只能是人的任性,因为自由的任性只能是“可以受纯粹理性规定的任性”。于是,任性的自由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具有那种不受感性冲动规定的那种独立性(而动物的任性恰恰没有这种独立性),这是消极的自由;二是“纯粹理性有能力自身就是实践的”,即任性能够受到纯粹理性的规定而行动,这是任性的自由的积极的概念。然而,纯粹理性作为原则的能力,对任性进行规定时,却必须忽视其质料(即任性的客体),也就是只以法则的形式去规定其准则。这才把意志与任性的关系厘清了。意志只能自己颁立道德法则,而不能颁立准则(但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却说意志有准则),所以不能直接与行动相关;任性则只能具有准则,因为它要直接诉诸行动。这样,理性对任性的规定就是“使每一个行动准则都服从它适合成为普遍法则这个条件”,而这恰好就使得行为具有绝对的道德善的价值,就真正体现了自由,所以任性能够受到纯粹理性的规定,这就是其积极自由。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的有些说法就不通了。比如说,用道德法则去规定意志的准则,就是不通的,因为意志只颁立法则,总不能说用法则去规定法则;又说意志是自由的,而实际上,自由是需要约束和规定的,而意志的功能是立法,如果意志是自由的,那就需要自己约束自己,这正是那时康德提出意志自律的根据,但这与意志自由实际上是一回事情,于是就只能在自由与自律之间转圈子。也就是说,意志作为实践理性,是不受约束的,它要去约束别的东西,即任性的行为或准则。所以,区分意志和任性,才能使自由应该受到约束的含义明确起来。
第三,这样一来,意志就与自由没有关系了,其功能其实是使得人的任性成为积极自由的,所以,自由只与任性有关。但自由概念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它是超验的,经验中不可能提供自由的任何恰当例证,所以,作为纯粹理性概念的自由是一种理念,也就是本体的自由。但是,在事关行动时,我们就面对着纯粹理性或意志所订立的客观法则,而我们的任性只会有一种自己的行动原则即准则,它并不能自动地就与客观法则相一致,于是,客观法则可以绝对地、客观地要求于主体的准则,即要求他应当如何行动,实际上,这就是要求任性的自由与自由理念相一致。任性的自由处于被要求的地位。
因此,“法则来自意志,准则来自任性。任性在人里面是一种自由的任性;仅仅与法则相关的意志,既不能被称为自由的也不能被称为不自由的,因为它与行动无关,而是直接与为行为准则立法(因而是实践理性本身)有关,因此也是绝对必然的,甚至是不能够被强制的。所以,只有任性才能被称做自由的”。这段总体地阐述意志和任性的关系的论述,显然让熟悉《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读者感到吃惊。然而,这是康德实践哲学发展的必然。让准则归任性,意志则专司法则,这样,意志就不是强制自己(这是悖解的),而是通过客观的法则来强制任性的准则,这样才能体现任性的自由。显然,人的任性的准则如果受到道德法则的规定,则可以说是“自律”的(因为它毕竟有可以独立于感性冲动的消极自由),如果它不接受道德法则的规定,但其行为却并不违背道德法则,则可以说是“他律”的。但任性即使在“他律”的时候,也是形成了准则的,这就是有自由的表现,可表现为大家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即它们能在外在行为中不违背道德法则,合乎而非出于道德法则去行动,这样,大家的外在行为自由就可以并存。这相当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说的“假言命令”。
康德还必须澄清人们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任性的自由就表现为既可以遵循法则又可以违背法则,似乎任性的自由就表现为这样一个任意的选择。康德认为,在经验中确实存在着违背法则的现象这样的例子,然而,经验中的例子是一回事,而把任性的自由解释为就体现在既能遵循又能违背法则之中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就自由而言,其消极义正是可以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刺激,所以,违背法则绝对不是自由的本质方面。任性的自由表现为它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法则,这样去行动,就是自由的积极义。至于人在经验上会“表现出一种不仅遵循法则,而且也违背法则作出选择的能力”,却不能用来解释我们作为理知存在者的自由,“因为显象不能使任何超感性的客体(毕竟自由的任性就是这类东西)”得到解释。仅仅用感性偏好的刺激规定自己,那是动物的机械性任性的表现,而决非人的自由的任性的表现。所以说,为什么人会有违背道德法则的表现,我们无法理解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因为自由是理智存在者(超出经验)的自由,不能用经验的机械因果性来解释。在康德看来,从概念分析的角度看,如果说自由是人的任性的一种能力,那么它就“与理性的内在立法相关”,故“背离这种立法的可能性”只能被说成是“一种无能”,而不能被认为是陷入动物的机械性之中的表现。
康德关于意志和任性的区分,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任性的肯定性自由就是能够受到道德法则的直接规定,那么它与意志就没有区别了。亨利·E阿利森则更合理地说明了任性的自由的特征。他认为,康德把人会违背道德法则看作一种无能是不妥的,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误用”:“只有存在者有了自由,从肯定的方面加以理解的自由,才能被认为是能够误用那种自由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偏离道德律构成了对这种自由的误用而不是它的缺乏。”我认为阿利森的意见是对的,因为这样理解任性的自由的特点,更使违背道德法则的任性自由的选择应被归责,即自由的人要为自己误用自己的理性而负责。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争论都没有注意到,康德区分意志和任性的真正目的在于明确意志是立法的,法则所强制的就是一种自动地形成准则、与行动直接相关的能力即任性,而不是强制那种不与行动直接相关的能力即意志。
五、康德道德哲学的晚年定论
在界定了意志和任性各自的含义之后,康德就展开了以下新的理论视阈:意志就是一种立法的功能,而自由的任性则包含着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准则。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而言,只要求它们能够符合意志的普遍法则,这就是行为的合法性,在这方面,主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内在准则。换句话说,只要我的行为不违背普遍的道德法则,即便我很想损害他人的自由却没有诉诸行动,那么我的行为也是有合法性的。人类的外在行为自由可以按照这样的合法则性而共存,它不需要直接规定任性的主观准则,也就是说,不管行为者持有什么样的准则,只要他在行为中不违背普遍法则,他就至少尊重了普遍法则,其行为就受到了普遍法则的强制,所以他实际上就行使了其任性自由,当然是外在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法理学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任性的外在行为的自由表现为在普遍的法则之下能够与他人的任性的外在行为的自由并存于世,这就是我们的法权的前提。法权的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任性还有内在准则,它应该受到普遍的道德法则的直接规定,不但其外在行为要合乎道德法则,其内在准则也要同时就是普遍的道德法则,即受到道德法则的内在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任性的行为及其准则才都是符合道德法则的,这才是合道德性的,也就是体现为任性的内在自由。所以,德性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的任性的准则能够抗拒把来自感性偏好的原理作为自己的规定根据,克服违背道德法则这一对任性的误用,而以极大的道德勇气用道德法则直接决定自己的主观准则,这种意志的力量就是德性。德性的形而上学的初始根据就在于此。由于有些学者对康德的道德原则经历了变化这一点没有深入把握,他们对康德前后著作中的用词的确切含义没有进行甄别,因而会出现误解。他们在对“自由的意志”和“自由的任性”作区分时就会陷入一种迷茫。比如有学者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不仅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还体现为一种消极的自由决意(die freie Willkür)”,认为自由的任性只有一种消极意义,其作用在于体现德性作为与偏好斗争的坚强和勇气。事实上,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言意志无所谓自由与不自由,自由的任性既有消极义,也有积极义,其消极义是它对感性偏好的独立性,其积极义正是道德法则能够作为任性的准则的规定根据。所以,这种对自由的任性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任性的自由并不仅仅是消极的。
Allen W. Wood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两部分即“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是彼此独立的,因为“法权是自然的时期的任务,而德性是自由的时期的任务。法权保护个体的外在自由,这是人类禀赋发展的条件,包括技能的培育和纪律的培育。道德的目的是伦理的关切之所在,它们在伦理义务的系统中得以特定化,并在最高善的理念中得以综合”。这是在康德整个实践哲学的视阈中来说的,即康德法权学说关注公民法治状态的建构,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的禀赋才能得到安全的发展,在文化的永无止境的发展中,才能有望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达到人类整体的道德化。虽然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是相互独立的,但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法权学说关注的是任性的外在行为的自由的实现,德性学说关注的是人任性的内在品性的自由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权学说可以看作关于外在行为的道德,有普遍法则对行为的强制,故也关乎自由,虽然只是外在行为的自由,所以它也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既然法权学说关乎自由,就不能说它仅仅关注自然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Allen W. Wood教授有所失察。
我们认为,康德通过确立任性的自由这一概念,既可开出法权的形而上学,贞定人们的外在行为的自由,又可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贞定人们的内在品性的自由,内外结合,构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整体,由此,康德建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这一毕生的学术抱负得以圆满实现。它展示了道德哲学作为义务论的特点,区分了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集中考察了德性的复合型结构,确定了道德情感在道德哲学中的地位。它更加符合人们日常的道德实践的特征,基础更加平实,在逻辑上更加自洽。虽然此书直到康德73岁高龄才出版,体系结构较为松散,行文也没有他在壮年时那种深刻峭拔、周密细致,但是此书是康德从中年时起就一直在准备写的,直到晚年界定了关键概念之后,才展开成书,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可以说,《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晚年定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fhH8aRCBn0C0IucIbM_CQ
编辑:陈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2-30 23:11
【案例】刘清平|自主责任何以必要?
原文来源:俗思哲韵
自由意志、自决选择、自主责任本身就是一根无法割断的因果必然链条……
自主责任何以必要?
刘清平
【摘要】 西方主流学界设置的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构扭曲了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的内在关联,把它变成了一个似乎无解的千古之谜。其实,依据自由意志内在遵循的人性逻辑,我们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既然人们总是为了达成自己意欲的善才基于自由意志从事行为的,他们对这些行为造成的恶就理应承担自己的责任,任何因果链条的决定性效应只能减轻、却无法免除这种自主责任。
一、自主责任的问题缘起
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里,“责任(responsibility)”概念都有“人们应当完成的任务(义务),如果做错了或没完成就要受到责备”的核心语义,并且能够回溯到人们在现实中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时经常扪心自问的那个问题那里:“我这样做(或不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在涉及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责任概念还往往凝聚着人伦道德的意蕴,诸如“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呀”“他的肆意妄为受到了舆论谴责”之类。就此而言,人生在世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主的责任,可以说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一种不仅司空见惯、而且意义重大的直觉性信念,并且很早就引发了哲学理论的关注。
不幸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关注似乎从开始起就误入了一条找不到出路的死胡同。当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围绕人们在命运的决定下能否做出自由选择的问题展开争论时,已经埋下了一根让它变成死结的伏笔:如果人们的一举一动无法摆脱因果链条的决定论支配,因而并非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凭什么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主责任、并且受到相应的赏罚呢? 这种质疑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中看起来是如此理直气壮,以致两千年后当休谟察觉到了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独树一帜地宣布“假如人类行为中不存在原因与结果的必然联系,那么不但施加的惩罚不可能是合乎正义和道德上公平的,而且任何有理性的存在者也不可能想要加罚于人”的时候 ,在其他方面受到他很大影响的康德还是未能看出这种洞见的深刻之处,反倒把它当成了一个“可怜的借口”来嘲笑,并且由于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在解答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的关联问题时陷入了包含逻辑矛盾的内在悖论 。进入20世纪,伯林也给休谟贴上了“自我决定论”“弱决定论”的标签,结果面对这个千古之谜照样束手无措,最终只好做出了某种苍白乏力的回应:要是凭借决定论否定自由意志的不兼容论立场真能成立,千百年来有关自主责任的通行话语就将彻底改变,以致我们不可能再用正义、平等、赏罚、公平这些概念来赞扬或谴责道德上的是非对错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多说,也不想多说” ,字里行间几乎流露出恳求不兼容论放过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以便给它们留下一些生存空间的意思。
伯林的回应从一个角度表明,西方主流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其实是某种削足适履的态度。一方面,如上所述,“人们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主责任”不仅是普通人广泛拥有的一种日常信念,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是没有了它,人们不仅不会在一己行为中看重西方主流哲学特别强调的理性“慎思(审慎)”或“明智”,反倒很容易在欲望激情的一时冲动下心血来潮,“不负责任”地任意作为,而且在人际关系中也会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却不顾及有可能给别人带来的坏恶后果,结果是没法展开持续性的人际往来,难以维系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主张自由与必然互相排斥的不兼容论又置这些简单的事实于不顾,单凭一个子虚乌有的二元对立架构,就坚持在决定论的语境下将人们的自由意志、自决选择和自主责任说成是并不真实存在的幻觉,结果呈现出了硬让无从否认的日常事实迁就虚构出来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的扭曲倾向。毕竟,假如人们的自由意志、自决选择和自主责任只不过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梦幻泡影,千百年来人们在道德领域展开的那些批评谴责,尤其是人们在法律维度上实施的那些严厉刑罚,岂不统统成了匮乏根基、毫无道理、既没必要、也无意义的无事生非了吗?
所以,考虑到伯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我们显然不可能在恪守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二元对立架构的前提下取得实质性的理论突破。相反,唯有从入手处抛弃这个原本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荒谬架构,直接面对人生在世基于自由意志、展开自决选择的日常现实 ,我们才有可能透过错综复杂的层层面纱,如其所是地揭示人们为何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主责任的本来面目。
二、自由意志的趋善倾向
严格说来,不兼容论依据二元对立架构宣称自由意志只是某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幻觉,也不算完全说错了,因为世界上的确没有他们指认的那种可以不受任何因果必然链条的支配、在随机偶然中纯属“非决定性”的自由意志。事情的真相是,人生在世拥有的任何随意任性的“想要”,不但统统是从外界的种种因果链条之中产生的,而且还始终遵循着自身的种种因果链条(又叫“人性逻辑”),以致可以说在双重意义上维系着与因果必然“两位一体”的内在关联。
首先,作为自觉心理中的“想要(will)”诉求,人们的任何自由意志总是来自为了弥补自己“存在”的“缺失”所形成的“需要”,因而就像这些需要本身那样,不可能摆脱这样那样的因果链条作为自己产生的必要前提。举例来说,无论是肯定性的“今天我想要吃牛排”,还是否定性的“明年他不打算外出旅游了”,在“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从心所欲背后,其实都能找到它们事出有因的生成根源:或者想要弥补自己存在的某种缺失(满足食欲),或者不想给自己的存在造成某种缺失(妨碍自己的工作事业)。不错,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确很难清晰地指认自己为什么会形成某种自由意志的具体原因,但这通常只是意味着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人们无法确定无疑地揭示它嵌入其中的那根“一定是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链条,于是只好将它置于“可能是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随机偶然之中,却不等于说它自身就像康德在谈到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时断言的那样,纯属毫无缘由的“绝对自发”“无因自生” 。事实上,倘若某人在日常生活中突然冒出了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明白从何而生的“自由意志”,他非但难以体验到天马行空、来去自由的惬意愉悦,反倒更可能在惶恐不安中觉得不自在:“我怎么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怪异念头?”
其次,由于这个原因,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流行见解相反,任何自由意志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毫无目标的空洞意愿,也不可能是时而趋善、时而趋恶、没有定准的随机变向,毋宁说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任何人都“想要”获得那些有益于维护自己存在、能够帮助自己满足需要、因而自己认为是值得意欲的好东西(“可欲之谓善”),却“不想”遭遇那些有害于维护自己存在、只会妨碍自己满足需要、因而自己认为是讨厌反感的坏东西(“可厌之谓恶”)。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时指责他人“趋恶避善”“为非作歹”,则主要来自他们站在不同立场上对于“哪些东西是好是坏”的规范性答案彼此不同(我喜欢萝卜讨厌白菜,所以认为你喜欢白菜讨厌萝卜是在“趋恶避善”),尤其来自他们因为对方的趋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坏恶后果提出的谴责非难(我讨厌抽烟,所以指责你为了自己过瘾当着我的面抽烟是“为非作歹”),并不能与人们的自由意志在元价值学维度上遵循的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混为一谈 。
更重要的是,只有依据人的自由意志与善恶内容的这种实质性关联,我们才能找到人们为什么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主责任的终极理据:既然一个人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的任何行为都是旨在趋于他自己意欲的好东西、避免他自己讨厌的坏东西,那么,无论这些行为同时还受到了其他因果链条怎样复杂纠结的决定性影响,他都没法推卸自己对这些行为及其造成的坏恶后果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毕竟,倘若你原本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某些好处才做某件事情的,你怎么有理由声称你这样做给其他人带来的伤害只能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外界因素,却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无关、你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呢?严格说来,休谟、伯林等人尽管对西方主流学界的扭曲见解也提出了某些异议,乃至自发地察觉到了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两位一体,却还是未能自觉地澄清自主责任何以必要的头号原因,正在于他们或多或少忽视了自由意志遵循的这种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例如,如果我们依然像伯林那样主张,自由主要“取决于有多少扇门是敞开着的,是如何敞开的……正是实际敞开的门,而非人们自己的偏好,决定着他们的自由” ,却忽视了自由意志与需要偏好以及善恶价值之间无从取消的内在关联,就非但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捍卫千百年来人们有关自主责任的通行话语,而且还会把自己也带进自败的沟里:要是自由意志的产生和实现不是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需要偏好,而是取决于实际敞开的外在之门,他们干嘛要对自己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的行为承担自主责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行为的后果多么恶劣糟糕,岂不是只有那些实际敞开的门,而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才有理由承担相关的责任吗?
三、自主责任的止恶功能
在此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自由意志总是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为什么它还会生成“自主责任”这种偏重于“责备”或“谴责”、因此主要是针对人们行为的“坏恶”后果来说的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诸善冲突(包括人际冲突)”这种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人生现象谈起了 。
问题在于,由于自身能力和外部资源有限的缘故,人们从事的任何趋善避恶行为总是处在“若干好东西不可兼得”的抵触冲突之中,其中也包括为了达成目的善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等工具善的情况。结果,撇开失败的行为肯定会产生对主体不利的后果不谈,哪怕是成功实现了主体意欲的目的善的行为,也会由于放弃其他善的缘故,在“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中造成某些在主体看来时坏恶的后果。例如,在健康与烟瘾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无论我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怎样的自决选择,或者成功维系了身体健康之善,或者继续享受着喷云吐雾之善,都必然会在“有得必有失”的悖论中遭遇到艰难戒烟之恶或身体受损之恶,却无法达成我期盼的两全其美。在人际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不同人们在善恶好坏的规范性评判中经常出现的歧异性标准,更会常常生成“你为了享受你想要的抽烟之善,却让我遭受了我讨厌的健康受损之恶”的局面。于是,诸善冲突在原本只是趋善避恶的单向度行为中导致的这类悖论性之恶,就构成了自主责任所以必要的直接原因:谁应当为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坏恶后果负责呢?
毋庸讳言,广义上的“责任”也会涉及到主体由于行为产生了善好后果所得到的奖赏:我成功考上了大学,就会觉得心花怒放快乐;你帮他度过了难关,他因此对你感激不尽并给予回报。不过,正如第一节的定义和第二节的讨论足以表明的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更倾向于“责备没完成或做错了的任务”,因而主要指向了行为的坏恶后果。深究起来,导致这种“轻奖赏重惩罚”的“责任偏向”的主要原因,就是任何行为在诸善冲突中都会产生坏恶后果的必然性:对于各种趋善避恶行为想要达成的有利后果,人们其实是用不着担心的,因为它们统统能够锦上添花地维系人们的存在、弥补人们的缺失;相比之下,倒是对于各种趋善避恶行为在悖论性结构中生出的不利后果,人们才有必要特别提防,因为它们只会雪上加霜地损害人们的存在、加重人们的缺失。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在趋善与避恶两位一体的人性逻辑中,消极避恶的一面对于积极趋善的一面也总是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换言之,假如人们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的行为只是产生了对人有益的善好后果,就不大可能出现“谁来承担责任”的严峻问题了;所以,人生在世之所以有必要追究责任、施加惩罚,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原本旨在趋善避恶的行为会由于诸善冲突的缘故生成对人不利的坏恶后果。
进一步看,尽管自主责任可以适用于人们行为产生的任何不利后果,但它的矛头所向首先又是指向了那些对人们来说严重到了不可接受地步的不利后果——或者说它的本质功能首先是以“两恶相权取其轻”的方式,防止“不可接受的严重之恶”。例如,在健康之善与烟瘾之善不可得兼、无论怎么取舍都难以避免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如果我考虑到了自己为此要承担的自主责任,就会仔细权衡两种可欲之善的主次轻重——也就等于是慎重比较我在放弃了它们后将会分别遭遇的两种可厌之恶的主次轻重,然后再按照人性逻辑的另一条原则“取主舍次”,基于自由意志做出我的自决选择,以甘愿忍受不那么严重的不利后果为代价,努力防止会给我造成不可接受损害的严重恶果。所以,倘若我在慎思后觉得患病之恶比戒烟之苦更严重,我就会做出不惜忍受戒烟之苦也要确保健康之善的自决选择,由此履行我“应当”维护身体健康的“责任”或“义务”,并且因为这种取舍防止了在我看来属于不可接受的患病之恶的缘故把它评判成“正当之对”(虽然从它同时还会让我忍受戒烟之苦的角度看,我不会把它说成是“完美的好”)。相比之下,假如我“不负责任”地拒绝慎思任意妄为,或者在权衡比较的时候把两种可欲之善的主次轻重弄颠倒了,结果做出了不顾健康继续抽烟的自决选择,以致接下来患上重病,我则会因为这种取舍给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严重之恶的缘故把它评判成“不正当之错”,并在遭受重病之恶的严厉惩罚中,承担起自己对于这种错误选择的自主责任,甚至因此展开“自责”。
澄清了人们在诸善冲突中如何基于自由意志做出自决选择的根本机制,我们就容易理解责任概念为什么会包含前面论及的“人们应当完成的任务(义务),如果做错了或没完成就要受到责备”的核心语义了。事实上,只要存在诸善冲突,人们就不得不在“善恶好坏”的评判标准之外诉诸“是非对错(正当与不正当)”的评判标准,乃至进一步诉诸“应当”的强制性“义务”,从而面临所谓的“责任”问题:既然你不履行或违反了你“应当”履行的“义务”,你就理应受到“责备”或“惩罚”。所以,“责任”的本质功能也像“是非对错(正当与不正当)”以及“应当”之“义务”一样,不是单纯趋于定量维度上更大更成功的善,而是归根结底为了防止定性维度上不可接受的严重之恶。换言之,只要存在诸善冲突,人们就像离不开“是非对错”以及“应当”之“义务”一样离不开“责任”。
从这里看,即便对于人们从事的那些仅仅涉及到自己、与他人无关的行为来说,自主责任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非如此就不足以防止人们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自决选择会产生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接受的坏恶后果。拿刚才的案例来说:倘若我“不负责任”地做出了“错误”的取舍,为了放纵抽烟的意欲拒绝履行维护健康的“义务(任务)”,我就不得不在“自责”中承担起患上重病这种既“受罚”、又“受罪”的“自主责任”。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俗话说的“自作自受”:既然是你自己自作主张酿下的苦果,当然也就只有你自己含着泪承受了。
四、人际责任的纠结机制
与一己责任相比较,人际责任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在前一种情况下,总是一个人在自己面临的诸善冲突中一方面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好东西,另一方面遭受了自己反感的坏东西,因而只有自己才会在悖论中既领受了奖赏、又承担了责任的话,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却是一方面甲作为某个行为的实施者(主体)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好东西,另一方面乙作为这个行为的受动者(对象)遭受了自己反感的坏东西,所以才会产生“甲是不是应当对自己在人际冲突中伤害了乙承担自主责任”的问题。按照不兼容论的观点,既然甲和乙在这类情况下都必然处在外界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不管是甲得到的好处,还是乙受到的伤害,也都应该首先归因于外界的因果必然链条,而不必追究甲应当承担的自主责任。然而,这种貌似有理有据的“宽容”说法却是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直觉体验正相反对的。有鉴于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应当抛弃那种关公战秦琼式的二元对立架构,直面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努力揭示人际责任何以必要的深层机制 。
首先,倘若甲在人际行为中是通过有意让乙受害的途径为自己谋取好处的,他理应对乙受到伤害承担自主责任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无论另外还有怎样的决定性因素促使甲从事这类行为,他归根结底都是基于自己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为了让自己获益才让乙受到伤害的——也就是通常说的“损人利己”。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甲的这类行为不仅会引发乙的反抗,同时也会受到旁观者的谴责,被认为是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坑人害人”,而在对乙造成的伤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谋杀、抢劫、强暴等),还会受到正义法律的严厉制裁——不管甲会找出什么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以逃避责任。进一步看,假如甲不是为了获取像金钱财富这样的实际利益,而是为了好玩取乐乃至心怀仇恨的缘故才去伤害乙的,同样不足以减轻甲理应承担的责任,因为甲依然是把“让乙受害”本身当成了可欲之善来追求的,所以还会由于“恶意害人”的缘故加重自己的责任。
其次,表面上看,如果甲是在无意中给乙造成伤害的,他似乎就不必对乙受害承担什么责任了,因为他既没有从中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没有拿乙受害来取乐的“恶意”,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不希望乙受到伤害。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这种情况下,甲照样有必要按照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承担自主责任的内在理据在于:尽管甲没有任何自觉的意图想要伤害乙,但他毕竟是在为了满足自己需要、实现自己诉求的行为中导致这种伤害的,所以才应当对这种虽然属于“无意”、却又确实“有因”的人际伤害承担“自主”的责任,尤其是承担由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趋善行为有可能伤害乙所导致的“过失”责任。严格说来,只有当甲是在基于自由意志从事像见义勇为这样的只利他不利己的趋善行为时无意伤害了乙的情况下,甲才能凭借“自己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动机”这条理由,免除自己对于这种伤害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深入辨析这类现实生活中常见而又微妙的差异,无疑有助于我们澄清自由意志的趋善避恶倾向对于自主责任的主导效应。
最后,假定甲是在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情况下给乙造成伤害的,他也能免除自己对于这种伤害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因为他已经由于某些非自主的原因(这一点构成了甲与在神智不清中伤害他人的醉酒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失去了正常分辨道德上是非对错的理知能力,以致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不对乙造成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由于甲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基于自己趋善避恶的自由意志从事相关行为的理据,如果甲给乙造成的伤害足够严重,他依然有必要对于这种伤害承担非道德的自主责任,并且因此接受更有强制性的监护监管乃至住院治疗。此外,像未成年人在伤害他人后有可能减免其自主责任、或是由监护人代其承担部分责任的现象,也能从这个角度理解:一方面,未成年人虽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伤害行为的,却又缺乏充分的分辨是非能力;另一方面,监护人虽然没有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从事伤害行为,却又在忽视自己的监护责任方面存在着基于自由意志的严重过失。就此而言,像西方主流学界那样在“认知”与“意志”的混淆中宣称“不受理性认知指导的感性欲望就不是自由意志”“失去了分辨是非的理知能力的人也就失去了自由意志(想要这样做或那样做的意欲愿望)”,显然也是脱离实际、无法成立的。
毋庸讳言,上面的许多讨论预设了现代法治的社会背景,而在历史上却往往存在下面的情况:虽然甲本来“应当”对于自己基于自由意志伤害了乙承担自主的责任,但由于种种原因,乙、公众或社会却无法让甲“实际”受到谴责或惩罚,以致甲成功地逃避了自己的自主责任。不过,这类现象并不足以否定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的关联,相反还恰恰彰显了基于这种关联确立现代社会的问责机制特别是法治制度的重大意义:倘若我们忽视了两者的关联,未能针对那些基于自由意志伤害他人的行为展开落到实处的谴责惩罚,以防止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就很难保持共同生活的平稳运行,维护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说穿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之所以构成了古今中外人们在道德领域广泛拥有的一种规范性的素朴共识,也就是因为它试图通过“责任感”或“义务感”的途径,影响人们自由意志的具体实施,严格要求人们在人际冲突中克制自己、尊重他人,尤其不可为了自己获取利益就对他人造成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
五、二元对立架构的致命伤
从前面的讨论看,第一节引用的休谟那段话——“假如人类行为中不存在因果必然,就谈不上道德责罚”——虽然有点笼而统之,未能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其基本思路却是入木三分的:倘若基于自由意志的人类行为不是在与因果必然的两位一体中遵循着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尤其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弥补自己的缺失、维系自己的存在作为唯一的目的,我们怎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对这些行为的坏恶后果展开问责、实施惩罚呢?毕竟,假如自由意志真像不兼容论宣称的那样能够摆脱一切因果必然的决定性支配,纯属难以捉摸、无从预测的随机偶然,我们试图让它承担的“责任”岂非注定了就是“莫须有”的吗?
当然,不兼容论在努力否定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的实际关联时,所依据的主要还是外界环境中对于自由意志的形成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果链条。同时,它的这类见解貌似也能从现实中找到经验性的实证支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确有人通过诉诸外界必然因素“一定是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影响效应,来为自己的不正当行为开脱,以求推卸自己本应承担的一己责任特别是人际责任:我是由于这样那样不可避免乃至不可抗拒的缘故,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如此”地从事某个行为的,所以对它造成的坏恶后果也无需承担什么责任,而应该把账记在客观必然的外界环境上。不难看出,这类并非罕见的日常辩解与不兼容论的基本立场之间明显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
不错,在许多情况下,外界环境的因果链条确实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主体对于行为后果承担的自主责任。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只要承认了自由意志遵循着内在必然的人性逻辑,我们就不得不同时也承认下面一点:无论外界因素具有怎样不可避免乃至不可抗拒的决定性影响,只要行为主体是基于趋善避恶的意欲愿望做出自决选择的,任何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如此的因果必然链条都不足以免除主体自身的自主责任。举例来说,张三由于顶不住抽烟朋友的苦劝染上了烟瘾而患上重病,他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自然就与李四顶住了不抽烟朋友的苦劝一意孤行地继续抽烟而患上重病的自主责任大为不同。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张三因此就有理由把自己的自主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虽然抽烟朋友的诱导对于张三抽烟的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是没有抽烟朋友的诱导,他或许压根儿不会抽烟),但他自己未能抗拒这种诱导染上了烟瘾、后来也没能戒掉,却无疑与他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自决选择脱不了干系,所以他当然不能声称他对于自己因为抽烟身患重病就是纯然无辜的。再比方说,甲由于外界环境的种种原因陷入了穷困潦倒,结果在某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如此的情况下偷窃了乙的财物以求维生,他同样只能凭借这些因果必然链条减轻而非豁免自己的自主责任,因为即便在这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如此的情况下,他也还是可以并且能够通过展开主次轻重的不同权衡,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不同的自决选择。归根结底,无论外界环境的种种因果链条发挥着怎样决定性的影响,既然一个人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好东西才在悖论性结构中生成了会让自己或他人遭受损害的坏东西的后果,难道不正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才应当首先对这样的后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吗?
事实上,正是由于伯林片面地强调“实际敞开的门,而非人们自己的偏好,决定着他们的自由”,他才会在努力捍卫自主责任的时候自败地宣称:指责某个人在酷刑下不得不出卖朋友是缺乏理由的,因为这个人不这样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显而易见,他在这里就是依据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单凭酷刑之下“不得不”的决定性效应,一笔勾销了这个人自由意志的真实存在及其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然而,伯林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又承认:尽管这个人也有理由说他的行为是“不自由”的,他毕竟还是做出了取舍,因为他也能选择被拷打 。比较而言,伯林后面这个见解无疑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正是由于这个人在酷刑的决定性效应下,也能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宁肯遭受拷打也不出卖朋友的自决选择,他才应当对他在酷刑下出卖朋友的行为承担起某种有理由适当予以减轻的自主责任。无论如何,就连这个人自己在出卖朋友后也有可能感到悔恨:“要是我当时再坚持一下不出卖朋友该有多好啊。”
因此,倘若考虑到某些人诉诸因果必然链条的决定性效应往往是出于为自己开脱、让自己免受应得责罚的偏私目的,我们与其说不兼容论在这方面拥有的经验基础足以证明它自身的正确合理,不如说恰恰反衬出了它自身的扭曲错谬:一种既不足以解释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的内在关联,也不足以彰显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而主要构成了某些人不想承担自主责任的堂皇借口的见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理论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对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来说,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义务)的上述关联恰恰构成了切中要害的致命一击,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现出它想要否定却又否定不了的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自由意志虽然总是随意任性地“想要怎样就怎样”,但同时又会受到“责任—义务”的必然束缚,不允许由它主导的行为产生不可接受的坏恶后果;否则,假如它试图“不负责任”地摆脱“责任—义务”的必然束缚任意妄为,最终就会受到“承担责任”这种更为严厉的必然束缚。就此而言,作为一个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并且发挥重大效应的人生事实,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义务)的内在关联可以说已经宣告了西方主流学界坚持的二元对立架构的最终破产。毕竟,削足适履与其说是在解释现实,不如说是在回避现实。
编辑:吴悠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6 20:18
【案例】
段伟文 | 数据智能时代的伦理反射弧
追溯信息技术和数据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及智能时代的发展历程,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一阕新的技术神话,都是一场技术与社会互构的传奇,其实质是旷日持久且规模不断拓展的社会伦理试验。在这一超级社会伦理连续大剧中,各种价值反思与伦理权衡一直贯穿其中。
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
[美] 富兰克林·福尔 / 著
舍其 /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9-12
1876年3月10日,美国发明家贝尔记录下了世界上首次电话通话——我对着话筒大声喊道:“沃森先生,到这里来,我想见你。”在这起改变世界的事件中,电话这种新的信息技术拓展出一种可以实时交互的信息空间(info-sphere),而这种非在场的交互体验让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虚拟在场。自此,各种信息空间和虚拟在场方式成为信息时代生活形式的基础,亦导致诸多价值冲突和伦理抉择。
在信息时代起步之时,人们就开始为隐私权、数据权利受到侵害倍感困扰。电话刚刚开始普及时,往往是一个小镇的几家人共用一个电话信道,结果各种家长里短、恋人间的悄悄话变得毫无隐私。后来,随着交换机技术的发展,这些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尴尬似乎得到了化解。但直到现在,从窃取电子通信录和通信记录到各种针对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的不当采集,从骚扰性的推销电话到借助人工智能语音造假的诈骗电话,信息通信技术的滥用乃至恶意使用仍屡禁不止,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已成为智能时代捍卫个人权利的焦点。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Spirit
Sherry Turkle
The MIT Press, 2005-09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照相成为记录人们生活的迷人的新技术。当第一次看到自己定格于时空中的留影时,人们大多倍感欣喜和惊奇,但也有人会油然而生一种狐疑:一旦人的影像被记录下来,会不会有一部分灵魂被偷走。虽然这种可怕的想象没有变成现实,但人们很快意识到:拍下某个人的照片,往往意味着拥有了某种针对那个人的力量。特别是随着各种便携式相机的普及,隐私权被侵犯开始成为人们在享受信息技术的利好时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近150年来,面对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伦理挑战,人们一般难以运用已有的道德规范加以应对,只能在其技术实践和体验中,逐渐构建起相应的伦理反射弧,进而在此柔性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刚性的和可执行的法律规范。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数据库的应用日益广泛,个人数据及隐私权保护才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
尽管当前在数据保护方面欧洲似乎更主动和积极,但美国却是信息时代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先锋。1973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任命的数据自动化系统咨询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公平信息实践”(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简写为FIPs)的概念以及五项原则,对个人数据的透明性、使用限制、访问和更正、数据质量、安全性等均做出了规定,这也成为美国国会次年通过的《隐私法》的基础。1977年,根据《隐私法》设立的隐私保护研究委员会向卡特总统提交了《在信息社会中保护隐私》的报告,将FIPs的五项原则细化为八项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是:开放原则,不应有一个秘密存在的个人数据记录保存系统,并且应对组织的个人数据记录保存规则、惯例和系统采取开放政策;个人准入原则,对于记录保存机构以个人可识别的形式保存的信息,个人有权查看和复制;个人参与原则,对于记录保存组织保存的个人信息,个人有权更正或修改该信息的实质内容。另外,报告中还阐明了任何数据保护系统都应该实现的三个目标:尽量减少干扰、最大限度的公平、合法与可执行的保密预期。
如今各国的数据保护规范均源自FIPs,透过这些早期的探讨,可以窥见管理者推动个人数据保护的初衷。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即便看起来是可执行的刚性规范,基于FIPs的数据保护在法律实践中也并不成功,隐私保护一直在路上,甚至越来越困难。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往往被忽视,隐私政策时常难以理解。对企业来讲,隐私政策又存在着高成本和互不兼容等问题。由此,一种必要的实践智慧是,在相关法律不能达到有效规制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变迁和复杂的现实利益关联往往使得相对刚性的法律规制难以有效执行。那么,能否从法律层面退一步,在价值和伦理层面构建起更细致的柔性约束,为更为务实有效的法律规制奠定基础?具体而言,在越来越多的数据驱动的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中,应该在法律层面确保个人安全、保证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实现保护的一致性和有效执行的同时,展开必要的价值权衡和伦理构建。一方面,通过价值权衡,促使个人数据与隐私的保护在预防数据流动对个人的危害与数据利用的效益最大化之间做出精细的权衡;另一方面,诉诸伦理构建,推动企业和机构对其行为的透明、诚信和责任做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伦理承诺。
除了隐私权和数据权利之外,信息时代的另一个更难以应对的价值伦理挑战来自数据造假。吊诡的是,虽然数据和信息被视为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带来的最大悖论却是低质量信息泛滥成灾,各种水军和社交机器人令人真假莫辨,大量虚假信息和数据使人面对后真相时代束手无策。尽管人们一度对科学实验数据、照片、视频刻画的世界和事实的客观性深信不疑,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凡是人从事的活动都可能造假,即便数据的记录过程是诚实的,人们对这些记录的解释和利用也不可能不偏不倚。抛开摄影术本身的视角选择和光影调配不说,照片并不是对世界赤裸而客观的记录,各种编排、增删和特定的解释会赋予照片不同的意义。
更让人有挫败感的是,由于数字技术和智能化的数据处理技术的加持,照片的伪造与变造成为与时俱进的数据造假方式。时至今日,生物医学研究中频频爆出图像和照片造假,严重削弱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恪守诚信的“人设”。面对生成对抗网络的发展,人们在为人工智能艺术前景欢呼的同时,难免担忧深度造假的滥用可能带来的危害。在《科学》(Science)杂志2019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甚至指出可以运用人工智能在正常的医学影像中制造罹患癌症的假象,并进而强调应防范医院与保险公司合谋以此坑害患者。[1]
在充满利益纠纷和权力争夺的政治领域,数据分析和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也沦为了造假利器。在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大选中,剑桥分析公司利用大量数据锁定并说服选民,通过人工智能加持的“心理战”干预了投票。据报道,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某国的一个互联网研究机构通过13 000个机器人账户在推特(Twitter)上假装为论辩双方发言,但赞同脱欧的内容是反对脱欧的8倍;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有1/5的网络辩论来自机器人。更充满魔幻色彩的黑色幽默是,2015年专为已婚人士寻求艳遇的约会网站AshleyMadison.com遭到黑客攻击,3 700万用户资料被泄露,结果显示,500万女性用户中的大多数在注册后鲜少登陆,而其中7万被称为“天使”的注册为女性的用户却十分活跃。“天使”们会主动与男性用户联系,但在对方付费后才予回复并在几个月间保持联系,以确保“渣男”们继续登陆和续费……当然,聪明的读者已经知道了荒谬的谜底:让登徒子们垂涎三尺而不得的“天使”们,无一不是边吃数据边送秋波如假包换的“机器姬”。[2]面对人工智能数据造假和机器人水军之类高技术含量的挑战,单靠价值反思和伦理调适无异于纸上谈兵,必须从技术反制和法律规制两个方面予以有力的制约。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9年11月底联合印发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无疑有利于遏制人工智能新闻造假等行为。
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英] 詹姆斯 · 布莱德尔 / 著
宋平、梁余音 /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06
不论信息和智能科技要进行什么样的社会伦理试验,最终的目的只能是创造一种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往往需要每个公民的实际行动。在信息时代的高歌猛进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颠覆性影响与其在社会政治层面所凝聚的知识权力结构休戚相关。而常识告诉我们,再完美的权力机构,也有阳光雨露洒不到的角落,而要改变这一点,需要每个人以切实的行动去矫正由权力盲区造成的公正落差。最简单的事实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信网络都建立在自然垄断的信息基础产业之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密歇根州等比较偏远的地区,被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电信巨头视为没有必要布线的无利可图的地方,那里有大约300万的农民通过自制的可以传导电信号的栅栏传递信息和通话。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Claude Shannon)小时候曾是维护这种电栅栏的能手。这个可能被历史遗忘的故事表明,纵使面对垄断和排他的知识权力结构,人们依然可以运用其掌握的技术发挥能动性。面对高度垄断的软件产业,开放源代码运动带来的开源软件使人们更多地享受到信息技术创新的红利;在地震等灾害中,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软件共享灾区的重要信息;在智慧城市实践中,很多软件工程师担当起公民科学家,投身公益性软件的开发。
互联网的概念来源之一可以追溯至人们对智能圈、超级智能等人类知识与智慧空间的向往,其目标是通过知识共享推动知识创造。1946年,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操盘手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恰如我们一样思考”(As We May Think)的文章,倡导开发能大规模记录人类活动以促进人类的经验智慧增长的技术。在文中,他虚构了一种被称为Memex的台式信息机器。这个机器由存储器、一个键盘、一块半透明屏幕等组成,可以通过微缩胶卷输入,用键盘检索大量的存储数据。这样一来,人们只要在办公室就可以检索和管理信息,通过各种知识库拓展智能,更好地管理各种事务。50年后,布什的这一构想被追认为网络超文本链接的原始构想。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数字乌托邦主义者才将计算机和网络等信息技术视为挣脱现代性对人的僵硬的安排的工具。他们创造了个人电脑、全球电子链接,建立了引领互联网早期发展的赛博文化(Cyber culture)。20多年前,在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和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等未来启示录式的畅销书中,展示了一系列以摩尔定律和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愿景,信息技术创新似乎会带来一种没有极限的增长,网络空间与虚拟现实会赋予人们一个更加平权、民主、自由的去中心化的前景。但这种貌似个体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摆脱现实社会制约的幻象很快就破灭了,信息网络空间并没有成为独立于物理空间的赛博空间,而是成了虚拟与现实相互交缠的数据空间和编码空间。
未来之路
比尔·盖茨 / 著
辜正坤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01
数字化生存
[美]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 著
胡泳,范海燕 /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1
随着谷歌搜索对百科全书检索式的雅虎等早期门户网站的超越,以及Web2.0和网络社交新媒体的发展,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不仅使网络为用户数据所驱动,而且这些数据反过来会成为人们的数据足迹。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数据的指数化增长,对人的线上和线下行为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则可能使每个人成为被追踪、观测、分析的对象。数据的掌握者由此可对数据进行认知计算,借助一定的算法对数据主体展开行为评分和内容推荐等,从而评判、引导和干预人的行为。从社会形态的变迁来看,不论是运用数据描述或干预世界和人的行为,还是运用各种可穿戴设备采集、分析数据以对他人或自己的生活进行量化自我等管理与治理,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社会——数据解析社会的来临。数据解析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革命性的:一方面,数据所扮演的角色如同13世纪出现的透镜,用透镜制造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让宇宙和微观世界得以被清晰地观测与呈现,如今“数据透镜”则使人的行为得到量化地记录与透视;另一方面,就像17世纪笛卡尔发明解析几何使自然界的结构与规律得以被探究一样,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的应用正在使人的行为规律得以被洞察和解析。
针对这一时代性的变化,互联网思想家马克·戴维斯(Marc Davis)对数字人和数字自我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3]在他看来,距今100万年或更早,人类先祖演化为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和认知能力的智人,作为物理自我的人成为一种可以在世界中行动的主体或自然人。约1万年前,伴随着《汉谟拉比法典》等法律制度的构建,逐渐出现了法人的概念,规定了具有行动自由和行为能力的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在最近的20余年间,在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推动下,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多地以在线的方式实现,个人信息或数据成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原料,人也因此获得了“数字人”这一全新的存在形态。这一人类新形态使人一时间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是尚未形成一种合理的数据规范。数据既是自我特征又是智能应用的基础,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难题。戴维斯认为,如同物理自我应该得到保护一样,数字自我也需要得到保护。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是隐私和控制问题:谁在采集你的数据?谁可以拥有它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如果说透过数据可以了解人的特征和行为,那么掌握这些数据是不是意味着对人的监控?大数据时代令人时刻感到焦虑的问题是:谁在何时何地能够看到你?
搜索:开启智能时代的新引擎
[美] 斯特凡 · 韦茨 / 著
任颂华 /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7-04
有关数字人或数字自我的讨论表明,人类及反映其特征和行为的数据已经逐渐融合为人与数据的聚合。一方面,通过各种监测手段获得的数据,可以直接影响到人的感知和行为。当早上起来感觉头晕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智能手环上显示血压较高或较低,就会感到紧张并立即服药。另一方面,基于数据的智能认知日益与人类认知形成无缝连接,甚至使人在生活中产生一种人数协同的数据感。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觉知能力正在演变为基于数据觉知的具身认知。心跳、血压、血糖等实时监测数据使人对自己的身体变化更加敏感,自动导航应用则会帮助方向感不好的司机更轻松自如地驶向目的地。而由此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才刚刚开始,各种数据驱动的智能系统未来将无处不在。就像人们现在佩戴的眼镜,这些智能系统将为人们展示一幅增强现实的世界图景:在去莎士比亚故居的路上,智能旅行系统会告诉你今天那里将有什么活动、最近有哪些名人造访过,而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一切皆顺理成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与数据的聚合正在成为构造世界和塑造个人的基础性活动。通过数据测量和分享,各种智能设备和应用将人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改变世界的行动者网络之中。以Apple Watch、Fitbit等可穿戴设备为例,这些正在智能化生活世界中恣意生长的新奇物种给人的承诺是,像贴身的健康卫士和健身教练那样,使用户的饮食、睡眠、锻炼等生活习惯得到实时的调节。人们每天运动的步数、里程、心率和所燃烧的卡路里等数据都会被监测,一套量化指标被设定为努力的目标。常见的画面是,倘若你久坐不动,智能手表就会提醒你运动。但在智能设备和应用所连接起来的行动者网络中,使故事变得完整的关键环节是,这些体贴入微的智能体扮演着无处不在的数据捕获者的角色。经常遇到的场景是,如果你愿意让可穿戴设备采集你的运动数据,保险公司可为你提供保费优惠;你如果同意刷脸支付,在自动售货机上买矿泉水时就可以得到几分钱的优惠。但人与数据的聚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和不知情的,企业、机构和相关部门则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以数识人”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自我认同,而且成为每个人被社会认知的基础。换言之,企业、机构和相关部门通过智能技术应用所捕获的“真实世界中数据”正在成为全新的生产手段和治理工具。单从工具理性来看,掌握数据中蕴含的个人身份特征、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让人的行为根据商业和政治的需求被智能化监测和调控。实际上,在当前两个合法的负面收割场景——赌场和网络游戏中,玩家真实的行为数据、情感反应数据得到了大量的研究与测试,所谓上瘾行为是智能化的被设计的上瘾。应该对这些以引导人的心流和欲望为目的的研究活动本身展开深入的研究,使其道德上的原罪被玩家知晓,以促后者自省。
[1] Finlayson, S. G., Bowers, J. D.,Ito,J., Zittrain, J. L., Beam, A. L., & Kohane, I. S. (2019). Adversarialattackson medical machine learning. Science, 363(6433), pp.1287-1289.DOI:10.1126/science.aaw4399
[2] 詹姆斯·布莱德尔:《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宋平、梁余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7—258页。
[3] 斯特凡·韦茨:《搜索:开启智能时代的新引擎》,任颂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76—177页。
来源:信睿周报
作者: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7 17:21
【案例】
技术伦理学:关切人类未来的伦理学
计算机技术兼具客体性技术和主体性技术的特征,串联并融合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层的伦理意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机关系、技术—社会双向形塑的伦理分析范型。我们可以深入分析计算机技术,以此为例探寻技术伦理学的时代性和未来性。
计算机技术带来诸多伦理问题
计算机技术催生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身体、扩展了人的智能,促成了万物互联,迎来真正的信息社会。一方面,它给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重塑了人类的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社会不动声色地预制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路径。计算技术经历了从巨型计算机到个人计算机,再到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将发展到普适计算的过程。巨型计算机使机器获得计算能力,人类因使用计算机获得延展的计算能力。个人计算机则将计算能力赋予寻常百姓,开启了一场技术赋权运动,人人拥有机器计算能力成了社会目标。互联网尤其社交网络和移动网络,将计算能力不可思议地转换成了信息权和表达权,全方位地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人类生存空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将计算能力进一步社会化和广谱化,使人类从科学数据化步入社会数据化、从生产机械化迈向生活智能化之路。电子政务、网络经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据人生成了新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样态,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成为赛博空间。人类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观正在浮现。
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亦面临诸多伦理问题和挑战,如网络安全、个人隐私、数字鸿沟、数据巨机器等。这些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促成了技术伦理学的大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广谱化和深层化,已经超越个体和区域,涉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未来。这使得伦理学正经历“未来转向”,要求人类不仅应对当代人负责,也应对未来人和人类命运负责。这一转向在二战后已经开始,原子弹爆炸、环境污染等关涉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的问题,催生了关于技术伦理的公共讨论和技术伦理学。随着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迅速崛起,技术伦理再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话题。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指向人类本身、人类的身心。如果说以往的技术指向的是客体世界,那么这些技术指向的是人类主体。这种主体性技术直指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对人类自身身体和智能的改造、延展或替代,对人类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更易引起人类普遍的集体忧虑,引起对人类未来的担忧。物理学家霍金认为,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就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而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之竞争,将被取代。《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技术带来了现代化生活,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人将变得毫无用处,人类可能灭绝。因此,技术伦理学既是部门伦理学,也是超越部门伦理学的时代伦理学和未来伦理学。作为对上述问题进行学术回应的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伦理学也具有这样的属性。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一直蕴含着几条相继或交错的线索、路径: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机器人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和全球伦理学、未来伦理学。
技术伦理学的多重面向
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控制论创始人罗伯特·维纳向世人提醒信息技术对社会构成的威胁,提出应将对新技术的讨论提高到道德认识的层次,由此奠定了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创始人的地位。计算机伦理学学科史始于美国计算机专家沃尔特·曼纳。在20世纪70年代,他注意到计算机伦理问题日益突出,提出研究这些问题的领域应当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将之命名为“计算机伦理学”,并将计算机伦理学界定为研究计算机技术引发、改变和加剧伦理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科。1984年是计算机伦理学发展的分水岭,它能够成为“显学”与美国计算机伦理学家詹姆士·摩尔和黛博拉·约翰逊不无关系。摩尔提出“真空说”,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一门全新的伦理学,因为计算机技术具有以往技术不具有的逻辑延展性,这一特性导致了理论的含混和政策的真空。从前的伦理学理论无法回答计算机技术提出的挑战,需要建立一门全新的伦理学来应对。约翰逊设立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议程,将计算机视为典型的社会技术系统。
人工智能伦理学的发展在上述线索中穿行。196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家韦曾鲍姆编写了一个名为ELIZA的心理疗法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表明计算机能够进行自动化的心理治疗,并容易导致将人看作机器的“艾丽莎效应”(Eliza Effect)。韦曾鲍姆担忧人类“信息处理模式”会增强科学家甚至普通公众把人仅仅看作机器的倾向,认为人工智能的滥用可能损害人类的价值。韦曾鲍姆是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先驱,代表计算机伦理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路径。1988年,IBM公司的雷蒙·巴尔金提出,如果机器人最终与人难以区分,那么我们必须制定伦理行为规范来调整真实的人与“人工的人”之间的关系。他编撰了“赛博伦理学”一词,用以概括这一研究领域。巴尔金提出的这条路径代表计算机伦理学的机器人伦理学线索。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商业化普及,网络伦理问题获得空前的关注。斯皮内洛、塔瓦尼等众多学者相继出版了大量网络伦理学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网络伦理学的研究热潮。
技术时代的全球伦理学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超越计算机意义上的计算机伦理学,预示着计算机伦理学中的全球伦理学路径。1995年,克里斯提娜·格尼娅科-科斯科斯佳指出,选择从事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在界定其研究范围和学科的意义时太保守了。当我们在谈论计算机伦理学时,我们是在谈论一种正在出现的全球伦理学,而且是在谈论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因为计算机影响人类生活的一切。她指出,到人类进化的现阶段,还没有创造出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全球伦理,未来的全球伦理学将是计算机伦理学。在她看来,计算机技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疆界,是全球性的;计算机技术涉及人类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整体,是全球性的。因此,计算机伦理学必定成为全球伦理学。
计算技术不只是延长或代替人脑,更重要的是促成万物互联。多种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能源技术等的融合,将加快万物互联的进程。技术的融合将促进人机的融合,促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使我们难以区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两类空间,难以区分我们的身体与人工物,并最终导致各类技术伦理学的融合。如巴尔金在1989年曾因科学家利用计算机使猴头存活36小时,预言赛博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将汇合到一起。计算机伦理学、互联网伦理学、大数据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等将汇聚发展成为基于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的赛博伦理学。
赛博伦理学是各类技术伦理学的汇聚,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时代伦理学和未来伦理学。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诞生和完成,将使人类社会真正奠基于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与时代同一,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即时代伦理学。人—机关系、人—万物关系,更准确地讲,基于技术的人与人的关系便成为技术时代伦理学的核心议题。赛博伦理学不再只是技术伦理学,它是技术时代的伦理学,是万物互联时代的伦理学,是关切人类未来的伦理学。
技术与人类未来、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是技术时代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探寻的核心。在不同的技术时代,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问题聚焦在不同的内容上。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它聚焦于人与机器的自由关系;在当今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它聚焦于人与信息、人与数据、人与自主机器的自由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技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关系,确保人类的未来,便成了技术时代伦理学探寻的终极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信息价值开发的伦理约束机制研究”(17ZDA023)阶段性成果)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学派
作者:李伦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7 22:19
德国发布AI和数据伦理的75项建议,提出数据和算法协同治理等理念 | 腾讯网络法专报
《腾讯网络法专报》汇集每月全球互联网法律政策新动态,涉及范围有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产业、GDRP等各方面,旨在从法律政策角度,为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专业解读。2019年10-11月《腾讯网络法专报》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责任、未成年人保护、人工智能、隐私保护、数据治理、虚拟财产等主题。
本文为精选Part1《人工智能与平台责任篇》,2019年10-11月《腾讯网络法专报》全部内容将于近期发布,敬请关注腾讯研究院公众号。
// 人工智能 //
德国发布AI和数据伦理的75项建议,提出数据和算法协同治理、分级监管等理念
关键词:数据、算法、应用伦理、算法问责
2018年,德国成立了数据伦理委员会,负责为德国联邦政府制定数字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具体指引。2019年10月10日,委员会发布“针对数据和算法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旨在回答联邦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提出来的系列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1]《建议》围绕“数据”和“算法系统”展开,包括“一般伦理与法律原则”、“数据”、“算法系统”、“欧洲路径”四部分内容。德国数据伦理委员会认为,人格尊严、自我决策、隐私、安全、民主、正义、团结、可持续发展等应被视为德国不可或缺的数字社会行为准则,这一理念也应在“数据”和“算法系统”的监管中加以贯彻。
数据治理方面,《建议》指出在一般治理标准指导下,对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分别监管,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建议》提出了治理的一般标准,包括数据质量应符合其用途;信息安全标准与信息风险水平相适应;以利益为导向的透明度义务(Interest-oriented transparency)。因此在数据治理中,必须建立具有预见性的责任分配机制,尊重数据主体以及参与数据生成的各方权利。总体而言,数据伦理委员会认为数据是由各方的贡献生成的,不能基于这种对数据生成的贡献来主张对数据的所有权,但是各方可享有对具体数据生成和利用的参与、共同决定等数据权利,反过来可能导致其他各方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意味着承认服务提供者对服务提供活动中产生的各类数据享有法律权益。具体而言,数据监管需要区别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因为不同类型的数据权利和义务是不同的。就个人数据而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权利应取决于如下因素:对数据生成的贡献程度;在数据权益中个人权益所占的比重;与第三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就非个人数据而言,《建议》提出在欧洲改进数据基础设施(例如平台、应用程序接口标准和示范合同等),防止过度依赖第三方的基础设施,防止欧洲创新型公司外流。此外,《建议》还提出要建立和推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open government data (OGD)),支持私营部门自愿的共享数据安排。同时,委员会认为非个人数据保护在推动数据开放与加强数据保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因此推动开放数据应审慎评估其对数据保护、商业投资的影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国家应优先数据的保护。
数据驱动下,算法治理重点在于“算法监督”以及“算法责任”。委员会认为以人为本,与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系统的可持续性、稳健性和安全性,减少偏见和算法歧视等理念是算法系统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上述基本原则为基础,《建议》提出制定算法评估方案,其核心设想在于建立数字服务企业使用数据的5级风险评级制度,对不同风险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2]:
(1)对于具有较低潜在危害的系统例如饮料制作机,不应监管;
(2)对于具有潜在危害的系统,例如电子商务平台的动态定价机制应该放宽管制,可以采用事后控制机制,加强披露义务等来降低其潜在危险;
(3)对于具有一般或明显危害的系统,应考虑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促使审批、监管常规化;
(4)对于具有相当潜在风险的系统,例如在信用评估方面具有准垄断地位的公司,应公布其算法细节,包括计算所参考的因素及其权重,算法所使用的数据,以及对算法模型的内在逻辑进行解释;
(5)对于自动化武器等具有潜在不合理危险的系统,则应该“完全或者部分”禁止。
对于二级以上的企业,委员会建议引入强制性标记系统(mandatory labelling scheme),要求运营商明确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算法系统。一旦运营商接受该强制性要求,就必须严格遵守该标记,否则其负责人需承担责任。数据伦理委员会将在“可解释人工智能”(旨在提高算法系统,特别是自主学习系统的解释能力)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包括编制和发布风险评估建议、解释数据的处理过程、衡量数据质量以及算法模型准确性的方法等。委员会认为,以上机制能成立的前提是细化GDPR第22条中自动化决策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并在算法规则以外引入外部保护机制,比如加强反歧视立法。此外,《建议》还就政府机构、媒介中介使用算法系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算法系统的责任方面,委员会建议必要时对《产品责任指令》以及其他责任法进行修订,增加针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侵权责任规则。最后,《建议》认为,即使是高度自主的算法系统也不能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经营者使用高度自主的算法技术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与以往辅助设备的负责人需要承担的替代赔偿责任制度相一致。
《建议》是德国数据伦理委员会设立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德国下一阶段数据和算法的监管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鉴于数据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建议》在数据以及算法的监管中突出了协同治理,分级监管,多样化监管的理念。治理手段不仅包括立法和标准化建设,还包括各方利益的协调以及行业自律。此外,数据和算法技术本身也可作为治理工具发挥作用。
《建议》侧重于数据与算法的监管,其所提议的监管举措也引发了对阻碍创新的担忧。如美国数据创新中心认为,该建议将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寒蝉效应:“德国希望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更具有竞争力,但不应该以监管来代替创新。这一政策将使在德的外国企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以这样的方式加强欧洲的数据主权是不可取的。”[3]
德国的立法动议往往影响广泛,此次《建议》中有关数据和算法的监管思路很有可能被纳入欧盟未来的人工智能规则构建之中,并进而影响全球的数据保护政策。德国数据伦理委员会在论及欧洲未来的发展时提出,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面对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更迭,捍卫数字主权(the digital sovereign-ty)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远见,还是一种必要的道德责任外化( expression of ethicalresponsibility)。德国乃至全欧盟成员国,应努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4]
AI
版权保护成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美国USPTO推进AI知识产权政策的明确化
关键词:人工智能、AI生成作品、人类干预、新型数据权利
随着人工智能(AI)持续影响内容创作、发明创造等人类智力创造领域,开始更多扮演“创作者”“发明者”等角色,国际社会已在着力应对人工智能对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8月27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就AI对专利制度的影响,向美国各界公开征求意见。[5]10月30日,USPTO再次发布通知,将公开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了AI对版权、商标及其他知识产权的影响。[6]此次公开征求意见表明美国在AI知识产权保护立场上的重大转变,因为在此前的猴子自拍案中美国法院认为,美国版权法只保护人类作者的独创性表达。美国版权局此前也明确表示,“机器或纯粹的机械程序在没有人类作者的创造性输入或干预的情况下,随机或自动运行而产生的作品”不具有可版权性。此次公开征求意见对AI创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还未可知,但未来USPTO可能就AI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布指南,进一步阐明AI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在此基础上,USPTO最终可能对美国的IP法律和政策作出调整。
就此次公开征求意见而言,USPTO主要关注以下方面。一是专利方面,如何界定AI发明(包括使用AI的发明和AI开发的发明);如何认定自然人对AI发明的贡献,如设计、调整算法,组织数据,训练算法等;开发训练用于进行发明创造的AI程序的公司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AI发明相关的可专利性条件、披露条件、据以实施要件、本领域技术人员、现有技术等事项有何特殊变化;AI专利是否需要新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数据保护。
二是版权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即是AI创作物的可版权性:AI算法或程序在没有自然人参与创作情况下产生的作品是否受版权保护?如果需要自然人的输入和参与,需要贡献到何种程度才能获得版权保护?具体可能有哪些贡献,如设计开发AI算法或程序或者为设计开发做出贡献,为训练算法等目的收集、选择数据,训练AI算法或程序的公司是否可以获得版权?此外,还涉及AI的版权侵权问题,即AI算法或程序通过摄入大量的版权内容来精进其功能,是否属于合理使用?作者能否控制其作品的此种使用方式?如果AI算法或程序生产的作品侵犯了他人著作权,如何分配侵权责任?
三、商标、商业秘密、数据保护等方面,AI如何影响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既有的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是否足以应对在市场中使用AI的风险?AI如何影响数据库、数据集的保护诉求?既有的法律是否足以保护此类数据?
可以看出,美国知识产权界已在全面审视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并寻求应对之策。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也在加速推进AI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建立。例如,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会(AIPPI)已于今年9月通过“关于AI生成作品版权保护的决议”,其中提出了AI生成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标准,核心即是存在人类干预(human intervention)的AI生成作品可以获得版权保护,不存在人类干预的则可获得邻接权保护。[7]12月13日,WIPO也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政策的文件”,就AI相关的专利、版权、数据、设计等问题向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此外,欧盟、日本等也在制定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显然,在当前阶段,AI尚不能在脱离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从AI算法或程序的设计开发,到相关数据的选择和输入,再到对输出结果的控制,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质性参与和贡献。因此现阶段人工智能本质上仍属创作工具或手段。完全可以比照“法人作品”的规定,由设计开发AI算法或程序的公司享有著作权。更进一步,除了版权问题,数据作为AI的核心,未来是否需要针对数据创设新的权利,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
平台责任 //
欧盟法院裁定各成员国可要求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和删除非法内容,《电子商务指令》适用范围引争议
关键词:不法信息、平台监管、Facebook、《电子商务指令》
10
月3日,欧盟法院(CJEU)通过了一项裁定:各成员国可要求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和删除被认定为非法的内容。该裁定源于2016年奥地利绿党议会前主席格劳琴向奥地利法院提起的一起诉讼,要求Facebook爱尔兰公司删除其平台用户发布的一条涉及其本人的诽谤性言论。奥地利法院支持了其诉讼请求,随后Facebook删除了该条内容。该案后上诉到海牙法院和奥地利维也纳高等法院,最终双方均向CJEU提起上诉。CJEU被要求裁定,针对社交网络运营商的删除命令是否也可以扩展到具有相同措辞或相似表述的内容,以及这种删除是否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由于该问题涉及对欧盟法律的解释,CJEU决定暂停诉讼程序,并分别就以下三个问题做出初步裁决:[9]
一是《欧盟电子商务指令》(Directive2000/31/EC)(下文简称《指令》)第15(1)条是否一般性地排除了所有在线中间服务者(OnlineIntermediaries)的主动删除非法信息义务;二是此处所指的非法信息是否不仅包括《指令》第14(1)(a)条的情形[10],还应包括其他相似措辞的等同信息(equivalent meaning);三是若对等同信息也同样适用,那么一旦平台知晓这些“等同信息”的存在,是否也需要采取删除等措施。
针对前两个问题,CJEU认为,不排除让Facebook等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删除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内容及其等同信息。《指令》第15(1)条规定,提供管道、缓存、主机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不需要承担主动监督信息存储和传输的一般性义务,也不需要主动收集表明违法活动的事实或情况。此条免除了特定在线服务商的主动检测与删除义务。然而本案中,CJEU认为,鉴于当下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各成员国应当及时决策并采取必要措施处理非法信息,减小其传播的负面影响。且《指令》在中间服务提供者责任一章中,要求在线服务商在一定情况下对网站内容承担责任的规定旨在制止任何可能的侵权行为并防止任何可能的进一步利益损害。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CJEU认为“任何”意味着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这些措施不应当有地域范围的适用限制。
根据移交的材料,法院认为原告格劳琴所称的“等同信息”是指传达了同样的内容,但是在措辞上与被法院认定为非法信息略有不同的信息,具体而言,可包括侵权人的姓名、侵权行为的情况以及与宣布为非法内容相同的内容等要素。如上解释,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进一步损害,该强制令在内容上也必须扩大到对“等同信息”的监管。否则,此类等同信息很容易逃脱禁令的限制,当事人可能需要启动多个程序去制止这种侵害。
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判断,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一旦平台知晓这些等同信息的存在,是否也需要采取删除等措施,CJEU的答案是肯定的。同时CJEU进一步解释到,网络平台需要删除的是相对于原始内容而言基本不变的内容,因此不需要Facebook进行独立评估,只需使用自动搜索技术即可筛选。
由于《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对于在线平台侵权责任的豁免,不影响法院对其发布特定的行为禁令,这为本案中禁令适用的扩张提供了正当性。CJEU做出上述裁定后,将就该案件的实体问题继续审理。Facebook对该裁定表示强烈的抗议,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法院细化该裁定的具体适用标准,否则这一裁定不仅会加重平台义务,且由于各国在隐私保护和言论自由规则上的出入,还可能面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尴尬。
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已经实施20余年,重点协调各国关于在线中间服务商就第三方非法内容(包括知识产权侵权、诽谤或者误导性广告等信息)免责的条件,《指令》曾为欧洲电子商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营造了较为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伴随商业模式的更迭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欧盟认为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内容监管措施。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正在商议制定《数字服务法案》(The Digital Services Act),根据连任欧委会竞争专员的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在质询会上透露的信息,《数字服务法案》将针对在线内容分享平台设定新的责任,包括强制在线平台删除包含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等在内的非法内容,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该法案如出台将会取代目前的《电子商务指令》,在打击仇恨言论和非法内容方面做出更严厉的规定。[11]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系列裁决也是在为《数字服务法案》铺平道路。
无论是《电子商务指令》的再扩张,还是拟制定的《数字服务法案》,或是已经颁布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GDPR,以及持续推进中的数字税、平台治理规则、互联网反垄断调查等,都是欧盟实施“单一数字市场战略”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欧盟各成员国国内立法和司法的差异阻碍欧盟的统一运作,尤其是妨碍了跨国界数字服务的发展,导致欧盟在互联网领域长期缺乏竞争力。因此欧盟希望通过立法、法律解释以及司法裁判等方式,来构建欧盟内部统一的互联网监管模式,以此促进内部数字市场的发展,并制衡美国等国际互联网产业力量。欧盟法院此次判决进一步体现了这一趋势,尤其是在涉及假新闻、仇恨言论等非法内容的治理上,欧盟频频给美国大型互联网平台施压。欧盟接下来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将可能代表未来一段时间欧盟针对互联网监管的整体思路,值得密切关注。
参考资料
[1]https://www.bmjv.de/SharedDocs/Downloads/DE/Themen/Fokusthemen/Gutachten_DEK_EN.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2
[2]https://algorithmwatch.org/en/germanys-data-ethics-commission-releases-75-recommendations-with-eu-wide-application-in-mind/
[3]https://www.datainnovation.org/2019/10/german-recommendations-for-ai-regulation-will-have-a-chilling-effect-on-ai-adoption/
[4]https://algorithmwatch.org/en/germanys-data-ethics-commission-releases-75-recommendations-with-eu-wide-application-in-mind/
[5]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8/27/2019-18443/request-for-comments-on-paten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inventions
。
[6]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10/30/2019-23638/request-for-comments-on-intellectual-property-protection-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innovation
。
[7]http://www.aippi.nl/nl/documents/Resolution_Copyright_in_artificially_generated_works_English.pdf
[8]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9/article_0017.html
[9]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docid=218621&text=&dir=&doclang=EN&part=1&occ=first&mode=DOC&pageIndex=0&cid=2108884
。
[10]
《指令》第14(1)(a)条规定,信息存储服务提供商在对违法活动或违法信息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员国应确保服务提供者不会因此担责。
。
来源:腾讯研究院
作者:曹建峰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熊辰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1 20:31
【案例】
如何以哲学思考病毒?|德里达鲍德里亚桑塔格韩炳哲
在《星球大战》和《太空入侵者》的时代,艾滋病业已被证明是一毫不费解的疾病:
“在细胞的表面,可发现一个感受器,其中完美地嵌着一包膜蛋白质,如钥匙之于锁。一旦病毒接触这个这个细胞,它就穿透细胞膜,并在穿透过程中瓦解细胞的保护壳.....”
随后,入侵者就以常见于科幻小说作品中的那种外来接管方式,一劳永逸地驻扎在那里了,而身体自身的细胞反倒成了进攻者。本没有保护层的病毒依靠自身携带的酶的鼎力相助。
“将自身的RNA转变成了...DNA,及生命体的大分子。随后,这个大分子穿透细胞核,把自己嵌入染色体,并部分接管细胞的工作职能,指导细胞制造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最终,细胞被自己制造的异类产品所征服,发生膨胀,并破裂死亡,新病毒从中涌出,开始攻击其他细胞。”
该隐喻继续描绘道,随着病毒攻击其他细胞“一群通常能被健康的免疫系统阻挡在外的机会性疾病也开始攻击身体”,而此时,身体的完整和活力已因身体免疫防卫系统崩溃后“异类产品”的大量复制而遭到了损害。“艾滋病人因这种攻击而逐渐变得衰弱,有时在距初次发现病症数月后,但一般是在数年后,就死亡了。”那些尚在挣扎的病人,被描绘成“遭到攻击,显示出该病的告警病症,”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携带这种病毒,随时都可能遭受病毒的最后的全面进攻”。
癌症使细胞大量繁殖;而在艾滋病中,细胞却接连死亡。甚至当艾滋病的这个元模型(白血病的翻版)被改变以后,对艾滋病病毒如何活动的描绘仍重蹈了把艾滋病看作是对社会的侵害的故辙。前不久《纽约时代周刊》打头的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云:“据观察,艾滋病病毒潜伏于细胞中,例行检查无法发现。”该文章公布了这一发现,及艾滋病病毒能在巨噬细胞里“潜伏”多年,“即使当巨噬细胞被艾滋病病毒充胀得几乎爆裂”,艾滋病病毒也不杀死巨噬细胞,而是瓦解其抗病功能,使其不再制造抗体,即身体产生的抵御“入侵物”的化学物质,抗体的出现被认为是艾滋病的绝对可靠的标记。艾滋病病毒现在被认为并不危害它们所寄居的所有细胞,这一观点只增添了艾滋病这个诡计多端、不可战胜的敌人的名声。
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做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正如梅毒这种以“杨梅大疮”之名为好几代医生所熟知的疾病一样,艾滋病也是一种临床的构建,是一种推演。它从一长串并且其长度还在延长的病症中提取一些业已在艾滋病人身上显露出来的症状,来建构艾滋病的病理特‘’征(但对艾滋病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有这些病症,就“意味着”病人所患的是艾滋病。艾滋病的建构有赖于如下两个发明:其一,艾滋病被当作一个临床项目,其二,发明了一种被称作“艾滋病相关综合征”的亚艾滋病,如果病人显示出发烧、体重减轻、真菌感染及淋巴结肿大等免疫系统缺失的“早期”症状或通常是间歇性的症状,就被诊断为患了这种综合征。艾滋病是逐步发展的,是时间的疾病。一旦症状达到某种严重程度,艾滋病的进程就加快了,并带来难忍的痛苦。除了那些最常见的“症候性”疾病(至少就致命性而言,其中一些到目前为止仍显得非同寻常,例如某种罕见的皮肤癌和某种罕见的肺炎),艾滋病的一连串使人衰弱、使人变形并给人带来屈辱的症状还使得艾滋病日益变得意志薄弱、倍感无助,既无力控制又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功能和需要。
就艾滋病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而言,它更像是梅毒,而不像癌症,前者是以“阶段”这个术语进行描述的。以“阶段”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艾滋病话语来说是基本的。梅毒的最可怕的形式是“第三期梅毒”。
被称为艾滋病的那种疾病被认为是三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身体感染了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这是免疫系统遭到侵袭的早期证据,随后,在最初被感染与“告警”症状出现之间,是一个漫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的潜伏期显然不如梅毒的潜伏期长,对梅毒来说,第二期梅毒与第三期梅毒之间的潜伏期可能长达几十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十五世纪梅毒第一次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于欧洲时,它是一种急性病,通常在第二期梅毒就导致患者死亡,有时是数月间或数年间)。癌症却缓慢地发展着:长期以来,人们并不认为它有潜伏期(以“阶段”来对过程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过程中的标准性延迟或中止这些概念,正如它以潜伏这个概念作为补充)。不错,癌症被划分了“阶段”。这是诊断的主要用语,意味着根据癌症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分类,判定其“发展”到了哪一步。不过,它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癌症在体内发展,按照可预见的线路传播或转移。与梅毒和艾滋病比起来,癌症主要是身体地理的一种疾病,而梅毒和艾滋病的定义却有赖于建构一个关于阶段的时间序列。
——节选自《病毒的隐喻》
病毒的转喻和范畴的传染
文/鲍德里亚
译/王晴
出于分类的需要,我曾经提出一种价值三段论:使用价值的自然阶段、交换价值的商品阶段、符号价值的结构性阶段...在这三种阶段之后,是价值的分形阶段...价值的分形阶段,或者说病毒扩散式发展、辐射状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任何参照对象,价值向各个方向、向一切空隙、不借任何参照、只顺从临接性,呈辐射状发散开来。在分形阶段,无论是从自然的还是普遍的角度来说,任何等值的观念都不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个阶段不再有所谓的价值法则,而只有一种价值的传染,价值的普遍转移,或是价值的任意增殖和散布。严格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再谈什么“价值”了,因为这种蔓延或连锁反应,使得所有价值的估定都变得不可能了。又一次,我们可以联系到微观物理学:我们不可能用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这些词汇去进行估算,正如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出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善不再是恶的对立面,而再没有什么能以横纵坐标得以定位。
就像每一个细小的粒子遵循自己的轨道运行那样,每一个价值或是价值的碎片,在模拟的天空中闪耀片刻,划出一道折线,几乎不与其他的线相交,随之遁入虚空。这就是分形化的模式,也是目前我们的文化所具有的形式。
...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传染,消解了隐喻的可能。一切成了转喻,而这种转喻,从其定义上(或其缺少定义上)就是病毒性的,病毒的主题,并非从生物学转引过来,这是因为所有事物都在同一时刻同样地被染上毒性,带入连锁反应,加入随机的无理智的增殖、带上转移的病症。也许是这一点造成了我们的担忧,因为隐喻仍然有它的动人之处,它是有美感的,与差异以及差异存在的幻象进行着互动...
...所有范畴都各自受到了污染,某个领域可以与其他的互换,各种题材混杂而不分。于是,性不再处于性本身之中,而是到处可见...每个范畴都经历了阶段转移,它的本质像在一次次小剂量的顺势治疗下逐渐稀释,而后在溶液整体中变得无限稀少,直到最终消失不见,留下一道没有标记的痕迹,就像水中留下的记忆。
因此艾滋病就是上述现象的一种反映,它与过量的性欲和性快感没有太多关系,它是性侵入生活各个方面而患上的代偿失调,也是性疏散而变为各式各样的琐碎诅咒。性的现状,在原则上发生衍射,进入分形的、显微级的、非人的层面,正式这种衍射,带来了传染病的根本性混乱...
...所有的集成系统、过渡集成的系统,包括科技系统、社会系统,甚至人工智能中的思想本身及其衍生物,它们都倾向于一个极限,即这种免疫缺陷状态。它们为了消除所有外在侵害,就分泌出自身内部的毒性,它们恶性的逆反性。当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这些系统就会自动地发挥逆反与变质的功能,走向自行毁灭。它们的透明性,同样带来了威胁,而水晶是会展开报复的。
身体在受到过渡保护的空间里,会彻底失去自身防御。在手术室里,人们要做与预防处理,让微生物和细菌在其中无法生存。但正因如此,我们见到其中诞生了某些神秘的、反常的、病毒性的病症。这是因为,就病毒而言,它只要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快速繁殖。当世界上原有的传染病都被清除,当世界处于“理想的”医疗看护下,其中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察知的、无可抗拒的病理学,它恰恰诞生于消毒本身。
这是第三种病理学。正如在社会里,我们需要对抗在放任式、和平化的社会的矛盾下诞生的新暴力,在健康方面,我们也需要面对新的疾病,而它们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生日在医疗与信息技术的人造防卫手段下,受到了过度防护。因此,身体暴露给了各种病毒,以及各种的“错乱的”和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这种病理学,不再是因偶然事故和失调状态而致病,而是根植于反常...(因此,)正如我们面对恐怖主义,显然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法,我们在面对艾滋病和癌症时,目前似乎也没有生物学上的解决方法,而这其中有着同样的原理:它们都是系统内部所产生的反常病症,都已某种反作用的毒性,阻断社会体所受到的政治管制以及相对短暂的生物体所受到的管制。
在病程早期,相异性发挥它的邪恶本领,呈现为事故、故障、缺陷等形式。而病程后期的形式,呈现出病毒性和传染性,这种病毒性感染整个系统并无可抵御,因为正是系统的继承本身产生了这种变异。
病毒之所以占领某个身体、某个网络、某个系统,是由于系统清除了自身所有的否定元素,并且分解成一些简单元素的组合。这是因为,那些回路、那些网络成为虚拟的存在、非身体,以至于让病毒在其中肆虐;这也是因为,那些“非物质”的机器远比各种传统机器更容易受到侵害。虚拟性与病毒性相伴而生。这是因为身体本身变成了某种非身体、某种虚拟机器,导致受到病毒侵占。
所以说,艾滋病(与癌症)成为现代病理学何所有致命毒性的原型,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因为将身体交由假体、交由各种基因改造的幻想,使身体的各种防御系统发生瓦解。于是,这样的身体变得分形化,去增殖它的各种外在功能,同时从内部增殖自身细胞。身体开始发生病灶转移:身体内部的、生物的转移、以及与此对称的各种身体外部的转移,即各种假体、网络以及分支。
在病毒的维度下,是你自身的抗体将你击垮。使生物自身的白血病,将它的各项防御瓦解,这恰恰是由于它完全脱离了各种威胁和逆境。彻底的预防,就是致命的。人们正是没有理解这一点,才像应对传统疾病那样使用药物去治疗癌症和艾滋病,而这些病症,恰是源自预防和药物的功绩,源自各种疾病的绝迹,各种病原体形式的消除。我们面对的是第三种病理学,对于它,任何上一代(人们在那时只用考虑可见的诱因与机械性的结果)的药物都是无效的。突然间,所有疾病的源头似乎都成了免疫缺陷(就像所有暴力的源头似乎都成了恐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病毒的供给与策略已经接管了无意识的工作。
——节选自《恶的透明性》
鲍德里亚的病毒学的弱点
文/韩炳哲
译/王一力
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例如历史上的细菌时代,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走向终结。尽管我们对于大型流感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身处病毒时代。有赖于免疫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阶段。从病理学角度来看,21世纪伊始并非由细菌或病毒而是由神经元主导。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S)、边缘性人格障碍(BPS),或疲劳综合征(BS)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它们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一种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学上他者的“否定性”导致的,而是由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引发。免疫科技以抵御外来者的负面影响为基础,从此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20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冷战也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20世纪的免疫学范式中充斥冷战话语,由一种严格的军事化规则控制。攻击和防御主导者免疫学式行动。这种免疫学原则超越生物学范围,到了社会领域,最终蔓延至整个社会层面,一种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对一切陌生之物,都采取防御措施。免疫防御的对象即使这种陌生之物。即使陌生着毫无恶意,即便他不会产生任何威胁,仍然会基于他的“他者性”而受到排挤。
近年来出现的种种社会理论,都明显以免疫学诠释模型为基础。免疫学话语的流行并非意味着,当今社会比过去更加受制于免疫学原则。一种范式自身成为反思的对象,这往往标志着该范式的衰落。近年来已经悄然发生了一场范式的转移。冷战的结束就发生在这场范式转移的进程中。
当今的社会状况,更加彻底地摆脱了免疫机制和防御模式。他者性和陌生性的消失标志着这种转变。他者性是免疫学的根本范畴。一切免疫反应都是面对他者的反应。现在“差异”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应,后免疫学,后现代式差异不再导致疾病。在免疫学层面上,它们是等同的。
过去,在陌生者的刺痛下,产生激烈的免疫反应,如今这在差异性中消失殆尽。陌生者被弱化为一种消费用语。陌生性让位于异国情调、游客们在旅行中寻觅它的踪迹。又可或顾客不再是免疫学式主体...如今所谓的“移民者”不再是免疫学上的“他者”,也不是具有真正危险性,引发恐惧的“陌生人”。移民或难民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威胁。电脑病毒问题也不再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的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学上自我持存。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预防式治疗,即注射疫苗,也同样遵循了否定的辩证法。一小部分他者被允许进入主体,由此出发免疫反应。否定之否定,这种情况不导向死亡,由于免疫反应并未与他直接对峙。人们甘愿对自身施加少许暴力,为了避免更大的、致命的危险。他者的消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精神疾病也遵循一种辩证逻辑,但并非否定的辩证,而是肯定的辩证。它是一种由过量的肯定性导致的疾病状态。
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或者外来者,还来自同类。鲍德里亚明确指出这种肯定性的暴力,他写道:“谁依靠同类存活,也将由于同类而死。”鲍德里亚还论及“一切现存体制的肥胖症”,包括信息、交流以及生产系统。目前尚不存在针对肥胖症的免疫反应。然而鲍德里亚却从免疫学角度描述了同类的极权主义,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弱点,“这绝非偶然,人们现在如此频繁地讨论免疫、抗体、移植和排泄物。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普遍的交流和信息过剩正在威胁全体人类的免疫机制。”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系统中,只能在一种比喻的曾米娜上谈论免疫反应。从严格意义上讲,免疫反应仅针对他者和外来者。同类之间不能产生抗体。在一个由同类控制的体系中,增强免疫反应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区分免疫式和非免疫式的排斥反应。后者来自过量的同类、过剩的肯定性,否定性并未参与其中。它也不是一种排他反应,这种反应需要免疫学上的内部空间为前提。相反,免疫反应则不取决于数量,它只针对他者的否定性。免疫学主体为了保护其内部空间而抵抗他者,将其排除在外,无论他者的数量多么微不足道。
由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肯定性暴力不再是“病毒性的”。免疫反应无法与之沟通。由过量肯定性引发的排斥反应不等同于免疫反应,而是一种消化神经上的功能异常和障碍。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鲍德里亚的暴力理论中充满了论证上的偏差和混乱,因为这种理论试图用免疫学方式描述肯定性或同类的暴力,尽管没有他者参与其中。他写道:“它是一种病毒性暴力,一种网络的、虚拟的暴力。一种温和的却具有毁灭性的、遗传学的、交流式的暴力;一种对立双方共识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病毒性的,因为它并不正面作战,而是通过传染,连锁反应或消除一切免疫力来侧面进攻、和否定性的、历史上的暴力不同,这种暴力通过过量的肯定性发挥作用,如同无止境地蔓衍、生长和专一的癌细胞。在虚拟世界和病毒传播之间存在隐秘的关系。”
按照鲍德里亚的敌对关系谱系学,第一个阶段的敌人以狼的形象出现。他是一个“外部的敌人,法以供给,人们通过修建防御工事和城墙来阻挡敌人。”在第二个阶段,敌人呈现为老鼠的形态。敌人在地下暗中行动,人们通过卫生措施将其清除。经历了第三个阶段即甲虫阶段之后,敌人最终以病毒的形式出现:“第四个阶段是病毒,它事实上活动于第四维空间中。人们很难对抗病毒,因为它们位于系统的中心。”
由此产生了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弥漫于整个空间,如同病毒一般四处渗透,侵入每一处权力的裂痕之中。”病毒性暴力从各自的独特性出发,作为沉睡细胞如恐怖分子一般潜伏在系统中,并试图从内部侵蚀整个系统。恐怖主义成为病毒性暴力的主要形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也构成了个体对全球化发起的暴动。
敌对关系即便采取病毒形式,也依然符合免疫学模式。危险的病毒入侵系统,按照免疫机制的运作方式,系统将病毒入侵者击退。然而敌对关系的谱系不等同于暴力的谱系。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种敌对关系作为前提,相反,它正产生于一个宽容、平和的社会。因此它比病毒性暴力更加隐蔽。
它存在于一个缺乏否定性的同质性的空间内,没有敌我、内外、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世界向肯定性发展,由此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
它们不再来免疫学式他者,而源于系统内部。正是基于它的内在性,免疫反应对它失去效力。这种神经暴力将导致精神上的梗阻,是一种内在的恐怖。它完全有别于那种由免疫学的他者引起的恐慌。美杜莎是最极端形式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另类形式,以至于人们一旦正式她的颜面,便走向毁灭。神经暴力则取消了一切免疫学表征,由于它不含有任何否定性。肯定性暴力不是剥离式,而是饱和式;不是单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们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暴力形式。
病毒性暴力并不适用于描述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等神经症状,因为病毒性暴力依然遵循免疫学模式,区分内外,敌我,并以一个对系统充满敌意的单一的他者为前提条件。神经暴力并不来自一个系统之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无论是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或疲劳综合征都只想一种过度的肯定性。疲劳综合征即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源自过量的同类者。多动症中的“过量”概念也不属于免疫学范畴,它仅体现了肯定性的过度。
——节选自《疲怠社会》
病毒、妒羡、书写
文/雅克·德里达
译/乔迎舟
...痂,哦我的妒羡,并且只要我还没有理解你,换句话说,缝合你,哦我的妒羡,当痂在血液上关闭以形成一个新的皮肤,只要我还没有从你开始爆炸之时理解你,我的妒羡,从你揭露了在最坏情况下的我身体的燃烧鲜活的内在之时,把这种糟糕的身体和痛苦缠扭在一起,这痛苦就像这张脸在最近三天里(1989年6月28日)始终在一张丑恶的鬼脸中瘫痪着,我清醒的鬼脸,只有一只眼睛睁着,并且在我几个月前提及的病毒的影响下被固定,回想起病毒将会始终成为我作品的唯一主题,“病毒是永恒的”,并且我那时讨论电脑病毒也讨论艾滋病,只要我没有写一本文献来标记(marking)我的妒羡的起源和结束,关于一个无可置疑的基础或我的妒羡的我思(Cogito),或再一次书写《一个母亲的忏悔》,我的生活将彻底失败并且我什么也没写,再见了!拯救,不可治愈的面部瘫痪,面具,虚伪,难以了解的伪证罪,黑眼镜,水倒流回我的嘴里,出于残疾的愤怒,增殖(multiplication),在我母亲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上,关于痂,关于词与物,我太热爱词了以至于我没有属于我的语言,只有失败的痂...(18)
...我或许很快会死,我和如此多的抗体相斗争,反对死亡的比赛比我和以斯帖之间的比赛更有力地再一次开始了,但我爱她,这里的异延(differance)就是如果我比她先离开那么她将对此一无所知,她让我昨天在Charcot演讲剧院(Charcot可能是指一位神经学家——译者注)Salpetriere医院(一家13世纪的教学医院——译者注)再次出发,属于我的他的东西,属于他的我的东西,那个尝试去暗示,尽管我并不知道,即这个“病毒”“面部瘫痪”“寒性神经末梢”(frigore peripheral)都曾是我的错误,尽管我曾经寻找过其他东西,在他之前并且要比,我的种种错误更好...
——节选自《割礼忏悔》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mbO_nT3YTy-jW2uqTNSxw
编辑:陈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19 20:13
【案例】
王露璐:应用伦理学如何面对疫情中的道德两难
编者按:
疫情仍然持续,很多学校都陆陆续续通过线上网课的方式,开启了新学期的历程。生活是最好老师,面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思,往往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日前,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就以一封信的形式,寄语“应用伦理学研究”专业课的博士生,从对疫情带来的道德两难出发,揭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要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研究中心
乡村道德与文化振兴研究所所长 王露璐
各位博士生同学: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3日,如果不是这场牵动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此时大家已经陆续返校,我们的博士生“应用伦理学研究”课程也即将开始。考虑到本课程总共只有36个课时,加之课程中有一些思想实验和实践案例的研讨,所以,目前我个人的考虑,我们的课程暂不做在线教学的安排,开学后以延长每周课时的方法完成课程教学工作。大家如有不同意见,可尽快向我反馈。
不过,尽管课程暂不开始,我们还是应当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面对疫情,“应用伦理学”该研究些什么?又应当如何研究?
伦理学在解决道德疑难问题中彰显学科价值
我多次在这门课程中谈到,应用伦理学起步虽晚却发展迅猛,已成为当前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应用伦理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伦理学在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道德疑难问题中显现了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学科价值。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专业层面,不少伦理学学者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和论述;在公众层面,各类媒体(包括自媒体)也出现了大量明显带有道德判断、评价或困惑的报道和表述。疫情中的诸多问题,比如食用野生动物、人群和区域的隔离、慈善捐赠及其分配、防护物资的供给、国际支援和救助等,就其体现的具体道德问题而言,涉及动物食用和利用中的道德正当性和边界、个体权利与公共善、分配正义、危机干预中的程序正义、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等等;就其伦理关系而言,关涉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就其道德规范而言,包括公共伦理、职业伦理、家庭伦理和个体美德;就其涉及的学科分支领域而言,可以说几乎包含了目前应用伦理学的所有分支: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医学伦理、公共健康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缘于此,作为一个伦理学研究者,面对疫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感慨、感伤、感动、感恩等情绪外,都会有一种探究这些问题的学术冲动,这既是一种职业敏感,更是一种社会担当。
困惑来源于理论反思带来的道德两难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与这种“冲动”与“担当”同时出现的,常常是一种“困惑”与“无力”?
这种困惑来自于,我们学习并掌握的那些伦理学的概念工具和知识体系,似乎更多地在让我们陷入某种道德两难:
当我们谴责食用野生动物造成对人类公共健康的巨大损害时,这是否仍然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如果某种野生动物被充分证明对人类的某种疾病具有无可替代的治疗作用,对其进行医学和商业利用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野生动物食用和利用的正当性边界究竟是什么?
为防止疫情扩散,采取隔离措施对感染人群给予限制合乎公共卫生目标,无疑具有充分的法律和道德正当性。但是,对其他人群的隔离和限制,究竟应当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在疫区和疫情严重地区,有限的医疗资源和防护物资采取计划分配还是市场分配更为正当和有效?采用计划分配,如何保证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而又不陷入“平均主义”?采用市场分配,又如何避免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暴利甚至“发国难财”?
在临床治疗中,对于新冠肺炎这种新型疾病的治疗,其医疗手段和药物是否可以突破常规的安全有效性评估程序?在“安全风险”与“生存希望”之间,何者具有优先性?
民间捐赠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标准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孤寡老人捐赠的新闻报道,呼吁“不要再收老人钱”的时候,隐含的逻辑又是否违背了慈善捐赠的“自愿性”,甚至可能走向慈善行为“收入决定论”或“阶层决定论”的“道德绑架”?……
凡此种种,似乎让人不断地陷入困惑的“失语”状态:不是不想说,而是想了以后似乎更不知道该如何说。这种困惑、失语与前述的冲动和担当相互交织,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除了听从号召宅在家中,每天看看各种媒体报道的疫情,为病痛者揪心为治愈者高兴为医护人员点赞,作为一个专业的伦理学人,我们似乎说不了什么真正有用的话更做不了什么真正有用的事……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但是,仔细想来,这样的状态可以说恰恰是应用伦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一种“常态”。20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加之伦理学自身的理论发展逻辑,共同促成了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在我国应用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关于“应用伦理学是什么(学科性质)”、“应用伦理学应用什么(理论资源)”、“应用伦理学应用于什么(学术使命)”、“应用伦理学如何应用(方法论)”等问题的探讨,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应用伦理学产生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态势,即:应用伦理学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它并不是传统伦理学原则的简单应用,更不是单纯的经验研究或一般的Case Study。
面对愈加复杂的道德现象与问题,传统的伦理学理论不足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回答,单一的学科视角和方法也会显得单薄或失之偏颇。但是,作为研究者的个体都不是“万能”的,总有其学科背景和学术积累的局限。面对之前谈及的疫情中诸多道德问题,如果不具备动物学、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背景,我们所提出的很多思考与对策,恐怕只能是“蜻蜓点水”或“隔靴搔痒”,甚至可能贻笑大方。然而,这些相关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又绝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短时间的“恶补”而掌握的。因此,这种“困惑”与“无力”,并非疫情所致,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特征的显现。
疫情当前,一些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也让我们似乎更加迫切地想要寻找答案。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从来就难以对某个现实问题给出标准答案,甚至也无法找到通向答案的唯一通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相反,我们正是要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掌握思考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工具、学术话语和理论方法。这既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要义,也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目标所在。
上述问题,与其说是我留给大家的课前思考,毋宁说是我们应当在课程之前、课程之中乃至课程之后需要一直共同面对和探究的问题。毕竟,伦理学是我们共同的专业选择,她会与我们一生相伴。
无论我们的课程何时开始,希望大家的思考已经开始;
无论我们的课程何时结束,希望大家的思考永不结束。
最后,非常时期,愿大家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好好学习,天天在家;远离病毒,各自珍重。有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或困难,可随时与我联系。
春天见!
王露璐
2020年2月13日
作者:王露璐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等
责任编辑:张伟东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25 20:30
【案例】
摘要
2020年伊始,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时时牵动着国人的心。中国民众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合作,同舟共济,共抗疫情。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诸多中华儿女在应对疫情、救助他人和彼此合作的过程中谱写着令人赞服的美德诗篇。正是他们的行动,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大地上的勇敢、仁爱与廓然大公的精神。
新型冠状病毒,自其粉墨登场以来,令世人诧异不止。而在疫情之下,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程序化措施,人情冷暖,人性美丑也一一呈现。其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那些谱写着美德之善的中华儿女。
随着疫情防控的展开,国人的美德随之呈现。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医务工作者毫不推脱,而是逆行至前线。白衣天使的冲锋陷阵彰显着新时代中国民众的勇敢之德。而在这场救助病人的大型工作中,不仅仅关涉着一线医务工作者,还有处理医疗垃圾的清洁员、日夜不息建造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人、支持医务工作者吃住的个体营业者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国人援助。正是每一个人的不忍人之心、仁爱之美德,点燃着病者生的希望,鼓励着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坚持。中国地大物博,人员众多,如果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将会各奔东西、一盘散沙。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不仅仅有党中央自上而下的领导部署,更有不少民间团体、线上线下间的互相配合。正是每一个人的奉献编织起共命运、同呼吸的大网,人性的广度被扩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廓然大公”精神,这正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根基力量。
一、应对之美德:勇敢
勇敢是古往今来、中外世界共同重视的德性之一。在防控疫情中,首要的美德莫过于医者的勇敢之德。他们直面人与病毒的矛盾,毫不懈怠地治疗病人,研究病源,研制疫苗。因此,社会各界纷纷致敬医者,他们的勇敢堪当应对疫情的首要之德。
然而,古代社会对勇德的重视始终不是首要的。如孔子之勇主要是士大夫之勇,而且受到礼义的限制。与孔子的高贵之勇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勇敢局限于城邦的战士,“除此之外的一切场合、人物、境遇——无论其多么惊心动魄(如海难)——都与勇敢无缘”。在这样的限定下,亚里士多德之勇总是遭遇莽夫式勇敢的质疑。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勇敢也不是首要的美德。
在现代社会,勇敢不再只是某个确定阶层的品质,而是风险社会之下必要且首要的美德。诚然,古代社会面临着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风险,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再如古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般宏大,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随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现代渗透式的风险情境,应对风险的人不再只是战士、有良知的大先生,而是任何可能卷入风口浪尖的职业团体、普通群众。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勇敢最为明显的体现在医生这个职业群体。在疫情发现之初,第一个坚持上报疫情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医生——张继先。她在接诊7名症状相似的肺炎病人时,敏锐地察觉到异样。在2019年12月29日,他和院方同事经过充分讨论,在没有任何权威力量的支持下,坚持实事求是上报,为政府和早监测疫情争取到时间。在张继先以及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各医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应对疫情之初抢占先机。
抗击疫情的医者扩宽了勇敢的含义,勇敢不仅仅是士大夫之气节、士兵的浴血奋战,更是每一个人志向与心力的坚定。尤其在面对未曾谋面的病毒,医者素来拥有的职业志向是他们应对与抗争疫情的根本力量。因而,现代的勇敢是默默无闻但锐气不减的志向较量,是每个个体的自觉担当。医者的勇敢体现出个体的意志之勇,这也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值得学习的榜样。
二、救助之美德:仁爱
孟子曾讲人有四心,其中恻隐之心是仁之起源。恻隐之心的生发是难以捉摸的,在孟子设置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孟子·公孙丑上》)的情景中,今人既不与孺子的父母交好、也没有去想扬名立万之事,只是因为看见孩子要掉入井里而生发“怵惕恻隐之心”。对于危险,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心头一震,但这种惊异会化为“恻隐之心”,回归于救人于水火的仁爱之德。
在疫情防控的实际展开中,救助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他人的救助。为了防止病毒传播,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出门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斩断污染传播途径、保护他人的举措。而每一个人在出门过程中自觉戴口罩,既是对自身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总是双向的,救助本身包含着自救与爱他人两个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自觉地执行防护行为,与疫情的防控情势息息相关。
救助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的行为,人与人之间心理救助紧密相关。不断增长的病患、生命的脆弱、对未来的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孤独、烦闷、消极情绪等等,都是疫情之下的“次发灾害”。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向大众开展疫情相关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是配合疫情、清除社会隐性问题的重要方式。疫情面前,不仅仅是治疗人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保证人心的健康,心理层面的救助工作可谓是国家救助中最富特色的一个举措。
三、合作之美德:廓然大公
疫情防控的工作既有救治之主线,也有统筹协调各方的综合设计。医生奋战在前线,而后方则是亿万个中华儿女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你们站在一起,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如何保证医疗资源的充分供给,如何确保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以及如何调配多方资源支援疫区等等,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更需要相关民众的参与合作。
在疫情爆发后,面对紧缺的口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与生产口罩的企业连线,关心其生产进度和困难。而民间,不少群众积极捐献可以提供的物资。甚至在国内紧缺口罩的情形下,不乏同胞亲自去国外购买口罩,无偿捐献给疫区的医院。口罩生产商、蔬菜供应商、超市便利店等流通部门各尽其能、集谋并力。无形中大家形成相互合作之势,配合着疫情的防控工作。如王阳明所言:“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防控工作,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公民自觉地配合体现出“万物一体”的精神,廓然大公的无私美德。
疫情防控除了需要人与人的合作之外,还警示着我们时时守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入源于人贪吃野生动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病毒的传染正是对人类严正的警示与告诫。社会的进步从来不只是人类利益的增长,更不应以一味地牺牲他物为代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保证动物的福利,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四、小结
时值今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战役还在进行,习近平总书记说道:“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久经磨砺,在无数次面对天灾人祸前都能顽强抵抗,屹立不倒。这不是凭借运气的侥幸赏赐,而是坚韧的决心、善良的仁心和无私的大公精神所促成的必然结果。惟有每一个中华儿女时时坚守美德,我们才能无惧困难、无畏挑战、生生不息。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等
原文链接: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29 19:13
【案例】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作者简介:杨通进,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
〔关键词〕道德行为体 道德承受体 道德关怀 机器人伦理学
道德关怀是指道德行为体对伦理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所给予的某种符合道德要求的待遇(moral treatment)。纵观各民族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即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道德关怀完成了从家庭到家族、从氏族到种族、从种族到民族同胞再到所有人类成员的扩展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的道德关怀范围开始突破人类的界限,逐步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自然。近年来,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已经或即将高度参与并介入人类的私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于是,机器人是否应当获得道德关怀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近年新兴的机器人伦理学(robots ethics)的一个重要主题。为厘清道德关怀的扩展逻辑及其伦理基础,本文拟首先探讨道德关怀的具体内涵,说明区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的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扩展道德承受体与道德行为体之范围的伦理理据及其可能的限度,最后探讨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给人类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
道德关怀(moral consideration或moral concern)这一概念是随着美国圣母大学教授古德帕斯特发表的《论道德关怀》(1978)一文而逐渐成为当代应用伦理学(尤其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的。在《论道德关怀》一文中,古氏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对于所有的行为体A来说,X应当获得A的道德关怀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在古德帕斯特看来,这里的行为体指的是“理性的道德行为体”(rationalmoral agent),而道德关怀指的是“实践意义上的最基本的尊重。当然,就道德实践而言,尊重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只有确认了尊重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的行为要求,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尊重原则的规范意涵。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需首先澄清“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内涵,才能真正确认尊重这一道德原则的具体内容。
在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道德行为体”(moral agent)与“道德承受体”(moral patient)是两个使用比较广泛且具有紧密联系的概念。道德行为体是指“所有具有以下这些能力的存在(being):它能够做出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行为,能够具有责任和义务,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些能力可称之为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判断是非的能力;从事道德慎思的能力,即思考和权衡赞成与反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之道德理由的能力;根据这些道德理由做出决定的能力;发挥必要的决心与意志力来实施这些决定的能力;因未能实施这些决定而对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正常而成熟的人类个体是典型的道德行为体。但是,并非所有的人类个体都是道德行为体。有些人(如儿童、青少年)是不完全的道德行为体,只对其行为承担部分道德责任。有些人(如婴儿、智障人士、胎儿)则不是道德行为体,不对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此,“不能把人类种属简单地等同于道德行为体种属。原因是双重的。首先,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道德行为体。其次,或许还存在非人类的道德行为体”。
道德承受体指的是具有道德承受性(moral patiency)的主体,它们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道德承受体“或许缺乏道德行为体的能力,但却拥有道德行为体对其负有责任的实体身份”,因为后者的行为能够使前者的福利或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或恶化。拥有正常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体既是道德行为体,也是道德承受体,无疑应当获得其他道德行为体提供的“道德服务”。但是,那些只具有部分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如儿童、青少年以及其他不正常的人类个体)甚至完全不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类个体(如植物人、胎儿、婴儿)也是道德承受体。不仅如此,“非人类动物也是道德承受体”,道德行为体在进行道德慎思时有义务把它们的利益也考虑进来。因此,道德承受体的种属比道德行为体的种属要更为宽广。
毫无疑问,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都是道德主体(moral subject),拥有道德地位,都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道德行为体对道德承受体所给予的最基本的道德关怀就是“尊重”。泰勒指出,尊重是一种终极的道德态度。“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某一套规则所制定的要求,他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体现了尊重自然的态度。”因此,判断一个道德承受体是否获得了恰当尊重的标准就是,道德行为体对他/她/它的行为是否遵循了一套恰当的、得到合理证明的道德规则。在泰勒看来,人类(作为道德行为体)要想对自然(作为道德承受体)表现出尊重的态度,那么,他/她的行为就必须要遵守四条基本的道德规则:不伤害(nonmaleficence)、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忠诚(fidelity)、补偿正义(restitutive justice)。如果一个道德行为体在与道德承受体交往时遵循了这些基本规则,那么,他/她/它就是给予了后者基本的道德关怀。当然,遵守这些规则还只是道德行为体的“显见义务”或“初始义务”(prima facie duty)。在不同的道德境遇中,针对不同的道德承受体,道德行为体所需履行的“实际义务”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对于那些既是道德承受体又是道德行为体的义务对象,“尊重”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会更为丰富。
当代环境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明确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这两个概念。传统伦理学的一个未言明的假设是,所有的人都是道德行为体,只有道德行为体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并成为道德承受体。但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却表明,很多人类个体都不具备道德能动性,但是,人们对这些人的行为也要遵守某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同时,随着动物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主流伦理学很难解释虐待动物与随意破坏自然环境等行为的错误。此外,生命伦理学关于“胎儿”道德地位问题(胎儿尚未出生,但是他/她们仍享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的争论更是使得传统主流伦理学的概念工具捉襟见肘。于是,环境伦理学对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所做的概念区分逐渐被当代应用伦理学所接受,并为我们证明作为道德行为体的人对不具备道德能动性的人(作为道德承受体)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表明,拥有道德能动性、成为道德行为体并不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尽管拥有这些能力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条件。这意味着,那些具备道德能动性的存在物可以自动地成为人们道德关怀的对象,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存在物(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不具备道德能动性就自动地把他/她/它排除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扩展了道德承受体的范围。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史怀泽重新界定了善恶的含义。在他看来,“善是保持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人类只有摆脱对自己的偏爱,抛弃对其他生命的疏远,与自己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才是道德的,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这样,史怀泽就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环境伦理学的另一创始人利奥波德则是通过扩展伦理共同体成员的方式来完成扩展伦理关怀范围这一任务的。在《沙乡年鉴》的最后一章“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首先讲述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赛的故事。奥德赛在一次战争凯旋后回到家乡时用绳子吊死了12个女奴。利奥波德解释说,奥德赛杀死女奴的行为并未遭受任何谴责,因为女奴只是财产,不是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把所有的人都纳入了伦理共同体的范围。在利奥波德的时代,人类还未开始考虑大地共同体的问题,而大地伦理学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展伦理共同体的范围,把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自然存在物都视为同一个伦理共同体的成员,“把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因此,根据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大地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以及大地共同体本身都享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纳什则把人类道德进步的历程明确地阐释成道德关怀与权利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
当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虽然人类是唯一的道德行为体,但是,道德承受体的范围却不限于人类。从不同角度扩展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构成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主题。从不同的伦理学前提与价值预设出发,当代环境伦理学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动物(至少是高等动物)、所有的生命存在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自然,并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理论流派: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中心主义(zoocentrism)认为所有的动物都享有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以泰勒、阿提费尔德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应当获得道德关怀的道德承受体;以奈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则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作为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
如果说当代环境伦理学还只是试图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自然存在物,那么,当代机器人伦理学则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范围的接力棒,试图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至人工物——人类设计并制造的机器人。当代机器人伦理学主要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
在现代文明社会,绝大多数人认为,虐待动物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人们用来证明这种错误行为的伦理理据则分为两种:即直接义务论与间接义务论。根据直接义务论,虐待动物的行为之错误之处在于,这种行为或者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解放论),或者侵犯了动物的权利(动物权利论)。间接义务论则认为,虐待动物的行为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由于这种伤害会导致对他人的伤害,而伤害他人是错误的;“不伤害动物”的义务是从“不伤害他人”这一直接义务中推导出来的一种间接义务。阿奎那(1225-1274)较早地表达了间接义务论的观点:“基督教的任何教义看起来都禁止我们去残忍地对待那些不能开口说话的动物,比如,禁止杀死幼鸟;这或者是因为人们会把这种思维转移到残忍地对待其他的人——既然会对动物残忍,也就会对他人残忍;或者是因为对动物的伤害会导致对他人的现世伤害——或是实施行为,或是其他暴行。”因此,在阿奎那看来,对动物的残忍行为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由于这种残忍行为会间接地导致对他人的伤害。康德也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对动物残忍的人在处理他的人际关系时也会对他人残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动物的方式来判断他的心肠是好是坏。”
上述理据完全适用于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人们拥有不虐待机器人的义务,因为,虐待机器人的人会养成虐待其他人的心理趋向与行为习惯。人们对网络暴力游戏的一个普遍担忧是,这种游戏会让游戏者养成“暴力思维”的习惯,并对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变得麻木不仁。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还只是一种“虚拟的暴力”,可是,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以虐待机器人为乐,那么,这种虐待就不是一种“虚拟的虐待”,而是“实实在在的虐待”,是对虐待行为的实施、练习与强化。如果网络中的“虚拟暴力”都值得我们担忧,那么,人机交往中的这种“真实的虐待”就更值得我们担忧了。因此,为了使人们避免养成虐待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我们就必须禁止对机器人的虐待行为。“即使在一个最为宽容的社会里,对虐待机器人的行为施加某些限制也是合理的。”
康德在论证人对动物负有的间接义务时,除了诉诸对他人的伤害理据,还诉诸人性与美德理据。在康德看来,履行对动物的义务,是我们的人性的展现。如果一条狗长期服务于它的主人,那么,“当这条狗老了不能再为它的主人服务时,它的主人应该照顾它,直到它死去”。相反,“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狗没有能力再为他服务而把它给杀了……[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人道的,是对他自身的人性的损害,而他有义务向他人展现出这种人性”。在这里,不承担对动物的义务的行为所涉及的,就不是对他人的间接伤害,而是对人性本身的损害。所以,康德实际上是把关心动物当作人性的内在要素来加以理解和建构的。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必须要把对动物的关怀当作一种直接的义务来认可与承诺。这关乎的不仅仅是动物的“应得”,更关乎人性的完整。康德还认为,关心动物是人性的内在情感,一个人如果“不想扼杀他的人性情感(human feelings),他就必须要以仁慈(kindness)的方式对待动物”。同理,如果人们虐待那些为他们提供服务、能够与他们交流并能遵循人类行为规范的机器人,那么,他们所伤害的就不仅仅是机器人,他们还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减损了人性本身的光辉,丧失了应有的美德。以这样一种形象展现在他人与机器人面前的人,建构与认可的是一种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格。
在讨论人对动物的义务时,康德曾指出,一条狗对它的主人提供的服务,类似于仆人所提供的服务;因此,“当这条狗老了不能再为它的主人服务时,它的主人应该照顾它,直到它死去”。康德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性或互惠性(reciprocity)。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都会对那些长期为其提供服务的家畜或伴侣动物抱有某种感情,人们会把它们当作值得从道德上加以关怀的道德承受体来对待,人们还会为那些“义犬”“勇敢的战马”等树碑立传。未来以强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机器人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无疑将比这些动物还要周到细致,而且,它们还能遵循人类交往的基本礼仪与道德规范。根据康德的相互性理念,机器人享有的道德地位不应比动物更低。
在一些学者看来,机器人即使遵循了人类的道德原则,它们也不是道德行为体,因为它们并不理解那些道德原则的内容,而且,它们并不是在依据道德原则行事,而是按照事先编程的软件系统在运行。这里涉及几个目前正在展开的理论争论。首先,现代伦理学在评价一个行为或政策(以及法律或制度安排)的道德价值时,大多采取后果主义立场,即更多地关注行为的后果,而不去追问行为主体的内在动机或主观意愿。其次,自然人的主观动机比较容易识别,但是,法人(如公司、各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的动机却难以确定,法人没有自然人那样的中枢神经系统,法人本身没有苦乐感受的能力。在对法人的行为或决策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主要根据该行为或决策是否符合或遵循了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原则或价值,是促进还是伤害了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而不是去追问这个法人的“动机”是什么。再次,根据行为主义理论,我们无法直接把握人们的主观动机与内在想法,只能通过其外在行为来推论其主观动机,我们无法在人们的外在行为与其主观动机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因此,在操作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或机器人的外在行为等同于其内在动机。在评价人或机器人行为的道德价值时,我们只需关注其行为的后果,无须追问其主观动机。最后,从决定论的角度看,人的道德决策与机器人的道德决策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人的道德抉择也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前置条件所决定的。当代的机器人伦理学正是从这种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设计与制造“道德机器人”的。因此,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只要机器人做出了与人大致相当的行为,我们就应当把机器人视为与人大致相当的主体来对待。“如果某个行为体在行走、交谈与行为方式方面都足够与我相似,那么,我即使不能合理地认为它拥有心灵(mind),我也有义务把它当作它好像是道德行为体那样来对待。”
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一个争议热点是,我们是否应当研制性爱机器人(sex robots)。美国学者勒维在2008年曾著书预言:2050年左右,人们不仅能与机器人做爱,他们还想与机器人结婚,与机器人保持浪漫的伴侣关系。反对研发性爱机器人的英国学者理查森认为,研制性爱机器人有物化女性与儿童的嫌疑;对性爱机器人的使用和消费会助长人类的性虐待行为,长此以往会使人们对其性伴侣失去同情心;使用和消费性爱机器人会导致性交易的泛滥,进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目前所研发的性爱机器人缺乏“知情同意”的程序设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性爱机器人的使用与消费不仅带有“强奸”的色彩,而且还会扭曲许多人的心灵,使他们误以为在与潜在的人类伴侣发生性行为时,后者的知情同意可有可无。
为了避免出现这些负面的结果,我们就必须要用尊重与知情同意的原则来约束人们与其机器人伴侣之间的交往行为。在与作为性爱伴侣的机器人发生性行为时,人们必须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我们认可的就会是一种包含了“强奸文化”的交往规则,我们与性爱机器人之间建立的就是一种剥削的、不平等的关系。而一种包含了剥削的、等级性的共同体是一种不健康的伦理共同体。因此,作为理性的成熟的道德行为体,我们必须要认可和接受性爱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把人与性爱机器人都看成同一个人机伦理共同体的成员来看待。否则,我们的共同体就会蜕变成某种接受“强奸文化”的畸形的伦理共同体。在这种畸形的共同体中,作为性别歧视主义的态度、制度与行为模式的结果,人与机器人之间的未经知情同意的性活动将变得常态化,“强奸型人格”就会成为人机共同体中的一颗毒瘤侵蚀伦理共同体的健康肌体。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与性爱机器人“比邻而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认可它们的道德承受体地位。如果我们无法否认性爱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那么,我们同样无法否认护理机器人、看护机器人、助理机器人、演艺机器人等社会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我们与这些社会机器人组成的共同体同样属于伦理共同体,这样的伦理共同体不能奉行否认其他成员之道德承受体地位的伦理歧视主义的文化。
如果说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工作重心是扩展道德承受体的范围,那么,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追求目标则是扩展道德行为体的范围。事实上,在机器人伦理学诞生之前,即使最激进的环境伦理学也只是认为,某些高等动物可能拥有某种道德情感或初级的道德能动性。泰勒在提到“非人类的道德行为体”时使用的界定词是“或许还存在”,他心目中的非人类道德行为体指的是其他的高等动物——一种自然的行为体(自然存在物),而非人工的行为体(人工制造物)。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思想家严肃认真地思考或探讨过人工道德行为体的可能性问题。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革命性变革表现为,它首先探讨的就是人工道德行为体(artificial moral agents;AMAs)而非人工道德承受体(artificial moral patients)的可能性问题;它对传统伦理学的最大挑战之处在于,它试图扩展道德行为体(而非道德承受体)的范围。
因此,当代机器人伦理学的目标与使命就是探讨人工道德行为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国际著名的机器人伦理学家、《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2009)一书的作者之一艾伦明确指出,“研发人工道德行为体(AMAs)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制造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体”。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教授、《机器伦理学》(2011)一书的主编安德森亦认为,机器伦理学的核心目标是制造自主的道德机器。事实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伦理学的主流声音是,“AMAs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研究与开发人工道德行为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势不可挡。
鉴于研发具有道德能力的智能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的既定目标,因而很多学者认为,机器人不仅是道德承受体,还能够成为道德行为体。在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萨林斯看来,自主性、意向性、履行责任是成为道德行为体的三个充分条件;将来的机器人能够拥有这三种能力。“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追求这种技术,那么,未来高度复杂的、具有交往能力的机器人将是拥有相应权利与责任的道德行为体。”土耳其学者达文波特亦认为,“与机器一样,人类及其道德都是可计算的,因而,前者可以被建造成一个道德行为体”。
事实上,不仅大多数机器人伦理学家认为,机器人可能成为道德行为体,而且,他们还对道德行为体的类型做了区分。例如,穆尔曾区分了四种伦理行为体。(1)其行为具有伦理后果的伦理行为体(ethical impact agents),即代替人类从事重复、枯燥或危险工作的行为体。(2)隐性的伦理行为体(implicit ethical agents),即安全性与可靠性程度较高、对它的使用不会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体。(3)显性的伦理行为体(explicitethical agents),即伦理原则与规范已经编入其软件系统、且能依据“道义逻辑”进行推理的行为体;获得沙特公民资格的索菲亚已初步具备显性伦理行为体的雏形,而电影《机械姬》中的“爱娃”则是合格的显性伦理行为体,已经属于享有道德行为体地位的机器人。(4)完全的伦理行为体(full ethical agents),即能够做出清晰的道德判断、具有较大的道德自主性的行为体。一般认为,只有具有意识、意向性与自由意志的存在者才能成为完全的伦理行为体。这样看来,第一类、第二类行为体都不能算是道德行为体,因为它们的行为不是出于特定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的引导。第三类行为体符合道德行为体的基本定义,因而能够发展成为人工道德行为体。第四类伦理行为体的标准比较高,只有那些正常的理性的人类个体(而非所有的人类个体)才会成为这类道德行为体。“鉴于我们目前对道德推理、人工智能、认知机制等的理解,我们至多能够制造出显性的伦理行为体,这种伦理行为体能够做出某些道德判断(这些判断不是作为软件预先编入其系统中的),并有能力对它们为何会做出那些道德判断做出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机器人不仅能够成为道德行为体,将来还会是拥有权利的道德行为体。荷兰学者科齐伯格从人机共同体的角度证明了机器人拥有权利的可能性。美国学者冈克尔根据“能够”与“应当”两个变量,指出了谈论机器人权利的四种不同话语表达方式。
第一种观点认为,机器人不能够拥有权利。根据“能够蕴含应当”的定律,机器人不应当拥有权利。因为,在机器人无法理解和享有权利的情况下,说它们不应当拥有权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这种观点完全把机器人当作工具来看待。第二种观点认为,机器人不能够拥有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作拥有权利的主体来对待。第三种观点认为,即使机器人拥有理解和分享权利的能力,它们也不应当享有权利。第四种观点认为,机器人能够理解并看重自己的权利,因而机器人应当拥有权利。冈克尔认为,第一种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是缺乏前瞻性;第二种观点值得同情,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第三种观点是非理性的。他自己赞成第四种观点,并依据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证明了作为他者的机器人拥有权利的可能性。
由上可见,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与机器人伦理学的推动下,不仅道德承受体的范围得到了扩展,道德行为体的俱乐部似乎也增添了新的成员:具有道德思维能力的机器人。从道德行为体的角度看,我们的道德生活空间似乎出现了三类不同的道德行为体:(1)完全的道德行为体(正常而理性的自然人);(2)不完全(显性)的自然道德行为体(青少年);(3)不完全(显性)的人工道德行为体(社会机器人)。我们可以把第一类道德行为体称为完美的道德行为体(perfect moral agents),把后两类道德行为体称为不完美的道德行为体(imperfectmoral agents)。完美的道德行为体享有完整的道德权利;不完美的道德行为体只享有部分道德权利。在道德行为体俱乐部中,完美的道德行为体享有家长的崇高地位与特殊责任,需要承担起对后两类道德行为体的监管责任与教化义务。从道德承受体的角度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五种不同类型的道德承受体:(1)既是道德行为体又是道德承受体的自然人;(2)既是道德行为体又是道德承受体的机器人;(3)作为单纯道德承受体的人类成员;(4)作为单纯道德承受体的自然存在物(动物、植物与生态系统);(5)作为单纯道德承受体的机器人。这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施加给道德行为体的义务的强度是有差别的。
很显然,随着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的范围的扩展,由多种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组成的伦理共同体变得更为复杂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因此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但是,人类研发更为先进和完美的机器人的步伐是无法阻挡的。人为地阻止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也是不明智的。因此,人类(作为完美道德行为体)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理性地面对科技进步给人类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应对这种挑战的方式之一,就是构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伦理文化。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我们认为,这种新型的伦理文化至少应当包含四个重要元素。
第一,伦理拓展主义(ethical expansionism)。面对日益多元的道德主体,我们需要拓展人类的伦理思维空间。伦理思维空间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伦理学维度,一个是作为生活实践的道德关怀维度。在道德实践与学术研究方面,近现代文明都只把人与人的关系纳入了伦理思维的空间。但是,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的神话思维中,人类、各种神祇甚至动物都是道德行为体;神与神之间、神与人类之间、神与动物之间、人类与动物之间都存在着某种伦理关系;神、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交往也遵循着某些伦理原则。因此,在道德主体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激发人类的道德想象力,从学术与实践两个维度拓展伦理思维的空间,重新勘定道德生活的空间范围。
第二,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随着伦理思维空间的扩展,我们发现,人类不仅不再是唯一的道德承受体,也不是唯一的道德行为体。毫无疑问,人类仍将是这个扩展了的伦理大家庭的家长和监护人。这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但是,人类肩负的道德责任也因此越来越沉重了。他不仅肩负着建构和维护人类内部的伦理秩序的重任,还肩负着建构并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伦理秩序的全新使命。在世俗的意义上,人类或许会活得“很累”,但在伦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也将因此而变得更加伟大和崇高,成为一个真正生活在“天地境界”中的“天民”。
第三,后科学主义(post-scientism)。科技的飞速发展把人类“抛入”了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人类的生活既是方便、舒适与高效的,同时又是充满风险的。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科学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陷入科学主义的误区。科学理性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它却不能解答“人类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梦想”的问题。要解决人们之间的价值分歧甚至价值冲突,我们也只能诉诸价值理性,而不能指望科学理性。在对那些将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决策进行选择时,我们需要在技术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实现某种平衡。总之,科学技术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助推器,但是,我们必须站在后科学主义的高度理性地把握文明进步的方向盘。
第四,全球主义(globalism)。技术的进步日益把地球缩小成“地球村”。全球气候变暖、全球金融安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反恐合作等全球问题使得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问题,人类需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认可并践行世界主义的全球共享价值,建构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体制的世界主义的全球制度。只有在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全球制度的保障下,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性的环保合作。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须首先实现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解。机器人技术的研发同样需要达成某种国际共识。一方面,我们应在联合国的协调下,防止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有主导权的国家)把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演变成军备竞赛的新战场。这意味着,应当禁止研发作为杀人恶魔的杀人机器人(killing robots),应当把“不杀害任何自然人”作为一条“底线伦理”植入机器人的软件程序中。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显性道德行为体(不完美的道德行为)的机器人的设计,国际社会也必须要达成某些共识;要把人类社会的价值共识当作这类机器人必须遵循的“底线伦理”。只有这样,未来的机器人才能真正成为人类道德事业的合作者,而非人类的终结者。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虽然日益频繁,但是,许多人在价值观上却仍然深陷在狭隘民族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的窠臼中。狭隘民族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不仅是国家间悲剧的主要根源,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主义文化的重大障碍。要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文化向后人类主义伦理文化的转型,人类就必须首先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价值观上实现从伦理相对主义向伦理普遍主义的转变,实现人类内部的和谐统一,建构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全球主义文化的培育作为构建后人类主义文化的重要抓手。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4-8 21:14
【案例】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用存在伦理学替代理性伦理学
摘要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美国知名伦理学家、传播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研究发现,克里斯琴斯的媒介伦理学思想体系建立在对启蒙主义的“个体理性崇拜”的抵制和反思的基础之上。他主张用“存在伦理学”替代“理性伦理学”,并呼吁基于作为整体的全人类而非具体的个体及个案,探索普遍性的德性原则。他同时认为,传播学界在追求“规范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掉入技术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虚无主义窠臼。
一、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学术思想概述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是美国知名伦理学家与传播学学者,是主流传播(媒介)伦理学学术体系的主要建构者。克里斯琴斯现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传播研究中心、媒介与电影研究中心与新闻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他于1961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8年于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1974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以题为《传播语境中的亚克·艾吕尔的技术思想》(Jacques Ellul's La Technique in a Communications Context)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克里斯琴斯在媒介伦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他主要关注技术哲学、传播理论和媒介伦理的交叉议题。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一直在探讨伦理和伦理决策的本质及其在专业媒体和人类对话领域内的作用。克里斯琴斯对新闻业所具备的独特的社会伦理价值十分关注,并着力分析新闻传播行业在年轻世代的社会伦理养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此外,他也致力于将传播研究的成果引介至宗教和神学领域。他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出版了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除了早期诸如《大众传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80)、《媒介伦理与教会》(Media Ethics and Church, 1981)、《传播伦理和普世价值》(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 1997)等影响力经久不衰的著作之外,近些年,他还陆续出版了《批判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Key Concepts in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2010)、《公共传播伦理》(Ethics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2012)、《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2014)等关注前沿技术哲学理念的著作。他于1983年出版的《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理性》(Media Ethics: 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是全世界范围被采纳最广泛的传播伦理学教材之一,目前该书已经更新至第十版,并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
除学术研究工作外,克里斯琴斯还热心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他不仅担任多个学术期刊的编辑,也是国际伦理圆桌会议(International Ethics Roundtables)的创始成员,该会议曾在南非、阿联酋、印度与中国等地举办。由于其卓越的研究与教学成就,克里斯琴斯还曾荣获“21世纪杰出学者”等荣誉,并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尊敬。
二、媒介伦理学的价值内核
克里斯琴斯教授是当下主流媒介伦理研究学术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主张媒介伦理研究应当超越“信息”和“媒介”等具体框架的限制,在更广阔的认知空间内实现与人类的基础行为伦理的对话。他用“非本质主义的元伦理”这一标准,来界定自己的媒介伦理学的概念内核。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常江: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媒介伦理研究的基础性原则在于探索或者明确各种媒介现象背后的非本质主义的“元伦理”。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要理解什么是“基础”,或什么是“基础性原则”,我们都应该从世界观与预设价值立场出发。我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落脚于以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演绎哲学的权威已是不可辩驳的真理。在那个被我们称作“世界观”或“预设思维”的领域,人们经常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存在着一个“不可移动的推动者”。这意味着我们在溯源或演绎思想时,必须在某处停止或开始。无限的溯源毫无意义。所有思想都应该从某个起点生发开来的。那种主张“无起点”的社会科学的中立性,或者伦理学中那种植根于自然主义的中立性只是一种粗糙的中立性,完全来源于个体经验,很多时候是不真实的。没有什么是中立的,所有的事物都以某种价值的形式存在,因而预设的价值立场作为一种伦理学思维,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以及“信仰”外,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始于一些学者尝试证明的价值命题。众所周知,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他认为科学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完全反映,但事实却完全决定着科学结论,也就是说,科学就是建立在一系列事实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库恩使用“范式”这一术语是因为他深知真相往往与政治或价值交叉在一起,而人们往往研究的只是自变量X的问题,而不是因变量Y的问题。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都是建立在思想之上的。人类自然有其生物学基础,因而可以在DNA粒子的层面上被理解。范式,如同媒介伦理学研究的“元伦理”,是一个包含着理性与客观事实的综合性术语,这一术语可以代表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所有思考。
常江:你还曾提出:我们所倡导的那种以个人自治为问题取向和以社会主义为研究基础的媒介伦理理论,实际上终结了社会变革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研究伦理问题应该从社区或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视角切入。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和女权主义者成为同袍,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非洲社会主义、儒家哲学这些从共同体角度切入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份。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为何会选择去理解这种或那种思想?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吗?或仅仅是为了反对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个体程序主义(individuated proceduralism)?近年来我在写文章时几乎不再使用“社会主义”而更多使用“社区主义”这一术语,因为我发现前者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内涵过于狭窄。我在《媒体伦理学刊》(Journal of Media Ethics)上组织的一期特刊中明确表明:你在社会主义中所主张的,正是人性在自身的哲学中所追求的。我从事这项研究已十余年,也在南非等国家召开过一些会议。总体来说,我发现使用了“公共”或“社区”等术语比“社会主义”更好,因为后者在美国语境中始终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前些年,我和中国的一位学者合作编了一本书,名为《跨文化传播伦理》(The Eth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位中国合作者写了一篇关于孔子的章节,并提出了一个我深表赞同的观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主张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但由这两人的思想出发,却分别产生了西方传统和东方传统下的德性伦理。基于此,我一直认为,西方哲学应该认真对待反启蒙运动,否则结果将会使许多人将社会主义而非个体理性作为思想的起始点。这就是对话的基础。如果我们意图参与跨文化沟通,与非洲社会主义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多种形态的佛教思想对话,我们不得不从一个迥异的起始点出发。
常江:多年来,您似乎习惯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人的行为乃至人的本质进行阐释。为什么选择这一阐释路径?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语言哲学的分析传统进行回顾。首先是教了42年修辞学的教授贾曼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所著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这是我认为关于人性的最好的著述。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语言学传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四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构成了我的各种论述的核心概念体系。在我读博士时候,有一位专门教恩斯特·卡西尔思想的教授,他要求我们必须通读该书。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他专门写了一个“精编本”,题为《人类论》(An Essay on Man),他的论述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你提到的问题联系起来。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能会说,我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研究伦理,超越了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界定。但正如卡西尔在他著名的“四卷本”中指出的,若要研究思想史,我们有三种选择:首先是人类作为动物的理性,这在古典希腊哲学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第二种是人类作为生物的动物性,主要源自达尔文与进化自然主义思想;最后,与前两者相对,卡西尔认为(也是我所主张的)人类的真正定义是作为符号的创造者。我和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正在写一本有关元伦理学的书,其中就有一章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我现在实际上正在探索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从技术哲学中认识到的基本问题之一。简而言之,我们只有将人类视为一种符号的存在,才能实现为不同的形式的交流划分层级,处理不同交流形式所处的环境。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类创建了数学符号、音乐符号、文学符号与视觉符号,它们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尽管我们从启蒙时代时起就被教导物理和数学在知识体系中是“高人一等”的,但实际上没有某一种符号比另一种更优越。语言哲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在理论思考中着眼于人类的“整体性定义”,这在我看来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难发现,克里斯琴斯主张伦理研究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起点,那就是对于个体程序主义和个体理性崇拜的反思。在他看来,人作为一个总体的“符号性存在”是其行为逻辑得以被观察和阐释的基础,也是当代媒介伦理研究的真正的起点。通过这种方式,克里斯琴斯的媒介伦理思想与语言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度的“接合”,并演变为一种富有解释力的研究路径。
三、指向“团结全人类”的伦理思想
克里斯琴斯的媒介伦理思想深受基督教神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努力将一种基于神性的、几乎不可言说的普遍性德性原则,与结构式的科学分析体系结合起来。他坚称“理论是对现状的抵制”,并主张西方视域下的伦理思想应当“抵制”的对象就是启蒙主义所推崇的“个体理性”。
常江:您近年来的思考似乎超出了媒介伦理的领域,而更多关注类似于“什么是理论的本质”这样的问题。能谈谈您思考的成果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到底什么是理论的本质,其实这是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实际上就是对现状的抵制。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并非凭空而来,他的相对论公式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通过对牛顿理论的抵制而来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对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抵制,而哈贝马斯(Habermas)的许多思想都与康德紧密相关。我的意思是说,哈贝马斯并非从零开始,他是从康德式的世界观出发才思考出“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首先确定问题是什么,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历史式的、思想史以及哲学层面的工作。然后,我们再去尝试理解问题,并从问题的对立面寻找策略以解决该问题。而这项工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的。这完全说得通。我们需要自由的人为他们的决定负责,如果人是不自由的,那么负责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总而言之,在希腊古典哲学、功利主义和康德传统中,个人理性一直是伦理学的核心。
常江:所以您的理论建构工作,其实是建立在对个体理性和自主性的抵制的基础上的?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是的。按照此前我们谈到的逻辑,如果自主性与个人理性是传播的核心,那么我就是要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正如爱因斯坦对牛顿所做的那样。我要从现状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我的伦理学理论要有限考虑的是普遍的人类团结而非个体的自主性。我的思考与人类整体休戚相关,这种观念与紧密围绕个体性生发的理论截然不同。我们要团结全人类:并非团结个体,而是所有个体的总和。这就是我们的理论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开始变得复杂的地方。什么是人类?全人类说着六千五百种语言,有着两万个族群,组建成二百多个民族国家。我们可能仅仅知晓其中的两千七百种语言,我们对于其中十六个国家的研究少得可怜。有一种说法是,当我们从海洋中拿出一杯水,海洋仍旧是海洋。对我来说,无论是伦理研究,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都应从普遍的人类团结开始。记得有一次,在牛津休假时,我和《传播伦理与普世价值》(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这本书的合作者迈克尔·特拉伯(Michael Traber)有过一次对话。他说:“我认为你所说的‘人类普遍团结’这是一个原始规范。”我当时就想,天哪!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一度追寻的!真是美好的一天!我期待上帝给我灵光一现,而这句话正是如此!它可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如既往地平淡无奇,但这是一种行动。正是这样,普遍性才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演绎和规范模型脱胎而出。在希腊语中,“原型”(proto)并不是样品,而是制造出的第一个模型,它意味着基础,是一种预设,一种将所有理论观念融为一体的底层信念。在我看来,“团结全人类”就是我的伦理学的原型。
常江:那么,在您看来,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伦理学”这个学科呢?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伦理学不仅是认知层面的理论,也不仅是对方法的运用。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它是一种实践智慧,是一种对自己所能观察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的智慧。我认为,当我们开始进行理论化工作时,需要从个人(即个体理性)开始,然后再努力发现其对立面,接下来制定原则,实施应用,一种伦理学思想就由此而产生。总体上,我不会去过分关注具体的个人、群体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职业伦理。我们领域中有一些学者已经从个体伦理研究转向组织传播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人转变为社群,然后开始研究职业伦理。如果不能让自己的观察超越个体理性,那么伦理的研究将始终无法突破研究者的自我中心思维。
常江:您一直不讳言基督教神学对您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而且也提出过“信念与学习的融合”这一伦理学研究路径。对此,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信念与学习的融合”是我根据理查德·尼伯(H. Richard Niebuhr)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发展出的研究思路。当然,这一思路有可能是错的,所以我建议每个人都去自己尝试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理查德·尼伯的论点包括:基督教的伦理体系是基于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基督教留给西方文化的遗产而非一味去抵抗它。对于西方的伦理学研究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视角,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从古典到现代过程中的转换者。我所要主张的理论改革,就是立足于基督教作为“文化的转换者”这一角色的。当我读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样写的《爱与责任》(Lov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保守的宗教信徒,而是一位变革主义者。我们要想改变一种文化,必须首先了解并尊重这种文化,然后在其之上建立新的神学和制度框架。由于存在着堕落和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的观点必须是整全的,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革命。因此,基督要么是文化的转换者,要么是文化的补充者。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我发现我和我的西方同行们谈论信仰和学习的方式似乎是相同的,只不过使用了略有差异的语言而已。换言之,由于我们都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参与学习的表述和方式才有了对话和通约的可能。我知道在你们中国,文化传统是多种多样的,但在西方,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学者对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看法与我几乎相同。我在一所世俗大学而非神学院工作,因为这是上帝呼唤我的地方,我必须做这个决定。但我有四位毕业生在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以及其他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学习。我在摄政大学(Regent University)、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多特学院(Dordt College)等教会学校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坚持做伦理研究,并以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去探讨伦理学习和信仰之间的调和方式问题。这是西方传统下的伦理学研究者能够形成共同体的原因。
克里斯琴斯并不讳言基督教哲学对自己的伦理思考的影响。在他看来,将爱的对象确定为“全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人,对于明确当代伦理学研究的目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同时也认为,在价值和思维方式高度多元的西方学术界,基督教传统使伦理研究的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他所主张的“信念与学习的融合”作为一种道德认知和学术探索路径,具有独特的价值。
四、媒介伦理学视野下的规范理论
克里斯琴斯一方面认为媒介伦理学的研究必须要以建立可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德性原则为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对于“规范理论”的过分追求有可能令研究者陷入技术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虚无主义状态。对此,他系统性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常江:许多学者认为,传播伦理领域需要一种高屋建瓴且被普遍接受的规范理论。而您却认为,当今的技术社会“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令普遍性的规范理论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您能就这个论断深入谈谈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认为,在传播技术发展迅猛的时代,那种试图追求建立普遍性的规范理论的人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宿命论、技术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历史或技术发展的潮流。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理论的发展将不可避免落入某种虚无主义的形式。因此,问题来了:既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理论化或概念化的普遍价值,以及基于普遍理论的理论,遑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模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从事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自己已经揭示出了一部分答案。如果一个人不是宿命论者,不是空想主义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也就是说,他不认为历史严格遵循自己的演进标准而人力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才能继续有动力去寻找使普世伦理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愿意坚持下去,我可能会说,因为我的世界观从来都不是宿命论。
常江:可是对您有深远影响的基督教神学,还是有着显著的宿命论色彩的。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如果人们打心眼里相信某些特定的“神启”决定或预设了我们的思想框架,那么很显然,他们所要遵循的神学的思维就是“从创造到救赎到末日”这样一条线。然而,我们从圣经中所获知的其实并不是宿命论或毫无意义的选择,而是:历史确实有其发展轨迹,但人的能动性仍然很重要,历史上总有一些运动由于人的选择而指向了某些特定的结论。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指向特定鹄的。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有存在的意义,或者人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尝试去思考人的选择究竟可以如何影响历史这个问题。我坚信,即使别人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相信普遍原则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行事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什么原则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
我认为,在传播或媒介伦理研究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寻找新闻工作者、编辑、记者、教师以及行事正确的学生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同事帕特里克·普莱桑斯(Patrick Plaisance)出版过一本有关新闻业的道德模范的书,他的研究没有仅着眼于人们在新闻上看到的负面消息,而是回答了诸如为什么如今还存在着道德模范、为什么有人能因道德高尚而获得普利策奖、为什么会有人被认为是伟大的记者这样的问题。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些人确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我的立场是:我们做媒介伦理研究不光要做批判,而更应该有教育工作者的自觉。我们必须及时指出人的行为中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不足的,并促使状况发生改变。我相信这是一种以基督教哲学的视角来看待生活的方式。即使堕落、邪恶、罪恶随处可见,但是仍然存在着在道德上向善的人类整体,这种整体包括着我们的思想、意愿与情感。基督教哲学其实告诉我们,人对历史的参与不是毫无意义的,从世界的诞生到上帝的救赎及至最后的审判,其实都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共同行为选择。比如,我认识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常驻埃及开罗,以治疗麻风病人为业的外科医生。他是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毕业于伦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与英国皇家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功成名就,但他选择去了麻风病的高发地。这就是我所见到道德模范:不管我们的认识论如何迥异,这位医师都可以被称为圣贤,他的行为符合一种“普遍性的”伦理标准。
说得太过简略了,但是我基本的观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当我们实践伦理法则时,一定不要抱持着“这个世界毫无希望”的想法,因为我们的德性原则需要某种理性防御系统,需要相信普遍性的东西存在于人类的选择而不是历史的自言自语中。
常江:我想再请您深入谈谈“道德模范”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树立起一些或抽象、或具体的榜样,来“鼓励”更加合乎普遍性德性标准的行为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眼下这个充满争议、混乱和分裂的世界中,人类的历史实践是不可能被完全规范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道德模范。有人可能会辩称:“我的行为并没有破坏整个伦理体系,而只是在质疑某一条特定的伦理法则。”对于我们这些有志于在学术上进行去研究伦理的人来说,的确可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在神学和哲学层面,我们一直以理性原则为指导。我们相信,正如康德所言,只要人类普遍具有理性,那么普遍性的道德标准终会普及开来。当世界崩溃时,与声称“整体的伦理是不存在的或不可信赖的”相比,问题的关键反而在于如何说明我们所推崇的伦理标准是基于人类自身,而非基于人类的理性的。这里面的“人类自身”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理性、行动、情感、精神和思想,以及它们共同构建出的世界观。
在我看来,对于研究伦理学的学者来说,挑战在于我们必须要去系统学习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密尔等人的古典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体系都是建立于对个体理性而不是“整个人类自身”的理解之上的。我们必须站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和选择的角度来看待伦理问题,不能仅对诸如撒谎、欺骗、侵犯隐私、利益冲突等焦点个案进行研究。作为对伦理理论和案例研究的补充,我们必须对像马丁·路德·金、甘地、纳尔逊·曼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杰出人类社会领导者保持兴趣,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尝试为“整个人类”设计更加符合德性原则的发展道路。所以,我的主张很简单:媒介伦理研究要从理性伦理学转向存在伦理学,我们要从人的存在本身出发去思考普遍性德性原则,这就是最重要的教学和研究方式。
常江: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媒介伦理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您在前段时间参加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组织的“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研究”论坛时,也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您能就此给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议吗?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我会建议学者们努力超越对当下历史时期的某些特定的技术导致的某些问题的纠结,而对人类行为在整个技术历史(尤其是数字技术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关注。我同时也认为,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要看到数字技术的标准化力量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不正义”的问题。如今,对于媒介伦理的系统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在新书《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与全球正义》(Media Ethics and Global Justice in the Digital Age)系统性地谈论了这一问题,希望能够给年轻的学者们提供帮助。
对于媒介伦理学视野下的规范理论建设问题,克里斯琴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以存在伦理学替代理性伦理学,从人的存在的本质出发,为“作为整体的人类”设计符合德性标准的发展道路。克里斯琴斯的“全球视角”和“人类视角”,以及他对技术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的角色的深刻洞察,对于我们从事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体系的建构工作,有着显著的参考意义。
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闻界
编辑:贾梦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4-11 16:16
【案例】
“搁置伦理学”是如何可能的 ——解析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
作者简介: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摘要〕“伦理学”已经知识化、学科化了。“搁置伦理学”就是返回知识学科出现之前古希腊哲人的“认识你自己”,这是公共思想感情问题出场之前的“我自己”的问题。海德格尔说它是“存在者”之前的存在或此在的问题,也是“主体间性”出现之前的亲自性问题,它导致“我在出神”,这就是原样的思想,它揭示了私密的自由或个人道德权利才是伦理学的基石,而“人道主义”之说,用高度形式化了的概念,抽空了伦理学的实质内容,导致道德土壤的贫瘠。
〔关键词〕伦理学 人道主义 海德格尔 出神 现象学
一
“搁置伦理学”是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以下简称《通信》)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而话题却是从分析“人道主义”开始的。海德格尔认为,“人道主义”就像“伦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一样,都是在人类早期思想没落之后出现的。但是,“处于伟大时代的希腊人,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如此贴标签,他们甚至没有把‘思想’称作‘哲学’”。出现“伦理学”这个说法的代价,就是直接从有了确定说法的“学问”出发,而抹去了被“主义”所代表的诸多细节元素。这种情形,有些像某些思想从此被认为不属于哲学。
但是,“从哲学出发”,这本身就可疑,因为自从哲学认为自己“知道”开始思考思想问题,就走上了一条知识化的道路。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哲学坚持“存在者”(étant)的总思路,而遗忘了存在(L’être)。关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我们不仅要看到海氏自己的说法,即“本体论的差异”,更要注意其中的时间问题,而他的代表作,叫作《存在与时间》,这个书名意味着重新思考时间,才有新的存在。“存在者”把原本动作或动词含义上的存在名词化、概念化、本体化了,也就是“已经知道”,而“存在”在时间中的含义却是“还不曾”——如果忽视了时间性这一最重要的学理依据,极容易把海德格尔的思想“老庄化”。我认为海氏思想与中国古代道家乃至佛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却也是本质的差异。由于海氏是从“存在”语言的辨析出发的,他的反哲学态度仍旧是一种“哲学”。我的证据在于,从他的分析中可以启发出德里达的“解构”或“différance”,而从道家或佛学中,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通信》对于逻各斯暨“人道主义”的质疑态度,并非政治上的,而是学理上的。“主义”意味着含义已经被完成了,那么关于“什么是人”(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已经被定义好了。这种知识论下的哲学在学理上的失误,并非在于它的定义正确与否,而在于它从确定性出发的态度,忽视了“还不曾”或者“不确定”才是人的原样——海德格尔在这里的洞察力精密且导致晦涩乃至神秘,他走出一条与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的观念”相反的思想之路。如何区分“还不曾”与“已经”呢?区分来自直觉的深刻洞见,而难点在于“还不曾”与“已经”是互相包含分不开的,但若不分开,思想就和存在一样“已经”存在了,而不会问为什么不从“还不曾存在”出发。这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若是从“已经”出发,等于从某种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概念出发,这种概念式思维是逻辑的(逻各斯、“主义”,例如人道主义)。若是从“还不曾存在”出发,就会自动衍生另一个关键问题:从“还不曾”到“存在”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不同于旧哲学的提问方式即询问发生了什么(这会导致概念思维),而是如何发生。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以突然或意外的方式发生,这种降临性相当于把存在瞬间化了。所谓“此在”,就是瞬间的场合与情景,这就远离了宏大叙事而接近了日常生活真实的细节,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思”。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思维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概念式思维,但它仍旧是哲学的或现象学的,是描述性的。这情形从《通信》阐述道理的方式亦可看出,它属于娓娓道来的描述,可以从开头往下读,也可以从结尾往回读——如果我们明白上述道理,“倒着读”也读得懂,不影响阅读效果,因为“确定性的真理”只有一个,但不确定的情形却是开放敞开的,相互之间并没有直线性质的“强因果关系”,拒绝莱布尼茨式的“充足理由律”。海德格尔的《通信》就像在聊天,其中有“没有逻辑的逻辑”或者“没有证明的证明”,可以称它为存在哲学,而不是“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知道,晚期海德格尔批评“技术”,但他所谓“技术”不仅指科学技术,旧哲学既然被知识化了,其思维方式就是技术性的。他写道:“我们必须从思想的技术性解释之中解放出来,这种解释的技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哲学从“已经知道”出发,到亚里士多德,近代以来的“知识论”已经初具规模,那么解释世界就成了一项“技术活”,它持一种理论的态度,它被冠以“科学”之名。但哲学若只是这样思想,就等于放弃了思想的本质。
二
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提法的批评,隐含着他思考哲学问题的方式区别于旧哲学。按照他的思路,学问不应该这样做:你给我一个概念,然后问我它的含义是什么。例如,“什么是伦理学?”这等同于事先就给我设下一个思想陷阱,等于克尔凯郭尔所批评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现在我们进入常见的关于“什么是伦理学”式的争论,争论有“正方”与“反方”。如果我们陷入支持其中某一方的思想情景,那么就已经是一种理论的态度,就是一个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
批评关于“什么是伦理学”式的争论方式,其道理把“伦理学”换成“正义”“美德”亦同样成立。但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如何出场亮相的?海德格尔的回答是,首先得有兴趣、有爱、有欲望、有冲动——这些才是问题的感情源头。这就像问“伦理学是如何可能的”先得有想到“可”的能力,将海德格尔式表达译成法文,例如把possible(可能的)写成“pos-sible”。在这样的思想情景之中,不一定出来“伦理学”,就像由“pos-”发起的法文词,未必一定得是“pos-sible”。也就是说,初始条件是混沌的、复杂的,“伦理学”说法的出现是偶然的,在“伦理学”一词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具有感情冲动之能力,有使用“pos-”构造更多不同于possible的其他词汇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返回自身的原样。就“伦理学”而论,它经历了如此从隐到显的过程,研究原样的思想要从隐出发,敞开隐蔽着的原初因素,这也就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过程。
用以上现象学的态度批评“伦理学”,并非无视人的道德感情,而是说当我们用“伦理学”的标签指代道德感情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忘记感情的血肉而只是将“感情”视为思辨的哲学概念,进入一个从属于逻辑的“帝国”。如果感情完全被逻辑所支配,血肉之躯的感情将不复存在。这种情形,就像用“哲学”取代“爱智慧”。当哲学走上“知识论”的形而上学,“爱智慧”的痕迹就被涂掉了。
现象学继承了康德的精神遗产,即问事物是如何可能的,而非独断论坚持的“必然性”或“已经可能”。要搁置“确定性解释”这一哲学技术活,因为它实际上是不生育的,它已经知道了事物的最终原因,它用“毕生”的精力解释“第一原因”的必然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它的总象征。
于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了这样的思想:就像哲学课或哲学书或哲学会议上可能并没有哲学一样,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人们从事‘哲学’职业,因此人们不再思考”。海氏这句话里有思想(只有原创性的思想才算得上哲学),因为它破坏了“从事哲学职业=会思想”的习俗看法,它建立起脱离这种同一性的思考,或者说建立起一种意外的因果关系。伦理学与“……主义”、与哲学职业是等值的,它用公共性取代私人性。对于个人而言,就像是在经历来自外部世界的精神暴力。在伦理学的公共性中,私人或纯粹个人问题被简单粗暴的“主体性”所取代——从这里出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求助于语言的诗性,因为语言的公共性、可交流性就像上述的“哲学技术活”一样是不生育的,冷冰冰的字面理解就像商品交换一样搁置了剩余的温度或者热情,以至于纯粹的私人性什么都不是,需要伦理学代替自己说话——职业、身份、名字、辈分、等级……这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伦理学,是其公共性,一种来自外部世界事先给予的幸福标准,而一旦达到某个标准,一个人就“应该”是幸福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情形不仅仅属于功利主义伦理学,而且也属于形式主义伦理学,上述公共性都是可交流意义上的标签,就像是纯粹私人感情必须给予如此的符号化、形式化,才可做出伦理学意义上的判断。质言之,公共价值取代了私人价值。
从此海德格尔只说“思想”而不说“哲学”,善于思考等于善于提出思想问题,它在看似差异的领域中建立起等值的精神连线,例如以上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主义、逻各斯、公共性、“应当”或者“普遍必然性”等。那么遮蔽个人或者私人,与漠视纯粹的偶然性之间,也是等值的。而海氏的dasein所强调的ici(这儿)或者là(那儿),恰恰在于描述所发生的(思想)事件是偶然的、突然降临的,海氏把真理诞生的过程形容为闪电、一件危险而惊心动魄的事情。每每在如此境遇下阐述思想时,海氏宁可求助于荷尔德林的诗,而不引用像黑格尔这样的思辨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哲学使思想沦为“技术活”、一种工具。哲学语言成为吞噬语言的“语言”,从而丧失了语言的质朴与纯粹。
三
从以上,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眼里“伦理学”的贫瘠,伦理学的纯粹概念操作法相当于给活生生的个人贴标签。海氏主张搁置作为标签的概念,使人逃离“主体性”——通过怎样的途径呢?虽然海氏很少直接使用“私人”这样的字眼,但是他在《通信》中用很多篇幅讨论“出神”(extatique)或者“痴迷”,此情此景(“此在”)只能在个人身上实现,它就像一张看似平滑的纸在显微镜下却有着凹凸不平的表面。出神是日常生活中的惊讶之能力,就像看似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时刻或者场合,发生着没有原因的深度无聊感,它是不曾发生的发生、实现着看似没有可能的可能——我们每个人不用旁证都能自证这种情形是真实的,“我”(任何一个人)只能记住对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至于该事情对别人来说毫无价值,我根本就不在乎(显而易见,知识化了的哲学无法深入这样的生活细节)。换句话说,人是活在细节之中的,也就是私人化了的“关键时刻”,把这些印象深刻的往昔连接起来,就是我们感受得到的全部人生,它们是碎片化的,相互之间“谁也不挨着谁”,无法整齐划一,更无从加以形式化。
可以把出神的能力上升到纯粹感情的高度,但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没必要施以标签化的“伦理学”,他甚至认为出神的能力(首先使哲学回归“爱智慧”,然后把思想细化为出神,从而使哲学思想场景化了),把人与动植物区别开了。出神的能力使人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一块石头没有它自己的世界,它只是顺其自然,听凭风吹日晒。
如果“自由”这个词已经被人说滥了,以至于不知所云,那么“出神”已经在神采奕奕地显露自由与制度无关或者无法约束,它无处不在,其发生与消失都无法预知,它是真的,也是美的,从而不可能不是善的,而且不存在什么正确与错误的出神,只是出神而已,它是思想与趣味的共同来源。
出神是人身上天然具有的精神能力,它使人的肉身不同于动物有机体。旧哲学连同伦理学都瞧不起“出神”这类小事情,因为只是在某具体场景下有人在出神,“人类一起出神”的场面是难以想象的,即“出神”与沉醉的能力一样,都是高度私人化的,无法普遍化、形式化。出神往往说不出或者难以言表,但却是使我们深有感触的纯粹思想—感情状态,就其性质而言,它往往更接近精神的艺术而非功利。
如果用出神的姿态批评已经职业化了的作为一门学科的伦理学,可以一针见血:伦理学原本与纯粹感情之事密切相关,但现在却从感情内部异化出去了,“伦理学家”只是在就概念讨论概念,陷入思想感情的空前贫瘠,这种可悲的情形,就像当“智慧”忘记爱这个泉源时,思想反倒被叫作“哲学”,但这只是已经知识化了的哲学。
关于人,传统哲学只想到作为“类”的人,它问“什么是人”,这相当于询问人的本质。接下来的,肯定是以定义形式出现的判断句,似乎人是某样普遍的“东西”。在哲学回答“什么是人的本质”的地方,海德格尔的回答像是答非所问:“人在出神”——这不是判断句,而是描述句,属于诗性的语言,它是某种场景化了的“私人语言”,也就是抗拒交流,“人在出神”不可用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加以理解,诗性语言是隐形的,人在出神等于“我在出神”,每个人都是一个“我”,同时却又是多么难以逾越的我啊!也就是不可能被他人完全理解(凡人都是在彼此不可能完全理解的情形下说“我爱你”的,而彼此理解的深度沟通并不可能自动产生爱,爱更像是最高层次上的出神能力,也就是深度的热情),这已经是理解的深渊,而我也不可能彻底理解我自己(这是苏格拉底式的表达),这是自我的深渊。人生永远无法摆脱这双重深渊——“我”对双重深渊出神,而出神是一件不由自主的痛快的事情,因为我正处于原创性的思考过程之中。
在以上的意义上,海德格尔不同意萨特“存在主义”这个说法(对“主义”的质疑如上述),他这样批评萨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论断:“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公式化了:存在先于本质。他在这里所谓存在和本质,都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说的,他说自柏拉图以来,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萨特颠倒了这个命题,但是颠倒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结果,仍旧还囚禁于形而上学命题之中。”简单说,萨特这个命题在说理,而不是在出神。如果结合海德格尔以上谈过的,联系在此的语境,他的意思是说,去思想就是在出神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说理,而正在说理者自己却完全可能并没觉察到自己已经在说理,这就是诗性的表达,它是在描述而非定义与命题。但是,这个过程不可以颠倒过来,不能以说理的方式出神,因为这里的“出神”是假出神,真道理,也就是道理或者“知道”仍旧在出神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萨特先想好了“存在先于本质”的道理,然后再用具有文学色彩的例子加以证明。在这里,一个微妙的却也是本质的差异在于,海德格尔的意思应该是——出神不知不觉地显现出“一大片”貌似“不是道理”的深刻道理,而不应该先有道理(即使是“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反对本质主义的现象学的道理,因此海德格尔在此对萨特的批评,其实也是对胡塞尔著书方式的批评),在预先已经存在的清晰道理或者立场(即使是现象学还原的“中立”立场)基础上的出神,无法进入诗性的描述,因此是一种假出神。
出神,除了是“我在出神”,其“道理”在不知不觉中递补着,比如“我”=亲自、私下,而出神=神往这儿或者那儿,海德格尔说“此在”(l’être-là),最远的成为距离最近的,反之亦然。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不过是一些情绪。但我认为不能将它们等同于自然态度下的感情或者情绪,海氏在此描述的仍旧是思想,是不拒绝情绪的思想,而传统形而上学把情绪排除在外。
在搁置了存在与本质的差异之后,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与其回答“人是什么”,不如说我就在这儿,就在那儿,当然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从此,哲学从天上落到人间,变成纯粹思想感情,而且是片段的、不连续的;第二,那儿、这儿,不仅指空间场合或者此情此景,还是短暂的瞬间,就是说人永远活在此时此刻。要看护好“我”的出神状态,因为这就是我的家,我就生活在此。这可以极好地澄清海德格尔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家的庇护下,住着人。”这里的语言,不是形而上学抽象形式化了的表达式,而是诗性语言,但区别于狭义上的诗歌,而是类似上述“出神”的思想描述,它把自我的身体、时空场景(生活世界)包容在内,与观念论(逻各斯、主义、伦理学或社会科学)分道扬镳。
四
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最难之处莫过于翻译,即澄清术语,比如“être”(being)与“L’existence”的差异,前者原本逻辑系词“是”,是拼音文字乃为形式化语言的最高标志,它什么都不是,却是一切“什么”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只要being开口说话,就得说点什么。这个“什么”就是存在。判断句或者命题,即系词(是)+谓词(什么),作为语言形式的being被赋予“什么”的内容,就是说形式思维与本体论的对立统一模式,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那么,如何翻译being呢?或者死守着其逻辑形式,一“是”到底,那么我们所进入的是逻辑学,而非哲学。哲学思想必须把being落实到存在,也就是本体论。现在海德格尔的问题是,要区别“être”(being)与“L’existence”,不仅形式要落实到“什么”的内容,而且为了使哲学回到生活世界,就得搁置“逻辑形式化”的抽象普遍性思维模式,那么being或者être就异变为l’être-là(此在,在那儿、在这儿),这就是存在哲学所谓的“存在”。海德格尔说,关于存在,中世纪哲学称之为“现实性”,康德认为是经验对象意义上的实在性,黑格尔理解为返回自身的绝对主体性观念,尼采则称之为同样的事情永远回来。可见大哲学家们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理解“存在”(而不是being)的差别,换句话说,即being到底在哪儿(等值于问being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现实(中世纪)、在经验对象(康德)、在绝对主体性(黑格尔)、在永恒归来(尼采)、在“此在”或者出神(海德格尔)——这是价值观—立场的区别。海德格尔之前的哲学家,对存在在哪儿的回答,大都是一个概念或观念论的回答,它们都不是直接描述存在到底在哪儿。尼采的回答是描述性的,即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明天乃至你的一生,还要重复经历——这已经开始脱离观念论了,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l’être-là(此在、出神)受尼采影响极大,但并非重复尼采的思想,因为海氏认为尼采固然敏锐地发现以往的哲学忽略了“重复”本身的思想意味,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扩展重复就是差异,而差异乃“在这儿”或“在那儿”的差异,它们是思想不断出神的效果,进而“发生”与“意外事件”在海氏看来,都属于哲学的关键词。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要如此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在尼采那里,这是一个视角或者价值问题),从而引入了“边缘域”(horizon)或有限性,而界限与差异是等值的。于是,作为抽象普遍形式的时空这类“天上”的问题,被现象学的“括号”搁置起来了,“此在”的现象学成为人的哲学根据,思想就此探讨距离人自身最近的“亲自性”,但海氏认为谈论自己反而是一件最难的事情。就像我以上所说,出神在两个无底深渊。海氏说从“此在”开始思想,走的是一条“无路之路”。在此,思想的姿态就是永远还不曾开始。
在深渊里出神,深渊既是思想感情的又是身体的,在这里有“神”或神距离人如此之近又充满魔力,以至于在深渊里出神是不由自主的。在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刹那之光”,这种新启蒙精神乃陌生的出神,不同于传统启蒙的“我已经知道”(这在康德的文章标题就显示出来了:“什么是启蒙”,他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光”,这属于广义上的柏拉图主义)。新启蒙思想说:最重要的,是拥有我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传统启蒙诉诸一个公共的世界。
这种新启蒙精神朝向纯粹思想感情的亲自性,它是自己的事(是对自己在生活世界所发生事件的感触),甚至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因为进入“之间”等值于进入某种“公共性”,就得操心同时发生、相符、重叠(例如爱情,不仅是自己去爱,还要操心对方是否爱自己)的问题,后者的内容,是广义上的“对象式思维模式”。
于是,“亲自性”引发的新启蒙令人震惊:它的出神或者入迷,从此不再进入公共的“主体间性”,即与引发出神的因素不再有相符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不再受康德式的抽象而普遍的形式(广义上的规则)所约束——亲自性源自一种卢梭式的朝向“抽象的孤独”之冲劲、叔本华式的自由意志。但是,对于此情此景,海德格尔却使用了一种学院式的表达:“存在的真理”——从字面上看,柏拉图主义也会同意这样的表达,但绝不会同意这真理的内容,即上述的“入迷”(思想之路是一条无路之路,或现象学意义上的“永远的开始者”)。
从此,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思路,搁置了附属于“什么”意义上的名称(主体意义上的“谁”),这就是海氏之后欧洲哲学与艺术中的种种关于“死了”(“主体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的说法的学理来源。
如果把海德格尔式的“出神”贯彻到底,就会走到使他本人也会感到惊讶的地步,就是说不仅一切都是一个“随想随明白”起来的过程(读与写),而且它是即刻发生的走神现象,起因或诱因与结果之间,不可能有事先可以预测的因果关系。因此,思想永远还不曾开始(因为它正在发生),永远重新开始——具体如何操作呢?就是把过往曾经发生的理论置于括号之中,存而不论,这意味着只有今天(更具体说,此时此刻、此时此景)才是我(们)唯一真实拥有的时间。进一步说,“发生”比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对于思想而言,重要的是发生的能力(即原创性)。显然,这也搁置了形形色色的目的论(例如,理想国以及康德所谓“人自身就是目的”),因为目的论仍旧属于形式思维或者概念思维。
在哲学史上,属于海德格尔这条精神线索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第欧根尼、奥古斯丁、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叔本华、尼采,他们都强调“我”、意志自由、不确定性,诉诸与“几何学精神”相冲突的“微妙精神”,强调返回原样的精神状态,反对用异化的或一般化了的概念标签取代人本身。
作者:尚杰
来源:道德与文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0-W837LXAWOfiAnhX4piA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4-12 20:13
【案例】
王沪宁:罗尔斯《正义论》序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自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不少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籍之一。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讨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约翰·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又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作为一名从大学氛围中产生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充满了学究气。有的评论家把罗尔斯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思想泰斗相提并论,但罗尔斯与他们有所不同。那些思想大师均著作甚丰,涉猎颇广,而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只有《正义论》一本。《正义论》一书,洋洋洒洒40余万字,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罗尔斯在前言中表示:“在提出关于正义的理论时,我试图把过去十几年中我所撰写的论文中的思想集中起来,使它们成为一种条理分明的观点。”罗尔斯最早于1951年发表了初鸣之作《适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纲要》。基本观念的确立是《正义即公平》(1958年)。其后陆续写出《宪法自由权与正义概念》(1963年)、《正义感》(1963年)、《非暴力抵抗》(1966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等。1969年至1978年。罗尔斯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完成了对全书的整理和加工。在这20年中,罗尔斯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这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完善自己的立论,反驳对方的观点。这样一个过程也使得《正义论》一书显得非常晦涩难懂,概念成群。为了说明一个问题,罗尔斯往往不得不一而再、而三地发掘论据。但他的前言展示了他的思想脉络。
《正义论》,顾名思义,是研讨正义的。正义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第1节)。罗尔斯把正义观的规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正义论》一书共分3编9章,第一编“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第二编“体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编确定的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里较为详尽地反映出罗尔斯高度思辨的正义观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学者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编“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课题。这一编与前两编不同,论述和分析似都与他的正义原则稍微疏远一些。其实罗尔斯认为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最后那一部分的论据,关于正义的理论也会被人误解(前言)。的确,如果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尽管这一编的内容不如前两编那样新奇,但在整个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
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坛、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如此等等。在当代世界,正义依然是人们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时代。罗尔斯热衷于介入正义问题的争论,绝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响应社会的感召。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也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正义现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罗尔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致力于正义研究的,其意图显而易见。如果《正义论》只是纯学术的产物,那它就绝对不会引起这样大的轰动。
罗尔斯对此是明确的,他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种体制。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批判对象。从事实上看,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一)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二)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三)它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用最大量地增加善来解释正当的理论,而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第6节)。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问题等。
既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不敷所用,纰缪甚多,那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正义观呢?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前言)因此,罗尔斯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契约论的方法。契约论在西方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近代的一些思想大家均为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他们的契约思想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震撼人心的作用,但后来时过境迁,契约论让位于功利主义。可以说,契约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经济上的实惠思想。在资本主义体制确立后,功利主义取契约论而代之是不奇怪的。罗尔斯重新举起契约论的旗子,这本身就属别出机杼。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 sition),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始状态纯粹是理性上的设想,在实践历史中无法论证。罗尔斯知道这一点,他说过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第20节)。在确定正义观的过程中,罗尔斯常常部分地倚重于直觉主义,他表示,正义即公平这种直觉观点将把正义的原则着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原始契约的目标(第20节)。原始状态的设计意图是排除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给出一个纯粹逻辑思维的状态,使人们产生正义原则。在原始状态中,所有各方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但是光有原始状态还不足以达成正义的首要原则,还必须设定其他一些条件。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一)正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二)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三)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会及各种背景因素制约,不可能像罗尔斯在理论上假设的那样行动。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第4节)。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一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策11节)。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1节)。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第一个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权等原则,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并无二致。争议最大的是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为在社会上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分配应对每一个人有利,于是人们使权力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来实行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第14节)。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31节),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部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经过这番论述,他重新表述了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享有与人人享有的一种类似的自由权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权利。
优先规则:正义的原则应按词汇式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和(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享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公民能够接受的(第39节)。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的标准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他表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对此现象从未采取过纠正措施,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严重得多,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了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第36节)。罗尔斯点明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缺点,但他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值的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表述得更为清楚。
第一个原则被确定为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按罗尔斯的话讲,这两个正义原则是按照“词汇式序列”排列的,即只有第一个原则被满足后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第8节)。事实上,因为第一个原则已有公论,罗尔斯并没有作什么创造性的论述,他花了大量的气力来论证第二个原则。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他提出了几项论证:(一)反效率原则。在分配上,效率原则是不包含正义原则的,因而一个人得到全部产品的分配或其他不平等分配的方式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而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超越单纯的功利观念(第12节);(二)差别原则。差别原则通过挑出某种特殊的地位来判断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将克服功利原则的不确定性。如企业家比不熟练工人有着更美好的前景,假设他们处在最初状态,那么怎样证明差别的存在是合理的呢?那就必须是这些差别有利于境况较差的人。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差的人,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个原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对西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人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三)连锁关系。这里假定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如果正义原则得到实现,这种连锁关系就会实现。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证,罗尔斯又将第二个原则具体表述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13节)。
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同时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倾向,最基本的就是“平等的倾向”(第17节)。差别原则意味着:(一)补偿原则。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差别原则不等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二)互惠的观念。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原则;(三)博爱原则。在西方社会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这些均为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为了指明西方社会改良的方向,罗尔斯集中在第五章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他先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这包括:(一)分配部门。负责保持价格体系具有切实的竞争能力;(二)稳定部门。负责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三)调拨部门。负责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四)分配部门。负责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大致的正义性(第43节)。社会通过调节这四个部门的活动实现正义原则。
经过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综合考察,罗尔斯又对两个正义原则作了完整的表述(第46节):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
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条优先规则(自由权优先):正义原则应按词汇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这里有两种情况。(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具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人能够接受的。
优先规则(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里有两种情况:(1)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2)过高的储蓄率在总体上能减轻为此而受苦的人的负担。
一般概念:(见前)。
至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了一个概括的轮廓。如前所述,罗尔斯的整个正义理论是改良主义的,即他想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某种修正,以缓和并协调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他在《正义论》中多次表示,两个正义原则规定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或轮廓,改革过程就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第41节)。不过罗尔斯没有直截了当地讨论现实问题,而是将正义原则及其展开部分均置于假设的条件下,并将其提炼到高度思辨的水平。其实越是抽象的理论,其内涵就越大。正义原则、自由优先原则、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差别原则、自由的概念、分配的份额、代际正义问题、自然义务原则、非暴力抵抗、平等的基础等问题均与美国乃至西方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罗尔斯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去描绘这些场景,而将一切现实都转为理性概念,这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学说带来了困难,因而,真正弄清他的学说,需要回顾一下30年来美国的历史。
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一文发表于1958年,《正义论》一书成于1971年。这些年间,正是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贫困问题、抵制越战的浪潮、学生造反……接连发生。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罗尔斯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认真思考和观察这些现象,并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正义观念的澄清。这自然是一个过份学究气的想法,但他作了可观的努力。必须指出,罗尔斯仅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现有范围内进行改良,而不是去改变它。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用正义即公平的观念来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权和贫困两大问题上。这两大问题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他提出的自由权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平等自由等观念,也都是为这些难题寻找出路。正像罗尔斯所表示的那样,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我行我素的权势集团,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配鸿沟,徘徊于街头车站的无家可归的人依然构成对制度的最大挑战,黑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令人担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构成《正义论》一书走红的社会条件。只要这些问题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不会结束。
罗尔斯贬低功利主义正义观,主张正义即公平的理论,还有以下背景;60年代之后,美国以及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争论-叫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两个并不那么协调的价值。新保守主义坚持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过份强调平等会妨碍自由的实现,自由主义者过份强调平等,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危机,而且侵害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突出平等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否则,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然会侵害一部分人的自由。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势力。可以看出,罗尔斯力图协调平等与自由两者。他的第一个原则突出了自由,他的第二个原则突出了平等。不过,他的总体倾向是突出平等的。因为这种争论有制度上的根源,罗尔斯的调和努力是难以成功的。若深入地观察,不难发现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排斥。这也使罗尔斯的理论实际上无法产生他所希望的社会效果。《正义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原因也在此。批评罗尔斯的人提出了种种观点,如:没有理由认为正义原则高于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无知之幕全然是人为的,政治权利绝对高于社会经济权利并不合理,第二个原则是绝对不合理的,等等。恐怕在美国现有的社会基本结构下,正义即公平的理论难以被接受,至少难以被全部接受,因而也难以达到改良主义的目的。
正义的两个原则带有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较多的道德主义因素。一种正义观的产生需要有客观物质条件,它不可能凭空产生,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正义观的改变就无从说起。在西方制度下,两个正义原则没有这样的基础。罗尔斯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个人的道德价值、自律、自我的统一与一致性等上面,而没有找到客观的基础。整个第三编都是用于这一目的的。罗尔斯表示,他要用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义观来解释社会价值,说明体制、社团和交往活动中的内在的善(第41节)。对正义原则的选择使人们产生了正义感和道德感情,而正义感和道德感情又是正义原则得以持续的条件。这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道德论证。罗尔斯还十分强调获得人的“道德人格的能力”(第77节)。这似乎是将正义原则的实现寄托于人的道德升华。但是人的道德和正义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社会条件的革故鼎新,道德革新就无从谈起。有时历史运动表现为道德与历史的交互作用,但纯粹依赖道德恐怕是不完整的理论。
罗尔斯理论的这种缺点还表现在他对用观念变革现实的信仰上。纵观罗尔斯的学说,他认为一种完美的正义观可以改革社会体制,几乎没有提及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条件或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制约作用,忽略了这一点,要改变社会是不现实的。当然。观念不是没有用处,但要与物质生活的发展相结合。也许罗尔斯看到了变革这些条件的难度,所以才寄望于人的内心道德的升华。他在全书最后表示:“心灵的纯洁(如果能够达到的话)将会使一个人明察秋毫,并……通情达理地、自我克制地去行动。”(第87节)人们能获得纯洁的心灵吗?这个简单的问题揭示了罗尔斯本人也许抱有的疑惑。《正义论》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思辨难度颇大的著作,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学术界20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而且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读者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文献。因此,我们应当感谢辛勤迻译此书的谢廷光先生和出版此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文发表时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
作者:王沪宁
来源:微信公众号—华理商业伦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aHiUxt1KNxosfAAwZJCkg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4-17 20:29
【案例】
现代美德伦理学的物理主义挑战及其回应
作者简介:李义天,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4)。
〔摘要〕现代美德伦理学对于道德心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和重视。它对现代规则伦理学的批评以及由此获得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对行为者心理状况的深入理解相关。然而,现代美德伦理学提出的心理知识必须接受现代心理科学的考察与评判。在经验证据的基础上,追求经验性和实证性并最终对包括心理现象做出物理主义的还原和解释,是现代心理科学的抱负与诉求。但是,这种物理主义挑战错误地判断了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并不充分的因果联系。作为某种心理状态的美德品质,既不能也无须被还原为或等同于物理的脑神经活动。关于心灵问题的物理主义还原论立场,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上,都是不充分的。
〔关键词〕现代美德伦理学 心理科学 物理主义 还原论
美德伦理学的源头在古代,但美德伦理学的价值在现代。正是在批评现代规则伦理学,改善现代伦理知识、更新现代伦理范式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逐渐赢得人们的认同。就此而言,真正激发我们重新理解现代道德哲学、反思现代生活状况的,其实是一种现代版本的美德伦理学。这种现代版本不仅意味着美德伦理学在借鉴古代资源的过程中会努力提出一些与规则伦理学相抗衡的命题,而且意味着它会面对古代思想未曾面对的严峻挑战,特别是现代心理科学的挑战。其中,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社会心理学的情境主义挑战以外,更深刻地,还有来自整个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挑战。如果说前者还是现代心理学分支的“进攻”,那么,后者则近乎现代心理科学的普遍“反对”。美德伦理学若要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站稳脚跟,除了正面回应这些挑战之外,别无他法。因此,本文在回顾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心理诉求并梳理现代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取向的基础上,试图表明,美德品质作为道德行为者的特定心理状态,既不能也无须被还原为物理活动。关于心灵问题的物理主义还原论立场,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上,都是不充分的。
一、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心理诉求
对于道德行为者的心理结构及其反应机制,现代美德伦理学始终有着特殊的兴趣。在一般意义上,“美德”意味着行为者的优秀品质(character)。无论它被阐释为“秉性”(disposition)、“态度”(attitude)还是“倾向”(orientation),“品质”总是对行为者特定心理状态的描述。不仅如此,从道德心理层面对规则伦理学展开批判,也一向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主要论题。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1958年发表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不仅从整体上开启了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序幕,而且开启了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心理议题。在她看来,现代规则伦理学存在的两个重大失误皆体现在道德心理层面。
第一,现代规则伦理学忽略了因文化背景变迁而导致行为者心理结构发生改变的事实,仍然固守某些已然丧失心理基础从而缺乏实践必然性的法则概念。安斯库姆指出,诸如“义务”“责任”“应当”这类概念,渊源其实在于基督教。只有在行为者理解并相信这些律法式概念的立法者(即上帝)存在的条件下,它们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才成立。如果脱离了本来的文化背景,这些概念不过保存了它的心理影响,而没有保存它的实质含义,更没有保存它的实践效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规则伦理学只是“一种不再普遍存在的更早期的伦理学概念的残留物,甚或只是这些残留物的衍生品”,所以“义务和责任的概念——亦即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概念——和道德上的对与错的概念,还有‘应当’的道德意义,如果在心理学上是可能的话,都应该被丢弃”。
第二,现代规则伦理学压缩了某些始终活跃并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遮蔽了那些实际存在且本应得到澄清和发扬的美德概念。她说:“在今天的哲学中,我们需要解释,‘一个不公正的(unjust)人怎么就是一个坏的(bad)人’。……但这种解释只有在我们具备了恰当的心理哲学知识后才能完成。因为,用于证明不公正的人就是坏人的论据,需要把公正(justice)描述为一种‘美德’。”现代规则伦理学虽然也同意“不公正的人是坏人”这个命题,但由于它们缺乏“关于人类本性、人类行为、美德品质的类型,以及最重要的,关于人类繁荣的描述”,因而导致该命题“在哲学上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意味着,现代规则伦理学日益表现出对人类经验尤其是人类心理经验的远离——“不管这种远离是因为功利主义者对于实现一种关于满足感的普遍计算的兴趣,还是因为康德主义者对于具有广泛一般性的普遍原则的关心”。对此,安斯库姆感叹道:“我们目前的道德哲学研究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我们拥有一种恰当的心理哲学之前,我们绝对应该先把道德哲学放在一旁。”
出于这样的不满和忧虑,现代美德伦理学在批评规则伦理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道德行为者心理状态的把握,即澄清行为者的真实心理结构,揭示行为者的具体心理反应。既有文献表明,这方面的探讨已成为现代美德伦理研究的重心。比如,菲里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美德与恶德,以及其他道德哲学论文》中延续安斯库姆的思路,着手讨论性格、欲望的伦理价值。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通过其代表作《论美德伦理学》力图证明,理性与情感在实践推理中同等重要。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源自动机的道德》等早年作品中,即系统地发展出一种“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试图将纯粹的内在性理解为美德的根本特征。而在《关怀伦理学与移情》等近期作品中,他又借助近代道德情感主义及其移情理论来为美德的有效性提供辩护。
现代美德伦理学对规则伦理学的批评,以及由此获得的吸引力与美誉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它对行为者心理状况的深入理解相关。或者说,正是对心理问题的强调与谋划,使美德伦理学成为规则伦理学的有力竞争者,从而跻身现代伦理学的主流。如果我们可以说,“对美德伦理学的理解,就是对伦理学的理解;对美德伦理学发展过程的观察,就是从一个特定视角对伦理学演进历史的观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重视现代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现代伦理学版本,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的积极诉求和建构。就此而言,不仅批评规则伦理学的心理缺陷,而且进一步刻画自身的道德心理学理论,便成为现代美德伦理学确立合法性、提升说服力的重要任务。正如罗伯特·劳丹(Robert Louden)指出的:“一个摆在那些针对新近美德伦理学进行细致分析的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在当代作品中,我们仍然缺少已经充分发展的美德伦理学范例。大多数这方面的作品,更多地是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冲击力——其主要目标更多地是批评它所反对的那些传统和研究套路,而不是积极而详细地阐述它自己这种替代性选项到底是什么。”美德伦理学对道德心理问题的关注,不仅是体现自身相对于规则伦理学的特点或优势,更是它完善自身理论结构、进而参与建构现代伦理体系的必要环节。
二、现代心理科学与物理主义还原论
现代美德伦理学虽然是当前伦理学中最为强调道德心理问题的一种理论类型,然而,它所提出的心理知识或相关判断若想成立,却不能仅仅满足于哲学的思辨,而必须接受心理科学的评判。因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对心理问题的解释或理解早已不是哲学的专门领域,而是(甚至主要是)科学的研究对象。
无论是作为哲学意义的心理知识,还是作为科学意义的心理科学,“心理学”(psychology)始终是一门关注和讨论人类心理活动与心理现象的学问。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并没有太多分歧。真正引发两者区别,或者说,真正使心理学逐渐以现代心理科学的面貌登上舞台的,在于后者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独特性。正如加德勒·墨菲(Gardner Murphy)所言,“现代心理学是在19世纪作为实验生理学、精神病学、进化论和社会科学交互作用的产物而兴起的……其方向是由自然科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所引导的”。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条件的相关突破,使得人类对心理问题的研究步入新的阶段。其中,既包括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也包括由于新的方法和工具而带来的新的解释和术语,还包括因此产生的新的研究维度与层次。
一般认为,德国人维尔海姆·冯特(Wilhelm Wundt)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建首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现代心理科学的开端。在实验室研究中,冯特创立并广泛使用内省的方法,训练参与实验的被试者报告自己的感觉和观念,获得他们心理活动特别是意识活动的直接经验,由此探索作为独特实体的人类心理现象的内部结构。冯特相信,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心理学可以将人的意识分解成最基本的元素,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构造、联系和规律,从而了解心理活动的实质。因此,他的学说又被后世称作“构造主义心理学”(structuralism)。
在广泛有效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为心理知识谋求更加确凿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是现代心理科学的起点和原则。这是因为,现代心理科学在现代生物学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基本信念,即,心理活动与心理现象就像其他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一样,都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实在。因此,如同我们可以通过外表来观测人的肢体及其运动,可以通过解剖来观测人的脏器及其功能,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实验或其他方式来观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冯特强调,在心理学中“只有那些直接受到生理影响的心理现象才能成为实验的题材。我们无法对心理本身开展实验,只能在它的外围进行实验,也即对那些与心理过程密切联系的感觉和运动器官进行实验。因此,每个心理实验同时也是生理实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心理科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一种诉诸人类生物基础的物理主义特征。或者说,正是这种诉诸人类生物基础的物理主义的发展,才使得心理学从思辨性的心理知识迈向实证性的心理科学。对此,心理学家毫不讳言,心理学在19世纪经历的深刻变化“主要是由生物学的进步引起的,它在概念和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很多地方受惠于生物学。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开始依靠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认为心理学可以变为一种类似生物科学的科学”。
一旦沿着这条路径起步,现代心理科学便很快发现,内省方法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经验性和实证性要求。因为,“内省”本身的主观性和易错性决定了,这种方法不能消除被试者所提供的报告的随意性和不精确性。毕竟,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没有真正介入被试者的内心,而只是停留于外部,等待对方提供报告;他们至多只能通过统计与均衡来降低这种随意性和不精确性,却不能消除它们。虽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chener)后来将冯特的研究方法给予更精细的推进,并且认为除了内省之外,还“应该在生理学中寻求解释”,但是,受制于心理现象的不可拆解和不可观测,他们所持有的结构主义立场逐渐被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为代表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以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所代替。
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为科学的心理学必须从可观察的经验证据出发,既然心灵无法被直接观测,那么心理科学不应将重点置于一种缺乏物理描述意义的心理元素及其构造上。对功能主义来说,“心灵”或“意识”概念是“无实体的空名”,而只有行为者实际表现出来的认知功能,才是可观测的研究对象。因此,心理科学的对象应当由心理构造转向心理机能。对行为主义来说,心理科学需要彻底抛弃诸如意识、感觉、情绪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完全转向可观察、可测量、可控制的经验行为。在行为主义看来,以往的心理学都是在笛卡儿主义的阴影下预设了某种内部的心理实体,都在“虚构”各式各样的心理结构。但是,真正的、奠基于牢固的物理基础之上的科学只是“对各种可观察变量间的相关方式进行归纳,除此之外再没有了”。所以,心理科学无须承认任何作为实体的“心灵”,无须构造人类的心理结构,而是要通过对经验行为的记录和测量,来澄清人类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机制。这是确保心理科学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唯一有效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替代结构主义,依然是心理科学追求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物理主义信念的内在动力使然。
然而,如果仅仅观测行为而不揭示心理规律,那么,这种理论与其说是心理科学的,不如说是行为科学的。因此,如何在保证经验性和实证性的基础上,既能规避对心理实体的预设,又能把心理活动继续作为一种具有物理主义基础的内部过程加以探究,始终是现代心理科学孜孜以求的方向。在行为主义之后,随着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成熟,心理科学开始重新关注介于外界刺激和主体行为之间的那个部分,即,作为“行为中的有机体的详细的工作模型”的心理活动。这意味着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经心理学(neuro psychology)的登场。它们同样没有抛弃,反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信念。
前者在行为主义的经验性原则之上,建立被试者在行动之前进行信息加工的认知模型与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坚信,关于这方面的探究必须“直到能够确认人类符号系统的各基本信息加工过程的神经机理,我们才能满意于我们对人类思维的解释”。而后者则凭借当代神经科学的进展,以迄今最彻底的方式将心理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将心理活动还原为脑器官的神经活动。在涉及道德问题时,神经心理学常常得出以下结论。(1)与其他类型的观念和判断相比,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对应专门的脑区。比如,“被试在被动观察道德的图片时,前额叶皮层中部的右中部眶额皮层和额中回有选择性地被激活了。当道德的和与道德无关的图片另外配上社会内容(比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被试被要求调整他们自己对道德图片的情绪反应时,前额叶皮层中部也被激活了”。(2)具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对应着具体的脑区。比如,平等的观念与大脑的岛叶皮层的关联程度更紧密,因为它会在被试者接受关于平等问题的测试时变得非常活跃。不同道德观念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与不同脑区之间的冲突相关,而是与大脑的特定脑区相关。比如,“当询问一个既可以作结果论又可以作义务论道德判断的情境时,人们的前扣带回皮层会被激活”,等等。
概言之,随着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深入到生物神经的层次,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特征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心理现象越来越被视为“特定神经回路和整体神经系统”的产物。而在这背后蕴含着也证明着一种立场强硬的“心脑同一论”(mind-brain identity theory),即“主张心理事件或现象与物理事件或现象的同一,认为心理状态本质上可以还原为物理状态,因此,这种理论也常被称作物理主义或物理还原主义”。在这种信念背景下,包括美德品质在内的所有心理现象,越来越频繁地被还原为一种依赖于、随附于甚至等同于神经活动的物理现象。
三、物理主义还原论的逻辑错误
接受物理主义还原的美德概念,尽管有损美德作为心理现象的独立性,但却会在物理层面上保留其实在性。这种做法至少能够保证美德依然作为某种物理实体(而不是作为心理实体)存在。这看上去降低了美德的“格调”,但由于确认了它的生理基础,反倒使得一种经过改造的美德概念在经验性与实证性方面显得更为确凿。
然而,诉诸心理科学的经验证据来证明心理活动的本质在于行为者的生理活动,这样的实验论证是难以成立的。它不仅在论证方法上同其他经验知识一样面临归纳难题与可证伪性,而且在论证逻辑上也错误地判断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充分的因果联系。如果神经心理学是迄今最具物理主义特征的心理学类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表明,即便是如此“先进”的心理科学,其所提供的实验证据也不能证明美德品质只是脑神经器官的生理活动反映。如上所述,无论神经心理学采取何种实验操作方式,它的物理主义结论都是建立在如下推理的基础上:
当心理活动A出现时,脑区R会产生相应的神经活动;当脑区R受损而不能产生相应的神经活动时,心理活动A将无法出现。所以,心理活动A归因于甚至等同于脑区R的神经活动。
仅从逻辑上看,我们便能发现,上述实验证据只不过证明“脑区R产生相应的神经活动”是“出现心理活动A”的必要条件,而不能证明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健全的脑器官对于正常的心理活动不可或缺——关于这一点,早在神经心理学出现之前,哲学家就已能给出类似的判断。而神经心理学的贡献和意义无非在于,它能够借助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技术,尽可能地澄清脑器官的生理活动与行为者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比如,到底是哪个脑区对应着心理活动A,又到底是哪个脑区对应着心理活动B。由此,哲学家所提出的相对抽象的哲学判断就能够得到细化和经验化,从而被奠定在一个更加精确扎实的基础上。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解释也仅仅表明,神经心理学能够说明心理活动“表现为”(be represented as)何种生理现象,却不能证明该心理活动就“归因于”(be attributed to)这种生理现象。因为,要证明后者,亦即证明“脑区R产生相应的神经活动”是“出现心理活动A”的原因,神经心理学的实验设计就不能仅仅表明一个必要条件关系,而是必须提供额外的证据,以证明一个充分条件关系:只要脑区R发生生理活动,就会出现心理活动A。而这方面的经验证据的获得至少应当来自如下实验过程,即通过有意识有计划地人工刺激某个大脑区域而导致行为者形成相关的心理反应。
可是,目前看来,神经心理学在这方面的实验证据并不充分。即使实验者在刺激脑区的过程中能够观察到被试者的心理反应,也不足以断定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毋宁说,这种实验过程恰好说明了,脑器官只是心理活动的生理载体,而真正引发心理活动的“原因”是来自外界事物(在这里恰恰是实验者及其所施加的某种信息或信号)的投射或刺激。实验者在观察心理活动的同时监测到脑神经的某种生理变化,与其说是找到了心理活动的生理原因,不如说是发现了心理活动的生理表征。换言之,神经心理学揭示的脑神经活动,最多只能被证明为心理活动必定具有的随附现象,而不能被证明为心理活动本身的激发因素。相反,仅就上述实验证据——尤其是“当心理活动A出现时,脑区R会产生相应的神经活动”——的字面意义来说,我们似乎更应该断言,心理活动A才是引发脑区R的生理活动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心理活动不能“归因于”生理活动,更不能“等同于”(be identified with)生理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物理主义取向的人常常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比如,“灵魂的各种感受,就它们是诸如激情和恐惧这样的东西而言,是无法与动物的自然质料相分离的,就像一条直线无法与一个平面相分离那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持有还原论立场:“亚里士多德把我们会看作心理事件的东西理解为某种特定形式的物理事件。因此,他告诉我们,愤怒就是心脏周围的血液或热物质的沸腾……处于某种恰当形式的沸腾的血液或热物质就是愤怒”,“亚里士多德的意思似乎是,用现代术语来讲,心理事件随附于物理事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更多是对自然/物理学家的评论,而不是对他自己观点的表达。正是在这番何为愤怒的讨论中,他否定了单纯从质料或形式方面来下定义的方式。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然/物理学家虽不会脱离质料,但也绝不会仅仅依靠质料来说明实体。正如我们既不能将“房子”简单定义为“一种挡风遮雨、祛暑避寒的掩体”,也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石头、砖块和木材”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将作为灵魂感受的“愤怒”视同于血液沸腾等生理现象。所以,虽然“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就像有生命的身体不能等同于它们的质料一样,心理事件也不能等同于其质料”。
其次,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这番话与其说是为了表明,一个心理事件可以被还原为一个物理事件,不如说它是为了表明,一个关于心理事件的描述可以也应当获得物理事件的证据支持。心理事件本身不可直接观察;我们只能通过行为者的表情、行动或言说来描述它们。因此,如果能够在生物层面上(尤其是神经层面上)发现某些随心理事件而出现的物理事件,那么,我们就更有把握判定我们对心理事件的描述是可靠的。但是,“物理状态的出现使得心理描述‘成为真的’,却并没有(有效地)导致被这样描述的那些心理事件、状态或特征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不是“事物A—事物B”的因果关系,而是“理论T—证据P”的逻辑关系。与上一种辩护方案相比,这种辩护虽然略有不同——它没有强调物理事件“在事实上”是心理事件的随附现象,而是强调关于物理事件的描述“在逻辑上”是关于心理事件的描述的支持证据——但它至少同样认为,心理事件不是因物理事件而产生,心理事件有着包含但不限于物理事件的更复杂的原因。
最后,即使事物A与事物B之间确实具有因果关系,也不意味着两者就是同一回事。换言之,即便我们假设“愤怒是由心脏周围的血液或热物质的沸腾引起”,即便随着神经心理学的推进,实验能够证明脑区R的生理活动就是产生心理活动A的原因,也不足以证明心理现象可以被“还原为”生理现象,更不足以证明心理现象就“等于是”生理现象。因为,如果生理现象作为一种物理事件存在,那么,无论它多么精细微小或难以观察,总会占据一定的空间;只要我们的观察技术和观察方法不断进步,那么,它在形状与位移等空间方面的性质就必定会以某种经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心理现象无论是否确实被物理事件引起,它们都是“精神性的”而不在任何意义上占据空间,也不在任何意义上发生位移。严格说来,我们无法借助任何仪器来确认心理现象——因为,所有仪器能够观察到的,都是某个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及其物理表征,而不是这个心理现象本身。所以,在本质上,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属,就算它们可以彼此影响甚至有所决定,也不代表它们能够接受某种还原甚或等同。正如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心理状态……不可能等同于任何物理或化学状态。因为……无论大脑的程序是什么,在同样的程序但完全不同的物理或化学构造的条件下,尽管不一定总具有可行性,但它必定在物理上可以产生某种东西。因此,将我们所讨论的(心理)状态与那种实现方式等同起来,无论如何,从心理学(它是一门相关的科学)的观点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是十分偶然的。这就如同我们遇到火星人,发现他们在所有的功能方面都跟我一样,但我们却因为他们的神经C与我们不同,便不承认他们也有痛苦的感觉。”
四、物理主义还原论的哲学限度
物理主义还原论不仅在实验论证的逻辑上存在诸多缝隙,而且,作为现代心理科学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原则,它还面临着自身在哲学层面的局限,特别是面临着现代心灵哲学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质疑,即“还原论”与“非还原论”之争。在现代哲学史上,针对心灵本质及其与物理事件之间关系的探讨,哲学家更多持有的是“非还原论”,而不是“还原论”。自笛卡儿“身心二元论”(body-mind dualism)以来,“非还原论”立场便占据主流。
笛卡儿之前的古代哲学,虽然已经出现了部分用于表述心理现象的“灵魂”概念,但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希腊时期的灵魂概念,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并不完全等于现代人所使用的心灵概念。尽管心理状态和心理反应可能是灵魂概念的核心部分,但古代的“灵魂”却是一种包括但不限于“心灵”的术语。就其外延而言,“灵魂”不仅涉及通常所说的思维性和精神性的方面,而且涉及营养、生殖、运动等生理性和物质性的方面。将古代的灵魂概念界定为“思维着的自我”从而转变成现代心灵概念的,乃是笛卡儿。在笛卡儿那里,“灵魂”已成为“心灵”“精神”或“思维”的代名词。他的身心二元论为一种在逻辑上独立的、作为实体的心灵概念奠定了基础。由此,现代哲学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围绕人类精神领域展开专门研究,名正言顺地探讨行为者的心理现象、心理能力及其运用过程。研究者表示,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对现代的心灵概念是一无所知的,它更多地来自笛卡儿的哲学。关于心灵和心智的现代论述,即便它们是反笛卡儿的,也都是在笛卡儿的背景下塑造自己的”。
而洛克在描述作为第一性质的物理现象和作为第二性质的心理现象的关系时,也同样倾向于非还原论。他说:“我们周围各种物体的大小、形相和运动,给我们产生了各种感觉来,如颜色、声音、滋味、气味、快乐和痛苦等。不过这些机械的动作,和它们给我们所产生的那些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可离的关系(因为在任何物体的推动力,和我们自心的颜色知觉或声音知觉之间,并没有可以想象的联系)……我们完全不能由物质的原因演绎出我们的心对可感的次等性质所有的那些观念来,而且那些原始的性质虽然在经验上可以给我们产生出那些观念来,可是我们在这些原始性质和次等观念之间亦并不曾发现出任何联系或沟通来。”类似地,狄尔泰更明确地指出:“物理过程与心理过程是不可通约的,从有关自然界的机械秩序的各种事实之中,不可能推导出各种心理事实或精神事实……因为人们不可能使精神世界的事实从属于那些根据机械论的自然观念确立起来的事实。”
尽管随着20世纪神经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特别是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心理与神经的密切关联又刺激了还原论的复苏与发展,掀起了一股新还原论浪潮”,但还原论的有效解释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这一方面体现在并非所有的心理现象都能在技术上被成功地还原为物理现象。也就是说,神经心理学虽然“可以高度精确地描绘某些精神现象的神经联系,特别是像颜色体验、记忆功能和疼痛感觉等感受状态;但像意愿、信仰、主张、权衡过程等精神现象却无法客观化,无法还原为大脑物质元素中点对点式的对应物。我们今天所具备的神经科学知识与测量手段提供不了这样的精神状态与神经网结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越来越少会有人采取神经心理学所预设的“同一论”(identity theory)——“每个心理状态或事件都在数量上同一于某个这样的神经生理状态或事件”,并且“心理的状态和实践实际上发生于其所有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来坚持强硬的还原论立场,而是希望有所折中,通过“随附性”概念(supervenience)等较宽松的方式来描述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或是定义“物理主义”。在这种观点看来,随附性“一般都想表达比还原论弱的命题,它们只使用充分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相应地,物理主义意味着“心理属性都将在概念上随附于物体所具有的物理属性,而且不管有什么心理规律,物理规律都蕴含这些心理规律”。
然而,随附性概念的出现本身就已经宣告了还原论的破产。正如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提示的那样,心理现象随附于物理现象的情况并不代表可以“通过规律或定义而从这种依赖性或随附性中推演出还原性”。因为,随附性至多意味着,一个心理事件必定随附于一个物理事件而产生,但并不意味着,一个心理事件必定因为一个物理事件而产生。戴维斯认为,“尽管我们只能用物理词汇来辨别心理事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纯粹的物理谓词具备与心理谓词完全一样的外延”。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完全搞清楚心理事件与生理事件的全部对应关系。正是心理事件的变异性和不可还原性,使得我们有理由在实践上将行为者及其行动看作心理自主的产物,而不是被生理规律所线性决定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理论与生物或物理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不尽相同。心理现象总有一些东西不能用物理的状态来说明,正如“对嫉妒、无聊、绝望等心理状态的现象学分析与对神经系统中的肾上腺素作用的计量和分析不是一回事;爱情的描述、定义、分析与大脑中的多巴胺的减少和消失的统计也无法同日而语;恐惧和发怒不等于心跳和血压的数字变化”。我们无须为了承认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联系,就一定要将心理事件还原为或等同于物理事件。
结 语
现代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诉求及其引发的挑战,不是专门针对美德伦理学而生,但是,它的出现却使得包括美德伦理学在内的所有强调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之独立性和特殊性的道德理论(乃至哲学理论)都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美德伦理学如果不仅想保持自己相对于其他伦理理论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的优势,而且要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真正站得住脚,那么,它就必须接受这方面的冲击,经历这方面的洗礼,回应这方面的挑战,从而使自身能够有足够的理由作为一种现代伦理理论立足于当下。
美德伦理学的回应看起来至少可以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承认现代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的有效性,进而将美德品质予以经验化实证化的解释。这虽然听起来是让步或屈服,但并非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似乎意味着人们对现代心理科学乃至现代自然科学的强大解释力和有效性的承认。然而,这种策略将使美德伦理学错失对现代心理科学的反思机会,错失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真实存在状态与可能性的反思机会。如果包括美德品质在内的心理事件全都遭遇物理主义的还原,如果我们不能比现代心理科学所发起的物理主义挑战提出更强大的反驳力量,那么,我们丧失的将不仅仅是美德伦理学的合法性,还将是全部伦理学的合法性。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本身就建立在人类的精神自由、独立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因此,面对物理主义挑战,伦理学更有必要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即揭示现代心理科学的物理主义在逻辑和内容上的漏洞或余地,诉诸或援引既有的心灵哲学资源,捍卫心理事件与心理活动的独特性及其不可还原性,进而为美德品质作为人类伦理生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确认存在论空间与理论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无须彻底否定现代心理科学的实在性与经验性,而只需证明这种实在性与经验性的限度即可。毕竟,经历现代心理科学洗礼并做出相关回应之后的美德伦理学,不再是也不必是一种奠基于古代心理知识的伦理理论。相反,它可以在现代心理科学和现代心灵哲学内部发现同盟军。在这个意义上,坚持现代方向但又规避其中的偏激之处,才是美德伦理学在现代社会的存有与发展之道。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2期
作者:李义天
来源:微信公众号:道德与文明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5-4 14:35
【案例】
辉格|二阶美德
按:本文摘录自辉格《群居的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6-301页。
…………………………
普世主义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浙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需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
孤立地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及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地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基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地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力量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仅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编辑:张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5-4 14:35
【案例】
马克斯·韦伯|信念伦理 vs. 责任伦理
按:本文摘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117页。
…………………………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的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然而,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就像费希特正确说过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他们是善良和完美的,他不会以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让别人来承担他本人的行为后果——如果他已经预见到这一后果的话。他会说:这些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信念伦理的信徒所能意识到的“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
但是,问题并未到此完结。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伦理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从道德的观点看,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到什么程度,诸位由以下事情即可了解:人们普遍知道,甚至在大战期间,(齐默尔瓦尔德一派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就主张一项原则,大家可以将它简短地表述如下:“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两个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革命,那我们就选择再打几年战争!”对于下一个问题:“这场革命能带来什么?”每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社会党人会这样回答:还不能说会发生一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在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可称它为社会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会重新出现,只是摆脱了封建成分和帝政残余而已,就是为了这么点稀松平常的结果,他们竟然愿意再来上“几年战争”,若是有人怀有以下想法,倒也情有可原:即便是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坚定信念的人,也可以拒绝这种靠此手段才能达成的目标,在布尔什维克党、斯巴达克同盟和一般而言所有类型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中间,情况也完全如此。当然,如果站在这个立场,对旧政权中的“权力政治家”使用同样的手段加以谴责,那真是十分可笑的事,不管你在否定他们的目的上多么正确。
正是在利用目的为手段辩护这个问题上,信念伦理必定会栽跟头。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对于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的行为,它一概拒绝。但仅仅从逻辑上说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断有这样的经历:信念伦理的信徒突然变成了千年至福王国的先知。举例来说,那些一贯鼓吹“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现在却开始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在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的军官也以这种方式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次进攻将带来胜利,从而也带来和平。”信念伦理的信徒无法容忍这个世界在道德上的无理性。他是一位普遍主义伦理观(kosmisch ethischer)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各位中间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当会记得“大审判官”的一幕,在那里,这个问题被极尖锐地展现出来。即使在目的使手段圣洁化这个原则上做一些让步,也无法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和谐共处,或是判断应当用哪一个目的来圣洁化哪一个手段。
我的同仁福斯特先生(F. W. Forster),对于他不容怀疑的真诚,我本人怀有高度的敬意,但是对于作为政治家的他,我却不敢苟同。他为:若想避开这一困难,采用一个简单的论点即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如果真是如此,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将不复存在。但是,在《奥义书》问世2500年之后,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论点出现,也着实令人吃惊,不但世界历史的全部进程,而且日常经验中每一个明白的事例,都指出真相正好相反。各种宗教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都是由这个相反的真相决定的。神义论的古老问题,正是由这样一个疑惑所构成:一个据说是全能而仁慈的力量,怎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让它充满无辜的苦难、不受报应的不义和无可救药的愚蠢?这个力量或者并非全能,或者并不仁慈或者,左右着我们生活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善恶报应原则——我们可以做形而上解释的原则,甚或是我们的理解力永远不可全及的原则。
因为体验到世界的无理性而出现的这个问题,一直是推动着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印度的“业论”(Karmanlehre)、波斯的二元神教、原罪说、命定说和神隐说(deusabsconditus),所有这些教义,都是由这一问题产生。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对于他们的行为,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往往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
我们置身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每一个领域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各种宗教伦理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希腊的多神教同时祭献阿芙罗狄蒂和赫拉、祭献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虽然他们知道这些神时常处在相互冲突之中。在印度教的生命秩序里,为每一个不同的职业分别规定了一种道德准则,一种“法”(Dhrama),用种姓制度将它们永远分开,从而使它们获得等级制度中的固定身份。生而为这种身份,非待来世再生,便永无摆脱之日。因此这些职业同最高的宗教救赎之善保持着不同的距离。种姓制度以这种方式,允许每一个种姓,从苦行僧、婆罗门到流氓无赖和娼寮中人,都有可能根据各自职业内部自治的戒律,形成自己的法。战争和政治也不例外。各位从《薄伽梵歌》克里西那和阿周那的对话中即可发现,战争也被纳入生命领域的整体之中,“做你当做之事”,这就是说,做那些按武士种姓的法及其规则,有责任去做的事,做那些按照战争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做的事。印度教相信,这样的行为非但不会危及宗教救赎,反而会增进这一救赎。印度武士在遇到英勇战死的时刻,他总是坚信有因陀罗的天堂存在,正像条顿武士对瓦尔哈拉的信念一样。印度的武士之鄙视涅槃,一如条顿人之讥笑回荡着天使歌声的基督教天堂。这种伦理准则的专业化,使得伦理可以通过让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条律,使自己在处理政治方面丝毫不受伤害,甚至可以使这门高贵的技艺得到极大的强化。
…………………………
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在超凡的博爱和圣贤之道方面表现卓绝的伟人,无论他是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来自印度的高贵种姓,从来不采用暴力这种政治手段。他们虽然曾在并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人物,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圣贤人物,依然是同他们最相近的造型。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甚至在教会统治的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教皇的禁令曾一再施于佛罗伦萨,这禁令对于当时的人们及其灵魂得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远远超出了——用费希特的话说——康德的道德判断力所具备的“轻微惩罚”,但是那里的市民仍要同教廷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当谈到这一情况时,写下过一段美好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颂佛罗伦萨的市民,因为他们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还要重要。
如果有人不提自己的城邦或“祖国”(目前这种东西所代表的价值,在某些人看来是令人怀疑的),而是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国际和平”,那么各位所面对的,便是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在讨论中,我从未因为有人提到出生证上载明的日期,便允许自己甘拜下风。但是,某人才二十岁,而我已年过五十,仅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觉得,这是一件足以让我神魂颠倒的成就。年龄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人们至多只能说一件事。如果在这些你认为不属于“无生育力的”亢奋——但亢奋毕竟不是真正的激情——的日子里,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Gesinnungs politiker),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编辑:张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7-20 16:03
【案例】
“互害现象”的道德软约束:贵州公交坠湖案反思
【编者按】贵州公交坠湖案的舆论风潮尚在持续,除了哀悼逝者,更应该反思本次悲剧的深层次根源。当下时代,公众的各种负面情绪堆积,仅靠制度的设计难以完全回应公众的情感诉求。生存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如果超出了人们能够承受的限度,往往会使人产生极度焦虑,进而形成一种戾气。它的不当宣泄则非常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彼此伤害。国家治理有多个面向,群众对国家与政府的想象并不仅基于理性的利益诉求,更基于感性的情感回应。法理情的深度结合,才有益于国民心灵秩序的重构。
“互害现象”的道德软约束
何中华 | 山东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负和博弈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人的社会交往中出现的 “互害”现象,乃是社会转型期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附带结果,它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客观基础。
从西方历史嬗变的过程看,商品经济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发生学的关联。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孕育出市民社会。这就难免导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同意的。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由此决定了“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只能表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重申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为就像恩格斯说的:在市民社会, “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历史地派生出来的市民社会,内在地隐含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表面上的“正和博弈”即所谓“双赢”,掩盖着背后的“零和博弈”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零和等局”关系,把人们抛入了一个利益互斥的竞争格局之中。这也正是达尔文所揭示的 “生存竞争”的生物学逻 辑,之所以适用于市民社会的重要原因。市民社会的逐步建构,使人与人之 间的利益矛盾愈益尖锐化,它往往表征为“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这恰恰构成“互害”现象得以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命题,构成改革开放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项具有前提性的历史任务。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其制度安排上的优越性;但也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普遍本质的约束,从而难以完全克服和避免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和局限性。这一点, 也已经被诸多经验事实所证明。
重建社会信任与重建道德
“互害”现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则是无意的,但都是对他人的戕害,甚至连人们之间彼此的冷漠也应属于“互害”的一 种。但这些表现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同信任的匮乏和阙如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互害”现象虽然归根到底是由利益冲突造成的,但又往往是通过这种冲突衍生出来的若干环节实现的。今天,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而其最终缘于背后的利益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互害”现象正是人们之间彼此不信任的一个直接结果;而“互害”的发生,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交易费用的急剧升高, 社会治理成本居高不下。因为信任危机及其基础上的“互害”现象,造成了社会的失序,要回归有序化,就不得不支付高昂的额外代价。这是目前在社会治理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社会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交往都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信任就像空气一样,是人们的生存所须臾不可离的绝对条件。如果说空气是人的自然条件,那么信任则是人的社会条件。其实,人际交往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靠法律和契约维系的,而是靠彼此的信任维系的。法律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以国家意志表达的社会契约,而我们知道,任何契约的缔结和达成,都必须以缔约双方的彼此信任作为绝对前提。所以,信任比契约具有更为原初的意义。
就整个社会的治理来说,靠他律得来的秩序和靠自律得来的秩序,其结果和效应是大不相同的。他律倘若有效,就一定不能离开有效的外在监督, 譬如法律就是这样。但它的局限性在于,一旦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变成了 “共谋”,就势必造成法律的失灵。此类情形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并不少见。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的自律性,能够使人达到“慎独”的境界,它甚至无需外在的监督和强制,而是依靠道德意识所保障的人的自觉自愿、自然而然,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因此,就社会治理而言,道德的成本最低。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维系自身的有序化,所依靠的主要是道德观念及其所强化的伦理秩序。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道德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惩治于“已然”。可以说,道德治“未病”,法律治“已病”。在社会治理中,制度安排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法律具有刚性的作用;但法律却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应该说,这句话很好地凸显了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局限性,它们只有通过彼此的互补,才能使一个社会形成公序良俗,走向健全。
同法律相比,道德的确有其“柔弱”的一面。作为一种柔性的力量,道德可谓是一个社会的“润滑剂”。儒家的“儒”字,其原初含义就同道德的这一特点有着某种一致性。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诠释:“儒,柔也。”儒家以德性为鹄的,其思想就体现着一种柔性的智慧。法国近代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根“苇草”虽然“脆弱”,却代表了人的尊严。因为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帕斯卡尔看来, “道德”是“能思想的肢体的开端”。既脆弱又是尊严的根基,正是道德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康德的“善良意志”是“软弱无力”的,它不过是“软 弱无力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偏好。马克思批评说: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但道德的软弱性并不是其缺点,而恰恰是其优点。所谓“软弱”,仅仅意味着对于道德命令的遵循和违反的两可性,而这正彰显出道德选择之崇高和尊严的原因所在。正因为道德律令是“软弱”的,所以才能彰显出遵循它的人的 崇高和尊严。市民阶级的偏好仅仅是“任性”,而不是“意志自由”。对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市民社会孕育的精神乃是启蒙现代性,而康德所强调的“善良意志”则属于信仰的领域。康德之所以立志“为信仰保留地盘”,正是为了同启蒙精神保持思想上的距离。
在现有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如何缓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便最大限度地弱化或消除“互害”现象呢?强化法律约束和调节这样一种刚性的力量,加快国家的法治化进程,无疑是标本兼治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从更深层和更长久着眼,除了法治之外,还需要加强道德的软约束。社会信任危机说到底源于道德的衰弱,因为道德是支撑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石。我们今天面临着重建社会信任的紧迫任务,说到底有赖于重建道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基础对于道德起着某种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利用道德的力量来优化社会治理,以保障人际交往走向健全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特殊难题,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
寻求“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首先需要我们对道德教化的可能性抱有足够的信心。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 预设,的确凸显了市场经济的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但预设毕竟是预设,它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找不到一个 纯粹“经济人”的。现实中的人总是受到错综复杂的变量的影响和规定,没有谁能够绝对地按照单一的预设行事,相反总是在诸多变量的交互约束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中既包括经济动机,也包括非经济动机,诸如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甚至个人偏好等。这意味着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人的选择始终都存在着某种可能性空间,都不是由单值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也不例外。
此外,人是具有可教化性的。儒家坚持的人的可教化性信念,为我们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中借道德路径改善并优化人的交往模式提供了信心。在儒家那里,人的可教化性最终源自性善论的人性论预设。譬如孟子持“善端”说,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
因此,“互害”现象的道德应对,乃是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一个可能的选项,而且它有着其他选项譬如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在道德应对中,儒家文化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资源。像“义利之辨”,并非一味地拒绝利益,而是主张要仔细地甄别利益。在儒家看来,利益可区分为合乎道义的利和不合乎道义的利,道德的约束就体现在避免不当得利,即所谓“义然后取”,也就是“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所谓“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亦即俗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义”、此“道”乃是不能或不应突破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见利忘义”,是“君子爱财, 取之无道”以至“无度”,这就必然使人们之间的交往陷入尔虞我诈、相互敌对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贪婪无疑是当下社会矛盾紧张和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消极后果是社会的恶性竞争和无序状态。
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把任何一种尺度变成宰制和支配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唯一尺度都是危险和有害的,无论这个尺度是经济的、政治的,抑或是文化的。当年我们曾经发生过教训,譬如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什么问题都被归结和还原为阶级斗争,并为此付出过惨重的历史代价。但若把金钱尺度独断化,同样是偏颇的。马克思指出:对于西欧来说,“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在这一时期, “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于是,“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从历史上看, 资产阶级通过把市场逻辑推向极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正是市场经济及其逻辑走向独断化的必然结果,但它决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应有的状态或格局。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认为:“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只有避免市场逻辑的独断化,才有可能使人们获得向善的信心。因此,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效地防止市场逻辑的僭越,乃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对市场逻辑适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构成道德应对策略得以确立的客观基础。
如果说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础是道德, 那么道德的基础则是信仰。所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互害” 现象,从道德应对的角度看,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特别是坚定信仰,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得以持续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建立一种虔诚的信仰?决不能小看精神的力量、心灵的力量,它能够使人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具有免疫力。在一个充满各式各样诱惑的时代,离开了虔诚的信仰,我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免疫力。
值得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坚定的信仰说到底离不开实际生活和文化氛围。在某种意义上,信仰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习得和在特定文化氛围中陶冶出来的。没有生活的磨炼和文化的养成, 信仰的确立就是不可能的。反观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存在的症结是教育日益同生活脱节、同文化脱节。如此一来,教育就不可能成为人格养成的重要路径,而是沦为单纯的价值中立的知识传递和单纯的谋生手段的训练。所以,我们又需要重建教育模 式,为坚定信仰的确立提供必要的前提。惟其如此, 人与人的关系的优化和改善才是可期的,从而“互害”现象最大限度的消除才是可能的。
作者:何中华
来源: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8-13 18:17
【案例】
【易小明】自由:从观念到实在
作者简介:易小明,男,土家族,1965年生于湖南省龙山县。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伦理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后,留德学者。主持完成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12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70余篇次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5部,主编著作3部;获省级科研成果奖6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首届"百位优秀社科人才",湖南省省级学科带头人。2008年评聘为中南大学"升华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评聘为河南大学省级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伦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哲学学会、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一、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
自由是人之欲念生成、选择、实现的过程。存在可分为自然、社会、精神三方面,人的存在只可能面对三者。于是,根据人所面对的不同存在对象,可将自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在精神中的自由,二是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三是人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自由。精神中的自由谓之观念自由,社会中的和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自由谓之实在自由。自由就是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统合。
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关系是:观念自由可由主体独立生成,实在自由必须体现主客关系;观念自由体现为理想自由,实在自由体现为现实自由;观念自由体现为思想自由,实在自由体现为行为自由;观念自由体现为现实的主观化运动,实在自由体现为观念的客观化运动。
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是不能剥离的:观念自由缘自于对实在限制的观念性超越,同时它又得返身于实在,其活动指向实在,总希望观念能够外化为现实;而对象对主体的限制,即实在自由的有限性,又总能不断激起主体的理想,以及主体观念对对象限制的无限超越。在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之间,观念的自由总认为实在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现实中因有异己对象存在而总使自由难以合主体之意;而实在自由则总认为观念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观念自由只是观念中的,其中许多方面因未顾及现实异己对象的限制而无法走出观念,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其实,双方各执一端都有问题,因为二者统一于人的存在活动过程,它们根本无法分开。
观念自由相对于实在自由而言是一种“绝对”无现实限制的自由,它可不顾及对象的限制而在主体的思想中完成。所以,在观念中你可以毫无约束地“想做”任何事情。但是一旦面对现实,观念中的自由马上就会受到对象的限制,因为现实不只是主体,而是主体与对象的共在,并且人面对这个对象时许多方面都无能为力。于是,观念自由一旦走向现实,向实在自由转化,就必然由独存的自由转向关系的自由,由无对象依赖与限制的自由转化为有对象依赖与限制的自由。
但是,不能因为两种自由的差异就完全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观念自由是现实自由的不竭源泉:离开了观念自由,现实自由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观念中的理想自由有的可以实在化,有的则不能实在化,所以,实在自由的范围比观念自由的范围要小。尽管实在自由也是开放发展着的,但无论如何发展,它永远都无法充满观念自由的巨大空间。观念自由是灌溉实在自由的不竭的源泉。
同时,就是观念中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其存在也为自由的实在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是这种不可能实现之欲念所体现的对现实的超越精神,不断激励着人们努力寻求导致观念自由转化为实在自由的各种条件,从而使许多主观的不可能最终转化为客观的可能,当下的不可能最终转化为未来的可能,进而推进现实自由的领地不断向外扩展。
迄今为止,造成关于自由的定义林林总总且相互冲突的原因,除自由本身因涉及主体、对象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具复杂性之外,主体认识方面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即没有在阐释自由本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明确的分域,没有将自由明确地分为观念自由与现实自由,也没有将实在自由再明确地分为与自然交往的自由和社会中的自由。由于自由的本质未定且划域不清,各领域相互交错,这就势必造成概念的混乱。
笔者认为,不根据主体所面对的不同对象来考察自由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想对自由进行高度概括、对自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体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其自由的内容与形式有很大差异。
二、从观念到实在:自由的三个环节
人的一生就是欲念不断生成、选择、实现的一生,因此,从观念自由到实在自由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之欲念生成、选择、实现的过程。欲念的生成需要主体有一种超越自身与对象的冲动力;欲念的选择需要主体有一种对自身与对象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的判断力;欲念的实现需要主体有一种对自身与对象进行全面把握的掌控力。可见,自由既是人之欲念从内生到外化、人之活动从主体到对象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的能力不断实现与提升的过程。
自由作为主体存在之去障碍化的过程,主要由三个环节构成:首先是欲念的生成,而后是欲念的选择,最后是欲念的实现。从主体与对象相关性之角度对这三个环节进行考察,在欲念的生成环节中,主体可以是独立的,可以完全不考虑对象;在欲念的选择环节中,主体则需要考虑对象,并且主体越是充分考虑对象,其选择便越可能客观合理;而在欲念的实现环节中,主体则需要直接用力于对象,这是一场主体与对象“物质力量”的较量。其实这就是欲念的一种运动过程:主观性不断走向客观性,随意性不断走向制约性,独立性不断走向相互性。从自由的随意程度来看,欲念的生成最自由,其次是欲念的选择,最后是欲念的实现。可见,在三个不同的环节中,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关系是有差异的。所以,若只用其中之一来概括自由的本质——从欲念的生成环节说自由是随心所欲,从欲念的选择环节说自由是选择,从欲念的实现环节说自由是认识必然、是主动接受限制与能动改造世界,都难以概括自由之全貌。而如果将自由理解为主体欲念从生成到选择再到实现的贯通过程,上述这些片面认识就可以消除。
人们谈得较多的是选择的自由,其实选择的自由只是自由过程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它要体现自我的主体性、任意性,另一方面它要体现对象的客体性、限制性,它是二者的综合。
所以,当我们谈决定自由时,不能将它向两端任意延伸,否则就可能陷入欲念自由或行为自由的两极。因为,决定的自由既不是欲念的自由,也不是行为的自由,而是决定本身的自由;决定本身的自由就是现实规定与观念规定、现实限定与观念超越的统一。
要说决定过程中存在自由,就必须反对决定论。有人用因果关系来证明:作出某决定其实早已被之前的原因所决定。这种决定论的失误在于:一是将自然因果等同于社会文化因果,其实在社会文化中,人的活动是能动的,不是完全被动地体现自然因果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某些自然因果关系;二是将有原因性等同于必然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不一定是必然的,有原因性基于既成事实,必然性则基于内在的固有联系。
但是决定的自由又不是不受条件的影响。如果决定的自由不受条件的影响,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决定的自由既不是不受条件影响的自由,也不是被条件完全决定的自由,而是在受条件影响的同时又不被条件所决定的自由。
首先,决定要受主体自身的影响:一是主体各方面的既定条件,比如生理条件、生活习惯、精神倾向等;二是主体历时过程中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可使后来主体对先前主体的行为进行反思。其次,决定要受外在条件即对象世界的影响,对外在条件的充分考虑可使主体的决定更加客观化。因此,决定的自由虽由自己决定,但一定要考虑到外在条件的影响。决定之作为决定,就在于它是做出某种行为的决定,它不是纯粹的想而是想如何去做,做就必然涉及对象,必然与对象打交道。决定的现实指向性是由主体欲念的现实运动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人毕竟是现实的存在者,人的现实需要决定了满足人之现实需要的欲念必须指向现实。
相对于决定受对象的影响而言,决定受主体自身的影响也是自由的一个向度,自由即由自己决定。这可从如下方面理解:一是决定的主体是自己。决定是自己做决定:没有征得你的同意,他人再能干也不能替你决定,更不能剥夺你决定的权利。二是如何决定往往要根据自身当下的现实条件来考虑,如生理条件、生活习惯或精神倾向。三是决定有可能因主体的精神超越而突破自身原来的思维—行为定势,具有某种偶然性。决定过程中所依据的自身现实条件,既有自然肉体方面的,也有文化精神方面的:决定越是受文化精神方面的影响,便越可能具有突破性、超越性;决定越是受自然肉体方面的影响,便越可能具有常规性、现实性。可见,由自己决定并不等同于自己决定论,自己决定论是必然性的,而自己决定则内含着偶然,也就是说不可能从自己以往的情况直接预推出某种既定的决定。同时,由自己决定更不意味自己就能操控决定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因此,决定对行为后果负责就只能是部分意义上的,即意志自由或决定自由只能使主体承担行为后果的部分责任。
三、实在自由的两个领域:自然与社会
人是在自然与社会中现实地存在着的,因此实在自由也就体现在这两个领域。而传统的关于自由的定义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首先,“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主要是人以实践的方式面对自然时对自由下的定义。也许有人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受必然规律支配的,但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自然现象不同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中没有人的意志参与,而社会现象中则始终都贯穿着人的意志,甚至它本身总体上就是人的意志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的非理性意志的参与更增强了社会发展的随机性。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人类自己所造就的社会也看作只受必然规律支配的领域,那么人的自由就几乎没有什么现实空间了,因此,“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限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比较恰当。
从自由是一个欲念生成、选择、实现之贯通过程来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定义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关注到欲念的实现环节而没有关注到欲念的生成和选择环节。同时,仅就人面对自然时对自由作如此定义而言,它也不太完整,因为人面对自然时,要获得较大自由仅有对必然的认识尚不够,还需有对客体本身的认识,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以及对主客体之间应然、实然关系的认识等等;同时,仅仅有认识也不够,还需有与自然或统一或斗争的实践能力,否则人的自由就会大打折扣,预计的目标就可能难以达到。
人要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自己的欲念,必须处理好与自然对象的关系。这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对象服从自己;二是自己与对象互有服从;三是自己服从对象。在这些情况中,无论主体是处在主动还是被动的位置,要获得相应的自由,其行为都应当建立在认识对象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事实上,自由作为主体欲念的生成实现过程,总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强制,既有主体自身的强制,也有对象世界的强制。在主体自身的强制中,既有肉体方面的强制,也有精神方面的强制;而在对象世界的强制中,则既有人为的强制,也有非人为的强制。在这些强制中,就包括必然性对主体意志的强制。主体自身的强制问题应当主要在主体内部解决,它既包括主体对自身必要的自然需要的尊重,也包括主体不同欲念之间的斗争与选择。而其受动与能动相统一的解决方式即选择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程度的主体自由。对象世界中的非人为强制,主要是自然世界对主体的强制,而自然的非意志性存在其实也为主体能动自由的发挥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对象世界中的人为强制,虽然也是人的一种欲念对另一种欲念的强制,但它不是同一个体内部不同欲念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同个体的不同欲念之间的斗争。当人类内部必要的行为规范没有建立或遭受破坏时,这种人为强制对自由的杀伤力最大。因此,自文明社会以来,自由最尖锐的问题一直都不是人如何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人如何从人自身的压迫中得到解放。
其次,康德基于实践理性的自由——自律。
关于康德的自由,国内学者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的争论,但不管是哪种分法,其实践理性的自由就是自律的观点是没有争议的。康德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指人在道德实践意义上具有不受自然律束缚、摆脱肉体本能而按自身立法行事的自由意志。显然,在人的行为如何在自然必然与社会道德原则之间进行过渡的问题上,康德首先需要借用“任主体之意”来摆脱自然必然而进入社会,而一旦进入社会他又用道德必然原则来规治“任主体之意”,从而使自由的大坝建立在反自然必然性与反个体任意性之间。于是,康德总是把感性的任意完全排除在真正自由的范围之外,认为只有不受感性的干扰而始终使用理性,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永恒的自由。他说:“理性给出了一些规律,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哪怕它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并且它们在这点上与只涉及发生的事的自然律区别开来,因此也被称之为实践的规律。”(Kant,S.830)
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康德规定自由的思路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思路同出一辙,那就是主体对客观规律的尊重甚至服从,只不过是将范围从自然搬到了社会,用人际活动规律即道德实践规律(其实不只是道德实践规律)代替了自然规律而已。但是,笔者认为,自由是无法脱离任意的:任意是自由的天然表现形式,并且冲破内心道德法则的那个任意与冲破自然必然规律的那个任意至少在根源上是同宗的。主体任意在面对自然和反自然必然性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在人类社会中同样会以其自然秉性而发挥应有的作用——人类社会的道德桎梏难道不是它打破的?只不过这种任意一定程度上由于主体间性之作用而转化为相对理性的、普遍化了的任意而已,但任意普遍化本身并不总是为了消除任意个性,而是为了营造更加可能与合理的个性空间。况且,任意作为意志的内在根据,总是从自我出发的;即便自我变成了成熟的、理性的、主体间性的甚至客观化的自我,它仍然是从自我而不是从他者出发的。因此,可以改变的是任意自我的素质,不可改变的是从自我出发的任意方式本身。
任意本质上或原质上就是感性的,所谓理性的任意(康德叫做自由的任意)实质上都已经偏离了任意之任性的精神本质。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讲,所谓理性的任意,往往是理性对已经产生的感性任意的一种合理处理,它并不与感性的任意同时产生,最多只能说主体的理性素质可能对任意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任意冲动的那一刹那,它只是暗合了理性的要求,而不是理性自身的冲动。
只不过在实在自由中,由于有一个“异己”的对象存在,主体必须通过与对象协同、有时甚至是妥协、服从,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欲念。但是,这种协同、妥协、服从并不是以完全消除主体的感性冲动为前提,恰恰相反,这些感性冲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积极换上理性的服装,悄然混迹于协同、妥协、服从的各个环节。
事实上,按道德原则行动虽然是在社会中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并不是其全部要件;就是说,在社会中获得广泛自由仅有道德自律是不够的,还需有其他方面正确的认识与实践,因为社会生活不只是道德生活。
四、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通达与划界
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通达,是由欲念本身的运动本质所规定的。欲念的生成与实现常常是贯通一体的,欲念总是针对现实、为实现而生成的,这就意味着观念自由总是要指向实践,要向现实自由过渡。
但是观念自由又必须与现实自由划界。因为观念世界是个体思想独存的空间,而实在世界是个体与对象相互依存的;观念世界的欲念是以个体自我为中心,其任意产生与扩展都没有对象的阻碍,而对实在世界的自由来说,虽然个体中心仍然存在,但其外扩时有对象的阻碍,因此有时还得以对象或他者为中心,比如生态中心、动物中心论等。观念自由有的能够实现,有的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有的自由永远都只能停留在观念领域,不能走向现实,而有的自由则可以走向现实并可能得到实现。因此,我们应当让不能实现的自由尽量停留在观念领域,让能够实现的自由尽量从观念走向现实。
对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划界不清,必然导致认识、决策、行为上的失误。比如“绝对自由观念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这一认识就是如此。绝对自由只能是观念自由,它要变成现实自由,须进入人与人的关系世界,没有进入这一关系世界的大门,它就不可能在其中表现,从而也就无所谓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观与无政府主义是两个领域的东西,必须对它们进行划界,否则就会用现实自由的有限性来规治观念自由的无限性,用社会稳定有序的要求来规治思想的自由性,从而人为地造成思维创新与社会秩序的冲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观念的绝对自由主义者,只要他能把观念与现实明确分开,能将绝对自由保持在观念领域,而在现实中知道如何遵守道德,如何尊重必然,不将观念中的东西全部外化到现实中。
观念自由与现实自由之所以能够相互区别又相互通达,原因基于人之存在的二重属性。
人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肉体与灵魂的统一,这也就是观念与实在的统一。因此,观念的实在化与实在的观念化,是人的存在、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人必然在二者之间穿梭:既有观念的实在化运动,也有实在的观念化运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人的自由、人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就是这两类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许是受物质决定精神之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更加重视观念的现实化运动,而忽视现实的观念化运动。人们重物质轻精神,重实践轻理论,重现实轻理想。这在基本物质条件匮乏的时期也许还可以,但在物质文明相对发达的今天,不顾条件变化而一味如此,就必然导致人的精神衰落。
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必然是限制与超越的统一体:观念自由依托精神力量不断飞升超越时,物质肉身总要将它拖住不放;而现实自由依托物质力量不断堕落瘫倒时,精神道德也总要拽着它向上提升。离开物质基础,人不可能存在;离开精神超越,人的存在失去意义。人既要在超越中拥有现实,更要在现实中有所超越。人如此,人的自由亦如此。
【参考文献】
[1]Kant, 1976, Kritik der reinen Vernuft, Hrsg. von R. Schmidt,Naohdruch: Verlag von Fel ix Moiner.
(原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
原文来源:哲学爱好者
作者:易小明
编辑:刘佳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8-18 11:33
【案例】
法伦理学研究论纲
作者简介:曹刚安徽绩溪人。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法伦理学、应用伦理学。
来源:《伦理学研究》2008年3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法制建设处在一个大规模的“立法阶段”。但中国的立法似乎更多地注重实用的和功利的论证,而缺乏系统的道德正当性的论证。这使得法律体系内部常常存在着价值的矛盾和冲突,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之间也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既影响了法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使道德建设付出了代价。法伦理学的研究将对现有法律体系做深入的道德反思,并系统论证法律的一般道德原理,其理论成果无疑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伦理学的一般原理研究
1.法伦理学的主题是“人”。“善”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存在与发展。这是一切人类文化所共有的最抽象形式。无疑,法伦理学的主题就是“人”。“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如果一个法律是良法,仅当它是为了人这个最高目的而存在。这显示了伦理学方法的本质:为法律世界规定一个最后的目的,法律按其与这个目的的距离远近而具有不同的价值。由此看来,法伦理学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价值科学,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必定不是费尔巴哈式的感性实体,也不是抽象的原子似的个体。而是现实的个人。法律伦理学只有把现实的个人作为逻辑起点,法律的世界才会成为有意义的世界。
2.在目的论的框架里,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法律便呈现出三重规定性:法律是人的生命存在形态,是社会的统制手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还显现出两个根本特征,一方面,法律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具有规范性,人类活动要尊其为行动的准则,另一方面,人类又要改造实在法,使其更能发挥经世济民的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探讨法的道德理念,并以其为评判实在法,改革现存法律制度的指导性原理。
3.幸福、和谐和正义是法律的道德理念。法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同所有的文化世界的产物,如政治的、经济的和艺术的,等等,分享着同样的理念,就是人的幸福;法作为社会的统制手段,同所有的社会规范,如道德的、宗教的、习俗的,等等,分享着同样的理念,就是和谐;法律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社会实践,有其独特的社会统制的特性和方式,从而有其内在的道德理念,就是正义。幸福既指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满状态,又包含了合目的性的价值取舍的过程,即扬善避恶的一般道德要求;和谐既指最合乎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状态,又指以合作互助为核心的,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共同善的秩序。而正义不过是人们运用实践智慧,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对幸福和和谐的追求。可见,幸福是法律的外在的、终极的道德理念;和谐是法律的内在的、高级的道德理念;正义是法律的基本道德理念。
4.如果说,伦理学就是关于正确行为的理论,那么,法伦理学就是人类法律实践的智慧之学。正义就是这种道德智慧的体现。具体说来,正义不过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社会和谐为基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我们可以把利益关系分为三类,即群体间的利益关系、群体与个人间的利益关系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对应不同性质的利益关系,自然有不同的“度”和把握“度”的不同方式,即不同的正义形式。交换正义是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基点,当个体追求私利而彼此发生关系时,依据严格平等原理,而确定的各自利益或不利益的应得的“度”。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不同,它虽也是个人的人格实现为基点,但它涉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依据比例平等原理,按照各人参与合作的程度和贡献大小,确定各合作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社会正义则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各自目的时所发生的利益关系,应依据社会的整体和谐,确定的各群体利益的一个“度”。
5.由于法律在确认、维护和调整这些利益关系中形成三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可以称为私法领域、公法领域和社会法领域。那么,交换正义的适用领域是私法。就权利而言,人格权、生存权以及对物、发明及他人劳务的权利,尤其基于私人之间交换经济的交易契约关系而产生的各种请求权都属此类。另外,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制度、报应刑制度都以此为基本原理。分配正义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公法,作用在于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公权力,在量刑(目的刑)、课税、就任公职机会、荣誉及其他精神和物质的待遇时,应受分配正义的支配。社会正义适用对象是社会法。社会保障、劳动法乃至国际法均受社会正义的支配。当然,上述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在现实的法律生活中,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作用。
二、宪法的伦理问题研究
1.宪法的正当性问题。国家所有法律的正当性都来源于宪法,因此宪法本身的正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社会的所有正当性论证,无论是神源、天道、人格魅力甚至终极规范的论证,在现代社会都失去了效用,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程序。问题在于,民主程序并不必然带来合乎道德的结果,而正当性本身并不只是个心理认同的问题。因此,在民主程序之外,我们必须找到可以提供正当性的道德的最终准据,这就是自然法。只不过这里的自然法,既非普遍的自然规律,也非人类永恒的理性,而是基于人的实践生活发展原理的“自然”,其实质内容不过是由人类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法作为储存人类基本价值的理想图景,指引着人们在法律实践中,尊重人的尊严,并成为评价、判断实在法规则的最高标尺。
2.宪法的道德理念是共和。共和作为一种理念,有三重规定:一是共和之“和”,即和谐。追求人类的合作互助,而非暴力争斗,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宪法的和平性。二是共和之“公”,即公共利益。宪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三是共和之“共”,即民主和法治。公共权力必须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加以运用才能确保公共利益真正实现。
3.宪法的正义形式是分配正义和社会正义。分配正义涉及国家与其成员个体间的利益关系,其实质是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间的关系,国家以公益为本位,按国家成员的贡献分配利益。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公民资格的分配,二是按功绩的分配。社会正义在这里其实就是国家正义。所谓国家的正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宪法确认的国家与人民、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等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其核心是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分配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4.宪法正义的核心原则是平等对待。正像德沃金说过的,一个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必须对他们的命运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否则不可能是个合法的政府。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平等对待既是所有国家法律制度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公民个人对国家的要求权。换句话说,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5.宪法是和谐社会的道德之帆。宪法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根本地位和功能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德沃金曾说,宪法是道德之帆。确实,宪法不但是一国的根本大法,也是一国的道德宪章。她应该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基准,并起着导航的指导性功能。
三、民法的伦理问题研究
1.民法的道德理念是人格自主。个人的利益除了经社会认可的普遍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私人利益。对这部分利益的追求是人格实现的前提条件,并且最能体现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民法以各人间的私人利益关系为调整对象,其道德理念必然是人格自主,体现在民法中就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意味着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即在法定范围内,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自己立法,自己负责。意思自治还意味着排除他人的干涉,尤其是国家的干涉。个体私人利益的满足和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规则和经济保障,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个体追逐私利需遵循的一般规则。除此以外,国家的公共权力就应当让位于私人的意识自治。意识自治还意味着个性和创造力。即人们力图自主地、富有创意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发展道路。
2.民法的正义形态是交换正义。交换正义实质上是对一种自然正义的确认,所谓自然正义事实上描述的是商品经济的一般状态,它以个体间的利益关系为调整对象,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关系。交换正义是一种非模式化的分配,按诺齐克的说法,就是分配没有固定的模式化标准,任何人都按自己意愿的方式来转让或交换,一句话,“按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交换正义的功能是消极的,它只是消极地确认和维护自然的分配状态,而不是积极地以促进当事人的利益为目的,因为积极功能的实现有可能带来对个体权利的伤害。
3.民法正义的核心是人格平等。“个人人格之绝对的尊重”,是民法的最高指导原理。民法是规定个人相互间的关系,即对等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如果说在公法中,国家可以拥有优越于私人的地位,其特色在于可以单方面地规定私人的义务,那么,私法是以人格平等为原则,权利义务的设定由个人之间自由的合意实现,不能单方面地给对方课以义务。人格平等是权利的平等。只要是人,就拥有同样的权利。人格是一种形式的平等。它强调机会的平等,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至于结果如何,机会是否能够同等地为人们利用,则任其自然。它完全不认为社会与自然的一些偶然因素(能力、财富与地位的分配),是应该考虑的因素。
4.民法中的公共利益。个体间利益关系领域是一个交换正义作用的领域,但它绝非一个孤立的领域,它还需要受到法律的和谐理念和其他正义原则的界定和制约。主要表现为:其一,绝对私有权原则的修正。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后,民法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受到两个方面限制,一是所有权绝对原则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提出对独占的禁止,强调对团体权的重视。二是禁止权利滥用,强化他物权,弱化所有权。其二,无过错责任的出现。如在高度危险、产品责任、环境污染等方面,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其三,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契约原则的确立。它们通过保持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平衡,合理地限制了契约自由的边界。山本敬三则认为,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都是要解决将共同体中的规范引入到裁判规范中去的问题。公序良俗是“否定不公正行为”,而诚实信用是“积极地实现公正”。
5.关于民法精神的检讨。民法精神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精神,要建立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民法精神。同时,我们也要认清民法精神的特性,它是立足于人的抽象性,作用于特定商品经济领域,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精神,如果将其扩张为和谐社会的主导精神观念,必使社会陷入欲望的体系,有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社会保障法的伦理问题研究
1.社会法的道德理念是互助。社会存在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的目标就在于相互援助,以弥补个人能力上的不足,从而满足人的不同存在层次上的需要和目的,促成个体的自我实现。正如狄骥所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连带关系,他们有共同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相互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就是说,社会中的人们必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为实现共同需要彼此之间要相互援助。社会保障法其实是一种风险分散或共担机制,风险共担本身即以互助为基石并在互助中使风险得到化解。可以说,社会保障法以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和追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社会法的正义形态是社会正义。社会法领域内的“社会”并非指全体社会,而是指特殊部分社会的社会集团,尤其是指在经济法则下为生活所苦的社会集团。在承认这种社会集团特征的前提下,建构满足生存权要求的社会法。社会正义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权,而是通过保障社会弱者这一群体的利益,如劳动者、失业者、老残孤疾者,后来又扩展到消费者、中小企业者等,来实现多数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整体的和谐;社会正义不是为个人私生活领域的自由提供形式上的平等保障,而是保障特定弱者群体,以求得实质的平等和自由;社会正义不是要求国家权力处于消极不作为的形态,相反,为了使社会经济弱者获得实际上的自由,必然要求国家权力介入和干预本属于个人私的领域,处于积极作为的形态;社会正义不是保障具有个人性质的权利,而是保障具有群体性质的权利。
3.社会法正义的核心是能力平等。能力平等是阿马蒂亚森反思和批判当前几种流行的平等观后提出的概念,其作为社会保障法的核心原则是合适的。该理论强调决定人的福利的非收入因素,并通过研究物质剥夺与非物质剥夺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显示了贫困的动态性。能力平等原则体现在社会法上,是由“倾斜立法”和“保护弱者”两方面构成的。总之,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些标准源于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保护弱者的原则正是通过倾斜立法,对失衡的社会关系作出的必要矫正,从而缓和实质上的不平等。
4.仁慈和社会权利。人道主义的宽容与仁慈是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它为社会保障法提供了个体的德性上的支撑,但是它却不能使我们获得合法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们的利益关系不能靠慈善和宽容来调节,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所确定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来调节。在现代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对弱者的保护已脱离了慈善救济的人道关怀的局限性,变成人人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社会权利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基本需要和利益保护的要求。社会权的确认,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地位,改变了社会保障法的慈善救济性质。
5.社会保障法要有利于自力更生。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障,对于解决社会不公,促进社会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仍需要找到两个平衡点,一是团结互助和自力更生之间的平衡点,一是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点。
五、司法的伦理问题研究
1.司法不直接追求和谐。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样式,有个人化方式、社会化方式和诉讼三种。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何种形式解决纠纷,取决于解决纠纷的道德理念是什么。如果纠纷解决的目的在于追求和谐,那么诉讼就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不得已的手段。最好的方式是忍与和解,再次是调解,最后才是诉讼,这样,追求“息讼”反而是一个在制度上和逻辑上都合理的选择。
2.司法是矫正正义的最好形式。矫正正义的概念来自于亚里士多德,波斯纳把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的根本要素归纳为三点,(1)为不公正行为所伤害的人应当有启动由法官管理的矫正机器的权力;(2)法官不考虑受害人和伤害者的特点和社会地位;(3)对不公伤害的救济。我们可把矫正正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二点,一是以权利为本位。原权利没有纠纷或冲突就不会有矫正。矫正实质上是相对于主权利的助权。从结果上看,矫正正义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二是以司法为最佳形式。矫正的实现形式有很多,但司法是最佳的实现形式,因为相对于个人化的矫正与社会化的矫正而言,通过司法的矫正因为依据有明确的法律规则,拥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威以及高度的程序保障,可以实现一种最彻底的公正,即最终确定权利的归属和赔偿责任。以司法为矫正正义的最佳实现形式,其实是其权利本位文化的必然选择。
3.司法如何运送正义。(1)规则正义。规则正义的含义有两重,一是规则本身的正义性,一是规则的严格适用。规则正义重在规则本身的正义性。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判决是法官依据裁判性规范作出的,依法作出的判决自然是正当的。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正当性,很难想象,一个严格依据极为残暴的刑法规定所作出的刑罚是一个好的判决,由此,司法的公正性在根本上还要取决于法律规则自身的正当性。(2)衡平与解释。一般法正义具有普遍性,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表现为同类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一般法正义具有确定性特征,这正是法之所以能起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的重要属性。但现实生活是变动不居的,这就产生了法与社会生活的不同拍。同时,语言本身的局限性、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都使得一般法正义在适用到具体情况的事物上时,有可能产生不正义的结果。法律解释和个别的衡平是化解一般法正义与个别法正义的紧张关系的两个具体步骤。(3)程序正义。司法的程序就是一种按照法定的方式、顺序和步骤作出裁判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评价模式有三种,即功利主义评价模式,成本评价模式和程序本位的评价模式,前二者都立足于程序工具论基础之上,事实上是对程序作的功利的或经济的评价,没有给程序正义以独立的地位。后者立足于程序的内在价值之上,是对程序作的道德评价,因此是程序正义的真实内涵。
4.法官的角色伦理和职业道德是司法公正的德性保障。法官的角色伦理和职业道德具有不同的理论视角。法官是一个角色丛,包括了官员和司法者二重基本角色,所以,法官的角色伦理不只是对其作为一个职业者的规范,而是二重角色规范的综合体,它反映了社会对法官的综合道德评价。作为“官”的角色,它被赋予的特殊道德要求是公仆意识、廉洁和公正;作为司法者,其特殊的职业伦理是刚毅、谨慎和勤勉。总之,着眼于法官角色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双重视角,对于法官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5.回到和谐:ADR的启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可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关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它包含着三个要素:其一,代替性,即指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判决的一种代替。其二,选择性,当事人可以自主地在法院的审判和判决与各种非诉讼方式之间进行选择。最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通过促成当事人的和解和妥协来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这使得它与以实现权利为目的的黑白分明的判决区别开来,并与审判一起共同承担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ADR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需求,也是对方传统文化反思的产物,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西方以恢复权利为目的的诉讼观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纠纷解决的和谐观的心得,因此,它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不但在西方法律社会形成了一种潮流,还为我们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创造性设计司法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契机。
六、回到伦理学: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几个伦理问题
1.培养公民守法的道德能力。法律作为人们追求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期望,具有高于个体目标的理想,是以一定方式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共同完善为特定指向的,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性。但事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普遍总是寓于特殊之中,且只有通过特殊才能存在。这个特殊物就是组成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各个个体的主体意识,即道德能力。事实上,没有个体守法的道德能力,法律就是一种纯粹的异己的东西,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守法的道德能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善观念、正义感和仁爱心。
2.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如果我们把公益本位作为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点,那么,法治和德治就是建构社会伦理秩序的两个基本途径。在关于法治和德治的争论中,法治似乎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没有反思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点是什么,没有搞清德治和法治的边界,恐怕是认识上的误区。我们认为,其一,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但法治是众人之治,德治则是精英之治。其二,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方略,但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其三,法治和德治既治民又治官,但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可见,法治和德治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3.立法中的几个道德难题。在狭义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道德难题的解决,为立法做准备。我们选择安乐死、动物权利和克隆人作为立法的道德难题予以研究,是因为它们作为道德难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程度,因而具有代表性。安乐死可以得到正当性证明,其实已不是道德难题,只要立法条件成熟,就可以由法律确认和保护;动物权利的正当性证明是由人的价值外推获得,但这个证明的过程难以服人,法律上只能把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即人格财产权来保护;克隆人的活动则具有对人伦秩序的颠覆性,无法由现有立法确认和保护。
作者:曹刚
来源:微信公众号—纯粹之学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gojdXXRFIoechCmdunNSA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8-22 23:37
【案例】
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紧紧抓住被康德道德哲学提升到本源性高度的自由意志,从人性、信仰、良知等方面考察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思想,并通过这种考察反过来揭示了西方文化、西方伦理学的内在结构,展现了中西文化心理、中西伦理学、中西人格结构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把一切善恶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并由此生出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或拯救之道;中国人则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把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甚至把自由意志也归结为自然本性,所以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人性的退化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而不需要拯救。
【关键词】康德/宗教哲学/人格结构
今天,康德已被许多学者看作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第三个问题属于宗教哲学(注:李秋零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1793年,正当法国大革命处于峰巅的时候,康德出版了他的宗教哲学著作,即《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中译本见李秋零译、邓晓芒校,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阐明了他的道德宗教的哲学原理。在这本书中,康德本着他一贯的精神,从现象和物自体、自然和自由、认识和道德(实践)的绝对二分原则出发,对基督教的《圣经》作了他自己独特的诠释和阐发,其思想的力度和影响的深远,几乎相当于"第二部圣经"。他由此揭示了西方宗教精神潜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给予了这一结构以合理的解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最好、最典型的标本。
一般说来,西方文化是一种反思型的文化,即把对象世界看作反映人心的一面镜子。人要认识自我,只有到对象世界中去寻求。这就有双重的结果:一方面,自我成了一个随着认识的不断扩大和加深而不断显露出来的无穷目标,是动态的、不可穷尽的;另一方面,对象上反映的都是自我的形象,对象本身反而隐藏不露,成了物自体。相反,中国文化是一种体验型的文化,即把自己的心看作对象世界的一面镜子,人要认识世界本体,只有到自己内心去体会。这也有双重结果:一方面,自我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点,宇宙的一切都反映于其中(万物皆备于我),唯有自我本身无法在其中出现,正如镜子本身不能反映自己一样,这是一个视觉上的"盲点",一个"无"、"空";另一方面,对象就是我看见的那个样子,直觉体验就足以把握本体,"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大问题是把握不住对象本身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毛病就是缺乏自我意识。
康德的立场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这一深层结构。从这种立场来看待基督教和《圣经》,就抓住了西方宗教精神的来龙去脉,这是过去的基督教神学没有自觉到的。我们下面打算从三个方面考察一下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想,并与中国文化心理相应的主题作一个比较。
一、人性和自由意志
康德是以道德哲学作为宗教哲学的基础的,在他看来,道德是独立的体系,不需要宗教也能成立。但道德本身在逻辑上必然要推论到宗教,因此考察宗教原理必须先讨论道德。
在道德学和伦理学上,中、西方都热衷于讨论"人性"问题,且都提出过性善、性恶、既善既恶、非善非恶、善恶相混这五种观点。但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一点是,他们很早就提出了另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伦理学问题,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中国传统伦理基本上不讨论自由意志(荀子接触到自由意志问题,提出过性恶论,但均未展开),因此对善恶的探讨最终归于对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没有这种独断的假定,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便无法维持。相反,西方伦理既然承认了个人自由意志,对善恶的探讨就必定要容纳性恶这种内在本源的可能性。这种考虑往往作为西方伦理学起码的基点,并由此出发去寻求由恶向善转化的途径、手段和拯救之道。因此西方人即使对通常的"善"的理解也与中国人有所不同,它必须包含中国人视为"恶"或不善的"人欲",即个人幸福。康德在人性观念上容纳了上述所有五种观点,但却认为这些都属于现象,人的本体之性则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虽然也被称之为"性"(Nature),但并非自然之性,而是本质之性(注:在西文中,nature兼有"自然"和"本质"双重含义。)。即是说,并非在时间上与生俱来之意,而是超越时空、因果律的。人在每一瞬间都可自由选择,并不因他从前、或生来是个好人或坏人而能决定其选择;用圣经的形象说法,人是从"天真状态"堕入原罪的。康德把人性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使人性成了一个不可规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物自体)。的确,人性正是这样的东西。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人就是、必然是、并且永远应当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东西,即"奇迹"。人的本性就在于创造。人将要怎样创造自己,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人不能凭借自己天生的"性"而对自己高枕无忧,而必须随时提防自己、警惕自己,畏自己。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人之善恶是先天规定好了的,是自由意志无法摆脱的;人最好是不要有自由意志,只须顺其自然就可以为善、成圣。现实中之所以并非人人成圣,是因为外来影响所致,所以道德就在于清除外来污染,诚实地回到本心、真心。中国人对自己不畏,只畏外来的势力(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不需要灵魂的拯救。因为他的本心是可以依靠的,只要"反身而诚",即可"乐莫大焉"。所以中国人最喜欢区分好人坏人,对好人大树特树,似乎他从娘胎里便是个好人,决不可能坏;对坏人、歹徒则要么诛杀,要么改造,使其"良心发现"。西方对于好人、坏人是就事论事的,一次荣誉不足以享誉终生,犯了罪,该判什么判什么,不搞从宽从严。因为人们相信罪犯也有理性,可以自己作判断和选择,感化教育通常是对儿童进行的,对成人则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
在康德看来,既然一切善恶都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那么自以为本心纯洁并将"天真状态"当作善的规定,这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恶,即伪善。因为在这种虚假的规定之下,真正起作用的是那可善可恶的自由意志。没有人能够宣称(保证)自己天生注定是本善的,人的"本心"不是起点,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只有上帝才是"知人心者",也才能作最后的评判。在这里,康德把伪善视为人性中的"根本恶",是产生其他一切恶(偷盗、杀人、奸淫等等)的总根源,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伪善就是自欺,即在行动上合乎道德法则,在内心却埋藏着非道德的动机,并为此沾沾自喜,自以为问心无愧,道德就变质为一种外在的形式、虚假的旗号,甚至作恶的工具了。其他的恶都是经验性的,可以限制和根除的,唯有自欺是理性(智性)的本性,是根除不了的,并且是人人具有、即使最好的人也概莫能外的。从这种观点来看,谁若标榜自己有一颗赤诚的心、明镜般的心、透明的心,就值得引起怀疑和警觉,许多坏事恰好是由这种心干出来的,干了还不知忏悔。耶稣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注:《新约·约翰一书》,第8~9章。)"天真状态"并不是什么善,而是动物状态,尚无犯罪的可能;只有犯罪的可能才使人成为人。所以黑格尔说:"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的。
二、信仰与得救
康德认为,由于自由意志,所以人性可善可恶;但自由意志首先表现为恶、犯罪(原罪),因为天真状态由于抽掉了自由意志而谈不上是善,人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只能是打破天真状态而犯罪。人一旦犯罪便永远不能洗刷,因为他表明他已是一个自由人、即一个可犯罪者了;然而,这种原罪正是人的高贵性(高于动物)的标志,他在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一点上已经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了。就连善,也只能体现为犯罪的人通过同一个自由意志而获救。恶是起点,善是终点;恶是现实的,善是潜在的。善恶在无限历史过程中达到调和,因此道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康德那里,正因为这一过程的无限性,所以有必要设定一个上帝来保证其完成,这种设定就是信仰。信仰不是外来的,而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当人意识到自由意志本来确实有违背现实世界的恶而向善的可能性时,他就已在逻辑上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在行动上有可能按照"好像有一个上帝那样"去做了,他就必须相信一个灵知的世界、彼岸世界。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理论的信仰和实践的信仰,哪个在先?亦即:一个犯罪的人是先认识到可以指望一个上帝的拯救,然后才按上帝的要求去过道德的生活,还是先着眼于要过一种道德生活,才能使自己配得上上帝的可能的拯救?换言之,信仰究竟是为了得救还是为了道德本身?可以看出,前者是不诚实的,把道德当手段,是一种"历史的信仰";可是后者是不现实的,是一种纯粹"道德的信仰"。康德主张的是后者。但他又认为,前者虽然不诚实,但却是历史上唯一可能发生的信仰,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向后者进化;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本体界,但在历史中二者可以统一。人们加入教会的目的总是功利性的,但随着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幼稚衣装应当抛弃,教会应越来越显出纯粹的道德性,成为道德宗教,教会史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正如康德在现实生活中承认恶的正当性,他在教会史中也承认恶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历史总是一个恶的王国,是以人性本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上帝完全有能力摧毁这个王国,但他不这样做,为的是通过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觉醒来做这件事,因为上帝与魔鬼争夺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不是自然之国而是自由之国。但自然之国是自由之国的学校,因而是一个不断进步并通向无限的历史过程。
将康德的这种观点和中国传统伦理比较一下,可以见出有如下显著的区别:
1.中国传统伦理不关心自由意志问题,而热衷于讨论性命、心性;或者说,人们不是把人性归于自由意志,而是把自由意志归结为人的天性、自然本性,而自然之性就是天道天理,本来就是善的,而且必然是善的。所以中国人认为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不是历史,而更像一面镜子,一种"境界",一种永不变化的天真状态。一切成长、发育、变化都属于道德的堕落,人性的退化,都是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的,所以不需要拯救,只需要还原(复性)。
2. 正因为取消了过程,中国人历来主张道德、善的当下性。如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禅宗的"顿悟"、"一悟即至佛",道家的"坐忘"。在这里,没有此岸彼岸之分,不需要设定上帝,在现实生活中即可超越(所谓"内在超越"),而达到圣人、真人和佛的境界。一切都取决于怎么想、怎么接受现实,超越一切现实的道德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也要把它现实化,所以道德的"德"也就是得到的"得",内圣也就是外王,礼也就是法,道德就是政治。
3.中国人的信仰没有二律背反。民间信仰完全是功利性的("历史性的"):圣人(如孟子)的信仰虽然有超功利性("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但最终是为了更大的功利(所以朱熹解释道:"言行不先期于信果","卒亦未尝不信果也")。这个最大的"信果"就是政治稳定、天下太平。所以道德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手段,为的是建立"德治"、"王道",而不存在真正的为道德而道德。
4.中国传统中善恶是绝对对立的,善人做善事,恶人做恶事。善人做恶事总是因为他先已堕落成了恶人,恶人做善事也总是由于他先已改变成了好人。但决不承认善人作为善人也可能做恶事,恶人作为恶人也可能做善事(或"恶是世界历史的杠杆")。所以中国人对历史的评价总是道德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标准表面上好像是依据动机,实际上总是按照后果来决定动机,即"成王败寇"的原则。
以上几点,最根本的是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像规定物一样去规定人的"性"。康德则明确奠定了自由意志的本源地位,将它抬高到摆脱一切经验现实影响的物自体的位置,并由此建立起上帝的超验世界及其对现实善恶的历史导向作用;不是用外在的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恶劣倾向("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就在恶中锻炼出善来,形成由恶向善的进化:这就第一次公开揭示了西方伦理学的内在本质结构,同时也将中西伦理学的根本差异之点摆在了突出的地位。
三、良知
康德的"良知"(注:Gewissen,德文有"确定的"之意。)是"确定的知",因而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这一点与孟子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但不同的是内容:它不是对某件事情应当怎么做的直接知识,而是"自己对自己做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是一种纯形式的规则,即:"切勿冒不义的风险作任何事情"。良知是自己对自己保持距离,当然更是对一切具体行为保持距离。我们要特别注意康德对良知的否定的表达方式:"切勿"做任何"不义"的事,而且是"风险",即可能性。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避免对良知作任何具体的经验规定,避免使之成为现实的绝对原则。孟子的良知则完全是经验的列举: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还不够具体,还要比喻"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都是一些肯定的规定。但可以任意改变、增删、搭配,如说"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都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康德的良知说是消极的,孟子的则是积极的;康德是超验形式的,孟子是经验具体的;康德是内在自省的原则,孟子是实行于外的原则;康德是对自我的超越和警惕,孟子是自我的直接在场,没有对自己"本心"的超越和警惕;康德是理性的、孟子是情感的;康德是基督教的谦恭,把决定权留给了上帝,孟子是无神论的自信,凭自己就可以决定善恶(或如王阳明表述的:"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由此可见,康德的良知只是每个人内心判断的事,很少能在社会上起现实的作用,孟子的良知却是一切礼法刑政的理论根据。王阳明说"致良知"的作用是:用来事亲便是孝,用来事兄便是悌,用来事君便是忠。但当家庭发生冲突、国家发生分裂之际,此良知并不能避免干出昧良心的事来,如在"文革"中,"阶级立场"、"路线"、观点的不同往往导致人们良心的丧失,因为这些具体的原则本身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相反,康德的原则由于超越具体情况,反倒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性的完全泯灭。他举例说,中世纪的异端裁判官能否判人死刑而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他认为,在宗教问题上要能判人死刑,需要一个绝对的"知人心者",但任何现实的人类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本人才具有这种能力,也才具有这种权力,而不至于陷入不义。凡人决不能自诩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或自诩自己对启示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可知,人做此事永远有可能是不义的,而夺去人的生命本身则是确实不义的。所以,以宗教信仰(或无论什么别的信仰)为借口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违背良知的,同样,以某种思想、政治观点为借口这样做也是违背良知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主人公虽不是先知先觉的英雄,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们称之为"义士"。
所以康德的消极意义上的良知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虽然不能促成任何事业,却能避免极端的不人道,也不会因政治观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或改变而导致矛盾冲突。但其前提是:人不可能对善恶作出绝对的判断,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拒绝对绝对善恶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也不是毫无是非,而是寄托于一个超验的上帝。当然,我个人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但我认为不妨从康德的意义上吸取基督教的谦逊精神,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精神,与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保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裁决的能力和余地。我们在认识论上反对不可知论,在道德行为上却应当为未知的、可疑的、不可知的事留下一点空间,这才能使我们的道德观念成为动态的、有生命的、不断前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要用有限的人和事作为绝对的无限的标准,一下子就把问题定死了,没有松动的余地了。从有限现实到无限意义的中介只能是自由意志,只能是永远能动的历史过程,它没有终点。
作者:邓晓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zlX2YZassMSEdVvfZ2KVw
编辑:宋婷
file:///C:\Users\dell\AppData\Local\Temp\ksohtml7108\wps36.png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9-12 09:31
【案例】
纪念尼采逝世120周年丨尼采:德性伦理学......德性政治学?
戴格尔:布鲁克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认为,尼采的伦理教义,可以用一种德性伦理学的形式来重构和理解。德性伦理学聚焦于道德主体的内在状态,关注决定主体行为是否善的内在品性因素。尼采正是在摒弃传统道德观的基础上,以超人的主体类型构想了一种善的观念和实现该种善的行动方案。因此,如斯洛特主张,尼采的伦理思想接近于一种以主体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尼采哲学中,关心所有人兴盛的德性伦理学与宣扬贵族立场、权力意志的德性政治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本文刊登于《现代外国哲学》第14辑,在此感谢译者韩王韦老师的推荐和授权。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尼采:德性伦理学......德性政治学?
克莉丝汀·戴格尔/著 韩王韦/译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15416\wps99.png
▲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
在这篇文章中,我打算重构尼采的伦理教义,并以一种德性伦理学的形式来理解它。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考夫曼(Kaufmann)关于尼采伦理学的丰富译述。在他的经典研究中,考夫曼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尼采伦理学有很大影响。此外他还断言,如果没有注意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尼采思想的激发的话,那么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就不能够被确切地认知。考夫曼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灵魂之伟大”(megalopsychia)这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和超人这个形象联系起来,他的断言就建立在这一联系之上。在论文第一节,我将通过各种方式来考察这一联系,并说明何以我们必须超越考夫曼。如果有人如我一般,选择忽视亚里士多德与尼采伦理学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尼采的伦理学不能够被解读为一种德性伦理学。在第二节中,我将阐明,把尼采的伦理思想解释为一种德性伦理学的培育(forming)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德性伦理学的聚焦点在于主体(agent)的角色发展。我将会给德性伦理学下定义,并说明尼采如何能够被视为一位德性伦理学家。我将会阐述,在那场主要于20世纪显现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中,尼采如何对批评性要素(the critical moment)有所贡献,以及他又如何对这场复兴运动的建设性方案有所贡献。在第三节中,我将处理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只要人们如我一样,把尼采理解为一位德性伦理学家,那么他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牵涉到特定文本中尼采的贵族政治思想。并且,当牵涉到尼采的政治思想,而他的伦理思想的明晰性存在争议之时,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我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主张的解决方式在强调一部分资料的同时,必定会忽视另外一些资料。
▲ 尼采出生地洛肯(Röcken)的村庄教堂
1 尼采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与尼采:“灵魂之伟大”(megalopsychia)与“超人”》一文中,贝恩德·马格努斯(Bernd Magnus)主张,对尼采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由瓦尔特·考夫曼倡导)必须被无视。在经典著述《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一书中,考夫曼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对尼采有着巨大的影响,只有通过那些亚里士多德术语,尼采对基督教的反对才能够被理解。依据考夫曼的观点,尼采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那里的受益是相当之多。他的论断根源于他在亚里士多德和尼采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4卷中的自豪概念(也意指“灵魂之伟大”)和“超人”这个概念之间。马格努斯认为,考夫曼对自豪之人和超人的解读是一种对两者的肤浅解读。进而,马格努斯讲道:“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乃至他的自豪概念——与尼采的道德哲学关系甚小,与尼采的‘超人’概念亦复如是。”马格努斯受到《善恶的彼岸》第198则格言的启发,在这则格言中,尼采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拒斥为“胆怯道德”的一个实例。
马格努斯的主要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幸福”(eudaimonia)和“实践智慧”(phronesis)有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人类依据天性而探寻之物:“eudaimonia”即“幸福”(happiness)。幸福是我们谋求的唯一至善。对人类来说,善是人的独特功能的实现,而人的独特功能,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即理性的运用。“eudaimonia”这个概念的确切解释是,“如果一个人致力于自我天性的积极运用和成功发展,特别是致力于跨时间的人类能力(human capacities)的运用和发展,那么他的生命就会旺盛,生活就会欣欣向荣(flourishing)”。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上文所提及的人类能力即是思想和行动中的理智。因此,如果一个人过着一种理性的生活(即一种被“实践智慧”所引导的生活),那么他就过着一种欣欣向荣的生活。“具备实践智慧者”(Phronemos)即拥有能够判定德性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人,而德性则被理解为过度之恶与不及之恶之间的中庸(mean)。“具备实践智慧者”基于善和幸福来判定德性,而善和幸福归根结底却是一种理智活动的生活。通过把理性视为幸福的根基,亚里士多德将德性树立为一个人自我兴盛(one's own flourishing)的路径。本质上说,德性是我们作为人类必需去张扬(flourish)的品性特征。“具备实践智慧者”基于他作为人类的成熟,即他的独特性和理智能力的发展,而选择德性。因为他在实践上是智慧的,所以在关系到他自己的特定环境中,他不可能不会确定正确的德性。也就是说,在实践上有智慧的人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选择德性,而是为了他们自身而选择德性。查尔斯·扬(Charles M. Young)解释说:拥有了“人之兴盛”(human flourishing)这个确切的观念(conception),该观念出自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7节,有德性者(the virtuous)就会自认为是这样一种存在者(beings),该存在者的本质是一种在思想和行动中让理性得以实现的能力(capacity)。既然依据理性选择原则行事构成了行动中的理性,那么有德性者就会把依据这些原则行事视为他们之所是的关键(constitutive of who they are)。这一种视角方法之于非德性者(nonvirtuous)是无效的。非德性者不能把他们的所为(do)视作他们之所是的表达,因为他们缺乏他们之所是(who they are)的确切观念。

▲ 洛肯尼采纪念馆墙面雕像
马格努斯正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好生活(good life)不会对尼采产生吸引,因为它与灵魂的沉思或理性活动过度纠缠在一起。作为柏拉图式理性主义的另一个实例,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生活的观点必定会被尼采所拒斥。事实上,尼采拒绝那种把人视为一种本质上有理性的存在的观点。他肯定会反对下述这种道德观:一个人通过运用实践理性在每一个行动过程中确立中庸之道,并以此来节制自己的兴盛。另外可能会让尼采感到冒犯的概念是“幸福”(eudaimonia)。没有哪一种道德像亚里士多德目的导向的幸福概念一样会被尼采所拒斥。在《敌基督者》第2节中,尼采说明道:“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权力增长的感觉——就是障碍被克服的感觉。”如果某人自身是其权力意志的表达,那么幸福就会和权力意志的运用相遭遇。这种对权力的断定与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沉思生活截然不同。
莱斯特·亨特(Lester Hunt)赞同尼采的伦理学与人之兴盛和品性塑造(character building)有关。他也认为,尼采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关系不大。尼采的德性主张缺乏审慎(prudence)和智巧(cleverness),而审慎和智巧却是亚里士多德式有实践智慧的人(the Aristotelian phronemos)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尽管如此,依据亨特的看法,尼采依然坚持的是一种纯粹德性伦理学。一种纯粹德性伦理学,按照特里安诺斯基(Trianosky)的定义,是德性伦理学的一种形式,“它认为只有德性的判断才是道德的基础,并且行动的正当性总是从人个性的贤德(the virtuousness of traits)中衍生出来。[……]对于纯粹的德性伦理学而言,个性的道德良善(the moral goodness of traits)总是既独立于行动的正当性,又在某种方式上引发行动的正当性。”亨特认为,在尼采的纯粹德性伦理学中,生命主义(Vitalism)是善的关键。对尼采而言,生命(Life)是唯一真正的善:“人类寻求的所有善只有在某种意义上促进生命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随后还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我赞同马格努斯的观点,认为考夫曼基于两个代表性概念(the two represented figures)之间的细小类似来让两种伦理学等同,是一种过度阐释。如卡梅伦(Cameron)在《尼采与道德的“问题”》(Nietzsch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一书中所说,当尼采谈论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其注意力主要用于亚氏的修辞学和诗学。尼采熟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但却通常并没有把亚里士多德当成伦理学家来处理。卡梅伦指出,一般而言,尼采虽然并没有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严厉指责,但是它并不足以说明尼采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尼采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持有直接或间接的正面评价。例如,在《敌基督者》第7节,尼采用同情的宗教来讨论基督教,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宣称:“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将同情视为一种有病的和危险的状态,时不时使用净化剂(催泻剂)对人而言是有益的:他把悲剧理解为净化剂(purgative)。”尼采想必会赞赏这样一种立场,该立场源自一种需要个性强韧(a toughness of character)的道德。不过,也存在亚里士多德遭受尼采批评的情况。如卡梅伦所言:“因为尼采把亚里士多德哲学视为反狄奥尼索斯的,并且把他自己的道德学说标榜为‘狄奥尼索斯道德’,所以可以推断出,尼采并不觉得他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有一种道德上的亲缘关系,尽管事实上两者都在强调‘人的卓越’。”

▲ 尼采纪念馆的尼采(与母亲)雕像和仿制墓地
2
尼采与德性伦理学
现在,我已经确定,一种在亚里士多德和尼采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不可能的。对于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把尼采理解为一位德性伦理学家。我认为,想要理解尼采的伦理思想,最好是把它理解为德性伦理学的亲缘相似物,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中所发现的那样。二十世纪的德性伦理学究竟是什么呢?“德性伦理学关注品性(character)而不是规则(rules)”,或“德性伦理学研究的是德性而不是正确的行为(right actions)”,我们需要的回答远不止如此。当然,上述定义是正确的,但却远非完善。如果我们要裁决尼采的伦理学是否是一种德性伦理学,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加细致的论断。
德性伦理学的定义提出了一种聚焦于道德主体(moral agent)的内在状态的理论,它并不聚焦于道德主体特定行为的实现(performance)。德性伦理学关注的是决定行为贤德(virtuousness of actions)的因素。因此,它注意的不是行为,而是主体的品性和贤德(virtuousness)。罗伯特·劳登(Robert Louden)认为,德性伦理学具有两个互补的方面:一种批评性的方案和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首先,我想要先探讨一下批评性方案。批评性方案究竟是什么?德性伦理学家总是在或明或暗地批评传统的道德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向我们提供替代性选择的根本原因。受到攻击的传统道德观是义务论的康德主义伦理学(deontological-Kantian)和后果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utilitarian-consequentialist)。具体来说,传统道德观被质疑的问题论点如下:过度依赖道德选择的规范模型,对道德主体性(moral agency)的过度理性主义解释,以及存在于这些理论中的固有的形式主义。第一个论点让人们注意到,一些理论中提出的作为行动最终指导的普遍规范和原则。第二个论点让人们注意到,那种对情感和欲望在道德生活中任何积极作用的否定。德性伦理学家关于第二个论点所做批评是:“道德上令我们最敬佩的人,并不是那些简单地履行职责和依循正确原则行动的人,而是那些伴随着恰当的欲望和情感,履行职责和依据原则行事的人。”可以说,德性伦理学家支持情感和欲望(我们自身的非理性部分)的复兴。至于第三点形式主义,德性伦理学家强调,道德(morality)远不止是一种对职责(duty)概念和逻辑论点的概念性分析。他们还希望在伦理思想中包含其他研究方法。
现在,我将转而讨论第二个方面,建设性方案。建设性方案究竟是什么?在摒弃传统伦理学的同时,德性伦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替代性选择。简而言之,建设性方案力求把注意力重点放在道德主体和德性决定论上。这样以来,德性伦理学就提出了一种人之兴盛的观点。在关注主体品性的伦理学和关注德性决定论的伦理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就伦理的“潜能”而言,我认为更有趣的标本是以品性为基础的伦理学。的确,它对主体以及其品性的关注,给一种以个体兴盛为导向的伦理学的发展留有了余地。如果一种德性伦理学提议要顾及个体的兴盛,那么必然,它就是相对论的(relativistic),或者它足够开阔,以至于能让不同个体按照自己的方式繁荣发展。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教义(tenet),亚氏宣称德性与主体和环境相关。无论如何,这里有着一种避免德性伦
理学沦落为无效伦理学的极端相对主义的方法。
▲ 尼采纪念馆的尼采雕像和仿制墓地
在此,我想思考一下克里斯蒂娜·麦金农(Christine McKinnon)的意见。她提出了一种奠基于自然主义方法(naturalistic approach)之上的德性伦理学。她宣称:“德性理论告诉我们,描述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假设性鸿沟应该被终结了:通过展示什么是人类所关注的自然善(naturally good),他们说明了为什么对人而言,以这些关注(cares)为中心的生活是一种好生活。”她认为,德性伦理学在其不同类型的主张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但她也主张,通过思考个体的天性(the nature of individuals),德性可以被客观地建构。为了支持这一论断,她给出了北美小野狼(coyote)的例子。对小野狼而言,鉴于其天性,拥有一件温暖的外套是自然而然的善事,小野狼的主观性评价(估值)与这种自然善事无关。同样,对于麦金农来说,德性是人这一物种,作为人之所是,所能够拥有的善事,它与任何的目的论考虑或偏好无关。把人与小野狼区分开来的是如下事实,德性不是先天的(innate),为了拥有它,人必须选择一种德性。人虽然并非伴随着德性而生,但却是伴随着培育德性的能力而生。麦金农将德性定义为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性格意向(dispositions),她将之称为性格意向产权(dispositional properties)。于是,主体选择德性作为性格意向,从而可以引导他们通过必要的有益行动和决定,进入一种兴盛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了这种自然主义方法的德性伦理学,仍然会给道德主体的兴盛发展提供各种的可能性,同时还会把有益于兴盛(flourishing-conducive)的德性与道德主体的天性关联起来。不是任何挑选出来的品性特征都会被视为德性。因此,关注于主体品性的德性伦理学是一种“品性建构”(character-building)的理论。主体选择德性去建构他自己的品性。主体被设定为这样一种存在,她会拥有一个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目标是幸福,但它也可以是其他什么东西),并且会通过建构她自己的品性来使自己离这个目标更接近。这种建构品性的进程和目标的实现,可能会激发人之兴盛。因此,德性伦理学是一种以人之兴盛为首要关怀的伦理学。
那么,在一种新的、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意义上,尼采伦理学能否算得上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呢?对此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将会说不,他主张不能把尼采的伦理学理解成为一种德性伦理学。他认为,尼采只对德性伦理学家的批评性方案有所贡献。不仅如此,依据莱特的看法,尼采在摒弃道德上面比德性伦理学家们走的更远,尼采不仅摒弃了传统的道德观,他还摒弃了所有形式的道德观。与莱特相对,我认为,在尼采那里存在着一种伦理学的方案,尽管它呈现的不系统,并且还可能需要去重新构建。莱特宣称尼采对“道德批评家”(Morality Critics)(这是莱特对批评传统道德的伦理学家的称呼)的批评性方案有所贡献,他是正确的,但在谈及尼采的非道德主义时却犯了错误。
有意思的是,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一位当代的德性伦理学家,他以谨慎的态度接近尼采,并质疑了尼采的方案对人类同胞缺乏坦诚(openness),因此可能是不合格的。经过审慎地评议之后,斯洛特推断说,尼采是“一位伦理学家,他认为我们应该推广善,但是,他对什么是善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和有争议的看法。”因为尼采构想了一种善,并且给出了如何实现善的方案,那么他肯定是一位伦理学家。斯洛特进而主张,这种类型的伦理思想接近于一种以主体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它致力于关注主体品性的发展,而并非具体行为的实施。这是尼采的伦理方案必须采取的方法,我赞同斯洛特的这一看法。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尼采是如何提出这种以主体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的。

▲ 尼采纪念馆的尼采雕像和仿制墓地
3
尼采的德性伦理学
在这一节中,我将描述尼采自己的德性伦理学。显然,尼采确实对德性伦理学家的批评性方案有所贡献。他对于传统道德和他所提出的虚无主义的攻击清楚地表明,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之于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疏离异质的。在《快乐的科学》中他说道:“‘别做这!放弃吧!克制你自己吧!’这种道德说教根本不对我的胃口。相反,令我喜欢的道德是能够激励我做某事的,并且是激励我从早到晚地一直做,晚上也会梦到它,除了想把它做好以外不考虑其他,如果我可以独自完成它就更好了![……]我不喜欢一切否定性的德性,即那些有着否定本质和主张放弃自我的德性。”(304节)另外,在《偶像的黄昏》中,他谈到了一种道德的罪过:“在每一种宗教和道德的基础上,都有着这样的普遍公式:‘做这个和这个,不要做那个和那个,这样你就会幸福!否则……’每一种道德、每一种宗教都是这种律令——我将之称为理性的巨大原罪,永恒的无理性。”(“谬误”2)尼采对传统道德的观点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不过,我认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上述引证已然足够。这两段引文澄清了尼采与道德的关系。传统道德的问题在于,它没有顾及到人性(human nature)。它没有如个体所是的那样来看待个体,虽然它力图接受个体,但相反却把人类现实中没有根据的模式(model)强加给了个体。
这种模式是一种超验的自然(transcendent nature),它与人类的内在自然不搭。
让我们回忆一下,在德性伦理学家的批评性方案中,传统道德受到指责的三个要点:过度依赖道德选择的规范模型,对道德主体性的过度理性主义解释,以及存在于这些理论中的固有的形式主义。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谈论德性伦理学家,那么我们会轻易地认定,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批评与尼采有关。尼采拒斥规范模型。他的创造性伦理学(ethics of creativity)认为,人必须为自己创造价值,而不是依赖任何外在的(超验的)规则。尼采也严厉地拒斥了那种对道德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解释。他努力恢复人性中被压抑的部分,并声称理性只是我们人性中一个非常细小的部分。他在一种虚构层面(a fiction)上来讨论人类(参见《朝霞》105节)。我们把“我们”这个概念搞错了:我们被引导地相信,我们恰好是理性和感性的二分。但这种二分是幻象。人类是一种由“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善恶的彼岸》19节)。我们拥有一个作为“本能和激情的聚合结构”的灵魂(《善恶的彼岸》12节)。尼采进而说:“如果我们渴望并且敢于依据我们的灵魂特性构造一个建筑(在这点上我们过于胆怯!)——我们的样板必定会是那错综复杂的迷宫!”(《朝霞》106节)事实上,我们决不是自我(The self)的传统构想,也决没有那种特别是由传统哲学方法和道德观所提议的理性的优越性。最后,尼采显然也拒斥了传统道德固有的形式主义,因为在思想中他通常会拒斥任何的形式主义。
尼采确实对伦理学家的批评性方案所有贡献。他提出的虚无主义应该对异化的传统哲学(及宗教)话语有所补救。但是,他是否止步于虚无主义的时刻?难道他的方案正如莱特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然虚无主义的?我在其他地方论证过,尼采的哲学是彻底建设性的,而绝非纯然的虚无主义。他的挑战在于通过摒弃现有的道德来重构一种新的道德。旧体系的缺陷不能够通过重组来校正。人们必须清除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他对道德的攻击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此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及其形而上学意义。尼采对他归因于自己的非道德主义很清楚:“根本而言,我所说的非道德主义者一词包含有两个否定。首先,我否定那些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高等的人,如良善之人(the good),乐善之人(the benevolent),行善之人(the beneficent);其次,我否定一种已经被接受并作为道德本身起支配作用的道德——颓废的道德,更明确地说就是基督教道德”(《瞧,这个人》,“命运”,第4节)。这样,尼采就把他对道德的拒斥清楚地定义为对传统道德的拒斥。他也谈及了非道德主义者同伴,他们“在肯定中寻找[他们的]荣耀”(《偶像的黄昏》,“道德”,第6节)。可见,并不存在放弃伦理学的问题。伦理学是必需的,并且将成为他重构工作起始的当务之急。只要它能够导致对错误伦理学的摒弃,它就是重构工作之前的当务之急。虚无主义是朝向这种重构的一个必要步骤。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所言:“我们要否定,并且必须否定,因为我们内在的某物想要鲜活并且肯定自身,此物目前我们也许还不了解,甚至还未曾察觉!”(307节)。

▲ 教堂祭坛后尼采出生的牧师住房
那么,想肯定自身的东西是什么呢?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尼采说道:“对于自身的存在,我们必须自己为自己负责;因此,我们想要扮演这种存在的真正舵手,想要让它远离一种随机的偶然性”(第1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人是成功的变为自己主人的人。他是一个人上人(Overman),超越了人的内涵,他是一个比人的内涵更加丰富的人类。为什么更丰富?超人是克服了传统固有分裂的个体。他是一个重新统一了自身,并决定完全如其所是地生活的人。他也是一个知道生活就是权力意志,并且知道自己是这种权力意志的一个实例的人。因此,他希望表现和尊重自己身上的这种权力意志。除此之外,他还接受了永恒轮回的假设。他准备假定,他一生中所做的行为和决定都将相同地永恒复返。从人到超人的转变是极其巨大的。转变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不能说从人到超人是一种上升(elevation),而应该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变形(transfiguration)。在尼采的著述中,即使最高种类的人,强壮的人(the strong man),也远比超人低下。他说:“你们的灵魂对伟大的事物如此陌生,因此超人的善也会让你们觉得可怕!你们这些聪明的和被启蒙了的人,你们会从智慧的烈日下逃逸,而超人却喜欢在这火热中裸晒!我的目光所遇到的你们这些至高者啊!我想,你们会把我的超人——称作魔鬼!这是我对你们的怀疑和窃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人的聪明”)。
超人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类型。每个个体都应该效仿这一理想形象,例如,只有当一个人从事创造性工作时,他才能够成为理想形象。当我说理想类型(超人)时,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努力向之看齐的形象,而不应该被混淆为一种人们可以达到的状态。一方面,在尼采的思想中,是否将来会出现超人,这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带给我们的这个形象阐释为一种动态的存在状态(a dynamic state of being)。如果超人接受生命以及接受他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实例,那么他将不断地演变(becoming)。追求更多权力的动力,这个尼采的存在(being)的特征,将导致个体持续不停地流变,以及不断地克服自己。这正是人们应当如何理解的超人之超越(über of übermensch)。但即使我们在谈论一种“流变状态”(state of flux),它也是一种当人投身于实现过程中时应该努力获取的状态。依据尼采的看法,为了接近卓越进而成为一个超人,有些事情是人们必须做的。创造自我和创造价值属于这些必做之事,这对于支撑一种新的伦理学而言至关重要。人类应该是自己的创造者。她(人类)应该是自己的主人,并且为自己制定规则(这正是那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主人道德”的意味)。一旦价值的领空被清空,那么人的任务就是去重新填满它。个体应当不再依靠任何超验物来提供这些价值,正如先前的基督教试验一样,它的超验道德已经证明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异化。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伦理学。个体必须创造出一种尊重自己作为人之本性和作为权力意志的本性的伦理学。这在尼采的如下箴言中被表达了出来:“你的良心在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快乐的科学》,270节)你必须兴盛!请注意,直到《善恶的彼岸》为止,在尼采的著述中都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表明,超人的道路仅仅是为某些个体准备的。他清楚说明这种潜能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身上。这只是个体依照权力意志选择去实现其自我的问题。于是,通过采纳某种与人的自身存在相一致的德性,强调的重点就被安放在了主体的兴盛之上。
就此,人们必须把尼采哲学的生命主义包括进来。在《敌基督者》第2节,尼采把这种生命主义表达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好?——所有提高人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东西。什么是坏?——所有从软弱里产生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幸福?——权力增长的感觉,一种障碍被克服的感觉。”如亨特所说,尼采的观点是:“生命是唯一的本身是善的东西,它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我们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表述他的基本道德原则:“任何肯定、创造和增强生命的东西都是好的。”个体必须依据此原则来选择价值,因为,如亨特所说,“人类所追求的一切善,只有在促进生命的意义上,才是好的”。因此,人类只能作为生命的一个实例来促进自己和自身的存在。个体将会忠实于自身。唯其如此,某人才能够说得上是作为一个人类而兴盛。所以,我们可以跟随着亨特说,尽管可以从权力意志中得出一个基本规则,但是尼采关注的焦点却是在品性发展之上,而不是在规则之上。
▲ 教堂墙下的尼采与家人墓地
那么德性呢?亨特认为,尼采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德性清单是可以完成的。[……]每一次一种德性的出现都与其他德性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除了‘每个人的特殊德性’以外,确实不存在什么德性。”(《快乐的科学》,120节)如亨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尼采那里(《朝霞》和《善恶的彼岸》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份德性清单。尼采在这两本著作中,认为勇敢、慷慨、文雅(politeness)、诚实、洞察力(insight)、同情心以及孤独(solitude)是德性。不过,人们觉得还有更多的德性存在,因为这两个清单并不详尽,并且没有怎样变贤德的秘诀,相反,传统道德就提供了这种秘诀:努力获取这些德性,你就会变得贤德。在尼采的思想中,德性与个体相关。但德性相互之间却可以是冲突的。在尼采的新伦理学中,人为其自身所采纳的一切德性,都是以自身的完成和兴盛为旨归。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与德性相关的品性概念是多么核心。德性的采纳应该基于人品性的发展。而品性则是需要改进的。当我们依据如何增强权力意志这个问题来考察品性时,就可以确定这个品性是否是好的。这样,被贤德主体完成的行为就是好的,因为这个主体的存在是贤德的,并且一些能够促进生命的行动其本身就是好的(good in themselves)。这正是生命主义与德性伦理学的关联之处。
除了超人和权力意志以外,永恒轮回这个概念在尼采的伦理思想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把永恒轮回视作一个本体论概念。尼采并不想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相反,他想制作一个为行动指南提供服务的思想实验。这是一个伦理学假设。就其本身而言,它有助于对行动选择进行验证。个体必须自问,是否想看到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the course of action)永恒复返。人们必须把自己的选择当作仿佛会永远复现一样来选择。从永恒轮回的视角来看,我不能选择令我不幸或愤恨的事情,因为这种不幸和愤恨将会困扰我一生乃至永生!而且,不幸和愤恨并不能够导向一种兴盛的生活。因此,人们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兴盛的生活。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想不断重复时,这个选择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什么是一种人人力求的好生活,决定它的是那服务于指导选择的概念: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如果一个选择能够像权力意志那样促进生命,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人们希望一个选择永恒复现,那么它也将会是好的。这两个考量是并行的,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选择通向其所觅求的兴盛生活时,他才会希望它永恒复现,而人只有依照权力意志实现自身时,一种兴盛的生活才能够发生。对于一个完美的世界来说,尼采的命令(injunctions)和处方(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似乎并不合适。他要求我们成为自己,但他也要求我们变得强大。我们的兴盛不在于安静的满足感,而在于一种不断的克服(overcoming)。他的德性伦理学及其对人类主体的要求确实非常苛刻。

▲ 尼采墓地
4
尼采的德性政治学?
在《敌基督者》第2节中,尼采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更多的权力;绝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不是德性,而是卓越(文艺复兴风格的德性,virtù,非道德的德性)”。这是他所描述的方案,依循的是他对自己奠基于生命主义的道德原则的描述。接着,是一个尼采自己的博爱宣言:“弱者和失败者应该灭亡[……]为此人们应当助他们一臂之力。”(《敌基督者》2节)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尼采哲学中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紧张。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依据能够把尼采理解为一位德性伦理学家,他关心的是所有个体的兴盛,那么,当他政治地言说时,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具备走上自我超越的道路的可能。因为每个个体都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实例,每个人都可以以此为任务来实现(他或她)自己的存在。一些人将会实现,一些人将不会实现。如果他们没有实现,那么他们就是人类中的低等类型。但是,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东西会阻挡人成为超人。鉴于此,我认为,尼采需要去提倡一种有利于所有人兴盛的政治体系。
这就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是一种关心集群中的个体兴盛的政治学。德性政治学想要构建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个体都拥有相同的自我兴盛的机会。没有人会陷入被压迫的或极端匮乏的地位,从而使其无法追求自我的发展。一种关心集群中所有人的兴盛的德性伦理学应该会宣扬机会上的平等。这并不必然会导致一种结果上的平等。再次申明,在尼采的构想中,一些个体会选择成为超人,而另一些却不会。他的想法是,在决定个体是否选择成为超人,或不成为超人即使他有这种选择能力时,社会和政治秩序不能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个体自身。那么,德性政治学会倡导一种什么样的政体?似乎能够最大化实现机会平等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民主政体,甚或是社会主义(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形式,而并非我们在20世纪某些国家中发现的冒牌的社会主义)。
应该遵循什么?我们都知道尼采鄙视过这两种政体形式。他厌恶民主并且嘲笑过社会主义。他说:“对我们而言,民主运动不仅是一种政治组织的衰败形式,还是一种人类的衰败形式,即渺小化形式,是人的平庸化和价值贬值”,他进而讲道:

▲ 位于瑙姆堡 (Naumburg)的尼采故居
“人的总体退化,直到出现今天社会主义蠢货和傻子所以为的‘未来人’——作为他们的理想!——退化和渺小化使人变成完美的畜群动物(或者依据他们的说法,变成‘自由社会’的人),人的动物化会令其变成平权及平求[]的侏儒动物,这无疑是可能的。谁把这种可能性思考到底,谁就了解到了其余人未曾了解的一种恶心,——但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使命!……”(《善恶的彼岸》203节)
这正是尼采思想的紧张之处。当他接触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完全不能清楚断定他就是一位“德性政治学家”。在许多文本中,他似乎采用了一种贵族的立场(如果不是柏拉图主义立场的话),这种立场只关心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体。他在许多地方似乎在倡导一种压迫的政治学,这与我所描述的德性伦理学不一致。在《善恶的彼岸》中他非常明确地说:“迄今为止,‘人’这个类型的每一次提高都是某个贵族社会的作品——而且永远都将如此:该社会信仰人和人之间有一条等级顺序和价值差距的长长阶梯,并且在无论何种意义上都以奴隶制为必需。”(257节)。在同一本书中他再次继续说道:
“那种内部个体皆以平等自处的群体,如前面所假设的那样——在每一种健康的贵族制中都是如此——如果它是一个有生气的而非垂死的群体,那么它内部的个体被禁止对他人所做的一切,也必然会施诸于另一个群体:它必将成为一个肉身化的权力意志,它将力求生长,扩张,抢夺,赢得优势,——这不是缘于哪一种道德性或非道德性,而是因为,它活着,因为生命就是求权力的意志。[……]“剥削”并非某种腐败或不完美的、原始的社会所专有:剥削作为一种有机的基本功能,它是有生命者的本质,是真正的权力意志、即生命意志的一个后果。”(《善恶的彼岸》259节)
现在,除非有人认为,在超人的英明指导和温和压迫下,软弱的人类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兴盛发展,看来,想调和贵族政治学和一种关注于兴盛的德性伦理学似乎是不可能的。
▲ 尼采故居(绘画)
在给个体对他人自由的估价提供依据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我们需要主动地促进其他个体的自由,以便他们也能如此地回报我们。她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都致力于挣脱压迫的解放运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为了他能够自由而让其他人自由(要真实,发挥自由,做出自己的选择,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果对每个人而言目标是作为真正自由的存在去兴盛,那么他就需要所有人在一个倡导机会平等的社会中进行合作。波伏娃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解释为何每个个体必须为他人的自由而努力的语境下,她以如下方式批评了尼采的观点。她说,一种让每个人试图发挥自己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哲学,只会导致个体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如果权力意志的运用被理解成为纯粹力量的运用,那么就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合作。不过,我们知道权力意志与残暴力量的运用无关。尼采甚至会把残暴力量的运用视为权力意志的一种衰败和退化的例证。令人惊讶的是,或许出于对波伏娃的厌恶,人们可以使用波伏娃作品中的相同论据来支持尼采那里有一种德性政治学。因为每个个体都是权力意志的例证,而追求兴盛则意味着,为了每个人能够具备兴盛的能力,所有人都要合作创造出最好的条件。在波伏娃的模式中,一个真正的自由个体所追求的是人类的兴盛,然而,在尼采那里,一个真正个体的兴盛是其所追求的权力意志的表达。
但还是要强调,尼采的大量文本都支持一种贵族的政治学形式,而上面的论述与这些文本很难能关联起来。人们会试图问下述问题:那么,当尼采讲优生学和消灭孱弱个体时他是认真的吗?当他说弱者与不合格者应该灭亡,并且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灭亡,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他将此称为自己的博爱。我们是置身于隐喻之中?抑或这些是对未来政治学的具体陈述?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可怕的人,通过消灭弱者,清除了上述的紧张局势。如果你的社会里尽是强壮的个体,那么你就可以拥有一种非压迫的政治学,它关心所有人的兴盛,并且会和德性伦理学保持一致。不过,在另一些段落中,尼采描述了一个需要孱弱者照料事务的社会,因为超人只关心他们自身的兴盛。例如,在《善恶的彼岸》中他说:“一个好而健康的贵族社会的本质在于,贵族并不觉得自己是职务(无论是王国的还是共同体的),而是觉得自己是它们的意义和最高的证成(justification),于是,他心安理得地接受无数人的牺牲,后者因其自身之故,必须被贬抑和降黜为不完满的人,成为奴隶和工具。”(258节)
那么,难道尼采拥有一种与我之前的定义有所不同的德性政治学?

▲ 位于魏玛洪堡(Humbold)街36号的尼采档案馆,系尼采生前的最后住所。
我所说的德性政治学关注的是一个集体中的个体的兴盛(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s within a group)。我们能否有一个关注于作为集体的个体的兴盛(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s as a group)的德性政治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把压迫作为强壮个体兴盛条件之一的社会,如果它能够导致一个集群的兴盛,那么它似乎就是可接受的。个体的兴盛并不重要;相反,整体的兴盛才是主要焦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希腊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大部分城邦居民的被压迫状态是城邦福祉的一个条件。我强调过,希腊民主之所以能够兴盛,不过是因为它在高等个体专心于高级事务的同时,依赖大量的奴隶去照料琐碎的事务。尽管尼采确实对古希腊城邦的一些特色有所赏慕,但倘若说他在谈论超人的时候会赞同这一点,却是很难想象的。
尼采会涉及的古希腊政治模式之一就是柏拉图的那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谈论了一种由三个阶层组成的理想城邦:监护者,战士,手艺人和农民。柏拉图解释说,战士的孩子将接受一个非常严格的教育计划,其能力将被测试,只有他们中最好的才会完成这个计划并且成为监护者。某种程度上,战士的孩子拥有一些机会上的平等。他们都有成为监护者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取决于金字塔底层(手艺人和农民)的存在。结果,我们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关心所有人兴盛的机制,相反,却发现了一个关心特定个体集群的兴盛的机制。
再次重申,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尼采的立场是,为一个只对一群人的兴盛有利的机制辩护。在我看来,从第二种意义上,谈论促进作为集体的个体兴盛的德性政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暗示为了一些个体的兴盛可以牺牲掉另一些人。那么,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关心每个人兴盛的德性伦理学,并且只有当你把尼采批评和拒斥的制度当成一种政治制度时,它才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出路?
难道除了道德问题以外,我们还需要在政治问题上进行价值重估吗?在道德上,尼采的任务之一就是批评和拒斥现存的价值。他也批评和拒斥道德。拒斥所有的道德吗?不,如我们前文所述,他只拒斥一种特定的道德,即那种不利于人类的道德。所以,尼采为了提出一种新形式的道德而重估道德。那么,一种道德的观念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只是某些特定的概念被抛弃了。民主难道也是如此吗?假如尼采真是批评和拒斥某种民主的特定形式会怎么样?假如他想去实现一种关心所有人兴盛(人们可以选择去兴盛,也就是说,一种机会平等)的政治体制会怎么样?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一种政府的民主形式。但是,正如他在他那个时代所见,民主会导致平庸。民主滋生平庸的个体,并且关心基督教德性,即弱者德性的培育。但是它真的必须如此吗?尼采认为,在民主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均等(adequation)。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美化了的民主,至少我们可以尽量在道德领域中设想一种价值重估。一种遵循尼采所倡导的新道德的民主,不会最终滋生出一种软弱个体。相反,它将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该体制包括了与尼采德性伦理学相符合的德性政治学。在我看来,这是把政治的尼采与伦理的尼采等同的唯一路径。

▲ 尼采档案馆内景之一
5
结论
在最后章节中,我已经阐明,把尼采的伦理观点与政治观点接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把他理解成为一位贵族政治论者,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和一些文本所呈现的那样,会排斥我所描绘的德性伦理学进路:该进路试图关心所有作为权力意志实例的个体的兴盛。的确,人们可以把尼采的伦理学解释为完美主义的和类似的德性伦理学,而不是把它普适化(universalizing)。在这种语境中,一种迎合高等个体兴盛的贵族政治学就是美好的。但是,这并不是我所采用的解释路线。鉴于我认为尼采德性伦理学是普适的,那么贵族政治学就会导致冲突。一个简单的出路就是说在尼采那里没有真正的政治方案。确实,人们经常会有如下印象,即尼采的个体,伦理个体,是一个孤独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上述看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查拉图斯特拉向民众言说,而并不和民众交谈。我们拥有的不是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对谈录》(Thus conversed Zarathustra),而是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孤独者。尼采把孤独这个德性囊括进他的清单中——另一种传记元素(biographeme)?如果一个人是独身(alone),并且致力于其自身的兴盛,那么德性伦理学就是美好的。但“没有人是座孤岛。”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且需要一种会让我们成功地一起生活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那么,超人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德性政治学来配合那貌似可取的德性伦理学方案呢?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德性政治学是一种重估的民主政治。即,不再是一种向下拉平的民主,而是一种力求让个体高级化的民主,一种关注所有人兴盛的民主。
作者致谢:
我要感谢Leah Bradshaw,她细心地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前的手稿,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也要感谢Martine Béland,他对我关于尼采政治学的一些想法也给予了最应该感谢的严厉批评。Brian Lightbody对本文的后半部分有所贡献,在我的一次关于尼采思想中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演讲中,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来源:微信公众号 伦理学术
编辑:贾梦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9-28 17:52
【案例】
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
注:【引用此文,请按照以下格式:韩东屏.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批判[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1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HUST2020-0009)。
作者简介:韩东屏(1954—),男,辽宁大连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哲学。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15页。
摘 要
康德的伦理学在学界广受推崇,但其实很烂。因为以他的伦理学奠基之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来看,存在的错误甚多,而且其中很多属于基本性的大错误。这些错误,可从方法与观点两个维度揭露。方法方面,其基本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徒有虚名,也不能成立和实际运用,同时还存在许多具体方法的错误;观点方面,其系列观点,包括初始观点、基本观点和最终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并且这些错误的观点之间还存在相互不自洽的情况。因此,此书有直接价值的地方甚少,想找到“道德最高原则”的初衷也没实现。何以至此?主要是康德在事物自身问题、人性问题、道德问题和至善问题上存在重大认知迷误。而“人本伦理学”理论则没有这些弊端,也找到了能经得起推敲的至善与道德最高原则。
关键词
康德;伦理学;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人本伦理学》
康德的伦理学和他的其他哲学著述一样,都有大批满怀敬佩之情的追随者。可在笔者看来,康德的伦理学其实非常糟糕,错误甚多,并且有不少是基本性的大错误。
康德的伦理学由《伦理学讲演录》(1775—1782)、《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这几本先后出版的著作构成。鉴于它们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只存在内容多少的差异,而第二本书又属于对“原理”的奠基,简明起见,这里就只以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研究对象,来展开对康德伦理学的分析与批判。
康德伦理学的诸多错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方法方面的错误,另一类是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以下将分别揭露这些错误,然后给出总体性评析。
一、方法性错误
康德的《原理》是从介绍他要用于此书的自创性研究方法开始的,这个方法就是不依赖任何经验的单纯形式化的形而上学。可是,这种研究方法真的存在吗?康德又是否是在用它进行研究?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
考察康德自己论及的三个相关观点,就可知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并不属于“完全消除了一切经验”的道德理论。一个观点是,“全部理性知识,或者是质料的,与某一对象有关;或者是形式的,它自身仅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一般地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1]35;另一个观点是,“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称为逻辑学”[1]36;还有一个观点是,“逻辑学没有经验的部分”[1]35。将这三个观点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在康德那里,逻辑学属于“形式的”“理性知识”,因为逻辑学就“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而所谓“形式化”,不仅指没有“质料”、没有“某一对象”,也指“没有经验的部分”。所以,逻辑学就是没有质料、特定对象和任何经验的理性知识。
那么“道德形而上学”是什么?康德说它是形而上学的两种类型之一,另一种是“自然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的对象性应用,即“当它(指逻辑学)限定在知性的一定对象上的时候,被称为形而上学”[1]36。既然道德形而上学是以道德为对象的,那它实际上就是“与某一对象有关”的有“质料的”“理性知识”,而不是“不涉及对象差别”的“形式的”“理性知识”,自然也不是“单纯是形式的纯粹哲学”,当然,也就无法提供不以“来自经验的论据为依据”的“思想的普遍必然规律”。换言之,这样的道德形而上学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一切属于人学的东西的道德哲学”[1]37。
康德的实际做法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原理》“前言”的结束部分介绍了他在此书中“制订”道德哲学的方法:“它分析地从普通认识过渡到这种认识的最高原则的规定;再反过来综合地从这种原则的验证,从它的源泉回到它在那里得到应用的普通认识。”[1]41 这就不能不让人生疑:如果道德形而上学真是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的理性知识或纯粹哲学,为什么要“从普通认识”而不是直接从形式化的命题或纯粹理性认识开始?由于所谓“普通认识”就是被康德不屑的依赖经验或来自经验的认识,就是“大众的道德哲学”或“属于人学的东西”,这就说明,康德研究道德和建构道德哲学的方法,同样是要从经验开始,并依赖经验才能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形而上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对从普通知识得到的最高原则起验证作用,并且最后还是要再回到应用的普通知识。可是,在康德之前的那些没以“形而上学方法”自诩的伦理学理论,哪个没有对自己所提观点的验证?又有哪个不认为自己的最终结论是可以应用的普遍性道理?
何况,根据康德自己在此书稍后地方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名称的解释,道德形而上学也不应该和不能够从普通知识开始。这个解释是:“在我们得之于经验的,对人性的认识中是否到处都能找到道德原则,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些原则完全是先天的,不沾带一毫经验,只能在纯粹理性中找到,而半点也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那么,是否应当把这种学问作为一种纯粹实践哲学,或者用人家的贬意之词,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区别开来,让它独立地使自己得到充分地了解。”[1]60-61 它的意思很清楚,“先天的,不沾带一毫经验”的道德原则,“只能在纯粹理性中找到,而半点也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既然如此,《原理》为什么要从属于经验的普通知识开始?这套从经验开始的理论又如何配称“道德形而上学”?
因此,那种所谓可以不依赖任何经验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并不存在,康德的《原理》同样是含有经验成分的非单纯形式的道德哲学。在方法上,它与之前的其他伦理学理论,并无任何实质性不同,顶多是给自己理论加上了几个唬人的华而不实的修饰词而已,即“形而上学”“纯粹哲学”和“涉及理性自身”之类。
康德的所谓不依赖经验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不仅不存在,而且,即便算它存在,也完全没有必要性,更不是他说的研究道德的起点。
康德在论述道德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时有如下论述:
一个道德形而上学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如果找不到主导的线索,找不到正确评价的最高标准,那么道德自身就会受到各式各样的败坏。要使一件事情成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规律还不够,而必须同时也是为了道德而做出的;若不然,那种相合就很偶然并且是靠不住的。因为,有时并非出于道德的理由,也可以产生合乎道德的行为,而在更多情况下却是和道德相违反。现在,除非在一种纯粹哲学里,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在实践上也至关重要的、真纯的道德规律。所以,形而上学必须是个出发点,没有形而上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会有道德哲学。[1]38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想找到道德上“正确评价的最高标准”或“真纯的道德规律”,必须从形而上学出发。但是,既然在还没找到它们时,道德实际上已经存在,否则道德就不可能“受到各式各样的败坏”,也不会有“合乎道德规律”或“为了道德而做出”的情况,那么,最高标准和道德规律就应该是在既有道德和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寻找或提炼,而那个要排斥一切经验其实也就是排斥一切客观事实,从而也就是一定要排斥一切既有道德的形而上学,则毫无用处,更谈不上“必须是个出发点”。
道德形而上学不是可行的研究方法,在《原理》的细节上也能看出。
康德说:“必须时时注意,不要通过例证,即通过经验,来证明在什么地方有这样一种命令式。”[1]70 此话表明例证就是经验。既如此,对要清除一切经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来说,就不是仅有命令式不能用例证来说明,而是一切问题都不能。但《原理》中不仅在属于普通知识论述的第一章里有大量例证被用于区分“合乎责任”与“出于责任”的行为[1]47,而且在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论述的第二章和属于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三章里,也都有例证式的论证。第二章在谈到命令式、理性是自在目的等问题时都用了大量例证;在论述幸福不能作为道德原则时干脆直接说:“经验已经证明,人的处境良好,他的行为也随之良好的设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1]96 第三章在论证普通人“也能从感性冲动中得到自由”的观点时,也用了一个关于流氓的经验例证[1]110。这就充分说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同样离不开经验。
在《原理》中,康德有时会以“我们知道”“众所周知”之类的话语,作为其所提观点的正确性依据,例如他说:“每个人都会承认,一条规律被认为是道德的,也就是作为约束的根据,它自身一定具有绝对的必然性。”[1]37 但那个每个人都承认的观点,是他们用形而上学的纯形式化的思维得知的吗?如果是,就说明道德形而上学早在人们心中,根本无须康德建构;如果不是,那每个人岂不就是凭自己的经验知道的?这就说明,康德这时也是在以经验作为自己观点的依据,只不过是共同经验。
《原理》除了基本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成立之外,还存在一些具体方法的错误。
其一是缺少对“道德”的界定。《原理》是以“道德”为对象的著述,以找到“正确评价的最高标准”或“真纯的道德规律”为研究目的,也使用了一系列由“道德”派生的概念,即“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哲学”“道德学家”“道德价值”“道德规律”“道德原则”“道德命令”“道德诫律”“道德评价”,等等。但是,书中却始终没有关于道德的本质性界定,这就无法使人明了他所说的“道德”究竟是指什么,那一系列带“道德”字眼的概念又是些什么所指。虽然康德后来也引申出了一些关于所谓“道德概念”的说法,但它们既算不上道德定义,也不是针对既有道德说的,而是说的他从责任推出的道德规律:“这种纯粹的,清除了出自经验外来要求的责任观念,一般地说,也就是道德规律的观念。”[1]61 康德被公认为是个逻辑性很强的哲学家,注重对概念的定义,也确实定义了很多概念,可是为何单单就不定义此书中最基本也最该首先定义的道德?只能是这种解释:康德还不知道道德的本质。康德在批评以往学者论述的道德原则时,指责它们没阐明道德,就暗中将其作为前提,这就会“不可避免地陷于循环论证,不能不把应该去阐明的道德,暗中当作为前提”[1]97。可他自己还不是这样做的!
其二是《原理》正文的开端有些莫名其妙。按照这一章的标题“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来看,应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或“道德理性”开始论述,但说的却是“善良意志”,一连几页都是如此,并且完全不交代如此开端的缘由。固然,从此章的实际论述过程看,康德是要由“善良意志”引出“责任”的概念,因为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此后再通过考察“合乎责任,而人们又有直接爱好去实行的行为”,推论出关于行为的道德价值的结论[1]49。可问题是,“善良意志”这个此前没人听说过的概念,是属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吗?再者,在善良意志这个概念还没被康德创造出来之前,人们显然也是知道责任并承担责任的,这时责任难道也是善良意志的体现?如果是,康德就不用再往下论述了;如果不是,那么,难道那时的责任就从来没有被体现?还有,责任至少存在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之分,那么,凭什么说从全称责任概念直接推出的就是行为的道德价值而不是法律价值?这些均说明,善良意志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开端。
其三是不先说明善是什么就大谈善良意志如何、如何。从逻辑上说,“善良意志”是“善”的下属概念,即先有“善”后有“善良意志”,因而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善”是什么,也就不可能知道“善良意志”是什么。在此情况下说再多善良意志是什么,如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自在的善”“彻头彻尾的善,而绝不会是恶”[1]90;它“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并且是“绝对价值”[1]43、“无可估量的价值”[1]78,“无比高贵”等,就全都是些没有根基的独断。
根据康德后面的论述可知,善良意志所以为善良,在于它愿意使自己的“准则变成普遍规律”,即适用于所有人的道德原则或实践规律,而实践规律也正是“对行为的道德评价的标准”[1]75。于是,能成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行为准则就是善,而违背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行为准则就是恶。可即便有了这些说明还是无济于事。首先,按照逻辑常识,一般性的善恶概念不能从特殊性的善恶概念如善良意志中引申出来,因为特殊只是一般中的情况之一,无法代表一般。而康德的善恶概念,却就是从特殊的善即善良意志推导出来的。其次,还可继续追问:为什么准则具有普遍性就可称“善良”?康德对此再没做任何解释。无论是“普遍性”,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准则”,都只是事实词,而不是价值词。如是,怎么能说普遍的就是善良的?如果一定要这么说,就必定属于犯了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即把“是”等同于“善”。并且,如果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就是善良的,那就意味着与它相反的情况,即非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必定是恶劣的。可这个推论能成立吗?按照康德的意思,帮助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是可以普遍化的行为准则[1]75,不过这种帮助存在多种形式,或情感送暖,或慷慨解囊,或肢体出力,那么,谁能说出其中的哪个准则是可以普遍化的?谁又能说,它们中不能普遍化的准则就都不仅不是善良的,反而还是恶劣的?又比如,“勿食荤”就不是普遍命令而是个人准则,可它是恶吗?
康德对善良意志的论述还存在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说,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善,而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另一方面又说,“我的行为的必然性构成了责任,在责任前一切其他动机都黯然失色,因为,它是其价值凌驾于一切之上,自主善良的意志的条件”。这就出现了两个悖论:一是无条件的善良意志却需要以责任为条件;二是体现善良意志的责任竟然是形成善良意志的一个条件。后一个悖论似乎不明显,其要害在于:一个东西的体现,不可能同时又是这个东西得以出现的条件,譬如黄色作为香蕉的体现,并不是导致香蕉出现的条件。
康德关于善良意志“是自然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不须教导”而“只须解释”[1]46 的观点也明显不对。凡是人本身固有的东西,不仅不须教导,并且也不须解释。难道利己心、本能、欲望、情感、知性、理性这些人固有的东西,是经某人解释才开始起作用的吗?相反,在康德还没提出善良意志之前,有谁曾有过和用过康德解释的善良意志?这说明它根本不是人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的。
其四是用设定的东西建构理论。《原理》中有两大设定,一是“意志自由”,二是“有理性的东西”。这两个设定对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意志自由”属于设定,是康德自己告白的:“自由必须被设定为一切有理性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1]102 这个设定的目的在于,说明人人都有善良意志是可能的,道德的定言命令及其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也是可能的。“有理性的东西”属于设定,康德自己没说,是笔者推论的。因为根据康德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可知,“有理性的东西”包括人类又不止人类。可人类之外的有理性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在哪里?此书却从无交待,更没提供任何证据。康德做这个设定的目的在于用它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
康德的这两个设定其实都属于个人假设,而凭个人假设为前提弄出的理论观点,一点可靠性都没有。虽然康德在后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把“意志自由”连同又提出的“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说成“三个公设”[2]144,但根本就不是,因为公设是虽不能用逻辑证明,却可以得到普遍承认,或者在经验层面能得到普遍支持。例如,经济学的“自利人假设”倒可称公设,因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几何学的“两点间直线最短”的公设则在平面上屡试不爽。可康德的这两个设定,除了他自己,还有谁认同?又哪里有普遍经验的支持?并且,更可悲的是,即便康德用了意志自由的个人假设,可直到此书“结束语”时,他还是要无奈地承认:“我们确实并不明了道德命令的无条件的实践必然性。”[1]120 既然如此,还费那么大的劲儿做假设及其推论干啥?此外,康德用有理性的东西作为论证道德普遍性的手段也很荒诞,比如他说:“那些经验原则,不论在哪里,都不适于作道德规律的基础。因为,如果道德规律立足于人性的特殊结构,或者立足于人之所处的偶然环境,它们就不会有对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有效的普遍性。”[1]95-96此话意为道德规律不能以人性为基础,因为其他的有理性的东西没有人性,所以这种道德规律不具有普遍性。可是康德既然从没说过其他有理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又凭什么知道和人能同样拥有理性的其他东西,就一定没有与人一样的人性?难道它们只是一些无身体的纯粹理性?更可质疑的是,那种立足于人性的道德规律,即便是只对人类有效,岂不也是一种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普遍性”?
其五是对概念的表述和使用相当混乱,且经常自相矛盾。
证据之一是,在康德那里,“有理性的东西”不仅指人,还包括某些非人的其他东西。可他又在一处说:“有理性的东西,叫做人身。”[1]80
证据之二是,康德一边把用于谋求幸福的手段称为“机智命令”,一边又说还有“使自己有德性的机智”[1]96。可是他的有德和有福又是互不包含的东西。
证据之三是,康德在人的本性问题上,一方面宣称:“约束性的根据既不能在人类本性中寻找,也不能在他所处的世界环境中寻找,而是完全要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1]37另一方面,他又在后面几次把理性说成是人的“本性”,其中一句是:“人性,一般说来,作为每人行为最高界限的理性本性是自在目的这一原则,不是从经验取得的。”[1]83 既然理性也是人的本性,为何说“约束性的根据既不能在人类本性中寻找”?
证据之四是,康德在谈“普通的实践理性归根到底也不能称之为善良”时,十分确定地说:“需要和爱好的全部满足,则被总括地称之为幸福。”[1]55但后面他为了说明“机智命令”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实际上并不能使人得到幸福时,又以“幸福是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作为理据:“虽然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幸福,但他从来不能确定,并且前后一致地对自己说,他所想望的到底是什么。”[1]69可是,如果幸福就是“需要和爱好的全部满足”,那么,一个人每一次、每一种的需要和爱好的满足,就一定都是对幸福的某种程度的实现,这里又有什么不能确定的?
证据之五是,对于意志,康德有“善良意志”和“被欲望作用的意志”之分,可在具体论述时,却总是用“意志”概念直接等同或代替“善良意志”的概念。比如“意志被认为是一种按照对一定规律的表象自身规定行为的能力”[1]79 这句话中的“意志”,其实就仅指“善良意志”,而不包括“被欲望作用的意志”[1]109。
证据之六是,康德先是根据他的事物有表象与自身之分的观点,“提出了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区分”[1]106。又通过“理性甚至凌驾于知性之上”的观点,说理性的“主要职责是区分感性和知性世界”,因而“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理智”。既然如此,在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之外,就应该还有一个“理智世界”,而康德也的确提出了“理智世界”的概念,但它对应的却只有一个“感觉世界”,另一个也要被理性加以区分的“知性世界”则不见了。康德没解释“感觉世界”与“感性世界”是不是有所不同,但“感觉世界”包括不了“知性世界”则是肯定的,因康德自己说知性“不像感觉那样仅包含因事物作用而引起的,从而是被动的表象”[1]107。更为奇怪的是在稍后的地方,当“知性世界”的说法再度出现时,俨然已成为了“理智世界”的代名词,因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规律”,而这个“理性规律”,正是被“知性世界”的成员“认识了的自律性”[1]108。而且,“知性世界”现在所对应的也变成了“感觉世界”而不是“感性世界”。接着还有更离谱的,那就是康德在对知性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关系进行一番论述之后,又忽然冒出了一个“意会世界”的新概念:“定言命令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由的观念使我成为意会世界的一个成员。”[1]109 至于意会世界究竟是什么,则不给任何解释。不过,从康德又用它与“感觉世界”相对的做法看,它也是“理智世界”的别名。
证据之七是,康德一方面说“关切是他律的”,“是对情感的依赖”,而情感属于要被理性摆脱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肯定“道德感”和“对道德感到关切”。尽管康德为了自圆其说,说道德感或道德关切是“出于作为理智的我们的意志”,“只有理性才对它提供客观根据”[1]118-119,可它们不还是属于情感,属于关切吗?否则,何必仍用“道德感”和“关切”的说法?这种随心所欲的使用概念的行为,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学术霸道。
以上证据说明了一个问题,康德的著作之所以被认为晦涩难懂,其实并不是由于其理论高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表述含混,逻辑相悖,概念混杂,违背同一律。
二、观点性错误
与方法方面的错误相比,《原理》在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更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大者来说,它们分别出现在下述议题中。
1 规律议题 规律是《原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此书“前言”第一页就出现了,后面正文中也频繁出现。康德认为:“规律只有两种,或者是自然规律,或者是自由规律。”它们都是人的规定:“自然哲学给作为经验对象的自然界规定自己的规律,道德哲学则须给在自然影响下的人类意志规定自己的规律。”[1]35-36
把规律说成是人的规定,或可称前无古人的独创,但它明显不对。“物体受热膨胀”是一个具有因果必然性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在还没有人类之前,更没有物理学的时候就已存在了,怎么能说是人或人的学问的规定?只能说物理学作为人类学问之一,通过研究揭示出了物体本身具有这样一个规律,并用文字将它描述出来。在自由方面也是如此,如果确实存在一个有因果必然性的自由规律,那它也不会是人的规定,而只能是人的描述。
康德之所以认为自由规律是人的规定,在于他把自由规律等同于实践规律,又将实践规律等同于“实践规则”,而实践规则也就是道德原则,它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道德原则作为实践规律所具有的必然性,体现为它“是个命令式,也就是说,任何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都必然地受到它的约束”。问题是所有命令都是针对行为的,那么,所谓“必然受它约束”,是不是指行为必然按约束的去做,再无其他可能?如果是,那这个道德原则就确实是实践规律;如果不是,就肯定不是实践规律,而只是一个命令而已。实际情况显然是后者。因为有合法暴力维系的对所有人都有最强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也有被人违反的时候,何况没有合法暴力做后盾的道德原则?被康德“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是“自律原则”,其命令内容是:“在同一意愿中,除非所选择的准则同时也能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就不要做出选择。”[1]94 既然康德也认为这里是怎么做选择的问题,所谓“普遍规律”也是需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也承认这里存在其他可能,并没有必然性。再说,这个“自律原则”是被康德提出的,那么至少在他之前,人们的实践就都还没有受到它的约束,从而也就不可能是人们的实践规律。
2 必然性议题 康德之所以会把道德规律与道德原则等同,与他对必然性的错误看法有关。康德说:“一条规律被认为是道德的,也就是作为约束的根据,它自身一定具有绝对的必然性。”[1]37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康德是把普遍性当作了“绝对的必然性”。但这二者是一回事吗?必然性一定蕴含有因果关系,体现为有P则有Q,再无其他可能。可普遍性根本没有蕴含任何因果关系,它不过是呈现出了一个共同点,所以与必然性无关。
康德必然性观点的错误,根源于他把客观等同于必然,“先天地、必然地,不过是客观地”[1]72,又把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视为客观原则,把没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视为主观原则,所以,前者就有了必然性,后者则没有。然而这个逻辑能成立吗?说“必然地”都是“客观地”可以,因必然性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却不能反过来说,“客观地”都是“必然地”。例如,一个已出现的偷盗行为显然也是客观存在,但有必然性吗?所以,“客观地”并非都是“必然地”。并且,由于已出现的偷盗行为虽也是客观的,却没有普遍性,这就还说明,康德用客观原则和主观原则的概念来区分普遍性原则和非普遍性原则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总之,不是只有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才是客观的,也不是只要是客观的就是必然的,因而由人规定的普遍性道德原则就根本谈不上客观。而且,退一步讲,就算它具有客观性,也不意味着它就有必然性,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3 理性议题 理性可谓康德伦理学的前提性概念,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基本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的背影。康德把理性视为“实践能力”,但“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因为用于幸福所代表的其他意图的实现所需要的规则,“如果是由本能来规定的话,对它来说,要比由理性来规定更加适宜,更有把握来达到目的”。相反,若用理性筹划幸福,不仅“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还会产生“对理性的憎恨”,“因为经过了筹划不论他们得利多少,……事实上所得到的终是无法摆脱的烦恼,而不是幸福”[1]44-45。
然而,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只有本能的动物和理性还极不发达的原始人,就应有比现代人类更舒适的生活,可真相恰恰相反。人的获利行为或谋求幸福的方式,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只有必然的一种,并且不同谋求方式的效果也必然不同,而如何能从中选出可达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只能依赖理性的计算,而不是本能的反应。康德后来在谈到“假言命令”的两种形式之一的机智命令时,等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把选择有关自己最大幸福的工具的机巧,狭义地称之为机智”[1]67,而机智岂不就是理性的一种?甚至还是一种高级形态。另一种假言命令被康德命名为“技艺性命令”,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做出的指示”。它同样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康德明确说,做出这样的指示是“一切科学都有一个实践部分”的“任务”[1]66。对于科学,有谁能说它不属于理性?既然如此,理性的真正使命就不止是产生善良意志,而是也要产生假言式的技艺命令和机智命令。在康德还没说出理性的真正使命是产生善良意志时,谁都不知道理性有这个“真正使命”,理性也没产生出总是指向普遍性道德原则的善良意志。这一事实证明,产生善良意志反而肯定不是理性的真正使命。因为使命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任务,可理性在人类出现后的数万年间,却一直没做产生善良意志的事,又如何能说它是理性的使命?
4 道德价值议题 这个议题关乎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康德的回答是:“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出于责任”也就是出于道德:“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1]49这表明康德是根据行为动机判断行为的道德价值,只有动机为责任或道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其他任何动机的行为,都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哪怕它们是表象上合乎责任或道德的行为,也是如此。所以,不仅商人出于利己心的公平买卖行为没有道德价值,而且“全无虚荣和利己的动机”而“尽自己所能对别人作好事”,只图内心“欣慰”的行为,“不论多么值得称赞,但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1]47。康德如此判断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这些行为及其准则“不具有道德内容”[1]48。
但是,一个合乎责任或道德的行为,怎能说“不具有道德内容”?难道说,它符合的责任或道德不属于道德?又难道说,它在价值性质上,和无关乃至违反责任或道德的行为竟然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善的反面即恶?如是,它又怎么会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实际上,只有对无关或违反责任或道德的行为,才能说不具有道德内容。而对合乎责任或道德的行为,充其量只能说它们所具有的道德价值没有出于责任或道德的行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那么纯、那么大,而不是完全没有。如若不是这样,康德自己怎么会说“幸而是……合乎责任”的“对荣誉的爱好”“应当受到称赞、鼓励,却不值得高度推崇”[1]47-48?这里的称赞、鼓励,如果不是基于道德说的,又能是基于什么?这就说明,两种行为均有道德价值,差别仅在于:出于责任的行为值得高度推崇,合乎责任的行为值得推崇。何况,康德在论述意志原则时也是把“符合性”当作了决定因素:“只有行为对规律自身的普遍符合性,只有这种符合性才应该充当意志的原则。”[1]51这就出现自相矛盾:同样是符合道德,为何一种有道德价值,一种完全没有?
5 最高善议题 康德是把善良意志作为最高善,他说善良意志“虽然不是唯一的善、完全的善,但却定然是最高的善,它是一切其余东西的条件,甚至是对幸福要求的条件”[1]45。
这个观点很成问题,“最高的善”居然不是“完全的善”,并且也不是幸福。最高的善既为“最高”,自然就在其他所有善之上,而且还一定是能统摄其他所有善的,否则怎能保证,那些在它之外而未被它统摄的善,乃至幸福,都没有它高?这其中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如果在于善良意志“是一切其余东西的条件”,那这个判断的依据又何在?一个具体善之所以为善,只能以另一个能统摄它的更高的善为依据,由于善良意志有没被它统摄的善,所以即便它是这类善的条件,也肯定不是这类善之所以为善的条件。换言之,善良意志只能是那些被它统摄的善之所以为善的条件,这些善就是符合善良意志的准则和行为,而不可能是未被它统摄的善之所以为善的条件。这个事实表明,不属于完全善的善良意志根本不可能是最高善,康德的最高善的观点是错的。
6 责任议题 “责任”在《原理》正文中,是紧随着首要概念“善良意志”而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康德用它直接得出了关于行为道德价值的结论、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和意志原则。同时,它也与定言命令、自在目的、目的王国、自律原则、自由意志等概念密切相关,是它们的间接前提性概念,因而在全书频繁出现。
康德关于责任有许多似乎相同而又有所不同的说法,其中堪称定义的应是这句:“责任就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50 然而,这个命题是怎么得出的?是他通过概括几个责任实例的分析所得。这种推论方式,不仅完全属于康德自己所反对的经验性论证,而且就是放在经验性论证中也不成立,因为一个有效的普遍性命题,只能是来自于对所有与之相关的经验事实的完全归纳,而不可能仅来自于其中的几个经验事实。
除此之外,更为致命的弊端是,这几个关于责任的实例反倒能证明康德的责任定义是错的。在分析这几个责任实例时,康德明确指出,“保存生命是自己的责任”“尽自己所能对人作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保证个人自己的幸福是责任”。既然如此,责任应该就是按规则行事。事实上,这也正是责任的要义。至于那几个规则,即“保存生命”“对他人作好事”“保证自己幸福”之类,是否是具有普适性的符合实践规律的准则,则根本不在责任的范围之内,只是人们在订立规则和评价、选择既有规则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如果有人提出,被订立或选择的规则应该具有普遍性,能适用于所有人,也不是责任,而是在发表意见。当然,如果普遍性确实成为了一条订立或选择规则的规则,那按这个规则订立、选择规则才属于责任。但它仅仅是众多具体责任之一,而不是所有责任。同样,一个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而按规则行动,也无关责任的宏旨,它关乎的是人的境界,比如自觉服从规则的动机要比被动服从规则的动机高尚。既然“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根本就不是关于责任的本质性说明,那么由它而来的关于责任的其他种种说法,也就都难成为有价值的观点,而“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规律”[1]73,也自然不会是什么“责任的普遍命令”,最多只能算是选择准则时的普遍命令。
当我们发现康德关于责任的各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后,也可以知道,在责任后面出现且以责任为直接前提或间接前提的那些观点,即道德概念、定言命令、自在目的、自律原则、意志自由等观点,全都变得不可靠。
7 定言命令议题 把道德原则及与之符合的道德准则称为“定言命令”,也是康德的一个独创。定言命令是指“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1]68 的命令。反之,受某种条件限制的命令,就都是假言命令,它包括前面提到的“技艺命令”和“机智命令”。若用形式化的语言表述,定言命令是“你应该(不应该)做A”,假言命令是“如果X,你应该(不应该)做A”。不过这个独创的意义并不大,只不过是陈述了一个向来如此的事实而已。因为从古至今的各种道德规范,作为对人的命令,如勿说谎、勿偷盗、要爱人、要诚信,以及康德说到的“生活要严肃、节俭,待人要礼貌、谦虚等”[1]70,一直都是无条件的定言命令。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已有的道德规范,其语言表述形式竟不属于定言。至于这些既有道德规范在现实中没被人当定言命令理解和服从,也不妨碍它们仍是定言命令。所以假言命令从来就不是道德命令,也从来没有变成道德命令。然而,当康德根据自己给出的“责任的普遍命令”,来通过四个实例推论四种不同责任的具体行为准则时,不仅仍然用了被他鄙视的经验、情感、愿意,而且得出的也并不都是真正的定言命令。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康德在论及对他人的责任时,认为应该帮助有难者,理由是“一个人需要别人的爱和同情”。但如果帮助有难者不能成为普遍性准则,在他有难时,“他就完全无望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了”[1]75。这就表明,与对他人的责任相对的“应该帮助有难者”的道德命令,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定言命令,而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言命令:由于我也会有需要别人帮助的困难时刻,所以我应该帮助有难者。
在定言命令议题上,康德通过四个实例推论四种责任的定言命令还得出了“责任应该是一切行为的实践必然性”[1]77的结论。可其中的逻辑不能成立,因为从这四个实例均有定言命令来相应的事实,推论不出一切行为都得有实践必然性,也就是都得有具有普遍性的定言命令来相应。比如康德每天下午五点钟准时散步的准则,应属于对自己的责任,可这个准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定言命令吗?显然不是。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必要在这种事情上确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言命令,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之多的。
还有,康德所区分的四种责任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然后每种责任又有“完全的责任”与“不完全的责任”之分[1]73,后来他在论述“自在目的”时,又把完全责任称为“必然责任或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不完全责任称之为“偶然责任,或者说可嘉的责任”[1]81-82。既然有此区分,那么用于对应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的定言命令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还是都“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如果是一样的,对责任何必要有什么完全与不完全、必然与偶然、不可推卸与可嘉的区分?如果不一样,对应后一种性质的责任的定言命令,就一定不再具有“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的“实践必然性”。易言之,不完全的偶然的可嘉的责任,应属于可履行也可不履行的责任。如是,它就不需要具有普遍性的定言命令来对应,这就再次表明,并非一切行为都得有定言命令对应。同时也证明,责任并不一概是“对我们的行动实际上起着立法作用”[1]76。
以上这两个关于定言命令的错误极其严重,因为《原理》后面论述的主要内容就是“定言命令如何可能”,即是否人人都能在一切行为中按定言命令行事。可这两个错误的存在,已经意味着没有了这种可能,后面的相关论述都是无用和多余的。
8 目的议题 康德认为,只有在“具有绝对价值”的目的身上,“才能找到定言命令的根据,实践规律的根据”。而“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能使用的工具”[1]80。学界普遍认为,康德这一把人视为目的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洞见。不过这个评价要打折扣,因为在康德那里,人之所以是目的,不是在于人本身,而仅在于人的理性。所以不止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并且,他由此“推导出意志的全部规律”的“实践命令”也更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手段。”显然,如果人直接是目的,就不该说要把“人身中的人性”“看作是目的”。而这个“人性”就是指“理性”,因为康德在说人是实践规律的根据之后,又进一步认为:“普遍的实践规律……的根据就是:有理性的本性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着。”[1]81 后面更是有“人性,一般说来,作为每人行为最高界限的理性本性是自在目的这一原则”[1]83 之说法。这就表明,理性才是真正具有绝对价值的自在目的,而人只不过是理性的载体,这才有幸也跟着理性成为目的。至于理性为什么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在目的,是因为“理性自然和其余自然的区别,就在于它为自己设定一个目的。这一目的,就是任何善良意志的质料”[1]90。正因为康德是把理性视为真正的目的,而人作为目的只是沾理性的光,所以当理性和人在特殊情境中发生冲突而不能得兼之时,被舍弃的将是人身。康德在后面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有个著名的例说:如果你已知来者要杀自己朋友,面对其朋友在哪儿的询问,也要按照理性关于普遍性准则必须无条件服从的要求如实回答。这就是说,人即便是理性的主体并因此也被说成自在目的,但相对理性或道德而言,仍然不过是手段。
9 自由议题 为了说明在实践层面,“一个彻底善良的意志”也是必然的,即“每个有理性的东西加于自身的,唯一的规律,不以如何动机和关切为基础”,必然按善良意志的原则或自律性行事,康德“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开始了对自由的分析。
自由,在康德眼里,就是意志自由:“意志是有生命东西的一种因果性,如若这些东西是有理性的,那么,自由就是这种因果性所固有的性质,它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地起作用。”这段话表明,自由就是有理性的生物的意志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独立地起作用。不过,康德又说这只是“对自由的消极阐明,因此不会很有成效地去深入到自由的本质。不过,从这里却引申出了自由的积极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另一东西,也就是结果,通过某个称为原因的东西而被设定”。这就是说,积极自由才具有“自由的本质”,它是意志以原因设定结果。但这种设定“并不是无规律的,而是一种具有不变规律的因果性”[1]100。而这个规律就是意志自律性引申出的道德规律,也就是道德原则,即“定言命令的公式”,所以,“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1]100-101;“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然而,是否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会按这种“自由观念”行动?康德说:“我主张,我们必须承认每个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东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从自由观念而行动。”[1]102 这个主张的根据在于,理性中的纯粹实践理性使人认识到在行动方面,“第一,他是感觉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规律,是他律的;第二,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规律,而不受自然和经验的影响”[1]107。由于“知性世界是感觉世界的依据,从而也是它的规律的依据”,“所以,我必须把知性世界的规律看作是对我的命令,把按照这种原则而行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1]109。也就是说,在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即道德规律同时对我起作用时,我只按道德规律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1]107。
康德自由议题的错误首先在于,如果自由确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那么在逻辑上就必然会有一个既涵括消极自由也涵括积极自由的全称自由概念。于是,就不能认定只有积极自由才是自由的本质所在,就不能说“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也不能说“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充其量这两个说法只是自由或意志自由的一种体现。第二个错误在于,由于康德对意志有“善良意志”和“被欲望作用的意志”之分,这就说明这两类意志都会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因而那个与“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的“意志自由”,也不能全等于积极自由,而只是积极自由的一种表现,即善良意志自由。第三个错误是人作为两个世界的存在者,只能按理性规律或道德规律行动的论证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结论的唯一理据,即“知性世界是感觉世界的依据,从而也是它的规律的依据”是不成立的。康德所以这么说,是他认为感觉世界对应的是事物的“千差万别”的现象,知性世界对应的是“始终如一”的事物自身,所以知性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基础[1]106。但是,如果感觉世界只有现象,怎么又会有自己的“自然规律”?规律作为不变的东西,按康德观点,理应属于现象背后的东西。再者,人在婴幼儿时,是有感觉、有欲望、有情感却还没有知性的状况,这说明知性世界既不是感觉世界的发源地,也不是感觉世界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此,后者怎能是前者的基础?要说后者对前者有什么作用,也就只是知性能意识到感觉世界的实存及其规律而已。可是,仅凭这个事实,就能推出人不需要按感觉世界的规律行事,而只能按理性规律行事的结论吗?
10 行为动机议题 康德设定意志自由,最终是为了让人们都有善良意志,把自己视为目的王国的成员,“在行动的时候排除一切欲望和感性的诱惑”[1]113,“不为感觉所决定”[1]112,“目的是限制感性动机”“消除来自感性领域作为动机的原则”[1]118,以实现在《原理》开始部分就提到的“更高理想”,这就是使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道德而做出”[1]38,只以“对道德规律的衷心关切”为动因和动力,“小心谨慎地按照自由准则行事”[1]119。而这里的所谓“自由准则”,也就是意志自由的准则,即从属于道德规律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康德希望每个人都有目的王国成员的想法值得肯定,只是让人仅以道德为行为动机的这个愿景太过乌托邦,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这一点前面已有多次证明,这里再从另一个逻辑证明一下。康德在谈到人对自己的责任时,通过举例说明人有不自杀的责任和发展自己才能的责任。但是,要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不死,就要满足自己的各种基本需要,也就是先天欲望;要发展自己的才能,就得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即后天欲望。既然如此,人能不为这些事而行动吗?这时人又怎么“限制感性动机”?因此,康德限制感性动机的观点与自己的责任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人之所以要行动,从根本处讲,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即先天需要和后天想要,诚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都不能做。”[3]342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仅以道德准则为动机而发起的行为甚少,一般只是发生在他人需要关照或帮助的特殊情境中,如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让座和扶贫济困等。而道德之所以要求人们进行这样的相互帮助,同样也是为了需求,即满足人们和谐相处的需求。何况,符合道德原则的具体道德准则非常之多,乃至不计其数,若只以道德为行为的唯一动因,请问康德,一个人每天该以其中的哪一个道德准则作为自己开始行动的动因?这里又是否有什么标准或理由来加以确定?显然,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好的回答。
三、总体评析
一套理论,如果它的基本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就已经是一个有大缺陷的理论;如果它的系列观点包括基本观点也几乎都是错误的,并且这些错误的观点还存在相互不自洽的情况,那我们就只能说它是一套很烂的理论了。而康德的伦理学,经过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可知,就是一个这样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和各个主要观点,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得到肯定,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在开始部分仅从几个有关责任的实例推出具有普遍性的“意志的原则”,不仅在方法上不合逻辑,而且在观点上也是错的。这个初始性错误导致后面以它为前提的所有论述及观点也不可能正确,包括与它意思一致的道德概念、善良意志公式、定言命令公式和自律原则。因而《原理》的价值最多只是给人以某些启发,并可经启发使其中有的观点通过改造或重释能得到拯救。这就是,善良意志的概念应简单理解为向善的意志,而不是什么要把准则变为普遍规律;自在目的的观点应改为人直接就是目的,而不是跟着理性才成为目的;自律原则即“在同一意愿中,除非所选择的准则同时也能被理解为普遍规律,就不要做出选择”[1]94,其实也是“定言命令公式”和“善良意志公式”,应重新解释为它是人在制定规则、选择规则和评价规则时才需要用到的方法之一,而不是人所有行动的原则,因前已证明并非人的任何行为都要对应具有普遍性的准则。自律原则被康德称为“道德最高原则”,自然也是道德“正确评价的最高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人的一切行为,这就意味着,康德在《原理》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道德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整个写作目的最终是失败的。
康德的伦理学之所以满是弊病,乏善可陈,主要原因是认知上存在四个根源性迷误:一是他独断事物现象背后的事物自身不可认知,从而凡遇说不清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归于此,使理论丧失彻底性;二是他在否认道德的约束性不可能来自人的本性的同时,还彻底割裂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联系;三是他没意识到理解既有道德的必要,并完全没有对它的思考;四是他错误地坚信人服从道德,只为道德而做就是最有价值、最有尊严的最高理想。
就第一点而言,正是这种不可知论,导致了康德把本属一体的东西硬分成两个互相对斥的部分,如理性与感性的对斥,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对斥。但倘若事物自身真的不可认知,康德就不知道它存在,也不能由于不同人对事物现象有不同的感觉而推论出事物自身不可知,因为事物自身为什么就不能是和它的现象是一致的?即如果现象是“千差万别”的,所谓“诸般现象的背后”的事物自身又为何不能是千差万别的[1]105-106?应该说事物现象背后的就是事物的本质,而本质也不是神秘的东西,就是此物具有的可区别于其他一切东西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了某物的独特性,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了它,再不会将它与其他任何事物相混淆,事物也再不会还有什么不能认知的秘密。而这个能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事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岂不就是所谓的“事物自身”?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认知的事物自身,所有以此为由形成的论述都是无效的。
就第二点而言,道德的约束性确实不能仅凭人的感性本性得到,但也不是与之无关,因为如前所说,人若无欲望或需求,就不需要做任何事,从而也就不需要有约束人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因此,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人都是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行动,只是满足需求的行为方式从来不止一种,且每种方式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于是从中选择哪一种行为方式来满足需求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而道德作为人的理性智慧结晶,就是用来指导人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人的需求作为人的本性乃是道德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生道德规范的理性乃是为人的需求服务的,因而道德的作用不是形成人行动的动因,只是为人选择满足需求的行为方式提供理由。康德蔑视和排斥人的本性,深层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本性是自利的,而自利就是恶,所以全书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提到“利己之心”“利己原则”。正因康德如此看待自利,他才会把与自利这种个体性的东西完全相反的普遍性视之为善。但是,人性自利根本就不是恶,当然也不是善,而只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客观事实,无所谓善恶。只有当人选择以什么方式自利的时候,才有善恶出现。按既有道德的观点来看就是:损人的自利方式为恶,利人的自利方式为善,既没损人也没利人的方式为非善非恶即正当。因为被各民族的道德所禁止的行为,如说谎、偷盗等,全都有损人的性质;被各民族的道德所倡导的行为,如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等,全都有利人的性质;而“各人自扫门前雪”类的行为,则既不被道德规范禁止,也不被道德规范提倡。所以道德对人的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的实际指导就是:禁止损人行为,提倡利人行为,允许正当行为。因而一个人的自利行为只要是不损人就行,就是对道德的服从,至于这种行为方式是否能变成具有普遍性的准则,则根本无须理会。这就再一次证明,对一切行为的普遍性要求是荒谬的;理性、道德确实是为人的本性服务的,属于人的工具。实际上人作为一个整体,他的感性和理性也不仅不可能互不相干,还相互排斥。虽然康德否认他是这种观点,但他认为在行动中要用理性排除掉一切感性动机就是铁证。
就第三点而言,康德没有关于在他之前已然存在数千年的道德的研究,根本不知道实际道德的起源与本质。不过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从古至今的西方伦理学家的通病。根据笔者的《人本伦理学》的研究,道德源自人的需求,形成于人的生活生产的活动之中,“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直接维系和推动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的总和,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4]45。既然道德源自人的需求并形成于人的活动中,那么,在论述道德时,就既不能排斥人的欲望和本性,也不能排斥一切来自实践的经验。既然道德是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那么,每个道德规范自然就有了康德极为看重的普遍性,并且这种普遍性还都是实质性的普遍性,而不是形式上的普遍性。道德规范本来就有普遍性的事实表明,康德根本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推论道德准则应该具有普遍性,也不需要去推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准则,而只需指出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即可。既然道德是善的为人处事方式,因为行为规范指导人做事,品质规范指导人做人,那么,只讲人的行为及其行为道德准则的康德伦理学,就注定是一个片面的伦理学,即德行伦理学。当然,德性伦理学也是片面的。从这点看,康德给出的道德最高原则,也不可能是道德最高原则,顶多是行为的最高原则,但不幸它还是错的。
就第四点而言,既然人们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那么,设想让人们都只为道德而做就是一个不可能的空想,从而只为道德而做也不值得赞扬。事实上,只有在任何时候都守住道德的底线即不损人,哪怕这样的坚守对自己不利,比如坚持不说谎而导致借不到自己急需的钱,并且在需要响应利人的倡导性道德规范的情境中做出了自己的响应,如雪中送炭、见义勇为之类,这才是值得称赞和有尊严的。即便如此,这种意义的服从道德也不是唯一值得称赞和有尊严的事情。人根本不是为了服从道德命令或履行道德责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为了求得不断地发展,以使自己活得更好。这不仅在于没有道德的时候就早已有人,也在于人类历史确实就是一个让人类活得越来越好的过程。因此,凡是能使人类活得更好的作为,就都是值得称赞和有尊严的,而履行道德责任则只是其中的一种。由于服从道德只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只是人们活得更好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直接让人们活得更好,所以履行道德义务就还不是最值得称赞和最有尊严的事情,从而也就算不上是比其他追求都“更高的理想”。
正因为康德在事物自身问题、人性问题、道德问题和至善问题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都存在认知性偏差或缺陷,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建构起来的伦理学也就不可能不是错误不断。有鉴于此,凡是运用康德伦理学去解释具体伦理问题和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而对康德伦理学文本进行不加批判或改造的详细诠释,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研究。
如果康德的最高理想是不成立的,那么,我们又该把什么作为最高理想?又是否能提出令人信服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最高理想?还有,如果康德的道德最高原则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是道德最高原则?又是否可能有向人们同时提供善的做人与做事的指令的道德原则?
必须承认,在以往的伦理思想史上,对这两个问题的确都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不过笔者的“人本伦理学”很可能不一样。它对最高理想即至善的回答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于这个至善,是唯一合乎至善必须同时具备的四个特征即普适性、综合性、现实性和永恒性的至善,所以它就是真正的至善。并且,由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能够涵括所有价值对象,意味着人的需求的全面性满足和提高,所以这个至善,也就是个人幸福所在[4]122-125。
对道德最高原则的回答与至善密切相关,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至善,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个道德最高原则是唯一可以同时满足堪称合理性道德原则的六个必备条件,即“是唯一的一级原则、是以人为本、是与至善一致、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能够同时提供为人处事的品质规范与行为规范、也能够为社会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所以它就是真正的道德最高原则,也确实能够同时为人提供根本性的善的为人处事方式。这就是:做一个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并使自己所有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活动,在客观效果上具有有利于其他一切人也如此发展的功效[4]120-121。又由于这个道德最高原则规定了至善即幸福,这就使道德跟幸福实现了统一,其基本关系是:道德是人追求幸福或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工具。
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复述关于这两个回答的全部论证,如果列位仍有怀疑,请读了笔者的《人本伦理学》后再看是否还能提出质疑。
不过退一步讲,纵然笔者的这两个回答都不能成立,也丝毫不影响已对康德伦理学作出的“很烂”的总评,它仅意味着我们还得继续寻找至善和道德最高原则。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韩东屏.人本伦理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韩东屏
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汇海洋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By8PjeoUCuc5ZE-GG0JxA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9-28 18:37
【案例】
福柯:边沁的“全景监狱”
边沁(Bentham)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一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因楚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从一开始,作为一种消极结果,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那些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禁闭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现在画面上,也曾被霍华德( Howard)描述过。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
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会有阴谋串通的危险,集体逃跑的举动、新的犯罪计划、相互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疯人,就不会有彼此施暴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Benthan,60~64)。
一座废弃的全景敞视监狱
由此就产生了金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 situation)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对于实现这一点来说,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太多了,是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瞭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力自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tham,45)。
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凡尔赛动物园设计图纸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二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house of 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 of certaity)所取代。权力的效能,它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应用外表上。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因此,外在权力可以抛弃其物理重力,而趋向于非肉体性。而且,它越接近这一界限,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这是一个避免任何物理冲撞的永久性胜利,而且胜利的结局总是预先已决定了的。
边沁没有说明他的设计方案是否受到勒沃(Le Vaux)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这最早的动物园与一般的动物园不同。它的各个展览点不是散布在一个公园里(Loisel,104~107)。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它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各种动物的铁笼。到边沁的时代,这种动物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在全景敞视建筑方案中看到了类似的兴趣,即对个别观察、分门别类,以及空间分解组合的兴趣。
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特定的分组取代了逐一分配,诡秘的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除了这点区别之外,全景敞视建筑也完成着一个博物学家的工作。它使人们有可能确定各种差异:对于病人,可以观察每个人的病症,又不使病床挤在一起,不会让污浊空气散播,不会有检查台上的传染后果;对于学生,可以观察其表现(不会有任何做假和抄袭),评定其能力和特点,进行严格的分类,而且可以根据正常发展情况,将“懒惰和固执者”与“低能弱智者”区分开;对于工人,可以记录每个人的能力,比较完成每项任务所用的时间,以及计算日工的工资( Benthan,60~64)。
勒沃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
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罪行和特点,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儿重新采用有重大争议的隔绝教育。
人们将能看到,当他们长到16至18岁,被放到其他少男少女中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人们将能验证,是否像爱尔维修(Helvetus)所想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学习能力。人们将能跟踪“任何可被观察的观念的系谱”。人们将能用不同的思想体系来教育儿童,使某些儿童相信,二加二不等于四或月亮是一块奶酪,当他们长到20岁至25岁时,再把这些青年放到一起。那时,人们将会进行比花费昂贵的布道或讲课有更大价值的讨论。人们将至少有一次机会在形而上学领域里有所发现。
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对人进行实验并十分确定地分析对人可能进行的改造的优越场所。全景敞视建筑甚至是个能够监督自身机制的结构。在中心瞭望塔,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护士、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甚至,总管本人也能被观察。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而且,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不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一起了吗?一个使传染病得以散播的无能医生将是传染病的第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能的监狱长或工厂经理也将是暴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Bentham,177)。全景敞视建筑像某种权力实验室一样运作。由于它的观察机制,它获得了深入人们行为的效能。随着权力取得的进展,知识也取得进展。在权力得以施展的事物表面,知识发现了新的认识对象。
瘟疫袭扰的城市与全景敞视机构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它们相隔一个半世纪之遥,标志着规训方案的变化。前者有一个特殊的形势: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它使自己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它创造各种新机制。它进行区分、冻结和分割。它在一段时间里构建出一种既是反城市(counter-city)又是理想社上会(perfect society)的东西。它进行一种理想的功能运作,但这种功能运作归根结底与它所反对的灾难一样陷于一种简单的非生即死的二元关系:运动者带来死亡,因此,人们要杀死运动者。反之,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毫无疑问,边沁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封闭的特殊制度提出来的。
但是,完全自我封闭的乌托邦已经够多了。与在皮拉内西(Piranesi)的版画上可以看到的刑具狼藉的监狱废墟相反,全景敞视建筑展示了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事实上,甚至到了我们现代,它还会产生许许多多设计中的或已实现的变种。这就表明了它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起人们的想像力。但是,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
勒沃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它是一种在空中安置囱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Bentham,40;边沁是把罪犯教养所当作首要的例证,这是因为它需要实现许多不同的功能—安全监护、禁闭、隔离、强制劳动和教育)。
在任何一种应用中,它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它是通过几种途径做到这一点的。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在上述条件下,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因此,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在物质、人员和时间上)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这是一种从权力中“史无前例地大量”获得“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的方法,“其优越性在于它能给予被认为适合应用它的任何机构以极大的力量”(Benthan,66)
这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中“一通百通”的例子。它实际上能被纳入于任何职能(教育、医疗、生产、惩罚)。当它与这种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能增加后者的效果。它能形成一种混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它能在“过剩的权力”与“过剩的生产”之间建立一种正比关系。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边沁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前言中一开始就列举了这种“监视所”可能产生的益处:“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护,工业有了活力,教育得到传播,公共负担减轻,经济有了坚实基础,济贫法的死结不是被剪断而是被解开,所有这一切都是靠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实现的!”( Bentham,39)
全景敞视的监狱剖面图,囚犯既被空间所困,
又因空间暴露了全部的隐私
此外,按照这种机构的设计,其封闭性并不排除有一种外来的持久存在。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中心瞭望塔,行使监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清楚地了解监视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任何全景敞视机构,即便是像罪犯教养所那样严格地封闭,都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这种无规律的、经常性的巡视—不仅是正式的巡视员的而且是公众的巡视。任何社会成员都有权来亲眼看看学校、医院、工厂、监狱的运作情况。
因此,全景敞视机构所造成的权力强化不会有蜕化为暴政的危险。规训机制将受到民主的控制,因为它要经常地接待“世界上最大的审判委员会”。这种全景敞视建筑是精心设计的,使观察者可以一眼观看到许多不同的个人,它也使任何人都能到这里观察任何一个观察者。这种观看机制曾经是一种暗室,人们进入里面偷偷地观察。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
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持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种普遍功能。瘟疫侵袭的城镇提供了一种例外的规训模式:既无懈可击但又极其粗暴。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权力用不断的死亡威胁来对付。生命在这里只剩下最简单的表现。这里是细致地运用刀剑的权力来对付死亡的力量。反之,全景敞视建筑有一种增益作用。虽然它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虽然这样做是为了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
权力如何能够在不仅不阻碍进步,不用自己的种种规章制度来压迫进步,反而在实际上促进进步的情况下得到加强呢?什么样的权力增强器也能同时是生产增益器?权力如何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增加社会力量,而不是剥夺或阻碍社会力量?
全景敞视建筑方案对这一问题做出的解答是,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保证权力的产性扩充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国王的肉体,它的奇特的物质表现,国王本人所动用的或传递给少数人的力量,是与全景敞视主义所代表的新的权力物理学截然对立的。
全景敞视主义的领域是全部较低的领域。这是各种参差不齐的肉体的领域,包括它们的各种细节,它们的多样化运动,它们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它们的空间关系。这里需要的是能够解析空间分配、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这些机制使用的是能够揭示、记录、区分和比较的手段。这是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的物理学。这种权力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能够用这些关系加以区分的肉体中达到最大的强度。在理论上,边沁确定了另一种分析社会机体及遍布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方法。从实践角度,他规定了征服各种肉体和力量的做法,这种做法应该在实践君主统治术的同时增加权力的效用。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纪律)的各种关系。
对于边沁来说,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但是,他也开始论述,人们如何能够实行纪律,使之以一种多样化的扩散方式在整个社会机体中运作。这些纪律是古典时代在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地方—一兵营、学校和工厂中制定的。人们只能想像在瘟疫流行的城镇—一这种有限而暂时的范围内,全面彻底地贯彻它们。而边沁则梦想把它们变成一种机制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全景敞视结构提供了这种普遍化的模式。它编制了一个被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的社会在一种易于转换的基础机制层次上的基本运作程序。
摘自/(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235页。
作者:福柯
来源:微信工作号——历史与秩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aW72osIAaKizHS2624aaA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9-28 19:03
【案例】
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
作者简介:李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中国伦理学70年的发展记录了新中国走过的极不平凡而又充满魅力的历程,深刻地昭示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如果说伦理道德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发展史,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就意味着伦理学发展的挑战与希望。
“学科危机感”隐藏的危机
伦理道德是文明社会人类生活的理性约定,是人类获得自由生活的内在精神,它与人类文明相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越充分、越高级,伦理道德的发展则越繁荣,按其历史逻辑,承载伦理道德研究及人才培养的伦理学学科,自然不会凋零。但是最近在多个相关学术研讨会或论坛上,不少伦理学界的同道都不约而同地在关注伦理学学科边界的问题,甚至担心多学科的侵染,使伦理学学科的论域似乎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小,对学科发展有某种或不同程度的忧患意识,我称之为“学科危机感”。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与伦理道德发展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因为这里至少包含两个前提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如何理解伦理学。大家知道,“伦理学”是一个外来词,在早期古希腊哲学家中,这个词表示某种现象的实质或是稳定的场所,后来专指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风俗,相当于汉语中的品格、德性,是指一个群的个性。在中华文明中,《说文》曰“伦,辈也”,进而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治玉也”,其解为治理或物的纹理,进而引申为规律、规则、道理等。相比较而言,西方文明中的“伦理”与“道德”在词源含义上基本是相通的,但他们更常用“伦理”,更关注、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特性、品格。即如黑格尔所指证的,“伦理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而在中华文明中,“伦理”与“道德”在词源含义上并不完全相通,我们更常用“道德”。《说文》曰“道,所行道也”,引申为规律;《管子·心术上》曰:“德者,得也。”道和德连用,在《四书集注·论语注》中解为“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得也”。如果“道”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的话,“德”就是指人们对这种普遍性存在的认知,进而表现为德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更关注、强调价值意义上的“道”之教育,强调个体如何通过“得道”而“合群”,这是中华伦理道德发展的重要特点、关切主线和传统。从新世纪(2001)发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到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都传承了中华文化的这个传统,都把道德教育作为重要的内容。毫无疑问,这个传统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宝贵资源,对于群体性生活的人类而言,个体对伦理的认知及其内在力的向善调控,始终是人类获得道德生活或美好生活的原点。
但是“伦理实体”是一个变化的历史实体,回望近百年的民族精神发展史,20世纪的中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人生观论战”,两次论战都历史地成为中国社会重大变革转型的前奏。反思两次论战的实质,与其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之争、文化选择之争,不如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意义上,对我们应如何生存、如何生活发出的先声,是文化自觉的深刻启蒙。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曾经维系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伦理之道必然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反映到学科上就是所谓的伦理学危机。正如樊浩教授所揭示的,中国伦理学出现了“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同行异情”,提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建设,必须强调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原则。显然,“伦理道德”的叠加,不是简单重复,而有其共在的深意。中国伦理学如何走出伦理与道德的“同行异情”之危机,正是伦理学发展的当代生机。
其二是涉及知识分类及学科划分的标准。所谓知识分类,就是按照不同标准和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及认识程度对人类知识体系进行不同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曾从知识内容的角度,把知识分为三类: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罗素从知识来源的角度,把知识分为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和内省经验;陶尔士等人则将人类知识分为四大领域:描述性知识、规范性知识、实践性知识与形式性知识等等。无论哪种分类,我以为都是从知识的某种特性,形式的、来源的、认知的或实践的等角度为依据划分的。在这个基础上,学科的划分更是一个从总体性到不断分支分化的过程,而其根源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有关。丁立群教授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前提:理论、制作和实践的三分对峙所做的批判与重构,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制作和实践的分离虽然打破了“德性即知识”体现的“伦理—认识平行论”,使实践哲学从理论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哲学形态,但也产生了诸多理论矛盾和内在张力,甚至导致唯科学主义的泛滥。换言之,理论、制作与实践的对立,为近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这使得实践哲学无法构成统一的世界观,从而亦不能成为一种一般的哲学形态,进而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以理论、制作和实践的统一性为内涵的新的实践哲学前提,克服三分对峙前提下的种种理论和现实矛盾,并由此引申出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范式。这个新的实践哲学范式的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所揭示的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人们的社会意识无外乎正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哲学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改造世界。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理解各类知识、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侵染,其所导致的“学科边界问题”就有了解题的答案:无论是知识还是学科都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不断变化着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的认识结果,随着客体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改造世界的不断深化,知识间的壁垒、学科间的联系必然在不断打破和超越中前行。伦理学作为研究以天人物我之间关系为指向的、追求善的学科,可以说最具有相互联系的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伦理问题,不仅不是侵染,而恰是知识、学科发展的突破和方向。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把人伦关系主要归结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个人与陌生社会大众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把此伦归结为“第六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虚拟人”已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虚拟人”是否可以逻辑地成为“第七伦”呢?而“真人”与“虚拟人”的伦理关系,和“熟人”与“陌生人”的伦理关系能否在同一框架下解释呢?这些都有待跨学科的努力才能突破,而这正需要冲破越来越自我封闭的学科,甚至行政壁垒。伦理道德的发展研究必须坚持开放的伦理精神,才能在历史与社会滚滚向前的潮流中,发挥伦理学在社会与人类生命安顿中的基石作用,若伦理学脱离人的生命与生活,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还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伦理道德都和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都和某种文化紧密相关。根据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收集的资料显示:文化的定义多达160种以上。但无论对文化定义如何诠释,它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系都是极为紧密的。梁漱溟把文化直接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的样法”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说文化传统对人类生活的“样法”有着无形的、潜在的和极大的影响。因此,即使在生产力水平、经济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类生活样法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种路径样法: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面要求;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条路向——变换、调和、持中;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向——反身向后要求。所以,“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和态度,就是他所走的并非第一条向前要求的路向态度。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我以为梁漱溟先生在此强调的是在一个没有文化交流的前提下,每个民族、族群怎样生活的方式就构成了该民族、族群的文化及其传统。当然“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与现代文明相对应的,特指建立在以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族群性的文化特征,它具有相对应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后者是指以该民族、族群为基础的,包含时代发展特质在内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族群性文化特征,它通过人类特有的自省、批判力,不断在传承传统文化中超越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因此可以说建立在那个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世代更迭中具有相当稳定与牢固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两词同源同意之意。
在中华民族进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代,如何深刻认识传统道德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中的意义及其现代价值是伦理道德发展的首要议题。当代著名哲学家杜维明先生和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艾恺先生的研究极有启示意义。
杜维明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始决心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浸润,又长期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华裔学者,他一直在努力开掘儒学传统及其内在精神的现代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更关注的问题是: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等领域,实际上杜先生所做的是如孟子和马塞尔所说的“掘井及泉”的工作。近年来杜先生提出“精神人文主义”问题,强调扎根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建构,指出这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的问题,而这一思想关联着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化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在杜先生看来,重建“精神人文主义”恰是对启蒙问题反思的结果。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在历史上发挥极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财富和权利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使得世俗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
与杜维明先生不同,艾恺先生是纯粹的美国人,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方面堪称第一人。对于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在他的学术人生。艾恺认为,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三种文化“理想典型”,表现出人的“意欲”面对环境障碍的三种不同方向,并把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的这一阐析看作是对历史的“后设推测”。他以历史演进的事实分析了东西文化精神带来不同的文明形态,指出,在现代,西方以“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启蒙人类的意志,将西方文化自私自利与理性计算两大基本倾向结合在一起,征服自然环境,因此发展出现代化的工业。但这种态度本身就蕴含了“毁灭的种子”,使人类“面临存在的痛苦与精神的污染”。而“儒家的生活方式并非基于智谋计算,而是基于情感直觉,因此更接近于宇宙永恒直流的真理”。在艾恺看来,中国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刺激欲望,征服自然,也不像印度人那样压抑欲望,中国人采取的态度是和谐与妥协,孔子通过礼乐将人的生活直觉主义化,“儒家礼乐之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创造了以重感情和精神上的安定”,“通过审美达到宗教所追求的目的”。因此,当人的本性处在人类演化的第一阶段时,西方文化会变成世界文化,而当人类演化进入第二阶段(即经过科技、经济的发展后),中国文化将会变成世界文化。换言之,他认为儒家文化解决现代生活隐含的问题比西方文化更有洞见。但由于中国文化有早熟的性质,“早在第一阶段的演化真正完成前,就已经预见到隐含其中的第二、第三阶段的问题了。而由于中国过去未曾完成第一阶段的演化,所以也未能真正实现中国赖以为基础的儒家理想”。
可见,如何理解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意义,杜维明先生的批判及开掘与艾恺先生的见解有着某种不约而同的洞见,他们对中华文明、文化的洞见有个交集点,即中华文化是一种与人的类生活、生命紧密联系、交融的文化,是一种关注、关怀人的生命、生活的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伦理学更具有发展的潜在力以及在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使命中特有的文化价值。现代中国人,正生活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交错汇合中,生活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维文化向度共存的空间里,他们是现代的,亦是传统的;他们是传统的,同时又是后现代的。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文化乡愁”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命中最为复杂,也最为生动。余光中先生给她的定义是:空间乘上时间、乘上文化记忆,再乘上沧桑感。中国文化的这种特质,对于治愈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应有某种不可取代的积极价值。
新文明建构与文化自觉
当今世界多元文明激荡,不同的文明观不仅会引导和改变世界秩序,也会改变人类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在书中他提出两个主要的观点:第一是冷战之后,文明将成为理解和把握世界关系的新范式,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将是人类最主要的危险;第二是西方文明是契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是世界秩序重建的文明范式和标准。此说一出,触动了各个文明敏感的神经。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不同文明必然走向冲突吗?世界秩序的重组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范式或者怎样的范式才是更合乎人类道德的?即我们需要审慎回答新文明建构的伦理精神是什么。
首先,多元文明的存在是个历史的事实。世界文明形态的演进和发展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就是不同路径的。恩格斯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向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时指出,东西方是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侯外庐先生认为,西方是从家族制、私产再到国家的;中国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在家族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家国同构”的概念。历史学家的考察和研究也表明,在人类轴心文明时期,世界上有几种文明形态,比如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文明等,几乎是同时相继独立形成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本源性的,并不存在哪一种文明去影响另一种文明,因为那个时代,世界是个“独白”的时代,还没有文明传播的条件和可能。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理据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文明这个活的有机体不断演进和变化,特别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后,各种本源性文明已毫无例外地被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他们不断相遇,不断被激活,相互产生越来越频繁的广泛的影响。而当“地球村“”的预言在今天已经变成人类日常生活的时候,不同文明间的影响当然变得更加明显和直接。
进而,怎样的文明观才是合乎人类之大道的?当代世界应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伦理精神?放眼世界,的确不同文明的冲突是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种可能性,但“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必然的,或是唯一的可能。我以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从轴心文明的历史视角出发思考,把握多元文明在日趋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为此必须提倡、弘扬“尊重、包容、互鉴、共生”的伦理精神。不同文明之间只有通过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和学习,才能寻求文明的和谐发展,共创、共建新的文明,也只有这种“可能”才是合乎人类文明之大道的。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源头活水,应该以同情理解的思维方式,通过文明间的沟通对话,才能培育创造并共享世界的和平文化。他提出的植根于儒家传统中的“精神人文主义”的主要价值内核是:要富强和自由,也需要正义;要发展理性,也要同情与慈悲;要发展法律,也要注重礼乐;要个人尊严,也要注重社会和谐;要讲人权,也要讲人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基础;社会和谐比个体发展更优先。显然,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外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对于世界秩序的重建毫无疑问有其特别的意义。任何试图以某一种文明作为典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去驾驭其他文明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如果按照亨廷顿所说的那样用西方文明作为新文明建构的标准重建世界秩序,那么势必使世界不同文明陷入更大的冲突和更大的危险。
最后,文明的对话、文化的交流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没有文化的自觉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交流。费孝通先生曾深刻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为什么“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呢?我以为至少有两点“固有的障碍”需要排除:一是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是,任何传统,无论其类型如何,都“可能成为人们热烈依恋过去的对象”,文化传统关联着人们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具有极强的“预制性”功能。二是文化传统的“预制性”表现为对现实的特定社群生存和社会发展显现出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影响特性,这种特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对异己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使得文化的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所以,文化的交流应该是认识自我和认识他者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鉴赏的过程,更应该是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对话、交流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潜在力,它们可以在世界新文明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汤一介先生指出,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文化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二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前者确实存在某种专政和暴力的性质,即使是这样,它也并非有着强烈的扩张性。而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主张“和为贵”,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儒家文化中“和”的对立面是“同”,“和”的先行条件是“异”,也就是说“和”是包含差异的。所以,儒家思想中普遍和谐的观念无疑将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中国“和而不同”的原则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对新文明的建构无疑具有正面的价值。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哲学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ux21tZvzwjhPQM3fZGk5Q
编辑:宋婷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0-28 19:30
【案例】
甘绍平 |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作者简介:
甘绍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出版《伦理学的当代建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人权伦理学》、《传统理性哲学的终结》、《伦理智慧》以及德文《客观理性哲学——理论与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著作、学派与概念》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
知识与自由关系的伦理反思
本篇探讨知识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与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信息是相对原始的、零散的知识,而知识则是经过思虑的、系统化的信息。本文所使用的知识概念,便是这样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信息概念,它不仅涉及普遍性、规范性、学理上的知识,而且也关照到具体的、应用的、经验的、实践的知识。
人类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大体上讲以社会变化很小、发展缓慢为基本特征之一。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信息的严重缺乏。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使知识与信息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而且还使得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以巨量的知识与信息密集交流为特点的统一性的网络世界。知识与信息通过占据了信仰曾经占据的地位,而强有力地定义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与信息革命完全可以与近代工业革命的意义相媲美,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事件。
知识的正负面作用
从人类发展史客观事实的角度来看,知识-信息与人的自由一开始是处于一种正向促进的关系:知识-信息越是增进,人们便越是自由。人们越是自由,知识也就越是繁荣。健康的人类理智应当是科学式的,即对偏见与专断的消除,对监视与控制的排斥,对内部与外部枷锁的挣脱。科学知识、技术发明不仅能够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令其告别饥饿与贫困成为可能,而且也能使人们得以祛除先前占支配地位的与社会、政治、宗教的观念相联系的精神强制与理智束缚,有机会仅仅是听从真理,而不是某种上位权势的征召。因而,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同时,知识与信息越是自由与发达,则社会便越易革新与开放。社会可以依照科学自由探索的精神和行为规范来实现其民主。而社会越是开放,则知识自由便越能够得到伸张,新知与发明便更加丰富,公助与私助的研究就得以推进,科学便越是发展繁荣并富有成效。
如上,知识能够促进自由,与人类自由处于一种正向的关系,因而知识逐渐获得了一种尊贵的地位和权威的形象。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知识与自由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知识的负面作用开始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显露了出来。
从内容上看,直到19世纪末,对知识的毫无迟疑的信任还一直都支配着人类社会。然而到了核知识与技术出现之后,这种无限的信任马上就被一种对所谓邪恶知识的巨大恐慌所替代。1945年美国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核弹,使人类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知识探索能够引发如此规模与烈度的灾难,人的发明创造竟可以导致人类自身毁灭的效果。而切尔诺贝利以及福岛的核事故则又使人们彻底丧失了对核能可以百分之百安全利用的信心。基因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可以借由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来实现对人的身体、认知、心理做出遗传物质层面的改变,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人类后代的生命与健康处于极大的且不可逆的风险之中。核能与基因编辑完全能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毁灭人类的未来,它们便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摧毁人的自由与文明的邪恶的、有害的知识,因而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防范与警惕。
从形式上看,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家们逐渐为科学知识赢得了一种能够征服万众的信仰物的地位,知识甚至是获取了一种现代的社会宗教的形象。人们信服它有关一种终极美好的社会状态的构想,冀望于它可以排除对痛苦、侮辱、剥削、贫困、暴力和统治奴役的恐惧。在一种信息体量剧增、外在环境异常复杂的世界里,简化繁复性、获取具体的行为导向的需求在民间就显得更为迫切。人们对知识的信仰,反过来也强化了知识的威权的地位与声势。知识可以如同暴力那样生发出一种垄断的作用,它能够支配人的世界观与生活意义的形成,影响当事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构,重塑其心灵秩序,克服其内心冲突与动摇不定,左右其对客观世界的解析、对终极目标的设定以及对行为方位的寻求。知识可以通过威权的使用和精神的导引,实现一种强有力的内在化的社会控制。这样,知识便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所谓异化现象的基本结构:知识原本是人们为了认识与改造自然从而造福人类的武器,现在却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思想、影响人的精神的工具。科学知识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一面引导人们从威权主义、宗教迷信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旗帜,而今天却已转变成为一种具有神圣光环的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抵制批判与质疑,从而转换到了其当年反抗之对象的位置上了。
常态化的无知状态对人类自由的威胁
人们认知客观世界和自身主观领域,通常需要依靠感觉与理性。尽管感知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变迁受到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和认可,但从总体上讲,通过理性来把握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坚定信仰。然而,对人类理性知识的乐观估计与信念,却难以避免与现实世界真实状态本身的碰撞:不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其所呈现的高度复杂性与不可形容性都远远超过了理性的认知与把握能力。随着技术探索能力在规模上的扩展和精度上的提高、人的研究水平的上升,人们发现认知越多则越是觉得自己的无知,以及越发感知世界的完全可知性的困难。知往往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无知则是常态。
这种所谓无知的状态是由于自然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自然世界以高度的复杂性为其根本特征。自然界所呈现的是一幅无数基本元素以无限繁复的方式扭结在一起的网络化结构的图景,其高度多样的因果联系是人们可以设想但难以掌握的。自然界图景的高度复杂性也使得人们对其的知识只能是朝着分散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一种全知全能的百科全书式的对物质世界的精准把握,特别是使其集中在一个头脑里,这或许将永远停留在幻想的阶段上。
人类社会有别于大自然之处在于,它不仅受制于复杂性,而且也深受这种复杂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对自身现有的多元性、多样化的状态以及人群中政治分歧、利益冲突的高频震荡的一种反映与折射。而当偶然性无处不在时,做出一种正确的决断自然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因而,对于作为性质复杂的有机体的人类社会,人们很难获得整全的充分的知识。我们所能了解的,仅仅是一部分的具体情况,而不是全部的具体情况;仅仅是某些性质,而不是全部性质;仅仅是抽象特征,而不是微观细节。这样我们就难以借由科学的解析力,来预测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全部的具体结果。以哈耶克举对球赛的预测为例:我们知道比赛的规则,了解每一位球员的竞技状态,但我们只能估量事件的一般特点,而无法精准地预测比赛的最终结果。于是,社会科学家就仅仅适合于提供一种对事件的总体宏观描述,而无法给出对细节的精细刻画。由于人们无法借由社会科学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的知识,故那种试图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的想法便是一种“知识的僭妄”。社会科学不能对未来发生的事件细节做出正确的预言,则我们对于社会知识的态度,就只能是小心探索、谨慎建构;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如园丁照看植物那样,细心养护花草的生长。
除了自然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造成了人的无知状态之外,人的主观世界本身的复杂性,亦即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构成了人们难以形成一种可在主体间交流验证的本质性知识的重要原因。在人类传统的认识论中,对理性的认知能力的信赖一直占据支配的地位。但是,这种传统上忽视感性直觉之作用的态度,已经在当代遭到了巨大的质疑。例如,哈耶克早就通过其“实践知识”的概念,对感性直觉的重要作用做出了系统的阐释。
哈耶克所看重的知识,是与人们在中学和大学及借由书本学来的理论知识相对应与区别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是一种无意识的感性直觉,包括习惯、立场、情感与态度,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与职业体验和实践总结,构成了人有意识的、理性的判断及行为取得成功的基础。实践知识这一概念所涉范围非常广泛,如工匠的手艺、医师的技术和投资家的经验。实践知识具有很强的个人独有特征,是下意识的,因而亦被称为隐含知识。隐含知识是一种针对瞬间事务的知识,它大部分基藏于下意识的底座,因而这种与经验相系的知识无法语词化,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并与他人进行理性交流,仅是借由个体行为得以显示。当事人完全可以清楚知道,在既定的情况下合宜的行为是什么,但他自己却并不明白,为何只有这一行为才能达到目标。这一理由深藏于其无意识之中,它们无法成为理性探讨的对象。哈耶克的“实践知识”概念清晰地勾画出了感性直觉的性质以及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确,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网络拥有着极为繁复的结构与层次,涉及到上百万个参数的上千亿的神经元以高度复杂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完成着同时处理信息的工作。人的大脑正是通过一种快速高效的评估系统,将收集而来的外界信息进行并行处理,使我们能够做出瞬间的抉择。这一直觉性的评估过程被称为黑箱操作,因为其运作逻辑是当事人自己所难以解释的,也不属于可供分析的对象,甚至也远离人的主观把控,因而其错误也无法得以修正。极速高效的直觉能力的提高,不能依靠理性启发,而是有赖于经验性的勤学苦练。这种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神奇的感性直觉能力,就如同梦想、顿悟、醉酒、狂欢等一样,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惊喜、乐趣与意义,但由于其非理性的特征而难以产生出可以为主体间交流讨论的本质性知识,从而也就造成了人们在主观的认识能力以及与此能力密切相关的认识对象上的一种持久的、不可克服的无知状态。
而无知状态对于人的自由则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人的知识质量与范围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其自由的程度与性质,自由的决策是建构在对事物的因果关联、对现象的展示逻辑的揭示之基础上的,可能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对充分知识的可信赖的把握。反之,如果当事人深陷于一种信息不透明的处境,那他就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自由的行动。总而言之,知识是自由之基,自由是知识之女。知识越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有上升的空间与可能。在自由与知识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
知识的去中心化与复杂自由的实现
主客观世界条件的局限性造成了我们认知的有限性,而无知的常态化又导致了人的自由行为的受阻。当然,这样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并不会泯灭我们对知识与自由的期望,而是促使我们自觉破除对所谓绝对知识及绝对自由的幻想,消弭试图通过整全的知识来充当救世主的那样一种狂妄。无知的常态化并不意味着知识与自由的彻底终结,而是意味着它们的登场与发挥作用需要以新的面貌和样态。
从知识的层面来看,在一种高度复杂、急速变迁的客观世界里,不透明性与无知构成了所有重要系统的普遍存在的运作条件,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客体的认知只能是从我们每个人所占据的专属的经验空间、实践领域或专业范围出发,决定了我们各自的知识-信息都只能是单方面的、零散的、探索性的、试验性的,然而这种部分的知识-信息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一方面恰恰是此部分的知识就可以为人们的部分的判断与决策奠立必要的基础,从而能够获得有限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些零散的知识还可以相互联接在一起,通过组合与相互重叠而无限接近一种对整体知识把握,从而从分散的智慧的有效结合中产生出一种自然发生的系统的透明性,这就构成了整体上对于管理高度复杂系统的有意义的知识,尽管它是一种从无数单个知识的拼接与联合中产生出的朝向整体知识的永恒的过渡物。
从自由的层面来看,在一种以部分的、零散的、单方面的知识而不可能是完整的和终极的知识主导的社会里,自由也只能是以部分的、单方面的、零散的知识为基础而呈现为部分的、分散的、有限的、探索性的判断与决策的自由,其本身不可能是整体性与绝对的自由,只是这些个别的自由的联合可以为朝向整体性的自由的演变做出贡献。这种无知社会中出现的部分的、有限的、探索性的自由,亦被称为复杂自由。
如上所述,在一种已被判定为是普遍无知的时代境遇下,寻求与获取单独的、零散的知识是人们试图有限克服无知的唯一选项,但同时也是当事人能够继续前行的必须的选择,因为它构成了我们享受复杂自由的必要的基础。而实现这种知识的获取又有赖于整个社会实施的知识去中心化的战略。所谓知识中心化,是指将所有的知识集中在“最聪明的”人的头脑里这样一种企图,由于少数精英获得了对全面知识的系统掌控,他们就可以做出比每个人分散时做的更好的决策。但是将所有的人的知识聚合起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的知识不仅有可供交流验证的理性知识,也有大量完全个体化的、基藏在下意识当中的隐含知识或称实践知识,这种知识无法借由文字得以表达,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获得交流,这样也就不可能为试图掌握全部知识的精英们所接纳和利用,于是其决策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知识的去中心化战略则要求,社会应赋予人们以自由,对成千上万头脑中所分享的知识以最大可能优化的方式予以使用,简言之,顺应时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特征,实现知识的民主化。只有每位个体才有可能最佳地掌握和应用自己创造和占有的知识,并以这种知识为基础做出更负责任的决断,这就像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那样。知识的非中心化以及相应的非中心化的决断,由于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从他人获取和占有的知识中获得益处,因而也就能够真正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知识的高效增长。
知识去中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开放的、自由竞争的知识市场的出现与形成。知识的去中心化就意味着知识的民主化,社会鼓励民众运用各种渠道积极获取经验,学习和应用所学之物,将这一活动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以这种方式探索新的知识,从而有利于所有的人的使用。知识-信息的更新与对不同的生活形式的实验相关联。这一寻求新知的过程,自然而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隐含着失望的可能,甚至不排除会犯错误的状态,然而所有这一切不利都应被视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必然代价,可以通过自由的益处得到补偿。自由概念本质上意味着实验与学习的自由,这种自由构成了尝试新知的前提条件。最有价值的结果恰恰是在自由的、无先决约束的、对尝试的多重实践中才能获得。因而人们对于看似无用的或者是错误的知识,也应该理解与容忍。就此而言,失误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新知以及社会繁荣的不可回避的先在因素。
原文来源:转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编辑:刘佳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2-9 21:06
【案例】
西方50位社会学思想家的思想
1、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实证主义手册》(1851),《实证政治体系》(四卷,1851-1854),《主观的综合》(1856)思想背景:18世纪末进步哲学特别是杜尔哥与孔多塞的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亚当·斯密和萨伊等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圣西门、康德、笛卡儿、孟德斯鸠、休谟的思想;孔狄亚克和 "观念学派" 以及牛顿自然科学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重整社会秩序的希望在于建立一种普遍人性的人道教,这是社会学的任务。在整个世界发展中,群体、社会、科学甚至个人思想都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科学三个阶段。按物理学的分类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是从社会变迁的连续阶段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来研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规律;社会静力学旨在研究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持久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研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方法。
2、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代表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共产党宣言》(184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哥达纲领批判》(1875),《资本论》(三卷,1867,1885,1894)思想背景: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辨证法思想;法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派的思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莱布尼茨的发展思想和康德的冲突中心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类学思想。主要学术思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形态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社会一切关系和形态变化的基础;阶级利益和斗争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历史既是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人类日益异化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是经济异化的典型形式和高级阶段;法律、政治、宗教等上层建筑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还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思想的根源在于倡导者的生活条件和历史环境。历史进化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它先前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对抗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后建立的共产主义。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和秘密,提出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是人的劳动。
3、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代表作:《政府的适当权力范围》(1842),《社会静力学》(1850),《进化的假说》(1852),《心理学原则》(1855),《第一项原则》(1862), 《生物学原理》(1867),《社会学研究》(1873)思想背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汉密尔顿关于哲学方法的思想;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中发展假想的思想,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赫胥黎的进化思想和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主要学术思想:事物的基本规律是 "力的恒久性规律",任何事物在这种力的规律的作用下,都不可能保持其自身的同质。作用于同质事物的力必将引发其不断的变化,普遍的进化框架认为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 (individuation) 的过程,社会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和自然的环境,不一定要经过预设的阶段,社会机构是功能与结构迫切需要的产物,不是行动者意图和动机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分开始分化,体现为结构的增加。在从无差别游牧部落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不断分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基本的社会分类是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前者中人类的合作是通过暴力,而在后者当中,合作是自愿、自发的。国家的唯一权利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地狱外部的侵略,好的社会基于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契约。社会科学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家须尽力摆脱不适当的偏见和情感。
4、齐美尔 (Georg Simmel,1858-1918)代表作:《社会分化》(1890),《历史哲学问题》(1892),《货币哲学》(1900),《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1908),《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1917)思想背景:法国和英国实证主义思想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观点,德国人类学的发展 "平行" 理论和利珀特的观点;康德与新康德哲学思想和方法以及尼采和柏格森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不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也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因互动而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的科学。社会学分为一般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三类,其中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识别人们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理解" 概念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难免带有主观的价值取向,其知识也具有主观的和相对的性质。群体互动形式的研究证实了大群体和小群体的差异。社会是一个包含合作与冲突、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合作与冲突的存在,社会冲突可以分为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它对于群体和社会的整合具有积极功能。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矛盾是文化的客观性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普遍的货币关系中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客观物质文化越发展,人的个性与创造力越衰退,个人在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的特征是对社会的疏远和异化,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个人的发展只能是畸形的。
5、涂尔干 (Emile Durkheim,1858-1917)代表作:《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思想背景:法国学术历史主要是启蒙主义传统尤其是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孔德和圣西门的社会观特别是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博纳尔和迈斯特尔等的反启蒙运动思想;库朗热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著作《古代城市》;哲学家布特鲁的反还原主义学说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勒努维耶的观点;塔尔德的《模仿的法则》中的理论;斯宾塞、齐美尔、藤尼斯和心理学家冯特的一些观点。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 "强制" 和作用于人们,塑造着人们的意识;人们无法摆脱这种强制的熏陶和影响,且如果对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整体方法和观点来解释。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和语言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统计方法可以帮助社会学研究处于社会现象层次上,防止任何形式的还原论;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是社会学两个不同但必要的研究方法;可以采用假设—推测—检验的研究步骤。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又可以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类型,有机团结基于社会分工,职业专门化使集体意识受到削弱的同时增加了相互依赖并要求新的职业道德的确立。社会危机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危机,现代社会团结面临着解组的危险和反常社会分工的破坏,需要建立一种与社会分工相适应的多层次道德体系。社会自杀现象根据溯源分类法可以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和失范型三种。
6、沃德 (Lester F. Ward,1841-1913)代表作:《动态社会学》(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社会学大纲》(1898),《纯粹社会学》(1903),《实用社会学》(1906)思想背景: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达尔文、斯宾塞、萨姆纳等的社会进化论,美国的进步运动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发展是宇宙发展的一部分,每一后续阶段都是前一阶段成就的积累;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社会学的基础在于心理学,人可以从理性上控制社会过程 (有目的进化论)。进步分为两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前者依进化的一般法则发展,是被动和消极的;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表现为更加复杂的理智、道德和审美进步,是主动和积极的。国家是集体意识的体现者,将来竞争和垄断应让位于自觉的协作,建立一个 "有目的" 社会,教育和科学是这种计划的工具,科学方法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有可能有意识地改善进化中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历史的自然方面,社会学研究人类历史的文化和心理方面;社会科学的使命应是赋予人类为寻求幸福而必备的知识。
7、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代表作:《中世纪商社史》(1889),《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1921年),《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思想背景:德国康德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中强调 "人是文化和历史领域中积极和自由的行动者" 的思想;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新康德主义者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区分的思想;雅斯贝斯关于解释与理解之差异的思想;经济史学家和历史主义经济学家罗舍尔、克尼斯、瓦格纳、布伦塔以及社会学家藤尼斯、齐美尔的思想;尼采和马克思关于意识与利益的观点。主要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研究关系到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中立性两个问题,一个涉及选题,一个涉及客观和科学的分析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既要反对纯思辩的哲学研究方法,也要反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决定论。(理解)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社会行动的 "主观意义",社会行动类型主要有四种: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合理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习惯性的。真正意义上的 "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 "意义"。理想类型是研究社会和解释现实的一种概念工具,是比较研究的得力方法。社会统治有三种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其中科层制 (或官僚制) 是法理型统治的最典型和纯粹的形式,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人的社会地位是由经济、政治、声望等多元因素决定的。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 "资本主义精神" 为支柱的,这种精神是西欧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世界宗教根据对待世界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入世禁欲主义、出世禁欲主义、入世神秘主义、出世神秘主义,现实中往往有各种成分的杂合。
8、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代表作:《社会阶级间的负债》(1883),《民俗论》(1906),《事实的挑战及其他》(1916)思想背景: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督教神学理论以及美国社会政治新思潮。主要学术思想: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中存在的合作与对抗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的状态和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竞争导致有益的结果:消灭不适应者,保持种族兴盛和文化繁荣。社会科学对民俗的研究,与生物学对细胞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意义,一切社会制度还原为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俗和民德;风尚是指人们在追求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个人层面上叫习惯,群体层面上叫风尚。民族风尚包括一切标准化的行为方式,其形成原因有两类因素:各种利益之争 (生存竞争中的保卫和进攻);人类行为的四种主要动机——食欲、性欲、虚荣心和逃避恐惧的心理 (其基础在于利益);风尚不是人的自觉意志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只是生物进化的一种形式,在于内群体间和外群体间的争斗和竞争;同一类习俗标志着同一个种族;内群体中存在一种团结的合作关系;和外群体之间是一种敌对关系 (民族中心论)。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或国家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社会整体运行的机制就是竞争,社会是竞争着的群体的组合。
9、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代表作:《社会学原理》(1896),《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1924)思想背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涂尔干、萨姆纳、沃德等的社会学思想和心理学研究,塔尔德的模仿论,密尔等的政治社会思想,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和亚当·斯密的人类情感说。主要学术思想:主观的社会事实即 "同类意识" 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同类意识是指一种含有同情和知觉因素的心理状态,它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社会是由同类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群;同类意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它使个人由最初模糊的群体状态进入到有组织的社会固定状态,使一切社会组织、社会团结和合作、社会适应和进步成为可能。最初的无意识行动变成习惯,直至成为必须遵循的标准规范;社会遵从的压力代替了环境造成的盲目压力,也取代了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带来容忍与合作,甚至超越冲突在联想、模仿等机制的相互作用中使人们对共同利益产生必然的认识。社会分为四个层次:同类意识发达的 (合群的人),同类意识不发达的 (不合群的人),没有同类意识的 (反群的人),同类意识堕落的 (伪群的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通过个人来透视社会,通过同类意识来透视 "社会性" 和社会协调的行动;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视为心理的现象;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同类意识。
10、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代表作:《有闲阶级论》(1899),《营利企业论》(1904),《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不在地主所有权》(1938)思想背景:贝拉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著作《回顾》中关于冲突性企业竞争和统一的有组织工业体系的思想;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异化论等观点;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尤其是斯莫勒的理论;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和生理学家洛伯关于本能和向性的理论,以及托马斯和博厄斯的人类学思想。主要学术思想: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放到它的社会背景中加以分析,人们的夸耀性消费模式是具有其内在潜功能的。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是指消费者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不是较低而增加,它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即凡勃伦效应);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人类进化是作为一种对环境有选择的适应过程来进行的,首先涉及到发明和更有效技术之应用,人类社会进化的四个阶段是:和平原始经济的新石器时期、掠夺性未开化的经济时期、手工业时代、机器支配的现代社会。思想习惯是生活习惯的产物,思考方式依赖于社会组织,人的看法和思想习惯取决于其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人的认识是由社会决定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们通过与同伴的价值比较判断自己的价值,同时也陷于对自我尊重丧失的恐惧中,每一个阶级都尽力模仿它的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 (竞争行为的社会诱因论)。先进技术和起阻滞作用的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制度一般相对滞后于技术的发展,新技术能战胜即得利益并按自己的需要重新制定新制度。股份资本论等一些理论命题奠定了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基础。
11、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代表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 社会过程》(1918 ),《生活和学者》(1927)思想背景:麦考莱、爱默生、歌德、斯宾塞和达尔文的一些关于自然与社会的思想;鲍德温的心理学理论和个案研究,詹姆斯关于心理实质与自我实质的观点和自我多元论观点;梭罗、帕斯卡、但丁、托马斯、白哲特、托克维尔、塔尔德、沃德、吉丁斯、斯莫尔、萨姆纳等人的一些思想。主要学术思想:心智不是笛卡儿认为的超然于外在的世界,而是个人与世界互动的产物;"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 概念体现了自我是与别人面对面互动的产物;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 "镜子";社会经过多次的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个性自我的一部分,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整体。社会是各种过程的复合体,每一过程在和其他过程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的差别在于前者规模较小,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 "亲密合作与面对面的沟通关系",是个体初级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和特殊品德的培育地;而次级团体则规模较大,并且 "分工互赖,以非情感的依赖相结合",有明显的阶层。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人类行为的研究必须同人类行为者赋予环境的意义相联系,对人的认识是基于研究者对人的动机和行为变化具有同感理解的能力。社会由行为者与亚群体之间的信息网组成,信息过程特别是它在舆论上的作用可以巩固社会的联合,社会冲突是必要和不可根除的。经济价值体系特别是货币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12、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 代表作:《伦理》(1909),《公社与社会》(1912),《公众舆论批判》(1922),《进步与社会发展》(1926),《社会学研究与批判》(三卷,1925-1929),《社会学引论》(1931),《近代精神》(1935)思想背景:德国哲学和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特别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和自然法学说;18世纪末启蒙运动和古典主义引起的浪漫主义思潮。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是研究人及其生理、心理和社会本质的科学,可以分为一般社会学(关于纯粹共同生活的学说)和专门社会学,后者又分为纯粹社会学 (概念阐述)、应用社会学 (用概念理解当前和历史变迁)、经验社会学 (消极关系和社会病态的研究)。社会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 "公社" 和 "社会" 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概念;公社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有机人群组合,它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 (本质意志);社会是靠人理性利益的权衡 (选择意志) 建立起的人群组合,是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一种机械合成体;从中世纪向现代的整个文化发展就是从 "公社" 向 "社会" 的进化。社会构成的本质要素有:社会关系 (纯粹类型为联盟)、社会集合体 (纯粹类型为党派)、社会集团 (纯粹类型为联合体),它们既可以表现公社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社会的形式。社会价值指具有社会本质的对象;社会规范指社会行动的规则,它分为三种形式:秩序 (基于和睦与常规)、法 (基于伦理与立法程序)、道德 (基于宗教与公共舆论);"社会相关物" 指与社会本质因素相关的体制和现实作用领域。社会学研究应当坚持严格的价值中立原则,摆脱价值判断。
13、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1848-1923)代表作:《社会主义体制》(1902),《政治经济学手册》(1907),《普通社会学》(1916),《事实与理论》(1920),《民主制的变革》(1921)思想背景: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关于权力斗争的政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孔德、斯宾塞、圣西门等的实证主义思想;现代数量经济学特别是瓦尔拉的思想;莫斯卡的《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塔尔德和勒邦的社会心理学和培尔的怀疑论。主要学术思想:人类活动分为逻辑性行动和非逻辑性行动,前者指在主观和客观上将手段与目的合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反之即非逻辑性行为;后者是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大多数人们的活动是不自觉的非逻辑行为。剩余物是人们没有直接认识或也不能间接认识的情感与表现和行为之间的中介物,主要是能导致推理的那些人的本能;派生物指的是意识形态、信仰和理论一类的东西,是剩余物的证明物,是相对易变的成分。六种剩余物是:组合的本能、组合体的持久性、行动的本能、社会性、个人的完整性、性本能;四类派生物是:简单肯定、权威论据、原则、口头论据。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与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之分,即精英与群众,这是认识和说明社会的前提;狭义的精英指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广义的指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政治变化的形式就是一种类型的精英取代另一种类型的精英的循环 (精英循环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系统,影响系统任何部分的事情都会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社会运行是由三个子系统同步循环和相互影响的结果——社会情绪的循环、经济生产的循环、政治组织的循环,它们之间发生连锁反应而展开,促成社会总体形式变化和运动;社会系统总是倾向于由不平衡走向平衡。
14、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代表作:《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年),《逻辑学理论研究》(1903),《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哲学的重建》(1920),《人性与行为》(1922),《经验与教育》(1938),《人的问题》(1946)思想背景:黑格尔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传统尤其是莫理斯的思想;康德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霍尔与詹姆斯的新实验生理心理学思想;欧洲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19世纪晚期的新哲学。主要学术思想:哲学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哲学家应走出思辩的象牙塔,投身于政治、教育和伦理的活动,用哲学推动民主。"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 强调有机界对环境的适应,精神是一种思想的过程,一个人在头脑中定义客观事物的过程,具有工具的性质;而思想产生于人类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勾勒出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设想某行为的后果,区分不能与环境协调的行为并计划消除之,寻找出能实现协调目标的行为方式。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应将日常生活状况和问题看作研究主题,证实一种社会科学是否正确需要将它应用于实际,看它解决实际问题的功效。人类的本质有很强的可塑性,可通过改善了的社会环境得到改进。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孤军奋战的,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群体而生存的;个人和群体关系以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将来的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明智地选择可能达到的预期目的,在良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人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生命,他更应该主动地塑造生活。
15、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1854-1926)代表作:《社会学通论》(1905),《亚当、斯密和现代社会学》(1907),《重商主义者》(1909),《社会科学的意义》(1910),《两个里程碑: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政治》(1913),《美国社会学五十年 (1865—1915)》(1916)思想背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涂尔干、萨姆纳、沃德、拉兹霍弗等的社会学思想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实证研究。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要着重研究人际之间互动的过程,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是研究的主体;要采用 "综合" 的思想关注对社会经验一切领域的全面研究,这将最终解决现代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冲突,走向能确保国家福利的有组织的和谐。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认为:个人和群体的生活充满了利益,其基本利益可分为六种:生理需要、财产、社交、知识、审美和正义,群体作为社会利益的聚集单位应当被看作有组织的利益的载体和社会进步的单位,这些基本利益的不断冲突、调整和发展构成了社会过程,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全部社会生活归根结底是发展、适应和满足利益的过程。学术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描述、分析、评价、建议;科学不应当放弃价值判断,而且这是科学的直接任务,社会学的真正目的是对人类实现更为正义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
16、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1863-1947)代表作:《性与社会》(1907),《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未经调教的女孩》(1923),《美国的儿童》(1928),《原始行为:社会科学导论》(1937)思想背景:冯特的心理学和拉撒路、施泰因塔尔的比较人种学理论;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和勒布的生物学理论;杜威和米德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和沃森的行为主义理论;迈耶的生活史研究、比勒的儿童研究和博厄斯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成员自发形成的情景释义和这个社会给予人的释义之间总存在一种对抗;人不但能对情景的客观特征做出反应,还能对情景所产生的意义做出反应,情景的意义一旦确定,那么人的符合该意义的必然行为也就产生了 (即情景定义);人的特殊行为模式和全部个性都是在生活道路上感受过的情景类型和经验特征所限定的;社会和个人之间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态度是人的意识过程,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真实的或可能的活动,即人们作用于社会客体的预先倾向;社会变迁总是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一个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从来都是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共同产生的结果。人类四种基本的愿望:要求新的经验、要求承认、要求支配、要求安全;需要同时关注文化价值观的客观性及其在特殊制度中的表现和态度、主观定义和共同经验的平衡。人类行为可分为守旧、反叛和开拓三种类型。
17、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1926),《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1929),《自由和文明》(1944),《科学的文化理论》(中译本《文化论》, 1944),《巫术、科学与宗教》(1948)思想背景:弗雷泽的《金枝》,摩尔根、泰勒等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布依赫的经济史研究,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理论,霍布豪斯的社会学理论,塞里格曼的人类学思想和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和社会需要时才能存留和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于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人类的首要需要是个体有机系统的需要——营养、两性及传种、防御、日常生活必备品,这些 "文化迫力" 促使社区发生有组织的活动;更高层次的需要和文化迫力表现在社会和精神的方面,功能始终产生于对文化迫力的反映。文化的功能就是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功能普遍存在于任何文化现象中,任何文化现象都发挥着不能为其他文化要素取代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它们共同使社会成为统一的整体。制度是使人们的活动有组织地满足某种重要需要的基本和相对稳定的方式;文化的真正要素在于它具有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和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合部分。
18、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代表作:《当代哲学》(1932),《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19世纪思想运动》(1936),《行动哲学》(1938)思想背景:新英格兰的公理会强调自主学术研究、对社区的道德义务的传统;强调实干的边疆传统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特别是变化永恒观点;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包括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等人的思想,以及冯特的心理学理论和伯格森关于经验流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处于社会过程中的个人活动或行动的学科;而个人的行动只有看作他所属的群体的行动时才能被理解。离开社会不可能有自我,也不可能有自我的意识和交流;社会必须被看作一种结构,它在彼此适应的人们所进行的各种交往中显现出来;意识必须被理解为产生于个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之中的思想交流,它是后天的,而不是个人先验的。人从孩提时代就具有了扮演他人角色并从他人角度观察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并产生出人的意识和自我;自我是一个社会实体,其实质在于它自身的反射;个人自我之所以是个人的,是因为它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关系;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自我是自我所具有的社会性实质。"自我" 概念可以区分为 "主我" 和 "宾我",前者是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后者是想象的一套组织化的他人态度,它们都必须与社会经验相联系。一个发达的有组织的人类社会以错综复杂的方式联系起来,必然存在冲突和协作。意识是一种依靠公众手段进行的内心对话,个人的经验可以通过应用有意义的社会符号获得,并从 "概化的他人" 概念意义上组织起来。
19、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1934年),《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1950),《时代诊断》(1950),《知识社会学论集》(1952),《社会学系统论》(1958)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和齐美尔、卢卡奇的思想;德国历史主义的相对理论;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心理事实中构造或结构要素的思想;新康德主义特别是李凯尔特的价值相关论和文德尔班的思想以及韦伯的解释;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谢勒的《知识的形态与社会》中的许多思想;黑格尔的历史环境与现象与“过程思维”之间的辨证关系思想;美国实用主义和杜威、米德、库利、艾略特等人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知识社会学探索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的社会条件和存在条件;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全部认识论包括现代认识论的基本要素;决定行动方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意识 "范畴结构" 中的社会 "存在制约";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包括真理都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并受其制约,知识是由存在因素决定的。社会结构与知识之间的确切关系只有通过对各种具体情况的经验或调查才能揭示出来,所有思想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所有的阶层和群体都根据本身存在的地位提出适应自己的思想,大也存在超脱社会的知识界人物,精神的社会制约性对精神彻底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当代的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一个 "彻底民主化" 过程的问题;群众社会组织内,能把各种活动有效并预测性地组织在一起的能力——功能理性取得长足进步,而能揭事件相互关系的睿智思维活动——实体性理性有所下降;拯救西方文化的唯一途径是彻底重建社会制度,依靠个人自觉的计划而不是市场机制实现对个人不协调行为的控制,在保障人的社会价值前提下,对自由加以设计,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调节,民主计划应推动整个社会重建;精英人物在这种重建中负有特殊使命。
20、帕克(Robert Ezra Pack,1864-1944)代表作:《群众与听众》(1904),《社会学科学导论》(1921),《种族与文化》(1950),《人类社区》(1952),《社会》(1955)思想背景:德国社会科学特别是齐美尔、保尔森、藤尼斯、施本格勒关于文化的研究;俄罗斯社会科学家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哲学和心理学家詹姆斯的自我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西杰勒、勒邦、塔尔德关于集体行为的观点等。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是 "集体行为的科学",社会控制是社会的主要事件和中心问题,指各种组织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机制;社会制约机制成功控制各种对立面使之相互协调即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四种主要的社会过程是:竞争、冲突、顺应和同化;社会距离指的是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偏见和社会距离在人类关系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但这不同于种族对抗冲突。社会变迁的三个阶段是:不满引起社会骚乱和动荡、群众运动、包含于重建的法律秩序中的顺应;各种群体在都市环境中划分出各自的生态位置,即他们的自然区域。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群体、所占有的土壤、生物系统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借鉴从事非人类共同体研究的生物学家的方法研究人类的聚集,社会是在个体共同行动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自我的构成基于我们所占的地位和在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个人对他自己的角色的理解而构成,同时也基于社会其他人对这些角色地位给予的承认;边际人是生活与两个世界自我概念不协调和矛盾的人,在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
21、布朗(A.R.Radcliff-Brown,1881-1955) 代表作:《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1952),《社会人类学方法》(1958)思想背景: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功能论思想;里弗斯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的功能理论。主要学术思想:功能分析不能脱离社会结构,某种文化现象具有特定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它满足了某种整体需要,社会整体是一个功能统一体,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不会产生不可协调的冲突;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规律或功能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功能上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 (功能指一个局部的行为对其整体的贡献)。社会结构指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中的人的配置,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经确立的行为规范和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功能分析无须假定普遍的人类或社会需要的存在,生存所必须的条件是一个经验,是每一个社会系统都涉及的问题;不同社会系统的生存条件存在差异,因此文化事项也是不同的,而且相同的文化事项也不一定都具有同样的功能。
22、索罗金(Pitirim Alexandrovitch Sorokin,1889-1968)代表作:《社会流动》(1927),《社会、文化与人格》(1947),《社会和文化动力学》(四卷,1937-1941),《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1950年),《社会和文化流动》(1956年),《漫长的旅程》(1963) 思想背景: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特别是赫尔岑、拉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的一些社会观点;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和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反单线发展观理论;科瓦列夫斯基的社会制度比较研究以及别赫捷列夫、巴甫洛夫的行为理论。主要学术思想:思想人的交往涉及三个方面:作为交往主体的动作者的人,指导人行为的意义、价值和规范,使意义和价值客体化的并体现为动作运载和传达工具的物质现象;超机体因素是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是相对连贯和完整的文化观点 (心态) 的积累,它们赋予人类历史某一特定时期以意义;理解真实性质的前提有三个:感性文化、心灵文化、理性文化,相应地真理存在不可分的三种形式:感觉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任何一种由主要前提决定的文化都服从一种内在必然性,并通过这个前提趋向极限来突破常态,使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得以降生,社会类型不是孤立的产物,而是永不中止的结合的结果 (极限原理),这导致了社会文化的周期性。任何发明发现真正新的成分是很有限的,时间、空间等概念是人类社会具体需要的产物,由存在所决定。社会流动主要研究群体之间人口交换的过程和结果 (也有群体内的分层的增加和减少),有两种类型: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都是在几何空间内发生变化和在历史时间中发生波动。西方感性文化崩溃后将是新的灵性文化,和谐文明所具有的利他主义的爱将战胜感性思想的竞争斗争。
23、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价值、动机和行动系统》(1951),《社会系统》(1951),《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1966),《现代世界体系》(1971),《行动理论与人类状况》(1978)思想背景:早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涂尔干的社会唯实论思想;马歇尔、帕累托的经济社会理论;英国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思想。主要学术思想:行动是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任何行动单元都可以分解为:目标、状态 (又可分为手段和条件)、规范取向;行动过程中人们在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时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同时也受社会文化价值规范和状态背景两个因素的制约。行动系统指行动者与其状态之间发生的某种稳定的关系,又可以区分为四个附属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行为有机体;各个附属系统按其所在的等级层次同其他附属系统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发生着控制和制约的关系。社会结构是指各个地位-角色之间的稳定性和制度化关系,行动者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角色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维持某种制度化的价值体系是社会系统稳定的基本前提。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必然面临五个方面的抉择,即五对范畴的模式变量:普遍性与特殊性、扩散性与专一性、情感性与中立性、先赋性与自获性、私利性与公益性;任何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都是以上五种抉择的某种组合。社会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要求,这些要求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它可以用四个基本范畴来概括:适应 (A)、达鹄 (G)、整合 (I)、维模 (L);一个系统是否稳定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满足其一般功能需求的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是否存在跨边界的对流式交换关系。社会进化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抽象演化形态:适应性增长 (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分化过程 (社会结构和目标的分化)、发展着的容纳过程 (系统整合的要求提高)、价值概括化 (抽象共同价值代替各种特殊规范)。
24、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代表作:《科层结构与人格》(1939),《大众信念》(1946),《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949/1957),《学生—医生》(1957),《科学发现的优先权》(1957),《科学界的马太效应》(1968),《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1975)思想背景:孔德、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韦伯、涂尔干、托马斯的社会学理论,英国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思想,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等的经验研究。主要学术思想:功能分析方法不是对现实做出抽象的和带倾向性的说明,而是发展出一种既可以解释经验材料又能被经验证明的 "中级理论";功能的性质需要在特定范围内借助经验才能加以确定 (功能分析的经验范式);功能需求的确定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即使已经确定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项目来满足。功能分析应把重点放在客观社会后果上,发现各种行动后果的集合性质,揭示建立在这些性质基础上的各种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第一步是明确对之进行功能分析的项目和制度化行动模式 (结构) 的客观后果;其次是认识到客观后果的多重性特别是潜在后果;第三步是结合时间要素根据特定后果与相应系统间的关系对之进行功能评价,并通过反功能考察社会问题和变迁现象;第四步是弄清后果所涉及的系统和群体范围,识别特定后果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功能性质;第五步是认清不同类型社会中功能替代的可能性,并通过对 "结构制约因素" 的考察解释替代过程。社会结构指一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它总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冲突,构成社会和文化结构的诸要素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分化是导致其变迁的主要原因,应当实现社会学分析的经验化和多元化。科学具有独特的规范结构和运行机制,构成科学精神气质 (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它们借助于制度化价值合法) 的制度规则有四种: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25、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代表作:《理性和革命》(1949),《爱欲和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论解放》(1969),《艺术和永恒性》(1976),《审美之维》(1978)思想背景:黑格尔的辨证法哲学思想,胡塞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拉康的哲学观点,弗洛依德的思想,主要是性本能理论和心理学;马克思的很多著作,特别是关于人的异化和全面发展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富足的社会,它高度发展的生产率通过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而造就出整合、包容所有社会力量的可能前提,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消除了危及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使社会政治成为“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政治;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创造出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方式,还促进了人们与现存制度的统一, 这造就了没有创造性的单面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知道追逐高消费而失去革命主动性,只有激进的学生运动 、流氓无产者、失业者、受压制的少数民族才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被溶合于社会整体中。人的心理结构分为 "意识" 与 "无意识" 两部分,"无意识" 比 "意识" 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性欲是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的核心和关键是劳动的解放,真正有意义的劳动,应该是人的器官的自由消遣,它为 "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构成的冲动" 提供了机会。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它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唤来一个解放的世界;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单向度社会中双向度的批判形式。
26、米尔斯(C.Wright Mills,1916-1962)代表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权力精英》(1956),《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关于人的幻想:社会学思考的典型传统》(1960)思想背景:贝克尔、葛斯和罗斯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帕累托、齐美尔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主要是社会冲突思想;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帕克和凡勃伦的社会冲突思想等社会学理论。主要学术思想:白领阶层 (企业家与工人之间形成的中产阶级) 的出现是20世纪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重要变化,白领劳动者的职业出现了自我异化和劳动异化两种心理反应;一个是异化造成的心理忧郁与迷乱,一个是由于社会结构对性格的影响使人们疯狂地休闲;他们置身于庞大的科层体系中,缺少控制生活的个人权力和参加政治事务的政治权力。美国是一个由权力精英控制的社会,作出重要决定的国家权力集中在企业家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手里,形成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的权力精英圈子,社会中的其他社会制度处于边缘地带;权力可以建立在财产之外的因素上,但权力精英因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维持一种持久的和战争性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应当防止过于注重实证的取向,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保持社会理论的创新活力。
27、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1910-1989)代表作:《人类群体》(1950),《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思想背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思想尤其是洛克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人类学中的交换思想,包括弗雷泽、摩斯、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的交换思想;行为心理学主要是斯金纳的行为研究。主要学术思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过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最高的报酬;社会是个人行动和行为交换的结果,个人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原则。六个命题的运用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1、成功命题:个人的某种行为越是经常得到相应的报酬,他越可能重复该行为;2、刺激命题:相同的刺激可能带来相同或相似的行为;3、价值命题: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对某人越有价值,那么他越可能采取该行动;4、剥夺与满足命题:某人近期内重复获得相同报酬的次数越多,这一报酬的追加部分对他的价值越小;5、攻击与赞同命题:当个人的行为没得到期待的报酬或受到没有意料的惩罚时可能产生愤怒情绪,当个人行为获得预期甚至超过期待的报酬或没得到预期的惩罚时心理上会赞同这种行为,行为结果的价值也增大;6、理性命题: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而是一种理性行为。
28、斯特劳斯(Levi Strauss,1908-2009)代表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忧郁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思想背景: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特鲁别兹科依和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学理论,库恩关于科学革命中的 "范式" 观点;卢梭关于人的理论;理性主义哲学、地质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一些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学术思想:地质学家是用某种模型把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表现出来,而精神分析学家是通过心理模型把人的心理世界表现出来,马克思是把一种类型的现实还原为另一种类型的现实。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 (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的人类研究可以寻找到对全人类 (不同民族、不同时代) 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所有可观察的现象是由那些一般的但是潜隐规律的作用造成的;很多表象背后的结构其实是相同的,结构是事物最普遍的因素,也因为这种结构的存在,它可以转换不同的现实,也才能更好的理解某一种现实。结构主义中的结构不是人为的结构,而是无意识世界的基本模型,它决定世界的意义和形态包括人的意识,而不是相反;结构是意识的主体。将人的精神、社会和情感生活还原为无意识的形式结构并不是要否认前者的真实性,而是要用一个统一的并表现在一切现象中的复杂结构来理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的复杂性,但不能从这个结构中先天的推出这些现象。
29、斯梅尔塞(Neil Joseph Smelser,1930-2017)代表作:《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1959),《集体行为理论》(1962年),《经济生活的社会学》(1967),《社会学解释论文集》(1968),《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1976),《变化中的学术市场》(1980)思想背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尤其是帕森斯的思想,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滕尼斯的社会发展观和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等。主要学术思想: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即社会结构分化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 一个社会角色或组织…分化为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充分有效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功能的角色和组织。这些新的社会单位在结构上互不相同,但在功能方面却结合成一个整体,能象分化前的那个整体单位那样发挥功能;在任何情况下,结构分化概念都为度量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尺度。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对位性相互作用的过程;从某一社会分化始点到某一社会整合终点,期间通常经过七个阶段:(一) 社会分化的缘起,(二) 社会动乱征兆的显现,(三) 社会紧张的控制,(四) 制度创新方案的制定,(五) 社会分化的发展,(六) 企业家的创新实践,(七) 社会整合的形成。因为分化和整合在社会内部不同部分的发展程度不一,引起各种社会紧张,其结果就是社会动荡不安和群体冲突。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对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历史过程导致了成功的经济性分化,并拓展了行动范围,产生了一系列响应市场要求的非经济性分化。
30、科塞(Lewis Alfred Coser,1913-2003)代表作:《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社会学思想大师》(1971),《结构与冲突》(1975),《社会结构中的本我》(1975)思想背景:默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齐美尔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帕累托、帕克、凡勃伦、马克思、韦伯等的社会学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是一个由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部分所组成的功能系统,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资源、声望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当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对分配方式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或部门之间关系失调时,社会就会发生冲突。社会冲突的原因可以分为物质性的 (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 和非物质性的 (价值观和信念的不一致);冲突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社会结构与心理因素两者间不同程度的结合。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对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可起到一种手段作用,还可以激励社会革新,导致社会变迁。冲突可以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前者有助于明确群体界限和使群体发展壮大;而后者可以导致群体新的团结和平衡,还可以通过排除外来者避免群体的解体。冲突还可以分为现实和非现实冲突,前者有明确的目标,后者纯粹是为了宣泄敌对情绪。围绕核心价值观发生的冲突可能威胁社会群体,表现性的冲突可以维护结构;社会冲突的功能有三个方面:社会功能、社会心理功能和分裂性功能 (反功能);频率高但强度小的冲突能增强系统内各单位的创造性,缓解群体间的敌对情绪,扩大社会联合,从而提高社会的整合水平,增强群体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安全阀机制有利于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为防止社会冲突发生在一个断裂带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应当在社会结构中加以制度化。
31、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代表作:《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走出乌托邦》(1958)思想背景:齐美尔、马克思、韦伯的的冲突理论,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政治学思想,帕累托的的冲突论思想和精英循环论,帕克、凡勃伦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基本现象,冲突现象可以疏导和控制或被压制,但无法彻底消除;社会每一个要素都可能促进社会变迁;每一个社会都以一部分成员压制其他成员为基础。社会结构分析的基本单位是是社会地位,多数社会形式中都存在两种不同地位:统治地位 (拥有权威) 和服从地位 (丧失权威),这两种地位的结合就是权威结构;一切具有权威结构的社会成员的结合形式即强制性协调组合,现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是权威的分享和排斥之间的矛盾。强制性协调组合中对立准团体的成员,除非受到被称为组织条件的经验变项的干预,都将把自己组织为有外显利益的团体,从而形成团体冲突;利益团体在涉及现状问题时经常处于相互冲突中,其形式由称为冲突条件的经验变数决定;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通过改变统治地位的占有者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变迁的种类、速度和深度取决于称为 "结构变迁条件" 的干预变数。结构变迁的突发性取决于团体冲突的激烈程度,结构变迁的激进性取决于团体冲突的紧张程度。
32、布劳(Peter M. Blau,1918-2002)代表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1964),《不平等与异质性》(1977),《相互关联的社会属性》(1984)思想背景: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的交换思想;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思想;德国理论传统和自由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社会关联属性的观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思想和研究方法。主要学术思想:交换关系指行动者与那些他们期待给能自己的行动以适当回报的他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交换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自愿性活动,影响它的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是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相互吸引是刺激人们进行交换的前提条件,社会交换是通过竞争得以实现的,竞争的结果是推动群体内部结构的分化,资源和交换地位的分化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权力的分化,形成群体的权力结构,在其中群体成员的交换地位表现为权力地位 (其根源在于交换各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平衡)。资源地位较低的一方以服从资源地位较高的一方作为条件进行交换,共同定义的权力情景形成合法权威,减少了竞争和摩擦,促进了群体整合;但当群体内部报酬 (或期待的) 结构发生变化时,由此导致一些成员的被剥夺意识,权威蜕变为强制性权力,导致群体对立和冲突,只有进行内部调整或推翻现有的权力结构。微观层次的个人交换通过共享价值观和制度化上升为社会宏观交换,从而解释了社会结构层次上的现象。一切科学的理论在形式上必须是演绎的,在内容上必须具有证伪性;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必须明确界定其解释物和被解释物;构造理论必须通晓有关的经验知识,提出一个崭新的理论观点,必须进行概念的精确化,形成一个由命题组成的演绎体系,并把这个理论同实证研究结果相对照;社会结构分析的参数有三类:异质性、不平等性、交互性。
33、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00-1987)代表作:《电影和品行》(1933),《劳资关系中的社会理论》(1947),《作为符号互动的社会》(1962),《工业化与传统秩序》(1964),《符号互动论:观点和方法》(1969)思想背景:苏格兰伦理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的思想;詹姆斯关于习惯和自我的研究;鲍德温的自我发展三阶段理论;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库利的 "镜中我" 思想,托马斯情景分析的思想,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主要学术思想:人类社会是由具有 "自我" 的个人组成的,人类创造并使用符号来表示周围的世界;互动是个人、他人和群体之间意义理解和角色扮演的持续过程;符号互动创造、维持和改变着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社会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客体是人的经验的产物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物质客体、社会客体和抽象客体),通过符号互动客体才被创造和赋予意义,主体所体验的客观世界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所想象的世界;人类对于某一客体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根据他们对客体所赋予的意义;人们赋予事物的意义产生于人们的互动之中;在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 指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采取的行动) 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通过各自的解释、定义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持续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解释过程中随时加以修正的,行动者总是根据特定的 "处境" 来选择、审查、修正事物的意义。就人类社会而言,经验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经历的和所做的一切,社会学方法应当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直接、密切的考察 (有探索和检查两种方式),必须着重于研究人们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理论应能解释互动过程,并指出一般行动和互动发生的条件;只有持续的参与观察—检验方法才适合于互动分析;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要求尽力把经验世界作为注意的中心,从经验和被研究者的立场来了解社会现象。
34、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1959),《公共场合中的行为》(1960),《相遇》(1961),《策略性互动》(1969)思想背景: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詹姆斯关于人的思想;鲍德温、杜威的社会思想;库利的 "镜中我" 理论,托马斯、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主要学术思想:根据人际互动的场合可以将互动分为两种:"社会机构" 内经常和持续性的互动、没有界限和临时性的互动。社会机构好比一个舞台,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按一定的常规程序 (即剧本) 扮演自己的多种角色,表演中人们都试图控制自己留给他人的印象,通过言语、姿态等表现来使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 (称为 "印象管理");为了实现印象管理,人们运用一些手段 (外部设施和个人的装扮) 装点门面。人们表演的区域有前台 (人们进行表演的地方) 和后台 (为前台表演做准备不让观众看到的地方) 之分;根据表演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 "误导的表演" 和 "神秘的表演"。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与互动就是一场游戏,是某个 "定义" 取得胜利或成功地被人们接受的过程,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个剧组进行合作。相遇式互动的最突出特点是人们之间持续性的相互注意,虽然区别于社会机构里的表演,但印象管理的原则在此仍旧是适用的;"角色距离" 是个人与其假定的角色之间存在的差距,它说明个人在某种角色上能否积极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与该角色相适应的程度。
35、舒茨(Alfred Schutz,1899-1959)代表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社会世界的结构》(1973/1989)思想背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和先验范畴论,特别是米塞斯和维塞尔的思想;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特别是其构成分析 (主体间性);美国的实用主义主要是詹姆斯的思想;考夫曼和古尔维奇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实证主义社会学把 "社会世界" 与 "自然世界" 等同和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 "社会事实",而是社会事实的意义。社会学应置身于生活世界中,对互为主体性的人们的微观互动过程进行研究,认识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性质;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对传统社会学进行彻底理论反思基础上建立起与研究人的行为相适应方法。任何实践世界都不同于生活世界,它以无目的性的生活世界为前提,又参与构成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结构性就体现在不同视角的人能够相互理解,行动的意义通过与特定社会场景的制度化联系,使每个人的社会行动成为可理解的。"库存知识" 是普通人建立生活世界社会现实的基础,人总是将不断变化的情景标准化变成例行的情况,然后使用类型化的库存知识来处理。日常生活中存在三个关联系统:主题关联、动机关联和解释关联;知识社会学的关键应该是探索“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
36、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2011)代表作:《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关于实践行为的标准结构》(1970)思想背景: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秩序的观点;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比如胡塞尔、舒茨、梅洛—庞蒂、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如奥斯汀和塞尔的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特别是戈夫曼的理论。主要学术思想: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行动包含四种要素:权宜性、场景组织、索引性、反身性和可说明性;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复杂的实践整体,行动处于局部场景中,而场景又是行动者行动构成的产物;说明是使行动成为可理解的条件,同时本身也属于构成行动者、组织并维持行动的条件;说明与场景也存在这样的辨证关系。社会现实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活动,是相互交往的参与者对现实的社会构造;社会事实不是社会学分析的结果,而是交往的积极创造过程自身,此过程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学家在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特征时,应注意把握 "索引式表达",还要利用 "破坏性实验" 的方法来验证所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 "隐含的行动准则"。实践推理不论是常人的还是社会学家的在思维方式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要通过彻底的反思检验社会学家的理论建构。社会学研究应根据社会现象及其局部场景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研究方法,使方法与研究对象统一起来,要以尽可能接近社会现象本身为原则。
37、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代表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1973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年)思想背景: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思想,滕尼斯的公社与社会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思想,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英格尔斯、列维、艾森斯塔德、本迪克斯等的现代化思想和依附理论。主要学术思想:从分析不同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分析社会发展变化时设法说明整个社会所环绕的动能原理和组织结构,趋中性而非因果关系)入手,可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它们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为中轴原理的概念顺序。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部门主要是第一产业,职业主要是农民、矿工和非技术工人,使用技术上主要是利用原料的技术,在社会意图上主要是与自然界竞争,方法论上主要是利用常识和经验;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苏联和日本,经济部门以第二产业为主,主要职业是半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使用技术上主要是能源技术,社会意图上主要是与加工过的自然界竞争,方法论上主要是利用经验和实验;后工业社会主要在美国,经济部门以第三、四、五产业为主,职业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使用技术上主要是信息技术,社会意图上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方法论上主要是利用诸如决策论、系统论等抽象理论。社会中轴原理: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考虑土地和资源的局限性;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考虑国家和私人对投资决策的控制;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的集中和具体化为轴心。未来的后工业社会将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核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主要源泉,将控制技术发展并对其进行鉴定,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38、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代表作:《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愿》(1976),《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1984),《性史第三卷:自身的关怀》(1984)思想背景:康德与批判哲学传统特别是对知识条件的批判性考察和 "当前" 历史处境的思考;尼采关于历史批判、权力性质、宗教道德、生命过程等问题的思想;形式主义传统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德里达的思想;法国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库瓦雷、巴什拉、康吉翰等人的思想;超现实主义者如巴塔耶、布朗肖和法国新文学。主要学术思想:真理体制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社会存在一些基本条件来保证区分那些现象可以看作知识的对象,那些知识可以看作真理,将这些知识构成真理的过程需要完成那些实践过程。知识的考古学是从话语实践的层次出发把握构成真理体制的各种知识条件,在方法上要尽可能回避各种人类学的普遍项而要考察这些普遍项的历史构成过程。话语事件的考察一方面要注意述说具有的经验特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 (话语形态分析)。权力是多形态的而非同质的,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和知识的积累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真理体制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同时也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权力在不同局部之间流动,具有多变的形态,遍布真个社会机体,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纪律权力在实现微观控制的过程中运用一些特有的策略:封闭、分割、功能场所的规则;控制生命的权力存在两个基本形式:控制身体 (人体的解剖政治);控制身体的权力技术 (人口的生命政治);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治理术、主权和纪律之间的三角关系,人的生命是它的对象。批判理论中的批判应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批判者只是指出危险而不代替行动者的决定,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在知识分子的具体领域行进的反抗;批判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谱系学的考察破除各种制度、实践和知识的自明性和想当然性。应该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非一个历史时期,弄清对于我们伦理主体的构成而言哪些因素是必须的;要勇于改变自身以及处境(自我技术)。
39、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代表作:《教育、社会和文化再生产》(1973),《实践理论大纲》(1977),《区隔》(1979),《实践的逻辑》(1990),《语言和符号权力》(1991)思想背景:法国社会学传统特别是涂尔干学派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结构主义与关系论尤其是索绪尔、卡西尔、巴什拉、潘诺夫斯基的思想;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哲学教育理论主要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应采用新的认识论秩序:与常识决裂—科学对象的构建—事实检验,以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代替实体论思维;要到结构与惯习的交织作用中来理解实践,反思性地考察科学的对象及从事科学的研究者自身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实践的重要特征是紧迫性、经济必须条件的约束、模糊性以及总体性;把握这些特征必须从对规则的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是在主体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环境中逐渐培养形成的,这就是惯习,它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塑造、组织着实践并生产着历史,而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一种人们后天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系统;场域是由附带一定权力 (资本) 的各种位置之间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的网络,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和运作、争夺和投入的空间,是人为的社会建构,是经历漫长的自主化过程才逐渐形成的。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两个过程。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同时体现了一种生成性;表现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兑换是分析社会世界再生产时不可忽视的问题。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动;社会的支配秩序依靠的是一种“沉默的”暴力;现代社会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学术场域中存在着文化资本的等级制度;权力场域是受不同形式的权力结构性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决定的一个力量场域,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游戏空间。
40、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1962),《知识和人类旨趣》(1968),《沟通行动理论》(1981),《事实与价值》(1992),《包容他者》(1996),《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思想背景: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帕森斯的早期社会学理论,韦伯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涂尔干、米德、马克思、帕森斯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日常语言学派的理论,皮亚杰和柯尔柏格的结构发展心理学。主要学术思想: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程序去检验或证实社会科学理论,社会科学中应当以 "共识真理论" 代替 "相应真理论"。人类语言中潜藏着 "达至了解" 的目的,进而蕴涵着一个 "理性沟通情景",其中有三个有效性宣称规范着人的语言行为:真理宣称、正当宣称、真诚宣称;一个社会行为是否属于沟通行为主要取决于,行为者所用的方法是否存在内外的制约并协调资源的运用来满足各自的欲望。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并非一种必然的现象,还存在其他发展的可能性;科技理性的独断把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纯粹工具式的关系,批判理论应当以人的相互沟通为依据分析人类行为的架构。生活世界结构上的区分指文化、社会、人格三种结构不再笼统地受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控制,而是各自沿着理性交往的角度独立起来,以及伴随而来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发展一方面是个人理性认识能力和自主性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社会系统的日益复杂和扩张,这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困境——系统控制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非商品化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性化过程对个人讲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社会来讲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传统规范秩序的有效性与事实性因为理性化过程而分离了,随着它们有效性的消失其事实性也无法执行,只有沟通行为可以重新把它们融合起来,但通过沟通行为达至共识的可能性并不稳定,因为内部潜藏着异议危机,因此需要对沟通行为进行限制和制度化,还应当求助于法律;同时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协调和疏解社会整合危机必须结合它的认受性和事实性。人类所有理性领域的基础知识分为三种类型: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的技术认知兴趣;历史—解释学研究包含的实践认识兴趣;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研究包含的解放认知兴趣,这三种兴趣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
41、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代表作:《文明的进程》(1939/1969),《社会学是什么》(1970),《知识社会学的新关照》(1971),《迈向社会过程的新理论》(1977),《科学诸建制》(1982),《论自然》(1986),《投入与超脱》(1987)思想背景:康德哲学传统主要是时空、因果、道德准则等核心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李凯尔特的历史主义思想;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韦伯及其后继者关于文化和文明的相关思想,雅斯贝尔斯的社会理论。主要学术思想:集体经验经过关键词语逐渐固化、积淀,成为下代人的集体记忆和一种实在;"文明化" 是指个体不断趋向以自己和他人的社会生活为取向,趋向稳定和均衡的自我调空以使每一个参与者乃至整个人群可增进生活愉悦和质量,也使每一个甘心自我调节的人更能获得愉悦和幸福。原本社会需要的行为成为自发的行为,原本形塑而成的自我控制成为自由意志的行为,这种文明化的过程使人们日益用理性化的方式思考解释问题;攻击性情感与行为的逐渐驯化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在日趋富于竞争的社会里,上层鼓励下层模仿自身行为方式,同时又不断提高自身行为的精致程度,在整个社会构成一个循环递进的过程,这就是 (某塑型在社会单元间传递的) 标准化或塑型化过程。理性化的过程是某一个社会领域中不同的功能群体彼此之间的张力或同一单位不同个人之间竞争的结果,不仅是所谓 "渗下效应",也是导致多极控制和愈益平等的 "功能民主化"。文明的进程中最基本普遍的结构过程是劳动分工的日益增长,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上升,人际依赖链条加长,对个人压力加强,从而需要更多的控制和预见;结果国家对暴力更有效的垄断形成更均衡的社会控制机制,个人人格中形成更均衡的自我控制机制。文明化进程中对暴力手段的控制逐渐体现出理性化和长期预见化的趋势。一个群体能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上加以维持,完全是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人类知识的科学化是与理性化、先见化、心理化、自我控制的增强等长期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需要长期的超脱的视角和实践途径。社会学研究应采用过程性的视角,其基本任务就是最终使处于各种群体之中的人更好的理解自身和他人。
42、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27-1995)代表作:《数理社会学入门》(1964),《教育机会的平等》(1966),《社会学理论的基础》(1990),《当代社会学理论》(合著,1993)思想背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统计调查与结构功能理论结合的取向;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政治和社会哲学对规范和法规的分析;新发展的博弈理论。主要学术思想:以个人行动为基础阐述系统行动的理论应该有三部分组成: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微观到宏观的转变;社会行动可以分为两类:交换行动,法人行动和规范性行动;行动者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并都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社会最优状态是在一定系统中最佳的社会均衡状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直接的交换关系和人际关系,与系统有关的权威和信任关系以及二者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复杂的权威结构由三种角色构成:支配者 (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和微观互动形成社会的权威系统和系统行动;信任结构有三种角色构成:委托人、中间人、受托人,中间人又分为顾问、保证人、承办人三类。社会规范是在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宏观建构,伴随着各种赏罚措施又影响着人们的行动,是与利益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它的产生是由于行动的结果对他人有影响,是通过社会共识而形成,可以分为共同性规范、分离性规范、惯例性规范三种。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依赖关系的无形资本和公共物品,难以通过市场交换提供。任何行动系统都包括四个概念:个人利益、控制分布、资源价值和行动者的实力、事件的结果;理想社会系统的关键是通过共识达到交换的均衡以降低交易费用。法人是通过自然人将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机构而形成,并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法律上可以代替自然人,其三种生存方式是:互惠生存、独立生活、总体生存;大规模法人系统中产生了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等问题,解决法人组织方式弊端的出路在于重建责任系统。
43、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的起源》(1974),《历史资本主义》(1999),《知识的不确定性》(2006,中文版)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新左派思潮;现代化理论尤其是依附理论;历史主义理论和全球化思想。主要学术思想:应当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考量;社会科学唯一合法和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是内部具有单一、完整、广泛、自足的社会分工的历史体系。在今天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知识结构的危机:各种学科都被一种信念笼罩着:仿佛知识是确定的;其实知识真正并永远是不确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封建主义的 "蹂躏" 中兴起有三个条件是必须的:剥削和殖民化导致的地理扩展,对世界经济各地区 (比如中心、边缘) 的劳动控制不同方法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强国的发展。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体系一旦建立,将围绕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等价交换" 和 "资本积累" 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历史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进步而是退步,产业工人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世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即生活在农村或在农村与城市贫民区之间流动的劳动力,他们的状况比他们的祖先更糟。政治民主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多党制,而在于工人是否有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己的力量才能反映出自己的意见,单纯的认为通过两党制的党派斗争使选民的意见得到体现是不现实和幼稚的,因为选民的意向不只取决于哪个党派更优秀,而是有更复杂的因素干扰民众的选择。
44、艾森施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代表作:《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现代化:社会的分析和分层》(1966),《政治社会学》(1970),《传统·变迁·现代性》(1970),《革命与社会转变: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思想背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等社会学理论流派主要是各种冲突学说,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学术思想:一定背景条件下,社会必然产生冲突与失序,社会通过发展出更为特殊的结构回应这些冲突,由此产生社会分化,社会系统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一些子系统,社会系统的不同功能部分同时也是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的社会群体,它们在履行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追求着自身的利益,为控制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而争斗;社会结构不仅是功能关系结构,也是利益关系结构,社会的结构功能分化过程也是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分化过程,社会的结构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社会冲突与失序内在根植于人类的先天本性中,人类基因符码的开放性要求必须通过符号形式和技术性组织来强制加以结构化,这就产生了一种对变迁和失序的开放性,进而产生有关人类目标与活动的自由性与可变性等方面的焦虑,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精英活动是制度化的一个相对自主方面,精英的活动与眼光以及精英之间的冲突对结构分化的形式与方向有直接的影响。
45、贝克(Ullrich Beck,1944-2015)代表作:《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思想背景:关于现代化的社会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结构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关于人的学说,知识社会学和后现代理论。主要学术思想:风险社会是一个反身性的现代化社会,它朝向一种 "新的现代性",但并非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只是它突破了古典工业社会的设计;工业社会的 "反身性现代化" 可以从两个角度给予说明:一是财富和风险生产所体现出来的反身性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特征是伴随现代化过程而出现的;风险概念是 "作为一种处理由现代化自身诱发而引起的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倾向导致个人生活、性别身份、婚姻家庭在个体化浪潮中被重新定义,同时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不仅没有使社会不平等消失,反而使之更加强化了;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对不平等进行了重新定义。多元性、个体主义和怀疑主义已被载入社会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和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自由的和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差异的有等级的确定性;旨在形成 "共担风险性" 全球道德的政治试验将形成有力的世界主义运动。不管是强调环境还是个体化之中的生活模式、科学和政治,现代化都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46、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年-)代表作:《冲突社会学》(1975),《社会学三大传统》(1985),《互动仪式链》(1986),《理论社会学》(1988),《四个社会学传统》(1994)思想背景: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符号互动论思想尤其是戈夫曼和布鲁默的观点;涂尔干关于社会实体的观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冲突的论述;现象学社会学和民俗方法学理论,马克思、塞克斯、谢格罗夫等的观点。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应该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社会现象以及相互转变,微观是基础,宏观过程是由微观过程构成的;微观过程中的互动仪式是人们活动的基本结构,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点。社会学的概念应建立具体微观层次上,它所解释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微观情景性的;这种还原方法可以在任何分析层次上提出经验性更强的理论,增加宏观理论的说服力,且微观分析都有一定的宏观关联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和对手可能得到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观地位和占有稀缺资源的数量,财富、权力、声望及其他产品的不平等分配必然引起冲突;人们生活在自我建构的主观世界中,一些人有力量去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主观经历,同时也会遇到反抗,从而发生人际间的冲突;不同性别和年龄的群体之间由于资源控制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冲突。组织和分层是日常生活中互动的基础,仪式 (人们各种行为姿势相对定型化的结果) 是互动的主要形式并产生相应的结果;人们以 "文化资本" 或他们所具有的资源在彼此相遇中展开互动,互动中带有某种动机或 "情感能量"(这与其占有的文化资本与权力、地位等有关),个体对互动场景 (人数、不同意见、礼节等) 给予关注。人们不同水平的际遇形成不同的互动仪式,它们经由时间延伸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形成 "互动仪式" (其延续依赖于彼此间情感能量和报酬的加强);整个社会可以看作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宏观和长期的社会结构就是通过这种 "互动仪式链" 建立起来的。
47、亚历山大(Alexonder Jeffrey,1947-)代表作:《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3),《新功能主义》(1985),《微观-宏观之环》(1987),《行动及其环境:迈向新的综合》(1988),《结构和意义》(1989) ,《文化和社会》(1990)思想背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现象学,戏剧论,本土方法学等社会学理论流派,特别是米德、戈夫曼、舒茨、加芬克尔的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学术思想:科学思维运行在经验环境和形而上学环境之间的 "科学连续体" 上;科学的发展既受经验环境的制约,亦受形而上学环境的制约;理论逻辑和经验逻辑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通过二者的双向运动推进对社会的认识。既要坚持环境对行动的强制性效果,又要强调行动的偶然性和创造性和行动对环境的变革作用;人格、文化、社会系统作为环境的行动因素进入行动过程,为行动者提供目标、手段、规则等,是行动展开的前提又是行动的产物,行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和构造;行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体随时都对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解释和谋划,制定行动策略做出行动选择。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多样的,功能性的分化和相对自主的亚系统以及精英的出现会促使现代社会冲突数量增加,同时缩小冲突的范围。社会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包含一个意识形态的部分,它自动地来源于该理论视角的预设、模式和经验命题。社会学研究者应当采取一种 "多维度" 的理论视角,融合不同理论传统和理论流派,重新解决社会学的前提预设问题,即关于秩序和行动问题,以达到新的综合。
48、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代表作:《信任与权力》(1979),《社会分化》(1982),《社会系统》(1984),《自我参照文集》(1990),《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1990), 《风险社会学》(1991),《现代性思考》(1992)思想背景:笛卡儿、康德、胡塞尔的哲学思想,英国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思想,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和帕森斯的系统等。主要学术思想:社会系统是各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它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和发展的能力,其形成的基本机制是借助符号规则进行的沟通,自我指涉 (系统按自身的规律对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偶发事件加以记录和加工处理的性质) 是它的重要特征;社会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从三个方面 (时间维度、物质维度、符号维度) 去降低由环境导致的复杂性,以维持系统与环境关系的有序运作。社会系统可以分为互动系统、组织系统、社会整体系统三种,它们之间既有分化又有整合的关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复杂化,社会系统之间不断分化,主要表现为:功能领域的分化、进化规则的分化和对不同沟通媒介依赖性的分化。社会进化是互动系统、组织系统、社会整体系统之间和各自内部的不断分化,还包括整体社会系统不断分化出各类功能领域 (伴随着不同沟通媒介应用的增加);进化过程伴随着个人、角色、节目和价值之间的明显分化,包含三种不同的形式:部门化、分层和功能分化;进化性分化提高了系统的复杂性和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系统的进化机制形成社会系统结构的变异,选择促进系统适应性的变异以及稳定这些适应性的结构;进化的状态表现为三个方面:变异、选择和稳定化。法律和知识一样,都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法律是社会的一种基本结构,最基本的功能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行为预期。
4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代表作:《社会学方法新规》(1976),《社会的构成》(1984),《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思想背景:现代哲学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和温奇等人的著作;受现象学影响的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主要是舒茨和加芬克尔的思想;戈夫曼的日常接触分析;自我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和埃里克森、莱恩的思想;解释学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时间地理学和城市区位地理学;福柯的控制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时空系统分析思想主要学术思想:社会学的宗旨不能限于建立 "法则",它是解释性的,作用在于促进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放;同时又区别于广义的社会理论,它只关注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既是对社会变及其结果的理解与解释,又是变迁的后果和原因。结构化理论关注作为总体类属特征的人类能力和根本处境,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产生和塑造了社会事件和过程的进程与后果;社会分析可以分为制度分析和策略行动分析,需要把传统的二元论改造成二重性,即结构作为自身反复不断组织起来的行为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不断的卷入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行动包含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的过程,该三个过程复合在一起构成人的有意图行动 (反思性的行动 "流")。社会互动包括三个要素:意义、规范和权力;日常互动的进行 (意义的交流)、权力关系的构成都体现出资源和规则的利用。社会系统是由通过时空再生产出来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结构指循环反复地卷入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要素,包括各种规则和资源;系统是被规则和资源“结构”起来的模式化社会关系形式,具有机构但本身不是结构;结构化是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而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时空分离及其不断的重新组合产生社会生活的时空 "分区";与时空分离相关的社会系统逐渐分离的过程;知识对个人与群体的行动产生持续影响导致社会关系不断反思性的调整。象征符号与专家系统两种脱离机制从本质上带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是时空延伸的前提,是现代制度比传统制度给日常生活提供更大范围保障的条件。现代性的高度发展面临四种主要的威胁:极权主义力量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常规战争、生态环境的破坏或灾难、经济增长力量的崩溃。批判性理论应保持社会学的想象力。
50、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1940-)代表作:《社会学:一门多元范式的科学》(1975),《古典社会学理论》(1992),《社会的麦当劳化》(1993),《表达美国:全球信用卡社会之评论》(1995),《后现代社会理论》(1997),《彻底变革消费方式》(1999),《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2003),《虚无的全球》(2004)思想背景:孔德以降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综合化理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思潮;文化社会学和全球化思想。主要学术思想:以麦当劳为典型范例的理性化浪潮不仅在美国境内得到迅猛发展,且已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越来越注重效率、可预知性、可计算性、用非人类的技术代替人类技术、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尽管先进的理性化已为人们带来了不尽的便利,但它同时也产生了一连串的负面效应;“理性的非理性”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更加严重;但不能将此现象简单视为一种向不理性化社会形式的回归,因为这样的回归不仅不可能且是不受欢迎的;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欠理性化的社会,而是对理性化过程的更好控制,特别是对其非理性后果的修正。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仍旧处于极少数学者视野的狭小圈子里,社会的发展还没有真正达到后现代的水平。
原文来源:哲学与艺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GudhGN6sx2bc4qyhU4XcA
编辑:刘佳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2-20 22:43
【案例】
康德真的去今远矣吗
——《很烂》一文很烂之随想
近日,某大学教授发表了康德伦理学《很烂》一文,各小号纷纷转发,该文刊发的源刊学报更公开征稿以求“学术争鸣”,大有搭建擂台之势。鉴于生于18世纪的康德先生早已作古,显然无法公开对此进行回应,这一擂台赛便成了编导方的单方叫阵。不过,康德先生的文本俱在,德英中文诸版本仍广泛流行于世,要想寻求问题的解答一点不难。若人们能耐心读完康德先生诸论著,相信疑惑自解。然而,也有围观吃瓜却不甚明了的热心读者,恐怕未能免于对此问题之好奇心,作为关注康德思想世界之人,笔者不妨再多说两句。
首先,要批评康德或任何问世思想体系之得失,就应先进入要批评对象的作品本身,看看作者到底说了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理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伦理学《很烂》”一文立足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我们就来谈谈《原理》这本书。这本书的中译本较为广泛流行的有李秋零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此外,杨云飞亦翻译过此书,翻译名同李先生。邓晓芒之《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则对此书进行了释义讲解,热心读者亦可翻阅参考。这是比较通行的该书中译本。此外即《很烂》一文(以下简称韩文)作者所引用的苗力田先生翻译版本,苗译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因笔者手上没有苗译版,以下以李秋零译《奠基》为据,简称李译。
康德在该书前言就对其要讨论的对象做了清晰说明,一如他其他论著所作的那样。康德明言,“关于自由法则的科学则叫伦理学”(387),也就是说,康德认为伦理学讨论的是自由法则的问题,又把它称为道德学说。而“一切哲学,就其依据的是经验的根据而言,人们都可以把它们称为经验性的哲学,而把仅仅从先天原则出发阐明其学说的哲学称为纯粹的哲学。后者如果是纯然形式的,就叫做逻辑学;但如果它被限制在一定的知性对象上,就叫做形而上学”(388)。在形而上学中,就分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每一部分形而上学,也就都包含了经验的部分和理性的部分。那么,道德形而上学里面,也包含了两部分,经验的部分称为实用人类学,读者可参看康德所撰《实用人类学》比较即知。理性的部分则称为道德学。以下康德又说:“既然我的意图在这里真正说来是指向道德的世俗智慧,所以我把上述问题仅仅限制在:难道人们不认为极有必要有朝一日去建立完全清除了一切只能是经验性的、属于人类学的东西的一门纯粹的道德哲学吗?”(389)那么,纯粹的道德哲学,一门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为了“探究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中的实践原理的源泉”(390),而《奠基》这本书的任务就是“找出并且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392)。到此我们比较一下韩文,韩文开头即错解了此段。韩文称“‘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的对象性应用,即‘当它’(指逻辑学)限定在知性的一定对象上的时候,被称为形而上学”。这个“它”韩文备注“指逻辑学”,其实指的是纯粹哲学而非逻辑学。由此明显的错解,韩文就认为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的对象性应用,应该是纯形式的,从而得出既然道德形而上学的对象是道德,就不可能是只涉及形式的理性知识,则必然涉及经验等等。这一段错解得莫名其妙,康德明明说的是纯粹哲学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两类,而《奠基》一书指向道德的世俗智慧,又怎么可能不应于实践?这样明显的曲解原文的做法贯穿于韩文通篇,使得其所臆想的康德的各处“错误”就显得非常乏力无理。那么,他揪住康德后面那段“清除了经验性的……”一语如何理解。康德其实说得很清楚,道德形而上学也分为经验的和理性的部分。而《奠基》这本书的主要问题是探讨理性的部分,即拷问关于自由的学说中那个不依赖于经验去建立的道德法则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说道德法则不应用于实践生活。道德法则的原理不出自经验,就不能指导经验的逻辑显然不能成立。至于说《奠基》一书为什么从普通道德认识开始,康德说得很明白。因为道德形而上学并不像它的名字看起来那么吓人,道德形而上学虽然基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但因为在道德领域,“人类理性甚至在最普通的知性那里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重大的正确性和详尽性”(392),那么,道德形而上学就并不是抛弃广大普通民众认知能力的傲慢学问,“只要人们愿意分析地采取从普遍知识到规定其最高原则的途径,再综合地采取从对这一原则的检验及其源泉返回到它在其中得到应用的普遍知识的途径”(392)。故此,这样一种先分析再综合的写作方法决定了这本书的写作章节如此安排。但并不意味着经验是道德性的最高原则。这一层逻辑若不弄清,则容易产生韩文式的疑问,以至于认为《奠基》逻辑不自洽。康德在前言中已将道德形而上学的任务和沃尔夫式的普遍实践世俗智慧区分开来,就是为了告诫人们,一种可能的纯粹意志的理念和原则才是人类理性实践的原理,这是基于对人类理性实践原理源泉的拷问,这一原则不来自于经验归纳,但不意味着它孤悬在天,隔绝人间,否则,又如何可以成为实践原理呢?所以,韩文的指责属于自身逻辑混乱所致,并不应归责于康德未说清楚。
由于韩文认为,“最高标准和道德规律就应该是在既有道德和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寻找或提炼”,又把最高原则排斥经验等同于排斥了一切客观事实加以歪曲,故而得出道德形而上学毫无用处的结论。从经验归纳中寻找道德标准,道德法则的根源,这自然不是从考察人类实践理性的原理出发,这种方式恰恰是康德在前言里指出的已有的一般伦理学的做法。抱怨一个立足于寻找人类纯粹意志的先天原则不从经验出发,不从既有的相对历史条件下已成的“道德”出发,纯属头上安头,脚上安脚的无理取闹。即使自己可以对道德下一定义另造体系,也不能说明康德自身的问题意识及其针对自身问题的解决思路不能成立。再延伸出抱怨康德缺少对道德的界定等一系列指责皆属由此而来的妄谈。当康德在寻找能够作为人类实践理性原理的根本法则时,他是非常谨慎的思考人何以为人,康德的问题意识出发点在于人是什么,若没有这一设问,不肯定人有自由意志,则无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源性工作。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已明言:“在哲学里,极其精确而明晰的定义应该不在我们研讨的起头,而在其结尾”,(A731/B759),如果要下了定义以后才能使用一个概念,那我们根本不可能采用一个概念。另外,康德也并非没有对他要拷问的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作出回答,只不过没有按照韩文设想的方式和内容去定义罢了。
康德给出的回答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421)。这一原则的根据是“有理性的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429),也就是说,康德首先规定了人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人是有人格的,有理性的存在者即人的人格,这不是一般动物或生物学的、经验的规定,而彰显出人禽之别。就人的实践行为指向发自每个人作为目的自身来说,它同时又具有普遍性,那么,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命令式:“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的人性中,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429)。这样一来,每个人才能成为通过自己的准则普遍立法之人,若自身的行为不能成为一个普遍法则,其行为之道德性深浅自现。换言之,道德法则的标准并不是某个人单独制定的,而是每一个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自发运用理性拷问自己,是不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去行事,就能够立刻判断出来的,“我根本不需要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就能知道,为了使我的意欲在道德上是善的,我应当怎么办”(403)。在康德看来,一般民众只要在行事前如此发问,就自然能够判断应该怎么做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若要在此之前强行定义道德,或者从经验中归纳出其定义,显然都不是把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之人看待,也不是从理性存在者的人格性去了解人之为人的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道德形而上学了。
举个例子,我们拿韩文的标题来看。《很烂》一文引起众人惊异的原因,其实首先是因为这一标题引发的心理不适。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很烂”一词造成的感官刺目并不能说仅仅是因为汉语常规书写用语上的罕见。它透露出的信息是对原书作者的一种不尊重。当然,韩先生以及部分读者可能会为此辩解,宣称并无主观上对康德不尊重的动机,这样的辩解当然完全可以言之成理。但我们可以把自己拉出来,从事件本身反过来看,如果把“很烂”一词普遍化的用在一切评论他人的文章、事件、行为上,将这一措辞普遍化,成为人人都能遵守的普遍行动准则,结果会是怎样?我相信如果对此发起一个网络投票,大家应该都无异议。“很烂”一词若能用在一切品评人物事件乃至作品中,乃至他人用于自己身上,不知大家将作何观感。正如本文的标题所示,“《很烂》很烂”云云,大家又有何观感?若这一原则无法成为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普遍行事法则,那么,无论使用者如何主观声明,其使用这一词的不恰当都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很烂》一文最后引出的全文重点,即优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乃是韩先生自己的《人本伦理学》,然后抛出自设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至善即幸福等观点做结。甚至宣称,以往的伦理思想史上都无人能作出满意回答云云。那么,在一篇以“很烂”批评康德诸多在作者看来甚至是明显错误的文章结尾,对自己的体系大加褒扬乃至言语间透露问鼎伦理学思想史巅峰之势,无论如何是无法避免由此带来的对其书的客观宣传效果的。正如韩自己所言,纵使他自己的回答不能成立,也不影响他对康德伦理学作出“很烂”的评价。那么,读者不禁要问,既然如此,又何必在这篇评价文章的结尾处画蛇添足的加上一段高屋建瓴又难脱自我宣传之嫌的点睛之笔呢?若“很烂”的评价真如作者所说那般发自肺腑不得不用此二字,别的词语都无法表达这一态度,而自己的《人本伦理学》这一段写不写都不影响这一评价,那加上这一段,以便于吸引读者好奇心去发现醉翁之意,就非常明显了。
当然,尽管作者可以继续辩解笔者的以上这番推测无法证成其客观必然合理,我们依然可以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找到评判办法。比如在评判一个行为合乎义务还是出于自私意图时康德所举例的那样:卖主不对没有经验的买主要价过高,而且生意兴隆时也不要价过高,而且对每个人包括小孩都固定一个价格,这当然是合乎义务的,但这种行为不足以使人们相信商人是出自义务和诚实原理这样做,还是他的利益要求他这样做,更不能由此断定商人对买主是不是还有仁爱方面的偏好(397-398)。因为商人这一行事的效果已客观决定了他的行为的获利性,而这一获利是私己的利益。就像一个企业商人慈善募捐,而使自己的企业无形中获得了某种社会关注及良好声誉,由此带来无限商机一样。既然在一个声称完全出自求真的行事动机中,最终呈露彰显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作品高于其要批评的其他学术作品,那么,即使主观上作者宣称无此自我宣传动机,也不能免于他使用“很烂”一词所带给他的“意想不到”的学术关注效应。那么,读者无法判断其用“很烂”一词的主观动机,兼以加上己书做结尾的这种写法,是不是如作者宣称那般纯粹出自义务,就很合情合理了。
由此可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既不高深莫测,也没有故弄玄虚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恰恰是肯定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每个人,有其自由意志,可以在行事中自己判断,这一判断的法则已如笔者在上文做所的试验那般呈现出来,更毋庸赘言。
《很烂》一文之所以很烂,就在于它不仅在炮制标题上难以免于对前人皇皇论著不尊重之无礼措辞的嫌疑,更在于其内容之不能成立。作者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充满错解,又以己意歪曲支离,作者既不想深入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内部分析,又忙于摆出自己架空康德后的理论体系,如何能使“很烂”令人信服?若理上无从成立,其言辞之故弄玄虚就更不可原谅了。幸好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原书篇幅不长,其《实践理性批判》等论著俱在,就算不阅读英文德文版,中文版的康德相关翻译论著也够读者们入其堂奥。正如一位康德研究学者所说:“康德的道德哲学不是经验的行为学,他的工作不是研究行为规范,而是探究人作为道德者如何因着其禀赋的智思物之因果性(即自由之因果性)创造一个自然的合目的性与自由的合目的性结合为一的道德世界。”[1]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一个从学理立场合理发问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何以可能?康德所建立的人的自由共同体王国,为着人是目的这一光辉高大的规定,有限的存在者如何真正做到有理性的实践行事,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拷问的。康德并非没有看到人的偏好、欲望诸因素在人们实践行为中的影响,但出于对人的人格性的设定,康德站在有理性存在的致高角度看待人之为人。当然,在康德看来,如何理解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了。毕竟“我们虽然不理解道德命令式的实践的无条件必然性,但我们毕竟理解其不可理解性”(463)。我们无法认知作为物自身的人是如何以有理性的存在者之姿出现的,但力求在原则中达到对人类理性的界限的哲学所要求的一切,也仅止于此。当我们扪心自问每一行事原则是否具有无条件必然性时,我们就在实践着一个有理性存在的自由意志主体应该做的事,这使我们即使不理解它为什么具有必然性,但仍然能够理解其存在。这也再次附带证明了为什么“很烂”一语不应用于任何平等真诚、出自求真的发问修辞的原因。
(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容牵涉甚广,读者若有兴趣,可参考以下学者的论著了解一二,此处仅列举少数几篇以飨读者,并不意味着康德研究中汗牛充栋的其他前辈论著不值一提,特此说明。当然,通过对比学界对康德哲学诸问题的研究,吾人应庆幸今日之中国学者的康德研究不至野马空行,康德亦未远于今人矣。)
1、 邓安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构成》
2、 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立论方式》、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句读等
3、 李秋零:《“人是目的”——一个有待澄清的康德命题》
4、 卢雪昆:《康德的形而上学:物自身与智思物》《康德的自由学说》
5、 刘作:《常识道德:哲学分析的起点和终点》
……
来源:敏敏布鲁鲁 游于弋
编辑:马皖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12-21 21:18
【案例】
道德伦理:人脸识别“热”中的冷思考
科技日报11月27日报道,人脸识别系统已经给我们的城市带来诸多方便。然而,在许多国家,对人脸识别的抵抗声也在不断高涨。研究人员、公民自由倡导者和法律学者都受到人脸识别技术兴起的困扰。他们正在跟踪其使用,揭露其危害并开展运动以寻求保障甚至是彻底禁止技术的使用。然而,技术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更多人认为该技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背后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近期,《自然》杂志的一系列报道对人脸识别系统背后的道德伦理学进行了探讨。一些科学家正在分析人脸识别技术固有的不准确和偏见,对其背后存在的歧视发出警告,并呼吁加强监管、提高技术透明度。
《自然》杂志对480位从事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人们对人脸识别研究的伦理学普遍存在担忧,但也存在分歧。
01
有些未经同意获取数据
为了使人脸识别算法正常工作,必须对大型图像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理想情况下,必须在不同的光照条件和不同的角度多次捕获这些图像。过去,科学家普遍招募志愿者,只为收集各种角度的照片;但现在,大多数人未经许可即被收集人脸图像。
在《自然》杂志的480位受访者中,当被问及对应用面部识别方法从外表识别或预测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或种族)的研究有何看法时,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此类研究只能在获得面部识别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在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代表讨论后进行。
大多数人认为,使用人脸识别软件的研究应事先获得伦理审查机构(例如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他们认为,对于在学校、工作场所或由私人公司监视公共场所时使用人脸识别进行实时监视感到最不舒服,但是他们通常会支持警察在刑事调查中使用人脸识别系统。
从法律上讲,目前尚不清楚欧洲的科学家是否可以未经人们的同意而收集个人人脸的照片以进行生物识别研究。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没有为研究人员提供明显的法律依据。在美国,一些州表示,商业公司未经其同意使用个人的生物识别数据是非法的。
受访者强烈认为,应该有其他法规来规范公共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超过40%的人则希望禁止实时大规模监视。
02
存在性别和种族偏见现象
人脸识别系统通常是专有的并且保密,但是专家说,大多数系统涉及一个多阶段过程,该过程通过深度学习对大量数据进行大规模神经网络训练。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称,人脸识别的准确率有了显著提高,深度神经网络在识别图像方面效果明显。但NIST同时也证实,相对于有色人种或女性,大多数人脸识别对于白人男性面孔的准确性更高。特别是,在NIST的数据库中被归类为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的面孔被误认的可能性是那些被归类为白人的面孔的10—100倍。与男性相比,女性误报的可能性更高。
领导NIST图像小组的电气工程师克雷格·沃森认为,这种不准确很可能反映了每家公司培训数据库构成的不平衡,一些公司可能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03
有待严格立法和监管
致力于人脸识别或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指出,人脸识别有很多用途,比如寻找走失的儿童,追踪罪犯,更方便地使用智能手机和自动取款机,通过识别机器人的身份和情绪来帮助机器人与人类互动,在一些医学研究中,还可以帮助诊断或远程跟踪同意的参与者。
人脸识别技术有好处,但这些好处需要根据风险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得到适当和细致的监管。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以及谷歌、亚马逊、IBM和微软等公司都呼吁在人脸识别系统方面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研究面部监控的计算机科学家、法学教授伍德罗·哈特佐格说视人脸识别技术为“史上最危险的发明”,说如果美国立法者允许公司使用人脸识别,他们应该编写规则,从健身房到餐厅都应当禁止“面部指纹”的收集和储存,并禁止将人脸识别技术与自动化决策(如预测性警务、广告定位和就业)结合使用。
04
尚须谨慎研究和思考
密歇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家阿尼尔·贾恩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大量正当而合法的人脸和生物识别应用。”但一些科学家表示,研究人员也必须认识到,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人脸进行远程识别或分类的技术从根本上是危险的,应该努力抵制其被用来控制人们的做法。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首要会议之一,神经信息处理系统会议是今年首次要求进行这种道德考量,即提交有关人脸识别论文的科学家必须添加一份声明,说明他们的工作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和潜在的负面后果。
此外,《自然机器智能》杂志也在试图要求一些机器学习论文的作者在文章中加入一项声明,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伦理问题。
纽约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社会学家凯伦·利维认为,研究人脸识别的学者意识到道德伦理问题,“感觉像是科学界真正的觉醒”。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7 19:38
【案例】
转 张崑: 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和意志(la volonté)是两个概念,在拉丁语和法语中都有明确区分,但在英语中,却是free will 和will 的分别,所以英文读者还能不能分清就不得而知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最早是中世纪神学家明谷的圣伯纳德做出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就是选择“是”与“否”的自由决断,而意志(volonté)总是意志某物,此物是被理性确认和分辨出来的物,所以意志总是与理性相伴,它是“理性的运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意志总是按照理性认为好的东西去选择,意志也常常违背理性,但只要是意志,就总是自由的。举例来说,在局限条件下,人可能被迫做出选择。比如为了生存违心地在论文中自我审查,此时,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说的是“好,我同意”自我审查,这是做出一个自由决断;但是,意志(volonté)说的是“不,我不同意”自我审查,因为理性告诉我这是不好的。明谷的圣伯纳德认为,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失去我的意志(volonté),即使我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不按意志(volonté)去选择。所以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也可以解释为:对自由的意志(volonté)做出的自由决断(注意有两次自由)。这些概念其后不断演化,五六百年后成为重大争议的核心论题,但这个最初的分辨,始终是理解后来一切变化的前提。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11 19:19
【案例】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自律”与“他律”
庞永红 滕文艳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康德强调道德自律的约束性与引导性,认为德以积极的自由规范人,以绝对的价值引导人,能够引人走正路。从他律角度思考,马克思关注法律之规范性与惩戒性,强调法确定自由限度约束人,以正当的惩罚制裁人,束人行正道。道德自律以积极之力,法律他律以刚性之力,在各自效用空间内,予社会成员行为以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性、急剧性、高风险性特征,加之道德自律的应然性仅凭自身难以实然化决定,从自律走向他律,以法律的刚性之力弥补道德自律之不足,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惟其如此才能经纬导人行。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道德自律;法律他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伤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此类事件直接关乎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安全,于此特殊时空场域中,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更离不开有效的规范与引导。于此,回顾康德与马克思关于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的理解与阐析,对我们认知自律与他律的本质与作用,审思两者在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行为时实际功用之“强”与“弱”,进而合理调度,补弱增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自律:引人走正路
自律是康德在驳斥宗教屈从观念基础上,基于对自治(self-governance)观念审思而生成的新概念。由此便彻底剔除了“善”“恶”等由上帝决定的僵死教条,将道德价值之根据从经验的外在对象复归先验的主体意志。康德于人的行动领域搭建起一个处于道德律之下的世界,强调经由自律的道德人格力量实现“善”“恶”间的抉择,为自身指路。在康德看来,“所有存在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目的本身,因为人凭借其自由的自律,成为那本身神圣的道德主体”[2]。自律,即作为神圣道德主体的人,始终以“人是目的”为根据,使道德本身之积极的内在自我立法与约束之力完全迸发,进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可见,康德的自律概念内在蕴含了双重意蕴,即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自律,以及作为自由的自律,由此具备了双重指向:
(一)德以积极的自由规范人
“道德所表达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即自由的自律。”[3]在康德看来,自由概念为说明自律之关键所在。他赋予自由两种形态,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以一种独立性呈现,即“因果性足以摆脱外来规定它的原因,而发挥作用”[4],意味着拥有意志的人不被自然因果左右,他们能够独立于经验映射、感性偏好而行动;“独立性是消极层次上的自由,而作为纯粹的、实践的理性的自我立法,却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5]。在康德那里,自律更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具备单凭其自身就能够选择道德目的、给定行动的能力,能够经由与纯然实践理性之结合完成自我立法。正是这种积极的自由,使得道德最高原则的自律具备了原初的规范属性,即在“自立法”中明确“应当”,在“自守法”中实现“能够”,德由己出,且自觉遵守所树之德,规范自身、抑恶迁善。
首先,内在的自我立法确立“应当”。康德始终强调,人由自身决定,“人应当把握自己”[6]。在他看来,“纯粹、且本身实践的理性的自己立法”[7]绝非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立法,更非每个人自行其是为自身的立法,而是理性人为自己所立的普遍的法,“意志所遵循之准则,必须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8]。每当个人计划施展一项行动时,必须叩问自身是否愿意以及可能,使此准则成为一个普遍化的道德准则,并且“只按照自身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之准则去行动”[9]。康德认为,人们作此抉择时,正予自身以规范与约束,同时与所有人共享这一自由价值,正是对自决、自为的纯粹理性存在者——人之主体性、能动性的权威彰显,将道德的基础由外在对象转移到主体自身。于此意义上,康德将人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自觉的自我守法确证“能够”。康德强调,人应自觉遵守所树之德,“人之所以服从,由于人自身是立法者”[10]。人的立法者身份决定,由其自身确立“应当”,才会考量“能够”,所服从的是自身理性决定且普遍的道德法则,违反则是对自己的违背、冲突与诋毁。“自律构成遵守道德法则的全部责任的唯一原理。”[11]在康德看来,自律作为积极的自由,将人与无能动性、完全受自然规律限制的动物区分开来。动物不用为其行动负责,而人不同。人以自律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崇高的道德法则存在于人心中,出于道德又合于道德的行动是人之自由的体现,人便意识到人对自身行为负有责任,“只有出于责任(由尊重法则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的行为,才具备道德价值”[12],不再受偏好、欲望干扰而恣意妄为,实现对自由生命存在的肯定与负责,焕发出自为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德以绝对的价值引导人
康德指出:“自律构成全部道德法则的唯一原理。”[13]这便在源头上奠定了道德的绝对引导性前提,即“除了道德准则规定的价值之外,无任何东西具有一种价值(道德价值)”[14]。由此“每位理性存在物的意志,必然作为条件受制于它”[15]。康德认为:“人理知世界存在的身份,决定自律能力,实为人格中人性亦是具有最高尊严与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理应遵循定言命令(道德准则)。”[16]即理性存在者能够无视感性偏好、感官刺激,抛弃一切偶然目的,经由纯粹意志以及实践理知能力,设定以理性原则决定、以理性自身为目的、适合于一切理性存在目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客观目的。自律这种蕴藏在人性中的绝对价值,使人真正成为超越经验世界及其必然招致的因果规律的能够赋予设定目的、规定价值的主体。由此,确证了人是目的,体现出人的崇高,具备了人的尊严。
首先,德以绝对价值表征“人是目的”,引导“何以为”。在康德看来,自律是对“人是目的”的肯定,当人完全将自身作为目的对待时,便可以提供一种绝对的价值,即目的自身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每个理性存在者,都作为目的本身而实存……人的一切,无论是针对自身亦或别人的行为中,必须始终被视为目的。”[17]在康德看来,要将每个人当为目的,就必须要求人之行动准则为所有人普遍选择。“当以如此一系列道德准则为依据的行为,成为所有要保存、增进的准则之时,才与每个人作为目的自身的价值相融。”[18]由此,康德便以“人是目的”表达了质料价值的最终根由,予道德以最高的规范性,德引导“何以为”:即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将所有目的系统当作其本身正视与对待。每个人视自身为目的,将引起一个自然序列,于其中所有人一并享有自在价值,敬重道德法则就是敬重人自身,从而人自觉按照道德法则行动。
其次,德以绝对价值完满人之德性,引领尊严配享。康德认为:“理性存在的人于世界上之所以享有尊严,原因在于自律。”[19]德性绝非与生俱来,它是理知世界主体在为己立法、进而克服盲目、战胜偏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力量,是自律于不同程度上的实现。在康德看来,尊严“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且无可代替”[20]。德性乃配享尊严之根据,只有在自律的引领下,合理利用理性、遵循道德法则要求,践行正确行动,才能获得高尚的德性,进而配享尊严,背离自律是对配享尊严之可能的剔除。“自律性就是任何人、任何理性本性的尊严的根据。”[21]自觉约束、引导自身的过程,正是塑造、完满德性的过程,完满的德性存在是自律实现之确证。经由自律配享最高尊严与价值,这便树立了一个楷模,肯定人有不断完善自身、迈向完满的可能,即在道德准则的引导下,人通过不懈努力,获致德性、配享尊严、接近崇高。
(三)积极之力的规范与形塑
习近平强调,要“学会自省、学会自律”[27]。位于意大利普拉托市的华人社区,创下了5万华人无一感染病例之纪录,可谓此次全球疫情中的自律典范。疫情爆发初期,该华人社区意识到疫情严重性后,便自觉进入封锁状态,这较意大利首次报告确诊病例早了三个星期。自发佩戴口罩、自觉居家隔离、保持社交疏远、接受远程健康监测等,都是当地华人主动采取的防疫措施。“这些都是我们自发做的,若不如此,中国人、意大利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当地华人卢卡·周说。事实证明,他们的高度严于律己,有效地降低了疫情风险,更是对国人素质及形象尊严的证明与维护。
其一,“道德自律”以“责任”框架规范人。此责任包括“于己”“为他”两方面,首先以“于己负责”之框架,自律使行为主体思量“想怎么做”前,将“应该怎么做”纳入考虑。在康德那里,人为自我立法且自觉守法。既然是为己划定的行为模式,任何越轨、偏差则意味着人立于自身反面而陷入自相矛盾与自我取消之境。出于对自我失责的怖惧,人便会严守行为界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德自律效用不辩自明。诸如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普通民众以不畏人知畏己知的约束之力,选择主动“宅”于家中,人员流动量明显减少,降低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有效缓解了防控压力,这正是自律力量在人民群众中的彰显,起到了一种正向、积极的预防作用。
同时,“哪里存在社会生活,哪里必定有道德”[23]。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决定,个体绝非孤立独存之微单元,于社会生活中决不能为所欲为。“自律是一切有理性者,相互之间的道德价值之基础”[24],它使人们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人在施以行为之前,便会权衡自身行为普遍化后将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由此在“为他”负责动机下施以理性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每位公民都是风险链上的一环,无人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彼此尽责尊重他人生命与健康权,才能维护整体安全与秩序。以此次疫情中辗转30小时回国的英国留学生为例,回国途中,谢同学自觉周密防护,口罩、护目镜配备周全,到达后严格服从检疫安排,主动接受集中隔离。其所言之“不给国家添乱”“对自己、他人负责”,正是道德自律的力量。自律引导下,她坚定驱除任何有悖“为己”以及“为他”目标实现的杂念,校正自身行为,有效保护了自身安全,且未将感染风险转移到其他社会成员身上。
其二,“道德自律”以“尊严”框架塑造人。在康德看来,敬重道德法则进而服从之,是人之崇高性的彰显。出于对享配尊严的渴求,人便会心生敬畏,“人身上重建向善之原初禀赋……存在于对道德法则之敬重中的动机,永远不会丧失”[25]。敬畏感使行为主体主动约束自身,不让自己受任何情感、偏好统治,以天地明查的敬重与怖畏之心行正当之事,进而形成完满德性,配享崇高尊严。这正是人向内对自身的一种积极塑造。以尊严为框架,使得自律超越勉强,是更积极的内驱之力,因为配享尊严往往与行为主体的人生导向、生活目标具有一致性,如此“道德自律便不再是勉强为善,而是一种从容向善的状态”[26]。在尊严导向下,行为主体能够有效抵御外在因素干扰,于自省中意识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任何不当行为,将使无辜的人陷入风险境地,便会严于律己,调控自身行为。此次疫情中,白衣战士毅然逆行、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高龄院士奋战疫区,他们在积极自律之力下,自觉将身躯化作全国人民的铠甲,实现价值主体最高层次的尊严。
其次,法律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维护人民普遍自由。马克思认为,法律绝非“单个个人的恣意横行”[35],而要保障所有人的普遍的自由。任何特权自由,都将使法律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沦为非法的工具。马克思据斥一切形式以特权自由为取向的法律。“哪里的法律变成真正的法律……便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36]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律以人民普遍的自由为目标,以普遍的规范为尺度,约束也是对所有人的行为施以平等、无差的约束。如此之法才是对人之存在固有本性的认可,释放的是一种心悦诚服的普遍性约束力量。
二、他律:束人行正道
马克思肯定康德自律概念对道德之宗教基础的消解作用。“良心(这玩意是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28]他同样强调,良心通过“与理智间的紧紧相连”[29]能够形成合一的坚定意志,可抵抗外力左右。与康德有异,马克思对道德良心的肯定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他认为道德自律绝不可能超越社会存在,它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决定于全部社会关系之总和,其中最具决定作用的乃是经济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30]离开社会关系,便无法解释善恶荣辱,作出正确的行为价值判断。关于对人的行动规范的思考,马克思未止步于道德自律,他认为构成人的行动的准则,也应通过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形成普遍效力,这是一种更为稳固、威慑的他律力量,对一切恶行的规制更为强硬。
(一)法确定自由限度约束人
“法律是肯定、明确的规范,此规范中,自由之存在具有普遍不取决于个别人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1]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具有双重内蕴——“普遍的规范”与“人民自由的圣经”。以明确的规范、法律确定自由限度,规制人们的行为于合理界限内,同时法律并不是为了压抑自由,而是防止任性。真正的自由是受客观、具有普遍性的法的限制的自由,在法律中才能实现。
首先,法律作为“普遍的规范”,划定人的行为限度。“凡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32]马克思认为,法律在前提上必须有客观依据,否则就是诸如“罗伯斯比时期,国家于万不得已时制定的……或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于腐败不堪境遇下制定的”特权、强权意志下的恐怖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依当事人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疑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33]在马克思看来,法律约束力的释放,建立在所有人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基础上,此客观标准即“非法犯罪行为”。以行为本身之利害为标准,才能约束行为本身。“我的行为,是我与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它关乎人之生存与现实权利,因而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现行法的支配。”[34]法律着力的是行为本身的合规则性,它为“利”与“害”划定界限,为“利”与“害”间的平衡提供公正原则,让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进而规范人的行为于一定的限度与边界之内。
道德根植于人们心中,是人为自身所下之命令。“人将道德法则,视作任性的自身充分动机的素质”[22],进行着自我决定与内在约束。在康德看来,于行动始初,行为主体依自身内在道德标准,在各种可能性预设、筛选中,完成“善”“恶”抉择,进而施展现实行动。它生发于己,经由主体内在之责任、尊严与敬重感,实现对自身的规范与塑造,因而更为可靠、持久。
(二)法以正当的惩罚制裁人
“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37]在马克思看来,法律建构在社会基础上,又指向保障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当一个社会出现不当行为,甚至是恩格斯所谓的“蔑视社会秩序之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犯罪”[38]时,何以保障整个社会的秩序?马克思引入了“惩罚”,从反面揭示法律的本质:“惩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39]
人是社会存在物,其行动牵涉人与他者间的一定利益、需要,所以行为必须有限度,行为本身必须接受法律规范,当人之行为越红线、破底线、踩危险线、甚至以犯罪形态呈现时,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受到正当的法律惩罚。正如马克思所言:“惩罚是罪犯行为本身的必然结果……他受惩罚的界限是其行为界限。”[40]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任何任性行为均将受到严厉制裁,甚至是消灭肉体,因而产生警醒,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力量,达致威慑、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惩罚必须是正当的,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正如马克思对普鲁士法律的反讽:“法律惩罚人,并不是因为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人没有做坏事,其实我受惩罚的原因,竟是我的行为并不违法。”[41]在他看来,普鲁士的法律显然是追究倾向的,惩罚沦为了特权的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便彻底“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42]。马克思认为,惩罚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施以危害性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对他人与社会造成了破坏,才能惩戒于他。无论这个他是谁,法律所惩罚的永远是错误的行为本身,绝不是无辜者,逆向错行则是对社会的违背。
(三)刚性之力的约束与矫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关乎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特殊场域中自律出现约束不足时,人们行为的任意疏漏都极可能随事件发酵而走向失控,予社会稳定秩序以冲击。由此,刚性之力——法律他律的介入更具实效。依靠法律的强制性与威慑力,划定自由限度(人们行为的底线),予人之行为以禁止性规定;加之处罚性规定双管齐下,超越法律之底线的行为主体将受以行刑衔接、过罚相当的严厉制裁。如此能够使人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同时又能对人们行为的任性发起制裁。
首先,法律他律以明确的边界对行为施以禁止性规定。“法律始终是……限制否定性自由的工具。”[43]自由绝非无限制的为所欲为,身处法治社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施展均不能越界、离轨。边界何在?与模糊边界的道德自律相比,法律为行为所划定的界限更为明晰,可为、不可为间界限分明。守望法律边界,便不再发生行为冲突。法律以明确、固定边界,约束行为主体于受法律所允许的最低限度与最广范围中行动,一旦触底、越界,就正式步入法律所设定的程序过程,将依据法律条款对此行为逐一甄别与裁决。当前我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能够予人们的行为以禁止性规定。可见,法律以强制的边界与原则性的规定,将人们从盲目的随机行为中拯救出来,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认定与划分,不给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留有余地,进而束人行正道。
其次,法律他律以严明的惩戒,对失范施以惩罚性矫治。我国《宪法》第53条明文规定了公民守法义务,不服从法律的行为将会导致消极后果,诸如对违法者实施强制惩罚。惩罚作为一种行为反馈负波,对人之行为起到警醒与打击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行为主体的越轨动机。违法要件一旦构成,罚款、行政拘留等惩戒性后果随即而至,正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存在(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44]特别是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极具侵害性、构成严重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必须施以最有效的惩罚性矫治,才能扶正祛邪,使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人付出应有代价,同时又对那些难以自律的不稳定分子予以警示与教训,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及时悬崖勒马。“经由法律惩罚之威胁,确保人们会依据法律要求,禁止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45]必罚、严惩和及时罚,法律以显见的惩治性后果特征在人们的行为选项中注入威慑性制衡。
三、自律向他律的走向:经纬导人行
为规范行为,人类发明了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两种利器。前者侧重内向发力、纠偏引正、提升德性,后者重于外在规制、硬性约束、威慑惩罚,其目的均为“除恶”“扬善”。恪守道德自律的行为主体,能够在自省中意识到自身不当行为可能招致的社会危害性,进而从源头上规范约束自身。自律之重要性显见,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人情、权力、利益等其他因素的诱惑下,原本稳固的自律也可能出现裂缝。当自律被层层攻破时,人们的不当行为便接连抬头。“当道德自律无法维持,要诉求于法律形式,使相关道德理念、原则融入法律。”[46]因而特殊场域,道德自律的部分功能让渡于法律,以法律的刚性之力弥补道德自律之不足尤为必要。对道德的一般指导性的有效分解,也更利于人们遵守。从道德自律向法律他律的走向,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一)从自律走向他律何以必要
首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共性、急剧性与高风险性特征,留予人们行为以极为有限的容错空间。以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形式呈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涉及公众健康等重大权益问题,始终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在事件波及范围广、扩散势头猛、危害风险高的现实背景下,人们的不当行为极易将自身与他人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致使事件持续发酵。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极具侵害性与不确定性之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刻不容缓。于此特殊时刻,在生命自保性、行为自利性、欲求冲动性的连环冲击下,以“软约束”“效用弱”“成效缓”为特征的道德自律,存在明显的力不从心。
自律不足,他律绳之。如此情境下,法律他律理应走在道德自律前面,且更有优势。以现有法律规范对行为主体直接规制,能够形成严密的规范闭环、管控闭环、惩戒闭环,对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效力更为强硬、精准。法律以直截了当的形式告诫人们:什么行为不允许,越界将受到相应惩罚。而道德则是使人意识到应该施以何种行为,否则将受内心的谴责。道德自律纵然更利于引人向上,形成至高至善的修养德性,然而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少了牺牲小我等高尚道德行为,暂且不会动摇联防联控的稳定根基,然而少了对失信(以隐瞒症疾、造谣传谣等形式出现)等行为的刚性规制,致使风险扩散,将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可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法律他律能够更迅速、有效遏制恶性效应蔓延。“错行必受罚”,又使得人们不敢轻易以身犯险,进而知所畏、知所拒、有所守。
其次,道德自律的应然性仅凭自身难于实然化。1.道德自律的自觉性决定约束效用“散”。所谓自觉,即行动上积极响应自主理性认知。这无疑悬置了一个“圣人”标准,即每个人都能够依靠自觉权衡行为、规范自身。然而,每位社会成员都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预设有失现实性。部分德性完满高尚的人,的确能够得道于己,拳拳服膺,但盲目冲动、逃避责任的个体同样有之,因而分散于自觉主体中的道德自律极为零散、有限,难以形成普遍约束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哪怕只是一个人的不自觉,都可能使大部分人在长期自觉下努力维持的防控成果功亏一篑,诸如一人症疾隐瞒导致一整楼封闭,正是约束效用“散”的体现。
2.道德自律的为我性决定抑制作用“软”。所谓为我,即道德自律是理性存在者为己发出的律令,归根到底仍然是为了自身的强健与完善。“为我”的特征决定,当人的基本生存处于较高风险或难以预估之境时,对安全的渴求、对健康的渴望、对生存的眷恋都将使人们长期形成的“道德自律”开始摇摆不定,甚至瘫软下来。人们为了“保命”,有可能不惜抛弃一切所谓高尚的“尊严”“责任”,进而酿成不良行为后果。
3.道德自律的过程性决定规范功用“慢”。过程性即道德自律,绝非即刻生效的一劳永逸式存在。它作为过程性存在,认知、判断、分析,进而抉择、行动、矫正,构成了一个漫长的闭环。面对紧迫、高危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拼时间、比速度,慌乱之中的人们很难不紧不慢地自我反省、约束一番,更不用说及时唤起自身责任与尊严感、自觉展开正当行为。正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发期,警觉不足的人们防范意识淡薄,过度担忧的人们施以过激行为,当约束失去了时、效、度便会适得其反。
(二)从自律走向他律何以可能
首先,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上具有同源与契合性,使自律走向他律成为可能。法律绝非与道德无涉的形式孤立之物,两者之间“通而不隔”,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律绝非只有形式而无道德”[47]。从渊源上看,法律经历了习惯——习惯法——国家法过程。最初氏族公社的传统习惯中,习惯的基本理念便内蕴着道德伦理的精神、原则和要求,这正是原初法律对道德价值的主动需要与间接反映。据此而论,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法律蕴涵着普遍适用的道德考虑,接受道德之检视,随着法的发展,如此道德精神又得以不断规范化与形式化。同时,道德与法律于价值诉求上具有契合性,它们存在着持平如水、除邪抑恶之共同的目的追求——正义、平等、人权、人道,如此既是法律之基本准则,又属于道德之价值范畴。两者在调整范围上又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一般而言,法律所维护之社会秩序、所保障之社会安全,均必须合乎正义的道德价值。同时法律所要求、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倡导、培育之行为;凡是法律所禁止、制裁的行为也为道德所据斥、谴责。法律与道德间的同源性与契合性构成了道德走向法律的第一前提。
其次,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相互补充、渗透,确证自律走向他律的实效性。道德与法律之目的,均是为了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二者能够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律之力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已然开始动摇,自保自利的利益衡量跃至决定人们行为的关键因素,行为主体恐难以抵挡偏好、物欲的诱惑,始终保持高度的良知与直觉,因而道德自律在很大程度上需借助于法律的支持。特殊场域,诸如诚信此类较为基础性的重要道德要求,却被频繁违背与挑战。隐瞒疫情、瞒报行程、编造散布谣言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依靠个体自觉、自愿下的道德自律已有明显的约束不足。这并不是对道德之价值原则与规范的否定,而是强调在规范的普遍践行全凭自律难于实现的情况下,法律担当着弥补道德自律规范力不足的重任。“道德原则之约束力的增强,是经由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48]由此,基础性道德向法律关联,“国家的立法部门将一定道德理念、道德规范转化、上升为,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49]。具有专门、明确实施的强制和固定化执行程序的法律,以其卓越的权威性、匡正性,能够有效弥补道德自律弱项,补充其自身无法保障的规范要求以及无法实现的严惩机制。法律冷峻外力型塑配合内在温和之力,刚中带柔又柔而不弱,使得道德基础、原则、要求得以普遍确认,在有效遏制、打击不当行为的同时,又能褒奖、激励合理行为。如此扶正压邪,失范之人付出应有的惩戒代价,才能更好地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曹康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17.
[2][3][5]〔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36,37.
[4][17][22][25]ImmanuelKant.Practical Philosoph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94,78,75,91.
[6]〔美〕保罗·改耶尔.康德[M].宫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1.
[7][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30.
[9][10][12][2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39,51,16,55.
[11][13][15]〔德〕康德.康德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01,102,103.
[14]〔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39.
[16]朱会晖.自由的现实性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新理解[J].哲学研究,2011(12).
[18]黄各.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J].道德与文明,2020(2).
[19]〔德〕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M].李明辉,译.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66.
[2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9.
[23]〔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夏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6.
[24]〔德〕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A].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74.
[26]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5.
[2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3.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67.
[29][31][32][33][34][36][40][41][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5,176,120,122,121,177,16,121,17.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9.
[35][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96,292.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3.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8.
[4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85.
[44]孟凡壮.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20(4).
[45]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7.
[46]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上海:三联书店,2001:1.
[4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69.
[4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61.
[49]高璐.对道德立法研究现状的分析[J].人民论坛,2011(17).
On"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in Public HealthEmergencies
PANGYonghong TENG Wenyan
(School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ImmanuelKant emphasized the constraint and guidance of moral self-discipline,Hebelieved that morality can lead people to the right path by regulating themwith positive freedom and guiding them with absolute value.Pondering over theperspective of heteronomy,Marx paid atten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andexemplary of the law,He pointed out that the law establishes the limits offreedom to restrain the behavior of people,punishes them with fair-mindedpunishment,and binds people to behave properly;with positive force and rigidforce,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legal heteronomy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social members in their respective utility space.Determined by thepublicity,urgency and high risk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and the oughtto be of the moral self-discipline cannot be realized by itself alone,so it'snot only necessary but possible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moralself-discipline with the rigidity of the law,only in this way can we guidepeople onto the right path.
Key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y;moral self-discipline;legal heteronomy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6-0070-009
收稿日期:2020-08-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的伦理研究”(16XZX011);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示范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庞永红,女,重庆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冯梦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21 21:04
【案例】
休谟论“道德情感”:社会功利、自爱与关心
1、在一切论题中,效用这个条件是引起我们赞许的根源。在一切有关行为功过的道德判定中,效用总是人们诉诸的根据。总之,效用是我们人类有关的主要道德的基础。共同的利益和效用(社会功利)可靠地提供了有关各方面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2、社会功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也是价值的唯一根据。正义这种德性完全是由于它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化状态有必不可少的用处,才获得其存在的。公平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态和条件,它们的发生和存在是由严格而经常地遵守这些规则给公众带来的功利所决定的。因此,人类的利益是所有法律和规则的唯一目的。
3、有一种所谓的“原则”颇为流行,但它与一切德性或道德情感完全不相容。因为它只能出自最堕落的心境,所以,它反过来,又倾向于更加助长那种堕落。这个所谓的“原则”就是:一切慈善都完全是虚伪的,友谊只是一种欺骗,公益精神是滑稽可笑的,忠诚只是为获得信任和信赖的一种诡计。既然我们归根到底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于是我们就披上这些绚丽的伪装,为的是使他人去掉戒心,使它们更深入地陷入我们的欺骗和诡计之中。(“成王败寇”与“人情练达”的“教导”就属于这种“逻辑”)
4、如果任何人由于感情冷漠,或由于性情狭隘自私,对人类幸福和苦难的景象毫无感触,那么,他对善与恶的景象也一定同样无动于衷。因为在另一方面,人们总是看到对人类利益的热情关注是由对一切道德差别的敏锐感觉相伴随的,这种感受亦即对施害者的强烈不满,对人福祉的热烈欢迎。(砖制与暴民是一体两面的:砖制底下没有任何“权利”,所以民众普遍自私冷漠麻木。相反,在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地方,人们普遍热情且更容易关怀他人)
5、在有些事例中,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是分开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自爱原则来说明一切道德情感的理论。我们必须采纳一种更广泛的爱,并且承认,社会的利益即使就其本身而言,也不是与我们完全无关的。凡是对社会福利有益的一切事情都会直接得到我们的赞许和好感。如果一个人的自爱不论用何种方式指引他去关心他人,使他对社会有益,那么,我对这个人是尊重的。如果他除了自己的满足和享乐,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那么我就憎恨或蔑视他。当人们对善的一切炽情和偏爱都被窒息了,对恶的一切反感或厌恶都被消除了,这就使人们对善和恶的一切区分都无动于衷。(一切“罪恶”的源头就在于“权利”的被剥夺:法家,政做民之所惡)
6、虚荣心主要就是在于:过分地炫耀自己的长处、荣誉和成就;公开地强求得到表扬和赞赏,以致冒犯了他人,过于伤害了他人潜在的虚荣心和功名心。此外,它也确实是内心缺少真正的尊严和崇高性的表现,这种尊严和崇高性是使任何品格都大为增色的。为什么你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人们的喝彩呢?就好像你不配正当地得到喝彩,好像你没有理由期待那喝彩永远伴随着你似的。(虚荣是“爱”的缺乏,是情感未满足的“恶果”,是对“认同”的渴望而不得)
7、迷信和正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浮华的、无用的、累赘的,后者对于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存在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迷信的人缺乏“主体”意识,因而也缺乏“权利”意识,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外界的偶然性和一种神秘莫测“力量”的结果,他们大多是充满“侥幸心理”的“赌徒”,“自利”是他们的最高“准则”)
8、道德赞扬的一个主要根据应当在于任何品质或行为的有用性,显然,在所有这类道德决定中,理性应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官能可以告诉我们那些品质或行为的倾向,指出它们对社会、对具有那些品质和有那些行为的人所产生的有益后果。那么,理性和情感在决定是赞扬或是谴责中能起多大作用?
9、理性既对事实也对关系做出判断。虽然理性在得到充分帮助和提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给我们指出各种品质或行为的倾向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但是理性单独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道德谴责或赞成。为了选择有益的倾向而非有害的倾向,情感在此必须有所表示。因此,道德是被情感决定的。它规定凡是给一个旁观者带来愉快的赞成情感的任何精神活动或品质,就是美德,而恶则相反。赞成或谴责不可能是判断之所为,儿只能是心情的作用;不是思辨的命题或断定,而是能动的感受或情感。
10、事实方面的错误和正当性方面的错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两者中通常一个是犯罪,而另一个则不是的理由。(锅人不能很好地区分这二者:往往想通过证明他人陈述事实方面的错误来“证明”他人“正当性”方面的错误,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伪善,背后起作用的是想“支配”他人的“权力欲”。)当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他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从一些无辜的、无意的情况出发,对自己从事的活动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而当尼禄杀死小阿格丽品娜,他对他们俩之间的一切关系和一切事实情节都事先知道,但是在他残酷的内心中,报复、恐惧或利欲的冲动压到了责任心和仁爱感。对这些情感,他因为承谄纳媚和长期穷凶极恶而变得麻木了。
11、罪恶或不道德行为并不是可以作为理智对象的特定事实或关系,它完全是从不赞成的情感中产生出来的。理性是冷漠而超脱的,因此不是行动的动力,它告诉我们趋乐避苦的方法,以此仅仅对我们由欲望或爱好引起的冲动进行指导;趣味是给人以苦和乐的,苦和乐构成了人的痛苦和幸福,因此趣味就成了行动的动因,而且是欲望和意志的第一个源泉或推动力。
12、人格价值完全取决于是否具有对自己或对他人有用或使之愉快的精神品质。因此,禁欲苦修这种僧侣道德,它与人们所欲求达到的那一切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它们使人的理智变得迟钝,使心灵变得冷酷,使想象变得混沌,使脾性变得乖戾。因此它恰恰是德行的反面,应当把它们列入罪恶之列。
13、历史学家,甚至常识告诉我们,不管完全平等的概念看上去多么合理,实际上它们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于是,财产权的观念在一切文明社会中变成必不可少的,正义由此而变得对社会有用了,而且仅仅由此,正义的价值和道德责任才出现了。
14、共同的利益和效用可靠地提供了有关各方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只有那些心胸更加宽阔的人才会由此发展到热心为他人谋利益,对他人的幸福抱有真实情感。
以上文字参考休谟《论道德原理》一书。
来源:微信公众号 冷冬长夜
编辑:贾梦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23 11:46
【案例】
差别原则的解释与辩护
作者简介:徐向东,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思考,也与他对正义的本质和目的的设想以及他对公共辩护和公共理性的思考具有重要联系,因此在其正义学说中占据了一个极为独特的地位。罗尔斯对差异原则的解释和应用也使得其正义理论显著不同于当代其他主要的正义学说。然而,差别原则在激发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的同时也备受误解。因此有必要澄清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解释。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两个要素(即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实际上都是立足于一个核心主张,即正义应当致力于纠正或缓解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这两个原则加上平等自由原则体现了罗尔斯自己对平等尊重以及公平合理的社会合作的理解,因此我们应该从一种整体论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差别原则 机会的公平平等 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 互惠性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8644\wps5.jpg
在政治哲学中乃至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超越职业哲学家的关注、对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哲学观念。差别原则不仅体现了罗尔斯对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思考,也与他对正义的本质和目的的设想以及他对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和公共理性的思考具有重要联系,因此在其正义学说中占据了一个极为独特的地位。罗尔斯对差异原则的解释和应用也使得其正义理论显著不同于当代其他主要的正义学说,例如罗伯特·诺奇克、罗纳德·德沃金以及杰里·科恩等重要思想家所持有的观点。然而,差别原则在激发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的同时也备受误解。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澄清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解释。具体地说,本文试图表明,在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中,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实际上都是立足于一个核心主张,即正义应当致力于纠正或缓解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这两个原则加上平等自由原则体现了罗尔斯自己对平等尊重以及公平合理的社会合作的理解,因此我们应该从一种整体论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本文提出的解释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科恩针对差别原则对罗尔斯提出的批评,并进一步澄清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提出的“民主解释”。
一、对差别原则的一般表述和辩护
罗尔斯对正义的基本理解体现在他所说的“对正义的一般设想”中,这个设想所说的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其中任何价值或所有这些价值的某种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在罗尔斯看来,不管人们在生活中想要什么,他们对生活计划的理性追求都要求所谓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这些东西被分为两类:社会基本善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我尊重的社会条件,自然基本善包括健康和精力、智力和想象力等。对罗尔斯来说,这两种善对于过一种基本上得体的生活来说都是必要的。罗尔斯在后来的著作中更明确地将基本善与两种道德能力的发展和行使相联系,即一种基本的正义感以及形成、修改和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计划的能力。一般来说,只要一个社会承诺了平等主义观念,它就应当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社会基本善。不过,自然基本善至少在起点上取决于人们的天资,即他们的自然能力和才能。如果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人们在天资上的初始差别,那么社会就需要通过某种实质性的机会平等来缓解人们在这方面的差别。不过,甚至这种机会平等也不足以保证结果平等:即使两个人都被给予了同样的机会,他们在天资方面的差别也会使得他们最终具有不同的生活前景。在真实世界中,不平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义必须设法应对这种不平等。罗尔斯认为这就是差别原则要做的工作:这个原则旨在缓解或反击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罗尔斯由此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具体地表述他对正义的“一般设想”:
首先,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平等的权利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某个最为广泛的组合,这样一个组合必须能与其他人所享有的自由的类似组合相容。
其次,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要如此来加以安排,以至于:第一,它们可以被合理地指望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第二,它们附属于对所有人开放的职位和职责。(TJ 53)
简单地说,第一个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旨在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行使基本自由,只要这样做不侵犯其他人对类似自由的行使。第二个原则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进一步的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对差别原则的最一般的表述,第二个原则就是所谓“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对正义的这种更加具体的设想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那个一般设想:罗尔斯按照他所说的“词序式顺序”(lexical order)来排列这些原则:基本自由权的平等分配具有严格的优先性,机会的公平平等要优先于“其他社会价值的分配要让每个人获益”这一要求。
对正义原则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理解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后面会加以讨论。目前我们可以认为,对罗尔斯来说,强调平等自由原则的绝对地位就相当于强调人们在基本尊严的地位上的平等——人们不仅应当被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应当有平等的自由行使自己的理性能动性,因为这是他们平等地追求自己生活计划的一个前提。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修订版序言中明确指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其优先性是要保证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对于他们适当地发展以及充分地和知情地行使两种道德能力来说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TJ xiii)。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只是旨在进一步说明制度安排如何实现罗尔斯所设想的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的目标,正如他所说,“社会基本结构要用符合平等自由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的方式来安排财富和权威方面的不平等”(TJ 38)。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旨在调节人们在初始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例如,出身富裕并不是一个人应得的,因此人们就不应当因为这个事实而占据有利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但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并没有矫正人们在自然才能或动机方面的差别,差别原则旨在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个缺陷。
对于罗尔斯来说,一个正义理论要以对公平的某种理解为出发点,通过考察人类道德心理的一般特点以及社会的基本条件来选择一套用来设计和制约基本结构的根本原则。正义原则主要是用来管理和调节公共生活领域,因此,除了要满足罗尔斯所说的公共性和稳定性要求外,一套合理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合情合理的(reasonable)人们能够彼此同意、接受和采纳的。在罗尔斯的晚期著作中,“合情合理”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人,然后才被用来描述正义原则。说一个人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就是说,他渴望认同和提议某些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来行动,而这些原则是所有像他那样的人都能接受的。合情合理的政治原则就是所有这些人都能接受的原则。用罗尔斯自己的话说,“合情合理的人们不是被一般而论的善所驱动的,而是本身就渴望这样一个社会世界,在其中他们都能作为自由平等的个体、按照所有人都接受的条款相互合作”(TJ 50)。因此,合情合理的人们不仅将彼此看作自由平等的个体,而且也愿意在这个认识或承诺下按照他们共同接受的正义原则来行动和生活。因此,合情合理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罗尔斯所说的“互惠性(reciprocity)标准”,大体上说即是,当他们“在一个跨代社会合作系统中将彼此看作自由平等的个体”时,“他们准备按照他们认为最合情合理的政治正义观向彼此提供公平的合作条款”。若将互惠性要求应用于差别原则,这个原则就可以被理解为罗尔斯对如下问题提出的一个部分回答:什么样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合情合理地接受的?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构成了他对差别原则的辩护。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主要理由来支持差别原则,其中一个理由出现在他对自然自由体制的批评中。这种体制在制度安排上预设了由第一个正义原则来规定的平等自由以及某种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制度安排要求一个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罗尔斯论证说,机会的形式平等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允许人们的生活前景仍然受到自然资产的累积效应的影响,而自然资产的初始分配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对正义原则的自由主义解释引入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一旦这种机会平等得到充分落实,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运气所产生的影响就可以得到缓解,因为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可以保证具有类似天资和动机的人们有大致同等的机会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然而,即使如此解释的自然自由体制“在排除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方面做得几乎完美,但它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由能力和才能的自然分布来决定。……这个结果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TJ 64)。如果人们的出身影响了其自然能力,如果后者的发展和成熟仍会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阶级态度的影响,那么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在缓解自然不平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差别原则旨在弥补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足,与其他正义原则一道致力于消除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
罗尔斯进一步论证说,差别原则满足了互惠性理想。这是他用来支持该原则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对罗尔斯来说,不仅我们的自然能力和才能以及我们愿意努力工作的程度受到了我们无法支配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些才能和努力转化为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能力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当然,一旦人们获得了公平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发展和提高其自然能力。但是,既然他们在社会合作的初始时刻就承受了自然不平等,他们通过获得和利用公平的机会而发展出来的才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自由市场经济可能给予人们的才能以不同的价值,市场价格未必能够公平地反映人们可以正当地要求的东西。在罗尔斯看来,即使自然自由体制在其背景制度中预设了机会的形式平等和自由市场经济,它对效率原则的应用仍然是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因为它根本上还是按照人们的社会命运或者他们在自然彩票中的运气来决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而这就使得效率原则的单纯应用仍然是不公正的。按照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设想:
这个原则是要通过挑选出一种用来判断基本结构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特殊地位来消除效率原则的不确定性。在满足了平等自由和机会的公平平等之要求的制度框架内,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一个改进最少获利者的期望的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它们才是正义的。这里的直观想法是,社会秩序不是要确立和保证境遇较好的人们的更有吸引力的前景,除非这样做有利于不太幸运的人们。(TJ 65)
差别原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等原则,而是要表明对平等的偏离在什么意义上是道德上可允许的。在《正义论》第13节中,当罗尔斯试图按照民主平等的观念来解释差别原则时,他还没有考虑通过原初状态设施对其正义原则的论证。不过,他已经假设了休谟所说的“正义的环境”并提出了自己对社会或社会合作的理解。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根本上在于三个因素:第一,资源的适度欠缺;第二,人们并不具有普遍同情心;第三,人们有普遍的愿望通过公平的社会合作来理性地发展和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若要将用来制约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选择出来,人们就不可能是道德上无知的,而是,他们必须有按照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来行动和生活的愿望,而且每个人都指望其他人知道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愿望是他们的共同知识,而且最好能够成为他们的共同承诺。罗尔斯旨在表明人们在社会合作方面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公平条款——其正义理论的核心使命在于通过采纳对“人”的一种康德式理解来寻求根本的正义原则。现在,为了对差别原则提出一个辩护,我们需要假设某种平等分配的基准,然后考虑对平等的什么样的偏离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他们不能合情合理地拒斥的。为了便于处理这个问题,罗尔斯做出了三个假设:第一,社会基本善一般来说要平等地分配,对平等分配的任何偏离都需要得到辩护;第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大体上可以被分为两个群体,即更加幸运的群体和不太幸运的群体;第三,社会在如下意义上是紧密结合的(close-knit):改变境遇较好的人们的期望总是会影响境遇较差的人们的期望(参见TJ 71-72)。如果社会资源是恒定不变的,那么,在那两个群体所构成的社会中,任何一方状况的改善都会降低另一方目前的状况。不过,社会无须是这种情形——如果人们的生产能力和动机能够以某种方式得到促进,那么社会资源就可以得到有效提高,与人们的初始状况相比,不太幸运的人们就可以享有更好的生活前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对初始状况的三种可能改变:
第一,要是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变得更差,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与他们目前的状况相比有可能就会变得更好。
第二,要是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变得更差,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与他们目前的状况相比也会变得更差,但是,要是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变得更好,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有可能就会变得更好。
第三,要是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变得更差,而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变得更好,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与他们目前的状况相比就会变得更差。
罗尔斯是通过设想三种假设性的情形来说明如何辩护差别原则的。在他看来,第一种情形是不正义的,因为它要求以牺牲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来改善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不是在说更加幸运的人们值得拥有他们的幸运条件给他们带来的有利地位。他所反对的是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的自然分布。但是,他并不否认人们可以正当地要求公平的制度规则由于他们对才能的协同利用而向他们提供的报酬。可以设想的是,彻底否认人们由于其自然能力和才能而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不仅会使得社会合作失去效率,可能也无助于改善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说“更大的能力是要作为一种社会资产用来服务于共同利益”(TJ 92)。罗尔斯将第二种情形称为“始终正义的”(just throughout),因为它具有如下含义:改变更加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也会使得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发生相应改变,无论这种改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罗尔斯并不认为这种体制是“最好的公正安排”(TJ 68),因为我们可以设想的是,更加幸运的人们可能持有极为过分的期望,因此,即使他们的边际贡献可以略微改善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但让他们的期望得到满足可能就会侵犯其他正义原则,例如会破坏机会的公平平等。第三种情形在罗尔斯看来是“完全正义的”(perfectly just),因为与这种情形相对应的制度安排不仅会让每一个人获益,而且也符合效率原则。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产生了罗尔斯对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如下表述:“社会与经济制度是要如此安排,以至于:第一,它们适合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最大期望利益;第二,它们附属于在机会的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职务和职位。”
二、优先性论点与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辩护了对社会与经济制度的这种安排?或者,在目前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辩护了对差别原则的这种解释?形式上说,完全正义的制度安排也满足了帕累托优化原则的安排,而这意味着,在任何其他的制度安排下,不太幸运的人们的期望都不可能再加以改进。现在的问题当然是,更加幸运的人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呢?诚然,罗尔斯已经限定了他目前对差别原则提出的解释,即只有在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都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应该用一种让社会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获得最大期望利益的方式来安排社会与经济制度。按照罗尔斯对平等自由原则的解释,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参见TJ 82节);罗尔斯后来更明确地认为,基本权利和自由旨在保证人们享有发展和行使两种道德能力的社会条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认为平等自由原则在他对正义的设想中具有某种绝对的优先性。然而,罗尔斯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为什么应当优先于差别原则。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两个原则实际上都旨在缓解或反击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只不过二者具有不同的关注焦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主要关心偶然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而差别原则旨在限制和调节自然能力及其累积效应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旨在保证具有大致同等的能力和类似动机的人们具有大致平等的生活前景。然而,这个原则在实际应用上会碰到一些困难:为了能够运用这个原则,我们就需要一个标准来衡量人们是否具有公平平等的机会。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某些程序性原则来决定某个机会对人们来说是否公平,不过,为了确定人们是否具有实质上平等的机会,我们就需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能力或技能。能力或技能的形成和发展,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受到了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出生在不同家庭的人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天资或才能,甚至女性在怀孕期间的健康状况和心理条件也会对即将出生的孩子产生影响。如果我们需要将人们在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追溯到其父母的状况,那么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就很难切实得到应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就像罗尔斯所建议的那样将正常成年人作为比较起点,那么人们在这个起点上已经继承了自然不平等。当然,罗尔斯认为,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但不可能彻底消除人们在初始时刻的不平等,正如他所说,“至少在家庭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只能不完美地得到实现”(TJ 64)。假若家庭之类的背景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能在根本上予以消除,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至多就只能保证人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取(access to)罗尔斯所设想的社会与经济利益,而不是实际上拥有这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让人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取社会上有利的职位为什么比尽可能改善境遇较差的人们的状况更重要?实际上,在境遇较差的人当中,某些人甚至未能具备机会的公平平等的条件。对罗尔斯来说,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所以应当优先于差异原则,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则旨在实现机会公平,正如他所说:
要求职位对所有人开放的理由不完全是效率方面的理由,甚至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理由。……(职位对所有人开放的原则)所要表达的是如下信念:如果某些职位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那么受到排除的人们就会正确地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尽管他们可以受益于获准持有那些职位的人们所做出的更大努力。他们有理由抱怨,不仅因为他们被排除在职位的某些外在报酬之外,而且因为他们被阻止去体验一种自我实现,即通过熟练而热忱地行使社会职责而获得的自我实现。他们因此就被剥夺了一种主要的人类善。(TJ 73)
在机会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当然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攻击。不过,对于一个因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受到排斥的人来说,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说法。在某些情形中,其处境甚至更糟。一个人或许会因为机会不公而未能进入美术学院深造,而他本来就把成为艺术家视为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他因此有理由抱怨那个不公正的社会。但是,假若一个人并非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他能够持有的合理抱怨似乎并不亚于那个本来有望成为艺术家的人的抱怨。二者所遭受的境遇都是社会不公的表现。那么,罗尔斯何以认为只有在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满足差别原则的要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一下这两个原则的根据以及罗尔斯对它们各自的职能的论述。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共同构成了罗尔斯对正义原则提出的民主解释,而不是他所批评的“自由主义解释”。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仅仅要求所有人至少都有平等的法定权利获取一切有利的社会职位。这种平等并不是实质上公平的,因为它仍然允许自然资产和偶然的环境条件不恰当地影响人们对职位的获取。为了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仅仅要求人们不要按照种族、性别之类的因素来区别对待他人(或者对他人采取歧视态度)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实缓解或抵消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同样具有天资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出生在不同家庭或者生活在不同环境中而做出极为不同的选择、具有很不相同的生活前景。为了让他们具有实质上更加平等的机会,社会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开办各类学校,并在教育措施方面向不太幸运的家庭适当倾斜。对罗尔斯来说,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意味着让具有类似动机和才能的人们在文化和成就方面获得大致平等的前景,不管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意味着对所有具有类似才能且有兴趣追求某个职位的人开放。这个要求可以在程序公平的原则下得到满足。然而,为了保证人们拥有实质上平等的机会,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就要求缓解偶然的环境因素对人们获取他们有兴趣追求的机会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设法让这种影响变得“中立”。罗尔斯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显然是因为他认识到财富不平等在超过了一定限度后就可以造成机会不平等,政治自由同样会丧失其价值(参见TJ 245-246)。为了让人们有实质上平等的机会竞争有利职位,一个正义的社会就要确保人们可以获得教育、训练以及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对于每个人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来说是必要的,而后者对于确保机会的公平平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不难看出,甚至在罗尔斯所设想的良序社会中,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不仅要求投入大量社会资源,而且其本身也具有分配含义。罗尔斯相信极度的财富不平等会严重威胁机会的公平平等。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发生(或者至少降低其发生概率),一个正义的社会就需要“逐渐地、持续地纠正财富分配”(TJ 245),例如通过某种累进税制。当然,罗尔斯承认“财富遗产的不平等就像智力遗传的不平等一样并非本来就是不正义的”,但是,他也强调说,“只有当财富的继承所导致的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幸运的人们并与自由和机会的公平平等相一致时,财富的继承才是可允许的”(TJ 245)。在这里,罗尔斯似乎将差别原则看作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的一种手段——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要求利用差别原则来调整背景制度。倘若如此,至少就这两个原则的实际应用而论,我们就不清楚为什么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必定要优先于差别原则。实际上,满足机会的公平平等的要求需要社会投入大量资源,而假如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必须优先于差别原则,它所要求的资源可能就会抢占或腾空差别原则的落实所需要的资源,从而使得差别原则失去用武之地。这显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因为按照罗尔斯自己对这两个原则的目的或功能的设想,差别原则旨在调整人们在天资方面的初始不平等对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旨在确保人们有实质上平等的机会获取他们愿意追求的社会职位;前者所要反击的是人们在天资方面的运气,后者所要反击的是偶然的环境因素对机会的获取造成的差别影响。但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天资和偶然的环境因素是耦合地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一旦人们已经开始进入社会合作体系,经济利益的分配都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相比,尽管获取自己感兴趣的职位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不仅取决于个人兴趣或偏好,而且并非所有社会职位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罗尔斯自己认为,人们应当按照他们能够正当地指望的资源(包括个人才能)来理性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计划。机会平等原则确实旨在保证具有类似才能和动机的人们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大致同样的生活展望。但是,如果实现机会的公平平等要求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差别原则的满足也需要一定的资源,那么当二者在资源要求方面发生冲突时,一个正义的社会大概需要按照具体情境来思考如何解决冲突,如何评估二者在应用方面的相对权重。既然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都旨在缓解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它们在实际应用上似乎就应当具有同样地位。
实际上,就罗尔斯认为第一个正义原则要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论,抢占资源的可能性在这两个原则的关系中也会发生。平等自由原则要求包括政治自由在内的平等的基本自由,这种权利旨在反映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些权利不只是要在形式上得到保证,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质上得到保证——用罗尔斯自己的话说,第一原则所要保证的是“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后者要求“具有类似才能和动机的公民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影响政府的政策、获得权威位置,不管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如何”。但是,在大多数现实社会中,甚至在法定政治平等得到保护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也有可能会威胁或破坏真正的政治平等并使得后者失去价值。为了切实保障政治平等,就需要适当限制经济不平等,以防止经济优势转变为政治优势。极度贫困不仅会破坏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也有可能让贫困者屈从于金钱方面的诱惑,因此很容易受到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们的支配;这样一来,权力就越加集中在经济上极具影响力的少数人手中,各种形式的政治腐败就更容易发生。罗尔斯自己认为,为了切实落实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就需要在经济上实现某种更加平等的分配,以便让人们首先摆脱受到压迫或支配的状况。政治平等的公平实现也需要社会投入大量资源。例如,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利,公民们就得首先具有基本的理性能动性。实际上,平等自由原则对经济不平等所施加的限制可能就比差别原则所施加的限制还要严厉。如果平等自由原则应当具有绝对优先性,那么,为了充分满足这个原则的要求,差别原则的满足所需要的资源很可能就会受到挤压。然而,就平等自由原则的满足要求适当限制经济不平等而论,在这个原则的实际应用中,差别原则就可以成为调节经济不平等的一种重要方式。
罗尔斯所设想的正义原则旨在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想。他自己认为他的正义观的力量来自差别原则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正是对这两个原则的承诺使得他对正义的设想不同于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参见TJ 220)。我们已经看到,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在保证背景制度的正义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在实现罗尔斯所设想的正义理想方面,这两个原则以及平等自由原则应当发挥协同作用——它们应当用一种整体论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在社会合作中可以正当地持有的期望,而这实际上是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本身所要求的。罗尔斯提出了三个论证来捍卫自由的优先性:第一个论证旨在表明平等的基本自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保障,而后者是自我尊重的基本前提;第二个论证旨在表明良心自由(因此,其他的基本自由)对于保证人格完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第三个论证将基本自由理解为人们自主地选择或决定自己生活计划的前提。总的来说,在罗尔斯这里,基本自由之所以应当占据优先地位,是因为它们是平等尊重的基本条件以及人们自主地追求自己生活计划的前提。然而,在《正义论》原版中,罗尔斯对自由的优先性提出的论述并不是没有受到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并未导致罗尔斯放弃优先性论点,不过,在《正义论》修订版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中,他确实对这个论点做出了限定,承认只有在某些条件得到实现的情况下,自由的优先性才能开始生效。罗尔斯依然认为基本自由属于人们的“高阶利益”——它们是平等尊重和自主性的根本前提;不过,他现在也承认,人们对自由的根本兴趣“并不总是主导性的。这些兴趣的实现可能必然要求某些社会条件以及需要和物质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有时候可以限制基本自由”(TJ 476)。假若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属于罗尔斯所说的“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那么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也可以出于类似考虑而受到限制——对于那些已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占据有利地位的人来说,并非对他们的任何机会的公平实现都要比改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期望利益更加重要。
罗尔斯对优先性原则的限制确认了我刚才提出的整体论立场:在罗尔斯对正义的设想中,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以及差别原则都旨在保证平等尊重的基本条件以及对社会合作中的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它们都旨在面对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些原则的具体落实不仅都需要社会资源,而且也都具有明显的分配含义:自由的行使要满足平等自由的相互相容原则,而这个原则本身就规定了个人能够正当地行使自由的条件;另一方面,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都旨在通过分配手段来保证基本的背景正义。既然这三个原则的落实都涉及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为了设法保证罗尔斯所说的那种“词序优先性”并缓解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方面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种可以设想的方式就是引入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social minimum)的思想。这实际上是罗尔斯在《正义论》原版中已经提出的一个想法。罗尔斯指出:
一个竞争的价格体系并未考虑任何[关于需求的主张],因此就不可能是分配的唯一手段。……适当调节的竞争市场保证职业的自由选择,并导致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对家庭的商品配给。它们将某种重要性赋予与工资和收入相联系的传统准则,而转让部门则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并尊重需求的主张。
在这里,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的思想是与基本需求的概念相联系的,而基本需求被理解为一个得体的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然而,在罗尔斯后来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这个思想。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指出,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要无条件地给予所有社会成员(他甚至将这个要求看作宪政的一个本质要素),以便他们具备发展和行使两种道德能力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回应哈特提出的批评,他现在承认,一个要求公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原则应该在词序上优先于平等自由原则,“至少就基本需求的满足对于公民们理解并能够富有成效地行使那些权利和自由来说是必要的而论”。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罗尔斯将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与公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人而应当享有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联系起来,因此实际上将它与一个政治性的正义概念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公民们不能被彼此当作自由平等的人来对待,那么至少其中一些公民就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采取两种可能的态度:首先,他们可能会变得愤世嫉俗,因此就会采取暴力行为来抗议他们的生活状况;其次,他们可能会变得对政治社会冷漠并退入他们自己的社会世界,而这会产生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他们都不可能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确认正义原则,因此就会变得缺失正义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就应该高于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供给不能仅仅是由“在心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来看待的人性的基本需求”来界定的,而是也必须认真考虑“社会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展开的公平合作体制”这一观念——“不管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在超越了必不可少的人类需求之后可以提供什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与政治社会相适应的互惠性观念”。罗尔斯认为,他现在对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的理解要求的是一种拥有财产的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而不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前者才能避免少数人对经济体制和政治生活的控制,而且也可以避免后者的一个主要缺陷,即某些社会成员因为长期依赖福利供给而不参与公共的政治文化。按照这种理解,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并不只是为了援助那些因为偶然变故或不幸而遭受失败的人们(尽管这也是它必须做的),而是为了让所有公民都能在某种适当程度的社会与经济平等的基础上管理自己事务”。
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从其目的或职能来看并不属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为什么不是运气平等主义者。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确实旨在缓解或反击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但是,与标准的运气平等主义不同,罗尔斯并不是按照“补偿”的概念来设想原生运气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罗尔斯认为,我们不应当把在社会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作为怜悯和同情的对象来看待,而是应当将他们的处境作为一个政治正义问题来关注,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让他们就像其他成员一样成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这是互惠性的一个本质要求。罗尔斯之所以强调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要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公民(不管他们所承受的不利条件是不是他们自己所能负责的),并不只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对待冒险或风险的态度本身就受到了遗传或环境之类的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认为两种道德能力的基本条件原则上必须绝对地得到保证。因此他也否认运气平等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即正义不要求关心选择运气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
三、互惠性要求与民主解释
罗尔斯对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解释构成了他所说的“民主平等”的核心内容,而互惠性概念对于他提出的解释来说则是关键的。罗尔斯认为互惠性概念已经隐含在他对“良序社会”的定义中。一个良序社会是一个旨在发展其成员的善、由一个公共的正义观来规定和管理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彼此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这些原则的要求,他们彼此也知道这一点(参见TJ 4)。因此,一个良序社会要求人们按照他们彼此都能合情合理地接受的合作条款来行动。而且,“当那些条款作为公平合作的最合情合理的条件被提出来时,提出它们的那些人至少必须认为其他人接受它们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他们是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来接受它们,而不是在受到支配或操纵的情况下来接受它们,也不是因为自己处于某种‘低级的’社会或政治地位而被迫接受它们”。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互惠性标准”。因此,在罗尔斯这里,互惠既不同于纯粹的利他主义,也不同于霍布斯式的理性互利(mutual advantage)。互惠性在内涵上更接近于传统意义的“博爱”(fraternity),即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的精神。差别仅仅在于,当传统意义上的友爱“涉及一种在更广泛的社会的成员之间不能被现实地指望的情感纽带”时,罗尔斯所说的“互惠”表达了人们在正义的制度框架下彼此持有的一种理性期望,即如下观念:“若不说为了让境遇较差的其他人获益,就不希望自己占有更大利益。”(TJ 90)罗尔斯自己认为他所设想的正义原则能够与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传统价值相联系:自由对应于自由平等原则,平等对应于第一个原则中的平等观念以及机会的公平平等,博爱对应于差别原则。
不过,按照我们前面对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关系提出的解释,互惠性实际上充当了这两个原则的共同根据——这两个原则都在一种强的意义上表达了将彼此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来看待的要求或理想。罗尔斯对于自然自由体制的批评明确地表明,将人们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并不只是在于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具有形式上平等的机会。假若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差别影响尚未得到缓解或纠正,他们仍然不是被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对罗尔斯来说,社会合作条款在他所要阐明的意义上必须是公平的,而一切自然不平等都会妨碍公平的理想的实现,它们进一步导致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很可能会让某些人受到剥夺、压迫或支配,因此就会对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造成严重威胁。既然自然不平等本来就是由人们不能自愿选择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就可以设想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有可能遭受自然不平等的侵害。只要一个人是合情合理的,他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而在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下,比如说,在资源适度稀缺且人们并不具有普遍同情心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可能由于能力方面的欠缺或者突如其来的坏运气而陷入糟糕的境地且得不到救助。对罗尔斯来说,社会合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弥补自然状态的缺陷。人们的自然才能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要被当作公共资产来利用,用来促进他们在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下能够合情合理地认同的共同目的或利益,并不只是因为一个合理地正义的社会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由于天资的差别和坏运气而遭受的不利条件,而且也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为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提供了充分保障,不用说,它还可以向人们提供自我实现的更有价值、更加丰富的目标。罗尔斯对所谓“精英政制”(meritocracy)的批评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他对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设想以及他对两个正义原则所提出的“民主解释”的要点:
这种形式的社会秩序遵循“前途向才能开放”的原则,把机会平等用作一种在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将人们的精力释放出来的手段。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在生活手段以及组织权威的权利和特权方面,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偏差。比较贫困的阶层的文化枯萎凋零,而进行统治的技术精英的文化则牢固地建立在服务于权力和财富的国家目的的基础上。机会平等只不过意味着在对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个人追求中把不太幸运的人们抛在后面的平等机遇。(TJ 91)
精英政制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正如罗尔斯立即指出的,其危险就在于它无视了平等尊重的要求,并通过它必然含有的那种等级制度造就了进一步的不平等,从而就有可能剥夺不太幸运的人们平等地追求自己生活计划的机会。民主解释要求以某种方式缓解道德上任意的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为此,我们就需要在全盘的利他主义和全盘的利己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出路。换句话说,在罗尔斯对如何选择用来制约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的构想中,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既不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前一种情形会使得正义基本上变得不必要,后一种情形则会使得正义在根本上变得不可能。这条中间出路的核心观念就是互惠性概念。当罗尔斯将互惠性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爱联系起来时,互惠性显然要求一种“厚实的”平等尊重:它不仅要求缓解一切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还要求人们具有实质上平等的机会追求自己理性地认同的生活计划。在罗尔斯所设想的良序社会中,人们必须对这两个要求具有明确的认识和承诺,而且彼此具有这项知识。唯有如此,罗尔斯为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所设想的那个公共辩护要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
为了阐明这一点,不妨设想一下更加幸运的人可能会对差别原则的应用提出的一个异议或抱怨。就差别原则的应用而论,理想的情形无疑是这样的:对某个指定的初始状况的改变不仅会让每个人都获益,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的期望利益。现在,假设一个人在初始状况已经处于某种有利地位,他可能就会问道:“我为什么应该接受这种改变?”这个问题不是根本上不可理解的,因为可以设想的是,在某种其他的制度安排下,他的生活前景可以得到更大提高,而不太幸运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只是略微得到改善。例如,充足主义者显然并不要求用罗尔斯所设想的那种方式来应用差别原则,而只是要求制度安排向所有人都提供某个适当的充足标准或者相应的资源。充足主义仍然允许有可能会导致社会剥夺或社会压迫的不平等,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按照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解释,差别原则旨在动态地调节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所有人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满足平等尊重的厚实要求,例如尽可能消除社会剥夺或社会压迫得以产生的潜在因素或条件。如果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差别原则,那么,对于一个在社会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与一个满足差别原则的制度安排相比,在任何其他的制度安排下,有些人甚至会变得比你目前的处境更糟”;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在社会上本来就占据有利地位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不错,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由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来主导的社会中,而且被给予了基本权利和自由,那么你就能利用自己的才能获得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利益,但是,你的才能的成熟和发展本身就得益于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你应得的,此外,假若你是合情合理的,你就可以想象自己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状况,因为说某个东西是道德上任意的,就是说它不是你自己能够自愿选择或控制的;因此,只要你是合情合理的,你就应该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也会陷入那种状况,这样一来,选择一种满足差别原则的制度安排对你来说并不是不合理的,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你的生活前景会比其他人更好。”对罗尔斯来说,在一个满足差别原则的社会中,有才能的人们的生活前景之所以会比其他人更好,或者与任何其他可能的制度安排相比会更好,是因为,假若他们的才能获得了公平合理的利用,他们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前景;另一方面,假若他们的才能因为坏运气而受到损害或剥夺,他们仍然能够享有一个得体的生活的基本条件以及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否幸运,他们都有权要求一个正义的合作体系及其社会有义务让他们满足的正当期望(参见TJ 88-89)。
因此,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解释似乎满足了他所设想的公共辩护要求,但却是在互惠性标准下满足了这个要求:合情合理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将他人置于受到剥夺或压迫的境地而试图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换言之,对罗尔斯来说,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都旨在实现一个实质上更加公平的社会,二者根本上说都是立足于如下主张:正义要求用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缓解道德上任意的因素对人们的生活前景所产生的影响。这两个原则旨在保证社会合作的制度背景在罗尔斯的意义上是正义的,而为了让人们具有两种道德能力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公平合理的社会合作,罗尔斯引入了最低限度的社会供给的观念。只有在这种供给在所有社会成员那里都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罗尔斯为其正义原则所设想的那种“词序式的优先性”才变得有意义,尽管我们也需要从一种整体论的立场来看待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落实。
来源:微信公众号 健康伦理学
编辑:贾梦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2-4 22:37
【案例】新刊推荐丨《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附:主编导读)
人类文明一直都呈现出非常脆弱的特征,许多文明在不经意之间灰飞烟灭,从历史记忆中消失,而现存于世的文明形态也不免伴随着野蛮与血腥,有时野蛮与血腥还会被强权者包装成不可怀疑的真理,迷惑住号称追求智慧而具有最深邃思想的绝世大哲。让文明死去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一种不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而是人类看不见、摸不着却来要人命的病毒。病毒一旦传播流行开来,医学与科学对它无能为力,就演变为瘟疫,让人类顿生渺小之感,文明摧枯拉朽,人类尊严顿失。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a)虽然不会让文明消亡,但足以令世上几乎所有被人敬仰的“主义”全都暴露出自身的脆弱与尴尬,一切正常的秩序几乎全部停摆,飞机停飞,国门关闭,封城封村,这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如果说特朗普在美国的偶然上台还只是给“全球化”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话,“新冠疫情”却直接让“全球化”了的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自愿不自愿地最终都意识到了文明的脆弱性。几乎可以说,这一次文明危机绝不仅仅只是“西方”的危机,只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必须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危机,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之脆弱性的危机。
......病毒显然只能是一个引擎,一个导火索。
——邓安庆:《为日益分裂而不知所措的世界守护伦理精神》(《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之“主编导读”)
《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12月
目 录
主编导读
01 为日益分裂而不知所措的世界守护伦理精神
邓安庆
原典首发
11 《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评论版“导论”(连载二)
「德」伊尔廷 邓安庆/译
32 精神对于自然“绝对地不感恩”——黑格尔“人类学”中的逻辑规定、肉体性、动物磁力以及疯狂
「德」卢卡斯 张有民/译
52 康德(与黑格尔)的人类学考察
「德」布兰特 徐 超/译 庞 昕/校
73 响应伦理学:在回应与责任之间
「德」瓦登菲斯 刘 畅/译 朱锦良/校
86 差异不同于自由——私密的自由
尚 杰
规范秩序研究
99 法—权的统一——《法哲学原理》题目释义
张尧均
115 语言的暴力与解放:从动物伦理到生命政治(下)
李金恒
129 论马基雅维利德行(virtù)概念的解释疑难与形而上学根据
蒋 益
143 “抽象法”中的人格、财产权与自由——根据《法哲学原理》
汪 希
哲学人类学研究
156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陈家琪
169 性差异:存在论差异
「法」德里达 张 念/译
183 导向儿童自我成长的实践人类学
张 娅
美德伦理研究
194 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与道德偏倚论的证成:王阳明的环境美德伦理学
黄 勇
223 德与Virtue
郑 开
描述伦理学
259 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或为文学辩护
「美」卡罗尔 唐 瑞/译 倪 胜/校
273 友谊与雅斯米娜·雷扎的《艺术》
「美」卡罗尔 唐 瑞/译 倪 胜/校
研究生论坛
281 灵魂的“病”如何产生?——黑格尔论精神在解放之路上的“下沉”
梁毓文
书评
289 从“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谈起
——评黄裕生教授《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尚文华
297 情感与意识的出路
——评《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
杨 铮
为日益分裂而不知所措的世界守护伦理精神
邓安庆/文
“主编导读”作者:邓安庆 教授
人类文明一直都呈现出非常脆弱的特征,许多文明在不经意之间灰飞烟灭,从历史记忆中消失,而现存于世的文明形态也不免伴随着野蛮与血腥,有时野蛮与血腥还会被强权者包装成不可怀疑的真理,迷惑住号称追求智慧而具有最深邃思想的绝世大哲。让文明死去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一种不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而是人类看不见、摸不着却来要人命的病毒。病毒一旦传播流行开来,医学与科学对它无能为力,就演变为瘟疫,让人类顿生渺小之感,文明摧枯拉朽,人类尊严顿失。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a)虽然不会让文明消亡,但足以令世上几乎所有被人敬仰的“主义”全都暴露出自身的脆弱与尴尬,一切正常的秩序几乎全部停摆,飞机停飞,国门关闭,封城封村,这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如果说特朗普在美国的偶然上台还只是给“全球化”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话,“新冠疫情”却直接让“全球化”了的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自愿不自愿地最终都意识到了文明的脆弱性。几乎可以说,这一次文明危机绝不仅仅只是“西方”的危机,只是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必须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危机,是人类的自由与尊严之脆弱性的危机。
如何理解世界的这场惊天之变,无疑成为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因为哲学号称就是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理解和把握了思想自身所处的时代,哲学才能被称之为智慧之学,才能进一步阐发如何建设未来更为美好世界的实践智慧。理解世界无论如何都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没有理解世界就着手改造世界,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而理解世界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大清的皇上们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理解世界在如何变化,了解英国当时在世上的地位,知道世上除了大清“神圣的”礼仪外还有某种叫作科学与技术的东西,也就有可能正视英国使团作为礼物送来的地球仪、天体运行仪、蒸汽机、棉纺机、迫击炮、卡宾枪等代表当时工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它们绝非什么蛮夷的“奇淫技巧”,而是正在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文明动力,就不会对英国使团不愿在皇上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吃惊和生气了。外面的世界早就彻底改变了,而唯有天朝大国视别国为蛮夷小国的傲慢未变,盛世的梦幻未变,后来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厄运也就不会那么难以理解了。
所谓以历史为鉴,实际上就是要明鉴历史上因不理解世界而遭受本不应该发生的厄运的惨痛教训。但历史就是历史。理解了世界才能知道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才能顺应历史的天命。虽然命运以某种铁的必然性主宰世界,但理解和把握这种必然性,按照必然的天道天理行事,走在正道上,才有好运之气的升腾,这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
当前,如何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突然遭遇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思想之开启的前提。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能超越康德这样一个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现代哲学家,就在于他能洞悉启蒙哲学内在的问题,并以整个“现代性”所遭遇到的危机与问题,而不仅仅是理智启蒙问题,为哲学思考的对象。理智启蒙的确为现代性催生了自由的个体,他们作为独立的主体自由地成长了起来,这无疑代表了现代性历史的根本方向。但是,自由了的个体随之必然要求其主观的权利,这也是非常正当的要求,且具有自然法的合理基础。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英法自由主义乃至康德、费希特对于现代性规范秩序的建构,都如同休谟批评现代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一样,是建立在观念之联想的极其不牢固的沙滩之上。
因而,在英国光荣地大力发展科学与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历史跨越式地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科技文明时代,现代性必须要有新的规范秩序。于是,启蒙了的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着手将现代性的观念、思想与价值变成现代性的自由的规范秩序之时,就遇到了旧欧洲一切保守势力的疯狂抵抗,法国大革命就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也就有了新的维度与前提。
在这里,我们无需更多地追述现代性的历史演变,只需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现代性遭遇到的文明危机已经非常多了,但之前的每一次危机,人类都能在反思中寻找到文明发展的方向,哪怕是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将国王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残暴专政,之后又出现了拿破仑横扫欧洲的侵略战争,如此等等,人类都能穿透思想与观念的迷雾而寻找到文明发展的基石与方向,从而守护着文明。但是,这一次“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文明危机却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文明的敌人既不是来自“敌对”力量的战争,也不是蛮夷的入侵,甚至不是意识形态的冷战,而只是来自大自然的病毒!让人匪夷所思的恰恰就在于,仅仅一个不明不白的病毒就让东西方严重分裂、左中右严重分裂,让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共同体”严重分裂,甚至至亲至爱的“家人”也很分裂;它不仅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方向,而且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最终连真相也都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彻底分裂的力量难道真是病毒吗?
病毒显然只能是一个引擎,一个导火索。
一个本身强健的生命不可能被病毒击垮,就像一台能及时给漏洞“打补丁”的电脑不会被“病毒”攻破而陷入瘫痪一样,虽然这次“新冠疫情”实实在在地让社会生活陷入了瘫痪。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一个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夜之间就彻底封城,人们只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家“斗室”之内生活几个月。放在之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尽管不愿意,世界大多数城市最终都走向了不同程度的“封闭”之路。
社交生活的“停摆”,意味着许多领域的“停摆”。大家都在经历众多“停摆”的阵痛。但对于哲学而言,最感痛苦的却是思想的“停摆”。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停摆”,不是说人不再思想。相反,思想是自由的,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人能自由地思想。而我说“新冠疫情”令思想“停摆”,指的是之前所有的思想,似乎都成了空头支票,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似乎在凶猛病毒的攻击下全都失灵了。此时,世上所有相关于“价值”或“意义”的考虑,据说全部让位于哲学最基础的问题——生与死的较量,最大的“义”就只剩下赤裸裸的“生”——活下去。当然,这样简单的道理不是人们不懂,分裂的更深的根源,不在于要不要活下去,而在于何种“活法”才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即对于一个人(der Person)而言,何种“活法”才是有意义的,何种“活法”简直不如不活。这种“活下去”的底线从而也适用于“死”的尊严。人都有一死,或迟或早。人世间最大的正义,就在于所有人都有一死,因而死无关乎人的意志或选择,但绝对关乎尊严。有的人活得高高在上,神乎其神,但临死时却失去了尊严,或者毫无尊严地暴死;有的人活得窝窝囊囊,但死时却死得很体面,死的尊严是生命尊严的确证。
表面上看,“新冠疫情”大敌当前,谁若让思想纠缠在这些最基础的哲学问题上,是可笑的、迂腐的,但是,如果不涉及这些问题,不以生的意义和死的尊严为依据,而单纯地讨论要不要封城封路,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出门社交,或者抽象地在要自由还是要管制之间争吵,哲学思想马上就迷失在无方向感之中而陷入“停摆”。因为在生与死的底线上,思想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本能上,理性无论如何是敌不过情绪的。情绪的反映不仅最为切身,而且最为激烈,从而也最为因时因地、因天因人、因灵因鬼,因各种固有的僵化的观念而变。所以,在此处境下我们看到了,不管任何想法和观点,都会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者,而反对者也仅仅只是因为要反对而反对,却提不出什么有真知灼见的思想来。如此这般的都因反对而反对,因否定而否定的争吵进程,就陷入了黑格尔说的“恶的无限性”。
但正是黑格尔关于如何消除“恶的无限性”之思考,开启了当前思想的可能性。因为“恶的无限性”起因于事物的有限本性,并各自封闭于自身的有限却要强装无限的自信。事物就其“存在”而言,具有逻辑上无限的可能性,而逻辑上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不能获得其现实的“定在”,即在时空世界中的“规定性”,就是“纯无”,因而,任何事物之有“定在”是就其“实存”而非就其纯粹抽象的“存在”而言,事物“实存着”即具有了存在上的规定性,并因此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个“定在”,即被规定了的实存。所以,实存是事物被规定的现实存在之进程,这种“被规定”同时也就是“被否定”的进程,因为任何一个说“事物是什么”的规定,是从否定它不是什么而来。说一个人是人,即用“人性”来规定人,就否定了人不是畜生也不是神。而反过来想把自己说成是神的人,也马上具有一种否定自己是人的危险,因为没有了人的规定性,你可以成为一尊神,同时也意味着你能成为一个畜生,这在逻辑上是同样的道理。人的定在,只在规定人的天命就是成为一个人时,这种“规定”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种规定不是限制,不是专制,而是自由,是由人之本给出人成为其自身的自我规定性。正是这种自我规定性的自由,具有内在自觉的否定性,即否定他既不是畜生,也不是神,从而不会陷入“恶的无限性”。
如此“定在”规定性之有价值,在于它守护着人本。“恶的无限性”因其突破事物之根本与本体,进行“无根”“无本”的否定,最终成为分裂世界的根源。理解现代世界分裂的这一根源,是我们当下寻找文明方向的起点。
黑格尔也正是通过否定“恶的无限性”来为现代性开启新航道的。
从思维方式来说,“恶的无限性”是现代知性思维之结果。实际上,“知性”执着于概念思维,这一点黑格尔自己也是坚持的,他说哲学思维就是以“概念”来把握现实。但关键在于,知性思维执着于概念的抽象规定,见山是山,见水为水,这种思维对于科学知识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科学事关已成“事物”的本质规定,必须确定而准确。这与诗人对山水的鉴赏性描述不是一回事,后者无关本质,无关山水真实定性,而仅仅描述山水给人的主观之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刘禹锡写下“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而说他没有反映出山水之本质,也不能责怪他把“山水翠”(或“山水色”)与“白银盘里”的“青螺”相比拟,此处如果采取知性概念的语义分析,就会导致“诗意全无”的可笑。所以,黑格尔对知性思维也是给予了高度肯定的,以概念及其语义的准确性来把握事物的真理,这对于哲学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但黑格尔高于现代哲学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看到了哲学具有超越科学的思想能力(这里的“科学”指近代以牛顿力学为榜样的现代自然科学)。“科学”从经验到的感性现象中“分析”现象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能进行真正的“思想”的。“思想”的真正对象不是当下呈现的现象,而是现象之“存在”的原因。但知性思维显然不可能把握到“存在”本身的复杂性。“现象”是一个确定对象,即已成的对象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存在”永远不是一个“已成的”现成的东西,它是未完成的,是要在其“实存”中“存在”并逐步获得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去趋向自身的完成。因而,“实存”既有“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维度,也有“存在”的空间性、社会性,乃至民族性与国家性维度,乃至“世界”维度,如此等等,当我们要给予“存在”或“实存”一个确定的“是什么”的规定时,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何种时间性与何种空间性,乃至何种世界性维度论说其规定。于是,所有这些规定都只能是一个暂时的、不可固定下来的定在之规定,因为在我们做出这些规定的当下,时间已经在流逝着,已经不是前一刻的时间了,时间变了,空间也会跟着处在变动不居之中。

但是,知性思维固执于把每一种规定都视为事物在一切时间与空间中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定,这就出现了问题。同时,知性规定是认知的主体(人)通过其以事物的“表象”和“意识”为中介做出的对于事物的“主观的”规定,它依然不明白黑格尔所坚持的,哲学的“客观思维”乃是这样的:思维所把握的既是思维着的主体之主观的意识,同时也是事物本身的存在。但我们能从固执于自身的主观的意识,回到事物本身是什么的“存在”层面时,也即回到“真理”面前时,“恶的无限性”才可中止。这就是黑格尔呼吁哲学必须以真理为己任的原因。
目前的世界之所以处在这种相互否定、各自对立的分裂状态,原因就在于,哲学长久以来在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中回到了知性思维,即回到了主观意识对事物当下现象之分析,从而只是对事物做主观的外部反思,而进入不了事物本身的存在,并因此也就放弃了哲学的真理追求。“后真相时代”提供了当代思想在真理面前退却的冠冕堂皇的“遁词”,但“后真相”对于哲学如果有意义,不在于放弃对真相的追寻,而在于意识到如果“真相”一直在延宕中而显而不露时,我们如何有新的方式超越主观性而坚持理性思维,无论如何,“后真相”并不能为任何主观的真理提供有效的辩护。
当我们把现代性分裂与对抗的起因归咎于知性思维,即主观性的外部反思之思维定势时,我们确实在走向黑格尔的哲学之途。但只有真正深入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精神之中,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黑格尔,理解现代性,尤其是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及其为现代性所确立的新的基础。
我们赞同哈贝马斯对他的这一评价: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作为哲学来思考的哲学家。他对现代性的思考意在真正理解现代性并进而推进现代性,就他自身的思想而言,他无疑达到了真实理解现代性的目标,但他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及其为新的现代性开辟的规范秩序建构的目标,实际上在他死后立即被中断了。
当我们这样言说现代性时,我们把“现代性”(Modernität)作为现代思维范式,这就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知性思维,这种思维一方面在知识论上为科学奠定基础,寻求科学知识的发现与求证的逻辑;另一方面在价值论上为“现代性”确立了“伦理原则”,这就是把建立在主观性自由(或主体性自由)基础上的“正义”作为现代的伦理理念;因此,现代性还必须有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实践哲学的“规范秩序”建构。黑格尔在现代性的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有其超越前人的独立创新之处:在知识论上,他不满足于英国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到休谟那里实际上在知识论上就走到头了,从单个的经验知识出发,并不能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确立基础;他也不满足于康德批判主义的先验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止步于知性思维从而把“知识”划定在现象界,事物之自在自为的本体却成为不可知的领域;在价值论上,他认同并推进了个体的主观性自由为现代的基本价值,并把它视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这个新的时代”(Die Neue Zeit)的时代精神。他比其他自由主义者做得更好的论证,就是通过对个体自由意识史的叙事,为现代个体自由价值做了详实的历史梳理:个体自由意识在苏格拉底身上明确地表现了出来,但这种自由无法上升到柏拉图的城邦伦理原则之中,“正义”作为城邦伦理原则因此无法纳入个体自由,因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被视为某种空洞理想的谚语,本质上无非就是对希腊伦理本性所作出的解释,那么在对渗透到伦理本性里的更深原则的意识中,这个原则在伦理本性上直接地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个腐败的东西表现出来。柏拉图正是出于这种渴望,不得不寻求援助来对抗这种腐败,但必须要从高处而来的援助,首先只能到希腊伦理的一种外部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他心想借助于这种形式就可以克服那种腐败,殊不知经他这么做,恰恰把伦理性更深层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人格,损害的最深”。到了希腊化时代,城邦伦理解体,无限的自由人格这种主观自由再次成为哲学的主导原则,怀疑论、犬儒主义和斯多亚主义都表达出以强烈的主观自由反抗习俗的伦理,但最终主观的自由让位于“自然”,“遵从自然而生活”成为斯多亚派的道德。只有通过罗马法私人财产权的确立,意志自由才第一次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定在”,通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主观的个体的自由意识才在现代哲学中确立起来,成为现代的伦理原则。

但是,黑格尔通过对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研究,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反思,更多地发现了“自由主义者”们在确立个人自由原则以实现现代性的规范秩序时的失误,这就是依然是以个体自由的道德意识,即单纯的意志自由作为基石,而没有发现一种真正具有社会历史现实性的自由的规范秩序,是不可能单纯依据道德性的主观形式自由的,它必须通过政治制度化的正义为优先原则以构成一个伦理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因为政治制度化了的正义,是伦理性自由而非道德性的自由。因为“政治”是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正义是保障共同体内部每一个个体自由成为现实的伦理原则,而不是个体主观意志自由的道德原则。这是黑格尔区别于所有以“原子化的个体意志自由”为基础构建现代规范秩序的关键之处。当然一提到“政治共同体”,现在有人立刻就把它与“总体性”“专制”“极权”联系起来,它需要得到黑格尔式的理解,就得理解黑格尔的“伦理性”与共同体之间的生命原则,它确实需要艰苦的哲学论证,在这里,我只能把他思想的结论与要点表述如下。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由单个的具有主体性人格的自由个人构成的,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理解没有差别,黑格尔也是坚持这一点的,但是如果立足于原子化的单个人的意志自由为起点,黑格尔则不同意,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知性的抽象,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原子化的个人,就像单个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样,单纯的个人意志自由也只是我们思考道德基础时,必须要有的一个先验设定,以便确立一个可以承担道德上赞美与谴责的责任主体。真正现实的道德自由,像康德所论证的那样,依然要考虑“意志的伦理性”,即你自愿意志的行动准则是否能够得到像你一样的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任意,如果不能,那么你的主观自由之意志依然是不自由的,无法成为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只有你在主观反思的“形式上”达到了意志的伦理性,主观意志的行动准则才是有效的,因而一个真正的基于主观自由的道德原则之证成,需要一个形式主义的“意志的伦理性”共同体。这就是康德的道德立法力主形式主义立法原理且有一个“目的王国”之预设的原因。
所以,道德上的单一原子化的个体意志自由离开了“意志的伦理性”不可能真正存在,那么从原子化的个人自由来构建政治伦理共同体的正义就更成问题了。我们依然以康德为例来说明。康德通过法权论来建构其基于个人意志自由的规范秩序,先从权利上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这没有问题,明确区分了“我的”和“你的”权利边界,使得我们的个人权利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从而得以实现,这是自从罗马法以来的传统。黑格尔也同意这一点,通过私有财产权的确立获得个人意志自由在法权上的“定在”形式。但法权的实现,不是有一个抽象法的规定就完成了,其真实的实现还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规范秩序,个人自由只是这个规范秩序具有正当性的先验基础,而不是已经实现了自由权利本身。法律规定了的权利仅仅是字面上的,其真正实现必须有一个真正承认法律价值、遵守法治精神、敬天守则的伦理共同体,才能以法律所规定的规范与秩序确立自己的职权边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才能实现。
所以,康德在“法权论”上阐明的法权或正当概念,不是单就个人的意志自由来确立,而是就每一个人主观的意志自由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自由如何能够共存来确立:“任何行为若能根据一项普遍法则而与每个人的自由共存,或是依据该行为的准则,任何人所意愿的自由能根据一项普遍法则而与每个人的自由相共存,这个行为便是正当的(recht)。”此“正当”就是“正义”。这里的自由就是个人行动的外部自由,康德强调了行为“正当性”的三个要件:每一个人自己所意愿的自由,根据一项普遍法则,与每一个其他人的同样的外部自由能够共存。因此,自由的边界就是自由之共存的可能性,即任何人自己所意念的自由没有任何理由损害他人意念的自由的权利,相反,必须根据一项普遍原则与每个人其他人所意念的自由相共存。于是,法权论上的自由之实现也就必须是在“伦理关系”中才是现实的,这种伦理关系意味两点: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之自由的共存性关系和这种关系是靠每一个人都能自愿遵守的普遍原则来维系的。任何符合这两点的伦理关系都是自由的,而不是强制的或专制的。所以,康德也论证了,哪怕是我们对外在物品的占有权,虽然意志自由是合法占有的基础,但是,“唯有在一个公民组织中,某物才能终极地被取得;反之,在自然状态中,该物固然也能被取得,但只是暂时地被取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任何单个的意愿和个人自由,要真正获得实现,就必须是在某种伦理关系中,这也就是黑格尔反对康德的道德性立场而要进展到伦理性立场的关键原因。
康德等主观性哲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单个人如何构成一个具有伦理性的社会共同体问题上,采取了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是黑格尔所不能同意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黑格尔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契约论,在单一法权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上,黑格尔依然是认同契约论的,但是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等伦理实体,黑格尔则坚决反对近代以来的契约论解释。

原因有三:其一,说家庭完全是契约关系,就把家庭真实的伦理意蕴给取消了,家庭之成立首先依据的是男女双方之间的爱情,其次才是法律契约,再次是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亲之爱的相互义务,契约仅仅只是家庭合法性的一种外在法律形式,契约可以缔结也可以废除,但家庭之间的血亲之爱,一旦产生就永久不变;其二,说国家是由契约产生,根本就是不顾历史现实的抽象假定,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根本不需要这种假定;其三,任何依据契约产生的共同体都只是原子式个体之间的一种外部联合,因此,只能达到一时的脆弱的外在联合形式,不能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的有机体。因此,真正的现代性自由的规范秩序,在黑格尔看来,就要放弃自由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单一自由个体通过契约来外部联合的做法,而要通过伦理精神的“活的善”来构建伦理实体的内在有机体,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规范秩序。
通过内在的伦理精神而不是外在的法律契约为什么就能真正构成一个真实的政治—伦理共同体而不重蹈专制城邦的覆辙?因为精神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构成性力量,它源自古希腊的“灵魂”概念,在1804-1805年的《耶拿体系草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中,黑格尔就把“灵魂”视为“一种把诸要素独自地、绝对被分离开的综合”力量,“一种交互作用的漠不相干的在完全一致中的综合”,透过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术语,黑格尔要说的是,“灵魂”是一个实体之成为一体的根据,或者说是这个根据本身的实存,这个根据本身并不脱离实存物,实存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实存物,因为它有灵魂,灵魂成就其实体之为实体。更进一步说,一个实体如果没有灵魂,就是一些漠不相干的“诸要素”,独立的、不相干的、绝对被分离开的东西,不成为一物,没有一体之生命,而有了灵魂(气息),这些不相干的“诸要素”就有了“交互作用”并有了生命之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体之物。所以,后来黑格尔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述了“精神与有机体”。
一个有机体是由各种成分或要素构成的,但各种成分或要素不会自动地交互作用,靠什么把各种要素或成分组合成为一个有机体呢?就是靠“精神”。因此,精神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因为有机体有“精神”,才有有机体之生命。精神于是就是内在的生命原则。生命作为有机体,意味着生命能把诸多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内在的交互作用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每一个组成要素都是一体生命的前提,可以独立存在,可以“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功能,但在整体中又没有一个部分或要素是多余的,每一个独立成分的损坏都可导致整体生命的死亡。因此,伦理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把所有单一的自由个体组成一个伦理共同体或伦理实体的内在生命原理。
有了这样的伦理实体,现代的自由规范秩序才能真正地变成现实,才既不会因知性思维的外部主观反思导致恶的无限性,也不会因临时任意签订的契约之不可履行而随时让法律政治共同体陷入瓦解的危机。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寻找到了现代性自由的规范秩序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向。以此为基础,善的脆弱性、文明的脆弱性危机,都可以寻到解决的方向与路径。
因此,在当前世界处在极不确定的无常而茫然无措时,黑格尔依然是我们的导师,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与领会。这就是我们《伦理学术》第9期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探讨核心的缘由。由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国内研究成果较少,目前只有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杨祖陶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对《精神哲学》中的“人类学”部分的研究国内尤其缺乏,因此我们特别翻译了德国当前相关研究专家的论文,应该说,对推动我们对《精神哲学》深入理解将大有裨益。至于黑格尔法哲学研究,规范秩序的建构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重点,本期也在深化讨论的内容。
关于美德伦理学的讨论,本期推出了黄勇教授、郑开教授的重头文章,非常值得关注。刘畅和朱锦良博士翻译的瓦登菲斯的《响应伦理学:在回应与责任之间》是一种新的伦理学纲领,推进了我们对于“责任伦理”的理解。尚杰教授的《差异不同于存在——私密的自由》和张念教授翻译德里达的《性差异:存在论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法国哲学的新思想。在“描述伦理学”栏目下,唐瑞和倪胜教授翻译的《马丁麦克多纳的<枕头人>,或为文学辩护》和《友谊与雅斯米娜雷扎的<艺术>》以新的视角阐释了伦理叙事中的文学与艺术的意义。本期还在人类学视野下,继续探讨关于动物伦理、儿童哲学和黑格尔有关“灵魂疾病”“疯狂”等伦理生活中的重要现实问题。
感谢所有作者和译者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在无常与不知所措的今日世界共同守护伦理精神的一种方式。
原文来源:微信公号——伦理学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pgZVqkBUcsqfNdnZ_-b5Q
编辑:刘佳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2-8 19:00
【案例】罕见!他们头版开天窗发动“战争”纸媒对科技巨头开战!加拿大多家媒体头版“开天窗”,只留下一句话
“想像一下这里没有新闻是什么样子。”
当地时间2月4日,包括《多伦多星报》、《多伦多太阳报》和《国家邮报》等在内的多家加拿大报纸发布了空白的头版,只在底部印了这样一句话。


“这不是印刷错误。”综合《多伦多城市新闻》、《多伦多星报》、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的说法,这是加拿大新闻媒体协会(NMC)发起的名为“消失的头条”运动的一部分,除了报纸的空白头版,还有一封致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呼吁渥太华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目的是让人们关注渥太华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围绕新媒体规则和法规的辩论,让人们感受到如果没有强大的新闻业,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并警告加拿大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陷入困境的新闻业可能会崩溃。据报道介绍,NMC是一个报纸行业协会,代表了加拿大800多家报纸。
这一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谷歌和脸书。《多伦多城市新闻》表示,两个平台(谷歌和脸书)都得到了传统媒体免费内容的支持。《多伦多太阳报》也控诉称,当脸书或谷歌——最令人讨厌的巨头——剽窃媒体内容并将其收入囊中时,我们并没有得到报酬。谷歌和脸书获取了80%的数字广告收入,却连一分钱的税都不交。不过谷歌对此反驳说,通过搜索新闻,报纸引起了更多读者和广告商的兴趣。
当天,加拿大邮报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露辛达·乔丹也在《国家邮报》刊文称,读者今天会注意到加拿大各地许多邮报传媒集团报纸的头版有些不同之处:它们是空白的。这代表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加拿大各地的报纸正在消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谷歌和脸书等全球科技巨头占据的主导地位,这些公司拒绝为加拿大新闻媒体创造的内容支付公平的价格,还获取了加拿大80%以上的数字广告收入。
《国家邮报》网站4日报道截图
露辛达·乔丹表示,我们的空白头版是NMC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人们认识,这种现象不仅对当地媒体,而且对民主本身构成的危险。
“现在是渥太华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露辛达·乔丹呼吁,对渥太华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通过立法,允许报纸就其内容的使用谈判一个公平的价格,如果谷歌和脸书拒绝合作,就会被处以巨额罚款。
“新闻不是免费的,而且从来都不是。”在一封写给环球新闻网的邮件中,加拿大联邦遗产部长史蒂文·吉尔博表示,“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新闻)出版业者的工作必须得到足够的报酬,我们会支持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的民主以及我们社区的健康和福祉提供必要的信息。”
吉尔博重申,加拿大政府打算通过立法创设“加拿大制造模式”,为加拿大新闻业者和数字平台打造全面、一致且公平的数字架构。
这些空白的头版也成功引起网友关注。虽然有网友认为“传统媒体正在死去,这是它们应得的”。↓
“我好奇广播有没有对电视发起过相似的抗议,或者马车商有没有抗议过亨利·福特?时代变了,传统媒体正在死去,这是它们应得的。”
但也有网友支持“公正的新闻报道”,认为纸媒此次传达了“很棒的信息”。
“很棒的信息”
有公正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支持所有不同类型的媒体渠道”
“这很有趣。我喜欢每天早上读报纸,这是我生活中的一点小乐趣。”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GLI8z1w8C8X4AwOuyrhHg
编辑:马皖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2-21 14:25
【案例】
罗尔斯诞辰100周年 | 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又有什么价值?
今天是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1921.02.21—2002.11.24)诞辰100周年。
罗尔斯是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思想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一生的经历看起来颇为简单,是个典型的当代美国学者,从学校到学校,精心地教学,写作哲学论文和著作。他甚至还不像其他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法国的萨特),参加过或直接推动了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而只是以自己为数不多、但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果影响了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
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
文 | 顾肃
来源 | 《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引言
转自 | 群学书院
01
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1943年本科毕业。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八所最好的“长春藤联校”之一,学校规模并不大,位于新泽西州。但该校思想自由开放,教学和研究水平尤其高,综合排名一直位居美国大学的前几名。当代最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只身来到了美国,一直在普林斯顿任教并从事研究,直到去世为止。该校云集了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保持了学术自由创新的优良传统。
罗尔斯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195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对伦理学、政治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为研究打下的基础却十分深厚。他的学术功底不仅表现在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而且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所涉猎。这些都为他此后发表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方面的论文乃至划时代的政治哲学名著《正义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至1952年,罗尔斯在普林斯顿大学留校讲授哲学。但美国大学教师流动性强,很少在一所大学终身任教。从1953年到1959年,罗尔斯又到另一所著名的康奈尔大学讲授哲学。从1960年到1962年,他转到了美国最好的理工科综合性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该校不仅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其文科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系科也相当出色,拥有像萨缪尔森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该校与美国最好的哈佛大学同在波士顿地区的文化中心坎布里奇市。罗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只工作了两年多,便被哈佛大学聘任教授,从1962年起在其哲学系任教。
哈佛大学不愧为美国第一高等学府,其哲学系聚集了一流的思想家。能够在哈佛取得终身教授职位,一般都要具有相当的学术成绩或潜力。此时的罗尔斯尽管还没有发表多少篇论文,但已经表现出了成为当代哲学大师的潜力。42岁的罗尔斯此前并无哈佛的学历,但能够被哈佛相中,显然有其非凡之处。他从1951年开始发表《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的纲要》,即表现出对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此后便潜心于社会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正义问题的研究,这包括基本理论的创新、制度的设计以及对其伦理价值观前提的周密论述。
为此,罗尔斯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论文。1958年发表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一文,为其正义理论奠定了基本概念的基础,即把正义定义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以此作为自己正义观的出发点。到哈佛以后,罗尔斯学术思想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1963年发表的《宪法的自由和正义的观念》及《正义感》,对正义观念的法治主义基础作了深刻的论述。此后他还在《非暴力反抗的辩护》(1966年)、《分配的正义》(1967年)、《分配的正义——一些补充》(1968年)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正义制度安排和分配正义方面的重要理论前提。
所有这些文章和研究都为罗尔斯精心写作《正义论》一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罗尔斯一生的著述不多,但非常重视其成果的学术质量、思想的创新性和深刻性,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实际上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才写成《正义论》一书。到哈佛大学以后,他为此书先后三易其稿,并利用大学教授学术休假的时间,到斯坦福高级研究中心集中精力修改完成此书。最终于197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正义论》出版以后,很快赢得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被西方学者推崇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人们经常把该书当作与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论自由》齐名的“自由民主传统的经典著作”,并认为该书是将道德哲学与政治、伦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是“在正义与西方文明的当代现实之间的一座桥梁”。这本书在当代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有人认为,任何人在处理这本书所触及的问题时,如果想要学者们重视自己的工作,就必须表示自己的研究与该书没有脱节。
02
《正义论》展示了罗尔斯精心阐述的严密而条理一贯的理论体系。全书分三大部分:
《理论》篇论述了他关于正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概念和范畴,基本出发点;
《制度》篇论述了正义原则如何运用于社会制度,探讨了自由、宪法、多数原则、政治义务、非暴力反抗等重大政治体制问题;
《目的》篇涉及理性、价值、目的、善等伦理价值问题,特别是社会稳定性的伦理基础。
罗尔斯由此而设计了人们相互奉献福祉、公正、和谐、稳定的理想王国。全书涉及内容广泛,论述全面而详尽。其风格也与二战以来英语世界大部分哲学著作有所不同,主要是再度采用较为思辨的语言引经据典地阐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而不是像分析哲学那样较多地集中于语言与形式方面。
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理论贡献表现在政治哲学上重新采用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全面论述了自己“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基本理论,并对功利主义作了相当深刻而全面的批评。他所反复论述的两个正义原则既突出了公民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应当享受的基本平等及其理论含义,同时又对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差别提出了独特的理论标准,并对正义理论的伦理基础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证。
政治哲学家虽然往往不情愿受社会现实所左右,而主张以彻底的理论改变世界,但其潜意识中却又摆脱不了与社会现实的干系。反过来,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特征也的确可以为某些重大社会政策提供准绳、启发和理论依据。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的情形便是一个重要的明证。
该书的出版正值西方社会中的黑人等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方兴未艾,政治反对派要求合法地位的呼声日趋高涨,人们在原则肯定自由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和产品的配置的同时,也抱怨此过程还伴随着难以接受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因而像福利国家等新的社会政策、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对个人权利和收入均等的要求也都诉诸正义的理论。罗尔斯颇为抽象深奥的正义理论在20世纪第一次与权利和分配领域的政策主张直接联系在一起,并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推向了一个高潮。反过来,作为该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正义理论又推动了西方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各种社会团体和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要求公平待遇、不利者要求有利对待的社会运动。尽管这一运动至今仍在开展中,所取得的成果亦因时因地而异,但思想家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成了西方当代政治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围绕该书的争论和文献也纷至沓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在《正义论》出版三年以后,哈佛大学另一位年轻的哲学教授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一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与罗尔斯进行了正面交锋。而就《正义论》召开的各种理论讨论会、发表的专门文集也相当多,足可见学界对该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和所阐述的正义原则的重视。罗尔斯本人尽管并不十分雄辩,他本人说不上是个出色的演说家,&127;但在理论上极其严谨,&127;对于各方面提出的商榷和论争都很有耐心地进行答辩(往往是以书面的方式),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回应文章。一直到90年代,罗尔斯还在与学界的同仁进行争论。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正义问题展开的论战。所有这些论争都进一步深化了罗尔斯本人的正义理论,也加深了人们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正义论》一书不仅在美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迅速传播至全世界,引起各国思想界的重视。该书被翻译成欧洲的所有主要文字,成为东西欧思想界特别是政治哲学领域数十年反复讨论的名著。该书在亚洲也产生了影响,被译成中文、日文和朝鲜文。这也反映出当今世界对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持久兴趣,学者们认真地讨论该书所提出的正义问题,以便为各国的政治和分配制度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03
罗尔斯是个不轻易写书的严谨的学者,在《正义论》出版以后的20年里,大多发表一些论文,围绕该书的问题发表一些重要的演讲,但没有再出版专著。这段时间的西方思想界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主要是出现了一些挑战分析哲学传统的所谓后现代思想家。同时,西方社会也开始向后现代文化转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罗尔斯本人难免受到这些倾向的影响,开始整理自己的前期思想,陆续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某些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他认真地修改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系列讲演和其他讲演及论文,提出了与《正义论》存在相当理论差别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这样,在《正义论》发表22年以后的199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自由主义》一书,成为代表他晚年思想的学术专著。
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继续论述了《正义论》中“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核心观念,但也对之作出了重要的修正。最重要的是,他所作的哲学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的前期著述以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为基本理论前提,这是指一种在基本道德信念上相对同质的、稳定的社会,人们对于构成优良生活的因素存在广泛的共识。所以他在《正义论》中反复论述“秩序良好的社会”这一基本观念。然而,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是,诸多不可兼容和不可调和的信念和学说(包括宗教、哲学、道德等方面)多元化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基本构架之中。当然,自由的制度和机构本身鼓励这种思想信念的多元化,把它看作是公民基本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现实与罗尔斯所设想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存在一定的差距,罗尔斯并不回避这一核心问题,而是认识到这是民主制度存在的恒久条件。他进而深入发问道,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所组成的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尽管深深地被这些自有其道理却互不相容的学说所分割,为什么能够和谐共存于一体?
这正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为此,罗尔斯重新定义了“秩序良好的社会”,它已不再是《正义论》中所强调的由其基本道德信念整合的社会,而是由其正义的政治观念整合的社会,而这正义正是对合理而广包的各种学说重迭共识的焦点。作为公平的正义在此并未失去意义,而是成了这种政治观念的一个典范,作为重迭共识的焦点,它意味着可以得到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长期维系的主要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认可。
罗尔斯认为,这种对合理学说的重迭共识代表了宪政民主制度下可以实现的社会整合最可能的基础。果真如此,那将可继续并完成三个世纪以前西方即开始的思想运动,这种运动伴随着对容忍原则的逐步接受,尽管有点不情愿。这一过程将以完全接受并理解现代各种自由观念而告结束。
罗尔斯是个广义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在《正义论》时期,他也没有脱离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主流。而《政治自由主义》一书则代表了一种以自由公共理性为基础的鲜明的自由主义,它为解决西方多元社会如今面临的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深刻见解。这是面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而在政治哲学上作出的新调整,它丰富并发展了西方数世纪以来不断更新的自由主义思想。
《政治自由主义》出版以后,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反响。有学者评论说:
关于现代社会的正义、宽容与稳定,存在许多问题,除非从罗尔斯所提出的理念开始,便很难讨论这些问题。罗尔斯从有关社会和经济正义几近普遍的道德理论转向现代自由国家的政治理论,与其多元论和宽容理论一起,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惊人而强有力的转变。(载《伦敦书评》)
杰罗米·瓦尔德龙则指出: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对《正义论》所作的充满说理而又不同寻常的评论,其作者认真地对待回应各类批评者的义务。另一方面,本书为早先出版的那本书添加了诸多细节,特别是他对制度稳定性和基本自由的讨论。然而最重要的是,与对于公共事务的规范性哲学化相反,这本新书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向。(载《政治自由主义》英文版封底)
从早期比较强调规范性政治哲学,到晚期更为现实地认可多元社会的多重学说和信念,并以重迭共识来解释正义理论和政治民主,反映了罗尔斯在后现代文化发展背景下作出的理论调整和思想转向。一个对自己的批评者、对社会公众和学界负责的严谨学者,不惧怕部分否定或改变自己前期的著名理论,真诚地提出新的学说,这也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
罗尔斯晚年退休以后,仍然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开设少量课程。只是健康状况的恶化使他不时中断课程,以致最后不再开课。然而,哲学界的同仁决没有因此而忽视他杰出的学术贡献。1996年,同仁们聚集于美国加州大学,隆重纪念《正义论》发表25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哲学家欢聚一堂,向罗尔斯致以崇高的敬意。罗尔斯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衷心感谢各国学者特地在此举行纪念活动,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近年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新成果。在当代哲学发展史上,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举行世界性的专门纪念会,的确不多见。由此足可见罗尔斯在当代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来源:齐鲁博士论坛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JLo7nBlVc6nro8CR39Blw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4-1 16:13
【案例】
道德许可效应
什么是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许可效应,指当自己对某事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做出与这项道德标准相关的行为和判断时,反而更倾向于违背这项道德标准的行为。
简单来说,当我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努力的事情之后,就倾向于做一些坏的事情、堕落的事情,来破坏自己之前的努力。
道德许可效应的实验
实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Benoit Monin)和戴尔·米勒(Dale Miller)研究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两种类别的问题:第一个类别是命题一:大多数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大多数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第二个类别是命题一: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有些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人们会不太容易驳斥这样的命题。它们看起来或许有点性别歧视,但人们很难驳斥“有些”这个限定词。结果判断前两个命题的学生立刻提出抗议,但判断第二组命题的学生态度则更中立一些。
断完这些命题后,学生要在一个模拟招聘场景中作出选择。他们的任务是判断几位候选人是否适合某高层职位。这份工作所处的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的,比如建筑业和金融业。候选人中有男也有女。对这些刚刚驳斥过性别歧视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看起来是项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当然不会歧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人。但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和那些勉强同意第二组命题认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学生比起来,那些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种族主义观点,并提供机会让他们表现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时,也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
学生们因为驳斥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而感觉良好,因此放松了警惕,更容易作出有歧视色彩的决定。他们更可能根据直觉的偏好作出判断,而不去考虑这个决定和他们“追求公平”的目标是否一致。这并不是说他们想歧视。他们只是被自己之前良好的行为所蒙蔽,没看到这些决定会带来的伤害而已。
道德许可效应的相关现象
“道德许可效应”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有明显道德标准的人能说服自己,认为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合情合理的,那些人包括部长、注重家庭观念的政治家、打击腐败的辩护律师。例如,一位已婚的电视布道者和秘书发生性关系,一位财政保守派利用公款修自家房子,一位警察对毫无抵抗能力的罪犯施以暴力。大部分人在觉得自己品德高尚时,都不会质疑自己的冲动。而一些人的工作总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品德高尚。
道德许可效应不可避免
所有被我们道德化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许可效应”的影响。如果你去锻炼了就说自己很“好”,没去锻炼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今天去锻炼了,明天就不去了。如果你去处理了一个重要项目就说自己很“好”,拖延着不去处理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早上取得了进步,下午就变懒散了。简单说来,只要我们的思想中存在正反两方,好的行为就总是允许我们做一点坏事。
道德许可效应向诱惑屈服
重要的是,这不是血糖含量低或缺乏意志力造成的。心理学家调查这些纵容自己的人时,他们都认为自己作决定时能够自控,没有失控。他们也没有罪恶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奖励,并以此为傲。他们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已经这么好了,应该得到一点奖励。”这种对补偿的渴望常常使我们堕落。因为我们很容易认为,纵容自己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励。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向诱惑屈服了。
道德许可效应出现的原因
1、大脑中的"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决定了是否会出现"道德许可效应"。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提出,我们大脑中的前额皮质,也就是我们额头脑门这一块,是指挥人选择做"更难的事情"。但是,就在这脑门小小的这一块地方,还会有区域划分。它分为三部分,左上部分是"我不要"的意志,右上部分是"我要做"的意志,下面最小的地方是"我想要"的意志。这就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常常出现摇摆、犹豫不决,或者抵挡诱惑、克制冲动,这些问题都会因为这三种意志力量的大小而决定。"我不要"和"我要做"两种力量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我想要"的力量往往就让人们发生了"道德许可效应"。
2、对于事物判断的绝对道德化,导致人们更容易发生"道德许可效应"。
什么是绝对道德化?就是自己在看待事物时候,都用"好"和"不好"这种刻板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和区分。比如,你想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如果闹铃一响,你就起床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棒,如果闹铃响了,你关了闹铃又睡着了,没按时起床,甚至导致你上班迟到,你就觉得自己很差劲。这就是你对早起这件事情的"好"和"不好"的评判。这种太绝对的判断,让你早起坚持不到三天就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大脑不喜欢被控制,这种绝对的"好"和"不好"标准让我们感受不到自由选择的快乐,所以在好的行为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做一点点不好的事。
如何避免道德许可效应
1、多用"我要做"的力量,弱化"我不要"和"我想要"的力量,明确自己行动目标。
做事成功的人往往不会纠结于"我不要"和"我想要"之间。这也是王阳明心学中提到的"事上练",知道再多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练,否则不能说真正会用。当你在闹铃响的那一刻,与其纠结我想起床,还是不想起床,不如直接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起床。多说"我要做",少想"我不要"和"我想要",会给你一个简洁高效的工作生活状态。
2、多想事情带来的好处,不给事物贴道德化标签,让习惯成自然。
无论是习惯的培养,还是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做了就好,不做就不好,而是你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改变,知道这件事情能够实现自己的什么目标。在你决定早睡早起时候,告诉自己,早睡早起可以让自己精神充沛,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让自己从容吃个阳光早餐,上班不迟到。当你不再对早睡早起这些事情标签、道德化去看待,不再认为做就是证明你好,不做就说明你差,那么坚持做这些事情,对于你就不再是难事。
3、减少行为的变化性,避免"道德许可效应"的反复出现
当你上班后,坐在电脑前,看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工作,会冒出:"这个工作我是早上做呢?还是下午做?"这就是变化性行为的选择,这种问句,我们要尽量避免。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自己:"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成,如果我拖延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也就是说,当进行一件事情时候,我们需要多问确定结果的问题,减少行为变化的选择性问题。当你今天要早睡早起时候,不要问自己,我是10点睡6点起呢?还是9点半睡5点半起?而是问自己,不早睡会不会无法早起,无法早起,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呢?
在企业中如何应对道德许可效应的负面影响
管理层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激励那些不愿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员工,但道德许可效应的出现会让管理层左右为难。
因此,我们建议管理层要多管齐下,避免组织员工出现过多的心理权利。
首先,管理层不应那么急迫地要求员工承担过多额外的工作,而且要重新评估公司的激励措施(对管理层重新进行培训,让他们管控好对员工施加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企业领导则应当为员工量身定制激励措施,并使其转化为员工积极工作的动力,不要想尽办法控制员工。对于那些主动承担额外工工作的员工,企业领导们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非正式积极反馈,并在公开场合多加赞扬。
企业也应当积极为员工创造一个鼓励自发积极工作的环境。例如,企业可以给员工自由度,调整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以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工作潜能等。企业也应当多聘请那些表现出很强的意愿和能力成为优秀组织公民的员工,并将优秀员工的故事广为传播。
此外,企业的高层领导则应当自觉成为标杆模范,而不求取额外的奖金回馈。
简而言之,避免道德许可负面影响的终极秘诀是在公司中推广良好组织公民的文化和价值观。
原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成林思语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4-3 22:13
【案例】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摘要〕如果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此前的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此后的伦理学则面临相对主义的难题。在古典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但形而上学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就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言,海德格尔哲学中有存在论而没有伦理学。虽然伦理学面临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却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能够和平共存而作为“底线”的基本规则。〔关键词〕伦理学 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 全球化
在现代哲学之前——我把19世纪以前的哲学称为“古典哲学”,把20世纪以来的哲学称为“现代哲学”——伦理学建基于形而上学之上,在中世纪亦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不过,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19世纪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的衰落,伦理学不再依附于神学和形而上学,但却面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难题。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似乎原本就存在着矛盾。通常我们说,伦理学以自由为前提,但当我们以形而上学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时,只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因”,人的自由仍然是难以解释的。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人的自由仍然是问题,伦理学似乎失去了基础。就此而论,当我们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参照系。
关于形而上学,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使用一些相近的概念。ontologia(英文为ontology)是17世纪经院哲学家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而生造的概念,过去译作“本体论”,按其本义则应译作“存在论”,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了。不过,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例如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通常被区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关系,他声称此前的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也就是说,此前的ontology打着“存在论”的旗号而实际上并没有思存在——所以我们没有改变以往“本体论”的翻译,只是把海德格尔的ontology译作了“存在论”。这不仅是因为语境不同,也有义理上的区别。总之,不得已而为之。
伦理学关涉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以及人与更高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虽然伦理(希腊语ethos)与“道德”(拉丁语moralis)均由“风俗习惯”而来,不过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做一些区分:“伦理”偏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道德”则偏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或境界。尽管都是“应该”做什么的准则,伦理规范相对而言属于外在的约束,道德境界则属于内在的理想。当然,这个区分是相对的,伦理规范完全可能内在化而成为人的道德理想。伦理道德在历史上以习俗或宗教为基础,在哲学上则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如果说宗法、宗教和哲学(形而上学)可以看作或者曾经是维系一个文明之统一的整体性价值观念,那么,伦理道德即是这一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它的具体体现。自17世纪以来,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形而上学的衰落,传统观念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生活的现实影响力,伦理学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限制而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至于人们有时称之为“实践哲学的转向”。然而,伦理道德原本是维系文明之统一的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如果伦理学失去了宗法、宗教和形而上学等——我们主要讨论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它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
那么,为什么要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当我们讨论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时候,海德格尔哲学恰恰起了一个凸显其困境的作用。19世纪以后的哲学家在伦理学问题上往往面临着类似于“布里丹的驴子”面对两堆青草时的困境:一边是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另一边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当我们以形而上学作为伦理学的基础的时候,这个基础是“自由因”,而以之为基础的伦理学却无法解释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当我们抛弃形而上学的基础之后,伦理学则面临着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困境。海德格尔试图跳出布里丹驴子的困境,他一方面批判形而上学,但却把存在问题从中拯救了出来,另一方面试图以存在的“尺度”或“秩序”取代人间的“尺度”或“秩序”,不仅没有允诺为伦理学重建基础,甚至当他以存在论作为“源始的伦理学”的时候,实际上取消了通常意义上的伦理学,以至于学者们经常会争论海德格尔哲学有没有抑或可不可以有一种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海德格尔的方式是成功的,不过作为抵御虚无主义的一次(也许是)失败的尝试,却为我们思考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因为它凸显出了当代伦理学的困境。
海德格尔哲学有前后期之分,我们主要关涉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及后期的思想。本文意在呈现伦理学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原本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但由于差不多全世界都走上了西方文明开创的现代化道路,以至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一
在传统上,哲学作为解决终极问题的理论学说通常总是某种整体性的规划或体系,虽然它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分支”或“部分”,例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但一种哲学理论在整体上总是要自洽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主要讨论形而上学问题而没有讨论伦理学问题,但他的理论却不能从中引申出某种自相矛盾的伦理学。原因很简单,就像笛卡尔把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一样——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科学是枝杈和果实——形而上学是为包括伦理学在内的一切知识奠基的。甚至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抛弃了形而上学之后也是如此。他们退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以便为伦理学重新寻求根据。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学派均以某种宇宙论作为伦理学的基础,都主张按照自然的本性生活,只是对自然的本性理解不同。这意味着,在传统哲学中,鉴于人的有限性,伦理学必须以某种形而上学作为基础。
形而上学试图为一切知识奠基,其理想架构体现为目的论的体系,因为它要解答的是终极之问。因此,尽管自公元2世纪以来,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以神学为背景,以绝对超越的上帝为核心的基督教哲学。但是,随着经院哲学的衰落,哲学回归自身,一种更加自洽的形而上学便脱颖而出。对它来说,宇宙是自成因果的:“作为原因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与“作为结果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是一个自然——自然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自己是自己的结果——这就是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然而,问题是:尽管近代哲学淡化了上帝的绝对超越性,但人却仍然只是宇宙的结果,而不是宇宙的原因。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能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因,除此之外都是它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实体的自由(实体即自因),却无法解释人的自由;而人如果没有自由,伦理学也就无从谈起。人的有限性意味着他的存在需要更高的基础和根据,安身立命的规矩不是由他自己制订的:他不是受自然法则的限制,就是受形而上学基础的制约。因此,人因为有限性而没有自由,即便哲学家们为人的有限存在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他仍然因为受制于这个基础而不是自由的。这个问题曾经以绝对超越的上帝与人的意志自由之间的矛盾而苦恼过教父哲学时代的奥古斯丁,同样也困扰着此后的形而上学家。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体现出其哲学的根本诉求:本体论是基础,认识论是通达这一基础的方式,而通达此基础的目的则是为了给人确立安身立命的根据。
斯宾诺莎以实体即自因作为基本原则,视思想与广延为实体的两个本质属性,万物皆为实体之属性的“分殊”,从而为伦理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一方面与因果律相关的“实体即自因”自身包含着矛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之第三组二律背反揭示的就是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只有实体是自因的,世间万物都由于“在他物内通过他物而被认知的东西”而隶属于因果法则,人之自由则要通过认识神的方式来实现,而“神”对斯宾诺莎来说不过是神圣的自然必然性,由此就有了“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说法。然而,按照康德,试图通过认识通达自由境界是不可能的,因为认识所能通达的只是必然性。所以,在斯宾诺莎哲学中仍然存在着自由与必然、实体与样式之间的矛盾。黑格尔以“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来弥补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缺陷,以实体自身就具有能动性(主体性)来解释“作为原因的自然”如何自我运动、自我实现为“作为结果的自然”,把宇宙解释为一个自己完成自己的目的论体系。同时,黑格尔试图消除主客二元论,他以人类精神作为绝对精神的体现,由此把必然与自由统一了起来:宇宙是一个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目的论的“圆圈”,所有的结果原初就蕴含在开端之中,一切都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实体即主体,宇宙的生成乃是自我完成的,所以又是实现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将人类精神看作绝对精神的“代言人”,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归根结底乃是绝对精神认识自己的过程,因而世界历史是自由的实现过程。看起来,黑格尔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以及自由与必然统一了起来,但实际上人类精神不过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工具。
讨论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在古典哲学中,康德或许是唯一充分意识到了、也揭示出了、并且试图解决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矛盾的哲学家,他独树一帜,不再考虑以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而是以伦理学为基础为形而上学寻求出路。
形而上学一向以科学乃至最高的科学自居,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必须通过认识论的方式,这注定了形而上学与其理想背道而驰的命运。按照康德,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不满足于自身的有限性,试图超越自身通达无限永恒的自由境界的理想,而科学则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且不论形而上学因其对象的超越性而不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即便它能够成为科学也不可能为伦理学奠基。因为它达到的是必然,而伦理学的基础必须是自由。因此,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是不能兼容的,以科学自居的形而上学也是如此。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康德需要做两方面的“协调”:一方面需要协调自由与必然,另一方面需要协调人类理性与纯粹理性;前者相关于道德与科学,后者相关于伦理学与形而上学。这两方面的协调集中于一点:道德法则乃理性之自律。就其面临的哲学问题而论,康德既要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同时还要证明人的自由,并且为之提供形而上学的根据,他的解决方式是倒转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承认自然界服从于严格的自然法则的前提下,仍然认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可以有自由的?康德的回答是: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由于他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认识事物,因而他的认识能力既是认识的条件,也是认识的限制。这一条件作为“先天认识形式”可以保证我们关于事物的经验所形成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但不可能认识事物自身。虽然如此,从逻辑上我们必须以这个超越了认识能力的事物自身作为认识的前提条件,而这意味着某种无条件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从而自由是可以设想的。康德称之为“先验的自由”,这便为一种伦理学提供了可能性。由于这个“先验的自由”是由不可知论引出的结果,因而康德采取了“绕圈子”的方式,以“先验的自由”为伦理学提供了可能性,再通过证明道德法则来印证自由的现实性,康德称之为“实践的自由”。看起来,康德把自由与必然统一了起来,自由即自律,道德法则与自由是一回事,但实际上康德仍然无法避免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关系的难题。首先,道德法则出于理性自律,但这里的理性并不就是人类理性,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因而康德实际上还要为人类理性寻求更高的根据。其次,对康德来说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它不依赖于神学,也不需要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但是,道德法则仅与实践理性有关,它影响的是行为的动机。行为一旦做出就不再由道德法则决定,而是受自然法则的制约。正如理论理性的自然法则不能僭越到实践理性的领域一样,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也不能超越自己的界限去决定道德行为的实现,唯有超越的上帝才有可能协调这两个领域的一致性。因此,不仅实践理性需要“公设”,而且就康德哲学之整体而言,亦最终指向了一种道德神学。或许对启蒙主义的反思使康德意识到了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伦理学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有面临崩溃的危险,但作为古典哲学家的康德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宣称“上帝死了”。在康德哲学中,没有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道德,但却需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神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康德哲学出发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但每一条道路似乎都指向了形而上学的终结:黑格尔把康德的人类理性与纯粹理性合而为一,视人类精神为绝对精神的现实化;尼采则倒转了柏拉图主义,类似将康德的纯粹理性还原为人类理性,主张以“超人”重估一切价值。所以,海德格尔把黑格尔和尼采都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并且称尼采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由此可见,在古典哲学中,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下面,我们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进一步讨论形而上学衰落之后伦理学面临的困境。
二
所谓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就是借助于海德格尔哲学来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就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海德格尔解决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的思考凸显了伦理学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难题。
古典哲学的主流是形而上学,但现代哲学一般而言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样是批判形而上学,英美分析哲学一脉强调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海德格尔强调的却是形而上学太科学了,或者说由于形而上学像自然科学对待自然存在物一样对待存在,因而表面上看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的,但实际上研究的是存在物,故而始终与存在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遗忘”。如果形而上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那么,所有的科学包括伦理学都建立在“遗忘存在”的基础之上。所以,海德格尔致力于将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对于现代哲学的“主流”来说,形而上学的衰落意味着伦理学摆脱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限制,而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则意味着要以某种非形而上学的方式重思存在。仅就早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而论,他试图以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建“基础存在论”而为一切存在论奠基,于是也就关涉了伦理学与存在论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存在论原本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但按照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从来就不是存在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海德格尔准备以存在论为伦理学重建基础?回答是否定的:他不是要让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是要让伦理学回归存在论。不甚恰当地说,其结果实际上取消了伦理学。
伦理学关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关涉人世间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境界,而“意义”和“价值”便涉及了“意义世界”的问题。或者说,伦理学的意义建立在世界的意义的基础上。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致力于为我们面前的世界提供意义的证明。哲学家们通常是用一个完美的本质世界为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提供基础和根据,这意味着一切意义(包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均来源于一个超感性的本质世界。换言之,“人间的秩序”(现实世界)源于“天上的秩序”(理想世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这个理想世界亦崩溃了。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启发下致力于克服传统哲学主客二元论的痼疾,反对仅仅从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把存在当作理性认识的对象,主张从人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更加本源的生存活动出发去“显现”存在。世间万物中唯独人这种存在者居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它是始终处在“去存在”之中的在者,因而存在(Sein)能够在此(da)存在出来,这就是人之为此在(Dasein)的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世界的意义不是通过思想来把握的,而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而生成的。所以,同样是zu sein(to be),在形而上学那里是“是什么”的范畴,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则是“去存在”的生存论规定。换言之,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范畴体系其实是关于存在者“是什么”的规定,而存在本身则需要此在“去存在”的“生存论规定”来显现。
不过,海德格尔关于意义世界的生存论规定只是揭示了生存实情,并不见得给世界提供了某种合理性的证明。恰恰相反,这个意义世界一向处在“沉沦状态”。《存在与时间》从“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生存论的整体现象入手分析此在的存在即生存(Existenz),最终将生存的整体性规定为“操心”(Sorge)。操心的结构为生存、被抛和沉沦。这意味着,此在是始终处在去存在之中的(生存)、被抛入可能性境域的、逃避自己的能在而沉沦在世的在者。此在虽然是“去存在”的在者,但“去存在”意味着此在必须面对可能性自己去筹划选择,并为此承担责任。于是,“去存在”之生存便成了此在不能承受的重负,它不愿意自己去存在,而宁愿把自己的存在交付给“他人”,亦即“常人”,这就是此在的“沉沦”(Verfallen)。所以,此在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意义世界是一个由闲言、好奇与两可组建起来的常人世界。这就是说,此在作为“自由-能在”的在者实际上并没有自己去存在,这种非本真的状态构成了此在生存的常态。那么,既然这是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为什么说这种状态是非本真的呢?按照海德格尔,恰恰唯有能自己去存在的此在这种在者能够不自己去存在。更重要的是,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常人“查无此人”且“从无此人”。换言之,此在实际上是以自欺的方式生存在世,而所谓沉沦就是此在“从自身脱落到自身”——归根结底还是此在自己在生存。于是,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让此在立足自身而在世,勇敢地承担起让存在显现的重任。因此,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了存在,在此在这里有其根源,因为此在一向在逃避自己的存在。当然,此在无论如何也是存在者,如何让它面向可能性,乃至于把自己当作可能性便成了问题。就此而论,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时间观。此在之生存以时间性为结构,生存论的时间不是以现在为核心的线性流逝,而是以将来为核心的立体结构。将来(Zukunft)不是“去远”而是“来临”,所以此在的生存不是消融于未知中,而是把可能性收回到自身来。如此这般,此在便能够始终保持自身为可能性的整体能在。
问题是:是不是如此一来存在问题就得到解决了?非也。《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后海德格尔便陷入了困境,他终于明确了自己的思想——无论此在本真地在世还是非本真地在世,通过它的生存活动而显现的存在都不过是此在的存在,还不是存在本身。此在居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它的生存活动既是对存在的显现,也是对存在的遮蔽,但我们只能通过揭示或解蔽的方式去接近不显现的存在。困难之处在于:如果一切存在者存在着,那么存在本身便“不存在”,当存在本质性地现身(wesen)之际,存在者存在出来了,存在自身则蔽而不显。因此,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之“元基础”(Urgrund),对我们来说却是“离基深渊”(Abgrund)。居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此在实际上只能“察觉”到存在者这一边,另一边相当于虚无。因此,海德格尔把惊异于存在者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看作哲学的“第一开端”,而把对于存在不存在(无)的惊恐看作“另一开端”。他倡导跃入深渊去测度存在:“对于基础的探基必须冒险一跳,跃入离-基深渊之中,必须去测度和经受住离-基深渊本身。”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并没有解决伦理学的基础问题,而是激化了问题。
首先,大多数现代哲学家以“形而上学不是科学”来拒斥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则强调,恰恰是因为形而上学太科学了,所以不可能回答存在问题。按照康德,如果形而上学是科学,它就不可能为伦理学提供基础,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伦理学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在科学不能解决自由问题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和康德是一致的,但海德格尔的自由与康德的自由是不同的。此在被抛入可能性的境域,它是去存在的能在,因而此在是自由的。但是,此在的自由源于存在,所以此在的自由并不是人的自由,它是存在论的自由、生存论的自由,不是伦理学的自由。
其次,形而上学的衰落激发了某种人道主义的潮流,海德格尔对此深感忧虑。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借助于尼采来反思形而上学问题,他称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尼采自称是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他通过从根本上取消超感性世界而肯定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感性世界,主张以往哲学家们归之于存在或超感性世界的所有意义原本都属于感性世界。当费尔巴哈把宗教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时候,他的思路和尼采是一致的。人们把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异化为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学理想,其结果就是理想世界是富有的、现实世界是贫穷的。海德格尔认同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但他认为,当尼采试图把归于超感性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还给感性世界时,他与形而上学一样都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的。就此而论,海德格尔既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以存在为伦理学提供基础,也不可能像尼采那样以“超人”为现实社会立规矩,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为伦理学提供基础的打算。在海德格尔这里,有存在论,没有伦理学。
再次,伦理学通常是为现实生活提供伦理规范和道德境界的,它解决的是人的问题。但在海德格尔眼中,由闲言、好奇和两可组建的现实生活乃是由“公众舆论”控制的沉沦世界。闲言无所不说,好奇无所不看,穷尽了一切可能性,使我们的生活一向处在两可之中,看似日新月异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海德格尔对日常生活的生存论分析就是要揭示此在的生存论机制,破除所有的规范,让每个此在立足自身而在世。这样的存在论——如果有这样的存在论的话——是不可能为现实社会“背书”的。与此相关,海德格尔看起来批判现代性,但同时也是反传统的,他将此在之去存在指向了将来的无限可能性,却又与现代性殊途同归,窃以为这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吊诡之处。或许施特劳斯坚持要回归古典传统,有他自己的道理。
最后,就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来说,很难想象存在如何能够为任何一种伦理学奠基。哲学诞生于希腊人走出神话和宗教而以思想照亮世界,以存在为认识对象的形而上学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概念思维被黑格尔看作是把握绝对精神的最高的认识方式。但是,海德格尔眼中的存在却是虚无的深渊。所以,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了存在,归根结底在于此在本能地在逃避存在。在《存在与时间》中,此在在情绪中现身,尤其是在最极端的情绪“畏”(Angst)中现身。畏启示着无,此在在畏中意识到,我存在且不得不存在,乃至于不得不能在,被嵌入到无的背景中,被逼回自身。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更多地强调存在在现身为存在者之际自身不在,因而存在作为存在者的基础相当于离基-深渊。无论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还是从虚无-深渊的角度,都难以设想一种伦理学。
所以,海德格尔并不是要为伦理学奠基,他思考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西方文明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他的“源始的伦理学”是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
三
如前所述,我们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因为在古典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主流,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这个基础当然是成问题的,不过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理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是伦理学的基础是什么。
伦理学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其地位和意义越来越突出。人诞生于社会性的生存方式,伦理道德源于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维系某个社会群体的准则,这些准则往往扎根于原始宗教、神话和宗法秩序,构成了维系人之社会存在的统一性的纽带。就此而论,套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伦理道德实际上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不过,随着人类相互之间交往的扩大,社会性的群体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到超越氏族的民族,从单一民族而形成多民族的文明,及至今天,超越不同文明而形成全球性的“地球村”,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适应于某一民族和文明的“风俗习惯”就不够用了,必须有世界性的宗教或伦理道德才能在政治治理的统治方式之外形成具有凝聚人心的统一性纽带。因此,虽然伦理道德通常是“地方性的知识”,但是这种“地方性”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当伦理学以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它所寻求的不能是“地方性的知识”,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则。过去,这一道德法则以宗教或形而上学为基础。随着宗教和形而上学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伦理学的作用和地位便越来越突出了,甚至有“实践哲学的转向”的说法。但这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跳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
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准确地说是西方哲学的产物。哲学作为对真理的追求,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地方性知识”,它要获得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应该说,没有哲学对知识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后来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问题是:哲学家们如何能够超越个人乃至西方文化而作为人类理性或人类精神的“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通过思想的抽象来通达普遍性的。所以,伦理道德源于风俗习惯,但伦理学却必须超越风俗习惯,获得普遍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法则。问题在于:在古典哲学中,这种普遍性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伦理学便不得不面对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难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伦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是近代以后的事。通常维系文明的价值观念均与宗教或带有宗教性的意识形态有关,哲学则属于极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其影响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即使在哲学的诞生地希腊也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发生。近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价值才越发受到重视。在西方文明中,哲学寻求的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因而不仅超越了个人的意见,而且超越了群体乃至文明的局限,虽然它也是或者说曾经是“地方性的知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具有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可以抽象出规律和法则,所以社会现象有没有普遍的规律一向是成问题的。但是,既然伦理学要成为知识或者科学,它就不能仅仅是“地方性的知识”,人们一定会在社会现象中寻求普遍性的东西。其实,既然同属于“人类”,都具有社会性的生存方式,不同文明就会有一些相同的伦理规范,例如做人要诚实,不应该说谎。甚至还形成了一些被称为“金律”的准则,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箴言,拉丁谚语quod tibi non vis fieri通常就译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伦理学寻求的是可以经得起理性证明和质疑的普遍法则,而不是看起来有道理的格言警句。换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和根据。所以,在古典哲学中,伦理学一方面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同样需要认识论的证明。
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是轴心时代没落的一部分,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相继构建了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核心理念。其中,印度、伊朗和巴勒斯坦形成的观念是宗教性的,只有希腊人创制了哲学,中国的诸子百家则是类似半哲学半宗教的思想。随着宗教逐渐弱化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哲学因为与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形而上学衰落的背景下,伦理学的基础问题越发凸显了出来。
我们讨论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矛盾,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通常的伦理学之间的冲突。就此而论,前者说明了形而上学不能为伦理学奠基,后者表明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不仅不能抵御虚无主义的威胁,而且有陷入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危险。于是,我们就像布里丹的驴子面对两堆青草那样陷入了困境:要么是绝对主义,要么是相对主义;要么回到过去的传统,要么面对不确定的未来。B.威廉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的序言中说:“我的结论是,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求是没有前例的,而大一半当代道德哲学所体现的那些理性观念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然而,古代思想的某些方面,若加以相当的改造,却有可能满足这些需求。”在我看来,古代思想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尚不得知,但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求没有前例则情况属实。自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几乎全世界都在西方文明的引导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发生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意味着,轴心时代维系各大文明的价值观念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影响力,存在、实体、真理、上帝、天、道……这些曾经构成了各大文明之最高的绝对价值相继陨落。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极端矛盾的现实:一方面是经济市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所有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碰撞到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伦理学有更高的要求。虽然全球化在今天遭遇挫折,但我们生活在连成一个整体的地球村已经成为事实的时代,我们却似乎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某一个社会群体自身内部可以由伦理规范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者说在不同国家之间,却仍然奉行着“丛林法则”,这当然不是构建某种统一的伦理规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反过来说,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伦理规范。显然,各大文明的传统观念随着全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失去了现实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即便能够返本开新,但它们都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如何让它们成为地球村的普遍共识,跨越文化之间的屏障呢?不过,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伦理学因为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反而有了用武之地,这就是威廉斯所说的: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求是没有前例的。
的确,面对当今时代的种种问题,伦理学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仅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伦理学首先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既然古典哲学以“天上的秩序”(理想世界)为“人间的秩序”(现实世界)奠基的方式失效了,立足“人间的秩序”又面临着文化之间的隔阂与相对主义的困境,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不再考虑最高的普遍法则,而是先来确立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共存的“底线”。不错,时至今日,全球化遭遇挫折,但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退回到从前了,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瘟疫……所有这些都唯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或许,形成某种能够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核心理念还有待来日,这需要各个文明共同参与构建新的轴心时代的价值理念。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走出“丛林”,形成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和平共存相互交往的基本规则。
在我们这个时代,伦理学需要做很多事,伦理学可以做很多事。
原文来源:道德与文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UoQvFAt0lj-7-O-SAY9Aw
编辑:刘佳莹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4-25 15:14
【案例】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作者简介:夏永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哲学国际中心副研究员(广东珠海 519087)。
〔摘要〕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关键词〕道德能动者 人工智能 机器伦理 理智主义 框架问题
导 言
为克服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有必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一个道德能动者(moral agent)。然而,除非人工智能成为道德大师(moral master),即它的道德表现达到人类的顶尖水准,否则我们并不会放心地将道德决策转交给它。因此,相比于如何让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我们更应关心它如何成为道德大师。关于前者,国内外已有大量讨论,但关于后者仍鲜有论述。实际上,这是两个逻辑上正交的问题。一个机器人可以缺乏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的先决条件,比如意向性、意识、责任性与自由意志等,但却可能做出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完美决策。同样,即便一个机器人满足所有道德能动性的条件,却可构想它实际做出的道德决策不尽如人意。
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道德发展潜力表示乐观。因为人类道德决策总会被各种偏见、情绪或私利所污染,而机器由于没有人类的这些弱点,只要它掌握了正确的道德知识和规则,其道德决策将更为公正、无私、理性和融贯。所以,人类总是不可避免地作恶,机器人却可以成为道德大师。这种观点一方面反映了元伦理学上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即把道德知识视为可被显性表达的命题知识(know-that),把道德决策视为基于显性道德知识的理性推理,而无关情绪、直觉与习惯;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机器伦理中瓦拉赫和艾伦所说的自上而下方案,它试图仅仅依赖基于规则的推理而把任务分解为一系列可计算的亚任务,最终实现实践推理和道德决策。
但从与之对立的立场来看,人工智能恰恰极为缺乏道德发展潜力。元伦理学中的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认为,道德知识更多是一种技能知识(know-how),成熟的道德决策不可避免地会诉诸情绪、直觉和习惯,而非仅仅诉诸基于规则的实践推理。与之对应的自下而上进路,则试图通过不断试错的演化或学习来接近某种期望的表现,通过非理智因素引导的行动来模拟人类水平的道德行为。由此可以做出相反的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相比并无先天的道德优势,因为它在决策和行动上需要模拟人类的非理智因素——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恰恰难于此道。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两种机器伦理进路分别绑定了不同的元伦理学,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技术前景,显然可以为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的争论提供经验证据乃至理论判决;反过来,对两种元伦理学立场的探究,也可以为我们揭示机器伦理研究的方向和限度。本文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人工智能可否成为道德大师的探究,实现一种机器伦理与元伦理学的双向启蒙(mutual enlightenment),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morality)的本性。为此,本文将首先梳理反理智主义与理智主义在人工智能和伦理学史上的分途;然后基于对相关案例的考察,分析两种进路在机器伦理中所面临的困境,重估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争;最后,本文将基于认知科学中的相关论述,从正面阐述道德大师是如何做出道德决策的,最终回答这一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道德大师?
一、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的分野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器伦理进路在工程学中分别体现为符号主义和非符号主义(包括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强化学习、统计学习和行为主义等),二者的差异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表征模式的差异。符号主义采用了符号表征,通过任意的原子符号及其所构成的符号表达式来表征世界状态,而非符号主义则要么完全反对表征的作用,比如布鲁克斯的情境机器人学,要么采取了替代的表征概念,比如联结主义的分布式表征。其二是对环境的响应和决策过程的差异。符号主义通过对世界模型的计算来规划行动,它遵循着“感知-模型-规划-行动”的程序;而非符号主义既不建立世界模型,也不预先植入的显性规则,而是通过演化和学习中获得的行为趋向来实现对环境的恰当响应。
两种人工智能进路背后包含了不同的哲学预设。德雷福斯指出,符号主义预设了笛卡尔以来的理智主义。它隐含了一套知识论和本体论假设,前者认为一切知识都可以形式化为以逻辑关系来表达的事实集合,后者主张存在是离散的事实的集合,它们以特定的逻辑或数学规则组合起来。这些观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并贯穿了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到逻辑实证主义的漫长哲学传统,最终构成了经典人工智能的前提预设。它意味着人的心灵是一种依据逻辑规则对原子命题做计算操作的符号装置。与之相反,非符号主义则与反理智主义哲学传统若合符节。在德雷福斯看来,神经网络抛弃了符号主义中的意义原子论的假定,更加倾向于“整体论”或“格式塔”的观念,并可能证明“海德格尔、晚期维特根斯坦和罗森布拉特认为智能行为并不需要关于世界的理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强化学习响应了梅洛-庞蒂关于技能学习的观点。能动者根据奖励反馈对自身行为趋向的调整,表现了一种对行动过程的好和坏、成功和失败的感觉,这类似于梅洛-庞蒂所说的平衡感(sense of equilibrium)。正是它指导着一个能动者对不同情境的熟练应对,而无须表征世界和规划行动。
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分野,同样存在于伦理学的悠久历史中。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一种理智主义的道德哲学。他的论题“美德就是知识”意味着美德是一种可以被显性表达的知识,具有知识就是具有美德。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则开创了一种反理智主义的伦理学。其一,他不再直接将美德的养成等同于知识的习得,而是明确区分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前者可以通过教导而习得,而后者只能诉诸习惯的养成;其二,他更多地将道德德性视为一种技艺而非可表达的知识,认为只有在德性的应用中才能获得德性。这意味着道德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技能知识而不是命题知识。
近代以来,理智主义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无论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都把道德决策视为形式合理性范围内的慎思(deliberation)活动,也就是通过合理的手段以达到某种合理的目标。总之,它们都是通过某种程序来规定实践理性。功利主义将其视为快乐最大化的计算,而康德主义的义务论则视之为可普遍化的程序。正如德雷福斯所言,这种进路的共同特征是倾向于关注显性道德规则的选择、责任和证成,而忽视了日常伦理行为中非反思的情景应对。
与此相反,黑格尔和查尔斯·泰勒等哲学家呈现了另一种伦理学。黑格尔指责康德混淆了道德与伦理,前者是在主体反思中呈现的抽象规定,以及决定这些规定的原则,而后者则表现为个人的风尚和习惯。因此,道德和伦理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道德知识,前者是抽象的规则,而后者则更多的是默会的技能。黑格尔赋予伦理比道德更高的位置,这意味着他将技能知识置于比命题知识更高的地位。沿着黑格尔的足迹,泰勒反驳了理智主义的知识论,重申了技能对于人类实践理解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理智主义将人类行动描述为一个遵守作为表征的显性规则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依赖于对行动背景的隐性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根源于我们的身体性的技能知识,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身体惯习。
由此可见,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分野不仅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机器伦理的对峙,而且界定了伦理学史上关于道德决策和道德知识的两种研究传统。自上而下方案试图通过在计算机中将道德规则以显性的方式编码,从而让人工能动者像计算机执行程序那样通过规则和推理来进行道德决策,这与理智主义伦理学是一致的。而自下而上进路则试图通过演化和学习让人工能动者可以灵活响应复杂的情境,无须预先编码的显性规则,这恰恰契合了反理智主义伦理学。正是由于任何一种机器伦理进路必然预设了某种元伦理学,通过检视不同进路的机器伦理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实际上可以为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争提供一个判决性检验。
二、自上而下方案的先天限制
理智主义和自上而下方案似乎是实现人工道德能动者最自然的方案,因为计算机更擅长基于推理和逻辑的行动规划,而人类却很难如此深思熟虑地行动。然而这样的期盼并不符合现实,迄今为止,自上而下方案还未建造出完全意义上的人工道德能动者。根据吉普斯(James Gips)的观点,一个功利主义的道德能动者的任务是找到一种产生最佳情境的行动,为此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可以描述世界中的情境;
(2)可以生成可能的行动;
(3)当一个行动作用于当下的情境,可以预测情境的变化;
(4)可以根据善好或可欲性评估情境。
吉普斯的上述四个条件实际上规定的是行为功利主义能动者,但对于规则功利主义能动者和义务论能动者,则不需要预见行动的后果或预测情境的变化——因此无须满足条件(3),并且选择可能行动的道德标准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补充以下两个条件:
(5)根据可带来好的后果的规则来选择可能的行动;
(6)可以根据相关的义务原则评估可能的行动。
当一个能动者同时满足(1)(2)(3)和(4),它就是一个行为功利主义能动者;同时满足(1)(2)和(5),它就是一个规则功利主义能动者;当一个能动者同时满足(1)(2)和(6),它就是一个义务论能动者。
那么,目前的道德决策程序是否满足以上条件呢?以下将以M.安德森和S.安德森开发的两个人工道德能动者Jeremy和W.D.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Jeremy基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行为功利主义理论。边沁主张对任何行动的评价,都应该基于它是否会增进或减小利益相关者的快乐。换言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道德决策的最终标准。边沁认为快乐或痛苦是可以被量化的,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计算不同可选行动的后果所带来的快乐净值,最终选择快乐净值最大的行动。Jeremy从边沁的道德算术中汲取了灵感,它的运作基于这样一个公式:
总和快乐净值=Σ(强度×持久度×概率)
任何一种行动对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快乐净值,与快乐强度、持久度和(产生这种快乐的)概率等三个量成正比,而总和快乐净值,就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快乐净值的总和。Jeremy需要用户输入对一项可能行动带来的快乐强度的估值,它根据快乐程度划分为五个值(-2,-1,0,1,2),并且划分了带来快乐的三个概率。完成后,Jeremy就可以执行严格的道德算术。
相比于功利主义模型,安德森夫妇更青睐义务论能动者W.D.。义务论的道德决策不再仅仅基于对后果的考察,而更多地考虑行为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 W.D.的道德决策基于罗斯(W.D. Ross)提出的七条基本义务:忠诚(fidelity)、补偿(reparation)、感激(gratitude)、正义(justice)、行善(beneficence)、无害(non-maleficence)和自我提升(self-improvement)。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特殊情境下会相互冲突。为此,安德森夫妇引入了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来作为道德决策的程序。这一方法基于主体的道德直觉,从特定案例中概括出某种道德原则,然后再用进一步的案例来检验这种道德原则,通过不断重复这一过程,最后发展出一个符合直觉的决策程序。W.D.使用了归纳逻辑规划(inductive logic programming)这种机器学习技术来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较好地学习和表示特定困境中不同义务之间的关系,最终从特定案例中学习道德原则。具体的训练步骤是:训练者描述一个特定行动,并根据道德专家的共识,评估它对每条义务的满足或违反程度,从绝对满足到绝对违反划分为五个分值,即(2,1,0,-1,-2),而当训练者输入足够完备的案例之后,机器学习模型就可以从中发展出普遍的伦理原则,在遇到新的案例时,就可以据此做出正确的道德决策。
以上两种程序都试图数量化道德案例的伦理价值,并通过特定的算法来最终做出决策。其中,Jeremy并没有满足一个行为功利主义能动者的标准。它无法表征世界的情境,做出自主的行动规划,也无法预知每一个可能行动的后果;尤其是,它对可能行动的伦理评估不是完全自主的,严重依赖于人类的量化评估。就此而言,它非但没有满足条件(1)(2)和(3),甚至没有满足条件(4)。而W.D.在经过训练后可以自主地进行伦理评估,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条件(6)。然而,由于W.D.并没有配置行动规划程序,它也没有满足条件(1)和(2),不能算作一个完全的义务论能动者。
有人或许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上的不断改进,最终建造出满足所有条件的功利主义或义务论能动者。然而,首先要回答的是,建造两种能动者是否类似于发明永动机或炼金术之类的目标?
我们首先来分析二者都需要满足的条件(1)(2)和(3),即描述世界中的情境,生成可能的行动,预知行动的后果。这属于人工智能中的行动规划问题,它需要用符号逻辑来刻画能动者及环境因素的行动的表征,并根据这些表征来进行推理。在开放场景下,这会面临著名的框架问题(the frame problem)。能动者需要基于对世界的表征而做出行动规划,当一个行动作用于世界时会引发相应的后果,世界表征也需要相应地更新。由于计算机缺乏相关的常识,难以判定世界中的哪些事物会随之改变,哪些事物不会随之改变,这样就需要对行动的后果进行全盘的计算,从而远超计算机的计算负载。于是,如何让能动者只表征行动的后果,却无须表征大量的非行动后果,就成为一个难题。虽然在一个简单的积木世界中,可以设置各种框架公理来描述一个行动后的情境变化,暂时地让能动者免于框架问题。然而,只能在积木世界中行动的能动者往往没有应用价值,这也正是如今各种专家系统的瓶颈所在。对于一个道德成熟的道德能动者而言,它所应对的是一个日常的开放世界,可能的行动、行动的后果、所处的情境、相关的常识其数量都潜在地是无限的,框架公理的数量也将趋于无限。于是,框架问题就成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屏障,条件(1)(2)和(3)也几乎无法满足。
为满足条件(4)(5)或(6),即判断可能行动是否符合特定的道德规则,需要存取大量相关的道德常识以做出正确的评估,而这又会面临同样棘手的常识问题(the commonsense knowledge problem),即“如何存储和访问人类似乎知道的所有事实”。常识是人类日常所需知道的一系列事实和知识;机器要理解自然语言或做出明智的行动决策,同样也必须根据常识做出推理和规划。在大多数情境下,道德原则需要被能动者做出解释之后才能应用于道德推理,这就需要一种把具体情境和抽象道德原则联系起来的常识。比如在情境“我看到一个老人倒在地上”与道德原则“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人”之间,就需要“把摔倒的老人扶起来是在帮助它”这样的相关常识。一个成熟的道德能动者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下做出道德决策,其所需要的相关常识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即便我们能穷尽这些常识并将其形式化,计算机如何快速有效地存取相关常识以做出道德推理,同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由于常识问题的存在,在开放场景下条件(4)(5)或(6)难以满足。
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都难以通过改进算法而得以解决。任何人工智能都只是一个资源约束下的有限理性能动者,但在符号主义框架下,建造一个成熟的道德能动者却需要几乎无限的计算资源。虽然正如符号主义的代表司马贺(Herbert A.Simon)所指出的,人类理性也同样是一种资源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不可能知道所有可能行动及其可能后果,但人类的行动恰恰并不会遵循符号主义的决策过程——对此本文最后一节将会详述,所以才能凭借有限理性而应对无限复杂的情境。因此,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实际上为符号主义划定了一个先天限制,即它根本无法在日常复杂世界中做出道德决策,这不仅意味着自上而下方案的破产,而且构成了对理智主义伦理学的有力反驳。
三、自下而上方案的后天限制
理智主义试图通过规则和事实来刻画道德,而反理智主义则认为道德是在能动者的演化历史和文化适应过程中突现出来的。后者与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若合符节。在种系发生(phylogenetic)层次上,道德起源于人类在狩猎和采集等觅食活动中的合作策略,个体之间的亲社会和合作互动逐渐在群体水平上发展出了完备的道德规范;在个体发生(ontogenetic)层次上,道德起源于从婴儿期开始的协作交互活动,之后逐渐形成了互惠与共享的行为习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互动的深化,人类开始理解和内化社会规范,逐渐成为完全的道德能动者。因此道德规范在根本上并非一种显性的、被约定的规则,而是一些基本的交互习性与技能。要创造人类水平的道德,最好自下而上地模拟道德能动者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学习过程,这也正是自下而上进路的要旨。在工程学层面,它或者采取了人工生命路线,采用人工智能中遗传算法和具身认知的方案,强调能动者与一个虚拟或现实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或者采取神经网络学习路线,通过对大量人类决策样本数据的学习,来生成一个泛化的决策模型以应对新的情境。以下将分别对两种路线的代表性工作进行分析。
人工生命路线以丹尼尔森(PeterDanielson)为代表。丹尼尔森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造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的具备读心术的人工能动者,通过对能动者之间合作与背叛的博弈过程的分析,他展示了这样一种结果,那些最成功的博弈者,是采取特定合作策略的能动者,而非直接追求私利的背叛者。虽然丹尼尔森的主要旨趣在于消除道德与合理性(rationality)之间的对立,但也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通过人工生命的手段来实现一种最小道德(minimal morality)。
机器学习路线则大多采取了强化学习或联结主义的方案。瓜里尼(Marcello Guarini)设计了一个名为道德案例分类器(The MoralCase Classifier)的人工神经网络,以对各种不同的道德情境进行分类。它包含了8个输入单元、24个隐藏单元、1个输出单元和24个语境单元,其中每一个隐藏单元都分别联结着1个输入单元和1个语境单元。每一个案例都包含了五类特征,即两个可能的能动者、两种可能行动、两个可能受动者、五种可能动机和五种可能后果。每一个案例都是五类特征的组合,比如“为了保护无辜者(动机),杰克(能动者)杀了(行动)吉姆(受者),最后让很多无辜者幸存了下来(后果)”。8个输入单元的组合被用来刻画这些不同的特征组合构成的案例。输出则分为道德上被允许的(1)和不确定的(0)以及不被允许的(-1)。通过给定一整套在道德上已经由人类做出判断的案例,构成训练集和测试集,这些神经网络经过训练集的训练之后,再经过测试数据的校正,就可以自动地分类那些全新的尚未分类的案例,即对它们做出道德判断。
那么,如何判断以上两种代表路线的成败呢?这种进路由于不必基于规则和常识表征来进行推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建造的能动者可以在世界中像人类一样合理地或熟练地行动。或者因为与之交互的环境是高度限定的,或者因为训练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这些能动者同样也只能在一个积木世界中行动。那么,技术和经验上的改进能否弥补这些缺陷,最终让这些能动者趋近人类能动者呢?自下而上的能动者设计是否像自上而下方案一样面临着不可解的先天限制呢?这需要澄清自下而上地建造一个道德能动者的条件,不过首先需要揭示人类的道德规范性是如何自下而上地发展出来的。
关于道德规范性的自然起源,目前占据主导性的观点是新亚里士多德式伦理自然主义。它认为美德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善(natural goodness)。自然善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动物和植物中的性状或活动,它们可以促进生命的兴旺(flourishing,eudaimonia)。比如“红猫在春天繁殖”这样的陈述,它表示的是一种可以发挥促进生命兴旺的历史作用的活动,这不仅是一个自然事实,而且是一个规范事实。因为一只不在春天繁殖的红猫,将不利于生命的兴旺,因而是有缺陷的。类似这样的陈述就被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称为“自然-历史判断”,它具有如下的逻辑结构,即“S具有/执行F,以便……”。在此,F的功能包括获得有机体的发育、自我保存、繁殖等生物学价值。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试图把道德判断视为一种自然-历史判断,它们共享了同样的逻辑结构。因此,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道德事实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事实,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执行了生物功能的人,这种功能就是为了获得生命的兴旺。那么,如何理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功能概念呢?其实,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呼应了生物学哲学中对生物功能的组织解释,后者认为一个生物性状的功能在于它可以贡献于有机体的自我维持。生命兴旺正是自我维持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规范性的自然基础就是一个具有自我维持的组织功能的有机体。
于是,要自下而上地建造人工道德能动者,就需要创造出具有自我维持的组织功能的人工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引入人工生命的研究,建造具有自我维持的组织功能的能动者。人工生命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进路就是自创生理论——对生物功能的组织解释正是建基于该理论之上。自创生理论用自创生(autopoiesis)、自适应(adaptivity)和参与(participation)等三种生命机制来刻画一个有机体的生物规范性。马图拉纳最早认为生命是一个自创生系统,即一个由各种系统组分的生产网络组合构成的系统,它可以持续地生成和界定自身的组织,从而维持系统的稳态,免于因扰乱而瓦解。在自创生系统中,规范性(或价值与意义)的唯一来源是系统同一性的持存,一种处境只要危及系统同一性的维系,它就是负面的,反之,则是正面的。后来迪保罗进一步认为,自创生仅仅能提供一种全或无(all-or-nothing)的规范,他由此提出了自适应性来作为一种更合理的梯度的(graded)规范性的基础。自适应性是一个鲜活的存在对自身的生存能力的调节,它可以调节有机体的存活条件的范围,从而建立一种更加细密的规范关系。对于更为细密的社会规范而言,德耶格和迪保罗认为能动者之间的协调(coordination)产生了一个耦合的系统,它具有更高层次上的自身的自主性,因而也会像自创生系统一样致力于同一性的自我维持。由此,能动者的相互影响产生了一种联合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而产生了社会认知。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获得和因循规范制序的过程,而且可以反过来塑造和影响制序。道德规范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再创造。
因此,基于前述的分析,道德规范性奠基于人类物种在演化过程中致力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只有一个会死的有机体才能在根本上建立对道德的敏感性。要自下而上地建造道德能动者,就必须首先建造一个具有生命的人工能动者,它必须满足三个先决条件:
(Ⅰ)能动者是一个自创生系统,可以自我产生和维持系统的同一性;
(Ⅱ)能动者是一个自适应系统,可以积极调控自身与开放环境的交互;
(Ⅲ)能动者是一个参与式系统,可以在人类社会中与他者协调和交互。
那么,自下而上方案是否可以满足上述条件呢?显然,条件(Ⅱ)和条件(Ⅲ)确定了能动者需要在一个复杂的开放环境和人类社会中行动,这似乎并不对目前的路线构成限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目前的模型,让它们可以在真实的环境和社会中演化和学习,最终不断逼近人类水平的道德。最为关键的是先决条件(Ⅰ),它同时也是其他两个条件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一切环境调节和社会参与最终都是为了系统同一性的产生和维持,更确切地说,都是为了生命系统的存活。为了满足这一条件,一个道德能动者必须具有它自己的生命。这并不会构成对自下而上方案的先天限制。虽然生命在本质上是不可图灵计算的,任何计算机仿真都无法实现生命,更无法模拟生物的组织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复杂的机械和仿生技术在物理上实现某种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的人工生命。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某种具有自创生和自适应机制的参与式能动者,从而获得某种自主的道德敏感性,在一个能动者社群中产生某种机器道德。因此,包括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在内的一切图灵式计算机在计算复杂性上面临的限制,都不必然构成对人工生命的先天限制,因为它们完全可以以非图灵计算机作为实现载体。当然,这里可能存在一种后天的工程学限制,即建造人工生命的技术难度太高,人工道德能动者也因此难以实现。
然而我们还需要担心另一种限制。既然道德规范性的功能是生命的兴旺,那么不同的生命形式具有不同的组织功能,它的生命结构、活动模式和生存环境都会直接地影响道德规范的内容,不同的物种将产生不同的道德。生命是一种高度具身的存在,不同的实现基质意味着不同的组织和功能,从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道德。最终,人工道德的内容可能与人类道德完全不同乃至相互冲突。虽然道德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存上的冲突,但却必然意味着道德考虑和道德行为上的差异。我们必然无法完全信赖人工道德能动者的道德决策,从而也就无法用它来辅助和替代人类的日常道德决策。因此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自下而上方案还存在着一种后天的规范性限制。
四、道德的认知科学解释
上述的两种机器伦理方案所面临的困境,为元伦理学中的对立进路提供了判决性的证据。根据前述的证据,自上而下方案由于面临着技术上不可解的先天限制,从而证伪了与之绑定的理智主义元伦理学,帮助我们从消极意义上回答道德大师不是什么;自下而上进路虽然面临着工程学和规范性上的后天限制,但由于它不存在先天限制,则为与之绑定的反理智主义元伦理学保留了正确的可能性。以下,我将引入与这种进路相关的联结主义和具身认知科学,从积极意义上评估反理智主义伦理学,最终回答道德大师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认知科学不仅颠覆了以往的符号主义认知科学,在丘奇兰德(Paul M. Churchland)看来,它甚至可以为道德提供一种科学的解释。联结主义把认知架构刻画为一个神经网络而非符号加工装置,它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构成,每一个神经层都由大量的神经元及其联结构成。基于这一架构,认知能力本质上是大量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联结的配置,而学习过程就是对联结权重的重新调节以产生某种特定的输入-输出函数。由于从感觉输入层到行为输出层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可解释的规则决定从知觉信号到活动信号的加工过程,显性的规则和原子式表征都难以在神经网络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单元。因此,丘奇兰德认为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就意味着获得一个特定技能,因为任何认知能力的训练都是在给输入-输出行为指派某种特定函数。一旦把联结主义的认知和行动模型应用于道德哲学,那么就可以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把道德决策视为一种技能活动。这种技能的获得依赖漫长的训练和学习,而非对规则知识的即刻把握。因此在丘奇兰德看来,绝大多数哲学家对道德的理智主义观点都是错误的。
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观点则在更大强度上支持了反理智主义伦理学。它主张认知并非一种离身的符号加工,而是依赖身体的结构模式和感觉运动能力。作为具身认知的先驱,德雷福斯试图用具身技能的获得过程来解释美德的养成和运作。在他看来,技能的获得分为五个阶段:新手(novice)、老手(advanced beginner)、能手(competence)、高手(proficiency)、专家(expertise)。前三个阶段试图以算计合理性(calculativerationality)的标准将情境分解为语境独立的元素,从而用命题知识的形式去把握技能。但这样的技能不能根据情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应对方式,只能应对简单的情境。只有到了高手阶段,能动者才会更加依赖创造性的直觉而不是算计合理性,从对抽象规则的掌握逐渐过渡到可以应对具体情境。后来,德雷福斯将这种纯粹基于技能知识的应对方式称为熟练应(skillful coping)。德雷福斯认为,这一技能模型可用于分析伦理活动。起初,我们通过遵守严格的规则来学习共同体的伦理;然后,开始应用的是一些语境化的准则;最后,彻底抛开规则做出自发的响应。比如对于诚实这样的美德,最初人们可能会在所有情境下都遵守不撒谎的规则,但当遇到一些复杂情境下的冲突性要求时,就开始寻找一些情境依赖的准则,比如“不要撒谎,除非告知真相可能带来伤害”。对于具有足够经验的道德大师来说,就会抛开所有规则或准则,而仅仅依赖情境来决定是如实告知真相还是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德雷福斯认为,自发的伦理响应并非仅仅涉及简单或熟悉的情境,相反,在复杂的情境下更需要这种基于直觉和经验的熟练应对。在他看来,经验越多,所需的慎思就越少。
因此,从联结主义的认知科学来看,道德决策和行动本质上是非慎思性的技能活动;从具身认知理论来看,伦理技能的获得和提升经历了一个从显性规则到隐 性技能的阶段。总而言之,两种认知科学都支持这一观点,即道德大师的道德决策不是机械地遵守某种规则,而是在道德困境中创造性地采取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行动。机器能动者或许可以通过遵守道德规则而成为道德能动者,但决不能达到道德成熟从而成为道德大师。
结论
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道德大师?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将道德决策完全卸载给人工智能。建造道德能动者的自上而下方案面临在哲学上不可解的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因而存在着先天限制;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但也面临着后天的工程学限制和规范性限制。这些考察结果具有机器伦理和元伦理学的双重含义。在机器伦理领域,这意味着我们难以建造一个人工道德大师;而在元伦理学领域,这意味着理智主义是错误的,但反理智主义却可能是正确的。通过引入联结主义和具身认知理论,可以进一步确证反理智主义的主张:我们不能依靠纯粹的遵守规则的行为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我们才能逐渐获得道德技能,达致道德成熟。因此,成熟的道德决策是一种熟练应对,道德知识是一种技能知识,在这方面,人心胜于机器。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1期
来源:道德与文明
编辑:古凤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4-25 15:21
[案例】
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人类道德决策的可行性研究
作者简介:周 森,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20世纪中叶罗德里克·弗思提出的“理想观察者”的理论模型,为道德增强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可以启发我们设想出一种辅助人类做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形式——“人工智能道德顾问”。它和“理想观察者”之间有着诸多相似性:二者在道德判断中都是无私的、冷静的和坚定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理想观察者”是绝对完美的理论模型,但人工智能道德顾问是相对的、致力于实用的具体工具,它将考虑使用者自身具体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并尊重个体的道德自由、直觉与情感,同时又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反思平衡。因此,人工智能道德顾问能够严肃地回应保守主义对人类道德增强的反对意见,并弥补高技术环境下人类道德能力的不足,帮助人们做出更为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有效地消除技术偏见,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道德领域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道德顾问 理想观察者 道德增强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规训人工智能、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不危害人类道德等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怎样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来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做出有益的贡献,但这方面的进步恰恰是技术最有可能带给我们的。
对新兴技术的警惕几乎是一种历史传统,许多新技术在面世伊始都遭到了哲学家的批评。如柏拉图就曾批评书写技术,认为文字不能像生动而鲜活的对话那样提供真切的智慧,但后来的发展证明:文字并不是对言说的拙劣代替,它发展出了言语所不及的奇特力量,大大增进了人们的交流。柏拉图对技术的批评在两千多年后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响应。海德格尔提出了著名的“座架”概念,十分深刻地剖析了技术对人的异化,他认为计算机以冷冰冰的、僵硬而机械的摩尔斯代码裹挟了人的自然语言,这最终将会带来人类社会的终结。这种技术悲观论影响深远,但历史发展真的如此吗?恰恰相反,计算机技术不但没有泯灭人性,反而以多种多样的实际应用滋养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技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对人的影响并非单向的,人也在根本上左右了技术的发展,将技术在最终应用中变得人性化。
正如海德格尔对计算机技术的过分悲观一样,我们也许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过分忧虑。技术在道德领域总是被视为无用的,“没有自动的道德指南程序”——哈佛大学在宣传人文道德教育时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诚然,道德有着高度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几乎是人类的专利,依靠电脑程序去寻找道德解决方案的设想看起来有点过于激进。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兴技术在与人的需求的反复磨合中,常常会发展出令我们十分欣喜的、意想不到的一些优势。也许人工智能非但不会成为伦理道德的破坏者,反而有希望成为我们的“道德顾问”。20世纪50年代罗德里克·弗思(Roderick Firth)提出的“理想观察者”的理论模型,可以启发我们以人工智能技术创建一位比任何人都更为强大的“道德顾问”。本文将具体说明人工智能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道德决策。
一、问题的提出:高技术环境对人类道德决策能力的挑战
在简单的、朴素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物质用具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所面临的人际网络也没有现在这样庞大,因而,仅仅凭借耳目的直接辨别,我们就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但是,在今天已经开始展现的高技术环境中,我们自身的辨识能力已远远不足以支撑我们做出足够有力的判断。例如,我们很愿意保护环境,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将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时,却不知道做工复杂的杯子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从而难以践行自己的道德原则。类似地,我们非常虔诚地想要保护动物,但是在购买衣物时,往往并没有可靠的设备和足够的时间来鉴别哪些物料来自动物皮毛。在知识的短缺外,情绪对理智的淹没也进一步将我们置于道德决断的窘境之中。比如在社会公共卫生管理中,某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引发的死亡持续而频繁,但即便它们的危害更大,也很难像突然暴发的瘟疫那样吸引公众和政治家的注意力,而在罕见的、突然的大规模死亡面前,人们在情绪的支配下往往反应过激,所做出的道德决策也几乎淹没在情绪里面,理性显得微不足道。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在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有不少个体采取了很多盲目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应对措施。
这些事例表明: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尤其是在资源匮乏或时间有限的紧急情况下,情感和直觉就代替了理智的判断。我们是道德愿景的制定者、信息处理者、道德判断者和行为实践者,但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天然就协调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在道德愿景方面做到满分,树立一个无比崇高的道德目标;但是在信息处理和道德判断方面却严重滞后,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充裕的时间和精确判断的工具,对直觉和情感的控制能力又有限,因而经常摇摆不定,常常被一些错误的情绪所左右。这种缺陷植根于人类古老的遗传信息中,最新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成果也已经证实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和道德判断。此外,人类还是软弱的道德实践者,即便我们已经做出了最佳的道德判断,自身生理的种种状态也可能会妨碍相应的道德行动。比如,虽然我们坚定地反对暴力行为,但某些超出我们主观控制的生理影响(血清素功能低下或低血糖)常常会使我们暴躁易怒,从而不由自主地沦为一个施暴者。因而,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越来越复杂和密集的高技术环境下,人类的道德胜任能力是不足的。
二、人工智能在道德领域的优势
我们常常将自己十分尊敬的人视为“道德导师”,在面对道德问题犹豫不决时,会寻求师长的帮助。那么,在道德领域最为理想的导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早在20世纪中叶,罗德里克·弗思在《伦理绝对主义和理想的观察者》中,夏普(F.C.Sharp)在《善与恶的意志》中都提出了“理想观察者”的设想。他们在理论上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角色,假定其拥有最全面的知识和全部的理性,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道德判断。如弗思提出的理想观察者就具有如下六个特征:(1)全知的,对道德原则之外的非道德事实也是全知的;(2)全能的,能够即时调用所有信息并给出运算结果;(3)无私公允的;(4)客观冷静的;(5)前后一致的;(6)正常的。这个理想的模型让人类自惭形秽,因为我们无法收集并使用所有的知识信息,也难以在情感面前完全地保持理智与公正,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因而,自然人也就永远不能成为理想的观察者。全知全能的“理想观察者”是绝对主义中的一个完美模型,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让这一理论模型不再只是哲学上的美妙构想,也有希望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技术存在。
彼得·辛格从功利主义出发来推行动物保护主义时曾提出过“道德专家”的构想:“如果有能力知道动物被屠宰时受苦的程度,以及饲养动物的详细方式,我们将有更充分的根据来决定吃肉是不是对的。如果能够计算出放弃吃肉节约出的粮食数量,以及素食对健康的各项益处,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种行为方式产生的幸福或痛苦的多少,从而更好地权衡道德与利益的各种冲突。”不难发现,使用计算机来处理彼得·辛格所描述的这些计算任务是更为高效和可靠的。因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最终将允许我们创建一个逐步接近“理想观察者”的人工智能道德顾问(Artificial Moral Advisor,简称AMA)来辅助我们做各种道德决策。
2015年,萨弗勒斯库(Savulescu)和马斯伦(Maslen)就曾详细提出了“道德人工智能”的理论雏形。最近,牛津大学的阿尔伯多·朱比利尼(Alberto Giubilini)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设想,并做了理论论证。他们基本的设想都是根据事先设定的道德标准编写一种能够提供道德建议的软件,这种软件所搜集到的信息更为全面和准确,运算速度也比人类大脑更快,并且不受情绪的误导,因而能够给出最明智的道德建议。例如,一旦我们设定了环保的道德标准,AMA就会分析废弃杯子的材质,告诉我们如何处置,从而弥补我们耳目等感官的不足,增强人们的道德胜任能力。因此,AMA软件可以胜任道德专家的角色,从环境中收集信息,然后根据我们提供的某些操作标准来处理信息,弥补我们在知识、时间和精力上的不足,提供最符合我们道德准则的行动方案。它将比任何一位人类道德导师都要见多识广,信息处理的能力也无以匹敌。
这种技术前景并不遥远,智能软件已经在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决策。如手机中加载的某些应用程序可以基于“情境感知”技术来识别环境并响应用户的具体需求,比如寻找最近的餐厅。复杂一点的智能应用甚至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病情,比如可以快速阅读海量医学影像资料的超级电脑“沃森”(IBM’s Watson)。但颇为遗憾的是,技术应用在道德辅助方面的应用并不多。然而,目前的智能信息技术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如素食主义者或动物保护主义者在就餐时最为关心的是动物的福祉,而对于餐厅的远近和价格并没有那么挑剔,因而他们更为青睐素食餐馆。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人工寻找这样的就餐地点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幸运的是,目前的电子地图只需要做某些技术延展就可以轻松地帮助人们定位素食餐馆。弥补人类在知识和信息方面的不足,还只是人工智能的初级应用,凭借强大的运算能力,AMA还能帮助人们避免情绪的误导。比如,在上文提及的2020年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AMA就可以辅助收集这种疾病的传染率、发病率、死亡率等各项信息,评估疫情的严重程度、预测可能的蔓延趋势,从而帮助人们制定最有效的对策并避免过激的反应,一方面以客观坚实的数据来说服人们尊重科学的医疗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公共卫生部门科学合理地制定决策,优化调整防疫措施,做好精准防控。
三、人工智能道德顾问潜在的技术问题
罗德里克·弗思的“理想观察者”是全知全能者,其理论模型假设它拥有全部的并且终极正确的信息来保证道德判断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这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相比较而言,可以投入应用的AMA是相对的、有限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计算机能够搜集到的信息的来源——人类知识网络本身就是有限的,还因为AMA的运算标准接受人为设定,软件在使用者的指令下搜集此类道德目标最相关的那一部分信息并给出有着不同价值侧重的建议,因而AMA是“理想观察者”的一种相对“精简”的版本。但是,这种“精简”反而可以让它保证人的自主性,从而在实践中成为一个巨大的优点。
毋庸讳言,AMA的实践模型将引发一连串的质疑,这些质疑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逐次递进的伦理问题:第一是这种道德强化技术是否会因为妨碍道德自由而取消了道德?第二,如果没有,置于人的控制下的AMA是否有被使用者误用甚至滥用的危险?第三,这种信息技术增强方式与生物增强又有什么区别?对自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诘问又当作何回应?第四,不难预料,AMA给出的建议会常常违背我们的直觉或要求过高,这又该如何处置?第五,情感是道德的基本要素,AMA排除了情感的影响,又何以能给出人性化的道德方案?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正确地处理道德判断中的情感问题?这五个主要的问题是必须要认真面对的。
问题一:AMA是否违背了道德自由而从根本上破坏了道德?
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在于它的自由、自主与自发性。不自由的或被迫的行为,即便产生的客观结果是良好的、利他的,也不能称之为道德行为。那么,作为一种道德强化方式的AMA是否因此损坏了道德自由呢?
事实上,AMA在两个关键的层面上保证了人的自主与自由:一是进行信息收集和道德运算的标准是由人来设定的;二是在给出建议之后,是否采纳、采纳多少以及如何践行,这些事实层面的选择与行动问题也是由使用者自主决定的。首先,影响道德方案制定的最关键因素是信息的选取标准,这一关键的问题留给了使用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人的道德自主性。人们在为AMA设定标准的时候,其实是在自由选择听取什么样的建议。由于每个人对什么是“道德的”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群主义者等都会有不同的倾向,因而需要AMA软件收集相应的符合个人道德标准的信息。因此,由人所设定的参数为道德信息关联的范围提供了必要的标准,这足以保证个人的自主与自由。任何由AMA提供的“你应该做x”形式的道德建议都可以被解释为“如果这些是你的原则(如保护动物),那么你应该做x(如去素食餐馆就餐)”。可见,这种相对主义的AMA尊重了道德自由,因而比绝对主义的“理想观察者”更加可取。此外,不同的道德准则还可以通过编程来做多元化的调和,如寻找餐厅时,AMA在确保动物福利之外,还可以询问是否考虑有机食品、公平交易等因素,这就如同让我们来选定不同的道德专家,然后请他们就具体的应用问题进行道德会诊。这就打破了因信息高度不对称所带来的无法做出道德判断的窘境,我们不必再孤独地依靠自己有限的知识和模糊的直觉以及冲动的情绪去做出不理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在听取建议之后,是否采纳和如何执行也完全取决于使用者本人,AMA不会做任何干涉,这也在根本上保证了人的道德自由。
问题二:风险防范问题。
AMA毕竟是受人操控的软件,它的运算标准由人设定,在保证道德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不管是圣贤还是暴徒,也不管使用人的标准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AMA只能机械地顺从。那么,如果有邪恶的使用者利用这种技术来追求不道德的目标,这种风险又当如何处置?作者认为,这是应该在编程AMA的一开始就需要先行处理的风险。比如,在确保AMA接受尽可能广泛的道德标准的同时,在最底层的原初性程序中加载基本的“道德过滤器”,可以以阿西莫夫的理论为道德标准设定最起码的边界,如不能偷窃,不能陷害他人,尊重和保护生命等。无论使用者是否承认这些基本原则,它们都会被强制执行,AMA只会遵循这些基本原则之上的其他不同的道德标准。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杀戮和偷窃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有时甚至是应该这样做的。例如,为了保卫平民不受伤害而杀死恐怖分子或为了不被饿死而偷窃粮食。但这类情况比较稀少,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AMA放弃执行这些任务。不过可以预期的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建模能力的成熟能够让AMA逐步处理这些特殊情况。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即AMA的确给出了不恰当的建议,行动的决定权仍在使用者手里,人们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AMA的建议。因此,实际情况并不会因AMA的使用而变得更糟。
问题三:对自然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回应。
是否要在道德领域进行“技术增强”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但现有文献讨论的技术手段主要还是以生物医学手段(如通过服用与注射药物以及基因编辑等方式)提升人的道德情感或认知能力来促进道德决策,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以一种外部的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道德能力的方案。
自然主义者和技术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物增强损害了我们的“真实性”和自然人的尊严,它损害了人类本性中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自然局限性”。技术增强伤害了我们“对未知开放”的能力,或者说与“有限”的和解能力,导致我们因此不能充分欣赏自然生命中的每一项天赋品质(包括缺点)。但十分有趣的是,自然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传统”的提升人们智商和情商的手段,比如教育以及更好的学习工具(如计算机)等。AMA恰恰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等新兴科技手段,是以一种外部的督促和提醒方式来做的道德强化,更像是一位老师在做细致的规劝和耐心的建议,这与内在的生物强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并没有“扰乱”大自然赋予人体的生理规律。严格来讲,这种外部技术手段并没有挑战人的“自然性”,没有扮演上帝的角色,因而并不是保守主义者瞄准的靶标,反对者的“举证”、攻击和诘难也因此落了空。
但是,AMA却还面临着“自举问题”:这种持续的监测、建议和提醒的道德建议机制会不会最终像生物医学技术那样改变我们内在的某些生理机制?尤其是在AMA提供的道德建议与我们的直觉频繁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性情会不会发生某些改变?或者丧失自己的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问题四:如何对待AMA给出的违背我们直觉的或要求过高的建议?
AMA基于更为全面的信息,所提出的建议也许会与我们的直觉不符。如果这是为了弥补我们知识的局限性,那么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如果使用者执意坚持自我判断,那么AMA的这些建议将不产生任何实际效用;但如果使用者考虑采纳这些有违自己直觉的方案,那么他必须在自我与AMA之间做出某种“平衡”。具体而言,这可以分为狭义的反思性平衡和广义的反思性平衡两种情况。前者是指在同一种道德视角(如平等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内审思各种判断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后者则需要平衡两种迥然不同的道德原则(如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等)。
AMA可以比较容易地帮助我们实现分歧较小时的狭义反思平衡,调整道德判断与道德标准相一致。而对于广义的反思性平衡,AMA的建议也不失为一种提点。如对个人主义者来讲,社群主义者的利他行为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当AMA持续建议把个人收入中的20%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情况下,原本吝啬的人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过激”的方案并折中一下,比如调高自我的道德标准,说服自己捐出10%的个人收入。
因此,AMA有助于我们实现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情况下的反思性平衡。与自我的直觉相反的建议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标准,从而让判断更为全面和成熟。这在事实上仍然是一种“教育机制”,因而避开了生物增强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止步于此,就有简化问题的嫌疑。既然引入教育视角,就有一重教育责任认定的问题:不当的建议或“教育”所引发的后果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澳大利亚的帕特星克·智璨·休(Patrick ChisanHew)教授曾认真考察过追究机器人道德责任的可能性,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技术进程内,人工智能对其行为将承担零责任。这意味着使用者将独自承担全部的道德伦理风险。这样的责任分配方式显然存在重大漏洞:使用者会以接受了不当建议为由而要求减轻处罚。因此,AMA有可能沦为新的道德失当借口。
一个减轻AMA责任的可行方案是:未来的技术将使这些道德顾问“真正倾听”,而不是提供答案,AMA会设定程序来问用户问题,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模式帮助用户澄清问题的含混之处,最终引导用户自己得出结论。因此,对于复杂问题,AMA将会把重心从结论的给出转移到协助人们进行分析推理,以详尽的推导过程来帮助用户自主形成解决方案,从而更加适合用户的需要且易于被用户理解。
问题五:AMA没有考虑情感要素。
作为一种智能软件,AMA具有“冷静”的特性,不受情绪(包括负面的厌恶、正面的偏爱或同情等)的影响,只执行不需要情绪参与的认知功能(收集、建模、解释和处理信息),从而在决策中排除情感的影响。但这种将情感从道德判断中剔除出去的做法也最为人诟病。在许多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看来,情感是道德判断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驱动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决策,还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最初的和最强大的执行动力。耶瑟·普林茨(Jesse Prinz)等人甚至提出了道德“情绪主义”,认为人们在具体情景中的所见所闻激发出的情感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力被远远地低估了,理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这不仅是一种情绪主义伦理学的哲学观点,而且还在不断被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所证实。一些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就证实了道德感是建立在有限的一组直觉和情感反应的基础之上的,理性常常是作为事后的合理化归因而已。
根据情感主义,道德判断本身就是某种情感的表达,情感在道德行为中起着根本作用,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道德实践中,情感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它的独特性上——为道德主体提供了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如果丧失了正常的情绪能力(同情、羞愧、内疚、悲伤),缺乏情感的推动,“人”就无法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因此,我们需要情感来推动我们自身践行AMA所提供的道德建议。这是情感的独特作用,也是AMA无法替代的。但是,情感虽能推动道德主体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活动,却也能扭曲我们的道德行为,它们往往还是各种偏见和非理性或不道德判断的来源,妨碍我们进行冷静而明智的思考。而AMA刚好弥补了这种缺憾,它以客观的事实信息为基础来做冷静而全面的计算,得出的结论就更为可靠。此外,对事物做出“正确”的情感反应并不是毫无规律可言的,随着运算模型的丰富,在履行情感在人类道德中的功能方面,AMA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它同样也可以提供情感方面的咨询。有理由预测,未来的AMA可以建议道德主体在何种情形下(如明显的不公正或抢劫等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的愤怒是合理的反应,甚至是采取行动的适当动机。
展望未来,AMA与其他技术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挥情绪的积极功能而避免它的消极影响。例如低血糖患者易怒,这让他们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行为。对此,AMA与神经生理学检测技术的结合可以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谷歌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可以即时监测血糖水平的隐形眼镜,AMA捕获到检测数据后能够帮助低血糖患者做出更好的决定,可以建议他们推迟某个讨论或者选择状态良好的时候再做出重大决策。再比如,用于老年护理的“环境辅助情绪调节系统”可以通过放置在贴身衣物中的感应芯片来检测老人的神经生理状态,当检测到老人处于极度紧张或恐惧的状态时,它能自动打开提示灯,并紧急联系医生。这样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普通人的情绪检验,帮助我们避开或克服情绪的干扰,做出更为明智的道德决策。
在检测和提醒的基础上,这种技术思路甚至可以发展出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某种锻炼来改进情绪能力的“神经反馈训练系统”(简称NFT),让受试者基于自己的神经生理参数(如大脑皮层的振幅和活动频率)来主动地调节情绪并改进大脑活动。目前,NFT已经被用来缓解焦虑情绪或通过脑功能的改变来提高移情能力。虽然目前神经反馈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方法和结果也存有争议,但这种方法本身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因而它开辟了一个前景极为广阔的发展方向。
结语
AMA为高技术环境下的人类道德生活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它在确保道德自由的前提下提高了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实践能力,帮助个体实现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情况下的反思性平衡。更为难得的是,它与生物增强不同,属于一种外部的教化方式,因而技术风险更小。此外,AMA不回避人类基本的情绪,能够辨别特定情境下的正确情绪反应,努力实现直觉和情感的积极作用而避免其负面影响,所以能最大限度地帮助人类提高道德水平。
诚然,人类有着极其丰富的道德生活,所面对的道德情景也是非常复杂的。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也的确没有哪种软件的灵活性可以比人更强,人工智能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人做得更好,但是随着建模能力的提升,它的确可以在越来越多样的道德情景中为人类提供可靠的建议。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道德顾问也不会很快篡夺或超越人类的道德自主性,尽管在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们应该承认自己在道德能力上的局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并利用我们无限的、可贵的认知能力来开发人工智能,从而实现高技术环境下的人类道德潜力。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1期
来源:道德与文明
编辑:古凤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4-25 15:34
【案例】

编辑:古凤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5-30 22:15
【案例】
响应伦理学:在回应与责任之间
[德]伯恩哈德·瓦登菲斯/文
刘畅/译 朱锦良/校
摘要: 响应伦理学不同于一切纯以共同目的、普遍规范和功利计算为导向的交往伦理学类别。对某人所行之事的责任与对他者的呼召和声言间的回应之间的截然区分构成了响应伦理学的基础。响应的逻辑包含有如时态延迟性、不可回避性、礼物以及发轫于别处的自由等等诸多方面。“对……负有责任”与“对……进行回应”两者在一个以惯习和规则进行调停的第三方那里相遇,然而他人的超乎常规的诉求却并不能被纳入到这一机制当中。响应伦理学为社会性中的非社会元素进行辩护。
Bernhard Waldenfels (2010). „ResponsiveEthik zwischen Antwort und Verantwortung“.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58, 71-81.
I. 响应伦理学与交往伦理学
从古至今伦理学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与行动?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从目的与价值出发,从法则与规范出发,从对话的有效诉求出发,或者是从有用的后果出发。与之相应,我们可以区分目的伦理学、价值伦理学、道德法则、对话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如下这些大名鼎鼎的人分别与它们相关:亚里士多德、伊曼努尔·康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我所构想的响应伦理学并不能替代如上那些伦理学,但它会强调不同的方面和要点。音调用于制作音乐,而响应伦理学也是用于制作“伦理学”的一种音调。
这种新的音调叫做回应(Antwort),也即对异己诉求(fremder Anspruch)的回应。回应并不只作为狭义的言语回应来理解,它在广义上包括那些亲力亲为的回应,它们延伸到所有的经验的“音区”之下。就如管风琴有繁多的音区,回应也具有多样的“音区”。感官和欲求的表达同样是回应的音区,亦如我们的回忆、期待、行动、手艺,连同那些仪式上的和技术上的手段。人们不仅可以用词语进行回应,也可以通过沉默;就如谚语所说,没有回应亦是一种回应。人们可以通过眼神和手势回应,就如通过行动和谋划来回应,人们能够感受到它们的效果。当我们为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荡的陌生人提供信息时,当我们对法官、医生和检查者的问题进行回答时,或者当外国人向警察出示证件时,我们都在实行一种回应,但回应本身比我们所完成的上述任何特殊行为都要意味深长得多。类似于感官的朝向、目标的追随和规则的奉行一样,回应是烙印在我们与世界、与自身和与他人的整体相处之中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我命名为响应(Responsivität)。在多数情况下这一基本特征都悄无声息地藏身于幕后。当我们问一名棋手他刚刚做了什么,他也许会如此说:“我要干对方的皇后”,而只有在特殊的情境下他才会说:“我遵守一条规则”。当我们问一名正在买单的消费者他正在做什么时,只在极罕有的情况下他才会说:“我在进行一项交换行为”。就回应而言,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通过特定的言说和行为,我们进行回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把言谈和行为自身看作回应。
然而,回应专门以发轫于别处的方式来标明自身。在我们设定目标和遵守一般性规范之前,就在某事或某人激发、引诱、威胁、挑战或招呼我们时,回应已发端了。当然这里会有一些日常的情形,我们根据一种“回应套路”(Antwortrepertoire)来对之进行回应。我们拥有回应的“套路”,正如有经验的演员具有表演的“词汇表”。当然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当我们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陷入并不“熟悉”的处境中时,或者说我们陷入那些通行的规则和谋划不再适用的处境时。在此存在有一个疑问,一个处境是否总是如此地寻常,以致一切惊奇之物都从中被根除了。只有当我们的行为举止近乎技术操作的演练以及处境被还原到需要进一步加工的数据上时,上述情形才是真实的。就算没有这一约束条件,我们也会陷入如同事故一般的处境。九一一的飞机恐袭就是这样的事件。此种在轰动性的事件中完全映入眼帘的异己性(Fremdheit),于平日里也会以隐没的方式广泛地发挥作用,比如通过陌生的目光或语词。不论我们是否乐于接受,我们都会遭遇这两者。我们此时行走在这样一块区域,它处在强迫与自由、善与恶的此岸。异端(Heteron)总是会闯入进来,在每一种感性学、每一种逻各斯、每一项实践和每一种治理那里烙上异质感性学、异质逻各斯、异质实践和他治的纹理。这同时意味着,逻各斯发源于一种激情(Pathos),它那令人惊异而恐慌的作用并不如人作为“占有”逻各斯的生物那般为我们所掌控。以上这些动机引导的响应伦理学既不制定新的规则,也不宣告新的目的。这种响应伦理学肇始于一个素朴但又根本的问题:当我们这样或那样言说和行动时,我们与什么相遇?我们对什么进行回应?与之相关的既可以是使我惊奇、侵袭着我的某个东西,也可以是伴随着请求、疑问、威胁或者允诺转向我的某人。
此时此地的以及总是可以重新出现的异己诉求是响应伦理学的出发点。就此而言,它要比立足于共同意图和普遍性规范之上的交往伦理学或理性道德更为深刻。响应伦理学回溯到了先于意图(präfinal)的和先于规范的(pränormativ)经验。惊异与厄洛斯(Eros)具有亲缘性(《菲德若篇》,249 c-d),柏拉图的哲学以及哲学对话以惊异起头(《泰阿泰德篇》,155d),而异己的诉求也扮演了与惊异相类似的激发性角色。在此需要注意,惊异展示了一种作为共同触发、共同相关和感性共通感而出现的激情,但惊异自身对于逻辑共通感而言是不可及的。人们可以理解惊异,但并不处身于惊异。在此就区分出了那种冲向人们的惊异和人对之有所选择的笛卡尔式怀疑。此时以类似的方式,也可把我所听取的异己诉求与那种寓于每个人的主张当中的普遍有效性诉求区别开。异己的诉求一出现,就中止了事情的正常进程;它把我们从我们的惯习中拽出来并抛入疑问之中。在此就不由地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那些对于交往和共同生活不可或缺的约束性力量及义务从何而来。它们是否来源于自然?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解决办法,因为自然中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强行归为敌对、奴役、歧视女性和对种族的吹捧和贬低。自然就如白纸一般默默承受。那么约束性的力量和义务是否又来源于契约?可只有当人们把契约当作已完成的事实(fait accompli)来看待的时候,人们才能如此主张。如我们在霍布斯和休谟那能够读到的,现实中的每一条契约都以尚未兑现的承诺为基础,这种承诺使得契约的每一次完成都承担了滞后的负担;承诺在此就与有待研究的时间错位有关。人们可以计算风险或者预先确信,但这都不会改变这一实情,即契约并不能自我担保。我给,好让你给(Do ut des);可我何以确信,你会给?非道德的声音向道德预先指出了道德自身的弱点和非道德,这种非道德的声音指明了我称之为“道德盲点”的东西。人们依赖于目的、价值、规范和利益计算,而道德却不能在它们中找到必要的立足点。好的东西为何是好的?我为何应当听从法律的声音?我的纯个人兴趣应当追随何者?在系统理论的形式语言中,上述疑难就转化为这一命题:区分好坏自身并非是好的。如果道德并不供认它自己的无根性(Abgründe),或者它被迫从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当中寻找它的外在立足点,道德就转变为一种类道德的信仰。若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表述,则此处需要的是一种伦理学悬搁。伦理学悬搁离弃了理所当然之道德的地基,而不必遁入一个属于纯道德或纯道德共同体的世界。在此需要的是目光与言谈的陌异化,这种陌异化使得道德的谱系学得以可能。在此极富助益的是文学上的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梅尔维尔的巴特比,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或者卡夫卡的K先生等文学形象能使我们避免简化为一种单纯的道德手册或常识性道德。
以上这些思索开辟出了一条路径,它使得我们能跟随尼采的建议去游历“可怖、偏僻又隐蔽的道德地域”。此处我们的讨论限制在三个步骤上:责任的传统角色,作为责任的对应面的回应,以及对责任与回应之间的连结线的寻找。其背景则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共性和社会性并不拒绝异己性,而是使之发挥作用的话,公共性和社会性会变得怎么样。
II. 为某事向某人的责任
责任的概念出自法律的领域,可它也具有神学上的弦外之音。在德国,责任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5世纪;在18世纪它作为responsibility和responsabilité出现。最早在希腊,它对应于对话上的logon didonai,它在德语中可以被很好的转述为“进行辩与答”(Rede undAntwort stehen)。逻各斯的“给予”与“接受”是对话的居间发生(Zwischengeschehen),但这种居间发生在指向唯一的逻各斯的过程中,倾向于把自己限制到一种与分派角色进行的独语(Monolog)之中。对于源自对话的经典责任观念有两个指导性的动因。其一为对合理解释的索求和提呈,它们以理由为支撑(论证,argumentatio);其二为对行为的归咎和指认(归责,imputatio),我们在法庭实践(也包括道德法庭的实践)当中已对之有所了解。在责任的这种运作过程中,有三个根本性的因素可以被区分出来。
(1)为某事(für etwas)负有责任,也即对人们随意说出口的、所做的或者疏忽大意地引发的那些东西负有责任。把责任的范围拓展到超出个人自身意向的东西上,这是责任伦理学有别于单纯的意图伦理学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持留在一种过去的视角下,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过去时态归为法庭辩论的类别。审判关乎的是已然成立的诸事实。类似的还有历史学的判断和道德判断。
(2)向某人(vor jemandem)负有责任。这个“某人”在此可以是被某些人所体现的权威,比如说法院,这个“某人”也可以是匿名性的场域,比如说公共空间、社会以及历史。此时人们就置入了一种中立性第三者的视角。第三者的原型就是法官,它站立在对立的两股势力间,以双边性的目光进行判断,不再有具体人格的外观。原告、被告和法官的角色在审判过程中严格分离,这种审判过程切不可与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公开辩论相混淆。如柏拉图的表述所确证的那样,在哲学的争辩中我们不需要法官,毋宁说,在哲学争辩中的每个人都同时是法官和发言人(《理想国》,398b)。可此处仍旧不缺乏第三方权威。逻各斯就是第三者,所有的对话伙伴作为理性的动物都分有了逻各斯。用现代的话讲,第三者的角色是跨主体的(transsubjektiv);只有在起始层面上,也即寻找论据时,第三者的角色才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ktiv)。当它关乎命题和决断的效力时,它就不再是主体间的了。
(3)人对自身负责。如果没有行为者对于归属于他的行为——无论他承认还是否认——的自我负责,那么,被审判的东西就单纯是人们澄清和描述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有疑点时需要证成的行为。对于现代的“主体”而言,责任具有特殊的意义。“主体”并不仅仅作为责任的承担者(Träger von Verantwortung)而出现,它还是负责能力的具体化身(Inbegriff der Verantwortlichkeit)。责任能力恰巧就是去判定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法人或道德人的某种标准。不对任何东西负责任地去有所作为的人,他既不是一个带有自己的公正观念和义务的法人,也不是一个成年的公民。我们需要重视的第三个方面便是执行者(Täter)的方面。
(4)最后还有一个可能性,也即人为某人(für jemanden)负责。这就是代理人(Stellvertreter)的方面。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略过这一方面,因为它惯常只作为次要的、衍生的责任形式被考察。只有当我们与勒维纳斯一道去呼唤一种原初的代理形式时,代理人的这一方面才开始具有意义;这种原初的代理形式意味着,当我们要在自由的领域中采取某种行动时,我们总是从他者那里出发。
我们业已刻画了责任的经典形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责任的经典形式还有着亟需修正的明显界限。这个界限可以在我们所区分出的上述全部三个因素那里得以展示。
(1)在行为成为既定事实之后,责任才姗姗来迟。此处、此刻以及在将来必须做什么,滞后的评判对这一问题没有给出答案。人们可以提出意见说,行动自身已经可以被规定为负责的和不负责任的了。可这种在行动中的责任(有别于在行动之后的责任)也不是某种统一的东西。它通常包含对规则的重视、对条件与后果的顾及以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配合。同样,如果行动自身没有被理解为响应性的(responsiv),那么那种我们赋予对异己诉求之回应和相应的应变能力的特殊价值就不会映入眼帘。
(2)如果我们把作为评判行动的基础的尺度也考虑进去,则我们又将发现经典责任形式的更多界限。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负责时,他或者她必须转向某种既成的秩序,它可以是政治、法律类型的秩序,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如此我们就必须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了,即每一种秩序从一开始就是偶然的。我们不能依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所促发的那样,去把偶然性与任意性相混淆。偶然意味着,行动的秩序如同语言的秩序那般也可以是另一幅模样。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是另一幅模样。把一个行动归类为偷盗已经预设了一个确定的私有财产秩序。逃避巨额税务的公民和赔付错误规划的管理者并不被视为骗子和小偷,这是基于我们社会的双重道德手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把暴力行为归为谋杀或凶杀、自发行为或者恐怖主义行动上。如同霍布斯已然敏锐地指出那样,行动是被视为(gelten als)偷盗和谋杀的。可如果秩序在总体上或部分上具有界限,这就意味着,实践判断虽然从它那方面来讲是有理由的,但这不是充足理由。只有当我们处身于莱布尼茨所谓的一切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世界时,才存在充足理由。
(3)最后,当我们考虑行动者的角色时,我们也会遭遇经典责任形式的局限性。那种不受限的自身负责(Sichverantworten)要求一个主体成为他言行的主宰,也即如康德那著名的自由定义要求的那样,主体得具备这样的能力:“完全从自身出发造就一个状态”。同样当我们承认一个人“不是自己家里的主宰”时,并且承认一个人在最内里包含有异己性时,那么,合理解释的提呈就会在所有算计和归咎中遭遇不可测度之物。即便道德的手册也暴露空档。
这种被我们展示出来的经典观念正承受着一种经由系统压力所加强的侵蚀。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无个性的人》(Mann Ohne Eigenschaften)中已经诊断了一个“没有人之属性的世界[…],一个没有体验者的体验的世界”,就好像“个体责任的友善重力消融在可能意义的公式系统中”。通过赋予他小说中的主角一种特定的“无可预料性”和“对理由不足的感受”(针对这两者,“逻辑的检察官和安全主管”无力去改变什么),穆齐尔抑制了一种错误的期待。生活世界愈是趋近于一种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只能通过维持系统功能的命令才能被联结和捆绑起来,在其中遍布广为称道的那种联通力),如下问题就变得愈发紧迫:谁向谁为何物负责?系统理论家不了解如何去着手处理异己性的主题,这并不令人惊奇。当每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具备异己的特质时,这就根本不再有人是异己的了。在对异化的系统性扬弃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要庆祝迟来的胜利?
III. 对……进行回应
当我们从回应而非从我们自己的言行出发时,情况就突然转变了。对异己的诉求进行回应,要比为某个行为向第三者负责意味更多。梅尔维尔的小说《巴特比》(Bartleby)中的一个场景对此有所启发。与故事同名的主角是纽约一所显赫的律师事务所的缮写员。在长期地在他孤独的工作台上“苍白而机械”地俯身工作后,他突然以一种特别令人惊奇的方式中止了他的服务。针对他的业务主管的要求——一般是协助文书的一些段落的定稿,他以一种“少见的温柔而肯定的腔调”进行了回答,并且是以一种老掉牙的空话进行答复:“我宁愿不”。一个无条件的否定。在我的著作《回应的音区》(Antwortregister)中我把这个故事解读为一种拒绝回应的情形。
以上这种对话的失败并不发生在通常的意向性层面、交往规则层面和实用状况层面。对话不是因为表述被误解和意义不够明确而失败。它也同样不是因为规则被破坏而失败;完全拒绝履行职责的人并没有违背规章制度,就如通常的罢工者抛下工作准备谈判那样。对话此外还不是因为表述不符合处境的情形而失败。对话的失败作为一种脱离正轨没有任何与之匹配的情形。对话的失败毋宁说等同于一种自杀,历史由之终结。被转交给一所难民收容所后,巴特比这位曾经的缮写员绝食了。从对话中抽身而出的对交流的拒绝让诠释学家、对话分析家和实用主义者可能的努力遭遇了一堵高墙。对话如今只剩下了对于拒绝的表述,它呈现在否定性语言行为自相矛盾的形式中:“我什么也不说”或“我什么也不做”。说话者说出了他所不做的事,并且他做了他不说的事。尽管言说者实际上卷入了一种被体验到的悖谬中,可语言实用主义者却把这种语言行为作为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搁置一旁了。就算是回撤到沉默中也无法扬弃这个矛盾,因为某人一进入交流的舞台,他的沉默也就意味深长了。就算是只作为黑色的阴影,沉默者也已经参与到对话中了。巴特比的故事向我们揭示的东西已经嵌入到了一个独立的深层维度中。如已经预先说明的那样,我把它称为响应。
这里所关乎的回应行为分裂为被给予的回答(也即命题内容,作为回答(answer)填补一个空洞)和对回答的给予(响应),它表现为我们着手处理异己的诉求或者想要从中抽身而出。缮写员巴特比的案例已充分表明作为给予(das Geben)的事件要超出被给予的内容之外。礼物可以具有金钱上的交换价值,给予并不如此,这就像被说出的东西会具有述谓的真值,而言说却没有。给予是一个事件,它只在重演性的再给予(Wieder-geben)那保持为鲜活的,就如勒维纳斯所说,言说指向着重演性的重述(Wieder-sagen)。与被掌握的知识类似,被给予的回答可以沉淀、惯习化(sich habitualisieren)或者转化为符号,但对回答的给予并不能如此,它在此时此地发生。
相应于回应行为在响应人这方面的二重化,也会有在发送人诉求方面的二重化。我们要区分开作为对某物之索求(Prätention)和对某人之吁求(Appell)。当我们说我们满足一个请求时,这种表述方式是二义性的。人们可以通过给予被请求的东西来满足一个请求;除非人们把一个请求认定为一种缺乏状态,不然人们就不能满足一个请求。感谢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赠予,不只是一个可计算的添加,它处在把礼物与给予以及把给予者与接受者划分开的裂隙中。朱塞陪·翁加雷蒂的颇具表现力的双行诗最为突出地表达了这一点:“在一朵栽下的花和赠予人的花之间/有不可言说的空无。”
在诉求和回应的双重事件中体现出了一种自成一格的逻各斯,它与一种特定的伦理(Ethos)结成一对。就如之前一样,有三个因素可在此引入,以说明回应的逻辑如何超出责任逻辑的界限。
(1)第一个因素关乎回应行为的时间性。异己的诉求不可还原到被规范地确保下来的权利,也即那种已然现成的并随时都能申诉的权利。那些影响到我们的促动、注视和称呼,并不出于我们自身,而是走向我们。这种方向上的差异是决定性的。那些影响我们的东西穿过了时空的距离挤到我们身旁。与我们的主动行为相比,它们总是来得太早。相反,与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东西相较,我们的回应又总是来得太迟。这里并不是说某个包含有后果的因果刺激物先行在我们之前发生。而是说,我们自己先行于我们自身。借用柏拉图在《巴门尼德》(141c-d)中对时间进行分析时的谜一般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说:我既要比我自己年轻,又要比自己年长。这里与我们相关的是一种原始的先行性和同样原始的滞后性,它们使得我们的言与行从未完全征服时间的峰顶。一个从别处开始的回应行为与它所回应的东西,通过一个停顿(Hiatus)而相互分离了。这种真真切切的时间错位,我借用一个古老的词汇来命名:分裂(Diastase)。
也会有一些具有更强感受性的经验,在它们那里这种错位特别清楚地出现了。比如由惊人的事件而导致的休克(Schock),笛卡尔说这种休克使我们的身体僵化成一尊雕塑。在现代美学中休克体验也众所周知地具有特殊的地位,比如说在瓦尔特·本雅明那里。此外还有那种只以后遗症方式出现的创伤性事件,对此,弗洛伊德已经在他对狼人的分析指出了,这种创伤性事件具有原始滞后性。针对创伤患者的失语症的斗争在此已归属于治疗惯例。同样需要考虑的是科学的发现和艺术的创造,通过这种发现和创造,科学家和艺术家并不仅仅是使得他们的周遭世界感到惊异,而是首先使他们自己感到惊奇。在托马斯·库恩笔下的科学史充斥着必须等待被承认的创新。最后还需要考虑的是政治和宗教秩序的创立(Stiftung),它只有通过附加的回忆才转变为某个可以被注明日期的事件。里希滕贝格的名言“它思”或者福柯的表达“有秩序”都指向了创立事件,它只有在再创立(Nachstiftung)中才能被把握到。每一个节日都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寻常活动,它包含着符号性的再创立和重复事件。
(2)第二个因素与回应行为的无可逃避(Unausweichlichkeit)有关。人们倾向于去追问,那些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对我们有所诉求的东西,是否由描述性的事实组成抑或是从先于描述的规范中推导出来。答案只能是:非此亦非彼。当我们遭遇到异己的诉求时自我观察,则会发现存在与应当以及个别事实与普遍规范之间的标准划分失效了。一个情境化的诉求,当它化身为对帮助的请求或对正确路线的简单询问走到我们眼前时,它就既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记录在案的纯事实也不属于某种普遍法则。哲学家宁愿把这些简单的事件推到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才处理的日常道德那边。但因而它们也为道德带来了培植土。保罗·瓦茨拉瑞克(Paul Watzlawick)的教导:“我们不能不交流”可以被直接转述为:“我们不能不回应”。这种双重的“不”指出了一个在实践必然性意义上的“必须”(Müssen)。类似地,有进行交流的情形,也就会有进行响应的情形。我们在诸如“别听我说!”这种要求中所设定的双重约束表明了一种内在的强迫,它不可与因果的规定相混淆。这种内在的强迫正如我们习惯去说的那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它绝不可被理解为一种不自由。在普鲁斯特的《问卷》中,濒死的作家贝格特(Bergotte)谈到了“未知的法则,我们臣服于它,因为我们过去接受它的教导,不知道是谁写下了它”。这一后知后觉的洞见的产生并不在于阅览一本道德教材,而是在于一个完全不起眼的主题,就如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的画作《代尔夫特的远景》(Anblick von Delft)中“一小段黄色墙壁”。尽管相较于普鲁斯特,勒维纳斯把伦理学与感性的东西更为深刻地区别开,可当他把异己诉求令人烦扰而又令人不平的特点树立起来并把伦理的东西规定在一种先于任何论证尝试的、并非无差异和并不漠不相关的形式中时,他和普鲁斯特的观点又近乎相同。
(3)如我所偏好去表述的那样,第三个因素关乎所谓的主体或自身(das Selbst)的状况。(自主行动着的)自律者的自由并不会随着异己诉求的出现而消失,它反而是转变为一种作为响应自由(responsiver Freiheit)的专有形式。我开始行动,不过作为回应者,我的行动发轫于别处,也即我不在、不曾至以及绝不将至的地方。我以双重的方式出场:作为某个东西降临于其身的承受者,以及作为对某个东西进行回应的响应者。在此,如拉康所承认的那般,自身便成为了被分割的自身。于此相同,回应也并不是如商品一般已经被摆在柜台上。我所给出的回应是需要去创造的回应,或者更准确地说:答案自行发现(Antworten finden sich)。我们再一次遇见了一种佯谬。如同热恋之人对于拉康那般,回应者给予了他并不拥有、但被要求交出的东西。布莱希特(Brecht)的《道德经产生史》以如下的诗句收尾:“因为人们必须先把智者的智慧夺走。/为此也得感谢关令尹喜:/“他向智者索求了智慧”。要求和回应、挑战与响应的谐音,为居间音(Zwischentöne)和不谐之音开辟了可能性,这种谐音给出了一种相关的历史模型,它是对某种具有目的论导向或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之设想。
IV. 回应责任
最后还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从异己的诉求出发的响应伦理学如何能与交往伦理学的公共目的以及相关地与道德法则的普遍规范齐头并进?如果它们互相是漠不相关的,则响应伦理学最终也只是一种远离尘嚣的、无历史的世外桃源,与他者的关系也就被限定在我(Ich)和你(Du)这样一个对子上了。把这两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的括号,可以在异己者(Fremde)和第三者(Dritte)之间的特有差异那被找到。第三者的身份在齐美尔、萨特或勒维纳斯等人那被打上多种多样的标签出现,并且它对于精神分析中作为 “超我”的机所(Instanz)而言也是根本性的,它总是已经发挥作用了。在我们说出的每个词语中,在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计里,在我们感受到的每一种情感那里都有它的身影。它即是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见到的共同生活(syzen)的维度,它在海德格尔那以共在(Mitsein)的形式重新出现并且在梅洛庞蒂那里被转写为共身体性(Intercorporéité)。这一维度藉由常人的匿名性(Anonymität desMan)被一道烙印下来,如果不把它真的(eo ipso)视为一种非本真的沉沦形式的话。共同的维度(Dimension des Mit)产生于一个文化和跨文化的居间区域(Zwischensphäre)。这一区域来自于共同触动(Koaffektion)、合作、生活节奏和社会工程,来自于血缘关系、传统、机构、价值面板和规范体系,来自于一切既不完全归属于我、也不完全归属于他人的东西。
本己之物以多种方式与异己之物纠缠在一起。这意味着他者总是作为某人与我相遇,作为男人或女人,作为老年人或年轻人,作为德国男性或意大利女性,作为外行或专家,作为健康人或病患,作为朋友或者敌人,诸如此类。以类似的方式,环绕着我们的、有助于或妨碍我们的一切作为某物与我们相遇,在其中他者再次以间接的方式作为某人与我们相遇。然而他者并不只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或者一个整体的组元。如我自身的异己性那样,他者的异己性冲破了我已经熟悉的框架。在特定的方式上,那些归属于我们的世界的事物的异己性也具有如上的特点。由于每一种秩序,包括道德秩序,都从出于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视角并且只拥有特定的范畴体系,每一种秩序便在超乎秩序之物(Außerordentlichem)那释放出了一种溢出物。超乎秩序者在他者的和我自己的异己性之外构建出了异己者的一个根本性维度。治理(Ordnen)意味着,如尼采所说,“不相同者的相等同”;所有的法律判决作为“使同质化”(isazein, :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五卷第7章)意味着,如同勒维纳斯所言,“对不可比较者的比较”。于是公正便不是在法律规章之外更高的法,而是在法的界限中,在异己诉求那的溢出物。所有的秩序形式都与此类似。正如超乎秩序者不可脱离于有秩序的东西,我们要寻找和给予的回应也不可脱离于社会责任。
人们同样也可以追随赫拉克利特,把有秩序者和超乎秩序者之间的关系称为在最极端冲突中的“冲突着的和谐”(palintropos harmonie)。单方面去强调常规、集体和规则的方面或者同样单方面强调反常、个人和无规则的例外情况的趋势总是不断产生。这两者相向而行的趋势(一方偏向稳定的平均值,另一方偏向不稳定的极端值),人们可以称为常规主义和极端主义。介于有秩序者和超乎秩序者的综合是不存在的,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将使得被生造出来的整体获得胜利。因此,我们要转向一种游走在常规性边缘的均衡行为,它为一个在世界和生活形态上的人格、国家和文化的种类的集合保留了余地。在此之上进一步就构建出了诸过渡形态(übergangsfiguren),它们既不内在于也不外在于多种多样的秩序。翻译员就属此类,他游走在多样的语言区间中。此外也还要提及暴行中的牺牲,它的那种承受在身体上的伤痛应被判定为违法的侵害行为,最后还有病患的那种作为某种类型的疾病被对待的苦痛。没有把对不公遭遇转变为案件、把对痛苦的承受转变为疾病的那种变形,就不会有法院和医院。然而那些专业性程序也会撞上异己性的界限。如果这些界限被忽视了,我们就会遭遇到对生命的法学化和医学化。类似的也适用于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退化。这种经济理论只认识交换价值,它把经济上的“不同类者的相等同”还原为“同类者的相等同”。在此也存在有作为溢出形态的给出(Gabe),它内在于被标上价格的东西之中,而又保存着无价之物。
这些思考可以被继续推进。它们指向了对某种异己者政治学的需求。这种政治学在那种在苏格拉底的无可定位性(Atopie)中被预示的、一切社会性中的非社会性那里达到顶点。作为城邦的公民,苏格拉底归属于城邦,但他又不完全归属于城邦,因为他向隐藏在所有自明之物身后的东西发问。当一个人说“我们”时,“我们”是我或者你,而非“我们”自身。每一个“我们”,不论是家庭、民族、教会、阶级或社群,都是有“缺口”的我们,如果没有异党的存在,它就会发展成一种专政。异己者和陌生的东西不应被视为某种我们应当与之脱离干系的瑕疵,它们反而应当被视为一种不断地把我们从标准化的“昏睡”中唤醒。那种映入我眼帘的响应伦理学,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纠错过程。至于作为我们的基本主题的回应与责任而言,这意味着,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爱德蒙·贾贝斯(Edmond Jabès)所说:“Répondre de ce qui échappeà la responsabilité”,也即“回应脱离责任之物”。
(文载:《伦理学术》第9期,注释从略。)
来源:大道不离万有
编辑:古凤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6-18 22:55
【案例】
威慑的伦理意涵
威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通过惩罚来抑制犯罪行为;二是维持军事力量以阻止对象攻击行为。一般而言,威慑的主体是群体,威慑对象是犯罪行为或攻击行为。威慑可以分为总体性威慑与个体性威慑,前者主要通过惩罚抑制可能的犯罪行为,它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对象,如刑罚威慑;后者是在紧急情况下抑制具体侵犯行为,如军事威慑。道德的核心功能是扬善抑恶。扬善是传统伦理的核心命题。救助、信任、关怀等就是以扬善为目标的行为,它们一直受到伦理学的重视,而威慑、惩罚等抑制恶的行为则受关注较少。一些道德难题的化解不仅需要求善的伦理学,也需要制恶的伦理学来另辟路径。
一、恶行的抑制
威慑作为一种行为控制手段显然是一种集体行为,它内涵一种“共享诸如信念、愿望和意图的意向状态”,是建立在“我们”对惩罚犯罪与侵略的集体意向性之上。这种集体意向性是个体采取一致的行为时所共享的意识状态,其影响着个体对恶的判断并引发惩罚恶行的共同需要。威慑通过惩罚手段增加给对象的外在刺激来调控行为,降低对象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但它并不一定可以消除行为的发生动机。因为运用强力作为控制技术也有其局限,它只能抑制行为的发生几率与行为强度,这种控制技术并不能压制一个人的思想。威慑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虽然不能作为社会控制的唯一技术手段,但也是不能缺位的社会控制行为。
威慑的基本功能在于抑制犯罪或侵略,它的基本目的是抑制恶行。威慑作为一种行为控制手段,它的伦理意义与伦理属性不是基于人性的预设,而是由它在人类道德与法律规范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威慑并不能消除恶的倾向性或恶的动机,只能抑制恶的行为。威慑主要是通过改变对象的外在刺激条件来调控个体行为,但它并不限制对象的意志自由。
恶与人的自由存在内在联系。恶是自我将他者贬低为异类。自我与他者在本源上是同质的,而恶破坏了这种同源性,使自我对他者的戕害影响了自我作为人的类属性。对他者自主性的否定最终会导致自我的存在性危机。因此,恶的本质就是对自由的减损,它动摇由人创造的道德规则体系,使人存在重返“物”的风险。由于恶损害了他者的尊严和自主性,恶的抑制就是帮助恢复自主性。威慑之所以能够抑制恶行是由于主体有意识地控制外在刺激的总量来调控对象行为,同时威慑并不直接干预对象的意志自由,而是通过激发对象的理性能力来增强自由能力。
威慑的直观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制造恐惧来阻止对象的侵害行为。恐惧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属性,人对恐惧的应用方式才决定它的道德性质。如果恐惧损害了人的自主能力,那这样的行为就是恶的。如果恐惧激发了主体的生存意志与理性能力,限制了任性的自由,那它就具有道德价值。因此,威慑与伦理并不直接冲突,威慑可以为自由能力培植理性基础,也为道德的产生或持存提供了条件。
二、规范性力量
威慑本身是权力主体宣称或暗示运用暴力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威慑是用具有自我限制性的暴力来限制任性的暴力,从而使任性的意志受到物质力量的限制。任性的暴力意味着主体与客体平等关系的破裂,把对象仅仅当作实现自我的工具来对待。任性的暴力实际上就是要求他者单向度地向自我呈现,抹杀了他者的丰富性。可见,威慑就是共同意志的化身,相比个体意志而言能增强抵御物质异化力量的能力,威慑本身就隐含一种对暴力的自我控制。
如果说道德是自我加之于自身的,那么权利则需要依赖外在的权威并通过强制力来维系。这种强制是以行为的更大自由为目的,它的对象范围并不是内在的自由意志,而是由自由行为交织而成的公共领域。法治状态下的强制力实际上通过对公共空间的限制来使群体中的个体分享最大化的行为自由,使群体的自由更加普遍化。威慑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公共领域的法治状态。威慑的对象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是行为自由可能附带的伤害性物质力量。威慑本身与自由意志并不冲突,它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也是建立在法的基础上。这种在尊重自主性前提下的强制力通过对个体行为自由的限制来实现群体中人的普遍自由。
话语是威慑的基本表现形式。如果说任性的暴力是我者对他者的工具化,那么威慑就是打开了我者与他者对话的途径。任性的暴力是对话语的缺场,威慑则是通过基于权力的暴力使任性的暴力主体重新确立内在的我者与他者的界限,以及外在的“你的”与“我的”的权利空间,并通过话语的形式创造话语交往的可能性。可见,从威慑的具体内容与手段来看,威慑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我者与他者的对话关系与交往基础。
威慑恢复了我者与他者的平等关系,我者再无权利要求他者以单向度的意象呈现,而是以对话的形式确立自身的存在。威慑不但创造了我者与他者的对话机制,也提供了权利的应答机制。正是在话语交往行为中,主体在申明权利主张中确认应答对象,从而确立权利本身。从道德规范的话语伦理基础和法律规范的权利应答机制来看,威慑为规范的产生或维系提供了物质力量基础与现实条件,它是形塑道德与法律等社会意识的规范性力量。
三、正义的基础
根据合作是否能够达成有约束力的契约,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刑罚威慑是一种合作博弈,而军事威慑则多是非合作博弈。在刑罚威慑中,由于公民先前默认的契约允许国家权力的介入权利,任何破坏法律者将会受到国家暴力的制裁,这使得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能够达成合作协议,倾向维护现有法律协议的效力。军事威慑虽然多为非合作博弈,但它包含非常复杂的心理互动活动。威慑主体与对象的行为博弈依赖于双方反复的心理博弈,需要依据信息流不断判断与决策,特别在现代军事技术的伤害性力量大增之后,军事威慑往往能够出现博弈均衡点,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威慑不但为合作提供了心理基础,也为它培植了情感条件。威慑的强制力实际上为正义感的稳定提供了保障。威慑内含“一报还一报”的惩罚逻辑,它不单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没有受到直接伤害的第三方也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感情。威慑的话语逻辑不仅是“你伤害我,我就惩罚你”,还意涵“你伤害他,我也惩罚你”。在桑塔费学派看来,这种即便与自身无直接利益关系,也对合作给予回报而对破坏者给予惩罚的态度就是“强互惠性”,而他们把这种互惠性视为正义感。
如果将道德视为合作体系,那么威慑在促进道德的合作上也有着特殊作用。合作为道德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道德的形成除了合作关系外,还需要理性、自主性与独立的思考等。道德植根于人类不断进化的历史,起源于合作与基于群体思维的相互依赖。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威慑通过对他者的强制,拉近了我者与类我者的距离,增强群体间的相互交往关系。威慑实际上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合作提供了群体思维与相互依赖关系。
合作的稳定性是对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信约的信心。威慑的强制力向对象传递维护秩序的信心,增强“破坏合作者将会受到惩罚”的信念。在国际社会中,威慑使已达成契约的双方避免倒退入“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威慑的强制力为正义提供了执行机制。可见,威慑在正义的产生与维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义需要威慑的物质力量做保障,否则正义可能被倒退的自然状态吞噬。
四、结语
威慑以抑制恶行的形式维护意志自由与行为自由的辩证统一,以人的生物性心理机制为基础,通过恐惧刺激人的精神性能力,为自由能力夯实理性基础,增强抑制恶行的道德能力。威慑建立对话机制来维护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关系,以确立权利的应答机制。威慑并不限制意志自由,而是对行为自由所依赖的物质性力量进行空间化限制。威慑通过强力稳固合作的互信,并以强互惠性培育正义感来促进正义的稳定性,也为正义提供外在执行机制,因此它构成正义的基础性条件。纵然威慑存在行为效用的限度和可能生发的伦理问题,它对人类规范体系的稳健运行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来源: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RXd8ol_rzRkw9EqyS0dHg
编辑:马皖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10 21:03
【案例】
邓晓芒 | 黑格尔论道德与伦理的关系
黑格尔论道德与伦理的关系
摘要:黑格尔克服了康德将伦理和道德混为一谈的局限,对法和道德、伦理三者的自由意志基础的揭示从理论上厘清了三者与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的对应关系,对伦理道德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法(权利)”的关系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思考,并以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眼光对这种关系的历史必然性作了透彻的解剖。但黑格尔法哲学把人类的道德伦理都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分解和辩证进展,将人的自由意志的异化即国家形态视为人的本质的最高形式,最终,人的主观道德和客观现实生活都失落在这个“地上的神”给人所规定的必然命运之中。
关键词:法(权利);自由意志;道德;伦理;国家
作者:邓晓芒,湖北大学哲学院资深教授。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1年第3期。
哈贝马斯的《再谈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又译《再论道德性与伦理性的关系》[1])是其九十大寿的主题讲演(2019年6月19日),谈及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道德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国际和国内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本文暂不想介入这一涉及当代政治体制、文化冲突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只想先就哈贝马斯文中作为论述的枢纽的、黑格尔对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方式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以期对问题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视野。
壹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作为法哲学的主体的三大环节是“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因此,当我们谈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关系时,免不了要谈到这三个环节的关系。而这三个环节中,在道德和伦理之前,最关紧要的是要澄清第一个环节,即抽象的“法”的概念,忽视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和理解,后面的道德和伦理的理解都是无法到位的。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德文Recht(法)这一概念不能被单纯理解为“法则”“法规”或“法律”(Gesetz,Norm,legitima),它同时兼有(个人的)“权利”(Berechtigung)的意思。[2]所以,Naturgesetze(“自然法则”)不等于Naturrecht(“自然法”,也译作“自然权利”),前者源自古代的自然法理论(如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和西塞罗等人),主要将自然法和理性(逻各斯)、正义和惩罚、义务和必然性等联系在一起;后者自格老秀斯、普芬道夫等人开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近代的权利理论,到康德正式确定唯一的“生而具有的”(angeborene)法权(Recht)就是“自由”[3],才将自然法的研究从以自然规律(自然法则)为基础转移到以人的自由为基础上来。当时,费希特、谢林都对此有过研究。[4] 而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则首次以自由为基点系统展示了这个自由理念本身的概念结构层次及其现实的演进。因此,他所谓“法哲学原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自由的哲学原理”,自由本身体现为客观的法或权利(法权),并将这种“法权”实现在主观的道德和主客观统一的伦理中。所以《法哲学原理》的副标题为“Naturrechtund Staatwissenschaft im Grundreß(自然权利和国家学概论)”,这里的“自然权利”也可以译作“自然法”(范扬、张企泰),只是要注意这个“法”不是单纯指法则、法规、法律,而且是指自由的权利。否则的话,这种“自然法”就有可能被理解为由自然界为人所立的法规,这样的“自然状态”就只能是霍布斯所说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黑格尔则与这样一种理解划清了界限,他说:
自然法(Naturrecht)这个术语对于哲学的法学说已经是常用的了,它含有这样的歧义:或者法作为某种以直接自然的方式存在的东西,或者它的意思是法通过事物的本性(Natur),即概念来规定自己。……因此,自然的权利就是强者存在和暴力有理,而自然状态即是暴行和不法的状态,关于这种状态除去说必须从它走出来以外,就没有比这更真实的话可说了。相反,社会其实倒是那个只有在那里法才有其现实性的状态;必须加以限制和牺牲的正是自然状态的任性和暴行。[5]
所以不奇怪,为什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区别了实然的法则和应然的法则。他认为“法则(Gesetz)分为两类,即自然法则和权利(Recht)的法则”,并且“在自然界中有一般法则存在,这是最高真理;而在权利法则中,事物并不因为它存在着就有效,相反地,每个人都要求事物适合他特有的标准。因此,这里就有可能发生存在和应然之间的争执,亘古不变而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法和对什么应认为法而作出规定的那种任意之间的争执”[6]。这正是准确理解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7]的钥匙,即:“理性”是实然中的应然,而“现实”是应然中的实然;双方一旦拆开,例如说,把“现实的”只理解为“存在的”,便没有了权利法则,[8] 所以只有理解为合乎理性的“权利”法则才具有“现实”的性质。而这同时也就是自由意志的法则。
从“序言”中的这一导向,顺理成章地就引入了“导论”中对自由意志的讨论,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基本原则。黑格尔指出,“法(权利)的理念是自由”[9],而自由的前提是意志,无意志的自由是不现实的,自由则构成意志的实体和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所以,“法(权利)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10]。至于什么是意志,这是在前面“主观精神”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就是经过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最后达到了“自由精神”,它是“理论精神和实践精神的统一,即自为地是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11] 但黑格尔在“导论”中对这个自由意志本身又进行了一种逻辑上的层次分析,即分为三层:(1)抽象的、否定的自由,即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由,例如法国大革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人们仅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自由(§5)。(2)特定的否定的自由,其实是有所规定、有所肯定的自由,也就是任意的、选择的自由,我要这个,而不要那个。这体现在康德对道德律的选择中(§6)。(3)既否定又肯定,“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他物中,守在自己本身那里”,“这第三个环节是自由的具体概念”,因而它成了“纯活动”。[12] “意志只有通过这种自我中介的活动和返回到自身才成为意志。”[13] 这样一种活动不是追求具体的对象,而是追求自身的实现,“所以当意志所希求的东西,即它的内容,与它是同一的,就是说,当自由希求自由时,只有这时意志才是真实的意志。”[14] 最后这个层次是以自我意识的思维为前提的,“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识,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的原则”[15]。
而一旦自由意志达到第三环节的层次,再回过头来看待前两个环节时,就把它们都提升起来了:它使得第一环节从一种单纯的否定性提升到了“抽象法”;使第二环节的特定的意志提升到了道德;从而使前两个环节从混杂状态(神法和人法)走向伦理中的辩证结合。但在此之前,真实的意志沉没入它的客观状态中,前两个环节还只能是潜在的法和道德,而它们的混杂则只是潜在的伦理。所以黑格尔说:“但是客观意志由于欠缺自我意识的无限形式,乃是没入于它的客体或状态的意志……这是儿童的意志、伦理性的意志、奴隶的意志、迷信的意志。”[16] 这里的“伦理性的”(sittlich)应当理解为“习俗的”,即“凡受外方权威领导而行动,并且尚未完成向自身无限返回的”意志。[17] 这个意思在§30中说得更清楚,就是说,通常所理解的“法”是形式主义的,相比之下,“精神的领域和阶段作为更具体、自身更丰富更真实的普遍阶段,正由于在其中精神使自己理念中所包含的更进一步的诸环节得到了规定和现实性,因此也就具有一种更高级的法。”[18] 在接下来的“附释”中,他总结道:
自由的理念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有的法,因为每个阶段都是在自己独特的规定之一中的自由的定在。当人们说到道德、伦理与法相对立时,所理解的法就只是抽象人格性的最初的形式的法。道德、伦理、国家利益,每个都是一种特有的法,因为这些形态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规定和定在。只有当它们站在同一层次上都要成为法时,它们才会发生冲突;假如精神的道德立场不也是一种法,即自由在其诸形式中的一种的话,那它就根本不会与人格性的法或另一种法发生冲突了,因为这样一种法包含着自由的概念,包含着精神的最高规定,与此相比其他东西都是缺乏实体的。但是冲突同时也包含着这另一环节,是受到限制的,因而是一种法从属于另一种法之下的。唯有世界精神的法才是无限制地绝对的。[19
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三大环节,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都是普遍的“法”(Recht),即一般自由理念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不能等同,甚至还有冲突,但它们都是同一个法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定在”,互相包含又互相限制,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世界精神”的绝对的法。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既然法是自由的理念,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那么各种不同的法也就应该按照自由意志的逻辑结构来划分。就是说,抽象的法对应于抽象的否定的自由,道德对应于任意的自由,而伦理则对应于“希求自由的自由”,三者走过了一个从个别性、特殊性到普遍性的上升过程。这就是黑格尔在§33的“本书的划分”中所展示的一般法的逻辑层次。
有意思的是,在按照“抽象法—道德—伦理”的层次从低级到高级地排列了法的逻辑层次之后,紧接着黑格尔又在“伦理”这一最高项之下列出了它内部的三个小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而这个小圆圈与大圆圈相比又是倒过来旋转的,不是从个别到特殊到普遍,而是从“自然的”伦理这个普遍到市民社会的特殊再到国家的个别,最后由此进入到“世界精神”即世界历史。而小圆圈中的这一逻辑倒转,又恰好与现实的历史发展程序相吻合,例如,在人类现实的历史中,都是最先有家庭(所以叫作“自然的精神”),然后才有市民社会,最后才有城邦和国家。[20] 因此他说:“这一划分可以被看作对各部分的历史的预告,因为各个不同阶段必须是作为理念发展的诸环节而从内容的本性中自己产生出来的”。[21] 但大圆圈所依据的不是历史的先后,而是逻辑的先后,所以必须反过来看历史,用他的话来说:
在更思辨的意义上,概念的定在方式及其规定性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应该指出这样一些环节,其结果是进一步被规定的形式,它们作为概念的各种规定而在理念的科学发展中先行于这结果,但并非在时间的发展中作为诸形态而先行于它。所以,像被规定为家庭的那个理念就是以诸概念规定为前提的,它作为这些规定的结果接下来才得到描述。但这些内在前提自为地也已经作为诸形态,例如作为所有权、契约、道德等等而现成在手了,这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它只是在更高度和更完备的教养中才使自己的诸环节达到了具有这种特有形态的定在。[22]
这里涉及的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他说:
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氏族,这倒是对的。……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23]
马克思把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比喻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4] 当然,马克思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所陷入的唯心主义的“错觉”。但总的来说,他对黑格尔是心领神会的。历史上的伦理关系(家庭和国家等)先于抽象法,抽象法的原理是经由自由意志的道德而在市民社会中才形成起来的;但要真正理解古代的家庭和国家,抽象法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25] 其实,抽象法与伦理,尤其是与其中的市民社会的第二环节“司法”“作为法律的法”联系得更紧密,经常可以看作同一个东西;而真正处于对立中的并不是抽象法和伦理,而是道德和伦理。
贰
如果我们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这种划分方式与他的《精神现象学》第六章“精神”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那里的程序与《法哲学原理》恰好相反,分为“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了的精神:教化”和“对其自身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也就是伦理在道德之先。而抽象法的部分则被提前在第五章“理性”的末尾“立法的理性”和“审核法律的理性”中交代过了,处在进入到“精神”的门槛上。这里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的颠倒。《精神现象学》作为“意识经验的科学”从时间上把伦理安排在道德觉醒之前;而《法哲学原理》则按照逻辑把伦理放在道德之后,伦理被说成是用道德来理解抽象法的结果。在古希腊,“伦理”(ἦθος)本身只是风俗、习惯的意思(本意为“住处“”家”),罗马人用moral(伦常、习惯)来译这个词(来自Moro,意即停顿、居住),可以说是恰相对应,两者都没有后来的“道德”的含义。但随着斯多亚派对“普遍自我意识”的发现,这个概念开始向个人内心深化,被理解为不依外界环境为转移的道德;到了基督教中,则更将道德固定于内心的“良知(”或“良心”)。拉丁文中的这一意义演化也影响了希腊文的ἦθος(因为在罗马,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官方语言,学者们通常也是双语并用),于是“伦理”本身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意味。而这一理解逐渐也就成了西方哲学家们传统的理解。
在康德那里,Ethos、Ethik(伦理、伦理学)和Moralität、Moral(道德、道德学)都还是混在一起用的。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他一开始分科就这样说:“伦理学(Ethik)的经验性部分在这里将有可能特别地被叫作实践人类学,而合理性的部分有可能被严格地叫作道德学(Moral)”[26],而“伦理学”又被“称为道德学说(Sittenlehre)”[27]。这就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这一命名的由来。他后来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直接追溯了“伦理学”和“道德学”的历史渊源:
伦理学[Ethik]在古时候就意味着一般道德学说[Sittenlehre](philosophiamoralis,道德哲学),后者人们也称之为义务的学说。后来人们觉得最好把这个名称只转用于道德学说的一个部分,即转用于不服从外部法则的义务的学说上(人们在德语中恰当地给它找到了德行论[Tugendlehre]这个名称),这样,总的义务学说的体系就被划分为能够有外部法则的法权论[Rechtslehre](ius)体系和不能有外部法则的德行论(Ethica)体系。[28]
上面这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伦理学”(Ethik),一个是“道德学说”(Sittenlehre),一个是“德行论”(Tugendlehre),三者经过从古代到后来的演变而成为了同一个概念,它们共同与“法权论”(Rechtslehre或ius)相区别。而后者显然与黑格尔的“法哲学”不同,所指仅限于黑格尔的“抽象法”。此外,这三者还与来自拉丁文的Moral(道德学)重叠,如康德经常把Moralität和Sittlichkeit相等同(中文都译作“道德性”),或者把Sittenlehre和Moral,以及Tugend和Ethic互换着使用。[29] 可见在康德这里,只有法权论(法学,即黑格尔的抽象法)和道德论的区别,而没有道德(Moal、Moralität、Sitten、Sittlichkeit,包括德行Tugend)和伦理(Ethos)的区别。[30]
不过在这里,“早已自在地完成了”并作为后来发展起来的法和道德的“承担者和基础”的“伦理”,并不是他要在这个第三篇中来阐述的“伦理”,而是在人类文明之初作为前述“儿童的意志、伦理性的意志、奴隶的意志、迷信的意志”而存在的“伦理”,或者说“习俗(”Sitten,又译“风尚”)。它和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伦理”相比,只是潜在的伦理,如古希腊的家庭、公民(Bürger,即市民)共同体和城邦(即国家)。这些都属于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实体性的伦理,因此未达到所谓“希求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它们不是在“伦理”篇中所要讨论的主题,反而常常被当作批评和对照的对象,来衬托真实的伦理的性质。[37] 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主题是“德行(”ἀρετή,即Tugend,中文又译“德”或“美德”),它不是着眼于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着眼于人的性格、气质,所以这种伦理学又译作“美德伦理学(”区别于康德等人的“规范伦理学”);黑格尔却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常谈德行,这是因为伦理已经不再是特殊个人性格的形式了。在世界各民族中,法国人最常谈德行,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伦理生活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特性和行为的自然方式的问题。德国人则相反,他们更习惯于沉思,因此同一内容在德国人就采取了普遍性的形式。”[38] 这里要谈的正是这种普遍性的伦理,而那些个人的行为方式或风尚,则不过是“对伦理事物的习惯”,它“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39] 一旦伦理成了习惯或第二天性(第二自然),人就“死于习惯”,成了丧失精神的行尸走肉。[40]这显然不是黑格尔所要关注的“德国人”式的“伦理”。
叁
例如,伦理的第一个环节是“家庭”;而家庭虽然还带有直接性和自然性,它是“以爱为其规定”[41]的,但这种爱已经被“统一在自我意识中”,是一种精神性的“自我意识的爱”,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42] 爱不再是一种单纯自然性的冲动,而是体现为义务,即婚姻。当然,爱情自古以来就有,婚姻也是如此;但把爱情与婚姻结合为义务,这只是近代伦理的产物。如果说家庭和婚姻是个体性融入普遍性中,那么市民社会则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分离,首先是个体与个体由于财产的私有制而分离;但个体同时又通过“需要的体系”而处于相互的普遍关系之中(政治经济学),这种关系凭借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而得到维持和平衡。而这套体制已经可以看作“外部的国家”(§183)了,它现在缺乏的只是作为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国家精神。[43] 所以,近代国家的理念只是近代家庭和市民社会形成的结果,如黑格尔说的:“除家庭外,同业公会是构成国家的基于市民社会的第二个伦理根源。”[44] 但只隔了一页,黑格尔似乎恰好说了相反的话。在§256中,他在提出“市民社会的领域就过渡到国家”这一命题之后,在“附释”中却解释说:
在与其他法律上的人格的关系中促成着这些人格的那些个体,以及家庭,构成了两个依然是一般理想性的环节,从中产生出作为它们的真实根据的国家。——直接伦理通过贯穿市民社会的分裂而向显示为市民社会的真实根据的国家的发展,并且只有这种发展,才是对国家概念的科学证明。由于在这概念的科学进程中国家显现为结果,因为它是作为真实的根据而产生出来的,所以那个中介和那种假象都同样地把自己提升(aufheben)到了直接性。所以在现实中国家一般反倒是最初的东西,在国家内部家庭才形成了市民社会,而且正是国家理念本身分化成了这两个环节。[45]
这话太吊诡了!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产生出”它们自己的“真实根据”即国家,那么,到底谁是谁的“真实根据”呢?岂不是倒因为果吗?何谓“发展”?何谓“科学证明”?然而,如果我们熟悉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论,特别是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圆圈式进展的思想,这一切都不奇怪。黑格尔说,在科学的体系中,“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是由根据产生的。”[46] 显然,这里面隐含着一种目的论的观点,即开端只是一种目的意向,只有最后的结果才是这一意向的实现,最后的东西就是最初的东西的展开,而中间的过程则是手段或中介,是以最后的结果为根据的。但毕竟,最后的结果是不能和最初的意向相等同的。我们不能用最初的国家来理解现代国家的理念,因为那里面充斥着太多偶然的因素,会将国家的本质掩盖住;相反,我们必须用现代国家的理念来解读早期的国家,才能发现其中的本质及进一步发展的规律。
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乃至于整个伦理思想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通常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的指责多半都是出于这种误解,即将黑格尔对国家的理解停留在他之前的专制国家的形态上,这种形态与个体的自由完全脱节,甚至与之对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也包含有限制个体自由意志的环节;但这种限制一开始并不是外来的压制,而应该是个体自由意志的自律,即所谓“对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只不过由于黑格尔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把理想中的国家描绘为一种开明的君主立宪,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封建时代的特权(如长子继承制和等级制之类),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47] 但马克思的批判只涉及《法哲学原理》§261以后,即专门谈国家学说的地方。应该说,在人的伦理生活中,尤其是在市民社会中,哪怕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都还是人的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自由的人,也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异化了。
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仍然击中了后者的要害。最重要的是,在黑格尔的道德和伦理的关系中,道德一旦被伦理“扬弃”,似乎就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只剩下伪善并成为讽刺的题材,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只讲功利或利益而不讲道德了。所以黑格尔对国家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正是符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一个案例。[48] 就此而言,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道德化、理想化的批判。[49] 但这恰好表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在跟随现实的必然性时失落了道德的维度,而这正是我们下面要考察的。
肆
其实,黑格尔在一开始就已经留了一手。当他说,“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时,他明明知道人们肯定会发生误解,以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他就是不点破,甚至还蓄意隐藏自己真正的意思。[50]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现存事物的批判的锋芒也就被窒息在思辨的迷雾之中,而将真正的“应当”交给了“天意”去掌握。国家就是地上的“神”,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对内不存在国家是否“合法”的问题。至于对外,当他依照“法”的逻辑推演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时,他发现在现实中已经失去了“法”的准绳,哪怕各国已经签订了条约,“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主权为原则,所以在相互关系中它们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因此,国际法的那种普遍规定总是停留在应然上,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合乎条约的国际关系与取消这种关系的相互更替。”[51] 事情又回到了“丛林法则”的原点,只是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提升到了“一切国家间的战争”。并且这一回,“国家之间没有裁判官”,康德所设想的通过国际联盟来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也是不现实的,“带有偶然性”的。[52] 那么现在怎么办?是谁握有终极的“法(权利)”?所谓“希求自由的自由”难道要寿终正寝了吗?幸好,黑格尔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诉诸“历史”和“世界精神”。黑格尔设想,“世界历史是一个法庭,因为在它的绝对普遍性中,特殊的东西,即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家神、市民社会和民族精神都只是作为理想性的东西而存在,而精神的运动就是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把它展现出来。”[53] 但在这样一个世界精神的最高法庭上,主审法官居然是“战争”。尽管黑格尔为现代战争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和辩护,说战争是为了保留“和平的可能性”,战争应当是“人道的”,战争只涉及国与国的关系而不涉及私人生活,战争要按“国际惯例”来进行等等[54],他甚至主张战争对于人类是必要的,为的是维持“各民族的健康”,以免他们由于长久的和平而导致“腐败”和“堕落”。[55] 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一条本质的原则:强权即公理。然而,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既然战争已经不是任何人可控的盲目的必然性,没有谁能够保证,说只要一个国家所代表的法的理念更高,就注定能击败或灭掉另一个层次较低的国家,那么,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原则即“法的理念是自由”实际上在这里业已失效了。
但黑格尔仍然坚持战争是有理的,“世界历史不是单纯运用其强权的法庭,亦即它不是盲目命运的抽象的和无理性的必然性。相反地,由于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而理性在精神中的自为存在就是知识,所以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仅出自精神自由概念的必然发展,因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56] 这种辩护需要预设一个前提,即超越于整个人类之上而成为人的宿命的上帝之手。现在只剩下上帝本人唯一地能够成为这种“精神自由概念”的承担者,成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主体,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57] 这种国家就是再糟糕,它的“地上的行进”就是再无道理,也是不能反抗而只能服从的。但黑格尔的这种辩护已经为20世纪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所证伪,人们现在认识到,即使是国家,包括整个民族(Nation),一旦被神化,也是有可能犯罪的。
我曾在《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58]一文中提出,康德哲学相比于黑格尔有三大优势,一是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二是直指人心的人类学立场,三是保守的理想主义。最后这点最为根本。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康德把理想主义发展成一种保守的理想主义,即不是为了立刻按照理想来改变这个社会,而是将理性的理想变成人类永远不可放弃的标准,在普遍的堕落中仍然能够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和眼光,一种末世论的警示。这种观点曾被黑格尔嘲笑为:“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骚动;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59 但正是这点,可以用来补救黑格尔的那种一开始极其现实和功利、最终却在神意面前让批判的锋芒丧失殆尽的“法(权利)”的理念。对康德而言,由于人性的恶劣和败坏,意志的自律也好,道德法则也好,“目的王国”也好,“永久和平”也好,很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主观意愿的美好的理想中而不具有现实性;但仍然可以说,有这个理想和没有理想是大不一样的。有这个道德理想,哪怕明知它不能实现,也就有了一个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标准,而人类也就有了一个不断改善自身、不断从恶向善进步的可能。哪怕这种善在现实中最终只能是伪善,也能够显示出真正的善的威力,它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整个人类从野蛮的“自然状态”逐步提升到文明的过程背后,终究离不开它的推动,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道德史”。[60] 但道德理想的最主要的作用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批判的。它永远也不能成为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而只可能是相对的精神,却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让人顶礼膜拜的上帝的精神。这就是康德哲学的开放性和人类学精神的由来。
由此观之,黑格尔把伦理看作因其具有现实性而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最高理念,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没有看到伦理和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伦理本身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意义。他宁可把这种发展归功于信仰,即对于国家这个“神”的信仰,而道德的主观性则是对信仰的摧毁。“主观性的这种形态只有在高度文化的时期才能产生,这时信仰的诚挚性扫地以尽,而它的本质仅仅是一切皆空。”[61] 他甚至明确地说:
因为世界历史所占的地位高出于道德正当占据的地位,后者乃是私人的性格——个人的良心——他们的特殊意志和行为方式。……至于“精神”在本身为本身的最后目的所要求和所完成的东西——“神意”的一切作为——超越了种种义务,不负任何责任,不分善恶动机,这些个人义务、责任、动机,只有在个人道德方面才有。……“世界历史”在原则上可以不顾什么道德,以及议论纷纷的什么道德和政治的区分……[62]
在黑格尔这里,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类的说法都等同于废话,顶多是政客们的宣传手段。在他眼中,“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63],“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64] 所以,国家对于这样一些“群氓”不用讲道德,只有一种“道德”是隶属于国家之下的,这就是“自我牺牲”“英勇”,其余都是虚饰。这就不但违背了人类普世道德的“金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黑格尔的这种极端的非道德主义是他的法哲学在道德和伦理、道德和国家的关系上的最大的失误。在这方面,康德的道德主义尽管有形式主义的抽象空洞的毛病,却划出了一条人性的底线,即有道德不一定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但没有道德则肯定不会有人的自由。人是需要有理想的,有理想才能有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才能有历史的进步和批判的动力,否则的话,人与动物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区别。
伍、结论
通过对黑格尔的道德和伦理的关系的这番检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黑格尔对法和道德、伦理三者的自由意志基础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对人的道德的自由本质和理性法则相同一的思想,并且从理论上厘清了三者与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的关系,至今对我们深入探讨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仍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2)黑格尔对伦理道德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法(权利)”的关系进行了特别细致的思考,并以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眼光对这种关系的历史必然性作了透彻的解剖。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做到如同他所达到的那种深刻性和现实感;直到今天,他的法哲学还是我们讨论当代法和道德、伦理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里程碑。
(3)黑格尔法哲学所存在的问题,除了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唯心主义错觉,即把人类的道德伦理都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分解和辩证进展之外,还将人的自由意志的异化即国家形态视为人的本质的最高形式,最终将人的主观道德和客观现实生活都失落在这个“地上的神”给人所规定的必然命运之中,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批判和深思的。
(4)联系到哈贝马斯的讲演,我认为其中最关紧要的两句话是:“黑格尔虽然要保留从理性当中产生出其法则的那个自由概念,但是在他看来,一个无力地面对着流行习俗的抽象的应当太不现实了。最终的分歧在于,在黑格尔所关注的国家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是否能既考虑伦理生活的现实主义,又同时不剥夺道德批判之异议的最后发言权。”[65] 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Diskursethik)并不能解决这一冲突,因为它缺乏一个预先承认的共识,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实践理性的理想,这是“商谈”不出来的,而是一切认真商谈的前提。只有将康德的理想主义和黑格尔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走出困境。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有人认为,Moralität和Sittlichkeit不能(按照词典)译为“道德”和“伦理”,而只能译为“道德性”和“伦理性”——参见邓安庆:《“道德性”与“伦理性”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张力结构——哈贝马斯〈再论道德性与伦理性的关系〉之批判》,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该译法是他在所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译者序”中定下来的,他甚至主张译作“道德法”和“伦理法”,乃至于“道德性法”和“伦理性法”(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序”第35—37页)。不过,在所译该书末尾的德汉词汇索引中,他并未遵守这一译法。
[2] 这种用法应该来自古代罗马法。在拉丁语中,Jus就既有“法律、法则”的意思,又有“权利”的意思。但如果把Moralität和Sittlichkeit译作“道德法”和“伦理法”,不但在字面上缺乏根据,而且容易被引向“道德法则”和“伦理法则”的理解,而把其中的“权利”丢失了。
[3] Kant,Metaphisik der Sitten,in Kant’sgesammelt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der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Band VI,Berlin,1914,S. 237.
[4] 如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1796),谢林的《自然法权新演绎》(1795),但都不如康德的影响大。
[5]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323页(《哲学全书》§502附释)。
[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序言”第14—15页,译文有改动。
[7] 同上书,“序言”第11页,原文为:Wasvernünftig ist,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然而,在斯图加特的黑格尔故居展览馆(MuseumHegelhaus)的墙上悬挂的一张宣传招牌上赫然印着黑格尔的“名言”:“Alles,was ist,ist vernünftig.”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我搜遍了《黑格尔全集》,没有找到这句话。后来德国美因茨大学的克莱默(HeinerF. Klemme)教授来武汉大学讲学,我曾当面问过他,他也说他没有见到过黑格尔的这句话,还说他下次去斯图加特,一定要和管理人员说一下,说有个中国人指出了他们的失误。
[8] 虽然黑格尔也说:“现在这本书,就其包含着国家学说的内容而言,它应当只不过是将国家把握和展现为一种自身合理性的东西的尝试。作为哲学著作,它必须极其远离应当将一个国家如同它应当是的那样建构起来的想法;本书所能够教的,不可能是教导国家应当是什么样的,而是它这个伦理世界应当如何来认识。”(参见同上书,“序言”第12页,译文有改动。)但这里的意思决不是否认国家理念中包含“应当”,而是说要从伦理世界的现实中认识它的应当。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1);又参见第36页(§29)。
[10] 参见同上书,第10页(§4),译文有改动。
[11]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第309页(《哲学全书》§481)。同样,在他的《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篇的最后向“精神”篇过渡的关头,也已经作了这样的预示:“精神本质同样也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它并不以这一个个体的意志为自己的基础,相反它是自在自为的,是一切具有直接存在形式的人的绝对的纯粹意志”,以及“所以伦理实体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而自我意识则是伦理实体的现实性和定在,是它的自身和意志。”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264页。
[1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页(§7补充)。
[13] 同上书,第18页(§7附释)。
[14] 同上书,第31页(§21补充)。
[15] 同上书,第31页(§21附释)。
[16] 同上书,第34页(§26)。
[17] 同上书,第35页(§26补充)。
[18] 同上书,第37页(§30),译文有改动。
[1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7—38页(§30附释),译文有改动。
[20] 这里黑格尔着眼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在东方则不一定遵循这种程序,有的民族至今还是家国一体的自然经济社会。
[2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2页(§33附释),译文有改动。
[2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9页(§32附释),译文有改动。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24] 同上书,第43页。
[25] 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及其“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出发对人类劳动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商品”或“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才有的概念。
[2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7] 参见同上书,第1页。
[2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译文有改动。文中圆括号里是康德原有的加注,方括号里是引者注明的原文。
[2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出于法则的义务理念同时是行为的动机的那种一致或不一致称为道德性(合道德性)。”译者简直没有办法把Moralität和Sittlichkeit这两个概念区分开,只好把后者前面加一个“合”字,实属无奈。又如第233页:“所以,道德学说(Sittenlehre)的最高原理就是:按照一个同时可被视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而行动。——任何不具备上述资格的准则,都是与道德学(Moral)相悖的。”(译文有改动)再如第249页:“要么是德行义务[Tugendpflichten](officia virtutis s. ethica)”;以及该页:“但是,为什么道德学说(道德学Moral)通常(尤其被西塞罗)冠以义务论,而不也冠以法权论的名称呢?”再看第394页:“但是,说伦理学[Ethik]是一种德行论[Tugendlehre](doctrina officiorum vertutis,德性义务的学说),这是从对德行的上述解释中……得出的”,如此等等。
[30] 可见,邓安庆教授说我和杨祖陶老师把康德的Sittlichkeit译作“德性”和“道德”是一种“误译”和“误导”,认为“把表达‘伦理性’的概念翻译为‘德性’,会造成整个西方伦理学观念的混乱”(参见邓安庆:《“道德性”与“伦理性”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张力结构》,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第136页),这种指责是多么的荒谬。这暴露出批评者完全不知道康德的实践哲学与黑格尔的法哲学有什么不同,竟然要求用后者的译名去强译前者的术语。这就好比要求把柏拉图的εἶδος(eidos)不译作“相”或“理念”,而是强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全部改译作“形式”一样。到底是谁在“误导”和“造成混乱”呢?
[3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2页(§33附释),译文有改动。
[32] 黑格尔只有偶尔在为《法哲学原理》所做的“笔记”(Notizen,邓安庆译作“笺注”,其实不准确)中提到ἦϑος(Ethos),例如§151的笔记:“伦常(Sitte)——ἦϑος——古人完全不知道良心——里默尔:ἦϑος,伊奥尼亚语为ἐϑος——习惯,风俗——在希罗多德那里尤其指住所”(Hegel,Grunglinien derPhilosophie des Rechts,Beilagen,Herausgegeben von Klaus Grotsch und Elisabeth Weisser-Johmann,Band 14,2. Düsseldorf: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2010. S. 721)。
[33] 参见《法哲学原理》的§135—140,都是对康德的道德命令(自律)进行批驳。又参见《精神现象学》“良心:优美灵魂,恶及其宽恕”一节(《精神现象学》,第381页以下)。还可参见拙文:《康德黑格尔论伪善》,载《西方哲学探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251页。
[3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1页(§141)。
[35] 同上书,第162—163页(§141补充)。
[36] 同上书,第164页(§142)。
[37] 例如对安提戈涅(又译安悌果尼)的法律意识的引用(§144补充),对赫克里斯(又译“海格立斯”)的德行(Tugend)的“精神的自然史”的评价(§150附释),都是这种作用。
[3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70页(§150补充)。
[39] 同上书,(§151附释)。
[40] 同上书,第171页(§151补充)。
[41] 同上书,第175页(§158)。
[42] 同上书,第177页(§161)。
[43] 古希腊作为由各个移民城邦拼凑起来的“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少国家意识,只有在涉及共同利益时临时组成区域联盟,如特洛依战争、希波战争,事情过后又各自为政。黑格尔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既无家庭,也无私有财产,因此被人们误认为幻想,其实是对国家理念的一种超前的提升;罗马世界的国家概念也只是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在现实中却并没有获得实体性的地位(参见同上书,第200页,§185附释);又参见“序言”第10页:“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成为一个成语,指空虚理想而言)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伦理的本性的解释。”
[44] 同上书,第251页(§255)。
[4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2页。
[46]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页。
[47]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5—404页。
[48] 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但波普尔恰好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柏拉图、马克思一起归入乌托邦式的“整体社会工程”之列,显得很不靠谱。参见拙文:《开放时代的自我禁闭》,载《中西哲学三棱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94页以下。
[49]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最后两页直接表明了自己对黑格尔的道德批判立场,他痛斥黑格尔的“官府智能”是“简直令人作呕”,“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说他“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像官僚一样心胸狭窄,在对待‘人民的主观意见’的‘自信’时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臭架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1页。)
[50] 海涅说:“我有时曾看见他小心翼翼地向四面看看,怕人们也许会懂得他的话。……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只有亨利希·贝尔听到了这句话。”(参见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附录”第161页。)
[5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48页(§333)。
[52] 参见同上书(§333附释)。
[53] 同上书,第351页(§341),译文有改动。
[5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0页(§338—339)。
[55] 参见同上书,第341页(§324附释)。
[5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52页(§342),译文有改动。
[57] 同上书,第259页(§258补充)。
[58] 收入我的文集:《康德哲学诸问题》(增订本),北京:文津出版社2019年版,第363—374页。
[5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57页。
[60] “如果要问:人类(整体)是否不断地在朝着改善前进;那么它这里所涉及的就不是人类的自然史(未来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人种),而是道德史了”,参见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5页。
[6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0页(§140补充)。
[6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页。
[6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19页(§301附释)。
[64] 同上书,第323页(§303附释)。
[65] 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姜锋校,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
来源:哲学分析
编辑:王奕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26 22:15
【案例】
康德与伦理学相关的往来书信选集(一)
本选集的编译是李秋零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译注”的阶段性成果。
一、这些书信全部译自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第 X—XII卷(第 2 版,1922 年)。
二、标题前的序号为该书信在《康德全集》中的序号。
三、置于书信正文前面的“解说”译自《康德全集》第XIII卷的编者注中与整封信有关的部分,包括该书信的现存地、历史上的刊印情况等。
本选集刊登于《伦理学术4——仁义与正义:中西伦理问题的比较研究》第1-16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1
【X. 73】40[38]致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1768年5月9日
【XIII. 35】解说:
多尔帕特大学图书馆。
在第二版中依据该信在多尔帕特制作的一张照片校正。曾在默克尔(Garlieb Merkel)的《文学与艺术报》上刊印,1811年,第10期,第39-40页(政论刊物《观察家》[Dei Zuschauer]的副刊),迪德里克斯在《老普鲁士月刊》发表,第28卷,1891年,第194-195页。
康德写错了年份。在第一版中亦是如此,但迪德里克斯证明,格曼在1768年才受聘为副校长来到里加(同上,第196页)。在1768年4月14日,此人在哥尼斯贝格向财政部请求允许接受聘任。根据5月20日从柏林发出的指示,【36】他于6月3日收到允许(哥尼斯贝格国家档案,财政部110,g)。此信据此排序。
赫尔德(JohannGottfried Herder,1774—1803)于1762—1764年在哥尼斯贝格上大学,与康德有友好的关系。自1764年始,他在里加任教会学校代课教师。参见赫尔德在《促进人道书简》(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中的表述,第79封;以及苏凡(B.Suphan):《康德的学生赫尔德》(Herder als Schüler Kants),载《德国语言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哈勒,1872年,第IV期,第225-237页。
【X. 73】尊贵的至堪敬慕的先生:
我抓住这个机会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和友谊。由于我在写信时的习惯性疏忽,可能会使这种敬意和友谊显得很可疑。我以某种虚荣心分享了您最近的作品在世界上获得的非同一般的赞赏,尽管这样一些作品纯然是出自您自己之手,而您在我这里所得到的那种指导我是无功可居的。倘若批评不是自身就包含着使天才胆怯起来的弊病,而判断的精细使得自我认同变得十分困难的话,我就会希望,根据我从您那里得到的那个小作品,可以预料您终将以本是智慧之美惠女神的、其中惟有蒲柏令人钦佩的那种诗艺成为大师。鉴于您过去的才华施展,我更加高兴地瞩望着才华横溢的精神不再被年轻人情感的热烈冲动所驱使而谋求安宁的时刻,这种安宁是温存的,但【X. 74】又是感情丰富的,仿佛是哲学家的沉思的生活,恰恰是神秘主义者所梦想的东西的对立面。根据我对您的认识,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您的天才的这个时期,期待着这个时期为您的天才所拥有的一种心境。在所有的心境中,这种心境对世界最有益。其中,蒙台涅地位最低,而据我所知,休谟地位最高。
就我而言,由于我无所眷恋,对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意见都深感无所谓,时常把整个大厦翻转过来,从各种角度进行考察,以便最终找到我能够由以出发真实地描绘这座大厦的角度。所以,自从我们分手以来,在许多问题上,我都给其他见解以地位。而由于我的注意力主要针对认识人的能力和偏好的真正规定和局限,我相信,在涉及道德的事情上,我终于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目前,我正在研究道德形而上学。在这里,我自诩能够提出显明的、蕴意丰富的原理以及方法。据此,那些尽管非常流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毫无成效的努力,如果它们应当提供什么用处的话,就必须以这种认识方式建立起来。我希望,如果我那总是变化不定的健康状况不阻碍我,就在今年完成这项工作。
我恭顺地请您代我衷心地问候贝伦斯先生,并向他保证,人们即便从不写出来,在友谊上也是很忠实的。将给您递交这封信的格曼先生是一个有良好教养而且勤奋的人,他会博得您的好感的,里加学校将在他身上获得一个能干的员工。向您致以真诚的敬意。
尊贵的阁下
您恭顺的朋友和仆人伊·康德
1767年5月9日
于哥尼斯贝格
2
【X. 96】57 [54]致约翰·海因里希-兰贝特
1770年9月2日
【XIII. 45】解说:
哥达公爵府图书馆。
在《兰贝特往来书信集》刊印,第I卷,第351-355页,但有一些省略和偏离。据此有《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康德短文全集》,第III卷,第110-114页;蒂夫特隆克:《伊曼努尔·康德杂文集》,第II卷,第587-591页;罗森克兰茨和舒伯特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莱比锡,第I卷,第358-361页;哈滕施泰因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仔细校订的全集版,第X卷,第480-483页;哈滕施泰因按编年史顺序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第VII卷,第661-664页。
【X. 96】至为尊贵的先生、至堪敬慕的教授先生:
借此机会,由我论文答辩的辩护人、一位能干的犹太大学生,把我的答辩论文呈送给至为尊贵的阁下,以求尽可能地马上根除对我长久没有回复您的珍贵来信的一种令我不安的误解。不是别的,正是这封来信中映入我眼帘的震动的重要性,导致我长时间地推迟依照您的动议回信。由于我在您当时注目的那门科学中已经研究多年,以求发现它的本性,并尽可能地发现它的常驻不变的、自明的法则,所以,我所希求的,莫过于有一位具有如此明显的洞察力和见识的普遍性、此外我经常认为其思维方法与我的思维方法相一致的人物,【X. 97】贡献出他以联合起来的检验和研究来为一个稳固的大厦绘制蓝图的努力。我决定要做的事情,不能少于提供我视之为这门科学的形象的一个清晰草图和这门科学的独特方法的一个确定理念。这个计划的实施,把我拖入了对我来说新颖的研究,由于我繁重的学校工作,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推迟它们。大约一年前以来,我可以自夸地说,已经达到了那个概念,我不再费心改变它,但也许可以扩展它。通过这个概念,所有种类的形而上学问题都被按照完全可靠的、简易的标准加以检验,并且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或者不可以解决的。
整个这门科学的草图,就其包含着它的本性、它的一切判断的最初源泉和人们依之就能够很容易地继续前进的方法而言,可以在一个相当小的篇幅里,亦即在不多几封信中呈交给您,请您做出缜密和富有教益的判断。我期望,这将会产生一个出色的结果,因此特别请您允准。不过,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计划中,如果能够提出某种完善的、持久的东西来,那么,耗费一些时间也根本算不得损失。因此,我必须请求您,为了我而始终如一地坚持参与这些研究的美好意愿,并答应我,在此期间为实施这个意愿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为了从折磨了我整整一个夏天的不适中得以恢复,而且尽管如此也要处理一些琐事,我打算到今年冬天再把我关于纯粹的道德世俗智慧的研究列入日程,并且加以完成。在这里,找不到任何经验性的原则,仿佛就是道德形而上学。鉴于形而上学的形式已经改变,它将在许多问题上为那些极为重要的意图开辟道路。此外我觉得,鉴于目前还如此糟糕地选定的实践科学原则,它同样是必要的。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倘若我能够带着我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几篇论文前往您那里的话,我将利用您过去给我的允准,【X. 98】把它们呈送给您。我坚决保证,不出现任何您认为不具有完美的自明性的命题。因为如果它不能得到您的赞同,那就没有达到使这门科学排除一切怀疑,建立在毫无争议的规则之上的目的。现在,您对我的答辩论文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有见地的判断会使我感到愉快,受到教益,因为我还打算给它加上几个印张,以便提交给下届博览会,其中我想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更好地规定自己的思想。第一章和第四章可以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而跳过去,但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尽管我由于不适,写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我还是觉得包含着一个大概值得仔细地、详尽地阐述的题材。最普遍的感性法则在毕竟仅仅取决于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的形而上学中不适宜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看来,必须有一门完全独特的、尽管纯然是否定性的科学(一般现象学)走在形而上学前面,其中为感性的原则规定其有效性和界限,以便它们不至于像迄今几乎总是发生的那样,搅混了关于纯粹理性的对象的判断。因为空间、时间和在其关系中考察一切事物的公理,就经验性认识和所有的感官对象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确实包含着一切显象和经验性判断的条件。但是,如果某种东西根本不是作为感官的对象,而是通过一个普遍的和纯粹的理性概念,作为一个一般的物或者实体等被思维,那么,倘若人们想把它们归摄在上述感性基本概念之下,就会产生出非常错误的立场。我也觉得,而且也许我如此幸运地通过这些尽管还很不完善的尝试而争取到您的赞同,即这样一门将使真正的形而上学避免感性事物的所有这样一些混入的预备学科,不必费太大的劲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一种适用的详尽性和自明性。
请您今后继续保持您对我的友谊,友好地【X. 99】参与我这些尽管还微不足道的科学努力。如蒙允准,我还代给您送这封至为恭顺的信的马库斯·赫茨先生请求,请您允许他有时就他的研究向您请教。我可以介绍说,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很勤奋的、能干的年轻人,他会遵从和采纳任何一个好的建议。致以崇高的敬意。
至为尊贵的阁下
您至为恭顺的仆人伊·康德
1770年9月2日
于哥尼斯贝格
3
【X. 143】79 [71]致马库斯·赫茨
1773年年底
【XIII. 60】解说:
戈特霍尔德·莱辛。
刊印:罗森克兰茨和舒伯特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莱比锡,第XI卷,1,第63-67页;哈滕施泰因按编年史顺序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第VII卷,第694-697页。这封信可能是赫茨致康德的一封已佚失的信的回信。康德在这封信中谈到一封给他的来信,而且这种猜测是可以理解的,即它是附在同样佚失的尼古莱来信(第76a封信)之上的(参见第77封信)。康德在他的信中所讨论的事情,未出现在赫茨过去的来信中。这封信的日期不完全确定。康德在尼古莱邮寄之前就了解《德意志图书总汇》第20卷第1册,这种可能性存在,但这种了解不可能发生在8月份之前,因为在这一册中,提到了发生在7月12日的一起丧事。在这种情况下,这封信中当然不十分明确的说明有助于把日期确定为这年年底。
【X. 143】尊贵的先生、至为尊贵的朋友:
得知您的工作进展顺利,我感到高兴,但更使我高兴的是,在您给我的来信中,我看到了友好的怀念和友谊的标志。您能在一位强干的教师指导下进行医药学实习,按照我的愿望,这是很合适的。在年轻的大夫学会应当怎样正确地开始工作的方法之前,教堂的墓地是不会被提前占满的。请多多进行各种细致的观察。理论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常常更多地不是为了说明自然现象,而是为了使概念易于理解。麦克布里德的医药学(我相信,您已经知道它了)就是以这种方式让我很喜欢。一般来说,我现在的健康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原因就在于,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对我不利的东西。由于我神经过敏,药物对我来说无异于毒药。如果我上午由于胃酸过多而感到难受的话,我惟一使用的药物,就是和水服用半汤勺金鸡纳树皮,就连这也不是经常的。【X. 144】我认为,这种药要比别的吸收剂好得多。通常,为了使自己强壮起来,我并不每天都服用这种药物。这种药物还曾经导致我的脉搏间歇跳动,类似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傍晚。当时我很担忧,直到后来推测到了原因才作罢。一旦排除了这种原因,那种症状也就消失了。不过,您可要多多研究各种类型的体质。我这种体质会被任何不是哲学家的医生弃之不顾的。
但是,您经常在博览会书目中“K”这个词条下寻找我的名字,这是白费力气。在付出许多努力之后,对我来说,最简便易行的办法,莫过于利用已经写好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作品来炫耀这个名字了。然而,由于我力图改造长期以来半个哲学界劳而无功地研究的那门科学,并且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收获,以至于我自认为已经掌握了那个学术概念,它将完全解开以往的谜,把自我孤立的理性的方法置于可靠的、易于运用的规则之下,所以我至今仍然固执地坚持我的计划,在我把我的布满荆棘的坚硬地基平整完毕,为普遍的研究做好准备之前,绝不受任何成名欲的引诱,去到一个比较轻松、比较随意的领域中寻求荣誉。
我不相信,许多人曾经试图依照理念构建一门全新的科学,同时也完全地实现了理念。但是,您几乎无法想象,就分配恰如其分的名称的方法而言,要付出多少劳动,花费多少时间。但是,在我面前闪烁着一个希望,除了您之外,我没有冒自命不凡之嫌把它告诉任何人。这个希望就是由此而以一种长久不变的方式使哲学发生另一种转变,对于宗教和道德来说,这种转变要远为有利得多。同时,还要使哲学获得一个形象,这个形象能够吸引住矜持的数学家,使他认为哲学是能够研究的,而且也是值得研究的。有时,我仍然希望能够在复活节前完成这部作品。不过,即使考虑到经常发作的小毛病总是造成【X. 145】工作的中断,我还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复活节后不久,我就要完成这部作品。
我热切地期望能够看到您在道德哲学中的研究得以发表。但是,我毕竟希望您在其中不要使用那个实在性概念,它在思辨理性的最高抽象中是如此重要,在运用于实践的东西时则是如此空洞。因为这个概念是先验的,但最高的实践要素却是快乐和不快乐,它们都是经验性的,它们的对象无论来自何处,都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仅仅一个纯粹知性概念是不能说明那种仅仅是感性的东西的法则或者规定的,因为在这方面,纯粹知性概念完全是未被规定的。道德性的最高根据必须不仅仅推论到满意,它必须自身就在最高程度上感到满意。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然思辨的表象,它必须具有推动力。因此,尽管它是理智的,却必须与意志的最初动机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如果我的先验哲学得以完成,我将非常高兴。它真正说来就是对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在这之后,我将转向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有两个部分,即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其中,我将首先发表道德的形而上学。现在,我已经在为它的即将面市而高兴不已了。
我已读过你对普拉特纳的人类学的书评。我虽然没有自动地去做一个评论家,但是,此时从这篇书评中看到评论家的技艺有所进展,仍然感到非常高兴。今年冬天,我第二次举办一个人类学的私人讲座。现在,我想使它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不过,我的计划完全与众不同。我的意图是想通过这个学科开启一切科学的源泉,即开启道德的源泉、技艺的源泉、交往的源泉、塑造和治理人的方法的源泉,因此,也就是开启一切实践的东西的源泉。这样,在这之后,我就不再一般性地探索人性变异的可能性的最初根据,而是更多地探索其他的现象及其法则。因此,完全删掉了对身体的器官与思想发生联系的方式进行的细腻研究,在我看来,这种研究永远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也始终不懈地坚持进行观察。这样,我的【X. 146】听众们自始至终从未感到学习枯燥,相反,他们由于有机会不断地把自己的日常经验与我的评论进行比较,反而觉得学习十分有趣。在我看来,这种观察说很受欢迎。在这期间,我力图使它成为学校青年人的技艺、聪明乃至智慧的一个预习。除了自然地理学之外,它与其他所有课程都不同,可以叫作世界的知识。
我在《图书总汇》的前面看到了我的雕版像。这是一个令我有点不安的荣誉。因为如您所知,我非常忌讳骗来的颂词和对引人注目的强求的一切假象。这虽然不怎么入时,但很得体。然而,得知这是我过去的学生偏爱我的举动,我还是很高兴的。这种偏爱是非常可亲的。在同一册中,还出现了对您的作品的书评,它证实了我的担忧:为了揭示新的思想,以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独具匠心和根据的重要性,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以便深入地思索这个题材,直到能够完全地、轻松地了解这个题材为止。向您致以真诚的爱慕和敬意。
您至为恭顺的仆人和朋友伊·康德
4
【X. 175】99 [90]致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
哥尼斯贝格,1775年4月28日
【XIII. 72】解说:
苏黎世中央图书馆。
刊印:《改革宗瑞士教会报》(Kirchenblatt fur die reformirte Schweiz),第VI年度,伯尔尼,1891年,第25号和第30号。
【X. 175】我的可敬的朋友:
年轻的冯·霍尔斯泰因-贝克公子的陪同人卢斯特先生和社交侍臣冯·内格莱因先生希望我能把这位主人引荐给一位在我们这里并且到处都极受尊重的人物。我是在给这位公子上课的时候认识他的,他是一位具有天赋和良知的年轻人,计划到瑞士去学习。我夸耀了您对我的亲切态度,说您将在瑞士的风土人情等方面给这位公子提供有用的、详尽的信息。您总是尽可能地赞助一切优秀的计划,这种高贵的乐于助人精神是众所周知的。
至于您委托我的私事,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把步兵苏尔策一事办成。我要看一看,在今年夏天训练期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X. 176】苏尔策通常举止良好,每个发薪日都可以从您上一次汇寄来的钱中得到一笔补贴。不过,这都被用来改善他那菲薄的月饷了。因此,为了不使这种资助中断,我已遵嘱借给他3个帝国塔勒或者1个杜卡特,这些钱足够他维持到6月底。他希望,到时候能通过您的斡旋而得到今后的补助。关于那笔钱,我已经把收据以及苏尔策让人为他写的一封短信一起寄出了。
您要求我对您关于信仰和祈祷的论文做出判断。但是,您知道自己为此找的是谁吗?是这样一个人,就心灵最隐秘的意念来说,他只知道最纯洁的正直,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任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够经受住考验的办法。同约伯一样,他把谄媚上帝和内心的认信视为一种犯罪。内心的认信也许迫使人产生恐惧,在自由的信仰中,心灵是不能与它共鸣的。我把基督的教诲与我们关于基督的教诲所拥有的信息区别开来,而为了提纯基督的教诲,我试图首先把道德教诲与《新约》的所有章程分别开来。道德教诲无疑是福音的基本教诲,其余的东西只能是福音的辅助教诲,因为后者只是说:就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称义而言,为了给我们的脆弱提供帮助,上帝做了些什么,而前者则是说,为了使我们配享这一切,我们必须做什么。即便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在自己这方面有所作为的那个奥秘,而只是坚信由于上帝的律法的神圣性和我们心灵的无法克服的恶,上帝必定在其意旨的深处隐藏着我们能够谦卑地信赖的、对我们缺陷的某种补充,只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以便不辜负那种补充,那么,在关涉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就受到了充分的教诲,神恩使我们获得援助的方式,可能就是神恩自己愿意的方式。当我在事实和启示出来的奥秘的混合中寻觅作为基础的教诲时,我在福音中所发现的道德信仰恰恰就在于:我们因此而对上帝寄托的信赖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无需一种好奇心,想知道上帝要如何完成这件事工的方式,遑论如此【X. 177】放肆,竟要依据一些信息,鉴于自己灵魂的灵性来用魔法召唤这种方式。在基督的时代,为了不顾其在犹太教那里遇到的反抗而率先开创一个废弃世上一切章程的纯粹宗教,并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它,奇迹和宣示出来的奥秘是必要的。在这方面,许多人为的论据也是必要的,它们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一旦善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中意念的纯粹性的教诲(无需宗教妄念任何时候都在于其中的所谓崇拜谋求,上帝已经以一种我们根本不必要知道的方式补充了我们的脆弱所欠缺的其他东西)在世界上作为惟一包含着人的真正救赎的宗教充分传播开来,以至于能够在世上保存下来,那么,既然大厦已经建成,脚手架就必须拆除掉。我尊崇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们的信息,谦卑地信赖他们给予我们历史信息的和好办法,或者也信赖上帝在其隐秘的意旨中可能隐藏着的别的东西;皆因即使我能够规定这种办法,我也根本不能由此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这种办法仅仅涉及上帝所做之事,但我却不能如此放肆,斩钉截铁地把这种办法规定为我惟有以它才能从上帝那里期待救赎的现实办法,并且可谓使灵魂和灵性变得沉重;因为这是些我与其产生的年代距离不够近、无法做出这种危险且肆无忌惮的裁定的信息&除此之外,尽管我肯定无疑地知道,虽然这件好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我却依然认信它、保证它,并以此来充实我的心灵,但这根本不能使我更配享这件好事的赐予,而是为了能够分享这种属神的、共同起作用的力量,我别无他法,惟有使用上帝赋予我的自然力量,以使我不致于不配他的这种援助,或者如人们喜欢说的,不致于无能接受这种援助。
【X. 278】至于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约》章程,我把它们理解为人们惟有通过历史信息才能够获得确信,但尽管如此却作为灵性的一个条件被规定为信条或者戒律的一切。我把道德信仰理解为对属神援助的无条件信赖,这是就尽管我们非常努力也毕竟不能掌控的一切好事而言的。任何一个人,在他有朝一日对道德信仰敞开自身之后,就能够无需历史的辅助手段,自动地确信道德信仰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尽管不这样敞开自身,他就不会自动地达到这一点。现在,我坦率地承认:就历史的东西而言,我们的《新约》经卷从未能够具有某种威望,使得我们会敢于非常信赖地把自己交付给这些经卷的每一行文字,特别是由此削弱对惟一必要的东西的注意,亦即对福音的道德信仰的注意。而道德信仰的优越性恰恰在于,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被集中到我们的意念的纯粹性和一种善的生活方式的责任心之上;而毕竟使得神圣的律法任何时候都浮现在眼前,并不断地告诫我们对属神意志的哪怕极小的背离都是要受到一位铁面无私的公正法官的审判的。对此,任何信仰表白、呼唤神圣的名字、遵守崇拜的戒律都无济于事,但尽管如此仍被给予令人慰藉的希望:如果我们信赖我们不知道的、深奥莫测的属神援助,尽我们之所能行善,那么,不用任何值得称赞的事工(无论是哪一种崇拜),我们就应当分享这种补充。显而易见,使徒们把福音的这种辅助教诲当成了它的基本教诲,而且把也许从上帝那方面来看确实可以是我们的灵性的根据的东西视为我们的灵性所必需的信仰的根据,不是把神圣导师的实践的宗教教诲当作根本的东西加以盛赞,而是不顾那位导师如此明确并且【X. 179】经常表示的反对,盛赞对这位导师自身的尊崇和一种通过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来祈求恩惠的方式。然而,这种方法更为适合当时的时代(他们也是为当时的时代写作,没有顾及后来的时代),而不是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新的奇迹必然被与旧的奇迹对立起来,基督教的章程必然被与犹太教的章程对立起来。我不得不就此住笔了,向您可敬的朋友普芬宁格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其他的东西只好留到下封信再谈了(现在,这类信可以很容易通过夹带寄出)。
您的正直的朋友伊·康德
5
【X. 175】100 [91]致约翰-卡斯帕尔-拉法特
哥尼斯贝格,1775年4月28日
【XIII. 72】解说:
多尔帕特,第III卷,第8封。
在《柏林政治与学术事务信息报》(Berlinischen Nachrichten von Staate—und gelehrtee Sacher)刊印,第187期,1846年8月13日。然后是我们在第一版的刊印。
【X.179】我现在有机会为我上一封中断的信再附上一些东西,我宁可不完备地利用这个机会,也不愿根本不利用。预设:没有一本书,无论它出自什么权威,甚至是我自己的感觉所遇到的启示,关于(意念的)宗教能够强加给我某种不是通过我心中的我必须据以对一切做出解释的神圣律法而成为我义务的东西,而且我不可以冒险用并非产生自这种律法的,未被伪饰的和不容置疑的规定的虔诚证明、认信等来充实我的灵魂(因为规章虽然能够产生戒律,但却不能产生心灵的意念),所以,我并不在福音中寻找我的信仰的根据,而是寻找它的巩固,并且在福音的道德精神中找到了那种东西,它把关于福音的传播方式的信息和把它引入世界的手段,简而言之,把我有责任的事情与上帝为我的利益而做的事情清晰地区别开来,因而没有强加给我任何新的东西,而是(无论这些信息是怎么样的)毕竟能够给予善的意念以新的力量和信心。就我上封信关于《圣经》的两个相互联结但又不同类的部分的分离以及把它运用于我的方式那一段的解释,就说这么多。
【X. 180】至于您的要求,即就关于信仰和祈祷的(在《杂文集》中的)思想说出我的判断,则请见下文。基督之教诲的根本的和最出色的东西恰恰是:他把一切宗教的总和设定在这一点上,亦即是从信仰中,也就是说从对上帝在这种情况下将补充其余不为我们所掌控的善的无条件信赖中的一切力量出发的正直。这种信仰教诲禁止一切要知道上帝如何做这件事的狂妄,和从自己的自负出发来规定就他的智慧的手段而言最合适的东西的放肆,以及一切按照所采用的崇拜规章对恩惠的谋求,并且除了对如果我们在事情取决于我们时通过我们的作为使自己不至于不配享这种好事的话,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总应当分享这种好事的普遍的和不确定的信赖之外,不给人们在所有时代里都喜欢的无限宗教妄念留下任何东西。
6
【X. 485】297 [277]自丹尼尔·耶尼什
1787年5月14日
【XIII.196】解说:
多尔帕特,第I卷,第120封,第527-530页。
【X.485】尊贵的、令人尊敬的教授先生:
倘若在对我的家乡的所有追忆中,对享受尊贵的阁下精彩课程的追忆下自身就已经对我来说是最甜美的和最珍贵的,它也必定在我目前的状况中让我觉察到,因为我处在一些本地学者的聚会中,罕有不听到提起您的名字的。《信使报》上关于您的哲学的书信造成了一种至为缠人的轰动,德国所有的哲学头脑似乎自雅各比争执、《结论》和这些书信以来,出自对门德尔松的《晨课》以之普遍遭到嘲笑的思辨哲学的冷漠,都被唤醒对您、我的教授先生至为强烈的兴趣。难以置信的是,迈纳斯和费德尔到处,因而甚至在格廷根人那里都如此少有声望和分量,在其造访不伦瑞克时,我结识了相当一大批格廷根人:一切都在至为热烈地研究您的《批判》,而我从格廷根收到的如此之多与此相关的书信表明,他们欣赏您,因为他们理解您。卡姆佩、特拉普和施图夫自一个季节多以来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新近,后者关于您的《批判》告诉我:一切神义论和沃尔夫派的卷册都是给他们的初级课本。81岁的耶路撒冷自己新近对我说:“我太老了,不能跟着康德思辨,但他在《柏林月刊》关于确定方向的文章是我的信仰告白的共鸣;门德尔松的先天证明只是通过康德哲学发现自己遭到报复的健康人类知性的打盹。”心理学杂志的编者、不伦瑞克宫廷的王子家庭教师波克尔斯【X. 486】,与最小的王子们曾计划去哥尼斯贝格旅行,但由于一次偶然事故而搁浅:在这期间他让人从格廷根给自己搞到您的道德和人类学的抄本,他自半年来给王子讲授。甚至在我到荷兰海牙的14天中,我也在我逗留的第二天偶然地发现了一位凡·卢瑟尔先生,他很了解德语文献,说很好的法语,在那里的蒂雷纳元帅酒店里面,手持您的《批判》寂坐他的房间里,我在此后极受他欢迎,尽管我在这个地方有完全不同种类的事务,仍必须每天4—5个小时陪他读过整整两个星期。以同样的方式,我在莱顿发现一星期之后成为法学博士、专攻民法的少尉凡·霍根多普是您的哲学的一位热烈的拥护者。与前者凡·卢瑟尔,我自半年来处于哲学通讯之中:他把我转告他您的道德体系的摘要和说明的手稿的两个印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人刊登在海牙的一家定期出版的刊物《哈格尔评论》上了,他在四星期前以荷兰原版赠送了我。
我的教授先生,您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在我认识的学者中间遇到了比您的《批判》异常多的抵触,且人们不可能愿意让自己确信,自然把道德建立在如此深邃的根据之上。在这期间,一些格廷根人狂热地写信告诉我他们的极为新颖的和引人注目的真理:一切都只是热切地盼望着您的道德形而上学。您的《自然科学初始根据》这个他们的哲学体系的试金石,迄今还少有人读,而读过它的人认为完全比《批判》自身更难懂,演绎的章节除外。
您在《德国丛书》上的评论者应当是费马恩的修道院院长皮斯托留斯,哈特雷的译者,他对您的《基础》的书评尽管所有表面上的严格却不够深入,【X. 487】但由于道德中的头脑都因通俗性而走调,所以获得了许多追随者。
我的教授先生,我在哥尼斯贝格最后一年半,在诸多完全不同类的事务中间,无论如何偏爱和确信您的体系,关于您的体系却陷入了昏昏沉睡。现在,由于对您和您的哲学的如此之多的回忆,因为如您所见,我从所有的方面仿佛是为您的哲学所围绕,我自己从这种沉睡中苏醒过来了:因为我能是别的样子吗?
随着六月份的来临,我与我的黄褐色马来人第二次到荷兰去,同时漫游到法国的佛兰德,在那里我给他请一位游伴,一位马尔蒂尼伯爵。
我希望米迦勒学期到格廷根去,以便在海涅和施勒策尔们中间学习。
我期望着您至为善意的惦念,并荣幸地自称为
尊贵的阁下
我至堪敬慕的教授先生
您至为感激的丹·耶尼什
1787年5月14日
于不伦瑞克
来源:伦理学术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j5-KI_0lqsYloEwPp6FIw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28 21:34
【案例】
康德论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道德价值
我乐意为亲友们效劳,可是——唉!这样我就有对他们偏爱之嫌了。/于是有一个问题折磨着我:我是否真有道德?/这里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尽量蔑视他们,并心怀厌恶地去做义务要求我做的事吧!(转引自古留加,第164页)
这是席勒的一段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诗文,体现了席勒本人和某些研究者对于康德著名的义务原则的评价。然而,这个评价准确吗?
康德对于义务原则的典型论述主要出现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中,其基本原理是:某一行动具有道德价值,当且仅当该行动是出于义务而作出的。(cf. Kant,1968a,S.397-399.下引康德外文文献仅标年份和页码)①康德的道德哲学被后人称为义务论,与这条被通俗地表述为“为义务而义务”的原理是分不开的。这条义务原理引起了很多困惑:比如,该原理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再如,康德将出于义务而行动严格区分于出于爱好(如同情心等情感原因)而行动,并提出后者不具有道德价值,这是否意味着康德所主张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为了尽义务而行善的观点?上面所引席勒的诗句正表达了这种困惑。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澄清围绕出于义务而行动这一观念所产生的疑问,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康德的义务原理。我将从介绍康德《奠基》一书论证的出发点和思路入手,初步阐明康德出于义务而行动这一原理的基本含义;接着,我将回应三种对于康德义务原理的最主要的疑问,其中包括席勒式的质疑;最后,我会简要地阐释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特质。
一、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道德价值:对康德思想的重构
要理解上述义务原理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康德在《奠基》中论证的目标、路径和出发点。这是康德讨论义务问题的起点。康德在该书“导言”部分对其目标做了明确说明,那就是“寻找并建立道德性(Moralitt)的最高原则”(1968a,S.39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德采用的论证路径是:首先,承认日常道德知识具有合理性,对之进行解析,从中提炼出普遍的道德规则(第一章);其次,在更高的道德形而上学层次上,以定言命令的形式更加完备地表述道德原则(第二章);最后,以理性批判的方式证明道德原则的可能性(第三章)。从论证模式来看,前两章采用分析的方法,从既有的道德常识入手,分析已经蕴含在其中的理论预设,挖掘出深层次的、哲学性的道德原则;最后一章则采用综合的方法说明这种原则的可能性。这与他在讨论科学知识时的做法是类似的:康德的知识论承认当时通行的(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数学知识和(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可靠的,所要做的是追问这些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说阐明其纯粹理性根据。
康德论证的出发点是某种在他看来大家公认的道德常识,这就是:只有善良意志才能无限制地被视为善的,或者说才具有绝对的价值。鉴于这是常识,康德并未进行正式的证明,而只是在与其他善物的比较中稍加说明。康德提出,其他东西,无论是才能、性情,甚至是被古代哲学家所推崇的自制等内在品质,都只是有条件的善,因为它们既可用于行善,也可用于作恶,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什么样的意志在支配这些东西。(1968a,S.393-394)比如说,一个医生在动手术救治病人时的冷静,与一个恶棍在犯罪时的冷静相比,都是情绪方面的适度,本身并无差别,但是却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这充分说明了冷静只是有条件的善。所以,只有支配这些东西的善良意志,才是无条件地善的,或者说自身具有绝对价值。对此,康德强调说,善良意志并不因为它产生了什么结果或作为手段是善的,“只是因为它的意愿而是善的,也即它自在的是善的”。(ibid,S.394)
值得关注的是:康德为什么会以善良意志本身具有绝对价值这一命题作为论证的出发点?事实上,被文明社会接受为道德常识的决不限于康德所提出的这个命题。无论是孔夫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基督教的黄金律“你愿意他人怎样对你,你就怎样对待他人”,甚至某些具体的规范如“不能杀人取乐”,都可看做道德常识。康德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些命题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开端,是由其道德哲学的基本主题和思路所决定的。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主题是意志和理性的关系,这也是《奠基》一书论证的内在思路。特别是从《奠基》前两章论证的演进来看,康德正是从善良意志出发,寻找善良意志之为善良意志的条件,而这就是普遍的形式法则或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从根本上说,一个善良意志其实就是被纯粹理性所规定了的意志。基于这种思路,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道德常识相比,善良意志具有绝对价值这个命题,最适合于引出上述基本主题。
理解了康德论证的出发点,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转而阐释义务(Pflicht)概念。我认为,这一转换的理由在于:义务概念中包含了善良意志的概念,通过分析义务概念,我们可以理解善良意志之为善良意志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因为,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其理性并不总是能够完全规定意志,我们的本能、各种情感偏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意志。由此,我们的行动体现出来的也许只是我们的爱好,而非善良意志的条件。我们要从处于这些限制和障碍的意志中寻找出决定道德价值的条件或根据。这就进入了对义务概念的阐释。
康德需要做的是表明义务概念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联。他把这种关联表述为:某一行动是有道德价值的,当且仅当这个行动是出于义务(aus Pflicht)的。这是康德对义务原则的基本表述。这个命题意味着:只有那些出于义务的行动,才是有道德价值的——这表明“出于义务”而行动作为道德价值的起源具有排他性,一切出于其他动机的行动均无道德价值;只要某个行动出于义务,那么就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这表明“出于义务”而行动作为道德价值的起源具有唯一性。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先澄清了道德价值的起源,才可能进一步分析出相应的道德性的最高原则。
对于什么才是“出于义务”的行动,康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康德把与道德相关联的行动区分为违背义务的与合乎义务的两大类。违背义务的行动即便有实际效用,但由于其直接与义务相冲突,当然谈不上是“出于义务”的。所以,我们只能从合乎义务的行动中寻找出于义务的行动。(ibid,S.397)对此,康德又区分出了三个子类型:(1)合乎义务、主体对之有间接爱好或利益关联的行动;(2)合乎义务、主体对之有直接爱好的行动;(3)出于义务的行动(即排除了一切间接的和直接的爱好而只能由义务动机所驱动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前两种行动与出于义务的行动区别开来?
康德提出,那些人们对之有利益关联的行动,很容易与出于义务的行动区分开来。因为在这类情形中,我们往往能够清楚地找出那些驱动人们行动的真实意图。康德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商贩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这是合乎义务的,但很难说是出于义务的。康德的理由是,商贩的利益诉求促使他提供诚实的服务,毕竟从长远来看诚实是最好的经营策略。正是自利的意图使一个商人公道地做买卖,所以,一个商业行为即便是诚实的,也不可能是出于义务的。(1968a,S.397)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指责:按照康德的论证,一个商人似乎永远没有机会在生意上表现出自己道德的一面了。可以为康德似乎“贬低”商业活动的这一例证稍作辩解的是:我们通常认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与促进他人福利为目的的慈善行为之间毕竟是有界限的,前者的出发点就已决定了其性质迥异于后者。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商人不能在其他活动中比如慈善捐赠活动中表现出自己的德行。
康德认为,最困难的是“去分辨那种合乎义务、并且此外主体又对之有直接的爱好的行动”。(ibid)对此,他不厌其烦地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这三个例子分别涉及保护生命、帮助他人和增进自己的幸福。第一个例子是,每个人都本能地贪恋自己的生命,假如出于这种直接爱好而保存生命,那么这虽然合乎义务,却并没有道德意义;但如果一个人身处逆境,活着对他来说只意味着痛苦和绝望,以致于他对生命没有了直接的爱好,他仍出于爱护生命的义务而坚强地生活,这个行动就具有了道德的内涵。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人如果出于同情心而帮助别人,那么其行为固然值得赞赏,却不具有道德价值;只有当他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出于道义而帮助他人时,他的行动才是善的。最后一个例子则是,人们对幸福通常有一种内在的爱好,但由于幸福概念的不确定性,有些人就容易沉溺于眼前的享受,哪怕这会损害健康并进一步破坏整体的幸福。比如,某个沉溺于某种不良嗜好(如酗酒)的人,可能为了满足嗜好而牺牲健康。如果这个人能够出于增进幸福这样一种(间接的)义务而战胜嗜好,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的行动是有道德价值的。(ibid,S.397-399)
这三个例子所涉及的都是主体对之有直接爱好的行为,并且包含了不同层次的爱好:保存生命是动物性本能,同情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禀赋,追求幸福则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性内容。这样,通过这几个例证,康德就对出于直接爱好的行动的类型做了较完备的说明。另外,从内容上看,前面商贩的例子和这三个例子合在一起,正好对应着一个完备的道德义务体系:对他人的完全义务(不伤害他人),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不伤害自己),对他人的不完全义务(帮助他人以增进他人的幸福),和对自己的不完全义务(促进自己的幸福以便更好地追求道德完善)。
鉴于康德的三个例子具有类似的意义,下面将只关注第二个例子。这是因为剖析这个例子最利于我们充分理解康德的义务原理,而且这个例子受到的质疑最多,有必要进行回应。在这个例子中,康德提出,尽可能地乐善好施是一种义务,如果有人出于同情心而非虚荣(如得到夸奖)或自利(获得报酬)等因素去帮助他人,那么其行动无疑合乎义务,并值得赞赏;但是,该行动不具有道德价值,并不值得尊敬。康德的评判似乎不符合通常的道德理解。他的理由是,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有道德价值,而在此,行善的人是出于情感或爱好才那样做的,这决定了其行动不具有道德性质。(ibid,S.398)为了突出这一点,康德设想了一种极端的情形:假设这个人自身处在困境中,忧伤使他无暇关心他人的福利,从而对帮助他人并无直接爱好,但他仍然仅仅出于义务而去改善他人的处境,“这时他的行动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价值”。(ibid)在这种极端情形中,驱使这个人行动的不再是情感或爱好而是义务,而道德价值正起源于义务的动机。
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出于义务是否就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唯一的判别条件。康德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康德甚至设想了另一种更为极端、更加违背常理的情况。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天生性情冷漠,对别人的、甚至自己的痛苦感觉漠然,那么在这个人身上,能否找到一种来源,给他带来一种胜过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所可能具有的价值?康德的回答非常坚决:当然可以!他甚至提出,恰恰是在这里,一种道德价值得以开始,“因为他帮助别人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1968a,S.399)在这种情况中,康德把出于爱好这种可能的动机彻底排除了。
从康德的上述例子尤其是那两种极端情形,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康德的主张:一个行为是有道德价值的,当且仅当是出于义务而做出的;同情心或情感偏好并不能带来道德价值,所以,哪怕是一个同情心比较淡漠的人,只要他能出于义务而行动,其行动就是道德的。
二、回应对康德义务原理的三种质疑
康德对于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道德价值的描述,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常见的质疑有如下几种:为什么同情心不能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出于义务而行动必须排除情感满足吗?冷漠地出于义务而行动与热情地出于义务而行动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吗?下面我将依次回应这些可能的疑问。
1.回应第一种质疑:为什么同情心不能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
从日常的观点看,同情心是非常宝贵的,人们往往对具有丰富同情心的人赞赏有加。甚至在许多哲学家看来,正是同情构成了道德价值的来源。比如18世纪的哈奇逊、休谟等启蒙哲学家,20世纪的一些元伦理学家,以及中国哲学中的某些主要的思想流派,都主张一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纲领。那么,康德有何充足的理由拒斥同情作为道德价值的来源呢?首先,在《奠基》的开篇处康德就已初步陈述了他的理由:同情心,甚至更宽泛地说,道德情感,仅仅是有条件的善。(ibid,S.393)同情心需要善良意志作为其指导原则,才能用于善的目的,同情心本身并非总是促成善的条件。对于恶人的同情,有时反而会成为罪恶的助力。著名的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大概正是这方面的例证。可见,同情心只是某种有条件的善,不足以成为无条件的道德价值的来源。
其次,康德的理由不止于此。在他看来,同情心或情感偏好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确定性。(康德,第27-30页)康德把包括同情在内的情感偏好描述为病理学的(pathologisch),他采用的不是这个词的现代的、与病变相关的意义,而是其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即感性的、被激发的这样一种含义。情感能否被激发出来、能否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环境与条件,这一点使之无法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1968a,S.442)按照情感偏好的原则,是否行善或如何分配各种善好之物,往往是不确定的。以康德上述例子来说,即便是一个具有丰富同情心的人,当他受到某些负面情绪的困扰时,也可能难以保证会对周围处于困境中的人施援手。这正是爱好原则之不确定性的表现。而真正道德的行动应当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不是取决于是否有适当的环境激发或有特定的情绪作为铺垫。
最后,同情心或情感偏好不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因而不适于作为道德价值的起源。(ibid,S.442)假设一个人拥有向其他人分配公共福利的权力,那么按照情感偏好的原则,很可能会出现下述情形:假如这些人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大概会一视同仁,从而做出比较公正的分配;但假如这里面有他的朋友,甚至有他的亲人,而他对他们怀有强烈的情感偏好,那么他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在分配时向他的亲友倾斜。按照情感偏好的原则,即便是一个具有强烈同情心的人恐怕也难以排除特殊情感(如亲情)的干扰。这是因为,从性质上看,普遍的同情感与特殊的亲近感都属于自然的情感禀赋,而且前者通常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扩充和发展出来的。所以,同情感在与特殊情感的纠缠中常常会受到后者的制约。比如,由于受到亲情、友情等影响,即便在分配公共善时,按同情原则行动的人也容易偏爱身边亲近的人。②所以,同情心的效力是相对的,缺乏普遍性,很难成为客观价值的起源。
情感原则的缺点从根本上看来自于情感本身的质料性、多样性的特点。康德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这一点。在《奠基》中,康德提出道德情感(作为情感)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程度上具有无限差别,从而无法提供一个同样的、确定的善恶标准,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情感很难进行稳定而有效的道德判断。(1968a,S.442)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进一步把建基于苦乐同情等情感之上的实践规则归结为质料原则,以区别于作为形式原则的理性法则。无论种类还是程度,情感满足都因人而异,甚至在同一个主体中也因具体情况而差别较大,所以情感原则本质上是一个偶然的实践原则,不能成为普适的客观法则。(康德,第26-33页)③概言之,情感或爱好本身作为某种经验性、质料性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有条件的,因而不可能由此产生无条件的道德价值。
2.回应第二种质疑:出于义务而行动必须排除情感满足吗?
即便人们同意康德所主张的观点,即出于爱好的行动不符合道德的要求,康德的论证依然让人感到困扰。以康德所设想的作为参照的第一种特殊情形来说,那个处于痛苦中的人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出于义务去帮助他人,而正是这样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这很自然地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无动于衷地、甚至愁眉苦脸地“为义务而义务”,才是真道德。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席勒的诗句正是代表了这种反应。难道出于义务而行动就必须以排除愉悦情感为代价?
我认为,这种质疑恐怕误解了康德的意思,而这种误解产生于混淆了行动的根据与结果。康德的意图是把出于义务确立为行动的根据,为此他要排除情感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一个行动是否道德,不在于行动者在行动时是否快乐,而在于其出发点是义务的要求还是情感的驱动。康德之所以举出上述极端的例子,正是要彻底排除情感作为行动的可能根据,使出于义务成为行动的动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出于义务而行动的人就不能在行动后产生出或在行动中伴随着快乐的情感。出于义务而行动,决不排斥从善行中获得情感的满足。关键在于,情感满足只是道德行动的一种伴随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有研究者把康德的上述立场总结为:一个人可以伴随着爱好(mit Neigung)出于义务而行动,但不能同时出于义务和爱好而行动。(Baron,p.78)
对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当有德行的人战胜了恶习的诱惑,履行了那些艰难的义务时,往往会处在一种灵魂的宁静与满足状态,这可被视为德行自身的报酬;但是,由德行而来的满足感绝非这个人如此行动的根据,因为满足感之所以产生,其前提正是行动者出于义务而行动,并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由此而感到快乐,所以,这种状态只能是德行的伴随结果。(1968b,S.377)这表明,出于义务而行动与由此获得情感满足可以彼此兼容。
康德之所以设想极端的情况,有其特殊的考虑。《奠基》一书的任务是从道德常识中提炼出道德原则并证明其有效性。康德首先说明什么是有道德价值的或什么构成道德的根基,在这种说明中,他必须排除一切可能引起误会的因素,以便使道德价值的起源充分地显现出来。为此,康德特意列举了非典型的、相对罕见的情景:一个处在痛苦中的人依然出于义务去帮助别人,由此凸显义务原则乃是其唯一的动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善行只能愁眉苦脸地完成。
如果我们考虑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相关论述,上述观点会变得更加清楚。该书的任务是建立义务体系,即在道德的根基已经得到确立的前提下,规定各类具体的道德义务,以指导人们的实践。这时,道德情感是一种助力,甚至本身也是道德教化的一部分。康德提出:“德行中的练习规则旨在两种心灵的情致,即在遵循其义务时的坚强和愉悦的心情。”(1968b,S.484)这表明,在奠定了出于义务而行动这一道德根基之后,行动时伴随而来的欢乐也应当是道德改善的一部分。康德以斯多亚派的坚忍来类比追求德行的坚定决心,同时他又强调这还是不够的,必须附加某种符合道德的生活乐趣,或伊壁鸠鲁理想中的“永远快乐的心灵”,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备的修习德行的方式。(ibid,S.484-485)康德还把僧侣禁欲和自虐的修行法当做反面例子,对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自我折磨式的修行并非真正地致力于道德改善,而是狂热的涤罪,其中往往带着对于道德命令隐秘的仇恨,所以,排斥愉悦感的道德修行是不可取的;人们加诸自身的道德训诫,只能通过伴随着的愉悦感,才成为值得称赞和示范性的。(ibid,S.485)
康德对于德行与幸福之关系的理解,也表明他确实主张出于义务而行动与获得情感满足两者之间是可以协调的。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幸福与德行合比例的结合称为至善,并提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康德强调的是:在两者的结合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德行和幸福究竟何者处于支配地位,而正确次序是将追求幸福置于道德要求之下,保证德行才是至上的目的。只要保证了两者处于正确的顺序,德行处于优先的地位,快乐就是值得追求的。从根本上说,有德行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是快乐的。这种快乐甚至不限于由德行带来的宁静,而是各种主观意图的系统实现,即尘世的各种幸福。只是康德始终强调,幸福固然值得追求,但是追求幸福决不能成为行动的规定根据。幸福是一个人在按照德行的要求生活后才可正当地拥有的希望。(康德,第151-202页)
所以,出于义务而行动并不排除从中获得情感满足,甚至这种满足是道德教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满足感绝对不能成为行动的动机。正是为了说明后者,康德才设想了上述极端的情形。这一看上去很奇怪、甚至容易引起误解的例子,正是为了凸显道德行动必须出于纯正的义务动机。我相信,上面的阐释已经表明,出于义务而行动与从中感到快乐其实并不冲突,人们完全可以快乐地出于义务而行动。因此,本文开篇所引的席勒诗句中的质疑,实际上是对康德的误解。
3.回应第三种质疑:冷漠地出于义务而行动与热情地出于义务而行动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吗?
即便接受了善行并不排斥情感满足这一点,质疑者仍可以提出新的疑问。在康德列举的第二种极端情形中,那个天性冷漠的人,不带情感色彩地出于义务而行动,恰恰在这里产生了道德价值,而情感本身则不会成为道德价值的来源。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类冷漠地为义务而义务的行动,就会和出于义务同时伴随着情感满足的行动,从道德价值上看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同样让人困扰。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疑问,让我们设想下述情形:一个朋友在我处于困境时出于义务帮助了我,并对于能帮我走出困境感到高兴,在我向他表达谢意时,他这样回答我:我非常高兴能够帮上忙!毫无疑问,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善的,而且让人感到愉快。再设想另一种情形:另一个朋友同样在我处于困境时帮助了我,但由于他天性冷漠,对我的遭遇并没有多少情感上的反应,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这是道义的要求,所以他这样答复我的致谢:我是在尽作为朋友的义务!按照康德的说法,从道德上看,这两个人的行动是同样地善的。但是,热情地出于义务而行动与冷漠地出于义务而行动,两者竟然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这实在与人们的直觉和通常所认可的道德评价标准不符合。难道第一个朋友的热情、他温暖人心的言辞,竟然没有使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变得更善?而第二个朋友的冷漠回应恐怕会让人感到别扭,这难道没有使他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吗?
这类质疑并不奇怪。想想第二个朋友的回答:我只是在尽义务!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德语、英语等西语中,义务一词都带有某种被强制的意味,即出于职责、道德或权利方面的约束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意味。说一个人是在尽义务,给人的感觉是他未必乐意这样做,而只是出于某种约束而不得不做。所以,第二个朋友的回答恐怕很难让受助者、甚至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感到舒服。
解答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康德强调的是这两种行动在道德价值上是一样的。而道德价值如《奠基》开篇所说的,是一种无条件的善,只体现在善良意志中。除了无条件的善,康德还提到了有条件的善或价值。比如才能、气质以及在激情方面的自制能力,都具有某种有条件的价值,并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奠基》第二章,康德把这类事物命名为具有价格之物,并与具有绝对价值的德行进行了对比。康德区分出两类具有价格之物:直接满足人类的爱好和需要的事物,比如工作能力、技艺,具有市场价格;适合于某种鉴赏力,使人的内心诸能力在纯然无目的的游戏中感到愉快的事物,比如机智、想象力、具有感染力的生动情绪,具有欣赏价格。(1968a,S.434-436)这些都构成了有条件的善物。相应地,出于基本道德法则的好意,按照义务的要求而行动,则具有内在的绝对价值。这两种价值是不同的:相对价值可以满足某些爱好或者使人愉悦,具有实用性;而道德价值则源自意志出于义务原则而行动,体现了意志因受理性原则决定而具有的完善性。
按照康德对于两类价值的规定,我相信他会这样回应上面的质疑:那个热心的朋友满足了人们某种情感需要,使人感到愉快,这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这只是有条件的价值,与道德价值绝不能等量齐观;就上述两个朋友的行为的道德价值来说,的确是相同的,因为这两人均是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这一动机构成了其意志的内在价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一个朋友的温暖言辞并不产生道德价值,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一个陌生人基于道义无私地帮助我之后,什么也不说就离开,或者由于受教育程度或性格直率等原因,这个助人者在帮忙过程中言辞有些粗鲁,但是在此,沉默或言辞上的不完美并不会减少其义举的价值,甚至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他的举动的纯粹性。可见,关键是动机,方式或者后果并不能决定道德价值。
按照这个解释,我们不仅可以理解,热情地出于义务而行善和冷漠地出于义务而行善,在道德价值上并无区别,而且可以发现,日常的道德评价或者我们的道德直觉,虽然已经包含了道德原则,但这种原则往往是处在混杂或遮蔽之中的。就这里讨论的情况而言,质疑者混淆了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这也可以解释,康德虽然是从分析日常的道德知识入手,但并未停留于这个层次,而是剥离了这些知识中那些混杂的经验性成分,使之真正上升为哲学层面上的道德原则。
三、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澄清,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康德在理解道德根据方面彻底的理性主义倾向。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特点。它体现了康德的一个基本考虑:真正的道德原则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理性的原则与情感的原则相比,在这方面无疑是有优势的。这是因为,仅仅诉诸自发的同情、仁爱等情感,道德行动就有可能成为可做可不做的不确定的举动,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环境与条件;甚至与受助者的亲疏关系、对于受助者是否偏爱、自身的心态等等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行动的抉择。但一个真正有道德价值的行动,应当独立于这些主观爱好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理性原则而必然地做出,应当具有客观性。
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康德对于基督教的爱的诫命所做的重新解释。康德提出,《圣经》教导我们要爱邻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这种爱并不是病理学的或情感性的。原因在于,如果这种爱是情感偏好,那么恐怕很难成为命令的对象。情感之爱作为一种自然的倾向,往往是自发地作为反应而出现的,通常只能自然地产生或被激发出来,却无法被命令。(1968a,S.399;1968b,S.449)以爱自己的敌人来说,如果这种爱是情感性的,就意味着要消除自己对敌人自然的反感;而这种反感既然是自然的、自发的,那么恐怕是很难消除的。这就像外力可以强迫两个不相爱的人结婚,但无法强迫他们相爱那样,情感性的爱是无法被命令的。唯一可以被命令的爱,是一种从实践的原则出发的“爱”,这已经是理性的抉择,或者说是对于道德原则的认可,康德也称之为人类之爱(Menschenliebe)。(1968b,S.401-402)有研究者指出,在康德所设想的那个天性冷漠的人出于义务帮助他人的极端例子中,至少这种人类之爱应当是在场的。(Wood,p.38)
以爱自己的敌人来说,这种“爱”也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因为这实质上意味着,哪怕敌人伤害了自己,以致于难以抑制对敌人情感上的反感乃至仇恨,但还是要按照理性的原则给予他人道的对待。例如,在战争中对被俘的敌方人员加以人道的对待,往往是基于一种理性的原则才有可能。如果出于情感偏好的原则,对俘虏加以虐待甚至屠杀恐怕会是更加自然的选择。特别是在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更加可能如此:失去战友的痛苦无疑会大大强化对敌人的仇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到人类的战争史上,不难发现,以比较人道的原则对待战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尤其是在更加崇尚暴力和复仇的早期人类社会中,对待敌人的方式常常比较残忍,大规模屠杀战俘的记载屡见于史册。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对待敌人,大概是启蒙运动以来基于理性的人道主义原则逐渐传播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理性的道德原则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正是理性的道德原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或者说实践意义上的人类之爱,获得了一种较为稳固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以理性的原则而不是情感偏好等爱好的原则来厘定道德价值,很可能是稳定而广泛的道德进步的条件。而确立一种纯然理性的道德原则,在此即义务原则,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凡引自此书的文字,均由我译出初稿,并经邓晓芒老师校改,在此向邓老师致谢!必须说明的是:康德本人实际上并没有直接表述这条原理的具体内容,但是根据康德所作的具体解释,可以推出上述命题。同样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上一命题,康德的完整的义务原则还包括两个后续命题:行动的道德价值在于该行动的准则;义务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要性。(cf. 1968a,S.399-401)本文将集中探讨出于义务而行动具有道德价值这一原理,至于后两条原理的含义以及全部三条原理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科斯伽德(C. Korsgaard)的著作《创建目的王国》的第2章(Korsgaard,pp. 43-76),和邓晓芒老师的论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第1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邓晓芒,第80-90页)。
②休谟对此有真切的洞察。在《人性论》谈及仁爱(benevolence)的章节中,他明确地提出,人的慷慨通常很有限,很少能扩展到超出家人与朋友的范围之外,最大限度上也超不出本国的范围。(Hume,2000,p.384)休谟固然反对把道德的基础归结为自私考量;但他确实同意,人类的各种美好的情感如爱情、母爱、为朋友的得失感到高兴与伤感等,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往往是普遍同情(对同类的一般的同情)和特殊情感(基于亲情或获得帮助等因素而产生的同情)的融合,很难截然二分。(ibid,1998,pp. 164-169)就情感主义的立场而言,儒家伦理的基本路径与此类似:儒家通常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做道德的基础,而这种爱由近及远地向其他社会成员扩展则构成各种社会德性。
③由于情感本身在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情感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何使情感原则扩展为一个主体间普遍适用的社会性规则,始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有一个类似的批评:如何把适用于个人选择的功利原则扩展到其他人乃至全社会,是一个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cf. Rawls,pp. 22-33)
【参考文献】
[1]邓晓芒,2010年:《〈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第1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载《哲学分析》第2期。
[2]古留加,1997年:《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
[3]康德,2003年:《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4]Baron, M., 2006, "Acting from duty", in C. Horn and D.Schnecker(ed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Walter de Gruyter.
[5]Hume, D., 1998,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Kant, I., 1968a,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 KantsWerke, Bd. Ⅳ,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8b,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 Kants Werke, Bd. Ⅵ,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7]Korsgaard, C., 1996, Creating the Kingdom of End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8]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Wood, A., 1999, Kant'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链接: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1/t20131114_833596.shtml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30 20:29
【案例】
道德绑架为何难以避免
作者简介: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现有的报道与研究大多对施事方持批评态度,这既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直觉,更回避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实质。种种道德绑架得以进行,均需要预设以下核心论证:从道德上的好推出道德上应该做;从道德上应该做推出不做就应该被谴责;从应该被谴责推出对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替受事方辩解的阐述大多反对核心论证中的第二个命题,希望以此阻断核心论证,中止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以及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方式无法彻底阻断核心论证。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知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关键词〕道德绑架 谴责 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义务的整体性 免责条件
近年来,关于道德绑架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此起彼伏。然而,相当多的描述都不中立。以百度百科的界定为例:“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类似于百度百科的阐述很多。如吴轶群将道德绑架归类到“非理性道德”现象;王成兰、罗玮栋认为,“显然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都萧雅、王一帆断定,“道德绑架行为具有明显的伪善性”;余涌相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过错”。这样的界定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多数道德绑架案例中,施事方提出的要求往往并不高,更谈不上不切实际,如火车上让座。同时,这样的界定也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道德绑架可以通过客气的请求甚至眼神来完成,而不必诉诸“胁迫或攻击”行为。胁迫和攻击当然不对,但这种不对跟道德绑架无关。再者,这样的界定更不符合直觉:如果道德绑架错得如此明显,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反复发生的社会现象,会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理论热点。
客观地讲,道德绑架的施事方与受事方通常都各执一词。他们既感觉自己有理,同时又感觉自己的道理并不那么充分。把施事方说成是在撒泼和无理取闹,或者把受事方说成是道德冷漠,都先入为主地误导了问题,而不是客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道德绑架不是一个阴险者在折磨一个无辜者。受事方在道德上的错误通常是无可争辩的,但施事方却并非如此。
本文将给出道德绑架得以完成的核心论证。现实发生的道德绑架现象都预设了这个论证,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各自添加了不同的前提,但这些前提更为可疑。因此,本文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核心论证上,并主要处理“火车上让座”这个经典的道德绑架案例及其变体。这个经典案例是这样的:一位急于求医的老人,在没有买到全程坐票的情况下,由其女陪同上了火车,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了下来。该位置的座票的持有者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不同意让座或者跟这位老人挤着坐。在同车另一位乘客主动让座后,事态得到短暂缓解。老人的女儿在跟让座者的交流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学学”。这一内容引起了年轻女性的强烈不满,她感觉受到了道德绑架。据网上投票,近九成网友支持不让座。由于核心论证是所有道德绑架现象共有的,所以,我们要是能够阻断核心论证,就有可能阻断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阻断都不彻底。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要求事项的“道德性”与这一事项在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识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会长期存在。
一、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
综合种种道德绑架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施事方必定坚持了以下论证:
如果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应该做的。(“好-应该”联结论题)
如果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那么不做它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谴责论题)
如果不做一件事情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那么对此表达谴责就是恰当的。(谴责表达论题)
以在火车上给老人让座为例。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好的,所以它是应该做的。我是老人,我站在你面前,从道德上讲,你就应该给我让座。如果你不给我让座,你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既然这样,我就可以谴责你。
我们可以把这个论证称作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在道德绑架的典型场景中,施事方首先会倡议受事方做一件道德上的好事。这时,如果没有“好-应该”联结论题,受事方就不必去做这件事;如果没有谴责论题,就算受事方应该做而未做,也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如果没有谴责表达论题,就算受事方应该受到谴责,施事方也不能恰当地表达这种谴责。因此,无论如何,道德绑架要成功进行,这三个核心论题就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无理取闹。对于无理取闹,自然有另外一些应对方法。但道德绑架不是施事方的无理取闹,它多多少少会让受事方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也让施事方觉得自己有理。其中关键,就在于有这个核心论证。有了它,施事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选一件道德上的好事让受事方去做。在此过程中,施事方似乎立于不败之地,受事方必须按照施事方的选择行事,否则他将受到道德谴责。这很有些“要么听指挥,要么被谴责”的意思。
我们注意到,一些道德绑架现象显得生硬。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核心论证,而是因为它们添加了另外一些明显可疑的论题。比如,在核心论证前添上以下论题:
如果一件事情是好的,那么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好—道德好”联结论题)
这个论题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有的好跟道德上的好无关。把素描画得更美一些,这是好的,但并不是道德上的好。当施事方请受事方把素描画得更美一些时,如果受事方不听从,施事方对其施加道德谴责,这大约只会让受事方感到好笑,而不会使其产生道德绑架感。有的好甚至在道德上是坏的。教枪手瞄得更准,这是好的。但要是知道枪手会用这个技术去犯罪,还去教他,就成了道德上坏的。一个持枪罪犯要求一位旁观者教他射击技术,否则就会在道德上谴责他。这时,受事方产生的不是道德绑架感,而是荒谬感。
有的道德绑架,在核心论证后添上了这样的论题:
如果对此表达谴责是恰当的,那么我可以任性地表达我的谴责。(谴责表达的任性论题)
应该说,生活中很多的道德绑架都添上了这样的前提。在火车上不给老人让座,老人就满火车谴责受事方,或者干脆给受事方一个巴掌,或者拍下受事方的相片放在网上,或者不断地谴责,直到得到座位或者一方下车为止,这些当然都不对。就算谴责是可行的,也不意味着谴责的表达可以任性。任性地表达谴责往往会激起公愤,无助于道德绑架的成功。
很可能还有添加上其他可疑论题的,但这些可疑论题并不是核心部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冲突爆发点各不相同。在一些案例中,施事方因为事先的过错而造成他不得不求助于人,有的是因为第三者过错,有的是因为施事方的要求过分或者语言不得体,有的则是因为受事方没有道德付出的意愿,或者受事方有特殊的困难。很明显,它们都不是道德绑架的必要因素。不过,作为道德绑架,它们的核心论证是共同的。在本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上。
站在受事方的角度,这个看似无害的核心论证实在是麻烦之源。一个青年辛辛苦苦地买了有座票,上车刚坐下,来了一位老人,请求把座位让给她。根据核心论证,老人的请求一旦做出,这个青年就必定会付出代价:要么让座,要么被谴责。如果这位青年不想哀叹命运、怀疑人生,就不得不想办法破坏核心论证。
在核心论证中,“好-应该”联结论题很难被反驳。它几乎是定义性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好的,就应该去做。如果一个行动是好的,那一定有去完成它的理由。如果它是可能行动中最好的,完成它的理由就是结论性的,会胜过所有不去完成它(或者去做其他事情)的理由。”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那么它就在道德上是应该去完成的。道德上的好坏是道德知识,应不应该去做是道德行动。一般认为,道德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的一大特征就是唤起行动。应该去完成的事情是一种义务或责任,通过规定义务或责任,伦理学唤起相应的行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个别伦理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如伊莉莎白·安斯康就认为,道德哲学应该以心理学哲学为基础,“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概念,“连同道德对错,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应该’,都应该被抛弃掉”。如果道德知识不能唤起道德行动,道德绑架就会更加粗暴:你应该给我让座,所以,把你的座位让给我,否则我就会在道德上谴责你。你给我让座,跟它是不是一件道德上的好事无关。显然,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道德绑架现象并不是都这样的。无论是施事方还是受事方都会认为,施事方所倡议的事情是一件道德上的好事。对“好-应该”联结命题的认同,既助长了施事方的底气——他在要求对方做一件好事;也增加了受事方的压力——如果他不照做,就有一件道德上的好事他没有去做。因此,我们不准备反驳这个论题。
谴责表达论题也几乎是不可反驳的。直觉上看,如果某个行为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那么,行为者就应该接受对他的谴责。把这种谴责表达出来是让他接受这种谴责的必要条件,所以,对相应谴责的表达并无不妥。事实上,按照安吉拉·M.史密斯的看法:“在道德上谴责另一个人……就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表达对特定行为者对待自己或他人的一个道德抗议。”或者,根据C.V.富兰克林的说法:“(道德)谴责跟价值的联系是本质性的……要是我们在本该谴责时不去谴责,我们就没有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东西……谴责是对自由地无视价值(free disvaluation)的一个恰当反应……对于捍卫和保护道德价值来说,谴责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所以,它就不只是一个合适的反应,而且是一个好的、必要的反应”。当别人不能达到某种道德标准时,我们会伤心。但是,“伤心不能替代谴责”,因为“伤心是对损失的反应,而不是对自由地无视价值的反应。”当然,我们要把谴责表达论题跟谴责表达的任性论题区分开。表达谴责是恰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性地表达谴责也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道德绑架之争的焦点在谴责论题上。替受事方辩护的学者大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这个论题,但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些学者诉诸义务的分类,如余涌区分完全义务与非权义务,或者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郁乐区分义务与美德(大致相当于权利义务与非权义务)。这些学者认为,对于后一类义务,不履行也不该受到谴责。另一些学者立足于义务的整体性,他们发现,有时会出现两个或多个义务不相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履行其中一个义务就不应受到谴责,笔者本人就曾持此种立场。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将免责条件考虑进来。人们认为,虽然作为一般规律,不履行道德义务理应受到道德谴责,但在特定情况下,由于某些非道德的偶然因素,特定行动者不履行某些道德义务可以免于道德谴责。下面我将阐述,这些途径均不能有效阻断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
二、对义务的区分不能避免道德绑架
余涌等学者试图论证,道德谴责随着义务的不同种类而有变化。有的义务不被履行应该受到谴责,有的义务不被履行却不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承认,道德绑架中施事方要求受事方所做的行为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就算不被履行也不应受到谴责。因此,就算施事方未能得到受事方的积极回应,他也不能谴责对方。这样,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就进行不下去了。道德绑架的错误就出现在对两类义务的混淆上。
余涌对这种观点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述要点是:第一,两种义务的不同真实存在;第二,这一不同使得人们无权对后一类义务的不履行实施道德谴责;第三,道德绑架的错误就在于,施事方在无权谴责时实施了谴责。余涌注意到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区别:“法律义务的履行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约束;而道德义务的规范性或约束力则是诉诸社会舆论、个人良心以及风俗习惯等。”前一类义务是“完全义务”或者“完全强制性义务”;后一类义务是“不完全义务”或者“不完全强制性义务”。同时,他又注意到:“在不同的道德义务之间,其规范性和约束力显然存在差别,因而在重要性上也有区别。”针对这一差别,他认为,可以区分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对行为者的要求是绝对的,不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强约束力”,而“不完全义务对行为者的要求则是相对的,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弱约束力”。这种弱约束力有多弱呢?他说:“对于不完全义务,履行就应受到褒奖,而不履行亦无可指责。”在另一处,他指出:“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这种义务不与某种作为要求权的道德权利直接相关。”因此,这种不完全义务又叫“非权义务”。一般的义务,对应着权利。A对B具有某种义务,B对A就拥有主张A履行这种义务的权利。但不完全义务或非权义务却没有这种对应关系:A对B具有某种不完全义务,但B无权主张A履行这种义务。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给出了对道德绑架的诊断。“道德绑架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了这两种道德义务的区别,把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把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在某种情形下形成一定的舆论胁迫甚至是制度强制,在行为者非自愿的情况下对其行为形成道德上的压力”。
我们看到,区分不同义务的目的是希望就此阻断道德绑架中的施事方对受事方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把两种道德义务的区分依据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阻断是否可能。按照余涌的说法,道德不完全义务是非权义务,而“非权义务只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弱约束力,即在于表明,这类义务的履行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或偏好自主选择的,其约束力与其说源于外在的强制,不如说是源于个人的道德认知、道德自觉,抑或是个人的道德良心”。如果余涌的说法准确,那么这种义务的约束力也太弱了,弱到难以称它为“义务”。这样的义务完全缺乏外在约束,行动者可履行可不履行,履不履行完全看自己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以及有多喜欢。虽然他强调内在的约束,但这种内在约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约束,而是跟道德水准相关。如果行动者道德水准低,根本不约束自己,那就没有任何约束了。一种对行为的要求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力,与其说它是不完全义务,不如说它完全不是义务。由于这种所谓的义务所要求的内容在道德上是好的,我们充其量只能把它称作“道德倡导”。到底是叫“不完全义务”还是叫“道德倡导”,或者干脆叫“美德”或者“至善理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算这种区分成立,它真的可以阻断施事方对受事方的道德谴责,从而阻止道德绑架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哪怕把道德不完全义务弱化成道德倡导,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介入权。凡是道德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监督,否则就完全退化成了个人自主选择,跟道德全然无关了。我们承认,社会监督有强有弱,强可强到公开地、大规模地实施道德谴责,弱可弱到私下作出道德提醒。大多数的社会监督却摇摆在强弱之间。无论如何,我们在道德上都无法拒绝私下的道德提醒。一个人提醒另一个人去追求一个好结果,这在直觉上不可能是坏的。例如,提醒某人在自动扶梯上系上他的鞋带。在自动扶梯上系上鞋带当然是好的,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危险。如果系上鞋带是好的,而他的鞋带正好没有系上,那么提醒这个人系上鞋带就是好的。也许这个人没有注意到鞋带松了,也许他根本不想系,这些都是无关因素。类似地,履行道德不完全义务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没有履行道德不完全义务,那么提醒他去履行这种义务就是好的。也许他没有注意到眼前有道德不完全义务需要履行,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履行,因此反感他人的提醒。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别人的提醒是不好的。一件好事,也许不一定会被提倡,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禁止。
我们有理由相信,区分出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经典作家是赞成这种介入权的。以康德为例,他认为:“惟有不完全的义务才是德性义务。德性义务的履行是功德(meritum)=+a;但对它的违背却并不马上就是过失(demeritum)=-a,而仅仅是道德上的无价值=0。”由于违背不完全义务不是过失,所以也就谈不上谴责。但是,这种分析要成立,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除非主体的原理就是不服从那些义务。”这就意味着,行动者并没有不服从不完全义务的自由。出于某些原因,行动者可以在事实上违背这些义务,但这一违背,不得出于对不完全义务的不服从。因此,当违背现象出现后,他人就可以介入,以考察到底是单纯违背不完全义务,还是不服从不完全义务。后一类不作为,是要受到谴责的。
他人的介入权一旦存在,就为道德绑架打开了通道。大学生在火车上坐下,老人或老人的亲属往她身边一站,她们并不恶语相加,而是很有礼貌地提醒:你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她比你更需要你的这个座位。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应,她们就站着不走,每5分钟提醒一次。她们一直温文尔雅,甚至可以很体贴地告诉大学生:让座是你的不完全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30 20:29
【案例】
道德绑架为何难以避免
作者简介: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道德绑架现象频繁出现。现有的报道与研究大多对施事方持批评态度,这既不合乎事实也不符合直觉,更回避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实质。种种道德绑架得以进行,均需要预设以下核心论证:从道德上的好推出道德上应该做;从道德上应该做推出不做就应该被谴责;从应该被谴责推出对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替受事方辩解的阐述大多反对核心论证中的第二个命题,希望以此阻断核心论证,中止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以及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方式无法彻底阻断核心论证。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冲突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知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关键词〕道德绑架 谴责 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义务的整体性 免责条件
近年来,关于道德绑架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此起彼伏。然而,相当多的描述都不中立。以百度百科的界定为例:“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类似于百度百科的阐述很多。如吴轶群将道德绑架归类到“非理性道德”现象;王成兰、罗玮栋认为,“显然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都萧雅、王一帆断定,“道德绑架行为具有明显的伪善性”;余涌相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过错”。这样的界定显然不符合事实。在多数道德绑架案例中,施事方提出的要求往往并不高,更谈不上不切实际,如火车上让座。同时,这样的界定也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道德绑架可以通过客气的请求甚至眼神来完成,而不必诉诸“胁迫或攻击”行为。胁迫和攻击当然不对,但这种不对跟道德绑架无关。再者,这样的界定更不符合直觉:如果道德绑架错得如此明显,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反复发生的社会现象,会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理论热点。
客观地讲,道德绑架的施事方与受事方通常都各执一词。他们既感觉自己有理,同时又感觉自己的道理并不那么充分。把施事方说成是在撒泼和无理取闹,或者把受事方说成是道德冷漠,都先入为主地误导了问题,而不是客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道德绑架不是一个阴险者在折磨一个无辜者。受事方在道德上的错误通常是无可争辩的,但施事方却并非如此。
本文将给出道德绑架得以完成的核心论证。现实发生的道德绑架现象都预设了这个论证,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各自添加了不同的前提,但这些前提更为可疑。因此,本文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核心论证上,并主要处理“火车上让座”这个经典的道德绑架案例及其变体。这个经典案例是这样的:一位急于求医的老人,在没有买到全程坐票的情况下,由其女陪同上了火车,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了下来。该位置的座票的持有者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不同意让座或者跟这位老人挤着坐。在同车另一位乘客主动让座后,事态得到短暂缓解。老人的女儿在跟让座者的交流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学学”。这一内容引起了年轻女性的强烈不满,她感觉受到了道德绑架。据网上投票,近九成网友支持不让座。由于核心论证是所有道德绑架现象共有的,所以,我们要是能够阻断核心论证,就有可能阻断道德绑架。常见的阻断方式有三种: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主张义务的整体性、诉诸免责条件。但是,这些阻断都不彻底。道德绑架的实质在于,施事方所要求事项的“道德性”与这一事项在受事方眼中的“不合意性”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调解。由于资源、人的能力与认识的有限性,道德绑架现象会长期存在。
一、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
综合种种道德绑架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施事方必定坚持了以下论证:
如果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应该做的。(“好-应该”联结论题)
如果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那么不做它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谴责论题)
如果不做一件事情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那么对此表达谴责就是恰当的。(谴责表达论题)
以在火车上给老人让座为例。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好的,所以它是应该做的。我是老人,我站在你面前,从道德上讲,你就应该给我让座。如果你不给我让座,你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既然这样,我就可以谴责你。
我们可以把这个论证称作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在道德绑架的典型场景中,施事方首先会倡议受事方做一件道德上的好事。这时,如果没有“好-应该”联结论题,受事方就不必去做这件事;如果没有谴责论题,就算受事方应该做而未做,也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如果没有谴责表达论题,就算受事方应该受到谴责,施事方也不能恰当地表达这种谴责。因此,无论如何,道德绑架要成功进行,这三个核心论题就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无理取闹。对于无理取闹,自然有另外一些应对方法。但道德绑架不是施事方的无理取闹,它多多少少会让受事方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也让施事方觉得自己有理。其中关键,就在于有这个核心论证。有了它,施事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选一件道德上的好事让受事方去做。在此过程中,施事方似乎立于不败之地,受事方必须按照施事方的选择行事,否则他将受到道德谴责。这很有些“要么听指挥,要么被谴责”的意思。
我们注意到,一些道德绑架现象显得生硬。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核心论证,而是因为它们添加了另外一些明显可疑的论题。比如,在核心论证前添上以下论题:
如果一件事情是好的,那么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好—道德好”联结论题)
这个论题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有的好跟道德上的好无关。把素描画得更美一些,这是好的,但并不是道德上的好。当施事方请受事方把素描画得更美一些时,如果受事方不听从,施事方对其施加道德谴责,这大约只会让受事方感到好笑,而不会使其产生道德绑架感。有的好甚至在道德上是坏的。教枪手瞄得更准,这是好的。但要是知道枪手会用这个技术去犯罪,还去教他,就成了道德上坏的。一个持枪罪犯要求一位旁观者教他射击技术,否则就会在道德上谴责他。这时,受事方产生的不是道德绑架感,而是荒谬感。
有的道德绑架,在核心论证后添上了这样的论题:
如果对此表达谴责是恰当的,那么我可以任性地表达我的谴责。(谴责表达的任性论题)
应该说,生活中很多的道德绑架都添上了这样的前提。在火车上不给老人让座,老人就满火车谴责受事方,或者干脆给受事方一个巴掌,或者拍下受事方的相片放在网上,或者不断地谴责,直到得到座位或者一方下车为止,这些当然都不对。就算谴责是可行的,也不意味着谴责的表达可以任性。任性地表达谴责往往会激起公愤,无助于道德绑架的成功。
很可能还有添加上其他可疑论题的,但这些可疑论题并不是核心部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道德绑架现象的冲突爆发点各不相同。在一些案例中,施事方因为事先的过错而造成他不得不求助于人,有的是因为第三者过错,有的是因为施事方的要求过分或者语言不得体,有的则是因为受事方没有道德付出的意愿,或者受事方有特殊的困难。很明显,它们都不是道德绑架的必要因素。不过,作为道德绑架,它们的核心论证是共同的。在本文中,我们把重点放在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上。
站在受事方的角度,这个看似无害的核心论证实在是麻烦之源。一个青年辛辛苦苦地买了有座票,上车刚坐下,来了一位老人,请求把座位让给她。根据核心论证,老人的请求一旦做出,这个青年就必定会付出代价:要么让座,要么被谴责。如果这位青年不想哀叹命运、怀疑人生,就不得不想办法破坏核心论证。
在核心论证中,“好-应该”联结论题很难被反驳。它几乎是定义性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好的,就应该去做。如果一个行动是好的,那一定有去完成它的理由。如果它是可能行动中最好的,完成它的理由就是结论性的,会胜过所有不去完成它(或者去做其他事情)的理由。”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好的,那么它就在道德上是应该去完成的。道德上的好坏是道德知识,应不应该去做是道德行动。一般认为,道德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的一大特征就是唤起行动。应该去完成的事情是一种义务或责任,通过规定义务或责任,伦理学唤起相应的行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个别伦理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如伊莉莎白·安斯康就认为,道德哲学应该以心理学哲学为基础,“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概念,“连同道德对错,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应该’,都应该被抛弃掉”。如果道德知识不能唤起道德行动,道德绑架就会更加粗暴:你应该给我让座,所以,把你的座位让给我,否则我就会在道德上谴责你。你给我让座,跟它是不是一件道德上的好事无关。显然,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道德绑架现象并不是都这样的。无论是施事方还是受事方都会认为,施事方所倡议的事情是一件道德上的好事。对“好-应该”联结命题的认同,既助长了施事方的底气——他在要求对方做一件好事;也增加了受事方的压力——如果他不照做,就有一件道德上的好事他没有去做。因此,我们不准备反驳这个论题。
谴责表达论题也几乎是不可反驳的。直觉上看,如果某个行为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那么,行为者就应该接受对他的谴责。把这种谴责表达出来是让他接受这种谴责的必要条件,所以,对相应谴责的表达并无不妥。事实上,按照安吉拉·M.史密斯的看法:“在道德上谴责另一个人……就是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表达对特定行为者对待自己或他人的一个道德抗议。”或者,根据C.V.富兰克林的说法:“(道德)谴责跟价值的联系是本质性的……要是我们在本该谴责时不去谴责,我们就没有重视我们应该重视的东西……谴责是对自由地无视价值(free disvaluation)的一个恰当反应……对于捍卫和保护道德价值来说,谴责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所以,它就不只是一个合适的反应,而且是一个好的、必要的反应”。当别人不能达到某种道德标准时,我们会伤心。但是,“伤心不能替代谴责”,因为“伤心是对损失的反应,而不是对自由地无视价值的反应。”当然,我们要把谴责表达论题跟谴责表达的任性论题区分开。表达谴责是恰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性地表达谴责也是恰当的。
由此可见,道德绑架之争的焦点在谴责论题上。替受事方辩护的学者大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反对这个论题,但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些学者诉诸义务的分类,如余涌区分完全义务与非权义务,或者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郁乐区分义务与美德(大致相当于权利义务与非权义务)。这些学者认为,对于后一类义务,不履行也不该受到谴责。另一些学者立足于义务的整体性,他们发现,有时会出现两个或多个义务不相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履行其中一个义务就不应受到谴责,笔者本人就曾持此种立场。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将免责条件考虑进来。人们认为,虽然作为一般规律,不履行道德义务理应受到道德谴责,但在特定情况下,由于某些非道德的偶然因素,特定行动者不履行某些道德义务可以免于道德谴责。下面我将阐述,这些途径均不能有效阻断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
二、对义务的区分不能避免道德绑架
余涌等学者试图论证,道德谴责随着义务的不同种类而有变化。有的义务不被履行应该受到谴责,有的义务不被履行却不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承认,道德绑架中施事方要求受事方所做的行为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就算不被履行也不应受到谴责。因此,就算施事方未能得到受事方的积极回应,他也不能谴责对方。这样,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就进行不下去了。道德绑架的错误就出现在对两类义务的混淆上。
余涌对这种观点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述要点是:第一,两种义务的不同真实存在;第二,这一不同使得人们无权对后一类义务的不履行实施道德谴责;第三,道德绑架的错误就在于,施事方在无权谴责时实施了谴责。余涌注意到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区别:“法律义务的履行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约束;而道德义务的规范性或约束力则是诉诸社会舆论、个人良心以及风俗习惯等。”前一类义务是“完全义务”或者“完全强制性义务”;后一类义务是“不完全义务”或者“不完全强制性义务”。同时,他又注意到:“在不同的道德义务之间,其规范性和约束力显然存在差别,因而在重要性上也有区别。”针对这一差别,他认为,可以区分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对行为者的要求是绝对的,不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强约束力”,而“不完全义务对行为者的要求则是相对的,可自由选择的,具有一种弱约束力”。这种弱约束力有多弱呢?他说:“对于不完全义务,履行就应受到褒奖,而不履行亦无可指责。”在另一处,他指出:“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这种义务不与某种作为要求权的道德权利直接相关。”因此,这种不完全义务又叫“非权义务”。一般的义务,对应着权利。A对B具有某种义务,B对A就拥有主张A履行这种义务的权利。但不完全义务或非权义务却没有这种对应关系:A对B具有某种不完全义务,但B无权主张A履行这种义务。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给出了对道德绑架的诊断。“道德绑架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了这两种道德义务的区别,把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把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视作完全义务,在某种情形下形成一定的舆论胁迫甚至是制度强制,在行为者非自愿的情况下对其行为形成道德上的压力”。
我们看到,区分不同义务的目的是希望就此阻断道德绑架中的施事方对受事方的谴责。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把两种道德义务的区分依据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阻断是否可能。按照余涌的说法,道德不完全义务是非权义务,而“非权义务只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弱约束力,即在于表明,这类义务的履行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或偏好自主选择的,其约束力与其说源于外在的强制,不如说是源于个人的道德认知、道德自觉,抑或是个人的道德良心”。如果余涌的说法准确,那么这种义务的约束力也太弱了,弱到难以称它为“义务”。这样的义务完全缺乏外在约束,行动者可履行可不履行,履不履行完全看自己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以及有多喜欢。虽然他强调内在的约束,但这种内在约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约束,而是跟道德水准相关。如果行动者道德水准低,根本不约束自己,那就没有任何约束了。一种对行为的要求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力,与其说它是不完全义务,不如说它完全不是义务。由于这种所谓的义务所要求的内容在道德上是好的,我们充其量只能把它称作“道德倡导”。到底是叫“不完全义务”还是叫“道德倡导”,或者干脆叫“美德”或者“至善理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算这种区分成立,它真的可以阻断施事方对受事方的道德谴责,从而阻止道德绑架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哪怕把道德不完全义务弱化成道德倡导,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介入权。凡是道德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监督,否则就完全退化成了个人自主选择,跟道德全然无关了。我们承认,社会监督有强有弱,强可强到公开地、大规模地实施道德谴责,弱可弱到私下作出道德提醒。大多数的社会监督却摇摆在强弱之间。无论如何,我们在道德上都无法拒绝私下的道德提醒。一个人提醒另一个人去追求一个好结果,这在直觉上不可能是坏的。例如,提醒某人在自动扶梯上系上他的鞋带。在自动扶梯上系上鞋带当然是好的,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危险。如果系上鞋带是好的,而他的鞋带正好没有系上,那么提醒这个人系上鞋带就是好的。也许这个人没有注意到鞋带松了,也许他根本不想系,这些都是无关因素。类似地,履行道德不完全义务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没有履行道德不完全义务,那么提醒他去履行这种义务就是好的。也许他没有注意到眼前有道德不完全义务需要履行,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履行,因此反感他人的提醒。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别人的提醒是不好的。一件好事,也许不一定会被提倡,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禁止。
我们有理由相信,区分出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经典作家是赞成这种介入权的。以康德为例,他认为:“惟有不完全的义务才是德性义务。德性义务的履行是功德(meritum)=+a;但对它的违背却并不马上就是过失(demeritum)=-a,而仅仅是道德上的无价值=0。”由于违背不完全义务不是过失,所以也就谈不上谴责。但是,这种分析要成立,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除非主体的原理就是不服从那些义务。”这就意味着,行动者并没有不服从不完全义务的自由。出于某些原因,行动者可以在事实上违背这些义务,但这一违背,不得出于对不完全义务的不服从。因此,当违背现象出现后,他人就可以介入,以考察到底是单纯违背不完全义务,还是不服从不完全义务。后一类不作为,是要受到谴责的。
他人的介入权一旦存在,就为道德绑架打开了通道。大学生在火车上坐下,老人或老人的亲属往她身边一站,她们并不恶语相加,而是很有礼貌地提醒:你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她比你更需要你的这个座位。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回应,她们就站着不走,每5分钟提醒一次。她们一直温文尔雅,甚至可以很体贴地告诉大学生:让座是你的不完全义务,你可以不让;不过,它真的是一种道德义务。这是一件凭良心做的事,你心安吗?或者更弱一些,她们只是一直渴望地看着她。可以想见,要是大学生的道德感未能在一次次的提醒中得到提升,她一定会产生道德绑架感。大学生虽然有不履行道德不完全义务的自由,但是,道德谴责是对自由地无视价值的一种反应,是一种社会监督。因此,另一方或者第三方也有表达谴责的自由。宰我曾经向孔子抱怨,父母死,服丧三年,为期太长。孔子只问:“于女安否?”如果心安,不服三年也无所谓。但是,在宰我离开之后,孔子却斥责宰我“不仁。”一种基于“心不安”而履行的义务,当然也可以基于心安而不履行。但既然是义务,不履行就难逃“不仁”之责。
第二,不完全义务的履行与否有可能涉及完全义务的履行。从表面上看,不完全义务跟完全义务切割之后,至少在不完全义务这里,道德绑架不再合理。但问题具有复杂性。一些不完全义务跟完全义务关联在一起,如果不履行不完全义务,就会导致相关联的完全义务得不到履行。如果坚持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一方就无法进行相应的提醒和谴责,而只能坐等另一方的完全义务不被履行,没有任何预先可用的手段。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例如,对他人行善被康德视为一种不完全义务,而不得自杀则被视为完全义务。设想以下情形:在沙漠里,一位医生需要一些食物才能保持体力。此时,一位吝啬而多疑的路人经过。医生请求路人分一些食物给他,路人并不乐意。在交流的过程中,医生根据经验得知,路人的心脏病很快将会发作,如果没有医生的全力帮助就会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医生得不到食物,他就没有足够的力气来帮助别人。于是,医生把这一切告诉路人,请他分一些食物出来,否则路人就有可能死去。因此,如果路人不让医生吃一些食物,相当于他很快就会自杀。但是,路人的生命危险此时尚未出现。医生到底是应该谴责路人不给食物呢,还是谴责路人正在选择自杀呢?谴责后者是荒唐的,路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也不相信自己会死,所以医生只能谴责前者。但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医生没有理由谴责前者,因为那只是一种不完全义务。
由此可见,就算他人对不履行不完全义务无从置喙,也可能从完全义务角度对不完全义务的履行情况提出批评。虽然这种谴责是从完全义务派生出来的,但这种批评的出现,意味着通过义务两分并不能否决谴责论题,自然也就不能阻断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承认义务的两分,道德绑架依然会在完全义务上发生。例如,在康德伦理学中,不说假话是完全义务。还是在那列火车上,这回站在大学生面前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八卦”老太太。这回老太太不是要求让座,而是要求陪聊。老太太希望大学生告诉她一些真相:大学学什么专业,专业学什么内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大学生精力有限,不胜其烦。当她准备敷衍两句的时候,阅人无数的老太太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并且说:“不要撒谎,要讲真话,这可是你的完全义务。”可以想见,大学生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绑架感跟要求她让座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她大概会主动让座,选择离开,以逃避不堪忍受的完全义务。觉得这样的例子难以接受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康德本人的例子更为严厉。为了不作小小的伪证,康德认为,在道德上宁愿选择领受死刑。
三、诉诸义务的整体性也不能避免道德绑架
单单对义务进行分类,并不能拒斥道德绑架中的谴责论题,因而也不能阻断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幸运的是,这并不是我们对抗道德绑架的唯一道路。一些学者指出,义务具有整体性。有时候,履行一些义务与履行另一些义务相冲突。这时,我们只能优先履行那些道德属性更强的义务。特别是,当两个冲突的义务具有同等道德属性时,行动者可以自由选择,不受外界干预。笔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要是y(受事方——引者注)有多个不相容的、道德价值大致相当的道德行动选项,而y中意的道德行动不是x(施事方——引者注)设想的行动A,此时若x对其实施现象刻画中的道德绑架,就会侵犯到y的道德自由,从而是一个道德错误。”以网上对某个特定自然人的逼捐为例,这个自然人没有不捐善款的道德自由。然而,如果善款有限,“他拥有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分配善款的自由”。强求他一定要为某个事件捐款,就妨碍了这个自然人“分配善款的自由”。因此,“如果对其实施道德谴责,就犯下了道德错误”。这个时候,提醒对方没有认识到多个义务(行动)的不相容将是两全其美的,既证明了自己是道德的,又纠正了对方的一个认知错误。
事实上,一些对义务进行区分的学者在解释受事方的自由时,也赞成利用义务(准则)间的不相容性来解释,而不是单独利用义务的不完全性来解释。如郭立东指出:“不完全义务留有主观任意的选择空间,但这个选择空间不是在没有道德理由的情况下任意选择要不要对某一义务准则破例,而是在不同的义务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他举例说:“爱邻人时也要考虑对父母的爱,因而一个人有时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一种爱压倒另一种爱的字典式顺序,“我不能将我全部的行动能力和资源用以帮助一般人,而不考虑父母”。或者用康德的话说,不完全义务“为遵循(遵从)留下了自由任性的一个活动空间”。但这个“活动空间”只是“不能确定地说明应当如何通过行动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而发挥作用,以及发挥多少作用”,它所许可的例外,“并不被理解为对行为准则之例外情形”,而要理解为“一个义务准则被另一个义务准则所限制”。
在此,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我们的道德义务不仅针对他人,也针对自己。他人的好可以是我们的义务,但他人的好只是好的一个部分,好还有别的部分。任何道德义务,都要给行动者的个人追求留出余地。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能力和资源去帮助别人,而不考虑自己。人不是螺丝钉,“螺丝钉精神”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行动者自由地选择了牺牲个人的小目标,以成就更大的目标。但这种牺牲精神,不属于道德义务,它会伤害行动者的基本需求。在道德绑架中,如果施事方的要求损害到受事方对自己的义务,受事方当然有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道德哲学的一些主流理论支持这一扩展。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总功利相当,行动者就拥有选择权。在道义论传统中,这也无可厚非。康德认为:“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做手段。”行动者自己也是目的,他不能把自己只当成实现别人幸福的工具。康德甚至说:“没有其他人有权要求我牺牲我那并非不道德的目的。”由于不得自杀是行动者对自己的完全义务,因此康德反对死亡前的器官捐赠,这“属于局部的自我谋杀”,哪怕“捐赠或者出售一颗牙”也不行。就此而言,施事方显然更不能把受事方看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哪怕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提升或实现受事方的某个道德目标。
但是,义务的整体性会带来一个麻烦。道德义务并不像法律那样形成了体系,内容明确,以至于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负有多少相关道德义务。眼前的一个行为跟哪些潜在的义务相关联,主要取决于主观的判断,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我们可以想象,在施事方和受事方都坚持自己立场的情况下,争执会演变成认知能力的竞赛。谁能想到对自己有利的相关义务更多,谁就能在道德绑架的争执中占据优势。仍以火车上大学生被强求让座为例。大学生可以说出一些她对自己的义务,比如她需要好好休息,回到学校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参加考试。这样的义务当然跟让座不相容,毕竟只有坐下来,才能好好休息。但是,施事方可以提醒受事方,她还有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甚至,通过履行方式的调整,义务的不相容可以得到有效规避。例如,施事方做出某种让步,座位挤着坐、轮流坐。如果受事方不让步,道德绑架的争执就会持续下去。如果做了让步,接下来道德绑架也有可能会在每一方占用座位的面积大小和时间长短上发生。
更麻烦的是,就算受事方在义务不相容的阐述中占优,施事方还可以利用事情的紧急程度来坚持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有发展自己天性的义务,我们也有救人的义务。在湖边练习小提琴的过程中遇见一个孩子落水。这时,道德直觉会让我们选择救人而不是若无其事地继续拉小提琴,因为救人更为紧迫。在大学生让座的案例中,也存在需要考虑的类似因素,生病的老人的确比青年人更需要座位。除非受事方提出的义务能够在紧急程度上占优,否则针对他的道德绑架就难以停止。
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单方面巧妙退出的方式(如假装睡着或者没有听见)来阻止道德绑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理由同样来自义务的整体性。康德提醒道:“不要回避那些缺乏最必需的东西的穷人所在的地方,而要寻找他们,不要为了逃避人们无法抵御的极痛苦的同感而躲开病房或者犯人的监狱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对他人命运的同情是我们的“间接义务”。
以上讨论表明,如果对义务整体性的诉诸太弱就不能阻断道德谴责。实际上,这种诉诸如果太强的话,又有滑向道德冷漠的危险。无论施事方提出什么样的道德要求,受事方一概予以回绝。在不涉及完全义务的前提下,若真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对于不完全义务,履行就应受到褒奖,不履行亦无可指责”,施事方就会丧失任何道德上的自我救济手段。这不是把道德还给了良心,而是完全抛开了道德,单纯依靠法律维护公序良俗。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四、免责条件同样不能免除道德绑架
还有一种回避道德绑架的可能途径。受事方承认施事方的要求属于自己的道德义务,并且也承认,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就理应受到谴责。但是,由于满足了一些条件,他不履行这些义务可以免于谴责。因此,他就不必去为免于谴责做普遍性的辩护,只需要提供当下这一次的免责辩护就行了。这大大降低了辩护的难度。
为免责提供支持的大多是一些偶然因素,并且大多是非道德的,如受事方的身体状态,施事方可以求助资源的数量,或者其他不幸的外部环境(被胁迫、被激怒)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行动者要么被迫进入某条因果链,从而不受控地避开了履行特定道德义务的可能性,如上课的教师有照顾学生的义务,但在学生发生危险时,教师碰巧上厕所去了,从而未能阻止不幸的发生。要么他虽然在履行特定道德义务的因果链上,却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能力去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教师由于知识或身体训练不够,没有能力预见到危险的发生,或者在危险发生之后,没有足够的体力中断危险。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概括为针对义务的“不可达性”(unachievability),即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履行相应义务。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行为的免责(excuse)条件并不是行为的正当化(justification)条件。普遍来说,一个经过正当化的行为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好行为,一个免责的行为却不是。相反,它只是令人遗憾的。
在大学生让座的例子中,如果大学生没有让座,并采用以下解释,直觉上就可以免于指责:她的身体不好,没办法久站;同时,火车上的人很多,他们都是潜在的助人为乐者,建议施事方转而寻找其他人帮忙;或者,仅仅是她误解了施事方的意图。在这些情况下,她承认,由于她没有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她肯定做错了什么。义务就是义务,就算对它们的履行会给行动者带来不好的后果,它们也不会就此失去义务的地位。就像上夜班的义务可能会引起夜班工作者的睡眠障碍,但它并不因此就不再是一些工种的工作者的工作义务。但是,由于以上列举的特殊情况,大学生的这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此,虽然不履行相应道德义务理应受到道德谴责,但对此处的不履行行为表达谴责却并不恰当,因为行动者可以免于这种谴责。这样,造成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就进行不下去了。
然而,结合生活中的道德绑架现象分析,通过免责条件避开道德绑架的前景并不乐观。施事方大多有不依不饶的特征,他们持续地坚持向受事方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相当多的免责条件会失效。首先,受事方主观认知失误带来的免责条件会失效。例如,受事方的多数认知失误都会得到施事方的及时纠正。大学生以误解施事方的请求为名,对最初几次让座的要求不予回应,施事方对此可以表示理解。但是,在得到正面的回应前,施事方会一再地重复自己的请求,并引导大学生对这一请求做准确的理解。其次,基于受事方的能力限制而来的免责的实际用处也不明显。在真实的道德绑架中,施事方会精心挑选更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行动者作为受事方。请求让座的时候,施事方不太可能去挑选一位白发老人,或者一位看起来满面倦容的病人;他们挑选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身着制服的人员,这些行动者身体好,对道德身份有一定的要求。请求捐款的时候,道德绑架的施事方会找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人,而不太会去找贫困地区的待脱贫人员。最后,因不可控因素而避开义务履行,这一点几乎没有用处。施事方的出现,已经把受事方拖入到履行义务的因果链中。因此,随着免责条件的失效,道德绑架的核心论证就会复活。
余 论
道德绑架频频在生活中发生,个别道德绑架现象中存在明显错误的因素。比如,施事一方将好视为道德上的好,将理应谴责误解为可以任意谴责;而受事一方将法律上的无义务视为道德上的无义务,将施事方可以求助对象的非唯一性视为自己无义务的根据。这些都属于双方的非理性冲突,并没有道德含义,它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里。撇开这些不谈,所有的道德绑架都包含着一个核心论证,这个论证从道德上的好过渡到道德上履行的应该,再从道德上履行的应该过渡到对不履行现象加以道德谴责的应该,最后从道德谴责的应该过渡到对这一谴责加以表达的恰当性。道德绑架中的施受双方,无论有多少对立,在道德谴责上的对立是核心。
为了消除这一对立,一些人诉诸义务的分类,另一些人诉诸义务的整体性,以阐明道德谴责并不是应该的,还有一些人诉诸免责条件,以阐明就算谴责是普遍应该的,但在特定某次对其加以表达,也并不具有天然的恰当性,或者说,谴责的普遍应该推不出这次应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阐释能够消除部分道德绑架现象。
不过,从根本上讲,我们无法将这类现象彻底消除。道德绑架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受事方而言,施事方所提要求的道德性与这一要求对受事方而言的不合意性同时存在。如果受事方完全不讲道德,道德绑架会被受事方直接视为无理取闹;如果施事方的要求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就算受事方讲道德,这一绑架也不是道德绑架,而是无理取闹;如果施事方的要求完全合乎受事方的意愿,道德绑架就会演化成求助于人与助人为乐的美事。问题在于,道德绑架中的道德性与不合意性的冲突会一直存在。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每个行动者也是有限的。每个人难免会有求助于人的时候,每个人也难免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或者单单只是想要休息或偷懒的时候。当施事方求助于人,受事方力不从心或者只是想要休息时,其中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另外,由于我们认知的有限性,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如连续性悖论。从表面上看,它们跟道德没有关系。但是,基于这些更为根本的未决问题,道德绑架会自然地发生。例如,就算施事方所请求的受事方乐于助人,但如果施事方的要求一次一次地加码,或者单单只是一次一次地重复,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受事方的不合意感会突然产生。一旦产生这种不合意感,道德绑架感就会出现。考虑到一次一次重复要求的施事方未必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些人,这样的道德绑架在生活中就会经常出现。一个经常在类似情况下帮助他人的行动者,突然在某一次停止了助人为乐的行为。对于受事方而言,他感到不堪重负;但对施事方而言,受事方的这一次回绝是他的全部。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如果受事方行事谨慎的话,他就会想到,他遇到的这一次请求,跟他从前满足的所有道德请求性质相同,如果他满足从前的所有道德请求,那么,他也就应该满足这一次道德请求。因为,所有的道德义务都要求不偏不倚的公正性。但这一次,他出于个人原因想要拒绝。也许,他还可以再坚持一次,但他知道,总有一次他会因为无法继续而回绝。既然总是要回绝,在哪一次回绝都一样。在哪一次拒绝,都会引起施事方的不满,而这一不满,是引发道德绑架的关键因素之一。除非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可以综合计算所有得失,告诉施受双方所有信息,这样才可能有效避免道德绑架的发生。但这样的第三方并不存在。一些学者抽象地提倡“宽容与大度”,并将其视为“最佳选择”。根据以上讨论,显然是不相宜的。
乞讨现象的存在,提醒着物质的相对匮乏和我们的爱心之间的矛盾。相似地,道德绑架现象的存在,提示着社会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我们在道德与欲望间的深层分裂。要求一个行动者在道德上尽可能好,能达到多高的道德水准就达到多高的道德水准,这是对“道德圣人”的要求。然而,正如苏珊·伍尔芙所言,“在道德圣人意义上的道德完美,并不是人生幸福模型的构成要素”,它既没有那么理性,也没有那么好,不值得人类去追求。因此,在最为理想的目标引导下,由于人性的限制,我们必须再往下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无人知道。如果这个平衡点是德性的话,它可能被过度与不足摧毁。从理论上看,我们(如果是功利主义者的话)可以规定,如果受事方对施事方再多付出一点,其导致的总功利就会变小,这时的付出点就是平衡点。但是,这样的理论在实践中难以推行。因为,总功利涉及因素太多,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计算清楚。避免道德绑架跟过上美好的生活一样,相当复杂,它也许需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智慧”。在获得这样的智慧之前,我们不得不长期跟道德绑架现象共处。没有良药,唯靠忍耐。
来源:道德与文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U7Uu9W5dDh3Xv-w0VmqSQ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7-30 20:32
【案例】
道德绑架与道德义务的划分——兼谈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
作者简介:陈艳波,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道德绑架现象成为社会热点,这使得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厘清它的概念内涵和错误原因成为必需。在这方面,苏德超对道德绑架做了深入细致的现象刻画。然而,由于他的整个分析预设了一条成问题的原则,所以未能真正地刻画出符合经验直觉的道德绑架现象。通过引入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划分,可以澄清道德绑架发生在康德所谓的非完全义务的领域,是施事方以道德的理由绑架了应事方在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选择。道德绑架的错误在于施事方将完全义务领域的要求等同到非完全义务领域,剥夺了应事方道德选择的自由。基于此,道德绑架现象可以重新加以刻画。
〔关键词〕道德绑架 完全义务 非完全义务 定言命令
近年来,道德绑架现象在社会生活中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有的学者尝试概括道德绑架的特征及内涵,有的学者从交往理性理论的角度来反思道德绑架,有的学者对道德绑架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目前,学界还较少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分析道德绑架的概念界定和错误原因,致使道德绑架成了一个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却仍然有待澄清的概念。在这方面,苏德超对道德绑架做了深入细致的现象刻画,并立足于此分析了道德绑架与道德自由的关系。但是,本文的分析将表明,苏德超并未能真正刻画出我们对于道德绑架现象的经验直觉。除此之外,余涌的文章做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将道德绑架限定在非权义务的领域,指出道德绑架的错误在于将非权义务当成了完全义务,不过他的讨论是存在缺憾的。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分析苏德超对道德绑架现象刻画的失误,然后引入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指出道德绑架产生的原因正在于对两种义务的混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讨区分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根据及其合理性,以回应余涌的观点,并重新刻画道德绑架现象。
一、道德绑架现象刻画的分析
对经验直觉进行准确的现象刻画是精准提炼概念的前提,也是进行理论思维的基础。一个好的现象刻画就是要实现概念与经验直觉的反思平衡,它既是通过经验直觉不断修正概念的过程,也是通过概念补充澄清经验直觉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概念的概括力和解释力与所指称的经验直觉之间的平衡。显然,为了获得好的现象刻画,首先需要弄清我们的经验直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概念并展开概念与直觉的双向平衡。
循此理解,我们来看看学界对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在这方面,苏德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面我们就对他的刻画作出分析。首先,他给出了我们对道德绑架的典型感觉:“施事方甲以道德的名义对应事方乙提出要求,如果乙不满足这一要求,将违背道德;如果乙满足这一要求,又违背自己的意愿。这时道德绑架感在乙处就被激发起来了:想要拒绝吧,要求是合乎道德的;不拒绝吧,自己又不愿意去满足它。又因为这一要求是由甲提出来的,于是,乙就会觉得是甲冒犯了他,在道德上绑架了他。”然后,他将这种感觉归纳为:要求的外在性、要求的合道德性和要求的不合意性。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刻画道德绑架现象的八个条件:
对于任意两个行动者x和y(x≠y)而言,当且仅当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施事者x对应事者y实施了道德绑架。
(i)x呼吁y采取行动A;
(ii)对y而言,y采取行动A是道德的,不采取行动A是不道德的;
(iii)y无意采取行动A;
(iv)y知道(ii);
(v)采取行动A在y的能力范围内;
(vi)如果y不采取行动A,x(或其他行动者)就会对y实施道德谴责;
(vii)如果y采取行动A,那么,(vi)是y采取行动A的一个重要理由;
(viii)在A之外,y另有道德行动选项B,B跟A道德价值相当,且A与B不相容。
苏德超认为,通常对于道德绑架的理解仅仅包含了条件(i)到(vii),有时候甚至还会漏掉其中几个,但仅仅满足这七个条件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道德绑架现象。因为,如果我们设想x=y,那么这些条件描述的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挣扎;如果x≠y,那么这些条件描述的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挣扎被主体间化和外在化”。然而,道德挣扎并不是一种错误。因此,仅仅满足这七个条件的现象并不是真正的道德绑架现象。基于这样的分析,苏德超认为必须在前面七个条件之外增加(viii)才能构成真正的道德绑架。条件(viii)的加入使得应事者获得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如果施事者以道德的理由剥夺了他的这种选择权利就会发生道德绑架。
苏德超的分析尽管看上去已经足够细致深入,但它仍然是不成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整个现象刻画的论证不够严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所刻画的道德绑架与我们的经验直觉并不足够吻合。当然,就后一个方面而言,苏德超也许会辩解说,是我们的经验错了或者我们和他的经验直觉不一样,但细致的分析将表明,经验的反驳仍然是足够有力的。
就论证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用来证明前面七个条件不能刻画道德绑架现象的理由反过来用在他给出的全部八个条件之上:设想x=y,满足这八个条件的现象仍然是“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挣扎”,当行动A和行动B不相容时,这个人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道德选择”,而道德选择并不是一种错误,因此,我们也不能说这种选择的外在化是一种错误。如果内心挣扎和外在冲突之间的类比能够成立的话,条件(viii)的加入就不能改变这种类比;而且,自我的挣扎和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并不具有相同的结构,否则我们就预设了他人是自我的外化,从而消解了他人。
除去这种类比的错误以外,苏德超所刻画的真正道德绑架与我们的经验直觉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常来讲,我们在道德绑架中有一种重要直觉,即应事方有一种强烈的被侵犯感或被冒犯感。比如,动车坐票女生不给老人让座,在遭受他人议论后,她感到很委屈,有一种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产生的被侵犯感,这也是在诸多道德绑架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觉。问题是,这种被侵犯感从何而来?被侵犯的东西又是什么?显然,这种被侵犯感并非来自有人对他进行道德呼吁这个单纯的行动。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一个人准备说谎时,我们将对他进行呼吁和劝说,让他讲真话。一般而言,这并不会让此人产生被侵犯感。这就意味着,仅仅是要求的不合意性并不会直接激起被侵犯感,因为还没有什么东西被侵犯。可见,应事方的被侵犯感有另外的原因。
我们通常认为,在道德绑架中,应事方之所以有被侵犯的感觉,是因为他在被要求所行的道德之事上是有选择权的,即他既可以选择按要求行道德之事,也可以不行这样的事情。正是施事方以舆论等手段相胁迫,让应事方受到绑架而在他本可以有选择权的地方失去了选择的可能,因而产生一种被侵犯感。这里,被侵犯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应事方在道德上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根据这种理解,在是否要给老人让座的问题上,女生是有选择自由的。人们的议论形成了舆论绑架,剥夺了她的这种选择自由,让她感到委屈,而产生一种被侵犯感。然而,正是在这里,苏德超的现象刻画与我们的直觉产生了分歧。
苏德超可能会这样来刻画动车女生所处的情境:女生(y)让座(采取行动A)是道德的,不让座(不采取行动A)是不道德的(依据条件ii)。这就表明,在让座行为的道德赋值上,只有道德或不道德这两种可能,这就将这位女生置于没有选择的处境中。选择做不道德的行为本身是不道德的,对不道德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也是正当的。所以,在一个没有道德选择的处境中不存在道德绑架。正因如此,苏德超才会认为,他的前七个条件不能真正刻画道德绑架现象。道德绑架是一种以道德之名而实施的绑架,它肯定是对应事方的道德自由的某种限制和剥夺(这是“绑架”一词的应有之义)。由于条件(ii)取消了道德选择,因此不可能有道德绑架发生。或许也正是因此,苏德超引入了他的条件(viii):“在A之外,y另有道德行动选项B,B跟A道德价值相当,且A与B不相容。”通过这一条件的引入,应事方就有了道德选择的自由,绑架的发生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的被剥夺。如此,苏德超也得到了他所刻画的“真正的道德绑架”,应事方被剥夺了在两个及以上的同样重要的道德选项间进行选择的自由。
苏德超的这种现象刻画是不成功的。首先,在动车坐票女生让座的问题上,直觉告诉我们,这个女生在让座和不让座之间拥有选择的自由,道德绑架的发生正是对这种选择自由(采取行动A或不采取行动A)的剥夺。我们当然可以设想某些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境,比如撒谎是不道德的,不撒谎是道德的。但是,撒谎与让座是两种道德性质不同的行为,前者是作恶,后者是行善,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一切与道德相关的行为都认定为非黑即白。苏德超当然可以坚持认为,在让座(即行善)的问题上,事情就是非此即彼的,但这种简单的判定却可能带来十分荒谬的后果。设想强制让座成为合理的行为,可能就没人愿意买坐票了。因为他的座位可能被强制占据,他自己也可以合理地强制别人给他让座。设想强制行善成为合理的,那么人人都将为帮助他人而疲于奔命。因此,直觉给予让座或不让座的选择自由恐怕比苏德超对于这种选择自由的取消更合理。
其次,苏德超通过引入条件(viii)来刻画道德绑架中对选择自由的剥夺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此被刻画的现象已经很难说是一种道德绑架了。道德绑架是以道德的理由实施的绑架,我们很难想象,施事方能以什么样的道德理由来绑架应事方在两个道德价值相当的选项中的选择,因为在把两个选项的道德价值评估为相当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几乎所有的道德理由。这就意味着,施事方可以通过一些理由(比如晓以利弊或动之以情)来绑架应事方的选择,但一定不是道德理由。不以道德理由产生的绑架,很难说是道德绑架。在这里,苏德超明显将“以道德的理由进行的绑架”替换成了“在道德领域发生的绑架”。苏德超在文中所举的那个医生给病人输血的例子,尽管在他看来是真正的道德绑架的案例,但其实并不符合他对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因为,未被救治的病人乙的亲属谴责医生的道德理由是见死不救,这确实是一条道德理由,但乙的亲属以此理由来对医生进行道德谴责却是无法成立的。医生并没有见死不救,只是他救的是病人甲。换言之,即使乙的亲属会以见死不救的理由来对医生进行道德谴责,并未实施见死不救的医生也可以不为所动。这就意味着,乙的亲属的道德谴责不会成为医生的行动需要考虑的理由,也就不能满足苏德超的条件(vii)。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乙的亲属要对医生构成道德绑架,必须提供医生只能救治乙而不是甲的道德理由,只有这种理由才能构成对医生的道德选择权利的剥夺。但苏德超无法提供这种理由,因为他已经设定医生面临的是两个道德价值相当的选项。或许正是因为很难设想出医生只能救治乙而不是甲的道德理由,苏德超为了满足他的现象刻画条件,特别是为了满足条件(ii),才设想了这样一个对救治乙或者甲都适用的道德理由。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就没有办法满足条件(vii)。因此,苏德超的困难在于,由于条件(viii)的引入,道德绑架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
综上所述,苏德超对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的根本失误在于,他预设了一条基本的原则:不行道德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正是基于这条原则,他才提出了条件(ii)。但是,这条原则在人类的道德行为中其适用范围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如果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完全义务”的领域,超出了完全义务的范围,人类道德行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与不道德。而且,大部分道德绑架现象的发生恰恰不是在完全义务的领域,而是在康德所说的非完全义务的领域。下面,我们将根据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来讨论道德绑架的问题。
二、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
众所周知,康德的道德哲学被称为义务论。对康德而言,道德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所谓义务就是说,道德行为是某种受到强制而履行的行动。一般而言,说某种行为是受到强制而履行,往往意味着它受到外在的强制而不是出于自愿。强制之所以是外在的,是因为强制往往只可能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意志之间,即一个意志强迫另一个意志履行某种行动。如果不存在一个另外的意志的影响,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自愿的。但是,当康德强调道德行为是一种义务,并且义务意味着某种强制时,他恰恰认为这种强制并非来自另外一个外在于我的意志,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意志。换言之,在履行道德行为时,我们是自己在强制自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自己强制自己这种奇怪的状况呢?因为,在康德看来,人是一种双重存在者。一方面,人是理性存在者,理性规定了他行动的原则,他的意志就是“按照原则去行动的能力”。这样一来,所谓强制,就是理性对于意志的强制。但是,如果人的意志本身是被理性完全规定了的,没有一种与理性相反的行动原则,也谈不上理性强制意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掉理性(原则),意志甚至连行动都是不可能的。自然界的事物仅仅是按照自然规律来运行,而不是受到自然规律的强制。因此,当我们说义务意味着我们自己强制自己时,一定是因为意志在理性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规定或者影响。这就涉及另一方面,人也是感性的存在者,感性偏好是影响意志的另一种因素。对此,康德说:“意志还受到那些并不总与客观条件相一致的主观条件(某些动机)的支配”,这些主观条件就是“欲求能力对感觉的依赖性”,亦即感性偏好。正是由于这些主观条件的存在,才使得人的意志不能毫不费力地服从理性原则的规定,人也因此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样一来,所谓自己对自己的强制实际上就是理性原则对于感性偏好的强制。基于此,康德将义务定义为“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这里的法则就是理性法则,而必然性一方面意味着理性法则本身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法则对于偏好的强制性。
有论者将道德绑架归咎于它的强制性,认为道德绑架“剥夺了个人的道德自由”,“将一方的价值强行规范和限制于道德主体”。但是,经由以上对康德义务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强制性。因此,行为本身的强制性并不是道德绑架错误的原因。也许人们会反驳说,道德绑架的强制性来自外部的另一个意志,而道德本身的强制性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强制。这看上去十分有力。但根据康德的看法,这种观点仍然是不成立的。如果那个来自外部的强制性是基于理性的原则而不是感性的偏好,那么这种强制性就是符合道德的,自然不能被称作道德绑架。而如果那个外部的强制性来自个人的感性偏好,那么它根本就不是道德的,也谈不上道德绑架。实际上,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学说是允许外在强制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外在强制的有效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只有当外在强制被应用到其权力范围以外的义务上时,才会发生我们所说的道德绑架。
为了确定道德领域中外在强制的界限,康德将义务划分为非完全义务和完全义务,或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后者来说,一种外在的强制在道德上是可能的,但前者仅仅依据自由的自我强制”。也就是说,在完全义务(法权义务)领域之中,外在的道德强制是被允许的,而非完全义务(德性义务)领域则不允许存在这种强制。典型的非完全义务即是行善,比如帮助他人;典型的完全义务则是不要作恶,比如不要杀人。显然,在康德这里,是否允许外在强制是区分两种义务的本质特征。就完全义务而言,康德进一步认为,我们可能出于对理性法则的敬重而强制自己履行义务,也可能受到外在权力的强制来履行这一义务,前一种履行是“出于义务”,后一种则是“合乎义务”。显然,尽管只有“出于义务”可以被称作道德行为,但“合乎义务”的发生并不是一种道德绑架。因为,在完全义务的领域中外在强制是被允许的。事实上,只有就非完全义务而言,外在的强制执行才构成道德绑架,理由有两个:一是这种强制限制了非完全义务应有的自由任性;二是这种强制预设了错误的道德赋值。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康德认为,非完全义务的强制性仅仅表现为“法则(laws)要求行动的准则(maxims),而不能要求行动本身”。这即是说,我们在履行非完全义务时所依据的准则仅仅为我们划出了一个可能行动的范围,并不具体地规定我们一定要采取某种行动;这个准则并不告诉我们要如何行动,以及行动所要达到的程度。用康德的话说:“法则为遵循(遵从)留下了自由任性的一个活动空间。”这种自由任性的活动空间体现为:(1)判断某个行动准则与主体的当前处境是否相关的自由;(2)在确定一个与当前处境相关的行动准则以后,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方式来实现这一行动准则的自由;(3)即便在知晓某个具体行动满足与当前处境相关的行动准则的要求的情况下,选择执行或不执行该行动的自由。以行善为例,“帮助他人”作为一条非完全义务(的准则)应当在某些处境中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基本原则。比如,在公交车上遇到需要座位的老年人,我既可以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也可以呼吁其他人把座位让给他,还可以选择不做任何事。虽然这看起来与我们的直觉有些相悖,但康德认为,某一条非完全义务的准则可以被另外的义务准则(或者是完全义务的准则,或者是不完全义务的准则)所限制。因此,如果不为履行非完全义务留下那样的自由空间的话,那么所有义务准则就会陷入争夺优先权的冲突之中,最终使得所有义务都无法得到履行。因此,基于以上对非完全义务之履行自由的承认,当某个外在的要求强制我们在某个时刻履行非完全义务,又或者强制我们采取这样或那样指定的履行方式时,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遭受了道德绑架;同时,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指出这种道德绑架的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我们在履行非完全义务时所应当享有的自由。
与自由地履行非完全义务相关,道德绑架还体现为对道德行为赋值上的错误。在康德看来:“德性义务的履行是功德(meritum)=+a;但对它的违背却并不马上就是过失(demeritum)=-a,而仅仅是道德上的无价值=0,除非主体的原理就是不服从那些义务。第一种情况中决心的坚强其实只是德性(virtus),第二种情况中的软弱与其叫做恶习(vitium),还不如说只是无德性,是道德上的坚强的缺乏(defectus moralis[道德上的匮乏])。”这段引文意味着,在对某个行为进行道德赋值时,并不是只有正值和负值(功德和恶习),康德的道德哲学允许一种在道德上无价值的行为。对于有功德的行为,我们应当予以赞赏;对于恶习或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应当加以谴责。但是,对于道德上无价值的行为,我们就不应当给予附带价值判断的评价。与前述非完全义务所具有的自由空间相关的是,如果认为履行义务是有道德的,而不履行义务就是不道德的,那么就会通过这种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取消掉非完全义务的自由空间,因为我们通过道德谴责所表示的是必须履行义务要求。所以,如果承认我们在履行非完全义务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么就必须认可道德上无价值行为的地位。实际上,在康德看来,如果我们不承认在道德性方面无关紧要的事物存在,甚至在吃鱼肉还是吃猪肉,喝啤酒还是喝葡萄酒等事情上也要做一番道德价值上的考虑,“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义务……就会使德性的统治成为暴政”。因此,道德绑架正是人们将本来在道德上无价值的行为判定为应当遭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即进行了错误的道德赋值所导致的道德暴政。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一方面将道德绑架限定在非完全义务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通过对非完全义务的履行自由和道德赋值的分析阐明了为什么在非完全义务的履行中引入一种外在强制是对主体的道德绑架,以及道德绑架为什么是一种道德错误。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如何区分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或者说它们的区分根据是什么。
三、区分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根据
我们在前文的讨论中指出,只有通过对非完全义务和完全义务的划分才能准确地理解何为道德绑架以及道德绑架错在哪里。实际上,余涌就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来分析这一问题。在《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一文中,他认为“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在这里,“非权义务”是指:“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这种义务不与某种作为要求权的道德权利直接相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被称作‘非权义务’。”非权义务“不与某种作为要求权的道德权利直接相关”,意味着它不是外在强制的,因此在概念的外延上它与康德的非完全义务基本是相同的。换言之,余涌与笔者都认为,道德绑架是发生在非完全义务(非权义务)领域的一个道德错误。然而,对道德绑架的这样一种分析依赖于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区分的合理性,因为如果这个区分是不成立的,那么前面对道德绑架的内涵确定和错误指认就将失去基础。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康德在区分两种义务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标准,即看这种义务是否允许一种外在强制的介入。然而,这个标准仅仅是区分两种义务的手段,而不是对区分两种义务的根据的说明,也不是对说服我们接受这种区分的理由的说明。因为,区分的根据需要为两种事物表现出来的区分特征提供解释,而“是否允许外在强制”这一标准可以说仅仅是区分两种义务的根据所造成的结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义务之强制性的说明:完全义务的强制力较强,以至于它能够允许一种外在强制的介入;而非完全义务的强制力较弱,以至于它仅仅接受一种内在的强制。那么,是什么导致道德义务在强制力上的强弱之分呢?
在余涌的文章中,他试图用是否具有相应的道德权利来作为划分两种义务的根据,并以此来说明相关道德义务在强制力上强弱之别的原因。完全义务因为有相应的道德权利要求方,它的实现是以外在(来自权利要求方)的强制为基础的,而非完全义务由于没有相应的道德权利要求方,它实际上不存在外在强制的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成问题的。在这种看法中,要求方的权利成为义务之强制性的来源,如果某种行为没有相应的权利要求方,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强制要求别人施行这一行为。然而,对于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根据来说,这一看法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虽然区分开了两种行为,但却是义务行为和非义务行为(而不是非完全义务行为)。因为,当它以权利来为义务行为的强制性提供保障的同时,就在事实上取消了非义务行为的强制性。这种义务和非义务的区分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同时,将非完全义务完全视作没有权利要求方也是有争议的。比如有学者就论证说,某些不完全义务(比如感激)也是有权利要求者的,这些义务的权利要求者可能不是具体的个人,却可以是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因此,以是否具有对应的权利来作为划分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根据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此外,我们对于权利作为义务之强制性的来源这一看法也存有疑虑,因为它必须进一步解释权利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如果这种合法性得不到论证,那么它的强制性也是存疑的。
在“权利-义务”这一解释框架之外,余涌在文章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划分两种义务的根据,即“不同的道德要求对于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不同”。这一观点看上去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完全义务(比如不要杀人、不要说谎)对于一个有序的社会来说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以强制来要求人们履行这些义务,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然而,不完全义务(比如行善)无法在社会中得到普遍施行却不会影响社会的运转。事实上,现代社会中保障社会运行的法律是以“不干涉他人”为基本原则,而不是“帮助他人”。然而,这一观点依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首先,对于在社会生活中哪些道德要求更重要,哪些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缺乏一个区分和判断的依据。因此,这个观点用对社会生活重要性的强弱来取代道德义务的强制性的强弱并不能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其次,这一观点试图引入“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来帮助我们澄清两种义务的区别,但如果我们将维护人类社会生活仅仅理解为维护人类有序的社会生活,避免爆发出人对人的战争,那么所谓“重要性的不同”实际上就只是“重要或不重要”的区分,而不是“重要或次重要”的区分。如此一来,非完全义务作为“不重要的”义务实际上也就可能失去了它的强制性,因为维护人类社会的有序生活是不需要它的。因此,这一区分根据的引入实际上取消了非完全义务。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将“维护人类社会生活”划分为维护有序的生活和维护好的生活两个层次来避免上述问题,但我们依然很难给出充分的理由以解释好的生活如何使某些行为成为义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余涌给出的两个解释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区分的理由都存在逻辑上取消非完全义务的危险。实际上,已有学者基于我们很难给出两种义务的划分依据而主张取消掉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区分:“这里并没有严格的二元论,(最多)只有一种由非完全义务和完全义务组成的连续的义务领域”;或者去除非完全义务行为的义务性质,代之以“额外责任”(supererogation)的概念。其实,康德的道德哲学已经为两种义务的划分根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说明。在康德看来,前述方案的失败是由于它们试图在道德行为本身之外去寻求义务之强制性的来源(或者是权利,或者是维护社会生活的需要)。事实上,道德行为的义务性仅仅源于我们自身理性对于感性偏好的强制。对康德而言,理性对于偏好的强制表现为定言命令,它作为检测公式能够用来确定某种行为是否道德。因此,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定言命令来分析两种义务的根据。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要合乎道德,而且必须出于道德,这就要求道德行为不能以某种特定的意图作为行动的依据,而必须以理性本身为意志制定的法则为依据。这种理性为意志制定的法则被康德称为定言命令,“它不涉及行动的质料和应当由此而来的结果,而是涉及行动的形式及原则”;它所规定的行动“自身就是客观必要的”。它被称作“定言的”,是因为它作为“命令”的强制性并不来自一个有限的条件(或者说意图)——以有限的条件作为强制性之来源的命令被称作假言命令;相反,这一命令的强制性是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强制性的背后是理性本身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康德看来:“定言命令只有唯一的一个,这就是: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所谓准则指的是人的主观行动原则,法则指的是理性给出的客观行动原则。定言命令通过对准则的规定来规定我们的行动,它给准则的规定只有一条,即“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亦即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决定一条准则能否成为道德准则的关键所在。这种普遍性就保证了准则的强制性。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区分了两种获得普遍性的方式:“能够”和“意愿”。一条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遍法则,指的是违背这一准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对准则的违背会造成客观上的矛盾;“意愿”一条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则是指尽管可能违背这一准则,但人们却不愿意这种违背发生,对准则的违背会造成主观意愿上的矛盾。正是由于不同的准则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证自身的普遍性,因此,它们所具有的强制力也是不同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这两种取得强制力的方式来划分依照不同准则行动的义务,即完全义务和非完全义务。正如康德所言:“有些行动有这样的性状:它们的准则就连无矛盾地被设想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也不可能,更不用说我们还会愿意它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法则了。在其他一些行动那里虽然不会遇到那种内在的不可能性,但是却仍然不可能愿意它们的准则被提升为一条自然法则的普遍性,因为这样一个意志将会是自相矛盾的……前者违背了严格的或狭义的(不容免除的)义务,后者只是违背了较广义的(值得赞许的)义务。”
我们可以通过康德所列举的四种义务来更具体地理解上述区分。首先,康德从自然法则公式对道德准则的形式进行规定的角度来讨论的。诸如不要自杀或者不要做出虚假承诺这样的行为准则应当成为一种道德准则,是因为它们的反面准则(即自杀和虚假承诺)在普遍化的时候会遭遇自我否定:自杀这一准则如果被普遍遵循的话,就会使得自杀成了不可能的,因为已经没有人了;如果虚假承诺的准则被普遍遵循的话,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别人的承诺,而承诺被别人相信是虚假承诺之所以有效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虚假承诺也就成了不可能的。其反面不能无矛盾地设想的准则所规定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义务。诸如发展自身的天赋才能和帮助他人这样的行为准则应当成为一种道德准则,是因为它们的反面尽管是可以被设想的,但却不是人们的意愿。因为在康德看来,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都会愿意自己的天赋才能得到完善,或者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以上的举例是。其次,康德还从道德准则的质料的角度将定言命令规定为“行动的准则要以人性为目的”。在人性目的公式下,“能够”原则和“意愿”原则相应地表现不能违背人性和应当促进人性,同样也支持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
可以看出,在康德这里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依据可以归结为定言命令所具有的“能够”和“意愿”两个不同维度的区分。这一结论能够完全避免取消不完全义务的危险,因为当康德用定言命令来规定我们的行动准则之时,就已经用理性本身的绝对权威对我们的行动施加了不容置疑的强制力。至于说康德为什么不把一切道德准则都看作是完全义务而容许了非完全义务的存在,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出于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本性吧。
余 论
通过引入康德对完全义务与非完全义务的划分,我们发现,道德绑架发生在康德所谓的非完全义务领域,它的错误在于施事方将完全义务领域的要求等同于非完全义务领域的要求,剥夺了应事方道德选择的自由。由此观之,苏德超现象刻画的失误也在于他首先将道德绑架置于完全义务的领域中,从而未能真正刻画出符合我们大部分经验和直觉的道德绑架现象。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他的条件(ii)来完善对道德绑架的现象刻画,将条件(ii)修改为“对y而言,y采取行动A是道德的,不采取行动A是非道德的”。这一修改保证了行动A处在非完全义务领域中,对行为的道德赋值,不是道德与不道德,而是道德与非道德,这既为施事方以道德理由实施绑架留下了空间,也为行为者的行动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当然,正如前所述,修改需要抛弃苏德超的条件(viii)。经过这样的修正,道德绑架现象可以刻画为:
对于任意两个行动者x和y(x≠y)而言,当且仅当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施事者x对应事者y实施了道德绑架。
(i)x呼吁y采取行动A;
(ii)对y而言,y采取行动A是道德的,不采取行动A是非道德的;(道德选择条件)
(iii)y无意采取行动A;
(iv)y知道(ii);
(v)采取行动A在y的能力范围内;
(vi)如果y不采取行动A,x(或其他行动者)就会对y实施道德谴责;(绑架条件1)
(vii)如果y采取行动A,(vi)是y采取行动A的一个重要理由。(绑架条件2)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现象刻画是符合我们对道德绑架的基本理解和经验直觉的:道德绑架是施事方以道德的理由对应事方的道德选择实施的绑架。
来源:道德与文明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4rr5jgXfWerebn2vsPng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9-20 11:14
【案例】
甘绍平 | 个体的崛起与道德的主体
【摘要】现代性呈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个体崛起的趋势,这一趋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提升了人之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为每一个人内在潜力的迸发和自主生命的展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它对于身心皆具有无法摆脱的脆弱性的每一位个体而言,也意味着选择上的风险与挑战。在这种风险与挑战面前,每一个人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位理性、成熟的行为主体,就必须基于人性需求,通过对自身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他者利益及社会利益的全盘统一的研判与考量,自觉主动地与他人建构起一种对于自身福祉与社会秩序均有保障作用并体现出自主、理性、普适的契约道德。该道德呈现出对所有的当事人权益的珍视,对行为主体本身非理性的、极端自利的限制以及团结与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现代性语境下的成熟的理性个体,也就通过自立规则和自守规则,通过从外在强制向理性的自我强制的进化,通过从一位自由的个体到道德的主体的文明状态的转变,证成了将自由与道德统一于一身的逻辑必然性。
【关键词】现代性 个体化 自由 契约道德
最能够清晰定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市民阶层的政治革命、工业化的崛起以及社会分层的开始与持续这一连串相互关联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基本特征的核心概念,就是“现代性”了。现代性标志着整个人类跨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它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人的解放的重视与强调。这里所谓的人,并不是作为某一特定团体或整体之组成部分意义上的人,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写着的个体的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之个体的崛起。个体从传统的家庭角色、君臣等级、村落归属、交际网络、生活模式的制约中解脱了出来,从而在地理和社会的层面上真正因流动性而获得了自主性。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欧洲普遍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创造了我们称为个体性的事物:个体内在与外在地摆脱了中世纪的集体形式,这一集体形式将个体的生活塑造、确认、本质特征联结成一个同等的整体,从而从某种意义上使个人轮廓不再存有,个体自由、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个性以及自我责任等的发展也就受到压制。”[1]总之,现代性所提供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历史事实与经验便是个体性或个体化。个体性所指征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依附关系中的解脱,同时当事人又建构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主张,即个体已成为社会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其在应对所有生存问题与风险挑战时要将自己置于中心的地位。个体化是一种线性的不可逆的发展,“它标志着西方社会与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相伴随的一种转变的过程,即个体从异在决定到自我决定,亦即个体成为其自身社会现实之形塑者的一个过程”[2]。个体性或个体化表达了一种注重个体之人的强烈的价值诉求,尽管这一价值作为一个预期目标与社会现实总是处于持续的张力关系当中,但现代性的最大功绩恰恰就在于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共同体在缺乏个体认同的情况下难以维持辩护其存在的理由,社会结成与国家组建的宗旨被锁定在对个体利益的看护与保卫上,社会与国家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拥有反思及行为能力的个体的福祉;“个体人格尊严至上”之理念是形成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建构性条件,个体拥有不容侵害的权利,个体利益的优先性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让渡与限制,个体权利本位的立场作为一种核心要素支配了现代国家之整体治理系统的运作逻辑。
个体性是现代性的一个表征,其出现的历史也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随的。个体性之理念与实践的产生有几条线索可供溯寻。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早在古希腊传统中个体性的说法便得到了最初的孕育与萌发。基督教时代,教会阐发了一种人有罪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又往往与有罪的个体相系,因为对宗教律令的违背只能归罪于单个的个体,故个体的身份便从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发展基础。后来的宗教改革,又使得个体的良心自由及自我责任的意识成为人的自我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经过17世纪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和18世纪康德的努力,个体性的概念得到了哲学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系统表述,并且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新兴的市民阶层在与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抗争中逐渐崛起,他们试图摆脱专制体系的束缚,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呈现出自身的个体价值。敲响君主制度丧钟的法国大革命,更是导致了原处于臣民地位的市民阶级从无条件的服从义务中的彻底解脱,催生了每位个体作为国家公民都拥有平等的人格地位的理念,创造并展现出个体自身追求其自我利益最大空间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个体性现象的出现除有其思想观念、社会政治等要素的始因外,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劳动分工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功能的分化,则成为个体意识得以建构与强化的更为根本的动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一个功能上分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个体性或个体化则是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分工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一直就没有“社会由个体组成”的观念,因为“在节段或层积差异化的社会里,不是使社会的人而是家庭成为社会的核心”[3]。“古希腊社会一般被视为众多家庭的聚集。它们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个体只有作为家庭织网的一部分才能生存,脱离之既无自由亦无尊严。”[4]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劳动分工的进程,个体就不再被束缚在家庭或村落的结构之中,而是因一种独立原子的角色获得了巨大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变换性,原有稳固的血缘关系被一种松散的经济联系所取代,从而导致大家庭意义的丧失以及村落共同体的衰败。与传统社会里大部分成员聚集在一起,其特征相似、角色模糊的情形不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里,劳动分工导致角色确定以及岗位的专业化,例如企业家、技工、高管、科学家、医生、律师、记者、艺术家和教师等群体的逐渐出现。而从具体角色及专业岗位的感受里,当事人又能够生发特殊的体验以及独特的需求,“与此相应的是,个体在追求其自身利益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便发展出了一种不断提升的自我意识”[5]。总之,社会功能的分化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得作为过去集体中匿名的、消极成员的个体,成为具有独特性感受的独立自主的积极的行为主体。这样一种作为独立行为主体的个体的诞生,不论对于社会整体还是个体当事人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于社会整体来讲,作为原子式个体的行为主体,一旦被投入由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社会竞争之中,就会通过成就展示自我认同,通过成功赢得自我发现,通过对财富和地位的拥有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它促使每个人能力的迸发和财富的增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从中受益。“同时,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再由其原初的出身得到界定,而是由导致交换的、相互增进的利益格局得到确定。”[6]对于当事人个体而言,与在传统社会里个体只能承担某种被分配与指定的单一角色的情形相异,社会功能的分化迫使行为个体参与到复杂的社会系统所呈现的所有社会交往的关联之中,并在如家庭、学校、教会、协会、职场等场域所提供的不同角色中持续转换,从而成为各种社会联系中的纽结点。这样一种纽结点的地位,对于当事人主体意识的生发与强化是至关重要的:大家都是社会联系中的纽结点,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便会感受到互为主体;每位个体都是一个人,他不仅可以与“我”结成交往关系,而且也可以任意与其他人结成这种关系。从自我视角来看,“我”是各种社会联系中的纽结点,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便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从每位他人的视角来看,他也是各种社会联系中的纽结点,故他也是世界的中心与自我目的。这样,每个人都拥有尊严的想法与理念便油然而生了。故而,“自由与尊严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功能上分化的社会里的一种基本建构”[7],并且这一尊严之拥有并非取决于行为主体所作贡献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他所具备的行为主体之地位本身。因为他要参与到无限多的交往关系中去,包括目前尚未出现而是将来才会出现的交往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如此一来,他自然就会有一种对其尊严得到普遍认可的需求。正如菲茨(Gregor Fitzi)所言:“随着持续的分化,社会群体日益强烈地依赖个体的自主性,个体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是作为社会化过程的纽结点起作用的。这就使得社会导向对人的尊严予以机制化的保护,因为这关涉对人的生存基础的保障。”[8]
总而言之,伴随着18世纪以来社会功能分化的进程,个体由于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拥有了“社会联系中的纽结点”的地位。这一个体化的状态自然就会导致个体性、行为主体、个体自由与尊严等概念与精神得到显著的提升与强化,甚至成为现代性时代具有突出特色的文化诉求与价值模式。
file:///C:/Users/MS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
一、个体崛起的世界
如前所述,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核心价值在于人之个体的崛起,现代性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就是个体性或个体化。个体性或个体化意味着“人之个体的分量是否得以强调”已被视为社会观察与评价的尺度及价值判断的核心。
1.个体与个体性
对个体性或个体化予以深入阐释的前提条件是对“个体”概念的把握。这里呈现出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所谓个体就是社会最小的、无法再划分下去的单位。他因具备唯一性而与其他个体不可混淆;他因拥有目的意向性而成为一位充满活力的行为主体。他可以承担不同的角色而其同一性却得以保留,从而使其行动获得认定与溯源。正如林德曼(Gesa Lindemann)所言:“判断一位生物上活着的人的归属标准之特征,在于这一标准虽是社会学产生出来的,但最终还是作为一种非政治的、严格说来甚至是非社会性运用的标准而起作用。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在于,看一个人的身体,其内在目的性是否得以贯彻,即自身的生命活动运行是否能够得到观察。”[9]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成长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撑、影响与制约,这样个体就往往呈现出一种与集体相系的个体形态,从而也就实现了个体与集体的某种领域或某种程度的融合。但集体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体的根本利益而获得存在理由的,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离开了个体因共同的生活境遇及需求而自觉自愿地相互结合,集体也就无法形成。所以,个体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尽管在许多方面个体为了集体的福祉需要作出让步,但在人格尊严、精神自由这样的核心利益上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正如规范个体主义(Normativer Individualismus)所强调的:“个体绝不能被牺牲,即便是为了人性理念或者是为了未来世代的福祉也不行。…… 每个人都是一位个体;保卫个体的价值关涉保卫每位个体的价值。”[10]
明确了“个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就为进一步对“个体性”或“个体化”进行详尽的解析奠立了良好的基础。个体性或个体化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所谓“个体性就是自我确定的独特性”[11]。这就是说,“个体性”概念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个体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因其唯一性而与他人具有着差异,因与他人之间的不可混淆而呈现出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甚至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这通过施莱尔马赫而成为一种世界观的旋转中心”[12]。生命的使命在于充分展现自身的独特性,这样一种理念也在歌德、浪漫派及尼采那里得到了主张与发展。二是个体的自我决定。所谓自我决定“表征着一种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予以自由掌控的理念。这是一种立场,它使得为整体所忽视并屈服于整体的个体获得了中心性的意义”[13]。个体的自我决定能力的获得显示出他已经生活在一种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结构之中。在传统社会,个体被嵌定在别无选择的集体里,并因而使自己获得长期幸存的机会。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个体为了幸存而被束缚在某一固定的集体中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对于由传统、习惯和经验构成的有约束力的预制物,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可以自我选择的社会联系。在对这样一种可以自我选择的社会联系的生活体验中,个体对一切事物予以自我决定的意识与能力便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与强化。自我决定能力的增进,就会因个体创造力的迸发而带动起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科技创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
如上,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的个体性或个体化一方面体现为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呈示为人的自我决定的能力。就像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观念一样,个体性往往首先表现为一种应当遵循的价值模式或应当追求的规范目标,独特性与自我决定的现实实现程度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具体境遇和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法律规制的框架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齐美尔在他那个时代甚至认为个体性的两个要素(独特性与自我决定),在不同国家可能会得到不同力度的强调:“大体上人们可以讲,以单纯自由的、原则上被视为平等的个体性为特征的个体主义确定了法国和英国的理性自由主义,而注重性质的唯一性与不可混淆性的个体主义更是德意志精神中的事情。在建构经济原则的过程中,19世纪使得两者都得到了成长,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与平等的学说构成了自由竞争的基础,差异性的个性学说构成了劳动分工的基础。”[14]就此而言,独特性与自我决定一方面是个体性概念的组成要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概念所要求的应当达到的价值目标。不过,个体性概念本身无法担保这个目标的具体实现。期待在人生的每一秒钟都能展示自己的独特性与自我决定的能力,这无疑是一种无望的苛求。正如席曼克(Uwe Schimank)所言:“把自己理解为个体,这仅仅意味着一种相应的总体准备:尽管我在某一既定场合——或者甚至在大部分场合——没有展现为独特性的和自我决定的个体,我却留有在任何时候这样去做的努力。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中不再拥有这样去做的希望的场合经常出现,他的个体化的自我理解才真正受到损害。”[15]
2.个体化的两个极端
综上,拥有着独特性与自我决定能力之内涵的个体性或个体化理念,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作出了一种概要性的刻画。现代性呈现为一种不可逆的、任何作为当事人的个体都无法逃避的历史进程。现代性所蕴含着的个体化的趋势促使每一位个体都获得了一种以往历史阶段所无法提供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个体化的趋势意味着自我发展上的更好的条件、自主生活展开的全新的可能性以及个人机遇与机会的迅速剧增;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而言,个体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以前先在的联系被后选的自我确定的联系所取代,意味着从原来异在的强制和别无选择向必须自我决断的重大转变。“个体的人在决定关系的建构、持续与结束时,完全要依赖他自己。”[16]这样,获得了自由的个体立即就要面临选择的痛苦、选择的风险和迅速提升的自我责任。就此而言,个体化的趋势呈现给每一位个体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无需诅咒也不值得庆贺,而是有赖于当事人理性态度的慎重应对,特别是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由于难以承受选择的风险与责任,一些个体会放弃自己的自由,倒向极权专制的掌控;二是一些个体在选择之机遇面前变得无限的自我膨胀,从而滑入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体主义。
第一个极端表现为对自由的主动逃避。我们知道,现代性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个体的崛起以及个体地位的确立。个体性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流动性和自主性的行为主体。但是传统依附关系既表现为对个体的一种束缚和压抑,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一种依托、支撑与方位指南,并且也免除了当事人的决策负担。一旦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脱了出来,他马上就可以享受到无限选择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失去了可供支撑的稳定基点,陷入充满风险与挑战的不确定性状态。对于许多人而言,选择的强制则意味着一种无法忍受的苛求。“没有一种归属感,每一种自由的体验都将很快化为虚无的臆想。谁要是不知道,他的地方在哪里,他应遵循怎样的规则,他要朝着哪个方向,他就不仅失去视野,而且很快也会将自由感受为一种有威胁的负担。”[17]齐美尔、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贝克(Ulrich Beck)都曾意识到,许多已达个体化水平和阶段的人,由于不堪选择的重负,会自觉地转向对外在权威的寻求,退回到对一种处于上位的主管的臣服状态,以满足其受到保护的需求。“齐美尔鉴于个体选择的痛苦,认为他们会进入一种模式,该模式借助个体臣服于一种普遍的范型,一种——如果他们乐意的话——自选的奴役,而使他们摆脱了持续的个体决断的苛求。”[18]
个体以逃避自由为代价所等待和拥抱的是一种全新的集权性的等级系统,它向社会给出了一种提供秩序的承诺,从而能够让个体免除混乱、矛盾、冲突的纷扰,永享平和与安宁。更有甚者,这一等级化的系统结构在现代性时代还被注入了理性化的要素,整个社会可以如同一台构造精密的机器,在规制化、官僚化的气韵掌控下高速有效地运转。而个体在这一巨大的联动机器中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其所有的行动均受到监控、限定与压制,其本身借由驯服的方法而成为规训的存在,即个体不再拥有价值,只有整体利益才是一切。同时,由于劳动分工以及行为链条的延长,个体本身的行为后果自己无法予以识别,对自己造成影响的其他行为主体的身份也无法加以认定,因而他也就几乎丧失了任何道德责任感。“对组织及其成员的忠诚取代了能够造就责任的对他人的亲近。假如大家都把自己理解为一种处于上位的意志的工具,那么等级化的系统结构就会导致个体责任持续地向其他参与者推诿,这些他人中没有谁会因其道德责任而受到个体性的指认。”[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称,现代性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残暴的潜能,因为作为对自由怀有恐惧心理的个体之避难所的集权性等级系统,能够通过理性化、标准化、规制化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台高效的绞肉机,它以建立与维护秩序为名试图清除它所判定的所有社会异类,而失去了任何道德意识的个体马上就可以堕落为这台杀人机器的帮凶。故鲍曼称“只有现代文明的理性确定的世界才使大屠杀成为可能”[20]。原本从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个体,如今既失去了自由又泯灭了道德,通过对等级系统的绝对依附又返回更为严酷的被束缚和被强制的状态。
第二个极端恰恰与此相反,它体现为在从未有过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条件下,作为个体的当事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从自尊过渡到自傲再到自我膨胀和无度的自私,最终倒向极端的个体主义。齐美尔指出:“文艺复兴对个体性的有意的、原则性的强调似乎是其成就,并且首先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即权力意志、成就意志、自尊与成名意志在人们那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得到了普及。”[21]在前现代性时代,个体的任务在于从自然的、文化的和共同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要打破和祛除的是对集体、上帝的神化与膜拜;而在现代性时代,具有着不可逆趋向的个体性进程既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幸福,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也可能意味着失控的激情、无度的欲望、极端的自私、对秩序与规则的蔑视,以及社会联系的松脱与团结意识的丧失。以前对共同体和上帝的神化现在转变成为对个体自身的崇拜,个体演进为一种世俗化世界中的宗教体验的对象,个体绝对神圣被视为新的教条。这样一种对个体独特性的过度强调,只能导致个体当事人的彻底孤立化、危险化以及社会整体的失控。所以格罗斯(Peter Gross)指出:“人们可以讲,现代的个体化的人也是奴仆,只是不同于拥有外在于自身的主人的前现代的人,他是把自己作为主人,现在又在从自然、文化和集体中解脱之后,要从自身中解脱出来。”[22]
3.团结的个体
其实,以为“个体化所蕴含着的个体从传统依附中的解脱,就仅仅意味着个体的绝对自由,可以摆脱所有的人际约束,从而滑入彻底的个体主义”这一看法,是对个体性之特质的一种误解。实际上个体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合理的旧的传统束缚的挣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产生出新的社会联系与人际关系制约的可能性。个体化不仅展现出个体间的差异,而且正是基于个体间的这种差异才会出现团结的必要性,因为所谓“团结就是尽管存在着差异的依存性”[23]。团结就是指在宗教、政治、工会的归属性上完全不同的人们,仍然可以互相依赖地共同追寻目标。所以说,个体性既呈现出自由,也展示出团结,因而是一种团结性的自由。如前所述,这是由于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个体意识崛起最根本的动因在于劳动分工以及社会功能的分化。劳动分工一方面导致了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新质量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依赖。个体在任何时空环境下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联系和文化关联而得到正常发展。随着劳动分工,个体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越大,其相互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个体的成就越是独特,这种成就相互补充与扩展的需求便越是迫切。一句话,个体越是自主,便越是依赖于社会,劳动分工导致社会成员更倾向于相互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作为独立与自由之实现的个体性,恰恰又确定了新的社会化。齐美尔指出:“如果个体性的发展,有关仅仅依靠个体意愿和感受来展现我们自我的核心这样一种信念被视为自由的话,那么自由在这一范畴之下便不是表现为一种纯粹关联的丧失性,而是恰恰表现为一种与他人的完全确定的关系。”[24]
这样看来,作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的个体性或个体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运行阶段,即“从传统的集体联系中解脱出来,并且反应性地、二次地对新的再结为集体过程的进入”[25]。恰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依赖,使得个体的行为考量的底盘里必然会有社会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构成了个体决断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新的社会整合造就了个体作为“一种想着自己也为他人而在的统一体”[26]的诞生,这就不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体,而是一种团结的或利他主义的个体。个体此时之所以具有了团结或利他主义的特性,是因为当事人出于自身的兴趣与利益考量而与他人组成了统一体。这是一种全新的自觉自愿组成的统一体,其内在的精神支撑呈现为一种契约。在现代性时代,随着社会功能分化的进程,契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人际关系的媒介,无数的契约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约束性的基础。而所有的人对契约的恪守便体现为一种契约道德:当事人出于自主意志,为了达到维护其自身整体及长远利益之最终目的,展现出团结与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称“道德起源于群体生活开始之处”[27]。总之,现代性催生出自由的个体,但自由仅仅意味着挣脱以前不合理的外在强加性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其在行动上永远可以无拘无束。因为无拘无束只能导致人性中恶的层面的无限放任与膨胀,使整个社会处于极度无序的危险状态。自由的个体要想持续生存且不因其自然本性中恶的一面对社会需求与秩序造成损害,就必须自觉进入道德约束,从而接受社会控制。个体需要受到社会的控制,人的本性上的缺陷需要借由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得到弥补,甚至自由个体之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保持其个体人的特征。“个体性并非通过脱离社会控制得以发展的,而恰恰是通过社会控制……”[28]“个体是这样一种存在,作为有意识的和个体性的个人,只有当他是社会成员时才是可能的,他嵌入社会性的体验与行为过程中,借此其行为受到社会的控制。”[29]而个体的人成为社会的人的过程,就是自由的个体转变为受控的个体和道德主体的过程,是从外在强制向理性的自我强制转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朗(Heywood Brown)指出:“不可能不道德,这一点把人与动物区分了开来。”[30]
file:///C:/Users/MS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
二、契约伦理的时代
如前所述,现代性呈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个体崛起的趋势,这一趋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提升了人之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为每一个人内在潜力的迸发和自主生命的展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它对于身心皆具有无法摆脱的脆弱性的每一位个体而言也意味着选择上的风险与挑战。每一个人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位理性、成熟的行为主体,就必须既要防止主动逃避自由、重新返回到服膺异在专制的束缚与强制状态,也要避免盲目的自我膨胀、滑入毫无底线的利已主义泥潭,通过对自身利益、他者利益及社会利益全盘、统一的研判与考量,自觉主动地与他人建构起一种对于自身福祉和社会秩序均有保障作用的契约道德,从而实现从一位自由的个体到道德的主体的文明状态的转变。这一转变既包含着必然性的逻辑,同时也蕴含着其现实性的基础。人因其道德能力不仅应当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也能够作出这种区分。人类之所以有能力构建道德规范并自觉予以遵守,要归功于其在婴儿时期通过父母之爱就已营造出来的最原始的道德基底。对于这种作为人类道德意识产生之基础的最原始的道德基底,约纳斯(Hans Jonas)、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以及鲍曼等伦理学家都有所论述。
1.原始信任的作用
这种所谓最原始的道德基底亦被称为“原始信任(das Urvertrauen)”,它是婴儿在与其父母的接触交往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对其随后一生的道德意识的奠基与发展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婴儿从一出生时起,就需受到其父母的关爱。这就完美地呈现出了一种从存在到应当的过渡逻辑。婴儿应当受到父母的关爱,原因就在于他存在着。约纳斯指出:“新生儿,其单纯的呼吸便对周遭明明白白地提出了一种应当,即你要照顾他。”[31]也就是说,“一种单纯本性上的在那儿之存在,在此内在地、清晰地也蕴含着一种对他人的应当”[32]。这种从婴儿的存在到父母对其关爱的过渡,或许与婴儿的外表所展现的价值的吸引力有关。然而正如法兰克福所言:“对于这种价值的感受并不是爱的塑造性或根基性的条件。”[33]“我们对孩子的爱既不取决于任何一种独特的特征或贡献和德性,我们爱他们是无条件的;我们的爱也无关乎其他的什么可解释的个人本身,因为他们在出生之前我们就爱上他们了。”[34]也就是说,孩子的价值并不构成我们爱他们的重要理由,情况或许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爱他们,他们对于我们才必然赢得价值。总之,“对于一个人的爱既不能归于此人的特征,也与任何一种其他理由无关,而是源于这种爱给父母所指定的意志的必然性”[35],亦即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之进化的必然性。法兰克福说:“因为孩子从字义上就是来自其父母的身体!他本身在出生后……尽管并非以同样有机体的方式,但很长时间都是其父母的一部分。”[36]因为孩子是父母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其自保和延续生命之需求的体现。于是,“对自己孩子的爱是自然地和生物学意义上地被铸进了意志结构之中的”[37]。
尽管如此,父母对婴儿无条件的关爱,却促成了后者“原始信任”的生成与塑造。正是原始信任为当事人未来的道德意识的建构和发展奠立了基础。在对父母为自己劳作忙碌、满足自己各种需求行为的观察中,在对自身的存在受到持续可靠的关爱与珍视的感受体验中,婴儿可以推导出一种“对人尊重”的倾向与态度,这就是所谓的原始信任。而尊重个体不仅是道德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所有道德价值得以塑造的最初基底。“原始信任构成了后续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价值予以概括和内在化的基础与前提。这或许类似于鲍曼称为‘道德冲动’的事物。作为‘对个体的尊重’之价值诞生的开端,原始信任的发展涉及了一种对人的发展的深刻的嵌入……”[38]。
如上,通过父母之爱,婴儿被植入了作为对个体的他人的顾及与尊重的原始信任,正是在家庭这一共同生活的温馨的情感联系中,在乡土文化所蕴含着的安全、信任与可依赖的历史关联中,婴儿获得了身心上的健康成长,实现了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然而,如果没有现代性所激发的个体化进程,封闭状态下的个体所拥有的对他人尊重的意识或许会仅仅局限在家庭或村落的范围,所谓“尊重个体”中的个体也仅仅是指家庭或族群中的成员。作为行为主体的当事人或许也会成为父母,从而使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在自己与自己孩子之间得以延续。这种爱具有无私性,是以自己孩子的福祉为目的的,自己甚至可以为孩子的需求作出任何牺牲。这里关涉一种非对等的、非交互性的爱的关系:当事人将自己孩子的利益、希冀与恐惧等同于自身的,甚至于“我是为他者而存在的,这并不取决于他者是否为我而存在”[39]。而且对于作为当事人的父母而言,借助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如法兰克福所说的,“表面上的无私与自利之间的矛盾便消失了。只要人们明白,无私存在于施爱者的自利之中。……他只有在爱中忘记了自己,才能满足他自己的需求”[40]。因此这样一种父母之爱令人感佩,也值得大获赞赏。约纳斯盛赞“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所有责任的永恒的原型”[41]。
但是,不论婴儿所表现的“尊重个体”的原始信任,还是成人父母对其子女的无限关爱,都是基于密切的血亲关系的,都是局限于家庭或村落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的,它们具有情感上的偏向性与排他性。这样一种自然道德“不取决于事先的认可,不可收回,不可取消,且是全球性的”[42],与那种人工建构的、由对益处的权衡所驱动的、对所有陌生人都不偏不倚的、体现相互合作之关系并且具有收回之可能性的规范性的契约道德完全不同。而随着现代性、个体化的进程,行为主体只要离开家庭和村落迈进社会,告别亲人与熟人转向陌生人,在伦理意识上便需要经历一种从血缘关系的自然道德到陌生人间的契约道德的质的跨越。也就是说,现代性所催生的人之个体,要想在崭新的社会环境中应对挑战并获得顺利的持存,就必须自觉自主地重构其行为规范,这就呈现出从一位自由的个体向道德的主体转变的必要性,同时作为道德基因的“尊重个体”的原始信任,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由人际血缘密切关系所产生的信任与由遵守稳定的规范所引发的信任感是大不相同的。因而在宏大广博的陌生人社会里,自由的个体恰恰并不天然就具备道德的态度、立场与行为能力,他要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不确定性中与他人一起共同设置和形塑行为规范并自觉地予以恪守,从而顺利、成功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图景。因此,从自由个体到道德主体的转变进程最终有赖于当事人本身坚忍不拔的奋斗与努力。在远离家庭与村落的陌生人社会里,“不道德似乎是人的自然状态,道德或许只是一种长期的艰辛奋斗的成果,并通过持续的外在强制得以保障。依据这种观点,同情、感同身受以及对他人的关爱是人为的、获得性的特征……以便以后能够用以调节人际关系”[43]。
2.契约道德的特征
在由自由的个体向道德的主体转变的过程中,自由个体所自主建构的道德就是契约道德,或者说契约道德的出现,便是自由个体实现向道德主体转变的重要标志。所谓契约道德或契约伦理,是指进入陌生人社会的自由的个体,为了维护和保障自身长远和整体的利益,自觉自愿约定并遵守的行为规范,例如不伤害、公正处事、关爱他人等,它们呈现出对所有的当事人权益的珍视以及对行为主体本身非理性的、极端自利的限制之意涵。契约道德具有以下几项重要的特征。
其一,契约道德体现了道德的自主性。如前所述,现代性以个体性或个体化为重要表征,个体性或个体化则体现为个体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从家庭和村落里走出并投身到陌生人社会的个体,是一位、同时也不得不是一位自主决定其行为性质与行为规则的主体,即道德(行为规则)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自主设定,取决于人际的相互契约。“使得某种社会秩序的观念得以表达的普遍有约束力的规则结构,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显然失去了意义。在其位置某种程度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共识。……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设置其秩序。这不仅适用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且也适用于宗教、政治和法律领域。”[44]在倡导个体之人才是道德价值、伦理规范的创建者方面,尼采当属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尼采以“上帝死了”这一名句,来宣告人是因不信上帝而把上帝杀死的。上帝之所以可以被杀死,恰恰证明了它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类自身的作品。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人类也就能够意识到自身创造性的潜能。杀死上帝导致了人对自身力量的意识,这便为创造新的价值开辟了道路。“通过对自身创造性潜能的认知,人们便有了重新确定其价值宇宙的可能性与必然性。”[45]虽然尼采认可人类自身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且认定衡量价值的标准在于考察其能否推动人类的更高发展,但在他看来,这种创造价值的主体并不是广大芸芸众生、平常之人,而是超常之人,且所谓“超人”仅仅是未来可能的人类类型的象征,相当于今天的我们之于祖先——猿猴的样子。在上帝已死、传统道德观念完全崩塌、一切价值堕入相对主义偶然性设置的境遇下,人们唯一的指望便是超人对新的价值与伦理规范的自觉创构。按照尼采的观点,超人不仅仅为自己负责,也为人类共同体和种族整体承担义务,超人要确定哪些价值具有适用性,从而规划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推动人类的持续进化。显然,尼采在反对对弱者的同情、反对民主对人群中的自然差等不加区分上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强权主义价值取向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且他的所谓“超人”也是其一厢情愿的虚构杜撰,但在强调现代性的新形势下,在自由的个体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创造主体问题上,尼采的阐释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历,使尼采看到了人们对忽然获得的自由的不适,以至于让他不大相信大多数人拥有享受自由的能力,所以尼采会把为人类自身创设行为规范的重任寄托在未来的所谓“超人”身上。尼采的这一立场,反映了我们的前人对“从自由的个体向道德的主体”之转变进程认知上的曲折与艰辛。的确,从传统既存的道德向全新的、塑造的道德,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观念改观与进化。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在于,个体迅速增强的自主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基础上自主形成的规范性的价值。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个体本身,恰恰是通过其对道德规范的自觉设置而转变成为现代性社会契约型的道德主体的。现代道德是人工性的,是由行为主体在博弈中以契约形式建构的,契约道德的内容、任务与目标均是人们自身选择的结果,在理论和逻辑上也包含着收回与撤销的可能性。一句话,现代的契约道德是以人的自由为前提与基础的,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人类自主确定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自由构成了道德的核心。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自主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而是说,任何行为之所以被称为道德行为,就在于它一定是来自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正如迪尔凯姆所言:“我们相信一种道德行为,只有当其出于完全的自由且是没有任何压力下作出的,才具有纯粹的道德性。”[46]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是道德的前提、起点与基础。反之,一切并非来自于自主,而是在强迫下作出的行为都不具备道德价值。这甚至还可以意味着,在现代性时代,自由、自主性不仅是个体的根本特征,而且其本身也被赋予了道德性。这样一种对自由的道德属性的认知,要归功于康德和费希特。正是他们把自我不仅视为认识世界的主体,而且也将绝对的自主性变成了一种道德价值。就此而言,个体化进程所导致的对自由与自主性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的体味、理解与把握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过程。
其二,契约道德体现了道德的理性价值。如上,所谓契约道德或契约伦理,是指自由自主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自觉自愿约定并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其对非理性的、极端自利的限制。所谓理性,是指与逐利避害的人性相适应。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人性、人道、人权等价值在社会主导观念中占据着日益突出的地位,甚至构成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重要标志。迪尔凯姆说:“在我们看来群体不再是通过自身而拥有一种价值,它不过是人之本性得以展开与实现的一种媒介,而人之本性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理想。”[47]所谓人之本性则告诉我们,身体与精神上的某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这样一种满足便为行动提供了理由。前面讲过,个体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自主性,在于自由选择。但选择作为一种真实行动不可能是为所欲为,而总是在某种可能性范围中的选择。人性就为这一可能性的范围划定了界限。由于理性是与人性相适应,因而理性就意味着维护人的自由与利益而不是与之相违逆。但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理性并不倡导当事人对所有直接、即刻的欲望和需求的满足,恰恰相反,理性要求其对这种直接欲望的满足保持距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当事人自身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而为了实现自身长远及整体利益这一目标,对自己的行为予以规范和限制,正是伦理道德的一种要求。就此而言,道德与理性是相通一致的,道德的人即是理性之人,理性者应当会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的要求。“通过对德性的获取我们便成为独立的实践的行为者,并因此而实现了我们的理性本性。”[48]现代性的社会应当是一种依照道德与理性合一的逻辑运行的社会,现代性的个体能够跳出丛林法则,通过契约建构共同的行为规范,借助重复的博弈和制裁机制识别与淘汰背信者,依靠缜密的权衡使自己的行为置于规则的约束性与合理性的掌控之下,基于既利己亦利他的契约社会的价值导引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迪尔凯姆所言:“自由地意欲并不意味着意欲某种荒谬的东西。相反地,它意味着意欲某种理性的东西。在对道德要求、这种要求所依赖的理由以及这种要求中的每一个所达到的作用获得了合宜的理解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将这些道德要求与对理由的充分考量和充分认知相适应。而这样一种得到认可的一致性便不再会有强制物在内了。”[49]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道德与理性的合一观对人的利益是持绝对认可态度的。它与康德的道德观对利益的立场完全不同。康德所讲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出于义务的行为,即履行道德规范的原因并不在于对当事人形象及其需求与利益之满足、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影响等所谓外在因素的考量,而在于义务观念之本身,在于当事人自主地想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在康德那里,不仅遵守道德法则是个体自主性的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道德法则是行为主体独立于任何感性经验、利益考量与外在影响而自主设置的,这就说明了道德法则的确定与意志自由的合而为一。总之,按照康德的立场,道德的遵守与道德的确定都仅仅取决于人的自主性,而不取决于任何对当事人需求与利益等所谓外在因素的考量。康德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极高水平的道德个体,但这一形象仅具有很强的理想性而未能表达对人性需求的基本关切。契约伦理所体现的道德与理性的合一观则克服了康德空洞虚幻的道德说教的弊端,它不仅不排斥对人的基本利益需求的关切,相反地,它所坚持主张的对短期、眼前极端自利的限制的目的,恰恰在于对当事人合法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有效维护。
其三,契约道德体现了道德的普适性。我们知道,契约道德是陌生人社会的行为主体为了维护自身长远和整体的利益而与其他行为主体约定的行为规范,这一签约行为呈现出此一行为主体与另一行为主体之间是对等和相互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契约所导致的对行为的约束和这种约束所带来的益处对双方也是对等和相互的。在陌生人社会,对等性和相互性是一切契约关系得以出现与存续的基础。反之,在无法发生对等回报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权力关系。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甚至认为,“人须是相互性的,相互性作为社会道德强制深藏于部落生活中的婚姻买卖与血亲复仇、伴侣之爱和市场关系。它对于所有的文化都是建构性的,是一种普适物”[50]。契约道德的这种对等性和相互性,不仅发生在此行为主体与彼行为主体之间,而且人际的契约建构模式是能普遍化的,可以推广涵盖到陌生人社会中所有的个体。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需求与利益,每一个人为了自身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维护就需要遵循契约道德的要求。因此,契约道德具有全包性和普适性。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升,契约道德的适用与保护范围已经超出了陌生人社会具有行为能力的人群局限,涵盖辐射到了人类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未来人类。
契约道德的普适性有康德式与齐美尔式两种检验方法。康德考察道德规范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方式,是看它们能否在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均得到普遍的认同。康德的思路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道德规范是规约人际交往行为的,因此道德的普适性要在人群中间去寻找。齐美尔和尼采则秉持所谓的个体原则,即只有个体才是原初义务的终极来源以及合法的、原始的道德义务或评价的出发点。鉴于此,考察道德规范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是要看它们在每一位个体身上能否得到一生的践行。正如齐美尔所言:“你能够乐意,你的这种行为对你的一生都起作用?”[51]可见,齐美尔等考察道德的普适性并不是人群空间上的普适性的维度,而是个体时间上的普适性的维度。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绝对的个体性道德责任的构想,同时也体现了其所强调的个体的绝对自由与本真性。
3.契约道德的保障与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
一般而言,在陌生人社会,“契约构成了人际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媒介”这一点导致了契约道德的普遍有效适用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与应当。然而,逻辑必然性与社会现实性并非总是吻合的。陌生人社会无法排除总是有一些人并不依照契约道德的运作逻辑行事。因此,理论上的应当要想成为稳定的现实,就有待于一种机制性的保障。这就是说,要把契约伦理的基本内容与观念取向通过法规制度确定下来,并借由对违规现象启动制裁机制予以有效维护。“契约之约束性,只有当对契约的信守超过了契约伙伴的范围,而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有约束力的规范得以机制化,并且嵌进社会的价值系统之中的时候,才会出现。”[52]这是我们在探讨契约道德的普适性时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一个维度。
契约道德普适有效性的最有力的保障便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建构。与宗教、教育、知识、观念等文化符号相比,法律是保护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不公,则很难会有道德适用的可能性。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法律使以下成为可能,即能够知道,人们带着哪些期待找到社会支撑,带着哪些而找不到。”[53]也就是说,法律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运用自由时的一种普遍的行为期待结构,通过确定哪些事情不该发生而使社会灌注稳定性。现代性社会不仅是一种个体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一种法制化的社会。现代法律的出现展示了人们从服膺旧的结构向塑造新的结构的转变进程。社会的个体化意味着等级性的简单结构——这种结构所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稳定性——的瓦解。而从旧的结构中解脱出来的个体并非不再需要秩序,恰恰相反,“个体化是从旧的约束中的解脱,同时也是朝向新产生的关联的重新结集”[54]。获得自由的个体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混乱,必然要走向新的建立社会约束与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人们便基于普遍共识自主地创设了以法律框架和基本制度之形态表现出来的新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人造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它通过对行为期待的提示和对违规实施制裁的警告而使人们的契约道德赢得切实的保障。法律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合理限制,意味着对行为的普遍规范,它凝聚了契约道德的全部精神。一旦个体作出的行为是合规的,则人们就无需再询问该行为的道德性,因为它必然是好的和对的。
然而,这样一种为了防止自由了的个体堕入自然状态而创制的以法律框架为呈现形式的、新的而且是人造的结构,遭到了以鲍曼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批评。强调极端多元主义是所谓后现代的特征,故对后现代主义概念本身的界定与解释也难免带有多元的色彩。但有一点则是确定的,即后现代主义者坚决反对沉淀在上述新的人造的社会结构中的引领性的价值导向、共同的理想目标以及建构社会秩序的任何尝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社会建制本身都包含着一种对个体人性及道德自觉性的压制性的因素,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像纳粹时代那样的种族屠杀的残酷后果。故后现代主义要用规范个体主义来取代规范整体主义,禁止任何超个体性的引领性导向的存在。他们认为,那些主导着社会建制的少数精英尽管自称是民众利益的代理者,却掩盖了其压制个体人性的惊人现实。而“后现代意味着对这些代理者的拆卸、分解和松懈,这些代理者在现代性中被赋予了启发个体与整体的人朝向其理想状态进发的任务”[55]。
由于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任何建构社会秩序的普遍措施都被证明是一种压制个体性的因素,故他们自然坚决拒斥任何超个体的规约,在此基础上主张一种极端的道德个体主义。按照他们的观点,道德实际上是一种由个体依照人性自行决定的东西,“任何一种道德关系毫无例外都要通过个体,通过一种内在的、无条件的对责任的倡导得以实现”[56]。鲍曼认为,个体生来就具有某种道德基底,即所谓“道德冲动”,该道德冲动作为人内心中的善好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个体履行道德责任的能力都可归结为行为主体的这种潜在的素质储备。“道德作为冲动总是已先验地存在于个体之中的。”[57]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个体主义。鲍曼进一步指出,道德是一种个体体验,而不是普遍适用的法则规范,对道德行为的论证只能由个体作出。像尼采那样,鲍曼强调道德的个体,而不是如康德那样将个体束缚在可普遍化的行为准则上。因为社会的普遍性的行为规则只能导致对个体自主性与本真性的压制,对个体道德冲动的摧毁,以及个体的非道德化所带来的对道德责任的消解。
问题在于,既然不再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导向,不再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既然“在一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后现代世界里,理想状态下任何生活方式原则上都是允许的,或者说得更好,绝没有会让某种生活方式受到阻止的普遍原则明确地存在”[58],既然道德仅仅属于个人的私事、“后现代的道德里不具备真理、尺度与理想”[59],那么,如何从由无数自由且道德的个体所造成的复杂的偶然性状态中,塑造出社会的一种稳定的秩序呢?这个问题鲍曼显然是回答不了的,因为“就鲍曼而言,唯一合法的秩序是一种自我驱动的、出于道德之方面的、事实存在的、偶然产生的‘秩序’”[60]。在鲍曼看来,整个社会只能是陷入无政府主义,故“后现代生活是一种充满恐惧的生活”[61]。但这也是为了避免现代性残暴的潜能的生发,而在对现代社会寻求秩序建构的努力予以反抗时唯一的另类选项。可见,鲍曼的后现代主义蕴含着的理论困境使得他自己也被逼到现实的死胡同里去了。
以鲍曼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竭力反对具有现代性色彩的社会规制与人造结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在他们看来,过强的社会规约与价值导向会压制人性,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纳粹式种族灭绝的人道灾难。二是他们强调,普遍的行为规范会消解个体本真的道德自觉性,而道德归根结底属于个人的私事,因此应倡导一种极端的道德个体主义,把道德的着眼点放在个体的自行选择上。
关于第一个理由,后现代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以防止获得自由的个体堕入自然状态而形塑的法律规制及其他人造的社会结构,本意是维护人性的本质欲求,捍卫人的自由、自主的根本利益,体现契约道德的全部精神的,但在某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的制度框架的核心价值理念会遭到恶意的篡改,从而导致法律规制摧毁人性、造成人道灾难的后果。为了避免这类惨剧的再次发生,《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便呈现为一种全球性的道德契约的确立,它指导着国际社会在确立本国的宪法时须将人权、人道的理念作为终极的价值基石固化下来。如联邦德国在拟定其宪法(《基本法》)时,就在第79条第3款有意识地将“人之尊严不可侵犯,所有国家暴力受基本权利的制约以及共和国、民主、法治国家、社会国家、联邦国家的国家制度”等作为不可更改的内容予以确定。这些措施均有效地使人权价值、契约道德的精神以法规的形式得到机制性的固定与呈现。
关于第二个理由,后现代主义者重视个体自身的道德自觉性也无可厚非。的确,对于公共生活和私人幸福而言,人的道德素质问题是无法忽视的。最强调人的素质的伦理学派就是德性论了。在德性论看来,道德行为并非来自当事人对行为的得失后果的偶然权衡,或者来自一种自我抗争与克服后的胜利的结果,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该行为的道德质量就存疑了。实际上,道德行为是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此存在本身就已确定了该行为应当是怎样的。这个所谓人的现实的存在,就是其德性。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通过认知和意志而获得的态度”[62],体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可靠而稳定的品格。这样看来,道德行为并非偶然发生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不过是早已开始了的某个过程的一种延续,是人的道德本性的表达,或是一种从该本性中产生出的东西的现实化及圆满呈现。“应当并不是毫无关联地从外部通过一种异在的主管来强迫当事人予以认可,而是其理由已经存在于人的自然既定的实现之意志本身中了。”[63]总之,按照德性论的观点,道德行为不是偶然作出的,而是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素质,取决于其立场态度、情感体验、性格特征等复杂要素的有机组合。
由此可见,德性论基于当事人的素质储备为其行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走向预期。这一判断对于观察人的近亲关系当然是完全适用的。我们无法想象心智正常的父母会对自己的子女作出不利的事情;在当事人作出认可的决定之时,便已经站在认可的立场上了。但这样一种行为预期无法简单扩大化,推广到陌生人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在宏大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要求当事人作出一次合规的行动并不困难。但要求其行为每次都是基于其合规的品格素质而非出于对后果的得失考量,难度就太大了。德性对于当事人好生活的塑造当然是建构性的,但就人的一生而言,其品格素质往往并不是非常确定的。德性作为一种内在规范与社会外在的行为规范相比,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这种不稳定性。故可以说,德性是一种可期许但无法确切指望和统一要求的事物。因而近代以来的伦理学便往往体现为一种有关行动与放弃、允许与阻止、要求与禁令的行为规范的学说,它重视行为本身的好坏善恶,而不认为对行为者素质的考量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它相信人的行为性质可以规范,但人的素质的高低难以一致。
近代伦理学之所以有别于古代德性论而强调人的行为规范,这与现代性时代整个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的历史背景相关,与随着个体化的进程行为主体自由选择能力的极大增强相关,与自由原则强势进入近代伦理学的语境相关。后现代主义者鲍曼仅仅看到人所具有的本真的道德自觉性的一面,却看不到人也有恶的潜能,殊不知这种潜能相当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当事人素质的塑造。施密特-比格曼(Wilhelm Schmidt.Biggemann)指出:“恶是自由的代价。”[64]因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人所蕴含着的恶的冲动也就有可能暴露出来。这也与不断增长的个体化的趋势密切相关。“谁要是作恶,就是要成为一种唯一者、不可混淆者,一种极端的个体主义者。”[65]一旦人之恶性被释放出来,其恶劣程度显然可以远高于动物。“没有一种动物会真的进行一场故意的谋杀。它不会完全有意地、知道其行为后果地追捕其他动物,以便致其于死地,不论针对同类还是异类。这也是,就如其他那样,人的一种特性。……人不仅在紧急防御时或无意地杀人(过失杀人、打人致死),或者基于某种族群或某一部落严格的规范来杀人(杀婴),他也经常是有意识的、故意的杀人,他不仅有计划地消灭异类的生物,且首先是针对同类的个体——这才是真正的恶。”[66]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认知也十分深刻。康德虽然是以个体为其思考的出发点的,且认可人内心所具有的善良意志,但他同时也将个体坚决地置于超越个体的普遍规范的约束之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虽有道德之潜能,但这种自然的禀赋必须得到规训。康德在《论教育》中指出:“本性不受规则所束,便是恶的原因。人身上仅存有善的种子而已。……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67]否则的话,人内心中野性的恶欲也会勃然而发。“人从本性上讲在道德上是善的还是恶的?两者都不是。因为从本性上讲人并非道德生物。人只有当其理性上升为义务和法则的概念,才能成为道德生物。”[68]
因此,从个体发展本身的角度来看,“人需要超个体的道德规则,因为否则的话其本性会无保护地,也就是‘恶性地’得以展现”[69]。如果当事人完全听任本能欲望,毫无顾忌地谋求私利,其恶行总有一天会伤害其自身。迪尔凯姆说得好:“正如我们的肉身有机体要靠从外部获得的食物摄取营养那样,我们的精神有机体也要从社会提供的理念、感觉和实践获得养料。”[70]普适性的道德规范对于每一个人心智的健康成长都是必需的,因为“道德规则的整体实际上构成了围绕每个人的一道防护墙,能够防范人的激情波的冲击与继续发展”[71]。当然,在由外在的普遍规范的规约及训导的滋养之下,如果当事人不仅能够通过对规范的认同与恪守为自己的行为划定一条防范恶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而且还能够自觉地将这种普遍规范体现的契约伦理的价值内化为自身的一种恒定素质,亦即将规范融进当事人完整的人格结构之中,从而从一位被规范制度框住的行为主体转变成为一位有认知与反思能力的自觉的主体,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每一种行为都受限于来自社会结构的两个因素:一是内在的价值与信仰观念,这种观念依据对不同生活圈子的各种参与而浓缩为一种个体性的行为气质;二是社会行为秩序的调节程度。”[72]从陌生人社会中个体之间行为比较的角度来看,单个人的道德修炼再好,也无法带动和保障其他人具有同等的品格素质。若一个孤独的好人所遭遇到的都是坏人,则其出于道德考量的举动不仅无法持续,而且也失去了意义。一种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就起到了使陌生人社会中所有成员的行为达到一种道德要求的作用。这样的行为规范并不可能体现为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很高的要求只不过是遥不可及的道德目标),它只能是基于人性之需划分一种最低限度的禁止恶行的行为边界,这些以禁令形式(如不伤害他人,禁止杀人、偷窃、失约等)呈现出来的行为规范反映出社会最根本的道德共识,具有广谱的超个体的性质。而只有超个体的对每个人均有规约作用的普遍行为规范的存在,一种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秩序,这种秩序才能真正维持稳定,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安定才能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file:///C:/Users/MS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gif
结 语
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给所有的当事人创造了空前的自由选择的机遇。一方面,由于个体化彰显了自由的价值,并且它与自私自利的绝对个体主义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同时自由构成了人的尊严、人拥有其人之价值以及人类享受幸福与繁荣的先决条件,故个体化状态天然便具备一种道德制高点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化的过程并非作为当事人的个体自己选择的结果,因而个体化趋势本身也就含有一种强制性的意味,它迫使个体作为个体来行动。“用萨特之言便是,人被判定为个体化。”[73]卢曼也讲:“成为个体这一点,变成了义务。”[74]
与此同时,我们要破除一种极易产生的误解,即个体化进程必将导致社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恰恰相反,个体化并非意味着与团结无缘,而是将会孕育与催生出一种超越过往的新质的团结。传统社会严格说来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为了整体的幸存它常常需要保持一种整体对个体的压倒性的强制态势,共同体中所有的成员被灌注着统一的宗教信念与情感纽带,并借由对共同价值的认知与恪守而服膺整体的意志。“部落和封建社会是单质化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简单,是一种氏族化的、等级化的统一体,特征是同等者的‘机械性的团结’。”[7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性时代开启了个体化的进程,以往建立在血亲家族及村落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在民众中大大消减,“共同的理念仅在非常抽象的层面得到分享”[76],但这并不意味着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体就完全失去了与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关联。要想在陌生人社会中安身立命,自由的个体就必须在劳动市场中找到新的集体,在国家共同体中发现身份认同,同时为了逐利而与他人合作,为了避害而建构契约规则(该规则还要固化为普遍有效的社会建制),通过对劳动集体及社会建制之权威的自觉服膺而赢得自我选择的归属性和一种与集体及社会相生相伴的关联感,如此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机械团结的新质的有机团结也就孕育而生了。“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使一个稳定的秩序得以机制化,在这一秩序中个体采取了一种集体团结的基点并且能够为自己益处的极大化设置界限。”[77]
自由行为、自我决定者,同时也是一位自觉确立其道德规范者。通过这种自我确定,行为主体也就授予了自我权威,完成了自我肯定,达到了自我实现。确定了道德规范的自由者,意味着他真正具备了现代人应有的素质:一方面,依照人性需求,行事时着眼于维护长远和整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善于理性作为,乐于采用他人甚至是所有人的视角,顾及行为的社会关联以及对他人利益的波及与影响,如罗尔斯那样,不满足于一种纯粹的意志自由,而是将自由与正义联系在一起。这样,现代性语境下的成熟的理性个体也就通过自立规则和自守规则,证成了将自由与道德统一于一身的逻辑必然性。
来源: 哲学动态杂志
编辑:王奕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0-11 17:26
【案例】
《纯粹实践理性的诸原理》思路整理
纯粹实践理性分为要素论和方法论,要素论中又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在分析论中讨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诸原理,它包含有意志的一个普通规定的命题,而这个“普通规定”可作为多个实践的原则的根据在实践的诸原理中, 作为条件被主体认为仅对其意志有效(主观必然性)的原理称为“主观准则”,对每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称为客观原理(实践法则)。
关于实践法则,需要提到纯粹理性自身,纯粹理性为其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奠定基础,在运用中必须假定能作为规定意志的根据的实践法则,否则其后用就了能限制于准则上。
自然律,即在自然认识中凡发生的事情的原则,可确定作为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性,在自然律的刺激中,可从规定意志的根据中发现诸准则与其认识的实践法则的冲突,理性的运用在自然律那里是理论上的,理性的运用通过客体的性状进行规定,与之相对比的,是通过意志规定的,理性在实践上的运用。
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与主体和欲求能力相关,主体和欲求能力之间也是相关的,即主体的意志同时包含理性和欲求能力,它们决定了主体为自己所制定的原理,其中理性产生实践规则,对主体而言,它是先天规定的。
命令,即行动的客观必要性,它既考虑结果及其充分性、有理性存在着的原因性、作为起作用的原因的原因性,也考虑规定意志,意志并不考虑结果,这是一个定言命令,即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客观的。当命令本身是有条件时,意志需要考虑欲求的结果,这就只是一个假言命令,即把一个可能行为由实践必然性看作是人之所愿望的,至少是可能愿望的另一目的的手段这就不能作为实践法则,而只能作为实践规范,其缺点在于,把意态完全归于欲求能力,最终问题陷于,欲求对象是什么。
自己本身,即主体,是理性立法的前提, 它不将理性存在着区别开,同时给予实践法则客观必然性,这是同时考虑理性和欲求能力的结果,同时实践法则也是考虑理性和欲求能力的前提条件。
欲求能力的一个客体预设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实践原则,欲求能力即被欲求有现实性的对象,这个对象的欲望的原则先行于实践规则,并且这个对家的欲望的原则是成为该对象的原则的条件。
欲求能力通过其客体的表象来实践地规定任意,同时,欲求能力通过客体的表象与主体的关系来使该客体成为现实 ,这种关系对这种对象的现实性感到的愉快,必将被预设为规定放任意的可能性条件。
愉快,即生命与对象、行为其中的主观条件,它被建立在主体的感受性上,因此无法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都以同样的方式效.欲求能力建立于愉快之上,与欲求能力客体的表象有关系的主体通过被欲求有现实性的对象中的“现实性”和“对象”来实践地规定欲求能力。
普遍原则包括"自爱”与“自身幸福”,是一切质料的实践原则,幸福即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于不断伴随着他的整个存有的那种生命快意的意识,在对像的现实性范围内,它作为规定任意的最高根据。 因为是在对象的现实性范围内,所以自身幸福和自爱都属于“普遍原则”,普遍原则在低级欲求能力中建立意志的规定根据。
愉快结合着的诸表象的感受性程度是区别高级欲求能力和低级欲求能力的标准,其感受性 程度的高低也是意志的诸规定根据的唯一差距。
意志的规定根据与表象方式无关,即不考虑知性表象还是感官表象,因此纯粹理性有能力不预设任何一种情感而规定意志,即理性作为实践法则,可以独立地规定意志,它通过实践规则的形式规定意志,但并不存在规定意志的单纯形式的意志法则,它承认高级的欲求能力,即受控制的快乐,由于这个法则并不存在,更能证明愉快的诸表象的感受性程度才是区别高级与低级欲求能力的原因。
欲求能力作为理性存在者获得幸福的规定根据,其有限本性涉及欲求能力的质料,它规定满足欲求能力所需要的,而规定根据(不包含有意志的同一个根据)的根本问题在于,将幸福建立于什么之上?这个问题取决于主观上必要的法则,对规定根据而言,它作为一种实践原则,在不同的主体中必定是不同的,因此幸福的欲望并不取决于合法则的形式,而取决于合法则性的质料,即在遵守法则的前提下,是否快乐、快乐的程度,主体可以经验性地认识这规定根据。
幸福,作为一种诸主观规定根据的普遍称谓,是客体与欲求能力之间实践关系的基础。理论性的(表述原因与某个结果关联的)自爱的原则,包含意图找到手段的普遍规则。
基于理论性原则的实践规则,由于欲求能力的规定根据只关乎感受性的程度,因此这些实践见则并不是普遍的,它是欲求能力的规定根据与客体有关的一种主观可能,它具有主观必然性与单纯经验性。
欲求能力的规定根据通过爱好强加于主体,得到行动上的客观必然性,因为是“行动”,所以并不包含规定意志的成分。单纯主观的原则通过行动上的客观必然性可以上升至具有完全客观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可以被理性先天地认识,也因为任意的主观条件是实践法则的基础,同时也包含于单纯主观的原则中。这也是上升的原因。
当理性存在者的准则是按照形式(把意志的每个对象都排除掉)包含有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原则时,它可以思考为实践的普遍法则,该原则只剩下一个普遍立法的单纯形式,理性存在者可假定其准则的单纯形式适合于这个普遍立法的单纯形式,其准则的单纯形式也成为实践法则。
实践原则的质料, 即意志的对象,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在自然律的前提下,当意志的对象是意志的规定根据时,意志的规则服从于一个经验性的条件,这个条件与进行规定的对象和愉快情感之间的关系有关。
自然律中,规定意志的根据发现诸准则与其认识的实践法则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是,自然律的一致性与"一条法则的普遍性赋予一个准则”的极端对立,这最终导致这个准则本身与它的意图严重冲突并完全毁灭,原因是意志不具有同一个客体,对知性的对象而言,偶然中做出的必然事件不能被确定地包括进一个普遍的规则中去,经验性的规定根据不宜于用作普遍的外部立法,理性存在者准则的单纯形式可用来区别准则中的形式是否适合于普遍立法,即判断这条原则作为法则是否会自我毁灭,普遍立法是实践法则的基础,意志服从于实践法则,意志适合于实践法则的规定根据不能是某种主观准则,比如爱好,爱好的基础不同,因此不受法则统辖。
当仅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是一个意志的充分的规定根据时,意志的形状只能借此来被规定,自由意志从立法的形式中寻找规定根据,立法的形式包含于准测,准则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
在自然律的事件中,被思考为独立于自然律的(自由的)意志的规定根据必须是现象。
自由与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互相归结,从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中可以认识到无条件的实践之事。自由是无法直接被意识到的,因为道德律(现象的规律)独立于感性条件的规定根据,这种规定根据引向消极自由的最初概念,因为它不能从道德律中被推出。理性通过给予道德律必然性(对一切经验条件的剥离)来表现道德律。
纯粹意志的概念源于纯粹的实践法则。纯粹知性的意识源于纯粹的理论原理。实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使思辨理性陷入窘境,具体表现为现象在自由概念中无法解释,而在自然律中可以得到解释,总结起来就是,在实践中现象在思辨理性范畴内无法得到解释。
纯粹理性上升至原因系列的无条件者,其中的二律背反在自由概念方面和自由律方面都不可理解。其在自然律方面适用于解释现象;在自由概概念方面~可以以实践理性和德性法则为前提做某事,其原因是,意识到应当做某事。
意识到应当做某事作为做某事的原因即这个过程是一种预设,包含于纯粹几何学的些实践命题的公设中,这些公设涉及到“存有”的概念。其中的实践命题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实践原则,即无条件的先天表象为定言的实践命题,它通过法则的单纯形式规定意志,这个法则的单纯形式就是一切准则的最高条件。
从属于意志的某种或然条件之下的实践原则作为法则,可单就意志各准则的形式来先天规定意志的规则,同时也可以作为诸原理的主观形式之用,即借助一般法则的规定形式的根据来得到理性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强加于主体,因此它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来证明其原始立法。
实践的纯粹理性提供了主体德性法则。理性将意志的准则保持在先天实践的纯粹意志上,这个过程作为一种德性原则,不顾意志的主观差异,成为最高规定根据的普遍形式。这个德性法则是一种针对一切理性存在者而言的法则,理性存在者包括最高理智的无限存在者,他们具有一种通过规则的表象来规定自己原因性的能力,即有能力根据原理,从而也根据先天的实践原则来行动。
但理性存在者无法预设可以提出与道德律完全相吻合的意志,即神圣的意志,道德律作为一种命令,对理性存在者以定言的方式提出要求。
命令具有以责任为名的从属性,它强调理性和客观法则对行动的强制,由于任意,它本身就带有主观愿望,这主观愿望来源于主观原因,与客观规定根据相对立,而理性可以去解决这个对立。
一切有限的有理性存在者有权去做的唯一的事逼近原型,意志的神圣性则确保了逼近过程中的德行,意志的神圣性就可以用作原型的实践概念。但由于无法确定这个德行的无可置疑的的确定性,这德行作为自然获得的能力永远不能完成。
带有主观的愿望与实践法则的可能性条件相联结,形成了他律,他律与符合义务的道德律的唯一原则——意志自律相反,他律意味着对法则的质料没有独立性,这与德性是相反的,因此他律是与责任的原则意志的德性相对的,德性通过单纯普遍立法形式来规定任意,任意超过一切实践上有限制作用的法则。
独立性意味着消极理解的自由,这与纯粹且本身实践的理性的自己立法是相反的,它表示纯粹意志的自由,是一般法则的可能性的形式条件。
他律遵从自然规律的依赖性, 因此意志遵守病理学上的规范,不给自己提供法则,这与德性的意向相对立。
自由的自律本身就是一种单纯普遍立法形式, 在自律的条件下,一切准则通过它们的形式条件与最高的实践法则相一致。实践法则基于主观条件,主观条件具有与自身幸福相关的有条件的普遍性。
欲求能力对某个事物的实存的依赖性是意愿的基础,实存需要在经验性的条件中去寻求。
排除经验性的存在者的幸福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客体。幸福作为一种准则的规定根据来使主体预设在部分理性存在者的福利那里发现快乐与需要。准则的质料作为准则用于法则的条件,但把准则的质料加到意志上去的根据限制了准则的质料。
限制产生了责任,主体将质料赋予客体这个质料同时包含了主体和客体的质料,最终成为客观的实践法则。同样的限制出现在理性和立于爱好之上的准则之间,理性作为准则提供法则的客观有效性的条件;立于爱好立上的准测作为准则获得法则的普遍性的条件,法则的普遍性则是立于爱好的准则与纯粹实践理性相适合的条件。
自身幸福的原则直接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这与德性法则是相互矛盾的,这个矛盾是逻辑的、实践的,因此理性使这个矛盾更加明显、更加必要。立法原则的后果的联系有关,正义应当破坏“该当受罚”的概念。
在道德感官里,德行与快乐和满足联系在一起,这需要先估量义务,道德律在主体眼中提供的直接价值:罪恶与不安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这个前提是,主体意识到合乎义务的行动就感到快活,德性法则要先于“感到快活”的概念,但“感到快活”无法引申至德行与法则。
但道德感官只是以自身幸福作为法则而造成的错觉,道德律直接天规定人类意志(因为自由),在长期的练习中在主观上形成了道德感官中的德行和罪恶。因为快乐与满足、不安和痛苦,这些都是道德感的情感,它们属于义务,但无法引申出义务,因为需要设想对于法则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感官”不成立。
在德性原则中实践的质料中,客观内部的是完善,从实践含义上看,它表示一物对各种各样目的的适应性和充分性。完善与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的联系与目的有关,因为目的包含规定根据可能的一部分。
客观外部的是上帝意志,作为物的性状的完善,是被表现在实体中的最高完善,因为它包含存在者对所有一般目的的充分性,但当意志的客体不再依赖于上帝意志时,幸福论原则会充当意志的动因。
对德性原则中实践的质料分析的结果就是,除了客践理性的作为意志自律的至上原理,德性的一切迄今的质料上的原理:德性原则在其余的一切原理中提出的原则都是质料上的,正如德性原则中实践的质料,这些原然则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质料上的原则。但这些质料上的原则完全不适用作至上的德性法则。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只有实践理性的作为意志自律的至上原理适用于德性法则。 准则凭借普遍立法的单纯形式构成意志最好的直接规定根据,纯样理性的形式的实践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在规定意志时用作定言命令,这是德性原则的唯一可能原则,毕竟一切质料上的原理并不可能与德性法则相关。
理性存在者一方面要服从因果性,另一方面作为自在的存在若意识到自己在事物的某种理智秩序中得到规定的存有,即在感官世界中规定自己的因果性,意志自由给予我们这种规定自己的意识,而纯粹理性的形式的实践原则可以独立地 、不依赖于一切经验性的东西规定意志,同时凭借理性可以规定行动中德性原理中的自律,从中得到意志自由。
纯粹感性直观(空间和时间)通过感官世界的分析论与纯粹思辨理性批判的分析论的对比可能使感官对象的先天知识成为最初的材料。
从单纯概念而来的综合原理在本身是感性的直观的关系(可能经验的对象的关系)其中才能发生,简而言之,“直观”加“知 性概念”等于“经验性的知识”,经验性的知识无法在“本体”的范畴中得到并思考,但思辨理性可以思考本体。
思辨理性使得消极自由有了意义,消极自由,即假定与那纯粹理论理性的那些原理及各种限制完全相容的自由,也就是可以使纯粹理论理性成为客观法则,同时沒有提供确定的和扩展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使纯粹理论理性的原理得到知识。与这些确定的和扩展性的东西同样的, 道德律提供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既提供对某个纯粹知性世界的指示,也提供了对这个世界作出积极的规定,同时也认识了关于道德律的法则,这个法则使感官世界作为感性的自然获得某种知性世界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超感性的自然的形式,超感性的自然, 即通过主体的意志按照纯粹实践法则才可能的自然,这种自然并不影响感官世界的实存,因为最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就是法则之上物的实存。通过思辨理性与道德律的对比可知,思辨理性并不能给于对象知识,而道德律可以。
理性存在者的感性,就是他们在以经验为条件的那些规律之下的实存(他律),与之相对比的是纯粹理性的自律的法则之上的实存(物的存有依赖于知识)。一个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然,即原型的自然,可以作为纯粹知性世界的基本法则,实存于感官世界而不影响它,感官世界可以称为复本的自然,即摹本的世界,它包含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可能结果和纯粹知性世界的理念的可能结果,原型的自然可以在理性中被认识。
在道德律把主体所置于的自然中:足够多的给予对象实存的能力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至善。这整个过程作为一种形式被赋于一个理性存在者整体的感官世界。
在现实的自然中,一个经验对象只能是他律,因此无法建立按照法则与自然相适合的准则;一个非经验对象可以自律,一切准则都将服从于这个对象。
在意志所服从的那个自然的规律中, 客体必须是规定意志的那些表象的原因,这个课题属于纯粹思辨理性批判,其中客体以主观的方式被给予,这种实践原理使给予对象的和被给予但永远不能被完全给予对象的经验相关,这个方式只容许经验范围内的知识。
服从一个意志的自然的法则中,意志应当是客体的原因,这个课题属于实践理性批判,它涉及理性如何规定意志的准则, 意志是客体的原因,意志的原因性在纯粹理性能力中有自己的规定根据。
可以先天认识客体的纯粹理性直接是意志的规定根据,这个根据是对象本身实有的根据,借此根据,理性具有理性存在者中 的原因性。
超感性自然的概态不需要直观,因为根本不存在超感性的直观,可以作为自由意志实现超感性的自然的根据。其概念与思辨理性所涉及的经验无关,只与意愿在超感性自然中的规定根据有关,这与作为自由意志的意愿的准则的规定根据同义,意愿客体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此,具体表现为,理性的理论原则作为客体的实现的评判根据。
现象,作为经验的对象,这些经验都必须与实践理性原理法则相适合,现象按照实践理性原理法则的标准被纳入诸范畴中,进而被认识。
在意志对于纯粹理性来说是合法则的前提下,意志在实行中的能力按照可能的自然的立法准则产生相应的自然,同时可以作为纯粹理性是否和如何能够实践的评判标准。这两种行为都从纯粹实践法则及其现实性开始,纯粹实践法则将自由的概念作为服从意志的自然的法则的基础,这些法则只有在与意志自由相关时才是可能的。
理性的理论运用中,经验假定了基本的力量和能力,人类的洞见范畴便止于此。纯辉实践理性与经验无关,因为道德律可以先天意识到它与演绎、理论、思辨、经验性的理性无关,但必然确定一个纯粹理性的事实。道德得实际上就是出于自由的原因性的一条法则,因而是一个超感性自然的可能性法则,同样的道理,感官世界中的形而上学法则是纯粹知性世界的基本法则,因此是感性自然的因果性 法则,因而道德律规定思辨哲学中具有消极性原因的原则。
思辨理性使某种玄妙莫测的能力的演绎的原则取代了与道德健有关的演绎,并假定了自由的能力的可能能性。但道德律通过证明自由的能力针对对自己有约束的存在者是现实的来证明自由的能力的可能性。
思辨理性批判在假定道德律可能性的原因性之上, 加上了规定意志的理性的概念(通过意志准则的某种普遍合法则形式),这个过程就是从理性超验的运用到内在的运用,即通过理念而本身就是在经验领域中起作用的原因。
当感官世界整体上拥有具有完全由自身规定自身的原因性的无条件者时,即自由的绝对自发性时,感官世界就可以规定存在者的因果性:这实质上就是把自由行动的原因这个观念应用在感官世界的某个存在者身上,存在者作为本体时,存在者的一切行动都是现象并且是有条件的;存在者作为知性存在者时,自由行动的原因性是身体上无条件的。有条件与无条件者都与自然必然性的机械作用有关,后者使自由成为理性的调节性原则。无条件的原因是道德律,虽然无法扩展思辨理性的洞见范畴,但可以替代“无条件者"这样一个无法实在化的观念,这样可以使思辨理性调和其中的矛盾,保障悬拟的自由,即给予它客观性和实在性。
实践理性无法探究也可以不顾本体的原因是如何可能的,与道德律和思辨理性相比,可以在实践的意图上运用这个原因概念本身,但无法扩展原因性概念的运用范围。
实践理性将作为感性存在者的人类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建立于纯粹理性中,同时认识意志在感官世界中的行动的原因性,进而现实地产生行为,这关乎实践理性作为本体的原因性的概念,它通过道德律获得本体原因性的所指,即其法则的理念,这既具有原因性,也可作为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本体的原因性的根念理论上是一个可应用于对象的纯粹的、先天被给予的知性概念,无论是感性被给予还是非感性被给予。
道德原则上建立起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的原因法则超过感官世界的一切条件,同时思考作为属于某个理知世界的东西而可规定的意志,该意志的主体是一个纯粹知性世界的东西,它可以借助某种根本不可能归于感官世界的任何自然规则中的法则来归定意志的原因性,进而将知识护展到感官世界之外:这整个过程被纯粹理性的实践证明为无意义, 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纯粹理性的反驳。
原因的概念包含对不同东西就其为“不同的"而言的实存作联结的必然性 ,联结在知觉中被给予的条件是联结先天地被认识,这就是联结的必然性。但这种条件是将主观必然性偷换成了客观必然性,因为原因的概念在事物的实存中并不存在,因此对纯粹理性的反驳并不成立。
经验主义的原则根据想象力的规则期望平时相似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具有必然性,称它有必然性的原因是从结果上升到原因,这成了怀疑论的根据,而联结之必然性在内的原因概态是从事物的给予的规定中按照其实存而推论出一个后果,这前后是相矛盾的。
数学命题全都是综合的,比如说几何学就与因果概念有关,即由规定A过渡至规定B,几何学与事物的实存无关,但可以与诸事物在可能直观中的先天规定发生关系。规定B虽然与规定A不同,但必然联结,联结的概念与经验性的起源是相互矛盾的,休谟选择了“经验性的起源”而放弃了联结的必然性,而联结的必然性又是构成因果概念的关键,因此休谟只能用习惯代替因果概念,最终的结果就是,数学命题被认为是分析的,这就是陷入了原理中的经验主义,理性的一切科学的理论运用上的怀疑论便来源于此。
经验只与现象打交道,而与自在之物毫无联系,自在之物与设定作为原因的A和作为结果的B之间的联结的必然性相互矛盾,休漠认为,A、B可以在经验中作为现象以不是以理论知识为目的的必然的方式联结着,A、B在经验中成为对象并被我们所认识,这种经验对象的客观实在性证明了原因概念。
演绎,即将它的可能性依据没有经验来源的纯粹知性加以阐明,在因果性范畴内,可以将直观运用于对象,作为本体的对象之理论知识为目的的应用,因为本体的对象无法在没有直观的情况下从理论上产生知识、演绎在可能的经验对象方面铲除了经验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怀疑论,因为纯粹知性就是因果概念与一般客体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不包含任何不可能的知识。
因果概念能运用于自在之物本身,使这种情况对主体成为必然性的是实践上的意图。
思辨从有感性的有条件者到超感性的东西,完成关于根据方面的知识并为之划定边界,边界就是根据方面的知识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之间的鸿沟,用于抑制彻底的求知欲。
知性就是欲求能力的关系,纯粹知性通过某个法则的单纯表象是实践的就是纯粹意志,道德律通过一个事实给予了它客观实在性,先天的纯粹实践法则同样表明了客观实在性,与其相关的是不可避免的意志规定,纯粹意志包含带有自由的原因性概念,它不是按照自然规律所能规定的,同时不能有任何经验性的直观作为这纯粹自由意志的实在性的证明。
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的概念就是本体因的概念,它来自于纯粹知性的概念、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本身不局限于现相上,按照其客观实在性在一般对象上通过演绛而得到保证,由于该概念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该概念无法得到任何感性直观的支持,本体因因此只能作为一种实践的运用,而无法在理论上运用,关于实践上的运用,它可以将原因性概念与自由性概念结合起来。
因果性概念在实践中的客观实在性是因果概念的全部意义,与之相比,本体因由于通过实践关系中的意义被给予了道德律上的意义,即使本体因没有客观实在性,却仍是有可能的。当本体因实践的实在性引入纯粹知性概念在超感官领域的客观实在性后,就给道德律相结合的范畴以实在性,实在性对范畴与这些范畴的作用没有影响,这些范畴与理智的存在者相关,在这些存在者身上也只与理性对意志的关系相关,这个关系和超感官之物与实践必然性的关系有关:纯粹知性中概念设置超感官之物,超感官之物通过实践的必然性抑制了“彻底的求知欲”,这就是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一种思辨运用中它自身不可能的扩展的原因。
来源:费费 评论 实践理性批判
编辑:马皖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1-21 22:28
【案例】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Rational”与“Reasonable”含义及翻译辨析
当代西方分析路径的政治哲学以其推理的缜密和语言的精致而著称。然而,翻译的困难却为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这一派学说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本文试图梳理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rational”和“reasonable”,并澄清其在中文翻译中的混乱,以期让中国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rational”与“reasonable”在《正义论》中的不同含义
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学说中使用了“rational”和“reasonable”两个概念,并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罗尔斯最先在其论文《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1980)中阐述了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后来又在《政治自由主义》(1996)、《作为公平的正义》(2001)、《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以及《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等多部著作中重申两者的区别,并将这一区别提高到其正义理论的核心地位。
首先,罗尔斯在“rational person”、“rationaldecision”、“rational plan of life”、“mutually disinterested rationality”、“deliberative rationality”等术语中使用“rational”,并且将原初状态下的订约者构想为具有“mutually disinterested rationality”的。在这些用法中,“rational”指的是行为者能够有效地增进自己的利益,如罗尔斯所述:“狭义的rational所包含的意思——大体上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推进我们的利益。”[1]所谓“理性人”,他们或者是深谋远虑的(prudential),能够整合、规划自己的生活计划以促进自身利益,或者能找到实现自身目的的有效途径。[2]另一方面,罗尔斯在“reasonable constrains or restrictions”、“reasonable conditions”、“reasonableterms”、“the reasonableness ofthe principle”等术语中使用“reasonable”,其含义是:“乐于提出被所有人都视为公平的合作条款,或者当这些原则是由别人提出的时候,他们也乐于加以承认。”[3]从上述两个定义来看,“rational”与“reasonable”间的基本区别在于,“rational”只关乎自身利益的增进,而“reasonable”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一个要求“换位思考”,涉及人际(interpersonal)关系的概念。[4]
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将“rational”与“reasonable”之区分的起源归结于希伯利(Sibley, W.M)的一篇文章。[5]希柏利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论述了“rational”与“reasonable”之间的区别。首先,rational具备下述三方面的特征:1.在“目的”方面,rational指基于正确信息和仔细反思的、考虑到自身以及他人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自己最想达到的目的;2.在“手段”方面,rational指能够选取事实证明最为有效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3.在“意志”方面,rational指行为者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反思去行动,不受任何感情因素的影响。[6]希伯利认为,所谓rational必须具备上述三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根据这三方面的要求,希伯利还举出了rational的反面irrational的例子:追求自己认为的价值较低的目的;选择以不现实的手段达到目的;未能在实践中完成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等等。另一方面,希伯利认为reasonable意味着除了考虑自己的利益外,还会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from the other's point of view),并依据对别人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去行动。reasonableness要求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和客观性(objectivity),并被表达为公平(equity)。[7]
对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希伯利认为,无法仅仅从rational中推出reasonable。因为,对于一个rational的人来说,仅仅在其欲求reasonableness的时候,他才有理由be reasonable。所以,对于rational的人来说,reasonable是有条件的,而并非康德意义上的普遍的道德法则。reasonableness却不同,它从根本上预设了公平,预设了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其他人的利益和立场。Rational是一种理智的德性(intellectualvirtue),而reasonable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德性,它同时具有道德特性,仅从理智的德性中无法推导出reasonableness。这就像休谟的名言:“一个人如果宁愿毁灭全世界而不肯伤害自己的一个指头,那并不是违反理性。”[8]这样的人有可能是rational的,取决于其自身的目的;但绝不可能是reasonable的。
另外,希伯利还将rational和reasonable与康德对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区分联系起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区分了两种道德命令:普遍的道德命令和有条件的道德命令,并将前者称为定言命令,后者称为假言命令。康德论述到:“如果行为仅仅为了别的目的作为手段是善的,那么,命令式就是假言的。如果行为被表现为就自身而言善的,从而被表现为在一个就真实而言合乎理性的意志之中是必然的,被表现为该意志的原则,那么,命令式就是定言的。”[9]希伯利认为,rational所表达的含义取决于增进个人利益的具体目的,对应于假言命令;而reasonable则要求行为者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不依赖于个人的具体目的,对应于康德所说的定言命令。
罗尔斯继承了希伯利对rational与reasonable的区分,而且也将这一区分与康德对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区分联系起来。罗尔斯论述到:“rational自主(autonomous)属于作为建构行动者的原初各派;它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大体上类似于康德的假言命令的理念(或者新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rational理念);充分的自主归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他们以某种方式看待他们自己,并且认可和践行会被一致同意的首要正义原则。”[10]可见,在罗尔斯的阐释中,rational是较狭隘的,基于行为者对自身幸福的理解;而reasonable却带有普遍性的特征,与人们的“一致同意”相联系。与此同时,罗尔斯不仅将rational与reasonable的区分与康德道德律令联系起来,而且还将这一区分应用到原初状态的推导中去。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采用了契约式论证,对于原初状态的规定是“作为公平之正义”的理论精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rational”与“reasonable”两个概念在原初状态中的区别与联系直接决定着契约式论证的成败。在对原初状态的讨论中,罗尔斯采用了康德建构主义的路径,将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theory)与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通过一个“rational person”的选择而推导出正义的两原则。而且,罗尔斯认为如此推导出的正义两原则具有“reasonable”的特征。那么,罗尔斯必须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由“rational person”推导出来的原则会具有“reasonable”的特征呢?其秘密就在于通过“无知之幕”而对原初状态做出的一系列规定。
如罗尔斯所言:“我们把reasonableness看作是由对各派(作为rational 自主的构建行动者)的慎思施加的限制框架表达出来的。这些限制的代表是公共性条件,无知之幕、各派被相互对称地安置以及将基本结构规定为正义的首要主题。”[11]也就是说,在原初状态下rational的订约者想要增进自身的利益,但是,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之下,订约者实际上并不知道自身利益是什么。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善观念、以及任何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订约者无法通过对原则的选择而增进自身的利益。由此,rational person不得不在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订约各方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无知之幕”等相关设计,一个rational person能够提出增进各方利益的正义原则,这是一个能被订约各方所接受的公平的合作条件,而这样的原则是reasonable的。由此,通过对原初状态各种限制条件的规定,rational就成功地转变成了reasonable。订约者从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转变为同时为他人着想,并试图推进社会正义的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尔斯论述到:“实践理性的统一,是通过设定reasonableness框定rationality,并使rationality绝对地从属于reasonableness来体现的。……reasonableness与rationality在一个实践推理的体系里达致统一,在此体系里,确立了reasonableness对于rational的绝对优先权。”[12]
可以说,rational与reasonable分别是罗尔斯契约式论证的起点和终点。人们从rational出发,在原初状态的一系列规定之下而达到reasonable。因此,这两个概念对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了rational,亦即不从“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出发,那么论证就会失去可信的起点;而如果没有“reasonable”,论证又无法导出对社会制度之安排具有指导意义的正义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认为:“人们熟悉的正义原则就是reasonable原则的例子,而为人们熟悉的理性选择原则就是rational原则的例子。Reasonableness在原初状态中的体现方式导出了两个正义原则,这些原则通过‘作为公平的正义’构建出来,它作为reasonableness的内容,是为规导一个组织有序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制定的。”[13]
总之,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rational与reasonable两个概念既相互区别又互为预设。Rational与reasonable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例如:是否承认各方能接受的公平合作条件、是强调个人还是强调共同体、取决于个人的善观念还是同人们的正义感相联系、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等等。[14]从英文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区分,并理解其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的罗尔斯著作的中文文献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却极为混乱,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
二、“rational”与“reasonable”在中文文献中的翻译及其问题
据笔者统计,rational在罗尔斯的下述著作的中文翻译中被译成“理性的”,reasonable被翻译成“合理性的”:《正义论》、《正义论》(修订版)、《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在《罗尔斯论文全集》中rational被翻译成“理性的”,reasonable被翻译成“合情理性的”。由此可见,在罗尔斯著作的中文翻译中,对于rational和reasonable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而这正是将两个概念混淆的根源所在。在上述不同的翻译中,笔者倾向于将“rational”翻译成“理性的”,而将“reasonable”翻译成“合理的”或者“合情理的”。下面我将阐述如此翻译的三方面的理由。
首先,在中文中,“理性的”更符合罗尔斯所规定的rational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形容词的“理性”定义为: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与“感性”相对。[15]由此,当我们用“理性的”来形容一个人,指的是这个人能够用推理、判断等方式有效地推进自身的目的。这一含义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rational”的含义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将形容词的“合理”定义为:合乎道理或事理。[16]所以,如果用“合理的”来修饰一个人,指的是这个人“明事理”、“讲道理”,并非只想着自己而不顾他人。这一含义更接近reasonable。因此,从相关词汇的中文意思出发,应该将rational翻译为“理性的”,而将reasonable翻译为“合理的”,或者另外一些相近的概念,如:“合情理的”、“合情合理的”,等等。
第二,从与rational相关的一些重要西方哲学词汇的中文翻译来看,rational应该被翻译成“理性的”。例如rationalism在思想史上一直被翻译成“理性主义”,指的是与“经验主义”相对的认识论学说。该学说认为,运用理性或理智官能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而感觉经验并不能达到确定性。[17]另外,西方哲学中的rationality一词通常被翻译成“理性能力”,《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在定义rationality时,参考了休谟的论述,这与罗尔斯意义上的rationality是同源的。[18]如果将rational翻译成“合理的”,那么上述两个相关词汇的翻译也必须修改为“合理主义”和“合理能力”,而这将严重扰乱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
从其他相关学科的中文翻译来看,“rational”通常被译为“理性的”。rational一词不仅在哲学领域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相关学科,都频繁出现。我们可以参照哲学以外其他学科领域对“rational”的翻译考察这一问题。首先,rational一词在在经济学中占据了核心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模型中都必须有关于rational person的假设,指的是将经济生活中的人假设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对这一概念的翻译通常是“理性人”而不是“合理的人”。如果将rational person翻译为“合理的人”,那么将彻底颠覆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此同时,罗尔斯自己认为其所使用的rational这一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rational是一致的[19],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rational expectation通常被翻译成“理性预期”而不是“合理预期”。例如:史蒂文·M.谢弗林的著作《理性预期》(李振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二,Rational Choice Theory是当代学术界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的主题是考察人们在特定境况下,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如何计算出最佳选项。这门学科的重要翻译著作以及中国学者对这门学科的研究都将rational choice翻译成“理性选择”而非“合理选择”。例如:赵红梅主编《经济学基础——宏微观经济的理性选择》(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海蒂斯和道斯合著的《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基于上述各条理由,笔者认为,在对罗尔斯著作的翻译中应该延续思想史上的相关翻译,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翻译,同时和其他相关词汇的翻译保持一致,将rational翻译为“理性的”,而将reasonable翻译成“合理的”或者“合情理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许多翻译作品都将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倒过来呢?下面我将重点讨论这一问题。
三、造成翻译混淆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学界在最开始翻译罗尔斯的著作时会将rational和reasonable两个词的翻译倒过来呢?这或许与罗尔斯过于强调者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相关。
首先,在rational和reasonable的关系问题上,罗尔斯的观点与希伯利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如前所述,希伯利认为无法单纯从rational中推导出reasonable。然而,在罗尔斯看来,“rational”与“reasonable”虽然有根本性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预设的。罗尔斯论述到:“reasonableness预设着rationality,而rationality从属于reasonableness。Reasonableness界定了可为某些群体内所有人——这些人可被分离地识辩出来,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和能够运用两种道德能力——接受的公平合作条件。……rationality又从属于reasonableness,是因为reasonableness原则限制着可追求的终极目的。”[20]在罗尔斯看来,通过原初状态的恰当设计,rational可以转化为reasonable。而且,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的论述中经常使用“rational and reasonable”这一表述,认为人们通常同时具备rational和reasonable两种特征。
第二,罗尔斯自觉地认为自己的正义理论根源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且认为,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词合起来涵盖了康的哲学中的vernünftig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中文翻译通常是“理性的”。罗尔斯论述到:“康德使用vernünftig来表达一个厚实的观念,它涵盖了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reasonable和rational。”[21]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将“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特征,而且其道德哲学的所有推理都是以“理性存在者”为对象做出的。在中国学者对康德著作的翻译中,德语词汇vernünftig被翻译成“理性的”。而且,在所有包含vernünftig的相关概念中,vernünftig都被翻译成“理性的”。例如:“Vernunftwesen”、“Vernunftverbrauch”、“Vernunfterkenntnis”分别被翻译成:“理性存在者”、“理性的应用”、“理性认识”,等等。[22]
基于上述两个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rational和reasonable都可以翻译成“理性的”,因为是这两个概念共同组成了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vernünftig。这或许就是reasonable被翻译成“理性的”的原因。然而,这一结论下得过于匆忙。因为,在其后的论述中,罗尔斯明确地区分了英语和德语的不同表达。罗尔斯论述到:“在英语中,当某人说‘他们的提议,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下看来是rational,但这毕竟还不是reasonable’时,我们大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中所指的人正试图推动一项苛刻而不公平的交易,他们知道这一交易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能指望我们接受他们,除非他们知道他们处在强势的位置上。……Vernünftig在德文中具有同样的意思:它可以具有广义的reasonable所具有的意思,也具有狭义的rational所包含的意思——大体上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推进我们的利益。康德对Vernünftig的用法是有变化的,但当他去描述人之时,它涵盖了reasonable和rational两个意思。”从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并没有像罗尔斯那样对rational和reasonable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当他使用Vernünftig(中文翻译:理性的)一词时同时包含了rational和reasonable两种含义。大概在德语中,尤其是在康德哲学中,没有恰当的术语足以表达罗尔斯意义上rational和reasonable之间的细微区分。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将这两个概念混作一谈的理由。因为,对于中文表达来说,对应于rational的“理性的”与对应于reasonable的“合理的”是可以表达罗尔斯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的。
总之,中国学界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存在混乱,其原因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与希伯利强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不同,罗尔斯创造性地阐释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通过原初状态的恰当设置,rational可以转换成reasonable。而且,在行文中罗尔斯经常将这两个术语合起来使用,这是这两个术语的中文翻译产生混淆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康德道德哲学的紧密联系也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根据罗尔斯的阐释,在康德哲学中这两个概念原本就是一个概念。然而,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给出的三个理由,笔者认为在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相关著作的翻译中,没有必要独立于西方学术的其他学科而另辟蹊径,将这两个概念的中文翻译颠倒过来。这样只会引发许多不必要的学术纷争,使得政治哲学这门本来就精巧复杂的学科更难为中国学人所理解。
本文摘自《<正义论>讲义》,李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71页。
[2]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56页注释①。
[3]参见:[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该书将“reasonable”翻译成“理性的”。
[4]参见:LarryKrasnoff, "The Reasonable and the Rational”, The Cambridge Rawls Lexicon,edited by Jon Mandle and David A. Reidy, 2015, pp.692-7.
[5] Sibley, W.M., "The Rational Versus the Reasonabl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2, no.4, 1953, pp. 554-560.
[6] Sibley, W.M., "The Rational Versus the Reasonabl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2, no.4, 1953, pp. 556.
[7] Sibley, W.M., "The Rational Versus the Reasonabl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2, no.4, 1953, pp. 557.
[8]休谟:《人性论》,第3节“影响意志的各种动机”。
[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10]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48页。该译文将autonomous翻译为“自律”,笔者认为译为“自主”更为恰当,也与学术史上的其他翻译相一致。
[11]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58页。
[12]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60-361页。
[13]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58页。
[14]参见:刘敬鲁、叶源辉:《罗尔斯的the reasonable和the rational之区分的实质与中文翻译》,《世界哲学》,2018年第2期,第127-137页。
[15]《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36页。
[16]《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8页。
[17]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中英文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理性主义”词条。
[18]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中英文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理性能力”词条。
[19]参见引文:“rational自主(autonomous)属于作为建构行动者的原初各派;它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大体上类似于康德的假言命令的理念(或者新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rational理念)。”(《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48页。)
[20]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58页。
[21] [美约翰·罗尔斯,《罗尔斯论文全集》,陈肖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570页。
[22]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索引,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页。
来源: 她哲学
编辑:马皖雪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1-11-28 22:27
【案例】
重磅首发!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重思数字化时代中公共领域的转型|“矫正错误的媒介结构是宪法的要求”
导言
哈贝马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简称《转型》)。依托公共领域这一制度性基础,他进一步发展了交往行动理论与商谈民主理论。可以说,公共领域对于哈贝马斯关于民主制度和欧盟的构想具有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意义。公共领域虽然承载着规范性理想,但是它的历史演变从来都伴随着危机。《转型》就试图在政治、经济生产、家庭等一系列复杂的结构变动中刻画公共领域所面临的困难。而当前西方民主遭遇持续挑战,其公共领域也似乎日益撕裂。面对这些危机,人们自然会好奇,哈贝马斯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些新兴的现象以及它们对于自己的理论的冲击的。在2019年进行的访谈中采访者曾就此向哈贝马斯提问。哈贝马斯也承认自己对这些在公共领域中发生的新的改变感到困惑与不确定。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需要交给新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了。
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从这场讨论中退场。德国的学术杂志《利维坦》日前出版了一份题为《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特刊,其所集结的十余篇论文分别从商业化、全球化和数字化三个角度,讨论了在《转型》出版六十多年后,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新一轮转型。而在特刊的最后,哈贝马斯也写作了一篇题为《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的文章,来回应特刊中的一些观点,和自己由此的思考。这篇文章系统展现了哈贝马斯对于新型的公共领域的看法,但是它并非直接对于新型公共领域的研究,而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反思和对话。并且就如同标题提示的那样,虽然公共领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社会现象,但是哈贝马斯本人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讨论其对于维系民主共同体的意义。
这篇文章一共六个小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前三小节中哈贝马斯交代为何今天“民主理论”需要采取重构路径,并沿着这一路径呈现商谈民主国家的静态和动态结构,以及公共领域在其中的位置和功能;在后三小节中他具体处理在数字化和新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发生的新一轮结构转型以及其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我们对全文都做了概述。但是如果读者仅仅处于好奇想看看哈贝马斯是如何看待从推特到Netflix等一系列新现象的话,也可以跳过前半部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就像哈贝马斯在导言中澄清的那样,虽然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也可以被泛泛地用在舆论研究领域,但是在社会学领域它明确地意指那个在功能上与市民社会和政治系统区别开来的领域。
下面我们将对这篇文章逐小节进行一个尽量准确的概述:
第一节
哈贝马斯认为,在今日西方民主危机背景下,民主理论既不应采取纯经验性路径,也不应采取纯规范性的“建构”路径。前一路径仅仅描述民主舆论的形成机制,而不顾其规范性维度。后一路径以罗尔斯为代表,以“建构”出一套“理想理论”,即澄清正义政治秩序的诸原则为首要任务。哈贝马斯认为,在18世纪末期的两次宪法革命前,古典民主理论家可以无问题地采取后一路径,因为当时启蒙“理性道德”主张的基本权利或人权尚未在宪法中实定化,理论的使命是教育公众,呼唤现实。但在今天,人权的理念一方面制度化在宪法之中,另一方面也成为公民广泛共享和认可的基本理念。因而当前的理论的任务与18世纪时的不同就在于,要做的不是唤起人们对于人权的期望,而是基于这种已然实现的期望来重构出应然的政治秩序。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的稳定有两大“社会事实”作为其存在前提:第一,民主宪法的规范核心(如理性道德主张的基本权利)需内在于公民的政治意识,哪怕这些基本权利尚未充分实现;第二,公民信赖民主制度,相信人权理念能够通过平等投票、立法、司法、政府行动和决断修正等方面落实。今天的民主危机即这种信任的动摇。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政治精英在近几十年中没能满足人们受宪法保障的正当期待。在这一背景下,民主理论的使命是通过“理性重构”既定的民主实践,阐明(explizieren)参与政治生活的市民群众所暗含的(implizit)意识,并进而影响其规范性的自我理解,使实存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至于彻底破灭。因此,他转向对民主制度,尤其是公共领域商谈政治的重构。
第二节
现代多元社会中民主政治面临的整体问题是,不再有共同的宗教与世界观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因此,民主系统不得不通过作为法律制度的民主意志形成程序为民主统治提供合法性。从参与者视角出发,这一合法性以两个条件为前提:一为包容(Inklusion),即意志形成程序要求容纳所有具有同等权利的、与决策相关的参与者;二为商谈(Deliberation),即政治意志形成依赖于事先的、具有商谈性质的舆论。前者保障相关者的平等参与权,后者则尽可能筛选出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从合法性的这两个组成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政治公共领域对于基于代议制的商谈民主的意义。一方面,选举是唯一个容纳一切成年并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的制度,而舆论则直接影响了选民的选择;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并不能直接影响议会的具体立法,而只能为其提供多元的观点;舆论的质量并不直接决定立法的质量。政治公共领域虽然是民主系统流水线的重要一环,但也终究只是一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决断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汇入政治系统的、基于妥协的决断,后者又落实为政治结果。政治结果再一次被政治公共领域评价和批判,并影响下一次选举时的偏好,如此循环不止。
哈贝马斯强调,政治公共领域的商谈政治若能良好运作,需要“多”与“一”的统一。所谓“多”,指政治商谈中歧义纷飞、彼此争胜、相互批判的现象;所谓“一”,指相互批判的双方都以对共同宪法的认同为其展开商谈的基础。在“一”存在的前提下,歧义的“多”恰恰能通过改善信念和问题解决方法,使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提示作用最大化。然而,对宪法的共同忠诚的再生产,依赖于一种“经验”:选民能在政治系统输出的政府行动中证实政治公共领域商谈中的合理化力量。哈贝马斯认为今天的民主危机恰恰在于这一经验的阻断。赞成冲击或冲击美国国会者,恰恰是因为长年无法在政府行动中看到民主讨论结果得到“证实”。这一阻断的后果是,支撑起商谈政治的活跃市民社会逐渐萎靡,公民之再生产陷入困境。
在澄清了公共领域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之后哈贝马斯转向讨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共领域以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分离为前提。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同时关照到这种充满张力的双重身份。而公共领域的数字化,正如哈贝马斯接下来要详细阐述的那样,一方面没有改变造成这种身份张力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却模糊了公民对于这种张力的自觉认识。在社交媒体这样的半是私人半是公共的半吊子公共领域中,传统公共领域通过与私人领域自觉区分开来而艰难守住的包容性就消失了。在进入第4节和第5节详细论述新现象和新难题之前。哈贝马斯首先考察了活跃市民社会的三个边界条件,以为理解市民社会的新困境提供理解框架。
第三节
商谈政治的前提是活跃的市民社会。后者的存在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三大边界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可损害的。
第一,自由政治文化。自由政治文化的道德核心在于,市民彼此相互承认为彼此相伴的市民,具有同等权利的民主共同立法者。在多元社会中实现这种道德境地,首先需要做到“对陌生人的相互包容”,这种包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妥协,即不再将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伦理、语言等生活形式的“异类”视作是“敌人”(Feind)。相反,他们能够团结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之下,同时又保持这种陌生性。这种互惠关系既非利他主义,亦非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自私自利,相反,能够以共同福祉为导向进入到民主立法环节。这一文化的再生产不能依靠政治系统的动员完成,而只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和被制度化的政治教育范本代代相传完成,极其不易。
第二,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在宪政国家的基本权利秩序中有公私两组权利:一方面主观私人权利(和福利国家的要求)保障了市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主观-公共性的交往权和参与权则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主性。依据设计构想,两组权利能够功能互补:政治权利确保公民能参与民主立法,进而决定私人权利的分配,确保其作为市民的社会地位;而私人权利的兑现则保障市民有动机作为公民介入民主舆论和意志形成过程。但是这一互补的前提是,民主选举能切实有助修正突出的、具有结构性根源的社会不平等。但是今天的现实表明,这一前提可能不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可能发生。比如,底层民众发现选举出的政府迟迟不能改善生活条件,进而“放弃选举”;过去代表这一阶层的政党发现自己无法从中获取选票,故不再代表其利益。更坏的情况是,底层人民被重新动员为一种民粹力量败坏民主政治。
第三,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福利国家如何有效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三个条件。持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社会整合失效,这使国家调节成为必要。为了避免社会整合危机,哈贝马斯援引克劳斯•奥菲的说法,福利国家需要满足两个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为资本的增殖创造充分条件以创造税收,另一方面满足更广泛阶层的利益,保障其施展私人和公共自主的法律前提和物质前提。而国家的调控能力则是平衡两条律令的要求。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金融市场对国家的反向控制,使得问题愈发困难——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与非政治化,使得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受到了更多的内部挑战。这些问题在气候变化、新冠肺炎、难民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出现面前变得更加显著。因此,哈贝马斯在设想一种超越了单纯民族国家界限的、又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制度如何可能。
第四节
(下为哈贝马斯对新型公共领域的判断):在概要地重构了整个商谈民主的框架、边界条件以及公共领域在其中的位置之后,哈贝马斯将这一重构工作推进到公共领域内部的结构。从商谈政治的角度看,媒体系统对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意义在于产生相互竞争的公共意见。据此,哈贝马斯先给出了一个一般的评价公共领域对于商谈政治的意义的模型,它包括输入、输出和吞吐量三个环节:在输入环节上,公共意见的质量依赖于各个利益团体或者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对于议题的负责人的拣选,这保证的舆论的相关性;而从输出方面看,舆论的质量依赖于它能唤起大众的注意;而最关键是所谓的吞吐量,亦即大众媒体具有这样的功能,将所有的交往领域的噪声浓缩为与政治相关而有效的舆论。而在今天重新思考公共领域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数字化是怎样改变了这种引导大众交往的媒体系统的。至关重要的是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员,传统上,他们起到了舆论的守门员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位在新媒体上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新世纪开始的新一轮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首先可以在媒体使用的范围和类型上看到,但是这究竟最终如何影响了舆论质量(对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两个价值,理性与包容性)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哈贝马斯首先讨论新媒体的革命性特征。他认为新媒体不是简单的对于原有媒介的扩展,而是像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是传媒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跨越。传媒的发展具有打破边界的效果,对于其他领域来说这都是一种解放性的理论,但是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种去中心化对于需要定于一尊的政治而言却是背道而驰的。在其他领域中新媒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有些传统媒体,像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似乎在放到智能手机上以后也没什么不同;但是当电影被由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平台的时候,似乎带来了不同的作品美学。
那么这些影响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哈贝马斯在新时代的媒体中看到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为使用者提供了无限的联结的可能性,亦即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媒介,不如说是一个能够与任意受众沟通的“平台”:这种平台不再像传统媒体一样是内容的生产者,因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在公共领域中的交往模式因而也随之改变了,因为它使得所有的使用者都成为了潜在的独立自主平等的内容生产者。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都要经过规划和专业编辑的审核,但是新媒体对内容完全不加控制,仅仅是传播。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用户可以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像在白板上随意涂抹一样表达在这些新媒介提供的传播平台上。我们在传统媒体中能清晰地划分作者和受众,而新媒体则取消了二者的区别,为任意的两个人随时建立联系,使其可以相互交流。这看上去是无比平等的,但是在内容上却完全没有制约。平等与没有制约两个特征使得新媒体下的交往模式不可能兑现这些媒介的解放性潜能,相反,它使得交往碎片化,并形成一个个圈地自萌的小圈子。
回到对民主至关重要的两个价值上,即包容性和理性上。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具有解放性潜能,这在许多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内容上的平等也成为了极端右翼的温床。就像印刷术使得所有人都成为了潜在的读者,新媒体使得所有人成为了潜在的作者;但是,哈贝马斯反问,要过多久所有人才能真正学会阅读呢?传统的编辑模式使得公民在参政议政的时候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形成自己关于公共议题的判断。作者角色的存在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不足,但是这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作者角色只有经过学习才能形成。而正是这种角色的缺失使得去边界的公共舆论在政治中产生了碎片化:在某些议题上自发形成的没有边界不受引导的讨论具有一种离心力,使得一些教条化的交往回路不断强化和自我封闭;这种离心力抵消了传统公共领域的向心力。
第五节
第五节回顾了社交媒体在整个媒体服务中所占份额的发展。在对德国的相关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方面自新媒体兴起以来,虽然对于报纸的阅读大幅下降,但是电视和广播的收视/听率总体保持稳定,这些传统媒体在塑造政治议题上依然发挥重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Fake News大行其道表明人们对于传统媒体越来越不信任。这些数据反映了媒体供给和使用的变化,但是还不足以说明舆论的质量。哈贝马斯只能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猜测。第一,对纸质媒介的需求的下降反映了公众对于政治消息和议题的接受度在下降;这一点也通过原本政治导向的日报和晚报日渐娱乐化反映出来。但是,从他自己的经验来说似乎那些有全国范围影响力的大刊大报依然在引领政治议题上有重要作用,这特别是表现在这些纸媒为其他媒体,尤其是电视,输送了大量深思熟虑的文章和观点。另一方面,虽然其权威性还在,但是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伴随着对于政治阶层的怀疑与日俱增。哈贝马斯对此的判断是,供给侧的多样化和需求侧的多元化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批判性的、消除偏见的民意形成。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和复杂性驱使着媒介消费者中的少数派利用数字平台形成一个个屏蔽了不同意见的“回声室”。数字平台不仅仅能促成可以被主体间相互确认的自我世界,它也为竞争性公共领域的认知边界提供了偏执的交往孤岛。但是要分析这种现象,还需要回到经济层面——
第六节
在哈贝马斯看来,仅仅从技术层面来分析这些数字平台是不够的。这些互联网巨头同时是股票市场上的大公司,它们因而依然服从这资本增殖的律令,而其利润来自于对于数据的增殖:将其用作广告投放的目的,或者直接当成商品。当然传统媒体也接广告,在《转型》中哈贝马斯就曾以广告为切入点来讨论文化消费,但是新媒体的广告投放大量依赖个性化的算法,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将生活世界更进一步地商业化。但是更人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即这种新媒体的增殖逻辑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压力。因为传统媒体自己是广告的载体,但是它们的节目的成功与否却取决于受众,因而起决定作用的就不仅仅是资本增殖逻辑而是内容本身,从而取决于认知的、规范性和审美的尺度。这种内容上的认知尺度进一步可以在媒体在日益不透明的媒介社会中所发挥的导向功能上看到:传统媒体可以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起到中介作用,从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中剥离出可以被共享的和理性的解释内核。这并不是说出版业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终审判决,其功能在于,在庞大的信息流中,媒体能够持续对于日常生活中较为模糊的世界图景进行修正和补充、从而参与到对于我们共享的那种“正常性”的塑造上。而平台化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在于,它们无法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足够的发行量。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紧张而脆弱的工作关系(Arbeitsverhältnis)。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媒体,它们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Arbeitsweise),变为读者导向。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工作的专业化和政治化:它们从原先政治辩论的场所变为了创作和发行的协调中心。《转型》中就已经提到,文化消费可能会削弱公共领域的批判性,使其变为一种表演。这一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如今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媒体的任务从塑造公民的观点变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他认为,在一种注意力的经济学的裹挟下,媒体的娱乐化、情绪化和个人化的色彩都进一步加强了。其结果是去政治化。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供给一侧,现在考虑受众的改变。核心的问题是,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政治公共领域理解。Staab和Thiel的在特刊中的文章将这个问题与雷克维茨的独异性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新媒体为用户提供了自恋性的自我展示和独特性的表演的平台。我们要区分个体性与独异性。前者是在生活史中获得的不可混淆的人格,后者是一种公开可见性和区隔红利(Distinktionsgewinn)[布尔迪厄的概念,指通过制造区别赢得更多的符号资本。这种独异性通过自发进入到社交网络中来获得。意见领袖、大V们为了自己的节目和名声竞相吸引追随者的点赞,这或许就可以用“独异性的承诺”这个概念来刻画。对哈贝马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样自发而碎片化的公共领域中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解释和立场的不断自我和相互确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公共领域必然发生转型,并且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将重新调整,这必然对于那些新媒体用户的公民的自我认同带来深刻影响,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数据,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了。
回到对于社会领域的划分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区别于私人领域的独立领域依然是存在的,只是会遇到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被排斥的小众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的看法已经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因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的意义在减退。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代表性都在下降。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个假说,亦即这样一种虚拟的、没有审核的、匿名的虚拟公共空间也许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一种膨胀到了公共领域的原本属于私人书信交换的传播方式。在《转型》中哈贝马斯就注意到,随着家庭同生产过程的分离,家庭丧失了塑造个体的力量,原本基于私人书信的文学公共领域被半公共的商业化力量所侵蚀和扭曲,从而无法支撑公共性。同样的,在今天的公共领域中,作为作者的用户争相通过信息来博取关注,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只有在读者的评论和关注者的点赞中才存在。这种回声室一方面具有类似于经典公共领域的多孔的开放性,可以不断链接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根本不同于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因为它屏蔽了不同的声音,并将同质的声音吸收到自己的知识视界中来维系认同。而那种超出自己的视界的普遍性主张则被视为是虚伪的。从这种半公共性(Halböffentlichkeit)的角度看,宪政国家不再是竞争性观点得以澄清、普遍性利益考量得以实现的包容性空间。这种公共领域现在被下降为了半公共领域,其症状表现在Fake News传播的双重策略上,也表现在反对“说谎的媒体”的斗争上,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传统公共领域的不安[哈贝马斯没有具体说这种双重策略是什么,或指以特朗普为典型的人群,他们一方面指责反对者是Fake News,但是另一方面又传播自己所认可的。而正如我们在反新冠游行中所看到的那样,一旦政治空间成为竞争的公共领域的战场,那么由国家推行的民主政党的政治方案就会被以阴谋论来解释。这甚至会扭曲政治形式本身,就像在美国,当政党调整自身以适应一个天天发推来博取其民粹支持者的总统的自我认知之后,政治就连带着也陷入了公共领域的两极分化的漩涡之中了。
虽然我们可以将政治公共领域的失落追溯到资本主义民主的深层危机之中,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分析数字化的影响。哈贝马斯注意到硅谷的建立,亦即数字网络的商业化使用,是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方案在全球范围的铺开重合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借助数字网络无阻碍的流动,恰恰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理想市场的镜像。但是这种自由传播的过程会受到互联网巨头的算法的干扰,这解释了为什么欧盟试图依据竞争法(Wettbewerbsrecht)对这一信息市场进行监管。但是竞争法监管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即这些平台而非媒体对于信息的内容完全不负责任。我们不是在寻求对一个信息市场的监管,因为在其中流通的货物并不是纯粹的商品。这些信息首先应当被视为形塑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自我和集体认同的判断。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Fake News组成的真假难辨的世界中,那么他肯定会发展出显而易见的症候。所以矫正这种媒体结构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而是宪法上的要求,因为,从宪政国家的结构上看,这一结构是使得包容的公共领域和商谈性的舆论和公意得以可能的基础设施。
来源:现代性哲学+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dnGf3oVzSlGoTju6UFa6A
编辑:李佳怿
-
微信图片_20211128222351.jpg
(93.61 KB, 下载次数: 79)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2-15 21:41
【案例】
经典荐读 | 维特根斯坦:伦理学演讲
伦理学演讲
作者:维特根斯坦
译校:万俊人译孟庆时校
来源:哲学译丛,1987(04):23-27
在我开始正式谈论我的题目以前,让我先讲几句开场白。我感到我将很难把我的思想传达给你们,但我认为,一些困难可能由于我先提出来就算不得什么困难了。不用我说,第一个困难是,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因此我的表达常常不够精确不够巧妙,而这却是人们在谈论一个难题时应该能避免的。我只能要求你们尽量抓住我的意思,尽管我讲演中常会出现英语语法错误。我要说的第二个困难是,大概会同你们中许多人的期待相违,为此,我简单讲讲我选择这个题目的理由。当我荣幸地应你们前任秘书的要求给大家作个报告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一定要作,其次,如果我有机会和你们谈谈,我就谈论一些我渴望与你们交流的问题,而不会滥用这次演讲机会,谈论像逻辑这问题。我称为滥用,因为给你们解释一个科学问题,需要连续的讲演而不是一小时的报告。另一种选择是我可以讲讲所谓的大众科学,这种演讲打算让你们相信你们会理解一种你们实际上并不理解的东西,去满足我以为是现代人们最低的欲望之一,即对最新科学发现的肤浅的好奇心。但我不讲这些,决定给你们谈谈在我看来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题目,希望它会有助于说明你们对这个题目的想法,即使你们完全不同意我的意见。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困难是,听众难以认清演讲者所引导的道路和它导向的目标,这是很多冗长的哲学演讲常有的困难。这就是说,他或者认为:“他所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但他究竟用意何在?”或者他认为:“我明白他的用意,但他究竟怎样到达目的?”我只能再一次要求你们耐心,并希望你们最后既能认清道路,又能知道它导向何方。
现在我就开始演讲,正如你们所知,我的题目是伦理学,我将采用摩尔教授在他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对伦理学一词所作的解释。他说“伦理学是对什么是善的一般的研究。”现在我在稍微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伦理学包括我以为被人一般称为美学的最本质的部分。为了使你们尽量弄清楚我认为是伦理学主题的若干或多或少有些同义的表达,其中的每一种表达都可以替代上述定义,而且通过一一列举它们,我要像加尔顿那样,为了取得照相的人共同具有的典型特征而在同一照相底版上摄下若干不同面孔时,所获得的相同效果。为了给你们展示这张集体照片,使你们看清什么是典型的,比方说,中国人的面孔。所以,我希望你们通过我放在你们面前的这排同义词,能看到它们共同具有的特征,而这些便是伦理学的独特特征。现在我就说伦理学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研究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说伦理学是研究生活意义的;或者是研究什么使我们感到生活是值得的;或者研究生活的正确方式;而不说“伦理学是研究什么是善的。”我相信,如果你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片语,就会对伦理学关心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获得一种粗略的观念。
在这里首先我们发现,每一种表达实际上都是在两种非常不同意义上使用的。一方面,我把它们称为不重要的或相对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又称它们为伦理学的或绝对的意义。例如,如果我说这是一把好椅子,这意味着这把椅子对某一先定目的有用,在这里,“好”一词仅仅在这种目的预先确定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事实上在相对意义上,“好”这个词仅仅意味着符合一种先定的准则。因此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位好钢琴家,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能够灵巧熟练地演奏一定难度的音乐作品。同样如果我说,就我而言不要伤风感冒是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伤风感冒对我的生活会产生某种干扰。如果我说这是条正确的道路,我是相对于一定的目标而言的。用这种方式使用这些表达,并不会产生任何困难或深奥的问题。但是伦理学并不用这种表达方法。假设我能打网球,你们中有个人看着我打,并说“行啦,你打得够糟的。”假设我回答说“我知道我打得不行,但我并不想打得更好些”。那个人只好说“嘿,那就得了”。但是假设我对你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荒谬的谎言,他走近我说“你的行为像个牲口”,如果我说“我知道我的行为不好,但我并不想表现得更好。”那么他会这样说么:“哦,那就得了?”他肯定不会这么说,他会说:“哼!你应当要求行为举止更好些。”在这里,你们看到一种绝对的价值判断,而第一个例子却是一个相对的价值判断。很明显,这种区别的本质在于每一个相对的价值判断只是事实的陈述,因此可以不用带有任何价值判断迹象的形式加以表述,例如,“这是去格兰彻斯特的正确之路”这句话,我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想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格兰彻斯特,这便是你必定要走的正确之路”。“这个人是一位好赛跑者”这句话仅仅意味着他在一定时间内跑完一定的路程,如此等等。
现在我想争辩的是,尽管所有相对价值的判断可以用纯粹的事实判断表述,但并不是事实陈述都能够或者意味着是绝对价值的判断。让我解释一下:假设你们中有一个全能的人,他通晓世上所有死亡的或活着的肌体的运动,也通晓所有人类精神的一切状态;而且假设他在一部巨著中写下了他所知道的一切;那么,这本书就会包含对世界的整个描述;而我要说的是,这本书却不包含任何我们称之为伦理学的判断或在逻辑上意味着这种判断的东西。当然它包含所有相对的价值判断、真正的科学命题以及事实上能够得出的一切真实命题。但是可以说,所有被描述的事实都处于同一层次,所有的命题都同样处于同一层次。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一切命题都不是崇高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
现在你们有些人也许会同意这一点了,而且会想起哈姆雷特的话“没有或好或坏的东西,但思想却使它这样。”但这又会引起一个误会,哈姆雷特说的意思似乎是,虽然好与坏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的性质,却是我们精神状态的特点。但我的意思是,精神状态就它是我们能够描述的事实来说,在伦理学意义上并没有好坏之说。例如,在我们世界见闻录中,我们阅读了一起关于谋杀的详细描述(包括作案具体行动和心理活动),这些纯粹事实的描述并没有包含任何我们称之为伦理学的命题。谋杀和其他事实比如一块石头掉下来一样,完全处于同一层次。当然,看到这些描述会引起我们的痛苦、愤怒或其他情绪,或者我们会读到其他人在听到这种谋杀时所引起的痛苦或愤怒,但是这里仅仅只有事实!事实!事实!而没有伦理学。
现在我必须说,如果我沉思伦理学实为何物,假如有这种科学的话,我看这种结果相当明显。在我看来,显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或者说出这种东西应该是什么。我们无法写一本科学著作,它的主题能够是真正崇高而且超越所有其他主题之上的。我只能通过比喻来描述我的情感,即如果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本确实是关于伦理学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就会一下子爆炸毁灭世界上所有其他著作。我们所使用的词,正如我们在科学上使用的一样,是唯一能包含和传达意味与意义,即自然的意味和意义的容器。如果伦理学是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是超自然的,而我们的词却只表达事实;正如一个茶杯只能盛一杯水,即使我再倒上一加仑水,也只能盛一杯水。
我说过,在事实和命题的范围内,只有相对的价值和相对的善、正当,等等。在我继续谈下去之前,让我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阐明这一点。正确的路是引向一种武断的先定目的之途,我们大家都相当清楚,脱离这种先定目标而谈正确之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用“绝对的正确之路”这一表达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以为,这条路可能是一条每个人看见以后、由于逻辑的必然而不得不走的、或者因不走就感到惭愧的路。同样,如果绝对的善是一种可描述的事态,每个人就不会依赖个人的兴味和意向,必然地感到要实现这种事态,或因不促其实现而感到内疚。而我却要说这种事态是一种怪物。任何事态本身都没有我所谓的一种绝对判断的强制力量。
那么,是什么使得大家都像我一样,仍然诱使我们使用诸如“绝对的善”“绝对价值”等等之类的表达呢?我们头脑里在想什么?我们试图表达的又是什么?无论我什么时候试图弄清楚这一点,很自然,我就应该回忆这样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我肯定会使用这些表达,那时我与你们的心境一样,比如,当我给你们作一次关于快乐心理学演讲的时候,你们就会设法回忆起一些你们总是感到快乐的典型境遇。请把握住这种种境遇,因此我对你们所谈的一切就会变得具体,就是说,是可以控制的。人们通常也许会举他们在晴朗的夏日散步时的感觉为例。现在如果我集中我的思想在我所意味的绝对的或伦理学的价值事物上面,我就处于这种境遇之中了。而且在我这种情况下,总有一种特殊的经验的观念出现,因此,从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观念是我的典型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话中把这种经验当作我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例子的缘故。我前面说过,这完全是个人兴趣的事,别人可能会发现其他更突出的例子。为了能使你们回忆起相同的或类似的经验,我愿意描述一下这种经验,以便我们能有一个共同研究的基础。我相信,当我有这种经验时,描述它的最佳方式就是我对世界的存在惊讶不已。我倾向于使用“一切存在多么非凡”,或“世界的存在多么非凡”等等语句。我愿马上提及我知道的另一种经验,你们中的其他人可能熟悉人们可以把这种经验称为绝对安全感经验。我的意思是指这样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倾向于说“我是安全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伤害我。”
现在,让我考虑一下这种经验,我相信,为它们展示出的正是我们试图弄清楚的特点。我首先要谈的是,我表达这些经验的词是无意义的,假如我说“我对世界的存在惊讶不已”,我就是在滥用语言。让我对此作点解释:说我对事物的某种情况感到惊讶,这句话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和清晰的意义;我们都明白它的意思是说,我看到这么大个儿的狗感到惊讶,它比我以前见过的都大,或者对任何事物,就这个词的普通意义说,非常特别,而感到惊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对事物的某种情况感到惊讶,因为我能够设想不是这种情况的事物。我惊讶于狗的个儿大,因为我设想到了另一种个儿的狗,即想到了狗的一般的个儿,我不应该对这种个儿感到惊讶。说“我对如此这般的事物的情况感到惊讶”,这只有在我能够想象它不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此意义上,当一个人看见一座长期没有光顾过、同时又想象它早已被拆毁的房子时,他会对这座房的存在感到惊讶不已。但是说我对世界的存在惊讶不已则是荒唐的,因为我不能想象它不存在。当然,我可以对我周围存在着的世界感到惊讶。比如,当我仰视蔚蓝的天空时,就有过这种经验,我会对这种与乌云翻滚的天空形成反差的蓝天感到惊讶。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对不论什么样的天空都感到惊讶。人们可能会说,我是对一种同义反复感到惊讶,就是说,对蓝色的或不是蓝色的天空感到惊讶。但是,说一个人正对一同义反复感到惊讶恰恰荒谬绝伦。这同样也适合于我已经提及的另一种经验,即绝对安全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意味着什么。当我不会被一辆公共汽车轧过时,我在我的屋子里就是安全的。如果我患过百日咳因此不可能再次患这种病的时候,我是安全的。安全基本上意味着,某些事情从自然律上说对我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说不论发生什么我都是安全的,这十分荒唐。这也是滥用“安全”一词;正如在其他例子中滥用“存在”或“惊讶”各词一样。
现在我要求你们铭记,一些特有的滥用语言的做法渗透到所有伦理学和宗教的表达之中。这些表达乍看起来确乎是明喻。因此,当我们在伦理学意义上使用正当这个词的时候,尽管我们的意思不是指不重要意义上的正确,但是有些相似;同样,当我们说“这是个好人”的时候,尽管好一词在这里与“这是个好足球运动员”里的好一词意味不同,但看起来有某种相似性。当我们说“这个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我们的意思与我们谈到某些有价值的珠宝是不同的,但看起来有某种类似。现在所有的宗教词语在这种意义上似乎都被使用为明喻或寓言式的了。因为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时候,他看到一切;当我们跪下向他祈祷的时候,我们的所有词语和行动似乎是一种伟大而精心制作的寓言的一部分,这种寓言把上帝当作一个力大无边的人,我们力图去赢得他的恩惠,如此等等。但是这种寓言也描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经验。我相信,因为这些经验中的第一种经验恰恰是人们在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什么东西;而绝对安全的经验则是我们通过说在上帝的庇荫下我们感到安全这种方法来描述的。同样第三种同类的经验即我们感到负疚的经验,也是通过说上帝不赞同我们的行为而描述的。因此我们似乎总是在伦理学的和宗教的语言中使用明喻。但是,一种明喻必须是某种东西的明喻。如果我能用一个明喻来描述一种事实,我必须也能够放弃这一明喻,不用它来描述这一事实。现在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当我们试图放弃这种明喻,径直陈述它背后的事实时,我们发现并无这种事实。所以最初似乎是一种明喻,现在看来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
以上我对你们提及的三种经验(我还可以列举其他例子),在那些有过这些经验的人,比如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绝对的价值。但当我说它们是经验的时候,的确它们就是事实;它们是已经在当时当地发生并继续在一定的有限时间内存在,因而是可以描述的。所以从我几分钟以前所谈的事例中,我必须承认,说它们具有绝对的价值,这是胡说八道。我愿意通过说“一种经验、一种事实似乎应该具有超自然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的”,来使我的观点更为尖锐。现在我打算用一种方法来对付这一自相矛盾。
首先,让我再来考虑一下我们对世界的存在感到惊讶的第一个经验,让我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中称为奇迹的东西,很明显,它不过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像它那样的事件。现在假设这种事件发生了,以此为例:你们中有一个人突然长出了一个狮子头,并开始吼叫,这肯定是我想象不到的一件非凡奇特的事情。现在无论我们何时从我们的惊异中镇静下来,我就要提议去请医生,对它进行科学研究,而假如不是怕伤害他,我还会拿他解剖一番,看这种奇迹会发展得怎样?因为很清楚,当我们这样观察它的时候,一切奇迹都消失了;奇迹这个语词的意思除了仅仅是一种尚未为科学所解释的事实,还意味着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在科学体系中把这种事实与其他事实归类起来。这表明,“科学已经证明没有奇迹”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是真理:观察事实的科学方法并不是把事实当作奇迹来观察的方法。因为不论你想象什么事实,事实本身并不是奇迹(在这个词语的绝对意义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一直是在一种相对的和一种绝对的意义上使用“奇迹”这个词。现在我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描述对世界的存在感到惊讶的经验,即把世界视为一种奇迹的经验。现在我打算说,在语言中对世界存在的奇迹的正确表达是语言本身的存在,尽管它在语言中并不是任何命题。但是在某些时间而非在其他时间内意识到这种奇迹又意味着什么?因为就我曾说这一点而言,即,通过把奇迹的表达从一种依靠语言的表达转移到依靠语言的存在的表达上来,我所谈到的也还是我们不能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而且我们对绝对的奇迹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现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你们许多人看来可能完全清楚了。你们会说,唉呀,如果某些经验不断地引诱我们把我们所谓的绝对的或伦理学的价值与重要性的特质归诸于它们,这纯粹表明,我们不是借着这些语词而胡说,毕竟我们说一种经验具有绝对的价值,其意思就是一种象其他事实一样的事实。以上所说的一切意味着:我们对通过我们的伦理学的与宗教的表达所意味的东西仍然没有成功地找到正确的逻辑分析。现在当这种异议出现时,我便立刻清楚地看到,仿佛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我能想到的一切描述都不能描述我所谓的绝对价值,而且我反对任何人从一开始就根据其重大意义而建议的一切意味深长的描述。
这就是说我现在明白了,这些荒谬的表达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表达,但它们的荒谬性却正是它们的本质。因为我对它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去超越这个世界,即超越意味深长的语言之外。我整个的倾向和我相信所有试图撰写或谈论伦理学或宗教的人的倾向,都碰到了语言的边界,这种在我们囚笼的墙壁上碰撞是完全地、绝对地没有希望。就伦理学渊源于想谈论某种关于生活之终极意义、绝对善、绝对价值的欲望来看,它不能成为科学。伦理学谈论的在任何意义上都对我们的知识无所补益。但它是人类思想中一种倾向的纪实,对此,我个人不得不对它深表敬重,而且,说什么我也不会对它妄加奚落。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2-16 23:04
【案例】
前沿转载 | 万俊人:理性认识科技伦理学的三个维度
科技伦理学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及其蕴含的道德伦理问题的哲学反思,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基于公共理性论证的科技价值选择(科技之善或科技“向善”之可能)原则与科技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确切地说,科技伦理学包括科学伦理学与特殊专业化的技术伦理学两个方面,但由于现代技术与科学越来越难以明确分而观之论之(如计算机科学技术、纳米技术、生命〔物〕医学等),因而科技伦理学已然成为学界较为公认的学科概念。事实上,科技伦理伴随人类科技文明始终,古已有之,如斯尤盛。正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崛起与日益强大的功能展示,使得科技伦理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迅速崛起,并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应用伦理学的主体与前沿,不仅在实质内容和技术方法上,而且在几乎所有方面或层面,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因之也是现代应用伦理学研究中最为紧迫的主题。当然,科技伦理研究本身首先且最为根本的反思焦点在于,现代科技能否且如何“技顺乎道”“技进乎道”,进而“技达乎道”。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或“第一驱动力”,那么,科技伦理就是这个第一驱动力不可缺少的导航器,是人类科技实践能够始终沿着正确价值导向行稳致远的润滑剂和意义源。
科技伦理的“风险”与“难题”
科技伦理之所以凸显为当代最紧迫最重要的应用伦理学课题,首先在于现代科技活动本身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不仅直接关乎一般应用伦理学问题,而且关乎人类自身文明的价值导向和某些难以确定的社会风险,其复杂性和风险度都远超以往任何时候的科技伦理。德裔美籍伦理学者汉斯·约纳斯在1982年发表的《为什么技术是伦理学的课题:五个理由》一文,被学界公认为现代技术伦理的先声。在该文中,约纳斯提出现代科技之所以需要纳入伦理学研究的五个理由,即:技术之实际后果的矛盾性;技术应用的强制运行;技术实践在全球范围展开的时空影响;现代技术对人类中心论的突破;技术所产生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堆积”。约纳斯的“五个理由”其一是指现代科技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应具有正负两面性且相互冲突;其二是指现代技术运用因资本、市场和超高利润等因素的强力驱动而带来的强制性实施,以及这种实施所可能或实际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三是指现代科技应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合理监控困难或客观风险;其四是指人类对现代尖端技术及其成果(如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可能超出人类自身可控能力的担忧;其五是指现代技术及其应用中所蕴含或可能关联的价值评价问题,这些问题超出技术本身的范畴,需要哲学伦理学提供必要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持。
显而易见,约纳斯提出的“五个理由”都是科技伦理学自我证成的“正当理由”,但未必已然充分。最为复杂而紧要的理由是,一些现代科技的快速应用与扩展形成了许多不可预期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比如,“基因编辑”和“克隆技术”的人类自我应用显然会改变作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人类自身的本性或本质,形成非自然的“人工人”,由此带来的直接风险和挑战是: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的法律、道德、伦理甚或生命身份陷入困境甚至有可能被解构。还有,大数据和网络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如何有效解决诸如“私人信息泄露”或“个人隐私权”“数据集权控制”等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可能或者实际已经造成了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生活的某些不可预期且难以控制的风险。除此之外,科技应用还存在因其被资本市场化而带来新的社会道德伦理问题,譬如:强化社会不公正效应、科学技术人自身的职业道德操守、知识产权保护与被政治化且违背科学原则本身的技术“隔离”和“技术封锁”等,也都是现代科技伦理学必须面对并及时回应的道德伦理新问题,更不用说核能技术的两用(民用与军用)、无人机、核武器、太空武器一类的军事化科技所隐含的更为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了。
总之,现代科技的爆发式增长和无所不及的爆发式扩张,以及某些超级先进技术无所不用其极的实施运用(技术运用军事化作为其极端案例),都给现代人类社会提出了空前紧迫而严峻的挑战,而且我们还必须牢记一点:所有这些新问题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现代人类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这些空前的道德伦理新问题,它们既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建构现代科技伦理学的充分正当理由。
科技伦理的“底线”与“高度”
面对不断涌现的科技伦理新问题新挑战,不仅有许多伦理学研究者,而且有许多科学技术专家甚至是科技公司的从业者,都不约而同地给予积极响应,提出各种应对主张甚或科技伦理方案,其中,较为集中的应对主张大都聚焦于如何尽快明确现代科技伦理的“底线”,或曰,如何建构某种普遍有效的科技底线伦理。笔者认同这一主张,但以为建构“底线”仅仅是科技伦理学的基础性工作,不足以成就一套基本完备而合理有效的现代科技伦理学理论,遑论建立一套完备且充分有效的科技伦理实用指南了。
笔者无意奢求科技伦理学的完整理论,也不想——事实上也不可能——奢求建立一整套完备有效且一劳永逸的科技伦理规范系统,尽管这两者都是现代科技伦理学所寻求达成的理想目标。作为一门日益凸显且开放多变的跨学科、跨实践领域的新型综合性研究,科技伦理学首先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确乎是确立科技伦理的“底线”或者科技实践的行为界限。但问题是:科技伦理之“底线”的确立需要首先确立其理论基础和论理方法,否则,所谓“底线”就难免陷入“权宜之计”的困境。迄今为止的科技伦理学之所以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聚讼纷纭,难以归宗,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当然,根本说来,任何“底线”都是以某一确定的价值“高度”或者“高限”为定位参照的,无“高限”则无所谓“底线”。有鉴于此,笔者想先通过解析这两个问题,尝试给如何建构科技底线伦理的课题提供一种初步解答。
从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上看,科技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类科学技术活动内涵的“目的—手段(工具)”之价值关系问题,亦即科学技术的目的诉求与责任承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答这一问题将决定如何建构科技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并确立其基本研究方法与路径。究极而论,人类所有科技活动的根本目的都在于人类自身的文明和福祉,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从远古的钻燧取火到今天的网络信息技术概莫能外。与人类其他活动(如宗教、自我繁衍等)不同的是,科技实践及其进步不仅不断改善着人类生活和社会文明,而且内在地而非外在地不断改善着人类自身的生活品质与生活能力,也就是说,科技改善人自身,使人类自身的智力和能力获得持续增长。因此可以说,一切科学技术首先是“为人的”,同时也是“人为的”,因之始终是“指向人类自身的”。科技的这种价值目的性指向实际上内在地规定了科学技术本身之于人类及其文明的工具/手段性价值,在这一终极意义上说,科技同政治、法律、道德等所有文化或文明创造物一样,都是人类为自身及其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而创造的文化/文明化方式或工具。科技没有独立于人类目的之外的自在目的,即便是纯科学探究(如纯数学和某些特型的天文学探究)也是基于人类自身内在智慧需求的智力探险。
然则,哲学伦理学的终极归结总是抽象的,科技伦理学之“目的—工具/手段”之价值关系还需要有其独特确切的理论概述。笔者姑且以三个汉语命题来陈述科技伦理之三层递进式目的,即:“技顺乎道”“技进乎道”“技达乎道”。所谓“技顺乎道”,是指一切科学技术实践都应该以符合人类基本道德原则为前提和归宿,即科技求真符合道德伦理之善。这是科技伦理的底线原则。所谓“技进乎道”,是指科学技术的求真实践本身能够不断切近道德伦理之求善目标。而所谓“技达乎道”,则是科学技术实践达到求真与求善的高度统一境界,如果将科技与艺术审美的关联纳入整体考量,则可谓科技实践的真善美统一。与这三个层次的目的性原则相应,则可合乎理性地推出科技伦理的三个责任原则,那就是科技伦理的道德无害、道德为善和道德完善三个基本责任承诺。更确切地说,任何科学技术实践都必须首先避免给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明带来价值伤害,这是科技伦理的“底线要求”。进而,作为人类及其社会文明的改进方式和手段,任何科技实践都应有益于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明的改进和改善,这是科技伦理的“普遍要求”。最后,任何科技实践都应以人类自身及其社会文明的完善和完美为最高目的或目标追求。
科技伦理的“分衍”与“互联”
需要特别指出,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或特点之一,是其知识技术的专业化和部类化,以及更重要的是其技术专业领域和知识生产部类的快速分衍与更新。这一特点提示我们,在思考科技伦理问题时必须充分注意:一是现代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保持其理论体系与运思方法的开放性,使其能够始终切入当代诸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领域,援用诸科学技术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技术方法。二是现代科技伦理学研究还应当把握各门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对其可能的或潜在的道德伦理问题积极作出预判,使其能够真正发挥价值引导和效应预估的理论作用。三是鉴于现代科技本身快速分衍、多“技”突进的知识更新状况,现代科技伦理学研究还应该发挥其哲学反思和形而上价值学论辩的综合性或整合性功能,促进诸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互联,使其有可能形成多科对话、众技竞秀的“公共理性论坛”,从而不仅丰富自身的理论资源和技术条件,而且激发和促进现代应用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的理论更新改进。
因此,笔者想强调,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专业分衍,多学科多技术之间的交叉与互联必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紧迫和必要,这既是现代科学家、技术工程师和伦理学人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也是他们获取知识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新机遇。与之相关,由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更新,特别是由于现代科技应用与资本、市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勾连,许多新科技及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可能甚或实际上已然带来许多新风险、新问题,其中必有一些新问题难以给出及时而充分的解答,成为当代或未来的科技伦理学的疑难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和疑难,除了保持必要的理论谨慎和科学理性之外,还必须创立相应的公共论坛机制,改变既定传统的伦理学工作方式,即:变个体化的学术工作方式为公共探讨的学术合作“工作坊”方式,以寻求尽可能充分普遍的公共理性认同和价值观念分享,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合作、互联互动、取长补短的现代新型科技伦理学论理方式,从而使一种既具备较高理论理性又具有较为充分的实践解释力和规范约束力的科技伦理学成为可能。
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一如资本和市场,但其实践运用却是蕴含价值取向或价值偏好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不单要科学地了解现代科技及其成果本身的科学意义或知识价值,还要深刻了解并把握其市场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或意义。这是由科技伦理学的内在价值目的所决定的,也是科技伦理学研究者应当自觉理解并坚持的理论立场。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2-18 17:50
【案例】
听哲里丨简明伦理学第5讲:功利主义的历史
功利主义的历史
功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强大、最有说服力的规范性伦理学方法之一。虽然直到19世纪才被完全阐明,但在整个伦理理论史上都可以看到原初的功利主义立场。
虽然讨论的观点有很多种类,但一般认为功利主义是指道德上正确的行动是产生最多好处的行动。有许多方法来阐述这一一般主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该理论是一种后果主义的形式:正确的行动完全是根据产生的后果来理解的。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别在于相关后果的范围。在功利主义看来,一个人应该使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
古典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善与快乐相提并论,因此,与伊壁鸠鲁一样,是价值方面的享乐主义者。他们还认为,我们应该使善最大化,也就是说,为 "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数量的善"。
功利主义的特点还在于公正性和代理人的中立性。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将善最大化时,它是公正地考虑的善。我的利益并不比其他人的利益更重要。此外,我必须促进整体利益的原因与其他人必须促进利益的原因是一样的。这并不是我所特有的。
事实证明,这种道德评价和/或道德决策的方法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有些争议,随后的争议导致了经典理论的改变。
一
古典功利主义的前奏
虽然功利主义的第一个系统论述是由杰里米·边沁(1748-1832)提出的,但激励该理论的核心视角产生得更早。这一视角是,道德上适当的行为不会伤害他人,而是增加幸福或 "效用"。功利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采取了这种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道德评价和道德指南的理论。古典功利主义的早期先驱包括英国的道德家,坎伯兰,沙夫茨伯里,赫奇逊,盖伊和休谟。其中,弗朗西斯·赫奇逊(1694-1746)在谈到行动选择时是明确的功利主义。
一些最早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是 "神学 "功利主义者,如理查德·坎伯兰(1631-1718)和约翰·盖伊(1699-1745)。他们认为,促进人类幸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是上帝所认可的。在列举了人类承担义务的方式后(通过感知 "事物的自然后果"产生的德行的义务、由法律产生的我们的公民义务,以及由 "上帝的权威 "产生的义务),约翰·盖伊写道。"......从对这四种义务的考虑来看......很明显,一个充分和完整的义务,将延伸到所有情况,只能是来自上帝的权威;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在所有情况下使一个人幸福或痛苦:因此,由于我们总是有义务遵守被称为美德的规定,很明显,它的直接规则或标准是上帝的意志"。盖伊认为,既然上帝想要人类的幸福,既然上帝的意志给了我们美德的标准,"......人类的幸福可以说是美德的标准"。这种观点与带有自我主义因素的人类动机观相结合。一个人的个人救赎,她的永恒幸福,取决于是否符合上帝的意愿,就像美德本身一样。促进人类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是一致的,但是,鉴于上帝的设计,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然而,这种功利主义的方法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不清楚上帝做了什么基本工作,至少在规范性伦理方面上帝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答案。“上帝是规范性的来源”这个观点可以与功利主义兼容,但功利主义并不要求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盖伊对后来的作家,如休谟,的影响。正是在盖伊的文章中,涉及到了休谟关于美德本质的一些问题。例如,盖伊对如何解释我们对行动和性格的赞许和不赞许的做法感到好奇。当我们看到一个恶毒的行为时,我们不赞成它。此外,我们将某些事物与它们的影响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形成了积极的联想和消极的联想,这也是我们道德判断的基础。当然,我们将幸福,包括他人的幸福视为一种善,是由于上帝的设计。这是神学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休谟显然会拒绝这种方法,而支持对人性的自然主义观点和对我们与他人的同情性交往的依赖,这是沙夫茨伯里(下文)所预期的方法。例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后来发展了功利主义的神学方法,但由于在呼吁上帝方面缺乏任何理论上的必要性,其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小。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沙夫茨伯里的第三任伯爵(1671-1713)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的 "道德感 "理论家之一,认为我们拥有一种 "内在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进行道德上的辨别。这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与错的感觉,或道德上的美与丑。同样,这一学说的某些方面将被弗朗西斯·赫奇逊和大卫·休谟(1711-1776)所采纳。当然,休谟会明确拒绝任何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含义。如果道德感就像其他知觉感官一样,使我们能够捕捉到我们周围宇宙中的属性,这些属性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感知而存在,是客观的,那么休谟在这方面显然不是一个道德感理论家。但是,感知会捕捉到我们环境中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征视为具有偶然性。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休谟把道德辨别力比作对次要品质的感知,如颜色。用现代术语来说,这些是依赖反应的属性,缺乏客观性,因为它们不存在于我们的反应之外。这一观点对一些人来说是很激进的:如果一个行为是恶性的,它的恶性就是人类对该行为(或其感知的效果)的反应(给定一个修正的视角)的问题,因此具有一种似乎令人不安的偶然性,当然对那些选择神学选择的人来说是不安的。
因此,休谟的观点是,做出道德判断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与功利主义的发展有关的是,沙夫茨伯里关于有德行的人有助于整体利益的观点,也会出现在休谟的著作中,尽管有所修改。就休谟的人为美德而言,它是对整个系统的利益做出贡献的美德。
沙夫茨伯里认为,在判断一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美德或善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人对他或她所处的系统的影响。在这里,有时很难区分沙夫茨伯里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明确指出,无论有什么指导力量,都使自然界成为这样:"......每个人的私人利益和利益,都要为普遍的利益而努力,如果一个生物不再促进这种利益,他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着想,不再促进自己的幸福和福利......"。有时,很难辨别 "因为 "的方向——如果一个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别人,因为它支持一个自己的幸福更有可能的系统,那么它看起来真的像一种自我主义的形式。如果一个人应该帮助别人,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幸运的是,它最终也会促进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更像是功利主义,因为对自我利益的促进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效果,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或行动是合理的。
此外,要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必须具备某些心理能力——例如,他们必须能够反思性格,并向自己表述他人身上被认可或不认可的品质。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任何生物能有公共利益的概念,并能达到对道德上的好与坏、可敬与可责、正确与错误的推测或科学时,我们才称其为有价值或有德行....,我们从不对任何单纯的野兽、白痴或变种人说他有价值或有德行,尽管他曾经是那么善良。
因此,根据该观点,动物不是道德评价的对象,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反映能力。动物也缺乏道德辨别能力,因此似乎也缺乏道德感。这就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道德感似乎是对某件事情的一种感知。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允许我们对感知进行分类的辨别性的感觉。它也有一个命题的方面,因此,在其他感官方面不缺乏的动物在这个方面也是缺乏的。
有德行的人是指其情感、动机、倾向是正确的,而不是指其行为仅仅是正确的,她能够反思善,以及她自己的善。同样,恶毒的人是一个体现了错误的精神状态、情感等种类的人。一个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伤害他人的人,"......因为他抽搐,使他打伤接近他的人",这不是恶毒的,因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愿望,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身体运动是他无法控制的。
沙夫茨伯里通过美德和恶习来进行道德评价。他的功利主义倾向与他的道德感方法以及他的整体感性主义不同。然而,这种方法强调了利己主义的观点——这种趋势被赫奇逊和休谟拾起,后来被密尔在批评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时采用。对于沙夫茨伯里和赫奇逊这样的作家来说,主要的对比是与利己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
与沙夫茨伯里一样,弗朗西斯·赫奇逊对美德评价非常感兴趣。他也采用了道德感的方法。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对行动选择的强调,以及道德审议对行动选择的重要性。在《关于道德善恶的探究》中,赫奇逊相当明确地阐述了行动选择的功利主义原则。指出,是莱布尼茨首先阐明了功利主义的决策程序。
.... 在比较行动的道德品质时......我们被我们的道德感引导着这样判断;在预期从行动中产生的同等程度的幸福中,美德与幸福所及的人数成比例(在这里,人的尊严或道德重要性可以补偿人数);在同等人数中,美德是幸福的数量,或自然的善;或美德是善的数量和享受者人数的复合比例,....因此,最好的行动是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最坏的行动则是以同样的方式造成痛苦。
斯卡尔指出,有些人认为道德感的方法与这种强调使用理性来确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方法不相容;在仅仅领会什么是道德上的意义与我们需要用理性来弄清道德对我们的要求的模式之间存在着对立。但斯卡尔指出,这些实际上并不是不相容的。
从赫奇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一种分工,在这种分工中,道德感使我们看好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不看好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而结果主义推理则决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实际选择的更精确的排序。
然后,斯卡尔用说谎的例子来说明:说谎对被说谎的人来说是有害的,所以一般来说,这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然而,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如果一个谎言对于实现某些明显的利益是必要的,那么后果主义的推理将引导我们支持这个谎言。但这个例子似乎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对道德认可和不认可的后果的考虑上。斯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指出,道德感关注的是动机——例如,我们赞同仁爱的动机,而且范围越广越好。认可和不认可的对象是动机而不是后果。但是,只要道德上的好人关心别人的遭遇(她当然关心),她就会根据行为对别人的影响来排列顺序,而理性是用来计算影响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不相容的情况。
赫奇逊致力于实现功利的最大化。然而,他坚持一个警告——"人的尊严或道德重要性可以补偿数量"。他还增加了一个义务论的约束——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凭借他们的人格给予他们基本的尊严,而不管有多少人的幸福会受到有关行动的影响。
休谟深受赫奇逊的影响,后者是他的老师之一。他的体系也包含了沙夫茨伯里的见解,尽管他肯定缺乏沙夫茨伯里的自信,即美德是其自身的回报。就他在功利主义历史上的地位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体系有两个不同的影响。首先,他对人为美德的社会效用的论述影响了边沁的效用思想。其次,他关于情感在道德判断和对道德规范的承诺中的作用的论述影响了密尔关于道德的内部制裁的思想。密尔在发展功利主义的 "利他主义 "方法时与边沁有分歧(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但后面会详细说明)。与密尔相比,边沁代表了利己主义的分支——他的人性理论反映了霍布斯的心理利己主义。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李佳怿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2-27 23:57
【案例】
经典荐读 | 罗尔斯:道德理论的独立性
推荐理由
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道德哲学是从属于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的,因此,只有在诸如自由意志和人格同一性等问题有了答案后才能对之继续研究下去。对于这种看法,罗尔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这篇文章是罗尔斯于1974年在美国哲学学会上的主席讲演。在其中,罗尔斯对道德哲学与道德理论进行了区分,阐发了反思平衡的理念,讨论了道德理论与哲学其他领域如意义理论、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的关系问题,并认为道德哲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道德观念结构的更深刻理解。道德理论的独立性这个基本理念,此后被应用到政治哲学中去,并且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希望概括一种有关道德哲学的观点,并且表达我目前关于如何最好地从事该学科中心部分的研究的一种确信。我的讨论的大部分都是方法论上的,尽管这些都是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但我相信我所描述的观点现在、并且也许一直以来就为许多人所持有,至少自十八世纪以来就是这样。我在本文所做的评论的目的,是通过阐述那些适合我们时代的解释而去支持哲学这个分支中一种为人们熟悉的传统。
I
也许我最好从解释题目的意思开始着手。我对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与道德理论(moral theory)做了区分;道德哲学包括后者,并将之作为其主要部分之一。道德理论是对实质性道德观念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正当、善、道德价值等基本概念被如何安排从而形成不同的道德结构的。道德理论尝试去鉴别这些道德结构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并且去刻画这些结构与我们的道德感受力(moral sensibility)、我们的自然态度的关联方式,以及去确定如果它们要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人们期望的角色的话,它们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道德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哲学其他分支的。一般而言,意义理论、认识论、心灵哲学对道德理论贡献甚少。事实上,在研究道德理论时,若一心关注这些哲学分支里的主要问题,很可能会阻碍道德理论研究的推进。当然,哲学的某一分支不是绝对独立于其他部分的;对于我称为“道德理论”的道德哲学的那个部分而言,这一点同样为真。但对实质性的道德观念以及它们与我们道德感的关系的研究,有其自己独特的问题和主题,这要求我们要为着这些问题和主题本身而去对它们进行研究。同时,对有关道德概念分析、客观道德真理的存在、人性和人格同一性等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这些道德结构的理解。因此,道德哲学中与意义理论、认识论、形而上学以及心灵哲学有关的问题,必定要求对道德理论有一种理解。
有人表达了一种相反的观点。现代哲学被认为是以笛卡尔使得认识论在方法论上先于哲学的所有其他分支为开端的。而自弗雷格(Frege)之后许多人又倾向于相信占据此优先地位的是意义理论。因此,人们认为:首先,除非认识论或今天人们所认为的意义理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否则哲学的其他问题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答;其次,这些先在的问题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对它们的回答既不取决于也不要求来自哲学其他分支的结论。因此,道德哲学也被认为是从属于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的,而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又是从属于意义理论和认识论理论的。因此,伦理学除了自身的问题外,也要等待诸如自由意志和人格同一性等这些问题有了答案后才能继续研究下去。
无论哲学其他分支的这种等级排列观念有多大的优点,我相信它不适用于道德哲学。相反,正如我们现在知道意义理论取决于形式逻辑的发展,打个比方说就是弗雷格依赖于哥德尔(Gödel),所以我们可以说:道德哲学的进一步推进,取决于对道德观念结构的一种更深刻理解,以及它们与人类情感的关系。在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的潜在结构以及数学基础在集合论中的获得理解之前,逻辑和数学哲学必定停留在初步和原始的阶段。而道德哲学目前的状况呼唤一种相似的、在我们对道德观念结构的理解方面的一个大力提升;并且这种探究,在许多方面与逻辑及数学基础的发展一样,是可以独立地进行的。正如意义理论和数学哲学相关于逻辑以及数学基础那样,或甚至如物理哲学相关于理论物理那样,因此道德哲学也是与道德理论相关联的,也就是与对道德结构的解释以及它们在道德心理学中的基础相关联。
II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道德理论独立于认识论的一种方式。我主张当前我们应搁置建构一种有关正当和错误的正确理论,也就是搁置对被我们看作是客观的道德真理做一种系统解释。因为道德哲学史已经表明道德真理的概念是成问题的,在我们获得对道德观念的一种更深刻理解之前,我们可以搁置对它的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在生活中表达着道德观念,且似乎受到道德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这些观念本身作为研究的焦点;所以暂时地,我们可搁置道德真理的问题并且转向道德理论:我们探究在恰当界定的条件下人们持有的或将会持有的实质性道德观念。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尝试去找到原则的一个体系,它能够与人们在反思平衡中的深思熟虑判断以及普遍的确信相匹配。这个原则体系体现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以及刻画了他们的道德感。人们可以将道德理论家看作是一个观察者,他尝试去阐明其他人的道德观念和态度的结构。因为看起来人们很可能持有不同的观念,并且这些观念的结构在任何情形中都难以描画,那么我们最好从研究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主要的观念开始,并且从那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开始,包括他们对特定的道德和社会议题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将我们自己包括进去,只要我们为详尽的自我检视做好了准备。
但在对自身进行研究时,人们必须区分自己作为一个道德理论家的角色与作为持有某种观念的某个人的角色。在前一种角色中,我们探究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方面以及我们道德感的结构;而作为后者,我们正在应用一种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可能(尽管不一定)被我们认为是关于客观对与错的一种正确理论。
反思平衡的程序看起来似乎是保守的,也就是说,它将探究限制到人们(包括研究者自己)当前所持有的观念上。但有几点防止了其保守性:第一、我们并不把人们特殊的深思熟虑判断(例如那些关于特殊行为和制度的判断),算做是穷尽了关于他们道德观念的相关信息。人们在所有一般性层次上都具有深思熟虑的判断,从那些关于特定情景和制度的判断,上升到关于宽泛标准和首要原则的判断,再到关于道德观念的形式和抽象条件的判断。我们尝试去观察人们怎样使得他们各种各样的确信整合为一个融贯体系的;每个人深思熟虑的确信,无论它处于什么样层次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初可信性。通过抛弃和修订一些确信,通过重述和拓展另一些,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系统的、组织化的观念体系。尽管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得以起步,各种判断要看作是足够稳定的,从而暂时地将它们当做是一些固定的点,但所有一般性层次上的任何判断,原则上都不是可以免于修订的。即使是特殊判断的总体也没有被赋予一种决定性的角色;因此,这些判断并没有取得如人们有时候赋予知识论中的知觉判断的那种地位。
我顺便提及一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可能是基于一些自明的首要原则的。反思平衡的程序本身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无论这是多么的不可能。因为在达致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有可能首要原则被阐述得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它们引导我们去修改前前后后所有与它们不一致的判断。反思平衡只要求反思的主体带着确定和信心去做这些修订;并且假如人们可以接受这些原则的实践后果的话,反思平衡会要求人们继续认可这些原则。
还有,因为我们的探究受哲学上的考虑所驱动,所以我们关心在经过宽泛的反思平衡(widereflective equilibrium)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反思平衡后,人们会持有的道德观念是什么;这种平衡是满足某些理性条件的平衡。也就是,我们采纳那个观察性的道德理论家的角色并去探究:当人们有机会考察另外一些可行的观念以及支撑这些观念的基础时,他们将会认可什么样的原则和接受什么样的结果?将此过程推至尽头,在对所有可行观念以及所有支持它们的合理理由进行理性考察后,人们就可以找到在此过程中幸存下来的那个观念或多个观念。当然,我们并不能现实地执行此过程,但我们可以执行一个次优的过程,也就是去描绘那些哲学传统中为我们所熟悉的主要观念,并且对那些对我们触动最大、我们认为是最有希望的观念进行进一步的提炼、阐明。
道德理论独立于认识论源自如下事实:反思平衡的程序并没有假定只有唯一一个道德观念是正确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将之看作一种心理学并且它并不预设客观道德真理的存在。即使假定每个人都达致了一种宽泛的反思平衡,但许多对立的道德观念依然存在。事实上,存在着许多可能性。某种观念可能打败所有其他的观念,并且非常狭窄地限制着我们比较具体的判断。而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又可能认可相互对立的观念。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就是一些观念能够通过反思平衡的经验而存活下来,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也许每个观念都与其他观念有冲突且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基础;或者它们之间以类似于不同的几何体之间相连的那种方式相互关联着。也就是说,它们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首要原则,这些原则如定义绝对几何那样定义着绝对的道德;然而在其他方面,它们采纳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不同的解决方式界定着与众不同的道德,一如对平行线不同定理的不同选择刻画着不同的几何那样。在后面这种我怀疑是最有可能的情形中,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些绝对道德原则的后果,以及这些原则是否足够厚实以至于能够提供一种相互调和的建构性基础。
人们很自然就会假定,客观道德真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经过宽泛的反思平衡后人们所认可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一种充分的一致性,当人们的道德确信满足理性的某些条件时,就可以达致这种状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充分的一致性是否能够达到,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考虑,因为任何这样的讨论都是不成熟的。在《伦理学方法》第一版前言中,西季维克解释道他希望抵制一种催促:去发现一种真确的方法,凭借此方法可以查明做什么是正当的。他转而希望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并且尽可能不偏不倚地详细描述在人类道德意识中发现的各种不同的方法,并将之整合进一个熟悉的历史体系中。道德理论现在也应做相同的事情,只是在此所展开前沿领域要比西季维克所尝试的更宽广。西季维克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被他当做是一种伦理学方法的理性利已主义,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所有道德观念的一种挑战,尽管研究这一点也很有趣。除了利己主义,西季维克将他的比较研究大部分限于直觉主义和效用主义。他很少关注完善论或由康德所代表的那种道德观念;我相信西季维克对康德的学说做了一个非常狭隘的诠释,并因此,他似乎默认效用主义优于所有其他观念。但完善论和康德的观念这两种道德观念或伦理学方法也必须要被涵括进对道德理论而言是本质性的系统比较中。做这样的比较这项任务是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完成的,它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哲学的其他分支的;并且在这项任务有进一步的进展之前,我们对道德真理的问题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法。西季维克认为道德哲学所取得的进步是由启迪的欲望(the desire to edify)所支撑着的;如果道德哲学的探究要让路于急着回答人们尚未准备好去怎么回答的问题,那么这只会对道德哲学的发展形成障碍。至少就此情形看,如果存在任何优先关系的话,那么优先次序也是相反的,即从道德理论到道德认识论。
III
现在我要讨论下道德理论独立于意义理论。但首先要指出,我的用意不是说意义理论,或有关规范语言特征的研究对道德哲学毫无贡献。给定作为整体哲学的发展和语言哲学的成长,肇始自摩尔的《伦理学原理》这个方向的许多努力已经成为一个自然趋势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我相信,从道德理论这个角度来看,关于意义的考量最好的也只能为道德观念中的首要原则提供一些必要的所谓形式条件。超过这一点就要求对道德结构做系统性的比较;因为当我们尝试去界定这些形式条件本身时必定会遭遇到一些问题,它们会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比较的必要性。即使在意义理论与道德理论看起来最相关的地方,它的作用也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相似的命运落在康德相似的努力上——他试图去表明道德法则的形式是先验的,可以将之从一个纯粹理性存在者的概念中推导出来。定言命令经常能给出合理的结果,但这只是因为引入了另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是不属于那个纯粹理性存在者概念的一部分的。
我想,这些形式特征最好被看作是一些非常一般化的属性,它们很自然地被以各种理由施加到道德概念上。这样做的根据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高层次确信:任何有吸引力的观念都必须满足这些规定;并且很明显,正是在这个地方意义理论进入来了。或者有人会认为,考虑到道德观念的社会角色以及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引入某些形式条件是恰当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以对这些条件的一个特殊刻画开始,随后依据该理论发展出自身的方式而决定这些条件的去留。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由于存在着对道德观念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不同理解,道德哲学的不同传统都将毫无疑问地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对这些高阶的条件做不同的诠释。我们需要确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并且需要对这样而产生的对道德观念的那些限制做比较和评估。这就要求对这些一般属性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东西做一个更加详尽的阐述;而这种探究超越了意义的问题。
更具体地说,考虑一下一般性、普遍性、有序性、终极性以及公共性这些形式条件。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不同的方式去界定,并且即使这些多样性初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其中的差异很可能是意义重大的。最恰当的定义并非是一个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此产生的理论整体上如何相互恰当地组合在一起的问题。例如,某些关于有序性(ordering)的形式条件,从道德原则处理冲突主张的这个社会角色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在此,人们脑海中想到的有序性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我们不会将斗争努力得来的结果,或遵循按照每个人的威胁性优势(threat advantage)来分配这个命令得来的结果看作是一种恰当的次序。但一种次序多大程度上受到历史的意外、社会地位的偶然性或人们在天赋和能力自然博彩中的遭遇的影响呢?仅仅关注有序性的概念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这就要求一种道德理论并且在这一点上对可能出现的观念进行比较,比如说,一种康德式的观点与一种自由至上主义观点的比较。
还有,一旦我们问有序性应该具备哪些逻辑属性,那么就会遇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因此,次序应该是完整的和具有传递性的吗?或者我们是否对只具有部分完整性和只是有时候具有传递性的次序感到满意吗?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希望道德观念应用情形的范围有多大;范围越大对道德原则的要求也越高。如果我们要求该原则在所有可能世界都适用,并因此允许它的领域涵盖所有能构想出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道德理论从一开始就被宣告是无用的。而且我们也尚未能对那些范围有限的传统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必须允许道德哲学自由地将其领域限制到理论的目前状态所要求的限度内,以及可行的经验性假设允许的范围内。一旦我们这样做,那么很明显,我们的探究超越了意义的考量。
相似的观察对于公共性(publicity)条件而言也成立,此条件在一种康德式的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概略而言,公共性要求:在评估道德观念时,我们要对它们被公共认可时会产生的结果加以考虑。每一个人都被认为是知道其他人也持有相应的原则,而这个事实转而又成为一种公共知识,等等。这就使得这些原则仿佛是一个协议的结果。但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共性。最简单的情形就是只要求那个正义原则是公共的;但人们另外也可能要求那些用来为该原则做论证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一般信念也应该是公共的,或至少应得到获得公共地接受的探究方法支持的。最后,公共性可能被认为意味着对道德的观念——当它以其自己的术语表达出来时——的充分辩护(full justification)应该是公共的。应用此形式条件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探究一下:若一种观念界定着一个社会的一部公共道德宪法,且在此社会里对该观念的充分辩护成为一种公共知识,那么此观念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就导向了符合此观念的组织有序社会的理想状况。对这样的理想状况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比较各种各样的结构。有时候,当一个观念不能被公共地实现,那么我们可能就说它被证明是不融贯的;在其他的情况下,它可能只导致了一些我们之前没有预见到的不便。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共性条件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影响所有观念的。在此意义上,它是有选择性的。
现在看来,这种公共性条件可能太过强了。所以,这促使我们问:为什么要采用它?首先,考虑一下它在政治原则上的应用。应用到宪法以及和社会基本结构原则,即使它在有利条件下是有辩护的,通常也会包含着一些法律强制机制。这些制度重要地塑造着社会成员的品格和目的,并对这些方面有决定性的长远影响。因此,要求社会合作的根本条款符合公共性的要求就是合适的。因为,如果制度依赖于强制性制裁,无论对这种强制使用的约束是多么的严格,这些制度的基础与趋向都应该经得起公共的审察。当政治原则满足公共性条件时,社会安排和个体行为就是同样地有辩护的,如此—来,公民能就自己的信念与行为向其他人做出充分的说明,并且这种公共说明本身将会强化这种公共理解。在此意义上,没有任何事情会被隐瞒。
支持公共性的第二种考虑与道德动机有关。一种道德观念包含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conceptionof persons )以及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那些在某种特殊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某种人,并且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以及处理他人的关系中会体现这种观念。因此道德动机的基本形式就是成为某种人的欲望,以及被其他人认可成为了某种人的欲望。康德可能把这种欲望界定为成为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欲望,以及被他人认可为目的王国的立法者一员的欲望。现在让我们假定,某些原则以及对它们的辩护事实上正是阐明了这样一种人观念。那么,给定我们对社会的依赖,除非制度发展和鼓励我们按照这种观念行动的能力,除非其他人也公共地认可这种观念的实现,否则我们不可能成为这类人。人们获得这样的人观念,是社会合作的成果,因为成功取决于社会形式和彼此认可。那么,某些道德观念非常自然地与公共性条件的某些形式联系在一起。
在此,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引入稳定性的理念。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一个完整的道德结构包含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这种人观念为对道德动机的说明提供了基础:成为某种人回应并集结自我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和抱负,并且使得人们更加有效地依照道德观念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和理想去行动。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去问道:一种道德观念是否是稳定的呢?也就是在这些原则得到公共地实现的社会或社会团体那里,这些原则是否产生出了一种自我支撑(generate their own support)。请记住,一个社会,如果一种道德观念既是公共的而又被人们一致地遵循着去行动,那么此社会就是按照这个道德观念有序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因此,稳定性的问题就是:符合此观念的该组织有序社会是否是稳定的,或相对其他观念而言它是否多少表现出了一种稳定性呢?我相信,对组织有序社会的比较研究,是道德理论的核心理论努力,它预设了对各种各样的道德结构以及它们与我们的道德感及自然态度之间关系的把握。这种努力与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有几分相似之处。在两种例子中,人们都是关注一种理论性定义的社会体系的运作,或关于这种体系的某部分的运作,并且尝试去考察它们的主要要素如何相互结合进一个持续运作的体系中去的。探究者并不期待能得到涵括特殊情形和特殊例子的那些详尽结论,而只是希望去获得关于这种较大的结构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维持自身的一个全景图。正是在对组织有序社会的比较研究中,道德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的关联性变得非常明显。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注意到公共性与两个实践的限制是相联系着的:原则的简明性(simplicity)以及原则清楚确定的应用所需要的信息总量。对简明性的需要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一种道德观念要是公共的,那么其原则的复杂性就必须要有一个限度:人们必须能够在没有太多例外以及不需太多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制定这些原则;并且原则的数量要合理地少以及规定了优先规则。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越简单明了的观念就越值得偏爱,并且若复杂程度越过了某一点,就会超出公共性所划定的边界。至于信息要求,应用原则所需的信息越少,以及关于它们曾经被正确地应用过的事实会有助于更轻易地确立起公共性。这可能是因为原则所应用到的那类东西,或被它们挑选出来是相关的那些特征,或它们要求我们对未来的计算有多远等,都取决于理论性的、或复杂的知识。当然,所有合乎情理的道德观念都要求相当多的信息,以便使之可应用到我们的世界中,以及引导我们根据当前环境来应用它的原则。但并非所有观念都要求同等的信息,有些要求的信息比其他的少得多。如果公共性被接受为一个重要的形式条件,那么简明性的约束以及对信息的限制就必须要考虑在内。这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问题似乎无法避免。
我已经讨论过有序性和公共性这两个形式条件,因为它们是如此明显地表明了意义考虑的限制。我们应该将这些观念看作是道德观念的非常一般的属性,并且尝试去考察它们怎样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结构,以及该结构的主要部分融合起来的。这些形式条件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力量,这取决于它们所归属的总体观念。我们已经看到,例如,公共性是怎样自然地与某些结构以及人观念(而不是另一些结构及观念)相联系着的。类似的,我相信一般性与普遍性在目的论和道义论中也具有不同的力量。当然,把意义的解释限于去考察这些形式性条件、或实际上限于一般性的道德结构,会招致一个反对:这把意义探究限制得太狭隘了。但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对这些条件的各种各样的描述,与某个特殊的道德观念(这些条件正是归属于此观念)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确定它们的意义并不是理解这些观念的一个独立的基础。
IV
现在我要去考察下所谓道德哲学依赖于心灵哲学的这种说法,人们经常举人格同一性(personalidentity)这个问题去证明这种依赖性。但是,我要先说明一下,相比于前两个解释,我对这种联系的观察更多的是暗示性的,并且至多只能表明一种有关道德哲学的重大意义的观点。接下来,我将简单地陈述一下我推测是如此的一些情况。
第一,心灵哲学在有关人格同一性问题上的结论,并没有提供一种基础让我们去接受主流道德观念中的此观念而非彼观念。无论这些结论是什么,直觉主义、效用主义、完善论以及康德式的观点,每一个都可以使用与这些结论相一致的同一性标准。因此,尽管心灵哲学也许能够建立一些任何正确标准都必须满足的条件,但传统的道德学说中没有任一个学说会受这些限制的影响,至少只要这些学说是在正常的人类条件下应用时就不会受其影响。
第二,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不同的道德理论中包含着不同的人观念和理想。因此,每一个观念都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人格同一性标准;而且,这些标准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变体,不同的观点对于人的某些特征的重要性如何看法各异。但同时,所有的标准又都同时能满足心灵哲学提供的结论;因此人格同一性标准的各种变体,并不是由心灵哲学这个学科来解释的,而是由不同的原则以及不同的道德理论中所采纳的不同的人观念来解释的。着重点的不同源于如下事实:一种关于同一性的标准会被调整,以使之适应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的要求。据此,人格同一性标准的各种变体并非是先于道德理论的,而是要由道德理论来对它们进行解释的。
第三,道德观念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以及相应的组织有序社会的理论。给定它们是可行的,那么这些观念的合理性转而又取决于它们的内容,也就是取决于这些观念的原则引导我们去追求的那种社会是什么,以及它们鼓励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心灵哲学中的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现在,我尝试去详细解释一下这些推测。为了确定理念,让我们把如下这些关于人格同一性的结论接受为是已经由心灵哲学所确立了的东西。就当前情况看来,它们体现了任何合理的同一性标准都必须满足的约束。首先,人的一个本质方面是精神性的,因此人格同一性的一种标准必须根据人的品格和目的,经验和记忆的连续性(continuities)来定义,这种定义也必须参考人们的生活计划以及在这种计划的转换与变化保持不变的那一类解释来进行。人的第二个本质方面是身体性的:人们总是具体地呈现着的,并且身体的连续性是人格同一性一种标准的一个进一步的必要特征。因此,总的来说,人是通过精神上的连续性,以及在时空中有计划行为的一种相连秩序而体现出来的。
我假定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每一种都能满足这些约束。当然,这些约束并非是没有争议的;尤其是,尚不清楚身体上的连续性是不是人格同一性的一个必要部分。但在使用各种例子去研究同一性标准时,如果我们将这裂变和身体转移这样假设性情形搁置一边的话,那么认为这些条件将会给出错误答案的主要理由就将会是神学上的。灵魂不朽的学说引导我们去否定身体的连续性是人格同一性所要求的。但即使在一个世俗的框架里身体的连续性被证明是不必要的,我的推测是:它仍然不会使得一种道德观念比另一些观念更合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继续讨论下去。人有许多方面是重要的:例如,意识与自我意识,推理和使用语言能力,品格与意志,等等。但从道德理论的角度看,人的这些方面最相关的是他们进入和维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能力、他们具有及分享特定经验的能力、参与具有某些特征的活动能力以及他们有能力发展出一种正当感和正义感,以及一般性的道德倾向。一种同一性的标准是用于建立起一种道德秩序的;正义与义务被分派给个人和社会地位,而这些又转而意味着某些责任和职责。正如一种关于物理对象以及时空的同一性标准要求去建构一种关于物理体以及时空中的事件的客观秩序一样,人格同一性的一种公共标准也要求去描画以及维持一种道德秩序。但是道德观念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人,并且对人性的不同方面赋予不同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每个道德观念都采纳一种符合心灵哲学结果的同一性标准,但每个观念都可能会具体化自己的准以使之符合一种特殊道德秩序以及人观念的要求。对这些问题的比较研究,属于道德理论并且会将我们带离心灵哲学。
这些评论可以通过比较一下在一种古典效用主义以及在一种康德式的理论那里对一种同一性标准的需要来进一步阐明。为了简明起见,我将以一种比较粗略的方式来陈述这种对比。追随西季维克对古典效用主义的阐述,我们假定存在且只存在一种终极的善,它是在意识上或知觉上令人愉悦的,并且理性的人是通过独立于所有条件与关系的内省来将它认可为终极的善的。说社会制度与个人行为是正当的,是在它们能够最大化如此理解的终极善的净余额这个意义上说的。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不考虑这些善好在人们之间的分配。这里所体现的这种人观念实际上是一个容器人(a container—person);人们被看作是那些内在的有价值的经验(valuableexperiences)的发生地,这些经验被认为它们自身就是完整的。这样,人仿佛就只是这样一些经验的载体。谁具有这些经验以及接下来的在人们之间的分配都不重要;这些考虑只是时间和处所的问题,它们本身是不相关的。效用主义集中关注这种有价值的经验本身,并且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所有容器人一起装载着的那些经验的总和。
和其他观点一样,一种效用的观念也需要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标准,有两个理由。首先,为了最大化善的剩余额,它在实践中必须对因果关系以及其他自然关系加以考虑,以决定怎样最好地取得剩余额的最大值。它必须追踪个体们的同一性,因为这是探究各种行为和制度的结果之必需。例如,如果前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影响人们其后对于那些有价值经验的装载能力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有能力去鉴别谁之前受过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需要人格同一性标准的另一个理由在于道德理念本身,而在这方面,效用主义除了使用人格同一性去评估有价值的经验总体外,它在其他地方其实不需要一种人格同一性标准。假定没有任何一种经验的持续时间会长于某一特定的时间间隔,那么效用主义就没必要去问处于在当前时间区间内的具有一定有价值经验的人,是否与处于前一个区间中的具有一定有价值经验的人是同一个人;因为各种间隔的时间序列不再相关,正如同一时间间隔之内的人际间分配是不相关的一样。查明人们同一性的唯一理由,就是估计令人愉悦的意识(agreeable consciousness)的净剩余额,以及防止重复计算。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康德式的观点。我们可以假定这种观点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它对某些首要的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的强调,这些原则把权利和自由权,责任和职责分派给个体们,并要求基本制度和社会合作要采纳某种形式或符合某些限制。在康德式的观点这里,根本没提及最大化善的总额,更不用说最大化有价值经验的总体了。相反,它确定了为推进人类目的而必须的各种一般手段,并且要求以某种与个体们的贡献相关的方式分配这些手段;另外,这些分配方式要设计得有助于保持社会制度的长期正义性。此观点所涉及的人的观念是一种自主人(autonomous persons)的观念,他具有一个最高阶的利益去关心自己的其他利益、甚至包括他们的根本性利益是如何受到社会制度的塑造和规约的。因此,首要原则的设计,要保障某些服务于推进这些利益的基本自由权,以及确立一个正义的背景体系,以便在此体系里为达成这些目的的必需手段能够被有效地生产出来和公平地分配。这里表达的一种关于人的理想是:这样的人对横跨他们一生的那些根本利益负责,并且认为实现这些利益的方式应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我们可以在与讨论效用主义对人格同一性标准的需要时所列的相同标题下讨论康德式观点的情况。在第一个标题下,一种康德式的观点,与效用主义观点一样,必须对关系到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应用其原则的那些因果关系与自然关系加以考虑。如果不深入一些细节讨论的话,这两种道德观念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差别。因此我们说,在这一点上,追踪人格同一性对两者而言都是同等的重要,即使相关的自然事实在不同观念那里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转到第二标题,即从那种道德秩序本身产生的对人格同一性的要求时,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康德式的观点,效用主义对人格同一性标准的需求是较少的;或者更好地说,它可以在使用一个比较弱的同一性标准的情况下对付过去。首先,因为效用主义把不将任何价值赋予善好的分配,所以它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同一性问题;而分配问题对于康德式的观点而言是本质性的——责任与贡献之间的链接需要历时性地追踪,并且保证分配恰当地与它们联系起来。还有,对横跨他们一生的那些根本利益负责的自主人的理想,它所持续的时间,比效用主义理论认可的最长的完整、有价值的经验所延伸的时间要长得多;并因此,我们必须构想一种同一性,它能延伸跨越更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在实践中一种康德式的观点更加依赖于人格同一性,也就是说,它依赖于一个更强的标准。
现在,我假定我们同意人们是通过精神上的连续性,以及在时空中的有计划行为的一种相连秩序而体现出来的。我将此论题看作是一种广泛的经验性心灵哲学的结果。我们的问题是:此结论是否偏向于依赖弱的人格同一性标准的那种道德观念?让我们考虑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精神上的连续性并不总是持续不变的:记忆会褪色、希望会破灭、品格和意志会改变,而且有时候还变化得很突然,更不用说计划与欲望的变化了。构成人的那些东西,往往是一些易碎的东西且经常会遭遇混乱。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事实,连同“任何人格同一性的标准都是最终建立在经验性的规律和关系之上”这个结论一起,支持效用主义而不是康德式的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效用主义不考虑分配问题或人们生活的长期的连续性问题,并因此它就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去担心人或他们的同一性的易碎性。从最大化令人愉快的意识的总和这个立场看,甚至鼓励记忆的褪去以及品格的改变也许可被证明是最优的选择。但对康德式的观点而言,此事实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它依赖于同一性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样式,并且它的人理想鼓励更强更持久的连续性。因此我们被引导去问:心灵哲学的结论以及精神联系的流转性及有时出现的短期性,是否是有利于古典效用主义理论。
在我看来,答案整个地取决于引起这些不连续性的条件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其他道德观念的可行性。例如,假定一种康德式的组织有序社会是可能的以及是可有效地运作的:它的成员能够并且一般而言的确是过着一种必要的、同一性能够被鉴定出来的生活。在这里,我假定这种人们可以过或的确在过着的生活,重要的是受到在他们社会中被公共地认可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将由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来塑造,并且这又转而受到我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形式的影响。
如果一种康德式的观念是可行的,那么效用主义或任何其他观点依赖于一种弱的同一性标准这个事实,或它们在长久连续性方面要求不高的事实,都是不相关的。并且,假如康德式的计划所要求的连续性不能在一个效用主义社会里存在,这同样是不相关的。我们可以设想人们是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他们的生活缺乏一种康德式的观点赖以运作的那种关联性(connectedness)以及长久目的感(sense of longerpurpose)。但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这些东西,并没有表明从一种道德观点看什么东西是可欲的。没有任何一种关联程度是自然的或固定的;人们生活中实际的连续性和目的感,是与那个社会性地去实现的道德观念相联系着的。
因此,最关键的要点是那个与某种道德观念相对应的组织有序社会,是否在其成员身上产生出那种对于维持该社会自身是必要的连续性以及目的感。我们还得考虑它是否是足够稳定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要说非连续性的一般可能性的支持一种效用主义的观点,只有在社会理论能够表明如下一点时才成立:在其他观念的情形中,这些观念所要求的那种关联性不可能产生。
但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让我们去相信这一点为真。不同的道德观念每一个都可能通过此测试。并且这证实了如下推测: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并没有在道德结构之间做有倾向的选择,它也解释不了各种道德结构对一种同一性标准的各种不同使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道德观点的内容以及它在人类情感中的根基。我们的研究的进一步推进,要求对道德结构及这种结构所包含的人观念要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还要对不同的组织有序社会进行一种系统化比较研究。
V
我现在必须简单地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观点。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质疑对哲学各个分支的那种等级安排,去表达关于道德哲学的一种观点。我相信,在意义理论,认识论、心灵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上,前者并非处于一种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相反,道德哲学的一个中心部分,我称为道德理论;它存在于道德观念的比较性研究中,而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我首先讨论了反思平衡的方法,并认为客观的道德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似乎取决于理性的人在达到或足够地靠近一种宽泛的反思平衡后能够达成的一致的性质与范围。这表明了道德认识论依赖于道德理论。接下来,我指出了施加到道德结构上的一些所谓的形式条件,并主张说这些条件最好的也只应看作是这些结构一般的和抽象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我们认为可以由一种意义理论来解释的这些条件,而是应该去检视它们作为整体道德观念的要素的力量。最后,我简单地考察了由人格同一性这个问题来示例的心灵哲学,并推测性地认为:所有主要的道德观念都可以使用一种与心灵哲学的结论相一致的同一性标准;但这些观念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具体化此标准,以便它能与自己的道德秩序观念以及人观念相适应。我认为心灵哲学本身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并且它也不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道德观念间做选择。
因此,我力主道德理论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独立于其他哲学分支的,并且有时候是在方法论优先于它们。但我并不太关心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我更倾向的理念是:哲学的每一个分支都有其自己的主题和问题,且同时与其他分支处于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依赖中。方法论上的等级制的错误,不同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等级制的错误:它导致了视角的一种扭曲,并且误导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形中,这种扭曲导致关于道德观念的实质性结构的许多问题以及对它们的差异的比较研究被推后了。人们夸大了道德哲学尤其是道德理论对哲学其他分支的依赖;并且我们对意义理论、认识论以及心灵哲学的期望有点过高了。
作为总结,我想重申我在开头说过的东西。也就是说,正如我们现在知道意义理论取决于形式逻辑的发展,打个比方说就是弗雷格依赖于哥德尔,所以我们可以说:道德哲学的进一步推进,取决于对道德观念结构的一种更深刻理解,以及它们与人类情感的关系;并且这种探究,在许多方面与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发展一样,是可以独立地进行。我们必须不能因为此项研究任务的大部分似乎属于心理学与社会学而非哲学就对它感到厌倦。因为事实是:其他学科的人不会为哲学性的兴趣所触动去探究道德理论;这种动机是本质性的,因为没有它的话,这种探究就会关注错误的焦点。道德哲学传统中的所有主要观念必须持续地更新。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尝试通过批评交流、相互吸收长处来不断增强对这些观念的系统阐述。在这种努力中,对某一特定观点而言最有吸引力的那些目的,不应被驳斥,而是要不断完善。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古凤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7 21:14
【案例】
哲学名家讲演录: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
导读
当时大陆和英国主要有两派在争论:大陆的唯理论派和英国的经验论派。唯理论派在康德的时代是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为代表。唯理论最早是由笛卡尔创立的,然后是斯宾诺莎……以后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之后是其弟子沃尔夫,沃尔夫把唯理论的思想大大地扩展了,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但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英国盛行的是经验派。那是由培根所开创的,并经过霍布斯、洛克到贝克莱、休谟发展的。……人的知识是天赋予我们的,这是当时的理性派的观点。经验论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天赋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后天的,是外界加于人们的感官造成的。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第一讲《纯粹理性批判》
1、2004年是康德诞辰280周年,逝世20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康德。……对康德哲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这是今天哲学界的共识,叫做“说不尽的康德”。(p1)
一、《纯粹理性批判》产生的历史背景
2、当时对康德的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休谟,他说休谟打断了他的独断伦的迷梦,也就是说,打断了他的教条主义的迷梦。(p2)
3、当时大陆和英国主要有两派在争论:大陆的唯理论派和英国的经验论派。唯理论派在康德的时代是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为代表。唯理论最早是由笛卡尔创立的,然后是斯宾诺莎……以后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之后是其弟子沃尔夫,沃尔夫把唯理论的思想大大地扩展了,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但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英国盛行的是经验派。那是由培根所开创的,并经过霍布斯、洛克到贝克莱、休谟发展的。……人的知识是天赋予我们的,这是当时的理性派的观点。经验论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天赋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后天的,是外界加于人们的感官造成的。(p2-3)
4、经验论在贝克莱、休谟以前基本是唯物主义的……霍布斯、洛克都是属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但贝克莱和休谟把经验论推向了极端,形成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只承认我们在感性中、在知觉中、在我们所接受的印象中所获得的东西,而把知识的来源问题撇开。……特别是休谟,他是一种怀疑论的经验论。他认为,一切离开我们直觉所获得的印象、知觉的知识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的认识永远超不出我们的感觉。(p3-4)
5、休谟一个著名的论证就是关于因果性的论证。……既然因果关系这样的概念是我们通过习惯性的联想形成起来的,那么,如果有某种效力的话,也只有主观的效力,而没有客观的效力。……当然,他不否认有客观规律,他只是说我们不知道,没有看到。休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休谟对于因果性的可靠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解构,这在当时大陆的学术界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因果性在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是一个理论的台柱。……休谟的批判可谓石破天惊!因果性都被摧毁了,那科学还有什么可相信的?都成了一大堆心理印象的偶然堆积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等同于一种错觉。(p4-6)
6、除了因果性以外,休谟还否定了很多,比如说实体性。他认为,我们没有看到客观物质实体,这个“实体”概念可以存疑。包括人格,一个人没有实体性了,那么人格的同一性如何理解?……没有人格同一性那还得了,那不天下大乱了!……人只相信自己的知觉、印象,就会没有任何规律可言。(p6-7)
7、为了回应休谟的这个难题,康德沉默了十年,思考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科学知识大厦的可靠性根基到底去哪里寻找。……直到1781年,康德才发表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发表以后震惊世界!……以往的知识都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真理定义,“知识就是观念和对象的符合”。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就是观念和对象相符合。但康德认为,这样的定义在休谟的攻击面前已经站不住脚了。你怎么知道你的观念是符合对象的?你凭什么断言你的观念是真理?观念是观念,对象是对象,你看到的还是你的观念,对象在你观念里就是一种观念,已经不是对象了,你怎么知道你的观念和对象是相符合的?所以,对象在休谟看来只能是存疑。……我们的观念要符合一个外在的对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观念要符合一个我们自己建立的对象是可能的。(p8-11)
8、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有知识的,人有理性,这个理性有一套固有的结构,人具有这套理性的结构就有了主体能力,就可以去认识……所以知识体系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不在于反映了外在的对象,那个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但知识之网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毕竟符合于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对象和对象观念。这个对象观念是显现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他称之为现象界——现象世界。(p11-12)
9、康德和休谟有一点区别,休谟认为物自体是否存在也不可知,但康德认为物自体还是存在的,但不可认识。(p12)
10、休谟把这个因果性给摧毁了……在康德看来,因果性有一种先天的必然性、普遍必然性。……康德认为这种先天断言的肯定性不是基于人的习惯……这不是一种后天的习惯,而是一种先天的认识结构……人有一套先天的先验的结构,科学家一手持着这样的先天结构,另外一手拿着由外界所获得的感觉经验、知觉、印象等材料,面对自然界的种种千变万化的现象,用主体的一套规范去审问自然界。(p13-14)
11、人在自然界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教师,人为自然界立法,不是自然界为人立法。人首先定了一套法律去规范自然界,让其守法,最后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知识体系相当于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人为自然界立法是康德的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往的人总是采取观念符合对象,类似于太阳围着地球转这样一种思路,但自康德之后,他认为他进行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观念。……这个可靠性和普遍必然性是人的认识主体能动地建立起来的,所以康德把人的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引入了认识论,客观对象即人的认识对象不是在那里等着你去认识,而是由你的认识过程能动地建立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首先是符合于主体,然后人的认识的观念才当然地符合于这个对象。(p14-15)
12、普遍性就是普遍适用性,必然性就是不可能有相反的情况,因果性普遍适用于任何一个经验和现象,而且必然适用于一切现象。“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智慧,一个傻瓜也知道一件事情有原因,这是人的基本认识结构。科学知识的信念就建立在这个上面。你要是把人所皆知的这样一种规律也否定了,那科学知识确实就没有什么根基了,就垮台了。(p15)
13、所以康德就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法庭,他认为人为自然界立法,立法之后的具体断案还有种种具体的情况,如石头热是太阳晒的还是火烧的,究竟是哪个原因,当然有后天的经验去断定。人为自然界立法,并不是说人把所有的具体情况都决定了,但是他建立了一个“法庭”,所有发生争论的事情,如太阳晒热、火烧热等具体的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法庭”打官司。……这是一个理性的法庭,如果你可以解释得头头是道,你就可以说石头热是太阳晒的结构,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但是如果这种解释跟其他因果关系冲突了,例如说,太阳并没有直接晒到石头上,你就得考虑了,是否换一种解释。但任何解释都必须建立在一切发生的事都有原因这一条上,你不能说有一件事没有原因,不能用它是纯粹的奇迹等来解释。所以人为自然界立法并没有解决一切科学知识的问题,它只是给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根基。这个并不能决定所有东西的可靠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基础,所有东西都要在这个法庭里面打官司。这是康德对休谟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以一个问题的方式展开的,这个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p15-16)
二、《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14、《纯粹理性批判》提出的总问题,也就是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p16)
15、先天和先验是有区别的,先验的当然是先天的……但是先天的不一定都是先验的。“先天的”是说我们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就可以先天断言它。“先验的”除了可以先天断言之外……可解释为关于先天的先天,关于先天的先天知识就是先验知识,先验的知识比先天的知识层次更高,它是对先天知识的反思,即先天的知识如何可能。先天的知识还不一定是知识……比如形式逻辑……不管大前提,很多错误的前提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所以形式逻辑是先天的,但它不一定是知识,因为它不管对象的问题,完全脱离经验。先验的知识肯定涉及关于对象的知识,只有关于对象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先验的就是关于对象的知识如何可能。所以先验的知识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知识,关于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知识,它先于经验,但是它又不脱离经验。……先验和先天具有一种层次上的区别。(p16-17)
16、按康德的说法,谓词已经包含在主词里面的判断就叫分析判断,谓词不包含在主词里面的判断就叫综合判断。……一切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他认为“物体是有广延的”是分析判断,但是“物体是有重量的”是一个综合判断,因为形成一个“物体”的概念不一定需要“重量”的概念。在当时牛顿物理学的背景下,人们认为重量是引力的产物,所以一个物体脱离了地球引力可能失重,就可能没有重量,但是它有广延。宇宙飞船到太空就会出现一种失重的状态。(p17)
17、康德认为,一切综合判断的特点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一切分析判断的特点就是……它只能澄清知识而不能增加知识。……一个不能增加新的知识但是有普遍必然性,一个能增加新的知识但是又没有普遍必然性。对此英国的经验派和大陆唯理论派双方各执一端。(p17-18)
18、康德力求在两派中作一个调和,在莱布尼茨和休谟之间作一个调和,在判断的理论方面也作一个调和。……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判断既是综合的……同时又带有普遍必然性、先天性?……如果有,那么这个判断就是先天综合判断。这就是他说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来由。(p18)
19、康德通过对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认为有这样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认为一切纯粹数学判断,一切数学的最高命题都是先天综合判断。……认为数学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这是康德的一个创见。至于自然科学里面的基本命题也都是一些先天综合命题,像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但是“一切发生的事情”这个概念中没有包含“因果性”这个概念。……但它可以先天断言,它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可见,以往的自然科学和数学都有先天综合命题作为它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是失败的,至少它们最终经不起休谟这一击。……即是它们全都失败了,但作为一种自然倾向,形而上学已经包含了先天综合判断。……所以康德认为先天综合命题存在于任何一种科学里面,甚至在一些失败的科学里面。(p18-20)
20、但康德问的不是先天综合命题是否存在,他问的是先天综合命题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因为这个命题涉及科学知识如何可能。(p20)
21、《纯粹理性批判》总的来说是两大部分,一是先验要素论,一是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是主体,它对人的知识体系、知识大厦的元素、原件进行一番拆分,拆下来一个个分析、检查。这也是当时经验自然科学流行的做法。……认识结构要素通常分析为两种:一个是感性的要素,一个是逻辑的要素。感性的要素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感性认识,逻辑的要素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理性认识。(p21-22)
三、先验感性论
22、感性论是研究人的感性能力所获得的知识的结构……认为感性具有先验成分,这是康德的一个首创……感性的形式框架即是时间和空间。……人的认识主体先有一套时间、空间的结构,然后用这套结构去接受物自体刺激人的感官所形成和产生的那些知觉印象,这才叫作感到。……如果把时间和空间作为一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单独把它从知识里抽出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用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数学如何可能、几何学和算数如何可能。康德时代所谓的数学包括连个方面:一个是几何学,就是关于空间的知识;一个是算数,是关于时间的知识。(p22-23)
四、先验逻辑之一:先验分析论
23、康德认为在人的知识里面有两大成分,一个是后天的成分,一个是先天的成分。后天的成分是经验性的,是后天获得的,先天的成分是由人的主体预先提供出来的,这两方面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人的知识,缺一不可。所以他认为经验派和理性派双方都有片面性,知性和感性、知性和直观缺一不可。“知性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这是他的一句名言。……自康德之后,人的认识就不再被看做是被动的,而是人主动建立起来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发挥。(p27-32)
24、时间是内部直观的先天形式,空间是外部直观的先天形式。……时间可以没有空间,它表现为人的意识流……人的意识不占空间,我可以天马行空……并没有真正占据空间。……所有看内部和外部的事物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流,是意识的时间过程,所以内部的时间要比外部的空间更占优势。康德对时间的这种看法很有意思。时间相当于后来人们所强调的认识的主体性……像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主张时间和自由意志具有同样的结构。人的自由意志和时间具有一定的关系,跟空间是相对立的。空间更多地表明人受到的限制,人受到空间环境的限制。空间更多地表达为一种必然性、一种命运以及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康德没有意识到那么多,只是认为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时间要比空间更具有根本性。(p36-37)
五、先验逻辑之二:先验辩证法
25、“超验的”……与……“先验的”概念,都来自于拉丁语。……都是超越于经验之上的意思。但在康德看来,超验和先验是有区别的,先验的东西超越于经验之上,却要应用于经验之中;而超验的东西超越于经验之上,却不能够应用于经验之中,而是完全脱离经验的。……也有人翻译成“超越”,但都是一个意思……是有关自在之物的,有关物自体的,不是有关经验世界的。(p48)
26、从物自身角度来说宇宙中是可以有自由的。比如你把人看作是一个自在之物,人作为现象也受因果律的支配,但是人作为自在之物,他有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一种设定,不可能用经验来证明,但用经验也反驳不了。(p49)
27、如果人按照一个严格的因果性在运转,那我就不是一个责任主体了,有功有过都不在我。……同一个行为你可以用因果性认识,但是你也不能够否认也可能用自由来加以解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物自体,你没有认识到这个物自体,你有什么根据来否定它呢?所以在认识领域可以预留下一个空位,虚位以待。这个空位在认识领域对自然科学家没有任何贡献,但是一旦进入实践领域就很有用了,空挡就会被充实起来。(p51)
28、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康德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康德的三大批判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问题。他的整个哲学都是为研究人的自由;他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自由;他把科学的范围限制在现象界、在经验领域,也是为给自由留下地盘。所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里说:“我们要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位置。”如何“悬置知识”呢?你要把知识的所有领域都考察一遍,建立和划定它的范围。有自由意志就有信仰了……(p51)
29、人具有理性,人比所有的万物都要高,是万物之灵长。所有的万物都为人所用,当然人就意识到自然界是被安排好的,都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安排。这是谁安排的呢?当然是一个比人更高的上帝。由自然界的合目的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最古老、最朴素的一种证明。(p52)
六、先验方法论
30、所以康德说,真正的纯粹理性还不是理论理性、思辨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为它不受经验的限制。……因此真正的法规就是实践理性的法规,实践理性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理性,它是完全不受感性的东西约束的。所以康德说实践理性要高于理论理性。(p60)
31、康德说,我的未来形而上学不是没有建立,我的《纯粹理性批判》同时就是我的未来形而上学,虽然它是一个导论,但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建立,里面已经勾勒了一个大体轮廓。(p63)
七、《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
32、康德处处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康德的好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些矛盾。……他解决的方式无非就是把现象和物自体区分开来,不让它们接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矛盾了。他恰好暗示了后来的人,推动了辩证法的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产生就是从康德那里脱颖而出的。……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不再是毫不相干的,道德律可以在自然界实现出来,你可以采用自然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难道一定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吗?按照历史的规律来实现道德的目的也是可以的嘛。(p67)
33、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发展康德的哲学,主要着眼于他的认识论的形式方面,着眼于他的形式主义。弗莱堡学派主要着眼于他的价值论方面,着眼于他的《判断力批判》和他的《实践理性批判》这一方面。马堡学派着眼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并在形式主义的方面发展出后来的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的倾向。……所以有人说,康德就像一个蓄水池,所有以往的哲学都流向他这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来。(p67-68)
第二讲 《实践理性批判》
一、《实践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的程序
34、《实践理性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是按照同一个“建筑术”建构起来的,但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纯粹理性批判》是探讨知性的认识能力……要从感性出发上升到先验逻辑……这是层层上升的……但《实践理性批判》不同,因为实践理性跟感性的世界没有关系,涉及的是物自体的问题,涉及的是人的自由、人的实践能力、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等问题。人本身不是从认识出发,不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然后才有意志,才有欲望。人一开始就有欲望、就有意志,然后把自己的欲望和意志表现在经验世界,体现并实现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感性的世界造成影响。所以《实践理性批判》不能从感性世界出发,而必须自上而下,从上面出发,降下来。这与《纯粹理性批判》是从下面升上去不同,《实践理性批判》从一开始就要从最高的地方降下来。所以它要从分析论中的原理分析出发——分析论中的原理分析是最高境界,……纯粹理性批判有了这些原理,它所作用的这个对象不是现实的感性经验的对象,而是一个概念的对象。这就是善和恶。……如果你把善恶当作自己的对象来进行实践,那么在感性世界中,你当然会受到影响。……感性的影响是你的后果,这不是你事先考虑的。你事先并不一定去考虑感性的后果,尤其是道德行为,是不应该考虑后果的,只有日常技术行为才要考虑后果。(p69-70)
35、康德在道德方面是一个动机论者,他要考虑的是动机。不过在康德看来,这个动机也有一半是在感性这边的……他是从先验的原理下降到人的感性……具体来说,就是人的道德实践,它所伴随的是一种对道德的敬重感,即道德情感。……所以它是从原理分析经过概念分析下降到感性的。这与《纯粹理性批判》的程序恰好颠倒。(p70)
36、纯粹实践理性还有一个辨证论,是谈人在实践中的两种取向……道德和幸福。……斯多葛派是主张道德本身就是幸福……这是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观,也是一种理性派的道德观。伊壁鸠鲁主义是一种经验派的道德观——幸福主义,认为幸福本身就是道德。……康德认为这是一个辩证的二律背反。(p70)
二、《实践理性批判》的标题
37、《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探讨的是理性本身在纯粹的形式下何以可能建立知识。……首先抱有一种反思的态度,甚至是怀疑的态度……《实践理性批判》不是对纯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它是对一般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一般的实践理性包括我们通常所讲的日常实践……非常世俗化,当然也包括道德。纯粹理性批判是一般实践理性中最纯粹的部分,它仅仅包含道德。……它的根基是纯粹的自由意志。一般实践理性的根基是一般的欲望。欲望跟意志还不一样,欲望里面可能包含一些感性的成分,一些本能的东西。……但纯粹实践理性是更高的层次,它摆脱了一切世俗的感性的需求和感性的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它是为自由而自由,为意志而意志,为贯彻意志而立法,建立自己的意志的法规、法律。(p71-72)
38、康德把这一批判的标题叫“实践理性批判”,意思是说,它不是要批判纯粹实践理性,纯粹实践理性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不需要批判。……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做什么可以受束缚,我想怎么做却可以不受束缚。……而是仅仅通过这样一种纯粹实践能力来考察和评价一般的实践能力,或是全部的实践能力,包括日常的一些具体、世俗的那些目的,那些目的的行为。……人具有一种纯粹的实践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是活的,人跟物不同,可以有一种意志行为。(p72-73)
三、导言:自由和道德只具有实践意义,不具有认识意义
39、康德认为我们虽然不能证明有自由,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不能证明没有自由,所以我们有理由、有根据提出一个先验自由的理念放在那里。……自由是没办法认识的,凡是认识的都已经处在必然之中了。如果要给自由找一个原因,那这个自由已经不是自由了。……他要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负责。所以我不必去认识它(自由)。……自由的内容在认识意义上是空洞的,但在实践的意义上是充实的。(p73-74)
40、“自由”的概念……就成了两大批判之间的一个“拱顶石”。……最关键的中间的石头,那个石头一去掉,两边都会垮掉。……自由是康德所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康德主要探讨的甚至终身研究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或者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p75)
41、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导言中,康德再次重申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康德的这两大批判,实际上处理的是人类的两种能力,一种是知,一种是意,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处理的是情。……所以他的三大批判合起来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类学,因为人具有知、情、意。(p75-76)
42、意志就是自己实现自己的对象的能力。……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的运动是由对象所决定的,……具有因果必然性。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意志是目的的活动,……我这个策划如果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话,那么它不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来策划的,而是根据意志本身的规律来策划的。我做事不管符不符合外在的规律,我首先要对得起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根据一种内在的目的来影响外部世界,这种能力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所以这种实践理性的能力不需要批判,不需要考察它何以可能,这种良心何以可能。良心直接的就在人心中……你是一个人就有良心,因为你有理性。这是可以直接确定的。(p76-77)
四、分析论之一:原理分析
43、在分析论中,康德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原理,一种是主观有效的准则,一种是对一切意志普遍有效的法则。法则是客观的、普遍的,它对任何人都有效,而准则是主观有效的。……总而言之,法则是更高的,准则没有普遍性,每个人的准则都是一次性的,都只适用于自私的目的,而法则是可以成为普遍的道德律的。(p77-78)
44、任何把法则区分出来?康德提出了四条定理。四条定理中的前两条是消极的,是指我不能怎么样。第一条定理是说,你不能把你的现实的一个欲望的对象作为你的意志的动机,你的意志的动机不能建立在一个现实的对象身上。……把功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就不能够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因为功利总是千差万别的。哪怕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实践的法则。
第二条定理是说,个人的幸福也不能成为法则。……所以幸福主义伦理学更强调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幸福感。但这个幸福感……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所以这个估计也不能成为实践理性的法则。
第三条是这样的:“能够提出这样一条实践理性的法则,就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成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要使你的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在比较粗糙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相当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立足于人的欲望之上的。
第四条定理是自律的原则,是说上面这样一条道德法则不是外人强加给你的,而是你的自由意志自己立法制定的。……这样一条道德律,是自律而不是他律,不是为别的目的,它就是为道德而道德。……自律的原则是康德的最高原则。自由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可见,意志中纯粹意志是最高的,是人生的最终的意志。人生必须有一个一贯的原则,而不是总是片段地使用自己的自由。如果那种片断的准则支配了一切行为,那么一生都在动摇,并表现出双重或多重人格,这看起来很灵活,其实是远远谈不上自由的。(p78-82)
45、功利主义、幸福主义都不能成为法则,真正成为法则的是道德律令。道德律令的根据就是自律。……你要使你的意志的准则始终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你要能够自律,也就是通常讲的听从良心的呼唤。……人是有理性的,跟动物不同……这个实践理性就是人的自由行为的一个摆脱不了的必然的法则。这个法则总是在人的内心起作用。……虽然人的行为掺杂了很多感性、欲望、情感的东西,是一种不纯粹的理性,但是不纯粹的理性之所以是理性,还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纯粹的理性。纯粹实践理性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什么理性,而是一般的实践理性中的一个层次,一个最高层次,一个必然的成分。不纯粹的实践理性和一般的实践理性,只是把纯粹理性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混杂起来,使它变得不纯粹而已。……人为什么有良心呢?就是因为人有理性。……一般的动物做了坏事,它不会反省;人做了坏事,他总有一点感到惭愧,感到有罪。这是原理论。(p76-84)
五、分析论之二:概念分析
46、善和恶只关乎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而跟它里面所包括的经验材料没有关系。……它只涉及人的动机……动机还是包含了效果的,但它不是从效果方面来看的,而是立足于动机,用动机去包容效果。……善的动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我们不能说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p84-85)
六、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47、动机就是促使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机缘,是行动的动力,属于感性的。……当然你可以按照概念去决定自己的行动的动因,最后可以追溯到道德律。但具体的感性的人要有一个动机。动因与动机不一样,动机是促发真正行动的感性作用的推动力量,动因则是在一切感性的后面起作用。……就是说,从上面降下来,你已经有了自由意志、有了道德律的时候,你怎么把道德律实现出来,这需要一个感性世界中的动机,促使你能够现实地作出一种合乎道德律的感性行为、实践行为。这个动机是一种情感,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带有情感的。(p87-88)
48、道德律本身有一种敬重感。……我的一切情感与道德律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通常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是永远达不到那种境界的。敬重感中还包含了一种喜悦,有点像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讲的“崇高”。“动机”这个词就是“发条”的意思,道德的动机就好比钟表的发条,能够推动人去做有道德的事情……道德的动因就不是情感,而是自由意志。……道德的源泉只能是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就以这样一种道德情感作为结束。(p88-89)
七、纯粹实践理性的辨证论
49、辨证论讲到两种幸福观——幸福和德性。……但是至善,不仅仅是要在道德上高尚,而且要效果好。康德在考虑道德的时候一般是不考虑效果的,效果是感性的。但康德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律不考虑效果,就使道德成为一种最高的却不是最完满的善,最完满的善是要考虑效果的。至善就是最完满的善。……这个意义上的至善,是道德和幸福相配。(p89)
50、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都把道德和幸福的关系看做是一个分析的关系,但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综合判断,“德福一致”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必须有更高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灵魂不死。……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上帝。(p90-91)
51、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两个假设是“德福一致”这个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它是通过理性推出来的,是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推出来的。……所以在这两大悬设之外还有第三大悬设,或者说最根本的悬设——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的悬设是最根本的。……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必须要有德,要有德又必须追求一种完满的善,即不仅仅是道德高尚,还要有与之相配的幸福,而要有这样完满的善就必须要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当然这是一个信仰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认识的对象。有了自由意志的人就会有信仰……道德本身可以没有宗教,它可以独立,但宗教不能没有道德。而道德一旦确立,它必然会推出宗教。道德本身是自足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会逐渐地走向上帝,走向宗教。这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所阐明的道理。(p91)
第三讲 《判断力批判》
一、审美判断力批判
52、《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认识论的,《实践理性批判》是关于道德以及宗教的。《判断力批判》的主体部分是关于审美的,除了审美以外还有一个目的论——自然目的论,所以《判断力批判》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审美批判力批判,第二部分是目的论判断力批判。(p93)
53、康德认为他的哲学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的问题,是由《纯粹理性批判》加以解决的。人能够知道什么呢?能够知道的都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这就是道德问题,是由《实践理性批判》加以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可以希望什么”,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由他的宗教学加以解决的,但实际上实践理性批判后面一部分已经为宗教奠定了基础,从“应该做什么”已经过渡到“可以希望什么”这方面去了。这三个方面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p94-95)
54、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审美能力得到了提高,于是从人类的审美能力就可以猜到人的道德,所以美是道德的象征。……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搭起一座过渡的桥梁,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虽然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但理论也可以暗示实践,实践则应当体现在理论中。……审美和艺术的自由还不是纯粹的自由,但我们可以抓住它进行彻底的思考,意识到人其实是有一个纯粹的终极的自由,这样才能建立起道德律,建立起道德意识。……第三批判的桥梁作用,体现在认识和实践两者之间的一个领域,康德认为就是批判力批判的领域。(p97-98)
55、批判力就是知性运用到感性对象之上的那样一种能力。……在认识领域的批判力起的是一种规定性的作用……一个医生在医学院里学了很多书本知识,现在他拿着书本知识要进行临床实践了……对具体场合进行规定。所以规定性的批判力有一个特点,它是从普遍到特殊,先有普遍然后把普遍运用于特殊的场合。康德认为这种批判力的结果是形成知识。(p99)
56、反思性的批判力是从对象反思到自身的原则,为它寻求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客观对象的普遍认识、普遍知识。……主体有一种先天的普遍性,人性中有一种先天的普遍性,这种反思的批判力通过反思而有所体会,所获得的是一种美感而不是知识,是一种主观感受。这种主观的感受又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感受,人性的普遍性的一种感受。这种反思的批判力回到人的内心,感到了一种普遍性的愉快。(p100-101)
57、审美的批判力的诸认识能力的活动不是为了认识外界的某个对象,相反,它是要从外界的某个具体对象返回到主体的内心,它是以内心的诸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本身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审美、欣赏不是为了受教育……我们是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心态、消遣娱乐的心态、放松的心态,走进电影院。电影所起的作用就是激发我们的自由协调的活动,至于它有什么认识上的意义或道德上的意义,我们不考虑,一考虑就败坏了欣赏趣味了。(p102)
58、反思的批判力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审美。审美又称之为鉴赏、或者鉴赏力。……所以审美批判力批判就是要研究人的鉴赏力和人的高级的鉴赏能力何以可能的问题。(p103-104)
59、审美就具有这种性质,属于这样一种合目的性的活动,后来人们把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看作是审美的本质特征。……只有抱着游戏的心态去欣赏,才是真正审美的态度。……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对最美的风景也无动于衷……审美就是这样,只有无目的、无利害,才能够进行欣赏。(p108-109)
60、审美与科学知识不同的地方就是,审美的普遍性人人认同,但不是通过概念达到的。牛顿物理学大家都承认,是因为牛顿物理学的概念具有普遍性,大家在上面认识到的是同一个对象。蒙娜丽莎大家都认同,很美,但它不是通过概念,它是通过感受。……想通过概念的贩卖来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往往是失败的,不但不能引起别人对这个作品的美的感受,而且令人怀疑这个评论家自己到底有没有感受。……欣赏就是凭感觉,我被它感动了,我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来,那就是欣赏;能够说得头头是道,那往往就不是欣赏了。所以通过概念来欣赏是非常荒谬的。(p110)
61、美的对象具有形式的合目的性,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欣赏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欣赏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我们常说某种东西中看不中用,中看就是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只要中看就够了,至于中不中用那是实用的态度。……康德把这个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称之为“自由美”,也就是摆脱了对内容的考虑的美。要考虑到内容,那就不是自由美了,那叫“依存美”,或者译作“附庸美”。这与西方传统的形式主义美学有很深的渊源。……对称、平衡、黄金分割律等,这都是从形式上来考虑的。……至于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从道德的眼光,从神学的眼光,从认识的眼光,从实用的眼光,你都可以评价,但是从审美的眼光,那就只是着眼于它的形式。这是审美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形式要具有一种合目的性,它要合乎人的眼睛的需要。(p110-111)
62、模态是讲必然性的。……它的根据就是共同感。……审美应该有共同感,虽然事实上不见得有,但是审美的目的是必然要趋向于共同感的。……审美就是为了传达情感,形成共同感。康德甚至把鉴赏定义为“对一个给予的表象的情感不借助于概念而能够普遍传达”。我们可以设想人类未来的目标,是越来越接近这种共同感的,人类在情感上会越来越达到相通,互相理解。(p112-113)
63、对美的鉴赏就是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协调活动。……光有想象力还不行……审美不是胡思乱想,必须有知性对想象力加以约束。……把它凝聚起来。……使想象力成形。……通过审美教育让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进入道德境界,审美欣赏是进入道德境界的一个预报阶段。(p113-115)
64、欣赏崇高首先要经过一种痛苦,就是知性面对无限感到无能为力,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然后经过理性训练的人能够调动自己更高的理性能力来把握无限,他的理性与想象力达成一种自由协调活动。……审美者就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愉快。(p117)
65、崇高主要有两种:一是数学的崇高,一是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就是面对自然界的无限的量、庞大的体积、广阔的地平线,我们感到人的渺小。……但人在调动其理性后就可以想到,尽管自然界有如此巨大的体积和数量,但这种物资的体积是盲目的,是无理性的。人的理性可以更高,人的理性可以超越它,而且从性质上来说,人的理性比珠穆朗玛峰更具有无限性,可以超越整个物质世界而达到精神层次、道德层次。……一个经常欣赏珠穆朗玛峰的人,他心目中也可以形成一种人格,一种崇高的人格,而具有这种崇高人格理想的人在欣赏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就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力学的崇高就是对力量的一种畏惧。……理性的力量是无限的……而自然界的力量是盲目的,所以人的力量可以胜过自然界的力量。就像巴斯卡说的,人是风中的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有理性的芦苇。……美不是道德……但它象征道德,它可以激发人的道德。(p117-118)
66、美的判断都是先天综合判断。……一个审美的判断首先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主观的,但看起来好像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又是一种主观的客观。……具有一种主观的普遍性,好像是客观的一样……它就具有一种人人都会感到美的必然性倾向。……康德认为是因为人有共同感。这种共同感是先天的……这是审美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除了这种先验的演绎以外,审美判断还有另一方面的演绎。……我们还有一种客观的经验手段,使我们能够现实地达成共识,这就是艺术。这种演绎就是经验性的演绎。(p119-120)
67、所以康德认为,人的内心的鉴赏力代表了人具有道德素质,因此比艺术要高,因为艺术家不一定是道德的……但一个能够欣赏自然美的人,一个能够在自然界的风景中感动得落泪的人,肯定具有道德心。……他认为,最纯粹的美应该是不带任何目的的,到自然界里面欣赏一片风景,就不带任何目的,但艺术美从创造出来就带有目的。……人们去欣赏的时候看不出它有什么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只是为了欣赏它的美。它越是没有表达出它的目的,人们就越觉得它好。所以艺术品好像是没有目的的,但实际上是有目的的,艺术家把他的目的隐藏得很深。在这一点上,艺术品要低于对自然美的审美欣赏。(p122-123)
68、经验派美学认为“口味面前无争论”。……但理性派美学总是要找一个评价标准来……古典主义美学最喜欢搞这一套……康德认为两派各有道理,但是两派都不全面。……“审美的理念”就可以作为标准。……共同感的理念要求大家都要感到美,为了达到共同感,你可以设定一些暂时的概念去进行评价。……对艺术品的好坏的评价,大致上会形成一个标准,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所改变……但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之内,毕竟有一个相对的好坏标准、美丑标准,这些标准是通向审美的理念的。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艺术标准方面的二律背反……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有相对的标准、有无限的标准,这就是康德的回答。(p123-124)
二、目的论判断力批判
69、人们通常把《判断力批判》当作康德的美学著作,严格说来,这不完全对。康德其实不把美学作为美学来讲,而是把它作为判断力批判的一个部分,他的《判断力批判》一部分是美学,一部分是自然目的论……讲美学的原理和人类情感的先天原则是很重要的,但从它的意义来讲,从美学的先天原则推出自然目的论的原则,这一点更为重要,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很大。……自然目的论涉及历史观,包括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涉及自然科学里目的论的讨论。当代自然科学界一直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科学问题,就是自然界的目的问题。(p125)
70、我们可以在自然界中自然天成的各种对象上看出某种目的、某种目的性,而且是某种实实在在的目的。比如说有机体,有机体是一个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目的论的产物,我们对有机体总是怀着一种有目的的观念去看它。如果我们对有机体仅仅从机械论的观点去把握,那是把握不了的。……有机体每一个部分表现为服从整体的目的,每一部分都以整体为目的。(p128)
71、一个艺术品,一个好的艺术品,它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多余的,每一部分都是那么天衣无缝地符合它的主题,促成它的主题。……所以艺术品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种合目的性的观点,就是部分服从于全体。……但有机体的观念和艺术品的观念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有机体碰坏了,比如说你擦破了块皮,过两天它自己就长好了,它能够自己修复自己,自己生长自己,而且这种自己修复不但是每一部分为了整体,还是整体为了每一部分。……关于有机体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自组织”……自组织的观点体现出一个目的论的概念就是内在目的论的观点,即自己以自己为目的。(p129-130)
72、通常讲的目的,除了内在目的还有外在目的,这个外在目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目的。……外在目的论的目的和手段是相互外在的。而内在目的论的目的和手段是内在的……互为目的,同时又互相利用,融为一个整体。……唯独内在目的是不能还原成机械论的。(p130-131)
73、在康德的时代……科学的观点就是机械的观点。……他认为生物学这个东西不能用严格的牛顿物理学来解释它……康德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尽量运用牛顿物理学去解释,解释不了的时候就动用目的论。采用目的论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动物学家只有把鸟的身体看成是有目的的才能解释。……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把握有机体的规律、生物学的规律。……我们就想到用目的论去解释,其意图就是暂时弥补机械论在解释上的无能为力……在康德看来,有机体也好,动物、植物也好,它们归根结底服从的自然规律还是机械因果律。而目的论只是我们人类在看待复杂的有机体时的一种无奈之举。这种无奈之举不是针对自然科学来说的,它甚至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但对人类本身来说,它是有意义的。……这种目的论的观点恰好表明一种反思的判断力,也就是反思到我们人类两种认知能力相互之间的一种协调活动。……就是知性和理性。知性的作用就是把握具体事务的规律,而理性能够把握无限的整体。……实际上是把人文的成分加入到科学之中,弥补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认识不能达到某些地方的缺陷。(p131-134)
74、康德从有机体的观念进一步推论……在一个有目的的有机体身上,我们要追索它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有机体跟它的环境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这样,本来是有机体内在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外在的目的。……整个自然界也是有目的的……对有机体来说,这些外部环境是一种外在的手段,它与这些外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时一种外在的目的论。……这些植物、动物相互之间处在一种毫无目的关系之中,它们相互利用,但没有一个整体目的,也不以哪一个为目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把人看作是高于万物的……所以人是万物的灵长,而凡是接近人的,就比那些更远离人的生物更高级。……最后他得出结论,人为什么高于一切是由于人有文化,人有理性……所以理性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人的生存,更在于人的文化。(p134-137)
75、自然界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康德最后得出他的结论:所有科学、艺术、法制最终都是为了启发人,让人最后反思自己的道德素质。……道德律是一种绝对命令,是自由意志本身的一种和谐。……有了法律,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道德,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应该尊重他人。……康德认为,整个自然界发展的目的唯有在道德方面能够找到自己的绝对的目的和终极目的。他认为人类的道德心通往宗教、通往道德神学,通往伦理神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上帝的各种证明进行了批评以后,认为唯有一个对上帝的存在的证明还有一点点道理,就是对上帝的目的论的证明即自然目的论的证明。自然目的论的证明实际上不是诉诸证明,而是诉诸人的道德情感。……这种对上帝的证明,康德认为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但在情感上是非常吸引人的。……整个自然界表面上好像是一种自然目的论,但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目的论,因为自然界只能以人的道德作为终极目的,其他的自然物都不足以成为自然界的目的。……所谓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本质是证明我们出于道德的目的必须相信有一个上帝。……但道德本身是不需要上帝来建立的,而它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必然会设定一个上帝。上帝是建立在道德律之上的。……康德对他以前的基督教的信仰作了一番重大的改造,认为不是你信仰上帝你就会有道德,而是你有道德才会信仰上帝;不是用《圣经》来解释道德,而是用道德来解释《圣经》。(p139-143)
76、应该说康德的道德思想是形式主义的。这种形式主义受制于人的内心的一种无法认识的能力即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意志的连贯性。……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道德律是空的,是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的时候,康德认为这就是一种人类的理想了,人类的理想社会以及永久和平就会有希望了。永久和平也是一个理念,永远也不会来到,但人们可以向它不断地接近。(p145)
77、作为科学家来说要尽量用机械论来解释一切……目的论只是一切努力之后的权宜之计。……前面一种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我们把目的论看成是对机械论的补充……这种目的最终如何构成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可以对自然界有一种道德眼光或者说是审美力。道德的眼光和审美的眼光在这里融合在一起了。我们认为自然界是非常壮美的,对这种美产生了一种惊异感……前面一种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我们把目的论看成是对机械论的补充;后一种是道德的观点,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机械论看成是目的论的一种手段。……整个宇宙是一个以道德为目的的大系统,但其中又有机械关系,这与所有的自然科学是不冲突的。
78、所谓科学、科学精神其实都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成分,我们可以从科学的眼光去看整个自然界,但最后要归到人文精神的眼光,从人文的眼光得到解释。所以人和自然界应该被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以人为目的,自然界向人生成,自然界生长为人,人是自然界的目的。但在康德那里,人的道德是自然界的目的,道德包含了一切。要达到道德,必须经历许多阶段,包括人对幸福的追求、人的意志、科学艺术、社会法治等,这些都是为道德的生存所作的准备。(p148)
79、自然界好像有某种合目的的安排,安排自然和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地发展。当然这个天意是人们想出来的,是从自然界里看出来的,自然界本身没有。……一个有道德的人能看出来……这种观点后来在黑格尔那里被发展成一种所谓的“理性的狡计”。……“理性的狡计”在这里就体现出了它的背后的力量。(p149)
著作简介
《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2011年10月第4次印刷;定价:20元)是一本系统介绍康德三大批判的读物,是作者根据2004年10月应邀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所作的有关康德三大批判的系列讲座的录音稿审定修改而成。作者从自然科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生动形象的事例出发,通俗地解读了《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并在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中展示了康德宗教思想的特点,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提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现代意义。《康德哲学讲演录》内容精妙,可读性强,对康德哲学研究具有现实性。
作者简介
邓晓芒,男,湖南耒阳人,1948年4月7日生于东北。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7年恢复高考,年龄超过了本省大学报考规定的要求。1978年以初中学历直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考试成绩合格,但因父母“右派”尚未平反,专业受限,政审没有通过。此后他重新选择了报考的专业,花了8个月的业余时间苦学他认为代表哲学最高水平的德语,终于在1979年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先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等。2009年12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来源:淦河家园
编辑:王奕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10 20:40
【案例】邓晓芒:从一则相声段子看国人的思维方式
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方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小生长在一个不讲道理的文化环境里,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讲道理,而是不会讲道理,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我们先看一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鼓》: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小,叫声为什么那么大?
乙: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声都大。
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大脖子憨,怎么不响呢?
乙:那它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它都不响。
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竹子编的,它怎么就响呢?
乙:它虽然是竹子编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响。
甲:竹子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子也是竹子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不响?
乙: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
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又响呢?
……
甲:泡泡糖为什么响?
乙:那是有胶性的,才响。
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
乙:那它挨着地了,不响。
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又那么响?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一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一团“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日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
其实,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为人们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大量的空间,而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片。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动脑筋,但中国人动脑子只动一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气磅礴,也可以是极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脑子,只需要用“心”。
人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人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诗性的负面。中国发生的种种怪事,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白白地过去了,而必须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边的人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读研究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黑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一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黑格尔都是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然而,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对康德哲学锲而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而感受到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对周围非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光靠说怪话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一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所以它是一种反思,一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一种重建。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在读康德的书时内心常常有一种感慨,觉得这正是我们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他所做出的解答,而是指他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我力图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把他这一套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学到手,然后用来影响国人。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因此,康德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在这里,所谓“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里不仅仅包括知性,而且还包括超越的“勇气”。为什么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因为知性作为一种被“运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动性,它只是逻辑理性,而非超越理性。它只有作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发挥其无坚不摧的作用。超越理性的勇气首先体现为怀疑精神,即像笛卡尔那样,对一切既定的规范原则加以摧毁。这就是批判精神。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第一个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体现了大智大勇。而这种勇气最终归结到人类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认知上和行动上,就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由自己亲证的道理,都愿意做自己自愿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环境、历史、传统给他预设的樊笼都是不能长期忍受的,都势必要加以突破。
那么,有了这种勇气,如何做呢?如何运用自己的知性呢?其实每个人只要是成人,都已经具备自己的知性,也会懂得如何去做。但这里做一点归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我认为,一般知性的运用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良好的记忆力,第二是敏锐的计算能力,第三是综观能力。
先说记忆力。是人都有记忆力,甚至动物也都有一定的记忆力,有的动物比人的记忆力还强。但动物的记忆力是外在的,只是外部事物刻在动物神经系统或大脑中的刻痕;而我这里说的记忆力是指内在的记忆力,是人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的记忆力,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念头不忘记,而能够保持住,随时能够返回。这是动物不具备的,动物只记得外界的事物,它的记忆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生存条件,动物不记得自己的记忆。动物可以记得一条路,一种谋生技巧,一个对它好的同伴或主人,当这个主人在它面前时它可以认得出来。但是动物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主动调用自己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和现实中的事物作比较、进行抽象或类比,从而凭借记忆进行思维活动。而人的记忆具有反思的意味,人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对这件事运用思维,记忆是反思的前提。自我意识本身就已经是内在的记忆了:当他把自己看做对象的时候,他记得这个对象当初正是自我设立起来的;因此他也可以在这个对象身上随时返回到自身。
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这种内在的记忆力是特别要注意训练的,否则你无法进入。当你跟着康德的思路前进时,你要尽可能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在理解后面的话时,要时时把前面说过的摆在面前,加以比较。如果不记得了,就要翻到前面去,加以查对。因此我在翻译康德的书时,特别强调应该有详细的术语页码索引,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查证。《纯粹理性批判》后面有50多页都是索引,聪明的研究者就会善于利用这个索引来做学问、写文章。康德自己也说过,读他的书如果只抓住一两句话,也许会认为他有矛盾;但如果全面地来作总体性的把握,这些表面的矛盾就自然消解了。
因此,我的讲解康德采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全息式”的讲解法,就是讲到每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前联后挂,联系其他地方相应的说法,特别是把康德前面已经讲过的话提出来,放到一起来理解。
同时,我们读康德的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记忆力的超强训练,因为康德的句子是有名的长句子,连德国人都嫌太长、无法卒读。如果一句话你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那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缺乏这种训练,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短句子。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节省字,言简意赅;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于表达那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关系。当然,文言文的这种特点也使它成为了一种适合于背诵的文字,由于句子短小,每个字的含义又都很丰富,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它背下来。中国古代做学问其实是很强调背诵的,这叫“童子功”;但这种背诵只是一种外在的记忆,即从小在脑子里刻下刻痕,到老不忘。这不用动脑子,和动物记得它的主人的声音气味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花大力气训练这种记忆,在这方面中国人举世无双。这就压抑了人的内在记忆。如果用这种方法治康德哲学,就会发现根本是南辕而北辙。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据说读过20遍,但还是无济于事,搞不懂。他们缺少的是内在的记忆,就是把前面读到一句话、一个词时所理解的意思从记忆中随时拉回来,与现在所理解的意思相比较,而不仅仅是把背熟了的那句话、那个词回想起来。
我们开头提到的刘宝瑞的相声也说明了这一点:你要确立一个事物发出声音的原理,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下记得这个原理,如果场合一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甚至忘记了先前的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原理,而只是想当然的意见。
下面再说计算能力。通常认为学数学的人比较理性,这在一般意义上也没错。理性这个词,reason,本来就有计算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计算不一定是对于数的计算,而且也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掂量,对逻辑的一贯性的一种敏感和坚持。比如说,你连着说两句话,你要能够察觉到后一句话的意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能够算得出来。
一般说,结果不能大于原因。你如果要说“因为”什么,“所以”就怎么样,你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如果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这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比如前面讲的那个相声,本来说的是蛤蟆叫声大是因为嘴大脖子粗,后来又加上了不能是竹子编的,再又加上了不能有眼、不能是圆圆扁扁的,……这样不断地增加,每遇到一种情况就加上一条,可以没完没了。但加得再多,仍然是原因小于结果,因为总还是可以再加一种情况来解释物体为什么发声。
我们很多人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这样,他们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凭感觉定一个意思再说,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大自己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一种泛泛而谈,甚至不知所云。比如说,李泽厚先生给“美”下的定义:“美是包含着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自然形象和艺术形象)。”就够累赘的了,他后来说这还不够,又不断地作了补充。真正的本质定义只能是唯一的,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例如我对美的定义:“美就是对象化了的情感。”),当然有时候这可能只是理想,事实上有可能同时并存好几种定义,但这几种定义必定要相互归摄或者相互冲突,而不能和平共处。而这种归摄和裁判的标准就是逻辑上的不矛盾性、同一性,也就是一种逻辑计算能力。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逻辑计算能力的训练,很多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人辩论中,拼命反驳人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人家没有攻击的观点。在读康德的书时,这就表现为不注意康德一句话中的逻辑值,任意减少和增添。康德的长句子最需要把所有的成分都考虑在内,他之所以要写那么长也正是出于这种意图,即将复杂的意思组织成一个固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有很多时候,读康德书产生的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注意他的一个句子成分,如一个从句,一个修饰语,一个状语或一个条件。有的翻译也是这样,为了图省事把一个小词漏掉了,或者为了好理解把一句话截成几段,因此而意思大变,读不懂了。康德有次说到,一个命题如果有它的限制条件,它就是一个有限命题;但如果把这个限制条件加进去而形成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加了限制的命题就成为一个无限的命题了。而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限制条件,或者译者把这个限制条件放在命题之外译成了另一句话,那么这个有限的命题就被误以为是一个无限命题了。
最后是综观能力。什么是综观能力?最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把两句或数句话合并成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同时又保持话语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的能力,又叫做概括能力。我们在日常谈话中是很随意的,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学术交流中也限于闲谈或漫谈,最终你会发现一无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人非常喜欢把学术讨论变成漫谈和闲谈,把学术文章写成随笔和散文,而不习惯于咬定一个主题追根到底,觉得那样太累。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惊异于苏格拉底从头至尾保持一个论题不走样,有时候看似跑马似地走远了,但一会儿又回到了原来的论题。苏格拉底的谈话对手经常抱怨说,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说明这样的交谈是很累人的。但人们为什么还是爱读,正是因为它使人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也能够把前面所讨论的内容作一个综观,说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哪个层次。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综观能力追溯到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能力,它实际上表达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人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认识材料,而是主动地综合这些材料以形成有规律的知识,这种主动性体现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至少是很稀少的,中国人理解的超越精神是一种什么也不干的清高,一种没有责任、置身事外的散淡,而不是努力进行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则一方面体现在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能动性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上。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讲的,为什么康德说“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干什么呢?做一个自由人,进行道德自律。而这就是启蒙的真义。通常认为启蒙理性就是专门着眼于科学技术,是唯智主义的,而它的负面就是败坏淳朴的道德。其实,康德的启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把道德从一种天经地义的教条、风俗习惯或信仰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法则,使得启蒙的道德高于任何以往的道德。
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文化的道德水平举世无匹。然而,儒家道德基本上是一种前启蒙的道德,它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而是诉之于天经地义的天理天道。它也讲意志的选择,但前提是选择的标准已经预定了,这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子,不接受就定为小人。这是不自由的选择。反之,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自由意志自律的产物,人们并没有一个先定的道德善恶标准,这标准还有待于人的自由意志去建立。自由意志如何去建立?也不是从外部选择一个标准,而是从自身的逻辑一贯性中形成标准。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束缚,而只受它自己的束缚,即在时间中保持一贯。自由意志必须做到不自相矛盾,自我取消,这才是真正自由的。
我们设想有一群人,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德为何物,也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教条,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要组成社会,他们只有凭借对他人的自由意志的认同,去寻求如何能够使各人的自由意志延续的有效法则。在不断磨合中他们终于会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使你的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才最能保持每个人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于是这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行为就被称之为“道德行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了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普世价值的因素。
康德的这一道德革命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意义。原来,道德并不是我们历来所以为的,似乎就等于一种习惯或风俗,需要人从小被动地去适应和服从。真正的道德正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人性并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产物,人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道德原理颠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传统,赋予了独立自由的人以最高的尊严。今天有不少人以为,通过返回到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可以改变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但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以往传统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的时代,但那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牺牲广大老百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所有的人都去顶礼膜拜一个至高无上的君权。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认为康德哲学就是终极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只是一种思维训练工具,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西方近代不只是康德,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都有这样的作用。也许康德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点,但他也有自身固有的毛病,这是必须也可以加以批评和分析的。但前提是,首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来源:思想严选
编辑:何晓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11 22:02
【案例】
孙伟平 李扬 | 论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高新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塑造着人与社会。在伦理道德领域,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问题,引发了剧烈的伦理冲突,特别是对人自身的道德主体地位提出了挑战。直面这些尖锐的新问题、新挑战,既有的一些伦理原则彼此缺乏联系,并没有作出应有的整体性回应,同时又很少顾及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伦理支持。立足于智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智能化趋势,在准确研判其伦理后果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个以人本原则为核心、包括公正原则和责任原则在内的整体性的伦理原则体系。它力求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予以必要的引导和伦理规制,实现其为人类服务、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崇高价值目标。
关键词: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人本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
作者:孙伟平,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李扬,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2年第1期。
目次
一、事实判断:人工智能之所“是”
二、关系判断:人工智能导致的伦理后果
三、价值判断: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体系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全方位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继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智能化已经成为时代强音,成为“现代化”的最新表征,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志。智能时代标志性的高新科技——人工智能——究竟会如何发展,可能导致哪些伦理后果,可能推动人与社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或许人们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视角不同,认知也不一,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基本共识,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开放性、革命性、颠覆性的高新科学技术,确实已经引发了大量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冲突。如何立足智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智能化趋势,准确研判其伦理后果,提出合理的、整体性的、具有前瞻性的伦理原则体系,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予以必要的引导、规制和支持,是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事实判断:人工智能之所“是”
显而易见,提出关于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具有前瞻性的伦理原则体系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所揭示的“应该”必须以“是”为基础一样,合理的价值判断也必须以事实判断为基础。只有回答了“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发展可能性”“人工智能可能给人与社会带来哪些改变”等问题,才能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合理的价值原则(体系)。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揭示发生之处,才有真实的东西”。
人工智能是以基于大数据的复杂算法为核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它比人类历史上所发明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更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究竟应该如何给人工智能下一个定义?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头痛、迄今仍然莫衷一是的问题。囿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特别是远未定型的事实,或许任何匆忙的定义都是不明智的。不过,无论“人工智能是什么”的问题具有怎样的开放性、革命性和颠覆性,我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它仍然是人类所创造并一直服务于人类的一种高新科学技术;或者说,人工智能与其他任何“属人的”科学技术一样,都植根于人类生活实践活动的需要,都服务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在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是具体社会实践的发起者与评价者,是实践工具的制造者和操控者,是社会协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实践动力的提供者和实践后果的承担者。在原始的渔猎、采集活动,以及农耕、家庭手工业活动中,人不仅需要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而且几乎包揽了全部的脑力劳动。以蒸汽机为标志性成果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以内燃机、发电机为标志性成果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通过机器代替人承担社会实践所需的大部分动力,承担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大幅提升了人类活动的能力和效率。机器在发展过程中,还通过“生产流水线”这一协作方式,将包括教育、文化在内的各项生产活动高效地组织起来。在“生产流水线”上,既有机器之间的,也有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分工与协作。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应用和普及,个体的人日益成为“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具体的社会实践不再仅仅由人发起,机器开始“承担”部分的脑力劳动,“接管”一部分职责和权力。“生产流水线”外化、固化了人的“生产思维过程”。每一步生产加工什么?怎么进行生产加工?各个生产加工步骤如何衔接?……这些原本人脑思维过程之中的内容使用“生产流水线”“表达”、固定下来了。当然,生产流水线般对人脑思维过程的外化、固化不仅是片段的,而且缺乏对思维过程的变动性处理,省略了作为思维过程背景的知识体系,造成了实践过程的“程式化”和“机械化”,产生了一系列非人性、异化劳动者自身的后果。对此,以马克思、马尔库塞、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同凡响,出现了模拟人的大脑和智能,并以“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为目标的人工智能。这导致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人工智能是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基础的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它基于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处理能力和大数据,弥补了生产流水线所欠缺的作为思维过程背景的知识体系的不足;它以算法为核心,不仅外化了人的思维过程,也可以对思维过程进行变动性处理,实现了机器在“思维”“理性”方面的跃升。无论是“弱人工智能”还是“强人工智能”,都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发起”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对实践工具的操控,组织人与机器的社会协作,并对实践过程适时进行评价和调整。作为“人造物”的人工智能甚至日益接近突破“图灵奇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接近成为像人一样的“主体”,从而前所未有地取代人的工作,将人从各种繁重、单调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
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在生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日益接近突破“图灵奇点”,日益接近成为“主体”,不可避免地给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全方位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智能科技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机器人在一定意义上日益成为“人”(如2018年沙特阿拉伯授予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研制的类人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而且促使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受无孔不入的“智能化洗礼”,导致我们身边的一切快速信息化、智能化,以至于“世界每天都是新的”。
首先,智能科技的发展和应用重塑了社会生产方式,使经济活动日益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这不仅极大提高了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导致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而且令信息和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在21世纪的数据驱动型社会中,经济活动最重要的‘食粮’是优质、最新且丰富的‘实际数据’。数据本身拥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数据领域的控制决定着企业的优劣。”信息、知识具有可共享性、主体依附性、价值增益等与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完全不同的自然禀赋,这种与源自资源的自然禀赋之不同正在深刻地改变经济活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例如,催生知识经济、智能产业快速崛起,将知识劳动者置于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位置。
其次,伴随智能产业的崛起和传统产业的智能化,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以往“机械”“呆板”的机器装上了聪明的“大脑”。智能机器不仅能够自己“看”和“听”,也能对生产过程进行“思考”,从而“自主”地运转起来,开展灵活多样的“订制型生产”。人们所从事的大量重复、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正被一批又一批地交给智能机器去做。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背景下,人与机器之间正在重新分工,传统的“人机关系”在轰轰烈烈的解构中重建。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知识劳动者”以其自身掌握的信息和知识,特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成为社会生产、服务、管理的主体;各种智能系统“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承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劳动任务和工作职责;一种人机协作、人机一体化的新型分工体系正在形成。
再次,社会上层建筑正在“重筑”,信息化、智能化的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渐成主流。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依靠土地、工厂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同,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资源的转向,使得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日益出现摆脱地域限制的趋向,虚拟银行、虚拟企业、虚拟车间、虚拟商店、虚拟博物馆、虚拟法庭、虚拟学校、虚拟医院、虚拟社区、虚拟家庭等新兴社会组织方式大量出现。新兴社会组织方式以其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特点,呼唤社会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变得更为敏捷,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管理结构日益显现出自身的弊端,组织管理结构出现了扁平化、分权式之类的趋向。
最后,在生产方式、社会分工、社会组织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的基础之上,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基于智能经济、智能社会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各种公共信息、文化服务和商业广告,可以越来越及时、精准地传递给受众。思想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同时,随着信息、知识转变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的变迁,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产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正在遭受猛烈的冲击。与全新的社会生活实践相适应,一种新型的具有智能时代特质的思想文化体系正在孕育、生成。
毋庸置疑,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处于早期,远未成熟、定型,它对人与社会的变革、塑造仍然是初步的。未来人工智能将如何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如何变革、塑造人与社会,仍然有待冷静观察。但非常明显的是,正在发生的变革与塑造之快速、广泛与深刻,是以往一切科技革命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人类正处在一场波澜壮阔的生存、活动革命之中。
二、关系判断:人工智能导致的伦理后果
伦理道德作为人与动物相揖别、“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体系”,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且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深刻改变世界、对社会“再结构”的高新科学技术,正在全方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关系。
(一)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日益增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越来越活跃,对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伦理道德曾被认为是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从传统伦理学的视角看,人因其有理性、会思维,能够根据自主意识开展活动,而被认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被设定为唯一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如果说人工智能作为“人造物”日益接近突破“图灵奇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接近成为“主体”,那么,它是否可能成为“道德主体”?这引发了持不同立场的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
弗洛里迪(L. Floridi)和桑德斯(J. Sanders)提出了判断X是否为道德主体的标准:只有X在能够起作用,例如对世界产生重要的道德影响的前提下,并且具有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它才是道德主体。即是说,只有X能够与其环境发生交互作用;能够在不受外部环境刺激的情况下,具有改变其自身状态的能力;能够在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中改变规则,才是道德主体。显而易见,智能系统能够符合上述各项标准,弗洛里迪和桑德斯由此直接承认了智能系统的道德主体地位。
而与此相对照,不少学者则表示质疑,拒绝承认智能系统的主体地位,最多只给予其“准道德主体”的地位。有些学者引用泰勒(P. Taylor)1984年提出的判断道德主体地位的五条标准:“第一,具有认识善恶的能力;第二,具有在道德选择中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第三,具有依据上述道德判断作出行为决定的能力;第四,具有实现上述决定的能力与意志;第五,为自己那些未能履行义务的行为作出解释的能力”,据此质疑、否定今天智能系统的道德主体地位。例如,布瑞(P. Bery)用道德主体应该具备的三个特征,即“有能力对善恶进行推理、判断和行动的生物;自身的行动应当遵循道德;对自己的行动及其后果负责”,来否定智能系统的道德主体地位。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地进行分析,那么不难发现,上述判定标准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判定标准,特别是其中“意志”“生物”等用语,直接显示了标准提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明显是以人为参照物来衡量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其二,根据上述判定标准得出人工智能仅具有“准道德主体”地位的结论,显示其理论视野仅仅局限于弱人工智能,而没有考虑到突破“图灵奇点”之后的强人工智能或超级智能。但无论学术界具体认定的标准是什么,无论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立场上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激烈的争论本身就表明,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与快速发展已经对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果说肯定纯粹由人所制造的智能系统拥有道德主体地位还存在难度,一时难以被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所认同,那么,说生物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混合体将拥有道德主体地位,则明显比较容易被认可和接受。因为,否定人工智能具有道德主体地位的关键就在于,人工智能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心灵”,而“心灵”则是独属于人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人的自然躯体一直在被修补、被改造。虽然这种修补和改造目前还是初步的,还停留在物质性的躯干部分(如假肢对手或腿的修补、冠状动脉支架对血管的改造),还没有深入到对人脑及其智能的修补和改造,但是,“生物智能必将与我们正在创造的非生物智能紧密结合”,人机互补、人机一体显然处于技术发展的逻辑进程之中。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强大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正是人的自然躯体所缺乏或存在严重局限的智能和技能。科幻小说中所描绘的在人脑中植入特定的芯片,辅助人脑承担感知、记忆、判断、表达等功能,创造出打破技术与人的传统界限的新生事物,都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在智能化进程中,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否定这种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共生体”的道德主体地位,将会直接导致对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否定。可见,人作为唯一的道德主体的地位遭遇到人工智能强有力的挑战。
人工智能在挑战“人的唯一道德主体地位”的同时,还通过所拥有的越来越强大的劳动能力,以及对人所占据的劳动岗位的排挤,令人的生存、生活环境变得恶劣。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正在日益增强,在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展现出相对于自然人的优势。它们不仅能够代替人从事各种危险或有毒有害环境中的工作,而且开始向曾经“专属于人的工作岗位”发起挑战。例如,在复杂的城乡道路上开车曾经一直是人的“专利”,而无人驾驶汽车正在兴起;写出自己所感、所想,引起他人共鸣,一直是作家引以为傲的资本,“薇你写诗”之类智能程序也可以做到;绘画、书法、作曲、弹琴、舞台表演一直是高雅的人类艺术,相应的智能系统正在向这些领域快速进军……在智能技术指数级进步速度的衬托下,人(特别是“数字贫困者”之类普通劳动者)的进步速度显得过于缓慢,远远跟不上智能机器进化的速度;加之现实社会中原本就存在的贫富差距、技术差距和“数字鸿沟”,“数字贫困者”之类普通劳动者在这场智能革命中很可能彻底丧失劳动的价值、工作的权利,从而被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排斥在外,沦为“无用阶层”或“多余的人”。在社会快速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中,这种不公正、不人道的“社会排斥”现象可能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丧失劳动价值、丧失工作机会,从而令自己在生活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遭遇危机,令自己的存在看上去变得可笑和荒谬。
(二)人工智能不仅重构了社会基础设施,而且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挑战。
首先,“人—智能系统”的道德关系已经引发忧虑与不解。人工智能既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工具,又绝非一般性工具,它具有成为“主体”的潜质。它剧烈地冲击、解构着传统的“人机关系”,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智能系统”的道德关系的热烈讨论。目前学者们的立场和观点越来越分裂,达成普遍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有些科学家和学者甚至充满忧虑地提出,“强人工智能”或者“超级智能”是否会失控、异化,反过来统治、虐待、奴役人类。如阿库达斯(Arkoudas)和布林斯约德(Bringsjord)在为《剑桥人工智能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供稿件中认为,人工智能不会仅仅满足于模仿智能或是产生一些聪明的假象,成为真正的主体是技术发展的逻辑追求。库兹韦尔甚至预言:“(有意识的)非生物体将首次出现在2029年,并于21世纪30年代成为常态。”这种超越其设计者的“强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自主创新、彼此联系,是否会超出原先设计者对其职能边界的设定而走向“失控”,成为统治、虐待、奴役人类的“超级智能”?这种“强人工智能”或“超级智能”是否会基于自身的强大,判定人类“没有什么用”,并且“浪费资源”,从而怠慢“数字贫困者”之类弱势群体,进而漫不经心地灭绝人类?
其次,人工智能对现有的“人—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带来了冲击。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尚未成熟、定型的通用型技术,已经展现出自身强大的威力,开始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经并正在造成一系列严重的伦理后果。例如,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本来存在一定的自然能力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别、社会分化等现象,这种不平等的现实往往令弱势群体感到愤愤不平,而在死亡面前的“终极平等”又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甚至是最重要的平等。或许正是因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不平等都变成了有限的不平等。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一些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可能更有条件实现“智能+”,更好地享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可能以知识、智慧为突破口而不断拓展,“数字贫困者”之类弱势群体可能处于更加无助、无奈的地位。医疗技术、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还可能对人的基因进行重新编辑,通过基因增强大大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大幅延长人的寿命;通过“思维上传”实现“精神不死”,甚至成了一些精英群体现在就开始讨论的话题。如果基因增强等技术真的能够实现,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自然更有可能受益,可能优先获得弱势群体渴望而不得的提升机会。这将直接瓦解“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然铁律,令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得以长期延续,甚至变本加厉。
再次,基于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可能产生难以计数的道德问题。例如,在具体的道德关系中,如何确定智能系统的道德责任就是当前困扰人们的一个道德难题。正处于测试阶段的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如果获准上路,马上就颠覆了传统的驾驶员与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智能无人驾驶固然可能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它显然并不能完全消灭交通事故。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传统的以驾驶员为中心的责任体系已经土崩瓦解,智能无人驾驶系统的设计者、生产者、拥有者、使用者等之间难以避免相互间的责任推诿。此外,智能无人驾驶系统本身还会加剧原有的一些“道德两难”问题。如义务论和功利论争论不休的“电车难题”并非没有根据的理论设想,完全可能出现在发达的智能时代。例如:一辆载有大量乘客的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突遇横穿马路的行人,在刹车不足以避免相撞的情况下,紧急转向可能导致车辆侧翻,造成乘客伤亡,而不转向、仅刹车则可能造成行人伤亡。面临两难情形,如果驾驶员是自然人,凭借自身的道德直觉所作的决定往往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而如果是算法主导的智能无人驾驶,则很难逃脱义务论者或者功利论者的苛责,以及没完没了的追责。
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可能导致的伦理道德挑战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人们热衷讨论的虚拟对真实的挑战、大数据与隐私权问题、算法可能内嵌的歧视问题、智能推送加剧人的单向发展问题、人形智能机器人对人际关系(特别是婚恋家庭关系)的挑战、杀人机器人的研制和应用问题,等等。我们可以肯定,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显现出来。所有这些新问题、新挑战对智能时代的伦理建构和道德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呼唤我们基于新的伦理原则体系重建新的伦理秩序,建设更加合乎人性、人们的幸福指数更高、社会也更加公正的新型智能文明。
三、价值判断: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体系直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的变革,以及所产生的新的伦理问题和挑战,社会各界对此都极其关注。不少组织机构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例如,微软公司将“公平、包容、透明、负责、可靠与安全、隐私与保密”作为人工智能的六个基本道德准则;腾讯研究院从“技术信任”“个体幸福”“社会可持续”三个层面提出若干道德原则;欧盟将“人的能动性和监督能力、安全性、隐私数据管理、透明度、包容性、社会福祉、问责机制”作为“可信赖人工智能”的七个关键性条件。乔宾(Anna Jobin)等人从美英等国84份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资料中,按出现频率的高低,将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归纳列举如下:“透明、公正和公平、不伤害、责任、隐私、有益、自由和自主、信任、尊严、持续性、团结”。还有不少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域提出和论证了“透明”“责任”“问责”等人工智能的伦理原则,要求智能系统具有一颗“良芯”的呼声此起彼伏。
然而,细致思考既有的各种伦理主张,以及所提出的各种伦理原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其一,诚如有些科学家所说,面对人工智能对世界的全方位改造和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参与,这些伦理原则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并没有针对新的问题和挑战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其二,这些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伦理原则更多是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消极预防或限制,而很少顾及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伦理支持。无论是从智能科技的良性发展而言,还是从智能社会的伦理建构来说,这两个严重的缺陷都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关注和解决。
基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建构能够整体性回应人工智能对现实社会的众多问题和挑战,并包含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必要规制和积极支持的伦理原则体系,必须寻找一个类似“阿基米德支点”的“基点”。这个“基点”,也就是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最高伦理原则。
这样的“基点”或最高伦理原则只能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立足人自身的立场去寻找。众所周知,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人工智能等高新科学技术,都是“属人的”创造物,都是为人类的根本目的和利益服务的。任何科技活动(包括技术的应用)本质上都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是“人为的”且“为人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类活动必须遵循“人是目的”,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的原则。因此,无论人工智能体多么接近突破“图灵奇点”,多么接近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主体”,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其“属人性”。“人”是我们在这里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人本原则”是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伦理原则体系的“基点”和最高原则。
当然,“人本原则”是既抽象又含混的,学者们对其内涵与外延的争议颇多,聚讼不断。但删繁就简,它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重含义:首先,在技术的伦理价值取向方面,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必须“以人为中心”,始终坚持“人是目的”,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维护人在世界上的主导性地位。其次,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为人类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在技术研发、应用的方向上,防止它朝着蔑视人类,甚至危害人类的方向发展。再次,就具体的风险防控而言,不能放任人工智能“随心所欲”地发展,不能对任何可疑的技术风险和负面社会效应听之任之;相反,正如稍后提到的责任原则将要论及的,必须强化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对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问责、追责。迈入智能时代,面对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人类自身的不完满、局限性和缺陷正在被不断放大。但是,不完满、有局限性和缺陷的人依然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依然是伦理道德或“人机(智能系统)道德关系”的主体,依然是一切科技、人文活动的目的和宗旨之所在。各种智能系统虽然可能在体力甚至脑力活动方面超过人,却始终只是人的工具、助手和伙伴。任何算法都不能忽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格和尊严,任何不直接受人控制的智能系统,例如“智能杀人武器”,都不应该被研发和应用,任何智能系统都不应在能够救人于危难时袖手旁观。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高伦理原则,“人本原则”是所有的、各个层级的伦理原则的“基点”和“统领”。即是说,其他各项伦理原则都可以从“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并基于“人本原则”得到合理的解释。
“公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德性之首”,是“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最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公正作为人们被平等相待、得所当得的道德直觉和期待,是社会共同体得以长久维系的重要保障;公正作为一种对当事人的利益互相认可并予以保障的理性约定,更是社会共同体制度安排、“人—人”的道德关系、确定主体和“类主体”道德责任最为基本的伦理原则。当然,对于公正是什么、公正怎样阐释才是合理的这类问题,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如何在现实社会实现公正,特别是解决一直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方法。或许应该说,公正的理解和实现都是历史的,人们永远只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踉跄前行。在促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并对人与社会带来革命性、颠覆性的改变时,我们需要“以人为中心”进行“公正的制度设计”,既遏制“资本的逻辑”之贪婪成性和为所欲为,也防止“技术的逻辑”的漠视人性与横冲直撞,从而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接触、应用人工智能的机会,都可以按意愿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并与人工智能相融合,都能够从这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中受益;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劳动时间、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体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数字鸿沟和“信息贫富差距”,消除经济不平等、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排斥”现象,维护“数字贫困者”等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
责任是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过程中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也是“人本原则”的逻辑延伸。如果说公正原则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整体,那么责任原则更多指向的则是个体。人工智能的研发毕竟是由科研人员进行的,他们往往是处在人类知识边缘的直接评价者和具体决策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往往决定着人工智能及相关产品、服务的社会影响,因而肩负着神圣的、不容推卸的道义责任。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不仅要关心技术的进步,以及技术的应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也要关注技术本身的伦理后果、技术应用的负面社会效应。这正如科学巨擘爱因斯坦对科学工作者的谆谆告诫:“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责任原则绝不仅仅局限在人工智能的研发领域,它同样也是对生产者、所有者、使用者的道德要求。它不仅是确定智能系统的道德责任的伦理原则,而且是在受人工智能影响的“人—人”道德关系中确定相应主体道德责任的伦理原则。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过程中,研究者、生产者、所有者与使用者都应该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应该让人工智能“可靠”地为人类服务;一旦出现问题,则可以及时、有效地追责;从而确保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为人类谋福利,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目标。
总而言之,以“人本原则”为“基点”和“统领”,以公正原则和责任原则为主干,这就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整体性的伦理原则体系。这一原则体系在逻辑上是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是一个有主有次、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它既涵盖了对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进行必要的伦理规制的内容,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提供积极的伦理支持。同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诸如公开、透明、可控、可靠等次级伦理原则,或者更为具体、更为细致的伦理实施细则,完全可以结合相应的生活实践领域,以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为基础加以解释,从而被纳入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体系之中,实现对由人工智能引发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的整体性回应。当然,在时代和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以上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整体性的伦理原则体系是否合理、是否有效,我们必须坚持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将其具体地应用于解决问题、应对挑战,使之在智能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完善和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智能时代人的新异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BZX001)阶段性成果。
来源:哲学分析
编辑:何晓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12 19:14
【案例】
听哲里丨简明伦理学第8讲:功利主义的历史——西季威克和理想功利主义
编者按
以声入心,倾听哲理,欢迎收听中国伦理在线语音播客听哲里,我是主播颜晗。在前三期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功利主义的历史》一文关于古典功利主义的内容,今天的节目,作为《功利主义的历史》一文的最后一部分,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关于西季威克、理想功利主义的内容,以及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概括性总结。让我们开始吧。
功利主义的历史
亨利·西季威克
亨利·西季威克(1838-1900)的《伦理学方法》(1874)是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中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它为功利主义提供了辩护,尽管一些作家认为,它不应该主要被理解为对功利主义的辩护。在《伦理学方法》中,西季威克认为自己关注的是,对“发现隐含在我们常见的道德推理中的不同的伦理学方法。”进行阐述。这些方法是利己主义、基于直觉的道德和功利主义。在西季威克看来,功利主义只是基础的理论;它简单地依赖直觉,却不能解决价值或规则之间的基本冲突,比如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冲突。用西季威克的话说,“我们需要一些更高的原则来决定这个问题……”这就是功利主义。此外,那些似乎是常识性道德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规则往往是模糊的和描述不足的,应用它们实际上需要求助于理论上更基本的东西——功利主义。然而进一步说,对规则的绝对解释似乎是非常反直觉的,而功利主义则可以为所有例外情况提供合理的解释。西季威克为功利主义在理论上的首要地位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作为一名英国哲学家,西季威克的理论是从边沁和密尔的观点中发展出来的,也是对他们的回应。他的《伦理学方法》是他对功利主义理论和主要替代方案的探索,也是一种辩护。
西季威克还致力于澄清该理论的基本特征,在这方面,他的论述对后来的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对功利主义者和一般的后果主义者,而且对直觉主义者也是如此。西季威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彻底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被最近的伦理学家们所发展的关切。
西德威克的观点中有一个极富争议的特点,那就是他拒绝了道德理论的宣传要求。他写道:
因此,功利主义的结论,仔细说来,似乎是这样的:认为保密可以使一个行为变得正确,否则就不会如此,这种观点本身应该保持相对的秘密;同样,认为深奥的道德是有利的学说本身应该保持深奥。或者,如果这种隐蔽性难以维持,那么最好是由常识来否定那些只适合于少数开明人士的学说。因此,根据功利主义原则,一个功利主义者可以合理地希望他的一些结论被人类普遍拒绝;或者甚至希望庸俗的人对他的整个体系敬而远之,因为其计算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它在那些庸俗的人手中可能导致坏结果。
这接受了功利主义可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如果人们不相信它,可能是最好的,即使它是真的。这一理论受到了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批评,他认为该理论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西季威克时代的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它是“政府大楼的功利主义”。他言论中的精英主义可能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态度,即受过教育的人被认为是比未受过教育的人更好的政策制定者。
上述评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与一般的实践审议有关。某一理论、某一规则或某一政策的支持者——甚至某一一次性行动的支持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他们认为人们实际上会做什么,而不是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做什么(例如在充分合理的反思下)?这是实际主义/可能主义辩论中出现的关于实际商议的一个例子。从上面的例子推断,我们有一些人主张说出真相,或者他们认为是真相的东西,即使真相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别人误用而导致不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有人建议在预测真相会被他人误用以达到不良效果时,不要说出真相。西德威克似乎建议我们遵循我们预测会有最好结果的路线,因为作为我们计算的一部分,其他人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失败——要么是由于有坏的愿望,要么只是不能有效地推理。威廉斯指出的担忧其实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具体担忧。西德威克会指出,如果隐瞒真相是不好的,那么人们就不应该这样做。当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直觉。
西德威克提出的问题产生的更深的影响在于我们对功利主义的基本理解。例如,早期功利主义者对效用原则的定性方式留下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主要的问题在于总效用和平均效用之间的区别。他在人口增长和越来越多的人(或有生命的人)的效用水平增加的背景下提出了这个问题。
假设人类的平均幸福是一个正量,假设享受的平均幸福不减,功利主义指导我们使享受幸福的人数尽可能多。但是,如果我们预见到人数的增加可能伴随着平均幸福的减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从未被正式注意到,而且似乎被许多功利主义者大大忽略了。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功利主义规定,作为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整体的幸福,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幸福。那么,如果额外的人口在整体上享有积极的幸福,我们就应该权衡额外人数获得的幸福量和其余人失去的幸福量。
对西季威克来说,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不是简单地争取更大的平均效用,而是把人口增加到我们使目前活着的人的数量和平均幸福的数量的乘积最大化。因此,这似乎是一种混合的、总平均的观点。这场讨论还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的政策问题,后来的作者,特别是德雷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两个问题。
理想功利主义
摩尔(G. E. Moore)坚决不同意古典功利主义者采用的享乐主义价值理论。摩尔认为,我们应该促进善,但他所认为的善其内容是远远超过可以简单的“快乐”一词的。在内在价值方面,他是一个多元化的人,而不是一个一元论者。例如,他认为“美”是一种内在的善。一个美丽的物体的价值独立于它可能在观看者身上产生的任何快乐。因此,摩尔与西季威克不同,后者认为善是由一些意识组成的。世界上的一些客观状态是内在的好,而在摩尔看来,美正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用他的一个更有名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这一点:他让读者比较两个世界,一个是完全美丽的,充满了相互恭维的事物;另一个是一个可怕的、丑陋的世界,充满了“一切最令我们厌恶的东西”。此外,人们想象,周围没有人类来欣赏或厌恶这些世界。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世界中哪一个更好,哪一个的存在会比另一个的更好?当然,摩尔认为很明显,美丽的世界更好,即使没有人在周围欣赏它的美丽。这种对美的强调是摩尔作品的一个方面,使他成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宠儿。如果美是善的一部分,独立于它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实际上,独立于它如何影响他人,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再在美的祭坛上牺牲道德。追随美不是一种单纯的放纵,甚至可能是一种道德义务。尽管摩尔本人肯定从未将他的观点应用于此类案例,但它确实为处理当代文献中被称为“令人钦佩的不道德”的案例提供了资源,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高更可能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但那是为了一个美丽的结局。
摩尔通过反对早期的功利主义者来反对享乐主义,后者认为善是某种意识状态,如快乐。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摇摆不定,摩尔始终不同意享乐主义,因为他认为即使美本身并不是一种内在的善,为了使对美的欣赏成为一种善,美也必须实际存在于世界上,而不能把它认为是幻觉的结果。
摩尔进一步批评了快乐本身是一种内在的善的观点,因为它没有通过他为内在价值提出的一种隔离测试。如果人们将一个空旷的宇宙与一个由虐待狂组成的宇宙相比较,空旷的宇宙会让人觉得更好。即使在施虐者的宇宙中存在大量的快乐,而没有痛苦。这似乎表明,善的必要条件至少是没有坏的意向性。虐待狂的快乐,由于他们伤害他人的欲望,会被打折扣——它们不是善,尽管它们是快乐。这与边沁的观点大相径庭,边沁认为即使是恶意的快乐也是内在的善,如果没有任何工具性的坏东西附着在快乐上,它也是完全的善。
摩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一个“有机统一”或“有机整体”的价值观点。有机统一的原则是模糊的,对于摩尔在提出这一原则时的实际意思有一些分歧。摩尔说,“有机”是用来“表示一个整体在数量上有别于其部分价值之和的内在价值”。而且,对摩尔来说,这就是它应该表示的全部内容。因此,举例来说,人们不能通过将身体各部分的价值相加来确定其价值。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只在与整体的关系中才有价值。例如,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如果与身体分开,可能根本没有价值,但与身体相连却有很大的价值,甚至会增加身体的价值。在《伦理学原理》关于理想的一节中,有机统一的原则发挥作用,指出当人们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知来体验快乐时(这涉及到在对适当的对象——情感和认知的一系列要素——的认识面前的一种积极情感),当体验的对象,即美的对象实际存在时,对美的体验会更好。这个想法是,体验美有一个小的积极价值,而美的存在有一个小的积极价值,但把它们结合起来有很大的价值,比两个小价值的简单相加还要多。摩尔指出“对一个物体的真实性的真实信念,大大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整体的价值。”
摩尔的这一原则——特别是适用于实际存在和价值,或知识和价值的意义,为功利主义者提供了应对一些重大挑战的工具。例如,在摩尔看来,妄想的幸福将严重缺乏,特别是与基于知识的幸福相比。
5
总结
自20世纪初以来,功利主义经历了各种改进。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很少有哲学家完全同意古典功利主义者提出的观点,特别是在享乐主义的价值理论方面,所以更多的是被认同为“后果主义者”。但古典功利主义者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在道德哲学中,而且在政治哲学和社会政策中。边沁提出的问题:“有什么用?”是政策形成的基石。这是一个完全世俗的、前瞻性的问题。这种政策形成方法的阐述和系统发展要归功于古典功利主义者。
来源:斯坦福哲学百科2009年3月27日首次发表;2014年9月22日最后修改。
参考文献:
Bentham,Jeremy, 1789 [PM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 1785 [OAO]. “OffencesAgainst Oneself.” Louis Compton (ed.), The Journalof Homosexuality, 3(4) (1978): 389–406, 4(1): 91–107..
Cooper, Anthony Ashley (3rd Earl of Shaftesbury),1711 [IVM]. Inquiry Concerning Virtue or Merit, in Characteristics ofMen, Manners, Opinions and Times, excerpts reprinted in Raphael 1969.
Cumberland, Richard, 1672. De Legibus NaturaeDisquisitio Philosophica, Londo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Maxwell, ATreatise of the Laws of Nature, 1727, reprinted New York, Garland, 1978.
Gay, John, 1731. 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Immediate Criterion of Virtue in FrancesKing's 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Evil, London.
Hume, David, 1738.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by L. A. Selby-Big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Hutcheson, Francis, 1725. An Inquiry into the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London; excerpts reprinted inRaphael 1969.
Mill, John Stuart, 1843. A System of Logic, London:John W. Parker.
–––, 1859. On Liberty, London: Longman, Roberts& Green.
–––, 1861 [U]. Utilitarianism, Roger Crisp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oore, G. E., 1903 [PE]. Principia Ethica, Amherst,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Price, Richard, 1758 [P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leQuestions in Morals, London: T. Cadell in the Strand, 1787.
Raphael, D. D., 1969 [R]. British Moralists, in twovolumes, Lond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risp, Roger, 1997. Mill on Utilitarianism., London:Routledge.
Darwall, Stephen, 1995. Hume and the Invention ofUtilitarianis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onner, Wendy, 1991. The Liberal Self: John StuartMill'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11. “Morality, Virtue,and Aesthetics in Mill's Art of Life,” in BenEggleston, Dale E. Miller, and David Weinstein (eds.) John Stuart Mill andthe Art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iver, Julia, 2004. “Pleasure as the Standard of Virtue inHume's Moral Philosophy.” Pacific PhilosophicalQuarterly., 85: 173–194.
–––, 2011. Consequentialism, London: Routledge.
Gill, Michael, 2006. The British Moralists on HumanNature and the Birth of Secular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ruschka, Joachim, 1991.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andOther Early German Anticipations of Utilitarian Theory,” Utilitas, 3: 165–77.
Long, Douglas, 1990. “‘Utility’ andthe ‘Utility Principle’: Hume,Smith, Bentham, Mill,” Utilitas, 2: 12–39.
Rosen, Frederick, 2003. “Reading Hume Backwards: Utility as theFoundation of Morals,” in Frederick Rosen(ed.),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from Hume to Mill, London: Routledge, 29–57.
Rosenblum, Nancy, 1978. Bentham's Theory of theModern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yan, Alan, 1990.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Scarre, Geoffrey, 1996. Utilitarianism, London:Routledge.
Schneewind, J. B., 1977. Sidgwick's Ethics andVictorian Mor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0. “The Misfortunes ofVirtue,” Ethics, 101: 42–63.
Schofield, Philip, 2006. Utility and Democracy: thePolitical Thought of Jeremy Benth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Bart, 2004. Henry Sidgwick, Eye of theUniver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rupski, John, 1989. John Stuart Mill,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何晓琴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15 11:18
【案例】
经典荐读 | 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
推荐理由
道德哲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在进行道德评价或确定道德责任时要遵循“可控原则”,即行为人所受到的道德评判仅仅局限在其能够掌控的因素之内。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两个人道德行为的不同仅仅是由某些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造成的,那么就不应该在道德上给予二人不同的评判。“道德运气”是一种被认为由于违背“可控原则”而具有“自相矛盾”特性的道德现象,这一概念自1976年被伯纳德·威廉斯等人提出以来,一直是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参见:贾佳.“道德运气”问题与道德哲学的当代发展——基于伯纳德·威廉斯的批判性立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4(04):43-48.
作者简介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早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哲学和古典学。威廉斯的主要工作领域是伦理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但他最重要的影响是在伦理学方面。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对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质的探究,主导了近30年来西方伦理理论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功利主义:赞成和反对》(1973,与J.Smart合撰),《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1985),《羞耻与必然性》(1993),《真理与真诚》(2002)等。
道德运气
译者:徐向东
来源:《美德伦理学与道德要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在哲学思想中已经有这样一个谱系,它把生活的目的鉴定为幸福,把幸福鉴定为反思性的平静,把平静鉴定为自我充分性的结果——不是处于自我的领域中的那些东西也不在自我控制之内,因此就受到了运气的影响,成为平静的偶然敌人。在西方传统中,这个观点的最极端的变种是古典时代的某些学说,尽管对于那些学说来说有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使好人或圣贤免于受到容易发生的运气的冲击,但一个人是否是一位圣贤或者是否能够成为一位圣贤却取决于我们称为“生成运气”(constitutive luck)的那种东西:按照这个流行的观点,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成为一位圣贤并不是他们不可企及的生活历程。
通过成为圣贤,一个人的一生就可以免于受到运气的影响,这个思想从那时起就很少流传开来(例如,在主流的基督教传统中,它实际上并不流行),不过,它的地位已经得到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的接受,那个思想就是:有一种基本的价值——道德价值——是不受运气所影响的。用那个思想的最严格的解释者的术语来说,道德价值是“无条件的”或者“不受支配的”(unconditioned)。按照这个观点,不管是对道德判断加以纠正的倾向,还是道德判断的对象,都不会受到外在偶然性的影响,因为在它们相互关联的那种方式中,二者都是那个无条件的意志的产物。不管偶然性是世界中产生的东西是幸运还是不幸,它们被认为都不是道德评价的恰当对象,也不是决定道德评价的恰当因素。在品格的领域中,真正算数的东西是动机,而不是风度、权力或者天赋这样的东西,类似地,在行动的领域中,在世界中实际上得到实现的东西不是变化,而是意图。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些考虑,那么甚至那种使得古代的圣贤们幸运地得到好处的生成运气就被认为消失了。实施道德能动性的那种能力,被认为在任何理性行动者那里都是存在的,在能够把这个问题向自己呈现出来的任何人那里都是存在的。成功的道德生活,一旦从对出生、幸运的培养的考虑中被移交出来,或者实际上从对一个非佩拉吉乌斯的上帝(non-Pelagian God)的那种不可理喻的恩惠的考虑中被移交出来,就被呈现为这样。
一种生涯——那种生涯不仅对这些才能开放,而且也对一切理性存在者在同样的程度上都必然具有的一种才能开放。这样一个概念把一种根本的正义放在它的核心,而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康德主义只是表面上令人厌恶:即使它在表面上具有这个特点,但它提供了一种诱惑,在面对世界的不公正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安慰。
然而,只有当某些东西得到承认时,康德主义才能提供这样一种安慰。即使道德价值根本上不受运气的支配,但如果道德价值只是其他价值当中的一种,那么它们不受运气支配这个事实就变得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为了具有这种宽慰作用,康德主义必须假设道德价值具有一种特殊的、实际上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或者尊严。假设确实有这样一种价值,它与其他类型的价值不同,是所有理性行动者都可以得到的,那么,要是那种价值只是一种最终的诉求,只是精神的卧室,那个康德主义的思想就不会提供多大的鼓舞。相反,那个思想必须在两件事情中具有一个主张:一件事情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而具有的最根本的关注,另一件事情是一个人对如下事实的承认:他被假设要把握的东西不仅是道德可以不受运气的影响,而且也是他自己可以通过道德部分地不受运气的影响。
按照这个观点,任何“道德运气”的概念都是极端不连贯的。这个短语听起来确实有点奇怪。这是因为:这个康德式的概念,在其纯粹的形式上,体现了一些对于我们的道德观念来说很根本的东西。然而,使道德免于受到运气的影响这一目的必定是一个很令人失望的目的。从哲学家们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点的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道德倾向,不管被放在离动机和意图的方向多远的地方,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有条件的”。然而,道德毕竟仍然屈从于生成性的运气这个苦涩的真理,尽管这一点并不是我即将要讨论的东西。那个康德式的观念把一系列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影响了那些概念。那些概念包括道德、合理性、辩护以及根本的或者至高无上的价值。在那个康德式的观念下,那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就对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反思评价产生了一些后果。例如,康德主义者认为,在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层次上,行动者在履行他所履行的行动上是否得到了辩护,这不可能是一个运气问题。
这个领域恰好就是我想要考虑的领域。事实上,关于道德,直到本章结束为止我说得并不多,相反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理性辩护的观念。我相信这是开始讨论问题的正确起点,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对这种关于合理性和辩护的观念具有某种承诺,另一方面,就道德而论,他们都倾向于认为那个康德式的观念就是问题之所在,那个观念只是表达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夸张。不过,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而且,那种试图摆脱运气的康德式的努力也不是一项毫无根据的事业。实际上,那种努力与我们的道德概念是如此亲密,以至于它的失败反而会促使我们去考虑这一问题:是否我们不应该完全放弃那个概念?
我将会很慷慨地使用“运气”这个概念,而且,即使我没有定义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它是可理解的。待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对某件事情说它取决于运气时,我并不想让这个说法具有这样一个含义:那件事情是没有原因的。一般来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很不寻常的状况,我要读者去反思一下他们如何思考和感受那些状况,但不是按照实质性的道德观念或者道德“直观”,而是按照他们对那些状况的体验去思考和感受它们。我不想暗示说人类不可能没有那些感受和体验。在不太寻常的情形中只有这样一个主张:我所考虑的那些思想和体验是可能的、连贯的、可理解的,而且,没有理由把它们谴责为不合理的。在更加寻常的情形中有这样一些暗示(我也会大致描述一下支持它们的理由);要是我们并不处于头脑含糊不清或者没有经过反思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状况相比,尤其是与某些哲学家通常所假设的状况相比,要是我们在生活中没有那些体验,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自我观念进行一种规模更大的重建。在这里,我所提到的那些哲学家是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就好像我们对自己的能动性的体验,我们对自己所持有的那种遗憾的感觉,在经过清理之后,不仅符合一个很简单的合理性图景,而且实际上已经符合那种图景。
让我们首先描述这样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为了过一个他认为他可以追求他的艺术才能的生活,他背离了人类社会对他提出的一些确定的和紧迫的要求。让我们把这位艺术家称为“高更”,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并不想要用任何历史事实来限制我的讨论。高更可能已经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向他提出的要求毫无兴趣,只是喜欢过另一种生活,而他的最好的绘画作品就是从那种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有可能也是从他的那种喜好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我将不关心其他人的主张不会对行动者产生任何影响的那种情形,即使这种情形可以提醒我们一些与目前的关注有关的东西,即:即使我们有时候受到了一个观念的引导,即:一个对道德加以普遍尊重,而且所有人都倾向于确认道德的世界,就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但我们实际上有深刻而持久的理由感谢那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所具有的世界。因此,我们不妨把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高更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关心其他人的主张,关心那些主张在受到忽视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忽视很残忍),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仍然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他希望实现他作为一个画家的天赋,在这个抱负下,他想要追求的另外那种生活可能不是他很明确地看到的,不过,为了把问题变得简单一些,我们不妨补充说,他确实在那个抱负下很明确地看到了那个生活——那个生活,作为将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画家的生活,就是他想要选择的生活。于是,在他的计划最终是否取得成功这件事情上,“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就变得比较清楚了——至少有一些可能的结果将会成为成功的明确例子(当然,这种成功与得到承认并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不管有多少其他的事情仍然是多么不清楚。
就这种情形的本质而论,他是否将会取得成功是事先无法预测到的。我们在这里所要处理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东西:把某件事情的外在障碍消除,而一旦那个障碍被消除了,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预测到那件事情将如何发生。在我们的故事中,高更是在把很多东西放到尚未把自己明确地揭示出来的那种可能性上。我想要探究和维护的主张就是这一主张:这种状况中,唯有成功本身才能为他的选择做辩护。如果他失败了,如果我们很快就会更准确地看到那种失败是什么样子,那么他就做错了事情,但不是在人们日常所说的意义上做错了事情,而是在如下意义上做错了事情:既然在那种情形中他已经做错了事情,他也就没有根据支持这个想法——在履行他所履行的行动上他得到了辩护。另一方面,如果他取得了成功,那么他就确实得到了一个支持那个想法的根据。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将把下面这个问题留到最后来讨论:辩护的概念如何符合那些与众不同的道德观念?然而,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即使高更最终能够得到辩护,这无需向他提供任何方式来向其他人(至少向所有其他人)表明他的选择是正当的。因此,对于那些因为他的选择而遭受了痛苦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表明他们将没有正当的理由责备他。即便他成功了,他并没有因此就获得了这样一项权利:那些人应该接受他不得不说出来的话;如果他失败了,那么他甚至就无话可说。
如果存在着一个辩护的话,那么这个辩护本质上将是回顾式的。高更不可能做那件被认为对于合理性和辩护的概念来说都是本质的事情,即: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一个人应该能够运用辩护性的考虑,而且事先知道他是否是正确的(在那件事情结果表明是正确的意义上)。我将主要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目前并不想要过分强调道德的概念,不过,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一个比较狭窄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预先按照道德规则对高更的选择提出一个辩护,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部分阐明将会深化我们对“辩护”这个概念的理解。
假设一位道德理论家承认,有某个价值与高更的计划的成功相联系,因此可能也与他的选择的成功相联系,那么,通过形成一个在结果出现之前就能辩护那个选择的辅助规则,他就可以尝试在一个道德规则的框架中来容纳那个选择。那个规则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它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规则:如果一个人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伟大艺术家,那么在决定忽视其他人的主张上他就在道德上得到了辩护。因为这种说法在内容上很值得怀疑,此外,在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既然一个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为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因此用来陈述这个条件的那句话也是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确信自己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个说法只会使得辩护条件具有一种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的色彩,而“……如果一个人合理地确信自己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个说法则是一种更糟糕的说法。因为我们可以问:在这种情形中,什么东西被假设是合理的信念呢?高更应该就这个问题与艺术学系的教授进行商榷吗?这些附属条件是荒谬的,而且恰好表达了如下做法的荒谬性:试图在道德规则的框架中来为这样一种情形发现一个地位。
与按照道德规则来提出的表述相比,功利主义的表述不会为理解这种状况做出更大的贡献。功利主义的表述可以提供“他选择那种生活更好(或者更糟糕)”这样一个思想,而且,在功利主义那里,这个思想的力量仅仅表现在“那件事情的发生更好(或者更糟糕)”这个说法中。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对于描绘行动者的选择或者它的可能辩护毫无帮助,功利主义本身没有特殊的材料来实现这个目的。如果功利主义试图详细阐明这个“更好”的内容,那么它就碰到了它的那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观点,高更最终所成为的那样一个画家变得越流行,他的决定就似乎已经成为一件更好的事情。但是,有比这种困难更加有趣的东西。就高更的情形而论,功利主义的观点会明确地(即使不是唯一地)错失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这个问题:什么样的“失败”可能与功利主义的道德评价有关?高更是为了某些好处或利益而做出他的选择的;从后果的观点来看,那些好处或利益要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体现,要么没有得到实际体现。但是,如果高更的计划失败了,那么“他的计划是因为什么而没能得到实现”这个问题就与我们正在考虑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关联。如果高更在去往塔希提岛的路上受到了某种损伤,结果使他无法继续从事绘画工作,那么那肯定就意味着他的决定(假设这个决定现在已经变得无法扭转)只是枉费,而且,在这个结果中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抵消了其他人的丧失。但是,那一系列事件并没有激发这个思想:他的选择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和没有辩护的。他并不知道是否他已经错了,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在他的计划中,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他错了,那么那个东西就不仅仅是他的计划失败了,而是他失败了。
这个区分表明:即使高更的辩护在某些方面取决于运气,但它并非同样地取决于所有类型的运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与那个计划本身具有多么内在的联系。至少相对于他的事业来说,他受到了损伤这样一件事情是一种最外在的和最偶然的运气。这种类型的运气以一种不可还原的方式影响了他是否会得到辩护,因为如果那种厄运落到他头上,那么他就不会得到辩护。但是,这种运气是一种过分外在的运气,因此就很难表明他的选择得不到辩护,相反,只有他作为一位画家所能做的事情的失败才能表明他的选择得不到辩护;不过,在另一个层次上,那种事故仍然是一种运气,即在一个人能够成为他希望自己可能成为的那种人的过程中所碰到的运气。有人可能很想知道那种事故是否根本上是一种运气,或者,如果它是一种运气,那么它是否可以不是那种对一切都可能产生影响的生成性运气,而我们现在已经把这种运气放置在一边。但我们还需要补充说,他成为这样一个人不仅是一个运气问题,而且是相对于进入他的决定中的那些思考而成为一个运气问题,因为正是相对于那些思考,他最终才成为他所成为的那种人,但他有可能(在认知上)还没有成为那样一种人。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一些情形中,虽然也许不是在高更的情形中,在这种决定上的成功可能被认为并不取决于相对于那个决定而论的认知运气。可能有一些理由断言:准备采取而且事实上正确地采取了那个决定的那个人,实际上知道他将会取得成功,不管他在主观上可能是多么不确定。但是,即使这一点对于某些情形是正确的,它并不有助于解决回顾式辩护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所使用的知识概念本身是回顾式地加以利用的,而且,即使这种运用说不上有什么错误,但它不能使得行动者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做出任何他不可能已经做出的区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中,即使结果表明行动者确实知道他将会取得成功,但是,相对于他在那个时候、在他做出决定的那个层次上可以得到的考虑而言,他竟然已经知道他将会取得成功这件事情仍然是一个运气问题。
在高更所做出的那样一种决定中,有些运气是外在于他的计划的,有些运气是内在于他的计划的;这两种运气对于成功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此对于实际辩护来说也都是必要的,但只是后者才与没有得到辩护相联系。如果我们现在略微拓宽一下范围,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内在运气的概念。在高更的情形中,他的计划本质上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两个区分大致是相吻合的。一个区分是在内在于这项计划的运气和外在于这项计划的运气之间的区分;另一个区分是在由他自己以及他所成为的那种人来决定的东西和不是被这样决定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在高更的情形中,内在运气本身实际上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他在绘画方面是否真正具有天赋,他在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上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显然,并非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的所有条件都在于他,因为其他人的行动和抑制提供了那项计划得以实现的很多条件,而这个事实就是外在运气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地。但是,在使他的计划得以实现的条件中,那些与没有得到辩护有关的条件,即内在运气的所在地,基本上是在他那里——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条件取决于他的意志,即使确实有一些条件取决于他的意志。这两个区分的大致吻合是高更的情形的一个特点。但在其他的情形中,内在运气(也就是说,内在于这项计划的运气)的所在地可能部分地处于行动者之外,这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实际上很典型的情形。
考虑另一个例子——安娜·卡列尼娜的例子,即使在这里我们同样只是很简略地论述这个例子。在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生活中,她仍然意识到了其他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意识到了她的儿子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事情已经变得好转,而且,相对于当她离开卡列林时她的思想状态而言,事情可能已经变得好转,那么她可能就是用那种意识来生活的。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她所处的社会状况以及她自己的精神状态都具有这个特点:她与沃伦斯基的关系在她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且,那种关系变得越明显,它所占有的分量就越大;我把这个事实理解为一个不仅与社会有关而且也与她和沃伦斯基有关的真理;而且,不管托尔斯泰根本上使得这个真理看起来多么不可避免,但相对于安娜的早期思想来说,那个真理有可能已经是另外一个样子。用目前的术语来说,她与沃伦斯基的关系是一个内在运气的问题,是在她的核心计划上的一个失败。但这个运气的所在地并不完全在她那里,因为也在沃伦斯基那里。
要是沃伦斯基实际上已经自杀,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内在的失败。要是沃伦斯基已经被偶然地杀死,他们两人的关系就不是一种内在的失败,而是一种外在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她的计划仍然会成为她的一个目的,但它不会遭受它实际上所遭受的那种失败。这个差别精确地阐明了我们所关心的那些思想。要是安娜在那种情况下已经自杀,那么她的思想可能就会是这样一个思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继续生活下去了。”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安娜在决定自杀时的想法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倒不如说,她的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与她已经做出的事情相联系。她现在发现她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得不到支持,因为她大概只能用她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来辩护她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不仅否定了她的那些希望,而且也反驳了那些希望。
正是对于这些思想,我想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将会使得它们的意义更加明显的结构中。我在这里的讨论首先不是针对我们或者其他人可能会对这些行动者提出的说法或想法(虽然它也具有这样一个含义),而是集中于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能够被期望有什么连贯的想法?在描述他们的精神状态时,我们肯定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遗憾(regret)的概念,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概念提出一些必要的评论。
遗憾的本质思想一般来说是这样一个思想:“要是事情已经是另外的样子,那么那就更好了”;只要一个人能够对一件事情形成“它有可能已经是另外的样子”这样一个概念,并且能够意识到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如何会变得更好,那么这种感受原则上就可以应用于任何这样的事情。在遗憾的这个一般意义上,人们感到遗憾的东西是事态,而任何了解那些事态的人原则上都可以对它们有所遗憾。不过,有一种特别重要的遗憾,我将把它称为“行动者遗憾”(agent regret)。只有对一个人自己过去的行动,或者至多只是对一个人认为自己参与了的行动,一个人才能感觉到这种遗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假设的可能差别,即:一个人可能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遗憾的焦点是针对那个可能性,而他对遗憾的想法部分地是由他自己对“他可能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这个问题的理解来形成的。“行动者遗憾”并非只是因为它的题材而不同于一般而论的遗憾。对于一个人自己过去的行动来说,也可以有一些遗憾的情形,但它们不是行动者遗憾,因为过去的行动是以一种纯粹外在的方式来加以看待的,就像一个人可以看待任何其他人的行动那样。行动者遗憾不仅要求一个第一人称的题材,也不仅只是要求一种特殊的心理内容,而且也要求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行动者遗憾绝不局限于有意的能动性(voluntaryagency),而是可以扩展来超越一个人在过去对任何事情有意地做出的行为,只要那些事情是他因为有意地做了某件事情而必须因果地负责任的事情。不过,甚至在能动性的很偶然的或者非志愿的层次上,行动者遗憾的情感也不同于一般而论的遗憾,例如可以被一位旁观者所感受到、在我们的实践中被认为有所不同的那种遗憾。假设一个卡车司机并非出于自己的过错而辗过一个小孩,那么他的感受就不同于任何旁观者的感受,甚至不同于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旁观者的感受,除非那个旁观者就像那个司机一样接受了这一想法:他自己可能已经避免了这场事故的发生。在安慰这个司机时,人们无疑会试图把他从这种感觉状态中解脱出来,实际上把他从与一位旁观者的地位相类似的某种地位中解脱出来,而且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被视为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情,不过,对于一位很容易被其他人鼓动来采取那个态度的司机,或者对于一位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很冷漠的司机,人们实际上仍然有一些怀疑。我们对那个司机感到遗憾,但那种情感是与如下这一点相共存的,而且实际上预设了这一点:这个事故的发生与他有一些特殊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可能只是因为考虑到那个事故的发生并不是他的过错就可以排除的。在能动性比在这样一个事故中显得更为充分的地方,仍然有一些更多的东西要说,即使行动者仍然是因为无知而无意地行使了他的能动性。
因此,行动者遗憾与旁观者所感觉到的遗憾是有差别的,那种差别并不仅仅是在进入了那种情感的思想和想象中显示出来的,而且也在表达方式的差别中显示出来的。假设那个卡车司机认为他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行动,也希望那种方式将构成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赔偿,或者至少认为它是那种补偿或赔偿的象征,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就是把行动者遗憾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然而,甚至当一个人认识到他应该进行这种补偿的时候,愿意这样做并不总是表达了行动者遗憾,而且,在这些方面,准备进行补偿这件事情可以在很不相同的意义层面上把自己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承认我们需要对我们无意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但这种承认是一种外在的承认,只是由一种很一般的遗憾相伴随,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遗憾相伴随。它可能只是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存在着另外的选择,如果受害者遭受的损失只是作为行动者的有意活动的一个附属效应而产生的,而这样一个选择是人们可以在他那里发现的,那么让受害者忍受损失就是不公正的。
在这种情形中,行动者意识到他已经做了一件对别人有害的事情。这个意识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行动者自己认识到那件事情是作为他的行动的后果而发生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这样一个思想:在这种情形中,那件事情发生的代价可以被公正地归因于他自己。行动者可以承认他应该进行补偿,而为了检验他是否确实处于这种思想状态,我们就可以追问这个问题: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否保险金额至少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不妨假设那个受害者已经被支付一笔保险费(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那笔保险费是由别人支付的,如果这样做有助于澄清这个检验的话)。现在,如果行动者了解到受害者将会得到那笔保险赔付,如果他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将会消除他所感觉到的任何不安,那么那种情形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外在的情形。这个检验有一个明显的和让人欢迎的结果,即:是否一个行动者可以用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把一个特定的情形看做是外在的,不仅取决于他与那个情形的关系,而且也取决于那个情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除了他是否应该赔偿而不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这个问题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所造成的损失是否是那种完全可以由保险金额来补偿的损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一个行动者意识到他是无意中才造成那个损失的,但他仍然会觉得他应该做点事情——他有这种感觉,不一定是因为他确实能够在保险金额无法补偿的地方进行补偿,而是因为(假若他很幸运的话)他的行动可能有一些超越了补偿的弥补含义。
在其他情形中,就没有任何恰当行动的余地了。因此就只有进行弥补的欲望和这样一个痛苦的意识:对于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某个其他的行动(也许不是那么针对受害者)可以充当来表示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在什么程度上是合适的,在弥补的行动中可以去尝试做些什么,或者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取代那种感觉,这些问题都是只有针对特定的情形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非理性的和自我惩罚性的借口,那种任何人都不太可能否认的借口,在这个领域中仍然是有一些余地的。然而,如果有人认为他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体验到这种情感,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处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如果有人强调说一个理性的人绝不会具有这种情感,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在持有一个精神不健全的合理性概念。此外,坚持这样一个合理性概念,除了会产生其他类型的荒谬外,还会把这样一件很虚假的事情暗示出来:如果我们用一种头脑清醒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我们自己与我们的行动的那些无意的方面完全分离开来,把它们的代价转移到(比如说)保险基金,而且仍然还会保留我们作为行动者的同一性和品格。一个人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历史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作为意志的产物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由那些不是那种产物的东西来环绕和支撑的,而且是由那些东西部分地形成的,以至于反思只能往两个方向中的其中一个方向上进行:其中的一个方向是断言“负责任的能动性”(responsible agency)概念是一个很肤浅的概念(在和谐化所发生的事情上用处很有限),另一个方向是断言那个概念不是一个肤浅的概念,但又认为它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净化——如果我们按照一个人已经做的事情,按照一个人在世界上要负责任的事情来理解他的同一性,并认为这种理解很重要,那么我们差不多就得接受这个说法:我们只能按照在一个人那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来理解他的同一性。高更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例子当然是有意的能动性的情形,但这种情形仍然与刚才提到的那种无意的情形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两人的“运气”与那些在结果的发生中起到了本质作用、但却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具有某些关联;而且,按照我们对这两个例子的讨论,它们以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体现了现实对结果的决定,在他们的意志之外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按照自己的决定所做出的判断的决定。此外,对有关无意行为的行动者遗憾的讨论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个二分法——有些哲学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经常依赖的那个二分法。这个二分法是用“遗憾”和“懊悔”(remorse)这样的术语表示出来的,在这里,“遗憾”实际上被鉴定为旁观者的遗憾,而“懊悔”就是我们已经称为“行动者遗憾”的那种东西,但受到了一个限制,即:它只是适用于有意行为。对于无意行为,我们有行动者遗憾,而且,若没有这种遗憾,我们就不会欣然承认一个生活,而这个事实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个二分法中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因为这种遗憾既不是单纯的旁观者遗憾,又不是用这个定义来得到的懊悔。
前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行动者遗憾。在这种遗憾和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情形中的行动者的感受之间,是有一个差别的。正如我们可以从无意行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行动者遗憾在行动者那里涉及到一个愿望,即希望他还没有做那件事。他深深地希望他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变化:要是他已经知道那个变化,那么那个变化就是他有能力控制的事情,而且会改变那个结果。但是,在我们的讨论中,不管是高更还是安娜·卡列尼娜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只有当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不会取得成功时,他们才会采取其他行动方式。(假设他们随后的思想和感受本质上仍然是由我们已经赋予他们的计划来形成的,那么至少在这个假定下,他们能够具有那个愿望,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失败了。不过,这种说法仍然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说法,因为他们显然可以在失败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计划,即使安娜并没有这样做。以下我将继续维持这个假定。)不管这些行动者在做出决定之后、但在宣告他们的成败之前具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些感受都不会产生一个充分发达的愿望,使他们已经采取了其他行动方式,因为那个愿望只有在已经宣告失败时才会出现。
遗憾必然涉及到“但愿事情已经是别的样子”这一愿望,比如说,一个人尚未不得不用他确实行动的那种方式来行动。不过,它并不必然涉及到这样一个愿望:在把所有的事情都加以考虑后,但愿自己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两个行动历程发生冲突的情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尽管这个例子基本上与目前的问题无关);在这两个行动历程中,每一个行动历程都是道德所要求的,而且,即使其中的一个行动历程被判断为是最好的,但采取它还是会使人留下遗憾,而且这种遗憾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行动者遗憾——对一件有意做出的事情的遗憾。我们不应该完全把行动者遗憾同化为刚才提到的那个愿望,即:在把所有的事情都加以考虑后,但愿自己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以及它们与我们对辩护的某些看法的联系。通过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的那个要素补充到我们试图描绘这些情形的努力中。
把我们正在讨论的情形与实践慎思的某些更直接的情形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那些回顾式的反思相比较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形,即纯粹利己主义的慎思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不仅行动者的注意力被限制到利己主义的计划,而且道德批评者也会同意这种限制的合法性。在这里,在一种意义上,行动者并不需要对他的慎思过程提出辩护,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是他必须加以回应的,但是,人们经常假设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在那种意义上,甚至这样一个行动者的慎思过程是可以得到辩护或者不可以得到辩护的。这种意义就是这样一个意义:不管他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相对于他的处境来说,他的决定可以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与此相关的考虑至少包括他的思想的一致性,他对各种可能性的理性评价,以及在时间上对各个行动的优化排列。
辩护的语言是在这种联系中被使用的,但与通常所假设的相比,不太清楚的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尤其是,说一个行动者不仅回顾式地关心他的决定的成功,而且也关心他的决定的合理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最终看到他的慎思与结果不相匹配,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他的那种回顾式的思想?如果他慎思得很糟糕,并因此使得他的计划出了错,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他对结果的遗憾如何恰当地与他的慎思联系起来。但是,如果他慎思得很好,但事情仍然出了错;尤其是,就像有时候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在他慎思得很糟糕的情况下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那么,当他意识到他“得到了辩护”时,既然他仍然倾向于对事情的发生变化及其结局有一种确定无疑的遗憾,那个意识对他的那种倾向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他认为他得到了辩护,这个思想中似乎包含了这样的东西:一方面,他对事情就是它实际上的那个样子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在一种与那个遗憾相对应的意义上,在他并不希望自己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的同时(因为他遵守了导致他的实际行为的理性慎思过程),他又希望自己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类似地,对于相反的现象也是如此:行动者在慎思中已经犯了错误,但发现得太晚,因此来不及改正错误,但却侥幸取得成功,而且,要是他已经采取了其他行为方式,他反而不会那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己就像实际上那样行动他感到高兴,缺乏采取其他行动方式的愿望。这种心态是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在那个层次上,即使他因为就像实际上那样行动因而有了一种自我责备或者一种回顾式的自我警告,但那种心态仍然符合后面那种感受。
这些观察都是一些很平常的看法,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它们的真实内容是什么。自我责备或者自我遗憾的说法并没有把什么东西反映出来,而那种共存的遗憾和满意则更没有把什么东西反映出来,除非我们能够把那种感受的某种表达方式鉴定出来。在这种情形中,那种表达方式肯定不是要被鉴定为对其他人进行补偿的倾向,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受到了影响。与此相关,其他人提出的批评,与他们在怀有怨情的时候所提出的批评相比,在基础上是不同的,正如在下面这种情形中体现出来的那样:一位行动者因为错误、疏忽,或者(很有趣地)只是因为选择了一个高度冒险的策略,从而使得人家委托他参与管理的一笔财物遭受到了损失的危险,而如果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那个策略是他完全有资格选择的策略。托管人没有资格拿婴儿的钱来赌博,即使他由此获得的任何利润肯定都属于那些婴儿,因为成功本身不会消除(或者开始消除)人家对他提出的非议。在纯粹利己主义的情形中,那种批评当然是不合适的,而且,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其他人所提出的批评并不仅仅是这个利己主义情形中的一个后果上的考虑,是从其他人对理性审慎的美德的推荐中产生出来的考虑,因为那些美德首先需要得到说明。
即便我们假设,在纯粹利己主义的情形中,并不存在对他人进行补偿的问题,但是,遗憾的那种表现形式,正如里查茨所说,看来必定是针对行动者对其未来慎思提出的决议。他对自己的慎思的遗憾自身表现为“下一次一定要好好考虑”这样一种决心;不管慎思的特定结果多么令人失望,行动者对慎思的满意是在下面这种做法中体现出来的:他从这种情形中没有发现什么有待吸取的教训,并确信下次即使他改变了方法他也不会有更好的成功机会(在某个特定的支付层次上)。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在理性慎思的一项政策或者一个倾向(应用于一类正在展开的情形)的语境中,行动者对他以前在慎思上的表现是感到遗憾还是感到满意的概念才变得有意义。
这是一个很谨慎的想法,不过,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个想法是多么谨慎。这个想法暗示了一类相对于慎思实践来说充分相似的情形,而一旦我们把握到了这种相似性,我们就可以把其中的一种情形转变为另一种情形;不过,它并不意味着这些情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实践推理的题材。我今天可以在某种类型的各个选项之间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且,既然我已经看到了这种选择是如何做出的,我就决定下一次以一种很不相同的方式来处理同一种类型的选择,但我并不需要从事(或者决定要从事)那种一下子对多个类似场合的选项进行权衡的实践推理。
这些不同状况的结果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当我们说理性慎思原则上应该对它们一并加以考虑时,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会产生一些压力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具有充分的信息,那么任何选择实际上都会被认为对所有后来的选择产生了影响,这样一来,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的理想极限,与一个正在展现的理性慎思倾向的那个很有节制的概念相比,似乎就成为了某种更加雄心勃勃的东西。这就是以一个罗尔斯意义上的生活计划为目标的理性慎思模型,它把一个人生活的所有时刻处理为那个人应该平等地加以关注的东西。提出这个理性慎思图景的理论家都一致认为:因为无知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对生活中的遥远时刻打折扣看来确实是合理的。这些考虑就是他们随后用来产生一个模型的考虑,该模型把一个人的生活设想为一个矩形,一开始就被勾画出来,然后再被优化地加以填充。那些理论家认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理性渴望,即渴望使我们自己的一切生活计划变得和谐。因此,在他们对那个模型的描绘中,那个模型不仅被认为体现了对那个渴望的理想实现,而且也被认为对一个思想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根据。那个思想就是:一种更为根本的遗憾是对在慎思上发生的错误的遗憾,而不是对一般而论的错误的遗憾。一方面,这种遗憾采取了一种自我责备的形式,另一方面,按照那个思想,假若我们用慎思的合理性来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使自己免于受到我们的未来自我的责备——“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免于受到我们的知识的模糊性和局限性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东西保证我们必定能够发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选择。用慎思的合理性来行动只能保证我们的行为是免于责备的,我们作为一个在时间上延续的人是要对我们自己负责的。”罗尔斯曾经倡导这样一个引导性原则:“一个理性的个体总是这样来行动,以至于不管事情最终是如何发生的,他永远都不需要责备自己。”而这些张力就聚集在罗尔斯对这个原则的倡导中。
罗尔斯似乎认为这个命令在某种意义上是形式的,并没有决定行动者应该采纳多么冒险或者多么保守的策略。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评论:当一个人因为发生慎思上的错误而责备自己的时候,如果他认为这种责备的一切根据都要在他的晚期自我的反诉中来发现,那么他就必须在一种实质上更加谨慎的意义上来考虑罗尔斯提出的这个命令。
然而,产生这个命令的那个模型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除了其他的困难外,它不言而喻地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过的那种生活支配了他后来的欲望和判断。那个回顾式的判官将是我的未来自我,而他的观点就是我早期选择的产物。所以,就不存在任何一组既是固定的又是相关的偏好,以便我可以按照那组偏好来比较我用来填充我的生活空间的各种东西。如果我要参考我在那些填充物中想要的各种东西来评价它们,那么相关的偏好就不是固定的,另一方面,如果我要用我现在(比如说)想要的东西来评价,它们,那么这种做法就会产生一组固定的偏好,而那组偏好不一定是相关的。在这个生活空间模型中来做出这种求助,实际上就是像功利主义那样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存在着某种满足的流通货币,按照那种货币,一个人就可以相对于一组偏好及其实现来比较另一组不同的偏好及其实现的价值,而且是以一种中立的方式来加以比较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存在着任何这样的货币,我们也没有理由假设实践合理性的思想应该不言而喻地预设这种货币。
如果没有这样的货币,那么我们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程度上从我们实际上具有的计划和偏好中进行抽象,于是,原则上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观点——从那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毫无偏见地比较我们用来填充我们的生活矩形的各个可供取舍的东西。对一个人的生活进行审慎选择的观点天生就是来自这里。相应地,用更加丰富的知识来进行评价的观点必然也是来自那里,我不仅无法保证那个观点事实上将是什么样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我也无法保证我主要的和最根本的遗憾将是来自什么样的评价观点。
有很多决定构成了行动者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不妨把这个部分称为道德生活的“常规科学”);对于这些决定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根本上说,遗憾的出现与否是由慎思过程的那个回顾式的观点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特定的结果来决定的。根本上说,一个人自己以及一个人的观点是被鉴定为与一个正在进行的决策序列相适应的理性慎思倾向,而不是被鉴定为在那些场合取得成功或者遭受失败的特定计划。但是,在我们正在考虑的那些情形中,有某些与此并不相似的其他决定。实际上,慎思的合理性以及随后对这种合理性的评价是可以有地方出现的。在我们的情形中,要是行动者尚未在其处境允许的情况下严肃地考虑这些理性想法,正如他们实际上可以针对他们的处境的现实条件来考虑的那样,那么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严肃的考虑。但是,他们并非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来回顾他们的处境的,这个方面也不是因为它对一系列的慎思状况做出了贡献因而就对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会从这个方面吸取教训,但他们不是以那种方式来吸取教训的。在这些情形中,行动者为此而做出决定的计划,就是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自我认同的那个计划:要是那个计划取得了成功,那么他用来进行评价的观点就会来自这样一个生活——对他来说,正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功,因此他就从这个事实中引出了那个生活的一部分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他失败了,那个计划在他的生活中就不再具有任何这样的意义。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他一方面欢迎这个结果,另一方面又对他的决定感到很遗憾。如果他失败了,他的观点就会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观点:对这个人来说,这个决定的根本计划已经证明毫无价值,而且,如果我们简单地假设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把其他恰当的计划产生出来,那么他的失败就只能给他留下最基本的遗憾。所以,如果他失败了,他最基本的遗憾就会与他的决定发生联系;如果他成功了,他最基本的遗憾就不可能与他的决定发生联系。当我们说他的决定对他来说能够得到成功的辩护时,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说的。
按照这个论述,清楚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很冒险的决定,甚至也不仅仅是那些能够具有一个实质性结果的格外冒险的决定。结果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实质性的——那种方式重要地支配了行动者对其生活的意义的把握,因此支配了他的回顾式评价的观点。由此推出,那些决定实际上是冒险性的,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冒险性的那种方式有助于说明外在失败和内在失败的差别对这些计划的重要性。就内在失败而言,把决定产生出来的计划被揭示为一种空洞的东西,一种无法为行动者的生活奠定基础的东西。就外在失败而言,那个计划不是被这样揭示出来的,而且,即使他不得不承认那个计划已经失败,但他并未抛弃那个计划,反倒是在某种新的抱负中利用那个计划来理解剩余的东西。在他的回顾式思考中,在那个思考对基本遗憾的分配中,他不可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把自己鉴定为他的决定,所以并没有发现自己得到了辩护;但是,他也没有与那个决定完全分离开来,他不可能仅仅把那个决定视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因此他并没有发现自己得不到辩护。
最终,我就辩护所说的这一切与道德究竟具有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吗?托马斯·内格尔赞同道德深深地和令人不安地受制于运气这一说法,但否认像高更这样的例子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例子只是表明:高更那种最基本的回顾式的感受并不一定是道德上的感受。
内格尔提出了一个理由来支持他的主张。正如我早期所暗示的那样,这个理由是这样的:在其他人不会具有正当抱怨的意义上,高更可能无法面对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然而,这个考虑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分量,除非我们对伦理一致性的本质提出一个很强的假设,这个假设大致是说:如果某个人已经有辩护地从一个道德的观点来行动,那么从那个观点来看,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正当地抱怨他已经那样来行动。但是,这个假设,作为一个一般要求,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因此就显得很不现实,正如我们可以从政治的情形中看到的那样,因为在那种情形中,我们(比如说)可以有理由确认结果,确认行动者产生那个结果的选择,确认他就是能够做出那个选择的行动者这一点,即使我们也意识到他的选择中已经有了一个“道德代价”。在这种情形中,指望那些已经受到欺骗、受到利用或者受到伤害的人们确认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也不应该屈从于一个要人领情的思想,即:当他们的抱怨按照这个总体的图景没有得到辩护时,他们与行动者的牵涉过分密切,因而就看不到真相。他们的抱怨实际上是得到了辩护的,他们可以很恰当地拒绝接受行动者提出的辩护,而那种辩护是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都可以恰当地接受的。他的行动已经涉及到了一个道德代价,而这个思想就意味着他已经做了某些糟糕的事情,更经常地意味着某个人已经受到了不正当的对待。此外,如果那些已经受到那种对待的人们并不接受他所提出的辩护,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要求他们应该接受那个辩护。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准备采纳能够使得那个辩护生效的观点,这是一个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问题。如果道德情感就像我们实际上所体验到的那样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不可能用这样一个世界观来作为模型——在那个世界观中,每一个事件与每一个人的距离都是同样的。我刚才所说的东西就是表达这个思想的一种方式,而时间上的距离则是表达这个思想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的情形确定无疑地不同于政治家的情形。在后面这种情形中,进行辩护的条件是与如下问题相联系的: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得到实现,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体制,在那个体制中我们想要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愿望本身是由“日常意义上的道德考虑是什么”这一问题来形成的。就我们的例子中的行动者而言,进行辩护的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例子之间本身是有差别的。如果高更的计划成功了,那么它就会给世界带来某些好处,而安娜的成功则不会带来这样的好处。道德旁观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他有理由为高更的成功感到高兴,因此也为他的努力感到高兴——或者,如果一个特定的旁观者发现他不想感激高更的绘画,或者不想感激一般而论的绘画,那么就不会有某个其他的情形。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表达了我们的这样一种感激心情:道德并不总是占据统治地位——道德价值已经被处理为其他价值当中的一种价值,而不是被处理为一种不成问题的最高价值。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错误地描述了我们与这个高更的关系,但我们也需要记住那种感激心情的根据、范围以及对道德的限度的意义,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如果道德实际上就是最高的价值,那么它就不得不普遍存在:就像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如果道德要成为真正无条件的东西,那么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东西来支配它。
这个要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要求,因此它就很容易渗透到这些情感中来。那个康德式的观点如此强制性地要求的那种根本的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既然道德不受运气的影响,它就应该成为最高价值。尽管这个要求在形式上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或依附,但是,就像罗伯斯比尔的政府一样(海涅曾经把这个政府与那个康德式的体制做了一般的比较),它事实上能够稳定地成长起来,最终就要求情感的广泛服从。正义不仅要求我是什么样的存在者这件事情应该不受运气的支配,而且要求我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成为什么样的存在者这件事情应该不受运气的支配。此外,按照这个要求,如果一个人欣赏、喜欢或者享受运气的幸运的表现形式,那么他似乎就是在背叛道德价值。即使一个人就像康德曾经认识到的那样认识到,有一些事情是一个人要负责任的,而其他事情是一个人不用负责任的,但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要对情感的提升负有一种罪过感。当那种康德式的正义感与功利主义的负面责任概念联合起来时,最终的毁灭就出现了,在任何具有重要性的层面上,人们只剩下纯粹的道德动机,而且这种动机的运用是没有极限的。最终,也许除了以健康的名义分配给一个人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无意义的隐私领域外,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也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因为这种生活是道德生活的一种真正病态的形式,道德的限度本身就成为一种道德上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位理论家仅仅把高更的决定视为一种超道德的东西的令人欢迎的入侵,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过分狭窄。只有当他把高更看做一位超越道德的人物时(这是我们一开始就不予考虑的假设),他的那种做法才是恰当的。如果高更不是这样一位人物,那么高更自己就会为他已经对别人做出的事情而感到遗憾,而且,如果他失败了,那么那种遗憾就不仅仅是他所具有的东西,此外,他甚至不再具有这样一个观点,在那个观点中,他可能已经用某个其他的东西来平息那种遗憾,正如我已经试图表明的那样。对于道德旁观者来说,这就产生了一些分别。即使那位旁观者可以赞赏那个超越了道德的高更的成就,而且实际上赞赏他,但另外那个高更却是这样一位人物——他自己就存在于道德关怀的世界中,并且分享了其中的某些关怀。这些行动者所经受的冒险本身就是在道德领域中的冒险,是他们当中那些已经超越了道德的人们不会经受的冒险。
如果这些行动者得到了辩护,那么他们的辩护不会恰当地平息所有的抱怨。不过,这个事实本身不会导致“那些辩护不是道德辩护”这一结论。然而,也许我们仍然应该接受这个结论。我们应该说,他们的道德运气并不在于获得一种道德辩护,而是在于他们的生活与道德的关系,在于他们的辩护或者缺乏辩护与道德的关系。那种关系首先必须在他们自己的观点中来加以看待,而他们自己的观点本身就具有了这一特征: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他们剩下来的就仅仅是遗憾。但是,他们的生活显然是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然而,现在有一个紧迫的问题:那个道德概念提供了多少东西?到论证的这个阶段为止,对于它所发生的事情,它到底有多么重要?不管运气是否是生成性的,是否影响了一个人的决定与道德的关系,或者只是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最终结果,运气对于道德生活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提醒我们自己注意到这个事实时,我们本质上利用了那个道德概念,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概念的核心运用中来反思“使用那个概念的基本动机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基本动机就是:通过使用那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决定和评价中把一个有望超越运气的方面确立起来。一旦那个动机得到了理解并被询问,我们就可以再次追问那个概念的目的,同样就可以追问这个问题:在那个概念所具有的特点中,有多少其他的特点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道德被认为摆脱了运气的影响。然而,一旦我们对这个观点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么那个道德概念就不可能处于它原来所处的位置了。这就类似于如下情形:我们通常假设存在着一个道德秩序,在那个秩序中,我们的行动具有一种不可能只是按照纯粹的社会承认来赋予它们的意义,然而,一旦我们怀疑我们对这样一个秩序所具有的最接近的形象,那么它就不可能依然保持原状。这些形式的怀疑论会向我们留下一个道德概念,但与我们通常所采取的那个道德概念相比,它就不再是那么重要;我们现在所得到的那样一个道德概念将不是我们的概念,因为对于我们的道德概念来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个道德概念要被看得多么重要。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
编辑:蒋可心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25 15:36
【案例】
职业伦理的现代价值与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
作者简介: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摘要〕职业伦理一直是人类不同历史时期道德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具有悠久和优良的传统。较之传统社会,现代职业伦理具有如下特性:利益与道义相统一;契约与德性相协调;制度与教化相结合。现代职业伦理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发展,当代中国四十多年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是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干出来的,凝结在他们身上良好的职业道德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当代职业伦理的成功实践经验主要是:利益和竞争机制的驱动,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长期有效的思想教化。
〔关键词〕职业伦理 现代价值 中国实践
职业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职业伦理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所有价值观念、规范体系与主体品质的统一,它既包含着不同职业群体所拥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如医务道德的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教师道德的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等;也包含着职业同事关系以及不同职业关系之间相互交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从业者作为该职业人的某些个人品质,如企业家精神、军人作风、干部作风、师德风范等。但从总体上看,职业伦理的重点似乎是一种做事的行业道德,虽然这并不排斥在职业活动中的做人道德与交往道德。职业伦理不仅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优良的传统,而且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职业道德的推动;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推动着中国人职业道德水平的提升和进步。
一、职业伦理的历史地位与优良传统
职业就是人因社会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正当谋生劳动、活动形式和人群集团。人类最初是根据性别、年龄等因素而形成的自然分工,体现了人类最初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状况。之后,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牧业、商业、手工业的相对分离独立。伴随着社会分工,从事某一分工的人员相对稳定,便形成了职业,相应地为调节职业活动而制定的规范、价值理念等职业伦理逐渐形成。在我国上古文献中就有职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记载,《尚书·夏书·胤征》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意指工匠艺人们用包含在工艺技术中的道理进行规劝,这说明当时不仅出现了各种技艺性的职业分工,而且有了一定的职业规范要求。《周礼》将职官分为六类: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这是官员的职业分工。最后一篇《周礼·冬官考工记》又把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职业分工概括为“六职”,即“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尽管这种分工还是社会阶级、职业、性别混合在一起,但已经有了职业分工及其伦理的初步思考。
在儒家原创时期,孔子、孟子、荀子都有关于职业分工及职业道德规范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还是很初步和简单的。《孟子·离娄上》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虽然这些论述更多的是在谈朝野官民、君子小人的政治道德,但也包含着政治伦理对“工”这种职业伦理的影响。《荀子·王制》则对“工”的规范进行了专门论述:“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考察工匠的技艺、审查生产事宜、辨别产品质量、挑选坚固好用的器具是工师的职责。《荀子·王霸》篇则认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荀子上述思想虽然仍有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混同,但毕竟已经开始清晰地论述了农、商、工、士四民的基本伦理义务,是儒家职业伦理思想的重要端启。
从古至今,凡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欲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生存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都要从事一定的社会生产劳动或工作,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凡人不可以无职业,何则?无职业者,不足以自存也。”他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无正当职业,“无材无艺,袭父祖之遗财,而安于怠废,以道德言之,谓之游民”,其实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职业不仅是人的谋生活动,更是一种以某种特定事业活动而结成人群集团的方式,或者说职业是因为这类人要做一种特定的事而结成的人群关系,因此,也就形成了这类人的行规、特有品质、价值观念和作风,即形成了不同的职业伦理。
涂尔干在其《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把道德规范分为政治规范与职业规范两类,这二者构成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公共规范。他分析了西方历史上职业伦理的发展,认为,“在历史中,这种职业群体被称为法团(corporation)”,“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职业都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涂尔干认为,古罗马时期的“法团”还不是纯粹的职业团体,还兼有一些宗教、家庭共同体的性质,只有到了中世纪,随着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达和城市生活的兴起,“法团”才具有更为典型的职业行会性质。“法团用牢固的纽带把具有同样职业的人们结合起来。……在每一行中,雇主与雇工的相互义务也都有明确的规定,雇主之间亦如此,……其他规定则旨在保证职业诚实。”“法团或法团制度(regime corporatif)的重要性似乎并非因为经济原因而是源于道德的理由。唯有借助法团体系,经济生活的道德标准才能形成。”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第三等级即平民阶层或资产阶级得以发展起来,“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资产阶级和商人是完全一样的,……资产阶级就是城镇居民”。“商人(mercatores)和居民(forenses)这两个词与公民(cives)是同义的:都同样适用于公民权(jus civilis)和居民权(jus fori)”。可见,西方历史上的职业伦理与公民伦理具有产生根源上的内在联系。到了现代社会,大工业消解了这种法团组织,因为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再是一种地方性、城市性的活动,但在现代社会,仍然需要职业伦理,只是现代职业伦理需要国家力量的更多介入,“所有分崩离析的情形,所有政治无政府状态的趋势都会伴随着不道德的状况而产生”;“国家首先是一个道德纪律的机构”,“国家的基本义务就是:必须促使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公民道德所规定的主要义务,显然就是公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反过来说,还有国家对个体负有的义务”。通过国家道德或者公民道德对职业行为的调节,最终形成“产品和服务之间稳定和谐的交换,以及所有善良的人的相互合作,才能实现人们没有任何冲突而共。涂尔干在此书中分析了西方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历史和现代职业伦理的国家干预,充分说明职业伦理和国家伦理(或称之政治伦理和公民伦理)始终是社会伦理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
职业分工逐步明晰以后,相应的职业道德或者职业伦理就产生了。尽管传统社会的职业伦理远没有现代社会那么重要,中国传统道德或者儒家道德往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方面加以分类的,修身伦理是基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职业伦理虽然也有其传统,特别是一些比较稳定的自由职业伦理,如医德、师德、武德等历史悠久,但在主流伦理结构中似乎不占统治地位,有的职业被消解在阶级伦理中,比如士人道德大多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伦理而非职业道德;而涉及商业、手工业等行业的伦理规范大多是以民间行会、行规形式得以传承发展,它们显然在主流社会道德结构中不占主体地位。尽管如此,职业伦理在传统道德结构中还是长期存在、发展的,甚至梁漱溟先生还曾提出一种不为过去主流观点认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假如西洋可以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合相需之征也”。
恩格斯说:“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在阶级社会,虽然各阶级都有其道德,阶级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着职业道德,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这是因为,无论如何,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能离开做事,离开了做事就不能生产出物质和精神产品,也不能产生在生产中因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从而对产品和利益进行占有分配的阶级关系,没有阶级的存在,自然阶级道德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阶级社会,职业道德与阶级道德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也可以说,阶级社会的道德结构主要是由这两种要素组成的。
正因为职业伦理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它自身也就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其中以亘古延续的“执事以敬”为代表。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作为一种临事执业的态度、精神、行为规范,是在中国伦理史上出现较早的德目之一,具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
第一,执事主一专一。宋儒陈淳在其著作《北溪字义·敬》中说,“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无适之谓敬;尤分晓。……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主一只是心作主这个事,更不把别个事来参插。若作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插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可见,所谓“敬”,首先是指对某种职业和事业要全心全意去做,不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敬”可以说是人们从业精神的总动员,而且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
第二,对待事情严肃认真。在西周金文中,王或者诸侯在册封官职之后,经常告诫被封者“敬夙夜勿废朕命”,显然是要求被授职的人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君主的任命。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这里“敬事”是指严肃认真地对待政事。现代大儒冯友兰也说:“有真至精神是诚,常提起精神是敬,粗浅一点说,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论语》说:‘执事敬。’我们做一件事,‘当心’去做,把那一件事‘当成一件事’做,认真做,即是‘执事敬’。”
第三,勤勉努力。《周礼》郑注:“敬,不懈于位也”,说的就是努力。《说文》曰:“惰,不敬也,慢,隋也。怠,慢也,懈,怠也。”这些字的说解从反面说明了敬有勤勉、努力的含义。“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类》)。
第四,畏惧谨慎。《诗·大雅·报》中有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戏豫”是游乐安逸的意思,只看这其中的“无敢”,便可知“敬天”之“敬”含有畏惧的意思。只有敬畏天地万民,才会办事谨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引逸《书》曰:“慎始而敬终。”可见,敬和慎义极相近。
在西方,受新教的影响,甚至产生了“职业是天职”的观念。在新教教义中,“职业”一词是“呼唤”“呼叫”的意思,即人的职业是上帝在天上对人类的呼唤和命令,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恩神的恩召的举动。天职是一种使命,人必须各司其职、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辛勤劳作,才能获得上帝的青睐。人应该将世俗的工作视作自己的神圣天职,视作自己的信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这种视工作为天职的观念作为一种精神道德力量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做法,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特有的组成部分”。这种基于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职业天职观,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人的职业伦理进步,使西方从业人员对工作保有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工作,不是仅把工作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为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意义而工作。在本职工作中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才能获得上帝的认可。在现实生活中,做好本职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更是提升自我,实现进步的阶梯。
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不同,在敬业精神方面既有共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点。“中西方敬业精神在强调勤勉努力、严肃认真方面,有一致性。但由于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不同,强调主一专心、谨慎稳妥则是中国传统敬业精神独有的,与西方之开拓进取、倡导冒险精神等是大异其趣的。而西方敬业精神中把赚钱、成功看作是人生目的和人的天职,特别重视职业责任等因素,则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等价交换规律、权利义务相统一等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独具特色的,也是中国传统敬业精神中所没有的。”“敬业精神,作为一种对待职业劳动与事业追求的执事道德,不像人际道德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特征,而有更强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我们在研究现代职业伦理时也要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
二、职业伦理的现代地位与特性
职业伦理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但相较于传统社会,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职业伦理的现代特征。
正如前述,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是以修身的个体私德作为基础,而以家庭(家族)伦理和政治(君臣)伦理为核心,以天下治平伦理为目标的。职业伦理虽然长期存在,但并不居于核心地位。现代社会的生产活动打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工,这导致了现代的职业分化越来越细。虽然家庭仍然是人们的私人生活场所,但其生产甚至生活功能、教育功能、交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分离出来,人们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主要是在职业场所和公共领域中进行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社会的经济活动、个体的谋生职业活动和交往显得比传统社会更加频繁和重要,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是凭借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根据社会学的研究,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逐步淡化,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已经由过去的四世同堂、聚族而居演变为核心家庭模式,即一对父母和儿女两代人生活在一起的模式。业缘关系的强化致使职业交往的频度和广度都增强了,随之地缘关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整个社会逐步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依靠业缘关系维系的,这种发展变化凸显了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从个体的角度看,现代人的社会身份、利益获取、社会交往、自我实现主要是通过职业活动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平等,相区别的只是职业身份,人们在社会中因职业不同而获得的身份认同不同,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公民在私人生活中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庭身份。现代社会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公民的社会公共身份主要是一种职业身份,从事不同职业劳动的公民,以自己特定的劳动提供相互服务,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获得收入和经济利益,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生活的意义感,使自我得到了实现并获得了社会交往和社会荣誉的机会。
相较于传统职业伦理,现代职业伦理具有下述三个特征。
第一,从现代职业伦理的动力根源看,是利益与道义相统一。人们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劳动方式和职业形式取得生活资源、获得收益,因此,职业劳动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如果某人不遵守一定的职业伦理,其直接的后果或者危机就是会“丢了饭碗”,这是人们遵守职业伦理的自然的、基本的需要和动力,这也完全符合马克思“需要即他们的本性”的人性理论。人首先是一个肉体的自然存在,故必然有其基于生存和享受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的满足必须通过一定的职业劳动来获得;而人不仅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更重要的,人还是一个社会存在物,因此,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质,即谋生和奉献社会,前者必须按照按劳分配的利益原则来实现,而后者则是职业劳动更加崇高的社会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职业的崇高社会价值和自我实现意义,因此,人们在选择和从事职业活动时,一定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选择那些高收入、高回报的职业,同时也应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并且具有崇高社会价值的职业。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过上既富足又高尚的生活。如果仅以收入的多少和待遇的好坏为标准选择职业就会带来人性的某些异化,使人陷入一种物役主义的状态,从而失去精神的快乐和幸福的体验。如果仅仅将职业当作一种谋生手段,那么,职业劳动和职业伦理对其就是一种外在的束缚;如果能将利益的追求与道义的追求结合起来,职业就变成崇高的事业,人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持久的工作热情。
第二,从现代职业伦理的维护手段看,是契约与德性相协调。职业伦理不是被外部权威附加的道德教化,而是从业者们自发地创造和自觉地履行的一种行为规范。这是因为,选择职业的行为是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契约关系之上的。职业契约关系既为自愿,遵守该行业的行为规范也应是自愿的。某个行业的从业者遵守该行业的职业伦理既是德性,也是义务。正如涂尔干所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生活必须得到规定,必须提出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扰乱经济生活的冲突才能得到遏制,个体才不至于生活在道德真空之中。……有必要确立职业伦理,……规范必须告诉每个工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它必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而不能采用笼统的说法,它必须考虑到每天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情。”这段话不仅强调了职业伦理的契约性的必要性,而且还要求这种规范细化,才会具有更好的可行性。职业伦理具有契约性、规范性,甚至技术性,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职业伦理就变成了职业集团内部的律法,它的作用只能是外在性的他律。真正的职业伦理还必须变成从业者真正的职业德性、品质和作风,才能真正内在地发挥作用,这不仅需要职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职业伦理教育,也需要职业人员对其职业伦理规范、价值观有内在的认同、服膺和践行,从而使其成为自己内在的德性。某些学者在介绍涂尔干关于职业伦理的相关思想时,比较强调职业伦理规范的技术性、价值中立性,甚至非道德化,这是值得商榷的。职业伦理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契约的行业技术规范,更应该具有其价值性、道德性,舍此就不能称为伦理或者道德规范。当然,该文最后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要化解职业道德带来的道德困境,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德性伦理来恢复职业道德的道德属性,让‘职业道德对人们的道德品质’发挥重要影响。”因此,现代职业伦理应该是契约与德性的统一。
第三,从现代职业伦理的培育方式看,是制度与教化相配合。契约与规范必然在各种职业团体中以制度的形式得到体现和保障。因此,现代职业伦理在各种职业团体中往往以制度、守则、公约、誓言、条例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各个单位均有不同的岗位责任制和各种制度、公约,这样便于不同的职业与行业人员明确和践行职业伦理规范。这种显性的职业伦理规范具有行业规范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并且可以用组织制度的机制力量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贯彻实施。因此,现代职业伦理建设与培育,首先要求各个职业团体和单位要建立健全本职业团体、本单位的各种制度,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规范内容,这是其道德成熟性的表现,也是建设现代职业伦理所必需的,是职业团体的伦理责任。如前所述,现代职业伦理不仅是契约性的约束性规范,它还是人的自觉德性追求与培育,而职业人良好的伦理德性的养成不仅需要个体的修养与实践,更需要社会与团体的思想教化。只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有明确的职业伦理规范与制度,又有对员工及时有效的职业伦理教化,从而促成员工职业德性的形成,才能真正培育建设好本职业团体的职业伦理与道德。
三、职业伦理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现代职业伦理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是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干出来的,凝结在他们身上良好的职业伦理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由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进入建设时期。要建设发展,自然需要各行各业职业伦理的支撑。我们在道德结构认知上,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国家道德和主流道德为主导的新的道德结构体系,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在三大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即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其中,职业道德居于重要地位,这并不是否定其他两个方面的重要性,而是突出强调职业道德是集中体现公民的社会贡献和实质价值的领域。因此,新中国出现了很多职业伦理的典型,比如工人职业的“以工人王进喜为代表的铁人精神”、农民的“大寨精神”、军人的“雷锋精神”“王杰精神”、科技军事的“两弹一星精神”、干部的“焦裕禄精神”等,要取得非凡的成就,离不开职业伦理精神的支撑。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是基于职业人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热情,但从行为和效果的角度看,显然也可以视作一种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
1978年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模式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日益扩大,体现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的活动是其职业生活。经济活动与交往的复杂化需要更为具体的职业伦理加以规范,因为大多数职业活动与经济活动都有联系,职业伦理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显著增强了。正因为如此,相较于前一个发展阶段,社会和民众会更加重视职业伦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职业伦理建设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对比这两个阶段我们能明显地感到:由于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大锅饭”制度,“责、权、利的结合还不甚紧密,干好干坏一个样,责任由集体承担,加之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上的论资排辈、缺乏活力和竞争机制,这些都压抑了人们的社会积极性与敬业精神,甚至在部分人中还形成了与敬业精神相反的一种德行——混事(世)伦理态度。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做和尚也不撞钟,对职业劳动缺乏创业的热情,更谈不上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优质服务、精益求精。缺乏严肃认真、恪尽职守的职业责任感。以至人们在打招呼时,相互问候不是说近来‘干’得怎么样,而是问近来‘混’得怎么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工厂实行责任制、股份制,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等改革,并把这种旨在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改革精神和物质利益原则向各行各业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各个行业从业者的积极性,使职业伦理的提升具有了动力机制,涌现出很多具有高度职业伦理精神的群体和个人先进典型,比如,“北斗”科技青年创业群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白衣天使群体,甚至近年来形成的快递外卖小哥群体,他们均遵守着不同形式的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奉献着自己的智慧、汗水和辛劳。从个人模范典型方面看,有为“辽宁舰”歼15舰载机做出突出贡献的罗阳,有两次援藏而献出生命的党的好干部孔繁森,有像袁隆平、屠呦呦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抗疫也使我们了解了钟南山、张伯礼等医者的大爱职业精神。这些群体和个人身上无不体现出当代中国职业伦理提升的现状。它们集中体现为一种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总结我们当代职业伦理得到提升的经验,主要是:利益和竞争机制的驱动,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长期有效的思想教化。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并在今后的职业道德建设活动中继续坚持,发扬光大。
第一,用利益和竞争机制作为激发提升人民群众职业精神的动力。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人们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即从事职业活动换取生活资料,甚至是某些生产资料。职业伦理作为人的一种职业精神,确实离不开思想教化与培育,但也离不开一定的利益机制作为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是要以某种职业开展其谋生活动,以维持其生计的,他如果想获得该职业的权益与利益,就必须遵守该职业的伦理规范,具有某种敬业精神。因此,这必然成为职业伦理的内在利益驱动力。为什么有些人愿意投入全部的热情与精力去从事职业劳动,因为那关涉他们的收入、地位、成就感、事业心、荣誉感等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利益,这成为他们职业活动的根本动力。国家用合理的利益机制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鼓励竞争、奖勤罚懒等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这样依靠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通过敬业创新、甘于奉献的职业伦理支撑取得的。
第二,用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作为人民群众职业伦理的可靠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的满足、利益的追求成为职业伦理提升的动力机制。但除此之外,还要用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将职业伦理加以落实,并保障其持久健康运行。这些制度是一个体系,包含着很多相互联系的制度设计,比如契约制度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了从业人员的职业义务和责任及其行为规范甚至技术规范;又比如企业普遍实行的股份制改革,把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很好地连接为一个整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极大地保证了从业者对企业的忠诚与敬业;再比如,诚信监督制度很好地保证了服务过程中的职业伦理规范的实施。以电商的发展为例,我们在网上下单购物,稍后就会有物流、安装、回访、投诉和评价等多个环节跟进和衔接,电商、快递投送业务之所以能够顺畅运行,皆源于有供货商、电商中介、送货几方的很好的制度安排与制约,这些都很好地保证了职业伦理和操守的健康实践。制度有激励性的,有保障性的,也有约束惩戒性的,如中共中央近年来制定的若干党内惩戒制度就很好地发挥了防止干部贪腐的效果,推动了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完善;教育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教师师德一票否决的相关制度,对维护师德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职业伦理建设来说,制度的保障作用不可缺少。
第三,将长期有效的思想教化作为提升人民群众职业伦理自觉性的手段途径。职业道德比社会道德更具体,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道德主要依靠宣传教化,它具有深厚的利益基础,也需要根本制度和行业制度的保障。即便如此,我们在职业伦理建设上的进步仍然离不开长期有效的思想教化,这是因为道德是人的道德,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如果不具备自觉性、主动性,这种道德有可能仅仅是利益追求的自然行为,制度约束的规约,而不具更高的道德价值。因此,职业道德建设最终还是要按照道德建设的规律进行,坚持对民众进行长期有效的思想教化,使他们具有职业伦理的自觉意识和主动精神,而真正化约成他们的职业伦理精神、德性和良好作风,甚至形成不计定额、不计报酬、乐于奉献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崇高境界。实际上,很多劳模和敬业奉献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就是这样做的,值得全社会见贤思齐,向他们学习。
国家、社会、单位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将职业道德作为主流社会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职业道德与家庭道德、社会道德作为社会三大生活领域的道德,并把道德教育的主体在过去的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基础上,把单位也作为道德教育的主体。2019年又颁布实施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道德建设,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在道德养成中的作用。我们长期坚持评选的全国道德模范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其中“敬业奉献”就是针对职业伦理而言的,“诚实守信”也是职业伦理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牛”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公开提倡和奖励甚至新发布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很多精神其实从一定的角度看都是职业伦理,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职业伦理宣传教化工作的重视。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全社会树立了职业伦理的价值引领和道德楷模。全社会各个职业团体尤其是企业,普遍进行了企业文化与伦理建设,创造形成自己团体的职业价值观、职业精神与伦理规范并加以宣传、推广、培训,使之成为员工的职业伦理行为和作风,我们大力宣传职业伦理中的敬业精神,使民众普遍形成了较强的职业伦理意识和敬业精神,职业伦理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和进步。
职业伦理是人类道德结构中的一个永远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需要人们用良好的职业伦理推动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行各业的中华儿女用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拼命奋斗才能实现,因此,今后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在社会道德建设中重视并加强职业伦理建设。
来源:道德与文明(公众号)
编辑:张铭麟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30 21:12
【案例】
前沿转载 | 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利他主义(上)
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利他主义(上)
作者:Richard Kraut
译者:王宝锋
来源: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altruism/
当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自己以外的人的利益,通常被描述为利他主义。这个词与“自利”、“自私”或“利己主义”相反--这些词适用于完全出于为自己谋利的动机的行为。“恶意”指的是一个更大的对比:它适用于那些仅仅为了伤害他人而表达出伤害他人的愿望的行为。
然而,有时这个词被更广泛地用于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这种广义的利他主义可能被归因于某些种类的非人类动物--例如母熊,它们保护自己的幼崽不受攻击,并在这样做时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如此使用,并不意味着这种成年熊“为了”它们的幼崽而行动(Sober and Wilson 1998: 6)。
本文将讨论前一种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即为了其他个体的利益而故意采取的帮助别人的行为。关于利他主义有大量的、不断增长的经验文献,这些文献询问人类的利他主义是否有进化或生物基础,以及非人类物种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这些问题在关于利他主义和生物利他主义的实证方法的条目中有所涉及。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利他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呢?利他主义是否一定令人钦佩?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着想而行动?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事实上是出于利他主义而行动,还是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是自利的?
目 录
1. 什么是利他主义?
1.1 混合动机和纯利他主义
1.2 自我牺牲、强和弱的利他主义
1.3 道德动机和利他主义动机
1.4 福祉与完美
2. 利他主义是否存在?
2.1 心理利己主义:强和弱的版本
2.2 心理利己主义的经验论证
2.3 心理利己主义的先验论证
2.4 饥饿与欲望
2.5 欲望和动机
2.6 纯粹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
2.7 利己主义是否存在?(本期结束)
3. 自我和他人:一些激进的形而上学选择
4. 为什么要关心他人?
4.1 幸福主义
4.2 不偏不倚的理性
4.3 内格尔和非个人立场
4.4 感性主义和同胞情感
5. 康德关于同情心和责任
6. 重新审视感性主义
7. 结语
1.什么是利他主义?
在继续讨论之前,需要进一步澄清“利他主义”一词。
1.1混合动机和纯粹的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行为不仅包括那些为了给他人带来好处而采取的行为,也包括那些为了避免或防止他人受到伤害而采取的行为。例如,假设某人在驾驶汽车时格外小心,因为她看到她在一个有儿童玩耍的地方,她想确保她不伤害任何人。说她的谨慎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是合适的。她并不是想让这些孩子过得更好,但她很小心,不想让他们过得更糟。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真正地关心他们,为他们着想。
此外,利他主义行为不需要涉及自我牺牲,即使是出于混合的动机,其中一些是自利的,它们仍然是利他的。前面的例子中的司机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到达她要去的地方;放慢速度和多加注意可能并不违背她自己的利益。即便如此,如果她谨慎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孩子们着想,她的行为也算得上是利他主义。她也可能知道,如果她伤害了孩子,她可能会因为鲁莽驾驶而受到惩罚,她当然想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她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她的谨慎既是利他的,也是自利的;它不是只受一种原因的驱动。我们不应该被“自利”和“利他”是对立的事实所迷惑。一个动机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特征;但一个行为可以从两种动机出发。
如果某人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而实施某种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自利的动机,我们可以把她的行为描述为“纯”利他主义的案例。我们应该注意区分纯粹的利他行为和自我牺牲行为:前者不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后者涉及一些损失。如果某人有一张剧院的票,但他因为生病而不能使用,他打电话给售票处,让别人使用这张票,这是一个纯粹利他主义的案例,但它不涉及牺牲。
1.2 自我牺牲、强和弱利他主义
考虑一个人,他的考虑总是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除非这样做对我最好,否则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这样的人拒绝牺牲自己的福祉,哪怕是最轻微的牺牲。但是,考虑到刚才的术语,他可能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或者甚至对他所做的大部分或全部事情有利他主义的动机。在任何特定的场合,他都可能有混合的动机: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但这也允许他受到他所做的事情对别人也有好处的观念的激励。
如果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利他主义者,那将是很奇怪或误导的。很多人都会批评他不够利他。常识性道德的一部分是,一个人应该愿意与他人妥协--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要求他接受对自己来说不如其他方式好的东西,以便其他人可以得到他们的公平份额。
这些思考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结果:这样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但我们却不愿意,而且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兼顾这两种似乎都很紧张的想法的最好方法是区分“利他主义”这个词的两种用法。如果一个行为是在感觉到它涉及到个人福利的一些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它就是强势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如果一个行为的动机,至少是部分动机,是为了使别人受益,或者是为了不伤害别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弱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上面两段描述的个人是一个从未在强意义上采取利他行为的人。这种政策似乎令许多人反感--尽管他在许多情况下可能采取弱意义上的利他行为。
1.3 道德动机和利他主义动机
在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中,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出于道德动机,但不是利他主义。假设A向B借了一本书,并承诺在一周内归还。当A在最后期限前还书时,他的动机可以被描述为道德性的:他自由地做出了承诺,他认为自己有义务遵守这种承诺。他的动机只是为了遵守诺言;这不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例子。但是,如果A把一本书作为礼物送给B,认为B会喜欢它并觉得它有用,他的行为只是出于使B受益的愿望。
同样,假设一位母亲不给她的成年儿子提供关于某件事情的建议,因为她认为她不应该这样做--这将是对他私人事务的过度干涉。即便如此,她也可能认为他将从接受她的建议中受益;她尊重他的自主权,但担心他因此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她的克制是有道德动机的,但通常不会被描述为利他主义的行为。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利他主义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出于道德动机的对待他人的行为,而是更狭义地适用于出于对他人利益的关注-—换句话说,对他人的福祉的关注。利他主义行为可能被描述为慈善或仁慈或善良,因为这些词也表达了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正确地对待他人。
通常情况下,作为利他主义行为“目标”的个人被选中接受这种待遇,是因为施惠者和受益者之间有个人联系。如果A在B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B特别好,而在后来B有能力帮助A走出困境,那么B对A的帮助就是利他主义的动机,尽管他们共同的过去解释了为什么B选择帮助的是A(而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这里假定B不是把促进A的幸福作为他自己(B)的幸福的一个单纯的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B就不是为了A而使A受益,而只是为了B而受益。(另一个假设是,B的动机不仅仅是他欠A的回报;相反,他不仅觉得欠了A,而且还真正关心他。) 我们以利他主义方式对待的人往往是那些我们对其有感情的人,或者我们对其感到感激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有些利他行为的动机仅仅是认识到受益者的巨大需求,而受益者和施助者可能是彼此陌生的。
一个行为的动机是利他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合理的或值得赞扬的。A可能错误地认为她在提高B的福利;B也可能错误地认为她在从A的努力中受益。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A的动机是值得赞赏的,但仍然可以判断她不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
1.4 福祉(Well-Being)与完善
如上所述,利他主义行为是由代理人对其他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福祉的假设所引导的。福祉包括什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没有争议的是,必须在(i)什么构成福祉和(ii)什么是实现福祉的必要手段或前提条件之间做出区分。这种区分是人们所熟悉的,并且适用于各种情况。例如,我们区分了早餐的内容(麦片、果汁、咖啡)和吃早餐所需的东西(勺子、杯子、水杯)。不存在吃了早餐却没有吃早餐所包含的任何东西的情况。同样地,必须通过寻求和促进福祉所包含的一种或多种物品来寻求和促进福祉。对立的福祉理论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竞争性方式: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在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需要解决如何最好地获得这些成分的进一步问题。(关于福祉的当代讨论可以在Badhwar 2014; Feldman 1994,2010; Fletcher 2016; Griffin 1986; Kraut 2007; Sumner 1996 Tiberius 2018中找到。)
福祉是有程度之分的:一个人拥有的物品越多,他的处境就越好。对一个人说:“她有福祉”是一种尴尬的说话方式。表达这一想法的更自然的方式是使用这样的术语:“她过得好(faring well)”,“她很好(well off)”,“她正在蓬勃发展”,“她的生活对她来说很好”。福祉的成分也可以说成是利益或好处——但当人们使用这些术语来指称福祉时,必须认识到这些利益或好处是福祉的成分,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价值。换句话说,利益和好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某人有好处的,仅仅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其他物品,另一类是对某人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是该个人的福祉的组成部分。
在擅长于什么和什么于自己好之间必须作出区分。说“他擅长于演戏”是一回事,说“演戏于他有益”是另一回事。哲学家们把前者称为“完美主义价值”,把后者称为“审慎的价值”。这是因为当一个人试图做好某件事时,他希望能更接近完美的理想。审慎价值是指某人对之的获取符合其利益——它属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术语组:“福祉”、“福利”、“利益”等等。
即使必须区分完美主义和审慎价值,也不应该推断出擅长某事不是福祉的构成要素。回到上一段使用的例子:如果某人有很好的演员天赋,并且喜欢表演和戏剧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说他的福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对这些活动的享受,是有道理的。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事实在起作用。(i) 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ii) 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对他有好处(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手段,而是作为他的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i)中提到的价值是完美主义的价值,(ii)是审慎的价值。换句话说,他继续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是审慎的。
这些关于福祉和卓越的观点与利他主义的研究有关,因为它们有助于防止对利他主义者可能在他人身上促进的各种益品的过于狭窄的概念。利他主义者并不只是为了减轻痛苦或避免伤害——他们也试图为他人提供积极的利益。什么算作利益取决于正确的福祉理论是什么,但人们普遍认为,某些类型的卓越是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例如,有人创办了一所学校,培训儿童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或在体育方面表现出色,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喜欢锻炼这些技能,这样的人将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公共捐助者和慈善家。同样,培养学生和孩子们对文学的热爱以及欣赏文学所需的技能的教师和家长也会被视为利他主义者,如果他们的动机是认为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对这些学生和孩子的好处。
然而,一个人有可能在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同时,对人类的福祉完全漠不关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并不倾向于说这样的人是受利他主义的激励。有人可能致力于某个学科——数学、哲学或文学——而不是致力于研究和掌握该学科的人的福祉。例如,想象一下一个文学学生,他非常关心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因为他认为它是人类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他不希望这本小说只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落满灰尘——它应该得到读者的喜爱和理解,因此,欣赏它所需要的技能必须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种对完美主义价值的奉献不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形式。
对于一个行为来说,利他主义的动机是施惠人——而不是受益人——对它有某种态度。一个从网球教练那里获得了优秀运动员的技能和对网球运动的热爱的孩子,可能只是把网球当作一种很好的乐趣,而不是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也不是他生活顺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孩子不需要因为他相信这样做对他有好处而练习他的技能:这不是他成为利他行为的受益者的必要条件。同样,有人可能否认身体上的痛苦算作对他不利的事情。(根据斯多葛派,他应该否认这一点。)但在任何合理的福祉理论中,他都是错的;一个人出于对另一个人的福祉的关注,旨在减少他的痛苦,就是利他主义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考虑一个人对哲学的热爱并沉浸在这个主题中。当她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时,她可能会回答说她的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她可能会说:“哲学本身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我想解决心身问题和自由意志问题,因为这些是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向她建议,她的哲学奋斗是她福祉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可能会认为这是看问题的一种奇怪方式。但她的观点并不具有权威性-——她是否正确取决于最佳的福祉理论是什么。其他关心她的人可以合理地认为,她对哲学的热爱是她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构成了对她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对她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管它是否导致了一些进一步的结果。如果他们仅仅为了她的利益而帮助她追求她的哲学兴趣,他们的动机将是利他主义的,即使她自己并不是因为认为哲学对她有好处而关心哲学的。
2.利他主义存在吗?
2.1 心理利己主义:强和弱版本
根据一种被称为“心理利己主义”的学说,所有人类行为最终都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心理利己主义者可以同意常识所认可的观点,即我们经常寻求使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受益;但他说,当我们这样做时,那是因为我们把帮助他人仅仅看作是为自己谋好处的手段。根据心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并不是为了他人而关心他们。换句话说,利他主义并不存在。
既然我们已经区分了使用“利他主义”一词的几种不同方式,那么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利己主义之间做出类似的区分将是有帮助的。回顾一下,如果一个行为的动机,至少是部分动机,是为了使别人受益(或不会伤害别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弱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上一段所定义的心理利己主义,否认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这是这种学说的最强形式;这通常是哲学家们在讨论心理利己主义时想到的。但我们可以想象更弱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会否认利他主义曾经是纯粹的;换句话说,它会说,每当我们行动时,我们的动机之一是对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渴望。另一种较弱的心理利己主义形式认为,我们从不自愿做我们预见到的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我们福祉的事情。这第三种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会承认,有时我们行动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为他人着想而做的好事;但它声称,当我们认为这样做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时,我们永远不会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
2.2 心理利己主义的经验论证
有人可能会得出这些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人类场景的敏锐观察者,而且她对其他人的了解使她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动机。但这种为心理利己主义辩护的方式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其他人可以对这个心理利己主义者说:“也许你认识的人是这样的。但我对世界的体验与你的相当不同。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努力造福他人。我自己的行为也是利他主义的。所以,你的理论最多只适用于你社会世界中的人。”
心理利己主义者可以用两种方式回应这种批评。首先,她可能声称他的学说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也就是说,她可能认为:(i)心理学家在精心进行的实验中研究的对象被证明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或者(更强烈的)这些对象最终只关心自己的利益;(ii)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验中推断出所有的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激励。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实验证据表明,对心理利己主义的强和弱形式表示怀疑,但争论仍在继续(见Batson 2011;Stich等人,2010)。
2.3 心理利己主义的先验论证
心理利己主义者的第二种反应是为这种学说的一个或另一个版本进行先验的哲学论证。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可以“从扶手椅上”看到——也就是说,不需要寻求任何形式的经验确认——心理利己主义(以其形式之一)必须是真实的。
这样的论证可以如何进行?借鉴柏拉图对话中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肯定两个前提。(i) 促使我们行动的总是一种欲望;(ii) 所有的欲望都应该按照饥饿的模式来理解(见Meno 77c;Symposium 199-200a, 204e)。
阐述一下(ii)背后的想法。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的饥饿感有一个对象:食物(或者也许是某种特定的食物)。但我们并不是为了食物本身而摄取食物;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我们期望通过吃东西而得到的满足感。摄取这块或那块食物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只是作为实现满足感或饱腹感的一种手段。
如果所有的欲望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所有的动机都采取欲望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心理上的利己主义在其强形式下是真实的(因此其较弱的版本也是真实的)。考虑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利他主义动机的行动。我给你一个礼物,仅仅是因为我认为你会喜欢它。现在,既然我想给你这个礼物,而所有的欲望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饥饿,我在渴望你感到高兴,就像我在渴望一块食物。但是,就像没有人愿意为食物本身而摄取一块食物一样,我也不希望你为自己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所寻求的是你高兴时我将得到的满足感,而你的高兴只是我获得满足的手段。因此,我们不必对其他人进行敏锐的观察,也不必看自己的内心就能得出心理上的利己主义。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动机和欲望的本质,就能认识到这个学说是正确的。
2.4 饥饿和欲望
但是,所有欲望在相关方面都像饥饿的假设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人在吃完饭后仍然感到饥饿,那么饥饿感就不会得到满足。它在自己身上寻求某种意识。但许多种类的欲望并不像那样。例如,假设我希望我年轻的孩子在我死后很久还能像成年人一样富裕,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实现这一遥远目标的几率。我的愿望是他们在遥远未来的繁荣,而不是我现在或未来的满足感。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真的会带来我所寻求的目标;我所知道的是,当他们成年时我不会活着,因此,即使他们繁荣了,也不会给我带来快乐。(因为根据假设,我只能希望,而且并不感到自信,我为他们所做的规定实际上会产生我为他们所寻求的好结果,所以我从我的行为中得到的当前满足很少。) 因此,如果说我不是为了他们而希望他们繁荣,而只是作为实现我自己的某些目标的手段,那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目标是他们的福祉,而不是我自己的福祉。事实上,如果我把我自己需要的资源分配给他们,希望这样做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在做一种心理利己主义所说的不可能的事情:为了别人,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心理利己主义者声称这种自我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欲望都像饥饿一样,那么回答应该是,这种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的欲望情况。
回顾一下扶手椅上的心理利己主义者所使用的两个前提。(i) 促使我们行动的总是一种欲望;(ii) 所有的欲望都应该按照饥饿的模式来理解。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二个前提是不可信的;而且,由于这两个前提都必须是真实的,论证才能得出结论,所以这个论证可以被拒绝。
2.5 欲望和动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论点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值得商榷的。
只有当我们很好地理解了什么是欲望的时候,这个关于促使我们行动的东西总是一种欲望的论点才应该被接受。如果欲望被简单地认定为促使某人采取行动的任何内部状态,那么,“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总是一种欲望”这一说法,当被更全面地阐述时,就是一个同义反复。它说:“促使我们行动的内部状态总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内部状态”。这不是对人类心理学的实质性见解,而是一个同义声明,其形式为“A=A”。我们可能以为我们通过被告知“促使人们行动的总是一种欲望”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如果“欲望”只是激励我们的任何东西的术语,我们就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见Nagel 1970: 27-32)。
这里有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观点:正如“欲望”(desire)和“想要”(want)这两个词经常被使用的那样,说:“我不想这样做,但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不愉快的责任或义务时,或者当我们面临一个我们预计会很困难和紧张的挑战时,我们经常会说这种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渴求我们走向的目标。因此,正如人们经常使用的“欲望”一词,促使我们行动的总是一种欲望,这根本是错误的。现在,为这一学说寻求先验辩护的心理学利己主义者可能会说:“当我声称促使我们行动的东西总是一种欲望时,我并没有使用有时使用的‘欲望’这个词。我的用法要宽泛得多。在欲望中,在广义上,我包括一个人应该做某事的信念。事实上,它包括任何导致某人采取行动的内部状态。”
显然,当我们这样理解时,那种认为促使我们行动的总是欲望的论调是空洞的。
我们经常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别人的常识性术语,并不需要指我们自己的欲望。你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了一个外表令人讨厌但似乎需要你帮助的人。他看起来很痛苦,或者很困惑,或者在某些方面有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你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向他提供帮助。你认为你应该问他你是否能提供帮助——尽管这将耽误你的时间,并可能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和不适。这些描述你的动机的方式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向他提供帮助,而没有必要再加上“我想帮助他”。诚然,当“欲望”被用来指代激励某人的任何东西时,你想帮助他是真的。但是,在这些情况下,起解释作用的是你对他的需要的认识和你的判断,因此你应该提供你的帮助。说“我想帮助他”会有误导性,因为这将表明你期望通过提供帮助得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东西。的确,在你帮助他之后,你可能会回想这次的遭遇,并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但你可能不会,你可能会担心你所做的事实际上使他变得更糟,尽管你有良好的意图。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回顾自己的善举时感到高兴,并不意味着感觉良好一直是你的目标,而你只是把他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有当欲望在本质上是一种饥饿的形式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2.6 纯粹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
在上面区分的三种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中,最不容易受到反对的是认为利他主义从来都是纯粹的弱形式。它声称,每当我们行动时,我们的动机之一是对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渴望。这个论点没有很好的先验论证,或者说,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关于最强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的先验论证并不支持它,因为该论证中使用的两个前提是如此的不靠谱。但还是有人提出,事实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一些自利的动机伴随着利他主义动机的行为。要反驳这个建议是很难的。我们不应该假装我们知道支撑我们行为的所有考虑和原因。我们的一些动机是隐藏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心理的全部。因此,就我们所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纯粹的利他主义者。
但是,另一种弱的心理利己主义形式呢?这种形式承认,有时我们行动的理由之一是我们为他人着想而做的好事,但声称当我们认为这样做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时,我们永远不会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换句话说,它说,我们从不自愿做我们预见到的会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我们福祉的事情。
关于这种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首先要指出的是,再一次没有先验的论据来支持它。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两个前提——所有的行动都是由欲望驱动的,所有的欲望都像饥饿一样——是不可信的,所以它们不支持我们从未在任何程度上牺牲我们的福祉这一论点。如果这种形式的心理利己主义要得到支持,它的证据就必须从对每个人的行动理由的观察中得出。它将不得不说:当我们的动机被仔细检查时,确实可以发现,尽管我们为他人着想而为他人做好事,但当我们认为这样做会减损我们自己的福祉时,我们绝不会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把别人的好处算作本身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但这总是一个弱的理由,因为它永远不会像来自我们自身利益的理由那样强大。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如此的统一。关于人类动机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它们因人而异,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从来不是利他主义者;有些人就像这种微弱的心理利己主义形式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利他主义者,但只有当他们认为这不会减损他们自己的福祉时才会这样做;然后还有属于第三类很大类别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为他人牺牲他们的福祉。在这个类别中,范围很广——有些人只愿意做出小的牺牲,有些人愿意做出较大的牺牲,有些人愿意做出特别大的牺牲。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允许我们对每个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证据,以便我们对他进行定性。我们不应该根据一些先验的理论给每个人贴上利己主义者的标签;相反,我们应该根据我们能看出的他们的动机来评估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程度。
2.7 利己主义是否存在?
关于我们假设存在利他主义这种东西的理由,还应该进一步指出。正如我们可以问:“是什么让我们有资格相信利他主义存在?”我们也可以问:“是什么让我们有资格相信利己主义存在?”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每当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种可能性?
利己主义者可能会再次回答说,我们所有的行为最终都只受自我利益的驱使,这是一个先验的真理,但我们已经看到支持这一论点的前提的弱点。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时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假设是真的,它必须基于由对人类行为的密切观察的支持而向我们推荐自己。我们必须找到某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促进自己的利益的实际案例。对这种事情有信心并不比对某人纯粹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行为有信心容易。我们意识到,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对其他人也有影响,而且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关心这些其他人。也许我们的最终动机总是包括一个关心他人的成分。要找到反对这一建议的证据比人们想象的更难。
如果把事情推向一个极端,可能会有人提出,我们的最终动机总是完全出于对他人的考虑。根据这一不可靠的假设,每当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时,我们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完全为了别人的利益。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否认利他主义的存在应该和这种相反的否认一样被怀疑,根据这种否认,人们从来没有最终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两者都是令人怀疑的普遍性概括。两者的可信度都远远低于常识性的假设,即人们有时以纯粹的利己主义方式行事,有时以纯粹的利他主义方式行事,而且经常以不同程度地混合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的方式行事。
译者:王宝锋
注: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王子笔记,原始链接:
来源:中国伦理在线(公众号)
编辑:马源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3-31 21:43
【案例】已贴网站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
“自由”二字,中国古已有之,但时常写作“自繇”。自由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是一剂具有诱惑力的毒药,人人都想要,却是一个贬义词。《东周列国志》中宣王斥责臣下曰:“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顾名思义,自由的意思就是“由着自己”,为所欲为,不受拘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据说隋文帝杨坚的爱妃被皇后偷着杀掉了,杨坚一气之下骑马出走,狂奔二十多里,流连于山谷之中,叹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后来皇后去世了,无人管着,杨坚压抑了多年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纵情声色,两年后便一命呜呼。临死前对人说,如果皇后在,我不至于此。宋儒讲“存天理而灭人欲”,自由大约也就相当于“人欲”的意思,也就是一种动物性的欲望冲动。
到了20 世纪,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自由论》( On the Liberty)时遇到了麻烦:他明知穆勒的自由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为所欲为的意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对等的中国字来译,只好权且用“自繇”这个今人不太常用的词来代替,并将书名改译作《群己权界论》。然而直到今天,懂得严复这番苦心的人仍然如凤毛麟角。有人甚至否认人有自由,认为所谓自由不过是人的心理感受而已,实际上人都是受规律和命运支配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自由?本文打算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自由的起源;二是自由的历史;三是自由的谱系。
自由的起源
通常我们讲的自由有广义的自由和狭义的自由。狭义的自由只有人才具有,是人和其他事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至于广义的自由,我们有时候觉得自然界也有,自然万物都在自由生长。但是就无机物而言,虽然物理学上有所谓“自由落体定理”,不过那只是借用,真正说来无机物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无机物没有“自”。什么是“自”?“自”具有一种自我保持的特性,是一个内在目的,所以它是属于有机物的。有机物有“自组织”的能力,西文“有机的”(organisch)一词本来的意思就是“组织起来的”、“有组织的”。但严格说来,有机体的自由也是我们人看出来的,是拟人化的结果。我们通过拟人化可以把我们的自由感推广到动植物身上,甚至于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身上,这就是“造物”的概念,“造化”的概念。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具体的自然物如动物意识到了自身的自由,但我们也的确可以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自由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从无机物到植物、动物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级的部分,所以人的自由就可以代表自然界的自由。有机生命是人的自由的前提,人要有自由首先要有“自”,所谓自由就是不受他者束缚,那就要有自和他的区别。有机体有了自和他的区分,就可以“依自不依他”,就可以摆脱“他”的束缚。但是有机体的“依自不依他”和人的自由还是有所不同:它是相对的,绝对地来说还是要依他:植物和动物都要依赖于整个自然环境。达尔文进化论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天择”,它自己没办法择,只能够适应。这种“天择”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动植物自己是料不到的,它们所依靠的是本能。动物的行为是由本能所支配的,它没有能动性,也没有创造性。它也可以有选择,有任意性,但动物的任意是以本能为边界的,动物从来不做那种不能够用本能来解释的事情。人则可以胡思乱想,并且可以把这种胡思乱想付诸行动。于是人就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有语言和思维,这就可以在一个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来设定自己的目的。人的目的不可能全都用本能来解释,有些完全是超越本能的,甚至于超越生命的求生本能,比如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么,人的自由与动物的任意这个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就涉及人猿之别的问题。人和猿的区别,按以前流行的观点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野生的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了。动物学家珍妮·古多尔告诉我们,黑猩猩为了吃到蚁穴里面的蚂蚁,它可以掰一根树枝下来,把上面的叶子去掉,加工成一根合适的钓杆,伸到蚁穴里面去钓蚂蚁。(参见古多尔,第277 页以下)那么人跟黑猩猩的区别究竟何在?我认为这个区别不在于制造工具,也不在于使用工具,而在于保存和携带工具:保存、携带工具比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关键。很可能,人类最早就是由于要携带工具才学会了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它不会保存工具,用完就扔了;它的前肢要用来走路和爬树,不可能把工具总是带在身边,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也不会把这种东西传下来。而人类则由于保存工具而使工具连同其使用经验都得到了传承,这是人类所特有的。只有保存、携带工具,才把工具当成了一种普遍的媒介: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而是可以反复不断使用的。这样一种行为使得人类的观念中产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一种“符号”现象:工具成了一种符号。什么是符号?就是一种普遍性的表象:与它相关的对象可以变来变去,但是这个符号永远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与此几乎同时,人类还制造出了另外一种符号,并且把它保存下来了,那就是语言。保存工具和形成语言在心理学上应该属于同一层次的功能,这是人类和猿类最重要的两大区别。动物也有类似语言的东西,它是呼喊性的,是“信号”而不是符号。比如狮子来了,黑猩猩用叫声提醒同伴,这不能说是真正的语言。什么是真正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是从“命题语言”开始的,它不是一种信号,而是一个“命题”:首先是对一个东西的命名,用一种发声来代表这个东西,并且对它加以陈述。这不是说:“狮子来了大家快逃啊”,而是说:“这是狮子。”这样一种客观的陈述才是符号,才是真正的语言。这样,不仅在狮子来了的时候可以警告大家,而且在狮子没有来的时候还可以谈论狮子,互相交流对狮子的看法,甚至还可以扮演狮子、模仿狮子。这种情况只有人才有,其他动物没有。例如黑猩猩在一起时是沉默的,顶多有些互相梳理毛发之类的“肢体语言”。工具是人与大自然交流的媒介,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这两者都是人的符号,从中就形成了概念。工具的保存和语言的形成都有一种抽象的作用,把动物的心理活动提升到了严格意义上的“意识”,也就是“类意识”。
人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自己的本质。类意识已经是一种超越意识了,它表现在语言上:语言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的手段,使人意识到他人和自己一样,是“同类”,这样人就在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人要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而在一个社会中,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于是人就产生了对自己的反思。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首先就体现在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反思自己。反思使人意识到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人的意识就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超越自己和对象的肉体的区别而看到了精神的共同性。
什么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在对象中看到自己,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由此形成类意识。通过类意识,人就不光是有物质生活了,而且也有了精神生活,有了理性,有了自我意识,动物性的本能欲望由此提升到了意志。欲望和意志是不一样的,欲望是随机的,饿了就要吃,满足了就没有欲望了。但意志是要一贯下来的,这就要求有意识的普遍性,它包含有理性。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意志力,是说他做事不能坚持。怎样才能坚持呢?必须有理性,还必须按照理性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什么是自由?自由首先表现为生命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多次提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不是单纯的欲望了。相反,对欲望来说,人的自由是一种克制。我们经常以为对欲望不加克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自由。其实自由在人这里一开始就是对欲望的克制,比如说劳动就是对欲望的克制。当我已经吃饱了时,为了生存我不能休息,还得去干活,甚至吃饱了就是为了去干活。还有克制食欲:虽然我很想放开肚皮吃一顿,但是不能,因为有的要留作种子。还有渔猎的诱饵,也是不能享用的。劳动首先就是对欲望的克制,这充分体现了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的,是对自然(本能)的超越。劳动也是创造: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要能够把它创造出来,这就是对于自然的超越。自然包括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然:克制欲望是超越内在自然,创造则是超越外在自然。我们今天的工业技术、飞机、电视机等等,都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单凭自然界是产生不出来的。在这两者中,首先是对内在自然的超越构成了自由的源头。真正的自由可以归结为在一个普遍理性的层面上驾驭欲望。当然也包含满足欲望,但跟动物的满足欲望不一样,它不是临时性地满足欲望,而是在一种普遍理性的层面上,有计划有步骤地驾驭人的欲望、规划人的欲望,并且通过克制欲望而更大地满足欲望。动物看到什么想要的,就扑过去把它吃掉;它不会像人这样设一个机关来捕捉别的动物。人借自己的理性而强过一切动物:他为什么能成为万物之灵长?就因为他的机巧、他的理性、他的普遍性的设想能力,以及基于理性之上的克制欲望的能力,通过克制欲望来满足欲望的能力。
而正因为人在日常的劳动、狩猎或种植活动中已经体现出有这种克制欲望的能力了,所以他同时也就具有了超越一切欲望的创造能力。最初的克制能力还是在欲望的框框之内,是为了满足更大的欲望;但这种能力一旦形成,人就具有了更高的超越的可能,就是说甚至可以不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而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欲望,纯粹为了精神的创造,比如说献身于艺术,发明“奇技淫巧”,或者为了好奇仰望星空,做科学和哲学研究,以及克制求生的欲望来成全某种道德理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一种超越精神。但是所有这些超越性的根,都是从劳动本身、即通过克制欲望来实现更大的欲望这种机制中培育起来的。只要培育了克制欲望的能力,人就有了很大的余地,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当然也包括为人类谋利益,但是还有更加超越的事情,这种超越就是真正的自由。科学、艺术、道德,这样的目标就是真善美的目标,也是真正自由的目标。自由的起源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就是从人的劳动中,从人的生命活动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地产生出来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超越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就是自由。
然而,卢梭说过,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第4 页)“生来自由”是人的一个使命,一种本质可能性,而非一种现实;人必须去不断地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自由人。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就是在枷锁中不断追求自由的人,但这恰好说明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只有感到不自由的人才会去追求自由。反过来,一个安于不自由的人,一个自愿做奴隶的人,他因此也必须独自为他的受奴役负责。所以,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和一个可能的自由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他们都在枷锁之中,但前者是不断地解除和突破枷锁而越来越自由,后者却是承认枷锁而自我禁锢,他的自由停留在沉睡状态。现实的自由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历史过程。
自由的历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人类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体现为从东方到西方的进程: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基督教以来的西方则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第19页)就东方来说,在中国,人们只知道皇帝是最自由的,但又人人都想当皇帝,人人都有帝王思想,这种观念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而古希腊知道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也就是奴隶主和自由民都是自由的,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奴隶除外。到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世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知道了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还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由健全的宪政法律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这一点直到黑格尔的时代都还没有做到。
但黑格尔的这一划分是很有历史感的。中国古代的自由意识正像他所说的,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他同时也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同上,第18 页)换言之,东方、包括中国古代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中国先秦时代,整个社会你取我夺、弱肉强食,礼崩乐坏成为流行时尚,自由也就被理解为穷奢极欲。孔子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这种自由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由,退回到了动物式的本能欲望。当然,动物式的本能从广义上也可以看作一种自由;但在狭义上,只有对这种自由进行反思,才会有一种人类起码的自由意识。儒家将这种自由冠以“人欲”而弃之如蔽屣,而道家则对人的广义的自由进行了一种反思。道家是拟人的,庄子就经常把河里的鱼、天上的飞鸟、旷野里的树都看作是自由的;但是庄子的拟人不是导致树立人的自由的主体性,而是导致回归自然。这是一种逆反,但这种逆反是否定一切社会生活;它不是一种反抗精神,只是一种逃避。
道家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本性,但是他们是在自然的层次上来理解这个自由的,是向后看的,就是说要能够离开社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那多好!他们以为脱离社会人就自由了。其实脱离社会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老庄是在生物界的自由这个层面上理解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上升到普遍的理性,不愿意上升到语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2章)、“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他们拒斥语言、拒绝符号、拒绝一切形式规范,只求内心的轻松,这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无意志的自由”就是植物动物的那种自由,它等于自然界。所以《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游于自然之中,和自然齐一。可见,与其说庄子追求自由,不如说他追求逍遥。什么是逍遥?就是脱离社会,到大自然里面去,你就逍遥了。今天很多人喜欢到处旅游,到大自然里去“放松放松”,放松就是逍遥。
儒家和法家都把自由贬低为人欲,一个要灭除,一个要利用。理论上儒家说得较多,主张不要太自由了,要坚守某些规范,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动物式的欲望。他们把道家的自由看作是动物式的欲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没错。道家确实是崇尚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其实是自然。而儒家是主张超出自然的,强调人禽之辨,但一超出自然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儒家讲的是一种意志,但却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有人说儒家也讲自由,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不就是自由吗?但是又不破坏规矩。只不过很少有人想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个“矩”,它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由先王传下来的,是无可选择的。孔子经过七十年的“克己复礼”的训练,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那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当然,儒家和道家的区别也不是那么严格的,道家有些言论也近似于儒家,儒家也常常表现出道家的情怀,所以李泽厚讲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结构,中国人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是片面的。(参见李泽厚,第49页以下,特别是第53页)但这个“儒道互补”并不是双方统一,而是交替摇摆,在穷达之间顺势流转:一会儿是“无自由的意志”,一会儿是“无意志的自由”;两者都跳过了中间的自由意志,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换言之,要么就没有自由,只有意志的强制;要么就像动物似的率性而为,没有规矩,这在社会生活中是容不下的,只好逃到自然界里面去。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也是有自由的,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的自由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所以中国人的自由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他们要么把自己的自由等同于自然,要么就不讲自由、贬低自由。这是中国文化对自由价值的一种遮蔽。
现在再来看看西方自由意识的发展。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产生则导致了西方个体人格的独立。马克思讲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册,第49页),他们的儿童期的自由意识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古希腊的神话里诸神完全是拟人化的。到了中世纪,他们的拟人化主要体现在上帝身上,对上帝的理解折射着人对自由的理解。但所有这些拟人化都已经不单纯是自然本能的发泄了,而是加入了理性。比如古希腊神话中有神的自由意志,也有神的法律,雅典娜是理性之神,宙斯是法律之神。基督教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的律法通过摩西传达给人类,上帝是立法者。宙斯和上帝都具有一种理性的自由意志。当然,宙斯还充满着人间的情欲,并且掌握着自然界的雷电;但他不仅仅是情人或雷电,他主要代表法律,代表对人间自由的调节原则。基督教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创造了自然界,但是上帝远远超出了自然界,他代表精神上的追求,代表正义。西方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的反叛,跟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对着干。这种自由被理解为一种逆反心理;但是与道家的逆反不同,西方人接下来就对这种自由进行积极的探索,产生了一批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他们每个人都来设计一种理想的社会,说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这样:以往的社会最多是自然状态,那是非法的,必然陷入到弱肉强食;我们从今以后应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当然,这个理想在法国大革命那里当时是失败了,因为法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还处在逆反期。但是英国早在17 世纪“光荣革命”时就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以后经过好几代人的修改和协调,使这个理想最终实现出来、完善起来了。
西方近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法权哲学,特别是权力制衡理论,标志着西方自由意识已经进入到了实行期和成熟期,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叫做“天赋人权”,也就是人人生来自由。每一个人都生来自由,那么这里面就包含有平等,就是平等地自由。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所提出的口号。但实行期的特点就是形成了政治自由的理念。光是有口号,没有制度保障,那还不是成熟的自由意识。政治自由就是着眼于建立保障每个人平等地自由的社会制度而提出来的,这是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由放在政治的层面上考虑过,它顶多被看作个人的一种心情或境界。政治自由为其他自由奠定了基础,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贸易自由、迁徙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没有一种是儒家或道家关心过的。自由和意志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体的:近代西方人一讲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自由和意志是不可分的,没有什么“无意志的自由”或者“无自由的意志”。
到了康德,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又为政治自由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自由主义人性论的理论建构。后来还有些改进,像黑格尔,他对康德的批判只不过是把这一套自由的抽象理论加以充实,在现实中加以推演,把它建构为一个历史过程。当然他也有很大贡献,但基本的自由原则康德已经奠定了。还有像现代的哈耶克、罗尔斯,进一步把自由理论细化了。哈耶克讲程序正义,通过程序正义来建立人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讲社会正义,强调最终还是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有大致相当的平等,要有起码的保障,能够使一个人和比他优越的人有大致相同的竞争条件。或者说,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这两者如何协调?平等究竟应该是起点上的平等还是分配结果上的平等?罗尔斯认为应该两者兼顾。这一套东西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引进中国,需要我们大量地去学习和领会。
自由的谱系
最后是自由的谱系。一般自由有三个层次,即自在的自由,自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
1. 自在的自由首先看自在的自由,这是最起码的,就是自由自在,怡然自得,逍遥。这在人的儿童期表现得比较单纯,或者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如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游荡,虽然已经是自由的了,但当时没有觉得自由;只有在后来的怀旧中那种生活才成了自由的理想。通常,这种自由自在只有在失去时才会被人明确意识到,而在拥有的当时则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自由。只有当产生了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失去了自由,才开始意识到自由了。文明时代初期,人们开始怀念这种失去了的自在的自由,所以这种自由意识总是带有一种怀旧的伤感。
2. 自为的自由自为的自由是第二阶段,它已经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自觉的了。文明社会的建立使自由受到束缚,在国家里面不可能为所欲为。在自然状态里面,是弱肉强食。国家束缚了人的自由,但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
(1)反抗的自由。对不自由的反抗最初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倒退,一种是前进。老庄是倒退、怀旧,想回到自由自在;有的人则说“不”,反抗不自由,还有的人甚至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反抗。老庄不是说“不”,而是说“无”;不是反抗,而是逃避。禅宗则是完全退回到了内心。能够说出“不”是最直接的反抗,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已经有一种行动,而不是一味逃避。当然,真正反抗的行动就是起义、暴动,但这其实还是很初级的自由。起义的农民唯一想望的可能就是“翻身得解放”。“翻身”是什么?“翻身”就是今天你奴役我,明天我要报仇,要奴役你。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反抗精神可嘉:如果连这样一种反抗的自由都没有,那么人就完全成了拉磨的驴了。但是它的层次是不高的,它停留在幼儿的阶段,只会说“不”。它只是自由意识的萌芽,但也是一切自由意识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层次。自为的自由里面首先就是反抗的自由,这是第一个层次。
(2)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个目的,这里面有一种理性的权衡,但最终是基于任意性,即任选一个。所以选择的自由就是在理性权衡之下的任意性。在反抗的自由里面没有理性,无可选择,只是要反抗、复仇,只凭一种情绪。但是选择的自由已经有了理性的思考:不是仅仅以当前的目的物为转移,而是在各种目的物之间有选择,凭借理性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害的最小化。但这种自由中有个问题,就是可供选择的目标是预先提供的,我们只能选现实已有的可能性。所以选择是自由的,但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是自由决定的。因此这种自由虽然比反抗的自由高了一个等级,但仍然不是彻底的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和儒家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孟子也讲熊掌和鱼、义和利,由你选择(参见《孟子·万章下》),但这种选择是规定好了的:如果你选择了见利忘义,那你就是禽兽,甚至禽兽不如。所以你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你不敢沦为千夫所指的禽兽。而英国功利主义的自由观,如边沁、密尔这些人所设计的选择,它的对象虽然不是自由的,但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有很多可选择的,你既可以选这也可以选那,这是你的权利。什么是权利?权利就是你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甚至可以不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人家顶多会说你不明智,但是不会说你是禽兽,那是你的自由。
(3)立法的自由。立法的自由其实在选择的自由里面已经有了,权利本身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法,所以又翻译成“法权”。权利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他人的自由。所谓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立法,这本身就已经是法治了,但是英国人还没有把这种立法当作自由本身的原理,而只是当作实现自由的一种工具。法律被视为只是对自由的一种外部限制:你要自由,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否则自由的总量就会减少了。伯林讲“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重要,因为积极自由总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使人不能为所欲为或任意选择,成为不自由。立法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减少:一个人不能把自由都占全了,你得分一点给别人。
这样,选择的任意性就提升到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志”,任意性和意志的不同就在这里。任意性当然也可以用理性来加以选择,但还是外在的,它本身并不是理性;而意志不但是有理性的,而且它本身就是理性的体现,是有一贯性的、有法则和规律的自由。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意志的意志”,因为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这种立法自由在西方古希腊就已经有它的萌芽了,但还是潜在的,直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立法的自由才得到彰显。卢梭的社会契约是在“公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还有“众意”,但法治社会中公意是最根本的。什么叫“众意”?众意就是大部分人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就是众意,是大众的意见,但是还不是公共的意见。我们一讲民主,就想到大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不完全对。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起点,起点是公意。那么,什么叫“公意”?公意就是所有的人都承认,都同意的。但是这样的公意存在吗?我们常常觉得,哪里有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但是的确有。比如说,一个社会“要有法律”,这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至于要有什么样的法律,那当然是众意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最后是要诉之于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没有人认为可以不要法律;即使造反的人,也是向民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有公平法律的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所以公意才是立法的最终依据,也是立法的自由。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有可能陷入“多数的暴政”,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事先有公意的认可,比如说先由所有的人同意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添加了保护少数的修正,那么即使某些人在投票时处于少数,他也仍然是自由的,因为他事先认可了他处于少数的这种可能性。
而到了康德,就提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这就是道德命令,它相当于法律上的“公意”。康德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西方的自由意识上升到了“自律”而不再是“他律”。自律是更高层次上的自由,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立法的意志,每个人都为自己立法,所以康德讲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意志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立法的自由既包含了反抗的自由,也包含了选择的自由,但是最终它是一种普遍的自律原则。它是超功利的,但又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并不违反功利。在外在的层面上它容纳了所有的功利主义原则,但在内在层面上它为这些原则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反思的道德维度。
3. 自在自为的自由比自为的自由更高的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那就是所谓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理想。人类的理想就是自由王国。这个理想康德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目的国”,在这个目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目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种目的国不同于设想中的“自然状态”:那种自然状态中虽然每个人也许都是为所欲为的,但总体上看却是弱肉强食。
这种自由王国还可以借用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来说,但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矩”不是由先王和传统所传下来的了,而是由人的理性建立在自律的自由意志之上。孔子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他的“不逾矩”是回到本性,属于人的“自在”状态;而“自在自为的自由”则是以前面两种自由即自在的自由和自为的自由作为前提的,是前两者综合起来的合题,所以这个概念不是以人的本性的善、而是以“人性自由”为前提的。而当这种目的国实现之日,孔子的另一句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话也就会成为现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终有一天,国家、法律都会消亡,由道德来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就够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只是一个逻辑推论,是否能够实现尚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个理想的终极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说人总要有点理想,不能只盯着眼前: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清通达这个理想的道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理想,就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看它的自由度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尺度是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没有努力的方向了。
总而言之,做一个自由人,为此而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它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它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正像胡适所讲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批奴才能够建立得起来的。(参见胡适)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一种突破。
本文原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来源:二哈轻阅读(公众号)
编辑:马源
| 欢迎光临 传媒教育网 (http://47.106.15.148/)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1)法律—政治平等;(2)社会平等;(3)机会平等;(4)经济平等。”19然而,社会平等是个笼统概念,它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等平等的统称。萨托利自己也说:“关于社会平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更加关心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阶级和身分的问题。”20所以,具体的平等问题便可以归结为三大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相应地,平等的具体原则也就分为: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
1)法律—政治平等;(2)社会平等;(3)机会平等;(4)经济平等。”19然而,社会平等是个笼统概念,它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等平等的统称。萨托利自己也说:“关于社会平等,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更加关心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阶级和身分的问题。”20所以,具体的平等问题便可以归结为三大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相应地,平等的具体原则也就分为:政治平等原则、经济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















































































